就目前為止,秋山光和教授的【佛教石窟寺院新考】(英文版【中國美術Ⅱ】),是有關敦煌佛教繪畫式樣開展,最好的一篇考察吧! 在這篇論考中,秋山教授著力於隋代出現的敦煌美術新傾向,在唐代初期的快速進展。 即 「(一到唐代)壁畫的主題漸漸以複雜的經典繪解(經變)和淨土圖等為中心,畫面不僅大,且構成組合多元。 大唐王朝的力量,甚而強勁地企達於這個邊境的小都,其結果就是,中央在這個時期達到急速發展的繪畫式樣,一下地也出現在此地的壁畫上吧! 」接著亦雲: 「8世紀初,一到所謂的盛唐期,質與量也更加地充實,開元年間(713-741)正是迎接敦煌藝術開展的黃金時期。 」
 樹下說法圖 唐代(8世紀初) 絹本著色 139x101.7cm
樹下說法圖 唐代(8世紀初) 絹本著色 139x101.7cm
在秋山教授對敦煌壁畫有關的記述中,隋、初唐、盛唐的遺品極少,然而,透過史坦因及其他人士自敦煌藏經洞攜來的絹畫、麻布畫、紙畫等,當然就可迎刃而解了。不過,絹畫、麻布畫、紙畫等,卻是個可以搬運且帶著走的繪畫,因此要考察它的式樣發展,是會牽連種種的主客觀因素,並非容易的。理想上,若是能與敦煌壁畫確實核對的話,且又沒有超越是最好的。不過,此時之際,實不應僅僅全神貫註在僅止「構圖、表現是否相近」這樣的觀點,再者,也應對這類可以搬運攜帶的絹畫、紙畫等的繪畫,因於奉獻者各面的情事,在材質的表現,以及其目的之不同,不斷地加以考慮。
 二觀世音菩薩圖唐代(9世紀中葉左右)絹本著色 147.3x105.3cm
二觀世音菩薩圖唐代(9世紀中葉左右)絹本著色 147.3x105.3cm
大畫面的絹畫,實是超越個人奉獻的負擔,就此意義言,可發現其性格是同於壁畫的。相對的,另外的其他比較小的畫面,舉目一望,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作品,是有畫家發揮才華之處,且有高低之差的。這類作品,想必因於供養人,或者一家族支付畫家報酬的多寡,在表現上有著差別。一般言,連細部都慎重專註地描繪,最後的修飾也極度優異的作品,可知都是付予極大報酬的。若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非常遺憾地,絹畫的小品,例如8世紀的壁畫上,尊像的頭光上卻看不到非常洗鍊且又優異的花紋表現。不過,代之而起的,這類小畫面的畫作,或者與經典組合的小冊子等,可以說反而是如實地反應敦煌當時的佛教徒個人信仰的水平情形。
 佛五尊像紙版(局部)五代至北宋初期(10世紀中期左右)紙、墨畫、針孔線本著色紙版整體:
79x141cm
佛五尊像紙版(局部)五代至北宋初期(10世紀中期左右)紙、墨畫、針孔線本著色紙版整體:
79x141cm
還有,在這類小品中,有不少可窺知與大規模營造之間的關係。例如在石窟天井和壁面上,為了描繪說法圖和千佛有使用紙版圖形(圖78-2、圖79-2)的,以及開運四年(947)曹元忠造的木版畫類(序文圖1、序文圖2)等。但是,這類木版畫類,其品質並非極好,可發現是在唐至五代,由中國佛教繁盛的中心地五台山或四川帶過來的。然在雕刻上、印刷上雖翻刻的不錯,但是總覺得幼稚且笨拙。事實這樣的情形不止於木版畫,絹畫、紙畫、麻布畫、壁畫的場合亦是,比敦煌制作更為優異的作品,現在皆已佚失,然而可想像在中原的長安、洛陽及其他都市的大寺院,應是會有的。
 如意輪觀音菩薩像 唐代(9世紀後半)絹本著色 111x74.5cm
如意輪觀音菩薩像 唐代(9世紀後半)絹本著色 111x74.5cm
此套全集對繪畫作品,儘量以時代的系譜來觀照,因此不問彩色圖版或黑白圖版,皆努力著力於一幅幅作品的制作年代推定,或許亦有伸縮的餘地。事實這對敦煌美術的整體探討而言,是個絕對必要的手段。
 觀世音菩薩像唐代(9世紀初-中期左右)紙本著色30x26cm
觀世音菩薩像唐代(9世紀初-中期左右)紙本著色30x26cm
至於年代的推定,因應於各種狀況有種種的方法,不過,有紀年銘的作品,不用說,是作為基本依據的。很幸運的,這類有紀年銘作品,不止於史坦因的蒐集品,其他的蒐集品也相當的多,因此可以與之比較。再者,也有從出版物的圖版,運用與敦煌壁畫相互比較的方法。事實供養人像的衣裳和髮型等,也是有效的線索。不過,任何的作品,最終判定年代的依據,還是在於線描和渲染的原本特質上,依此可以相互的鑑別同樣的作品。不過,加以細細辨別的話,不僅要對細部的表現加以特別的註意,而且對於被認為確實是初期人物作品的類似點,還必須要有貼切功夫的知識。這個,對美術史家而言,不管是哪個領域,都有突然碰到的可能,不過,就敦煌繪畫來說,甚而地,還必須理解期間亦有技術不成熟的畫家,影響了繪畫的品質。換言之,敦煌繪畫和幢幡,大體上而言,畫家並非為個人,而是為集體的制作。有些畫作因顏料剝落可以看到打底稿的線描,這時可發現底稿的線與修飾完成的線是有相當的差異,再者,主尊的相較之於圍繞其四周的眷屬顏面表現更為優異,即在於此。因此,隨著對初期人物所留下的特徵,以及不同水準的畫家,加上會有怎樣程度的影響,就需一面地思考且一面的鑑別。再者,敦煌因於地理上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使得在這個地區的歷史事件、僧侶、商人、為政者等的移動,以及中原而來的影響,對於本世紀初期發現的,甚而現在更新發掘的,對中央各地域佛教美術有影響的資料,亦有必要加以關註。
 藥師淨土圖唐代吐蕃期(西藏支配時代)丙辰銘(836)絹本著色 152.3x177.8cm
藥師淨土圖唐代吐蕃期(西藏支配時代)丙辰銘(836)絹本著色 152.3x177.8cm
事實中原和長安宮廷而來的影響,以及印度、中亞,特別是和闐佛教中心地而來的影響、西藏而來的影響等的種種要素,都滙融到敦煌美術裡,因此非常複雜,正如在序文中記述的,其範圍僅以史坦因蒐集品中的繪畫作品為中心。然而,因於全集的出版,卻出現不少可以作為資料的新發現。再者,既使是大英博物館蒐藏的史坦因蒐集的各種作品,包含不少是此次初次公刊的,因此可以確實比定出與這些作品的關系。例如,第一卷黑白圖版第113圖的殘片,在第一卷出版後,正如柳澤孝女士指證的,弄清是屬於【藥師淨土圖】(第1卷圖16-1)右下角缺失的部份觀世音菩薩。又,第1卷圖22的【靈鷲山釋迦說法圖殘片】,正在撰寫解說時,羅貝爾·傑拉=布劄爾來訪,得以弄清伯希和蒐集品中的殘片(第一卷圖22-5)亦屬於此畫作,再者,大英博物館的小殘片(序文圖3),亦是其中的一部份等,這樣就可以好好探索原本畫面的樣子。另一方面,令人知曉在敦煌石窟第72窟仍有與此鋪畫作同樣主題的壁畫,然而相關的資料僅有羅寄梅的拍攝資料,其餘的未見,因此無法充分地對照。
 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天復10年,910)銘 絹本著色 77x48.9cm
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天復10年,910)銘 絹本著色 77x48.9cm
第2卷收錄的作品,尤以五代、宋的繪畫為主,進行詳細的比較,不過,過往以【敦煌壁畫】為首的出版物中,卻甚少介紹此時代的壁畫,因此只有期待目前正刊行中的【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5卷,以及今後出版的資料。從來,有關此時代的壁畫出版不多的原因,就在此時代的繪畫隨著敦煌被中原孤立起來,至少是吐蕃期(781-847)之前,已陷入欠缺基於唐代培養的藝術獨創性的創作精神。但是,9世紀末至10世紀,儘管與中原的接觸幾乎完全斷絕,然而在敦煌卻是繼續著大規模性的藝術活動(正如第2卷圖7-1,唐王朝瓦解後,仍有使用唐代年號的作例,可窺知當時隔絕的情形),舊石窟的修復和新石窟的開鑿,仍是一直的增加。因此這期間,對於已出版且年代明確的作例要檢討之時,最有趣的,便是唐代的式樣與影像,在這個時期,有多少程度的被忠實地繼承下來,相對地,又有多少程度被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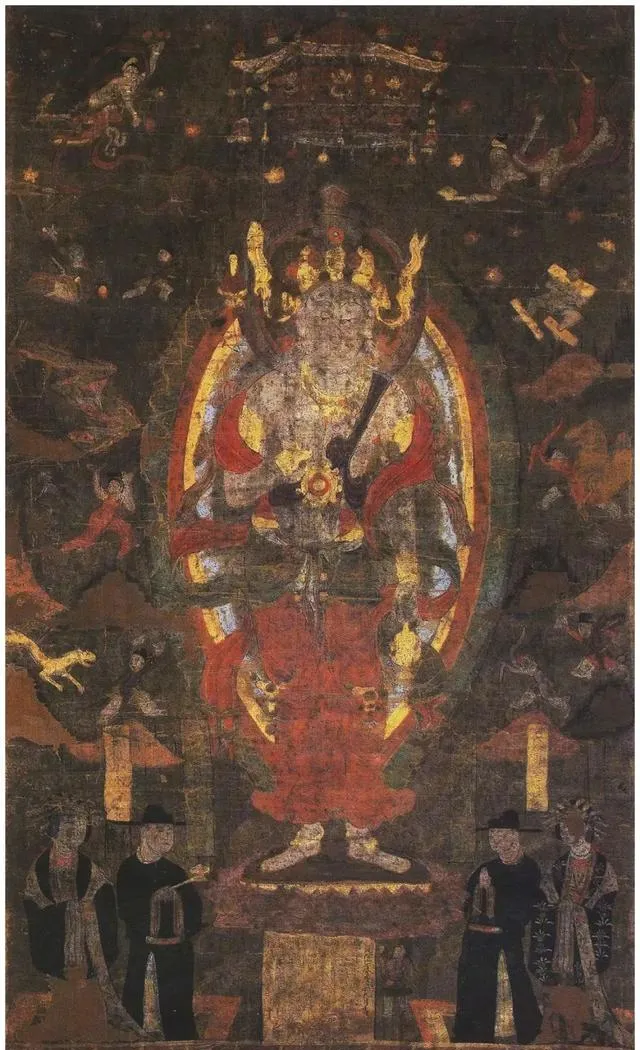 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 北宋建隆四年(963)銘 絹本著色 107x61.5cm
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 北宋建隆四年(963)銘 絹本著色 107x61.5cm
史坦因蒐集品的繪畫部份,作一環視,可知人物的先行作品是畫家所選取的,事實這類作品也留下較多,不過,一般地說,10世紀的作品,特別是作為繪畫基本的線描和彩色等的表現,已是顯著的衰退了。不過,有時卻能看到再現令人驚奇的,即初唐時期精緻線描和微妙色彩的優異作品。例如,第二卷圖25的【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即是其中一作,由經文中的紀年知,是建隆四年(963)之作。不過畫面上方的優雅飛天,足以與2世紀之前凈土圖上描繪的飛天表現相匹敵。又,第二卷圖12的【彌勒下生經變相圖】,也可舉出這類的例子,即,山水的表現很清楚是10世紀初,還有故事圖的表現,原畫是繪畫的呢?還是壁畫的呢?卻不清楚,不過卻是有這類的早期摹本,可知是以此為本而壓縮繪制的。然而,前景人物的衣裳,在技法上縱使令人顧慮,也難以辨識為9世紀的。除外,第二卷的圖13、圖14是一對普賢、文殊菩薩圖,亦是一例。事實這二尊菩薩的信仰,自吐蕃期開始,盛行於9世紀末至10世紀。因此,壁畫上早期至晚期各各作例間的式樣開展,期待有詳細的探討。
 引路菩薩圖五代(10世紀初)絹本著色 84.8x54.7cm
引路菩薩圖五代(10世紀初)絹本著色 84.8x54.7cm
正如踏尋著上述的這類各種情事,以下的各章,對彩色圖版和黑白圖版的各個名稱,正如想要作為表示年代推定的根據,可以有助於區別敦煌各時代的幾個特徵,作一記述。但是,這個,例如第一章,可發現除了壁畫之外,並未有早期的特色。事實在史坦因蒐集品中,有二鋪作品極為重要,深值關註。現在,擬對這個核心的作品,再度加以檢討。
本文節選自:【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史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序
作者羅德瑞克·韋陀,譯者林保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