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觀經過周秦及漢初的幾次實質性轉變之後,至漢武帝時成為了漢王朝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特別是董仲舒在【春秋】的公羊學詮釋中,將「奉天法古」與成為聖人緊密結合起來,使這一理想化的政治圖景有了實作的可能性,實際政治中的國君可以成為儒家理想中聖人的模樣,若非如此,則天會以災異的方式予以譴告。

在董仲舒思想中,聖人與先王等同,現世的國君亦為聖人,若背離聖人之道則會受天譴以改正之,或者另立「新王」予以取代。董仲舒把「【春秋】之道」概括為「奉天而法古」,繼而得出「聖者法天,賢者法聖」的成聖準則,從這一角度來看,【春秋】的編寫目的就是為後王提供思想行為上的借鑒,使之向聖人接近。
「奉天」與「法古」,表面上為成聖的兩條通道,其實質還是指向「奉天」,因為「法古」所效法的仍然是「先王之遺道」,而「先王之遺道」同樣源於「奉天」。

公羊學與漢初政治
漢初以黃老思想為主導,奉行休養生息政策,加上整體的文化環境較差,儒學發展緩慢,儒者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黃老思想雖有效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但外戚和諸侯勢力對中央政權的潛在威脅依然存在,匈奴對北部邊疆的侵擾並未根絕,公羊學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彰顯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力,適時地突顯出了自身的實用性,逐漸為統治者所接受。
【公羊傳】和【春秋繁露】是公羊學推進中出現的兩部重要著作,前者對【春秋】筆法的探討極為深入,是孔門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繼承,經戰國齊地學者再度闡發後,於景帝時著於竹帛;後者從理論的角度指出了孔子寓於【春秋】中的「筆法」,使公羊學達到了理論上的成熟。
此外,【公羊傳】的思想突顯出戰國稱雄時代,學者們希望以「文王之正」來實作大一統的理想政治格局,而董仲舒的理論闡發則是在統一政權已經形成的背景下進行的。

公羊學的形成
【公羊傳】著於竹帛之前以口授的方式傳播,「【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鄒】【夾】之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最為根本的原因可以視為「免時難」。

值此之故,對於【春秋公羊傳】的源流,經學史上並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緯書認為源出子夏,「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誌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何休解雲「孔子至聖,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
董仲舒以為源出孔門諸弟「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此外還提及子夏、世子、子池、曾子等人。

在這裏,緯書和董仲舒將【公羊傳】的作者指向了孔門弟子。但蔣慶否認了這一說法,「從學理上推之,【公羊傳】必為孔子所作。孔子自作【傳】以解釋【春秋】之經,【公羊傳】當是孔子自傳」,並進一步列出緣由,概而言之,一為【春秋】深奧,實非一般人所能知,二是形式上的一問一答類似於原始的課堂筆記,三是【春秋】詭其實、變其例,除孔子本人外無人可知曉。
蔣慶認定孔子作【公羊傳】的說法很難經得起推敲,若果真為孔子所作,就不會以此來命名,提及的三點緣由也多臆測之辭,正因為【春秋】深奧才有了後來的【傳】和對【春秋】義法的闡釋,而一問一答的寫作體例並非單見於【公羊傳】。

戰國時的諸子已經參與到【春秋】的解釋與傳播中,「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公羊傳】和【春秋繁露】當為最早的兩部公羊學著作,翻檢二書可知,【春秋繁露】所提及的經師不曾見於【公羊傳】,反之亦是,二書幾無重合之處。

雖然公羊學傳授譜系的記述相對清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生都著於竹帛」。
但這一說法受到了學者們的質疑,徐復觀直言其為憑空偽造,「只是出於因【公羊】、【左傳】在東漢初的互相爭勝,【公羊】家為提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來,以見其直接出於孔門的嫡系單傳」,黃開國解釋為「【公羊傳】的得名始於公羊壽與胡毋生將其著於竹帛,公羊壽與胡毋生有師生關系,胡毋生尊其師,而著名為【公羊傳】」,並進一步認為「【公羊傳】並不是公羊氏的家學相傳,而是戰國【春秋】齊學的傳本。

在戰國時的齊地,無論是【春秋】學說的口傳,還是文本的傳承,【春秋】齊學都應該有一個較為公認的版本,而這個版本數代相傳,並不斷得到修補」,這一解釋也印證了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等人對【春秋】義的闡發。
將【公羊傳】看作戰國【春秋】齊學傳本的說法,符合齊地的學術品格,也同公羊學的內在理路相一致。「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

陳麗桂認為齊地的地域環境因素決定了齊學的兩大特點,即「能深思,多智謀」和「荒誕的遐思」,這裏的「智謀」與「荒誕」可以視作是對先秦正統或原始儒學的突破。
公羊學的一大鮮明特點就是反對君主制度的絕對性、永恒性和神聖性,公羊學家在解釋「元年春王正月」。時就十分明確地把王置於天之下,將天和王進行了區分,所主張的三世學說和大同思想也是徹底否定了君主制度的永恒性。

與思孟學派的心性儒學相比較,公羊學更加關註現實政治,公羊學的核心理念和論述目的並非成己成德,而是指向政治領域的改制立法。
漢初的公羊學
劉邦在掌權初期並不認同治經儒生的存在價值,「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對劫後余生的儒家經學也是幸災樂禍,「吾遭亂世,當秦焚學,自喜,謂讀書無益」,直至叔孫通制定朝儀後,才意識到儒學的重要性。
漢初政治雖多受黃老之學的影響,尚清靜無為,但公羊學的勢力也在逐漸增強,魯地兩位儒生對叔孫通的指責和轅固生、黃生對待湯武革命的態度都體現了這一趨勢。
漢五年劉邦廢除秦朝的繁苛禮儀後出現了下不尊上的亂象,叔孫通適時提出與魯地儒生共製朝儀以顯現皇權尊貴的建議,獲得劉邦授權。

叔孫通在魯地征召的過程中遭遇了兩位儒生的批評,「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
儒生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叔孫通個人品質的懷疑和否定,認為他以阿諛奉承的方式獲取政治權力,喪失了儒者的品格;二是「起禮樂」不合時宜,依照舊傳統,禮樂的制定是在「積德百年」之後,而不是在政權草創之初、生民未養之時。

叔孫通並不以為然,認為這兩位儒生是「不知時變」的「鄙儒」,最後依然和其余諸生共同商定禮樂。顯然,這兩位儒生是以個人的德性和對尋常百姓的關懷為出發點,去看待制禮作樂這一事件的,力求「合古」。
以叔孫通為代表的其余諸生則更加傾向於制度的設定和皇權的維護,以更為積極的態度參與政治,註重「時變」,從這一角度來看,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就具有了一定的公羊學傾向,也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儒學才能夠登堂入室,逐漸獲得政權的認可。

另一個較為典型的事件是轅固生、黃生在看待湯武革命上的分歧。黃生認為「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在於「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為?」。
他否認湯、武革命的合理性,明「上下之分」,臣子的天職就是匡正、輔佐天子,若天子失德敗政,臣子也難辭其咎。轅固生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認為湯武誅伐桀紂是民心所向,不得已而為之,並非爭權奪利,完全肯定了湯武革命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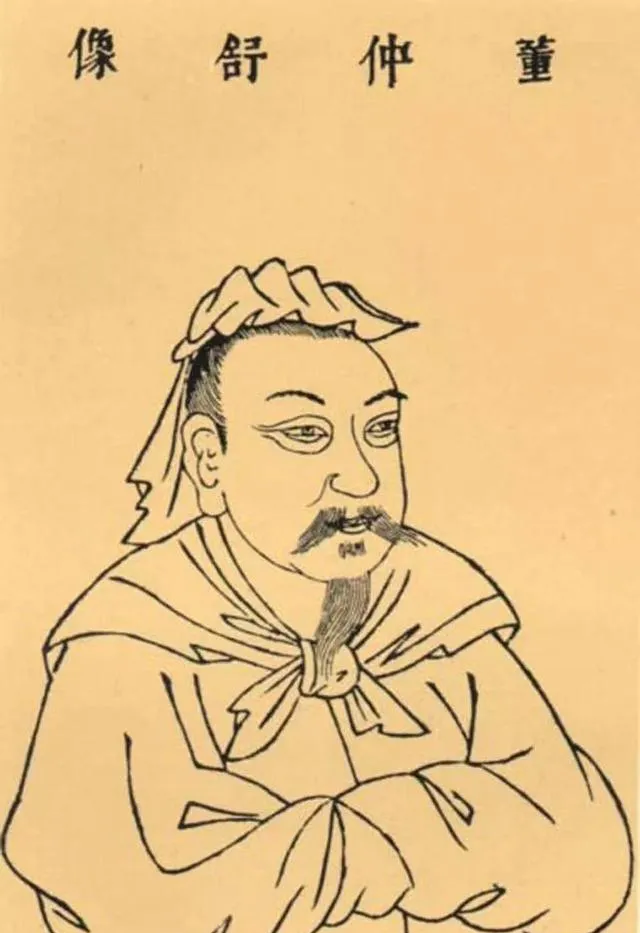
雖然黃生、轅固生都是從維護漢王朝的統治出發去評論湯武革命這一歷史事件,但黃生側重於相對保守的現存秩序維護,而轅固生則從民心所向、天命論的角度論證了西漢政權的合法性,與公羊學的思想完全一致,以最為直接的論爭方式將公羊學思想引入景帝的思考之中。
上述兩例中出現的「合古」與「求變」、維持現有秩序與建立新制度,一則偏向於傳統儒學,一則偏向於公羊學,就表面上來看,公羊學有著「背離」【春秋】主旨的意味,因為「【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提倡復古、反對變革、效法先王是【春秋】對於世事的態度。

待公羊學理論成熟後,這一看似矛盾、對立,與【春秋】主旨相「背離」的論述,就有了合理的解釋。在公羊學家眼裏,「新王必改制」並非是「改其道」、「變其理」,而是「順天誌」以「明自顯」,就是順從天的誌向來標識自己受命於天。
當然,公羊學思想在漢初的傳播並非一帆風順,也遇到過很大的阻力,喜好黃老的竇太後因轅固生視【老子】為「家人言」而「使固入圈刺豕」,反對武帝任用喜好儒學的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以及儒生趙綰、王臧,這些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都遲滯了公羊學的推進。
建元六年(前 135 年)竇太後去世後,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對策,置五經博士,就此推動了公羊學的發展,使之逐漸成為漢代的統治思想。因他的著述和思想對漢代政治產了重大影響,被司馬遷、班固贊以「唯董仲舒明於【春秋】」、「為儒者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