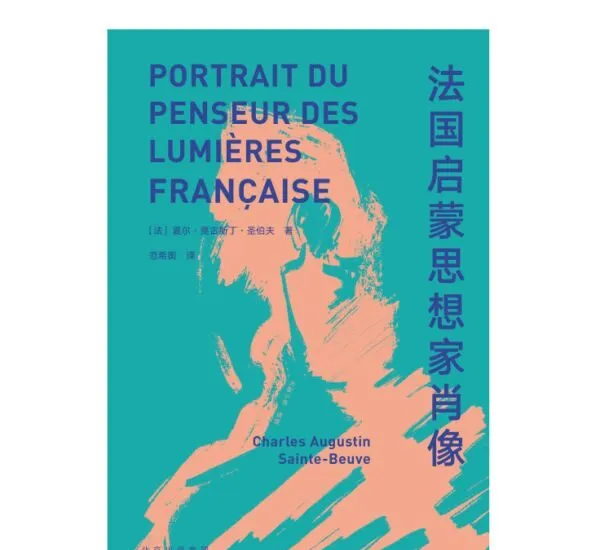
文丨夏爾·奧古斯丁·聖伯夫
伏爾泰是18世紀唯一真正的、唯一偉大的詩人。他的想象力永遠是在那裏。就整個的伏爾泰來說,他的作品常有差失,但是只要他的人在那裏,詩人也就在那裏。他是詩人,在一切自然流露中,在他的筆下一切無意的湧現中,小品文也好,諷刺詩也好,慧黠語也好,歌頭也好,生就是諺語的警句也好,不管是什麽題目,都從他的腦子裏冒出來,不脛而走地到處流傳著。他還是詩人,在談話裏,由於慧心的迸發,由於靈機的不斷閃爍,由於他說任何事物時都有那麽一種活潑嫵媚的語致。但是,他一受不到這種直接迸發的支持,一用心寫文章,他就弱了,風格就不夠了。在史詩和悲劇裏,他都只滿足於把他的時代應付過去,也就是說把那一個最缺乏詩意的時代應付過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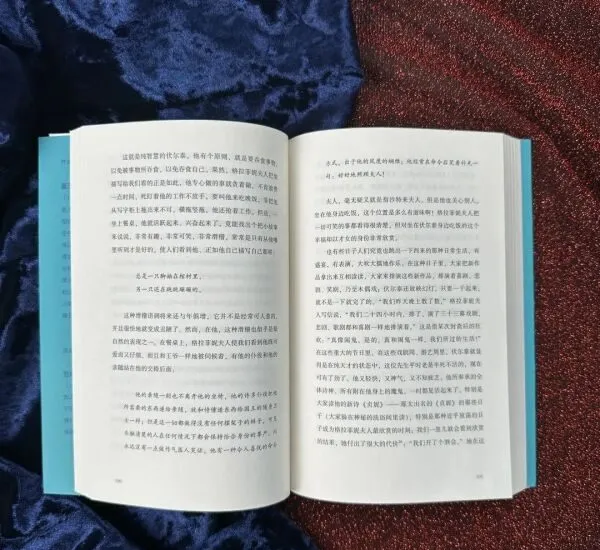
伏爾泰盡管有他的奇異的才華,卻沒有——大著膽子說罷——卻沒有適宜於賦予死者以不朽,給死者保證一個最後的、不雕的花冠的那種東西。是不是只在這種場合下他缺乏那種抒情號角的嘹亮聲響呢?毫無疑義,在他那種種不同的天賦中,這種抒情的天賦他是沒有的;他是個嫵媚可人的詩人,活潑潑的,詼諧起來無法可學,甚至也有陣發的感動力,飄忽的柔情和閃電一般,但是他既沒有形象的輝煌,又沒有格調的壯麗,也沒有班達爾所謂之「嘹亮的繆斯的純粹光明」。他在他的才調中沒有什麽可以證明那同一詩人所說的,並以其本身作為明顯例項的另一句話:「語言從深刻的智慧中抽繹出來的文辭,再遇到嫵媚之神,就能比行為更活得長久些。」嫵媚之神,他是常遇到的,他很樂意親近她們,但是那都是些家常的嫵媚之神;而班達爾所要求的另一條件,深刻,他就沒有了。他的繆斯在內心裏太放蕩了,口頭上自難有持久的神聖情感的流露。因而,特別是在這裏,既然這裏是要對一個死者致敬意,我們就明白感覺到他所還需要的是什麽,他還需要類似博敘埃熱情的東西,不說類似班達爾的熱情了。文辭的莊重、尊嚴,學理的尊嚴,那種出於信仰泉源的、口誦而心惟的靈魂不滅的思想,由說話的人擴及被頌揚的人身上,用他們的純化了的懿德把他們裹起來,像一層潔白的、不朽的屍布,這一切,他都沒有;同時,我們也該說,那位慷慨而高貴的邦主夫人所留下的印象也不適於引起這種宗教感。她的譏諷和她哥哥的譏諷太相近了;哪怕詩人再悲壯些、再莊重些,她的譏諷都夠破壞他的願望,攪翻他的意匠。佛勒德利克,請好好註意這一點,此時的做法幾乎是與他生平所持的原則自相矛盾的。他要人家為他的妹妹做的是什麽呢?他向詩人要求,向詩人索取一個苦痛的洪亮呼聲,一種公開的、持久的、顯赫的崇敬。但是,在這種莊嚴穆肅的動人時刻,他們都吃了自己的學理的虧了;他們此時卻發覺了一種無法補償的心靈枯窘。唯一的挽詞,一個真誠的伊壁鳩魯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倒該是這樣:「一切都完了,這是無可挽救的:我們自己明天也將同歸於盡。我們沈默地哭著罷。」伏爾泰倒不是個伊壁鳩魯主義者,但是題目卻引著他走向這條路,所以就寫出了一首振奮多於哀感的琴歌,費盡了平生之力;他叫道:
呵!巴蕾特啊!你,可佩的懿德與風姿!
你,無成見的奇女,無邪惡又無差錯,
死神把你奪去了,從這可悲的塵世,
從這些殺人越貨、慘象無窮的邦國,等等

但是這種趨勢支持不下去;文筆接不上來了,韻律已經不算是完備的,但是就意思來說還是太寬,作者的思想由於作意求高、求充滿這個韻律,結果疲乏了。伏爾泰暴露出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弱點,在最初發表這首琴歌時不得不以註釋形式加上、連綴上種種與本題無關的廋語,都是些對哲學的敵人以及對自己的敵人的謾罵:他在這裏特別看到一個機會,對全世界再散播一番譏刺,把它塞進這位著名的亡人的衣褶裏。在這種莊嚴的哀悼中來運用繆斯們的、運用這些神聖使者的翅膀是太不合適的呀。
【法國啟蒙思想家肖像】
夏爾·奧古斯丁·聖伯夫 範希衡譯
北京出版社
稽核丨貓娘
編輯丨闊洛 飽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