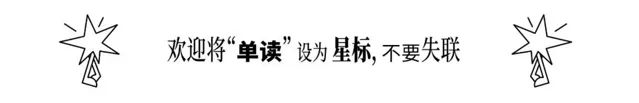

趙夢鶴擁有與父母都不同的姓氏——起名時,外公說如果孩子能夠跟著母親姓鄭,就為這個小家庭的第一套房子出一半首付。報戶口的事一拖再拖,直到母親回了鄉下,父親張光亮才帶他去了警局,說「我們姓趙」,百家姓第一。
這家人的生活看似尋常,像是任何一個生活在小城市裏的三口之家,卻擁有各自的荒誕故事——父親張光亮一直想要做預言夢,直到開始夢遊;趙夢鶴從小就更偏愛微小事物,養了一只名叫「福小姐」的寵物螞蟻,後來迷上微雕藝術,「課余時間都用來鉆研在粉筆、鉛芯與蛋殼上構築誰也看不清楚的精神世界」;母親鄭欣愛在八十歲罹患癌癥,卻適逢基因治療方面出現巨大突破,百病全消、返老還童後,在巴哈馬群島與一只豬相愛。
作為一個曾在由【收獲】雜誌主辦的「 無界·收獲 App 雙盲命題寫作大賽 」中獲得首獎的「新」作者, 林戈聲 的寫作無疑是少見的,她的文本形式多樣,結構與修辭也充滿了超現實的文學想象。在最新出版的小說集 【紛紛水火】 中,林戈聲寫下一群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因為受制於一些細小綿密,難以被察覺、更難被理解的痛苦,持續被欲望、恐懼和虛空塑造,帶著自身的隱秘病癥,活在「不過是一個巨大精神病院」的世界中。
今天單讀分享 【紛紛水火】 的首篇小說中,趙夢鶴的故事。在被確診為「巨物恐懼癥」之前,趙夢鶴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溫順的孩子,病癥的確診,讓他的許多癥狀終於有了容器,他開始擁有同伴、脫離舊生活,並在最終,找到了新的棲息地。
▼
單讀 2024 年的第一本書
【紛紛水火】簽名本現貨發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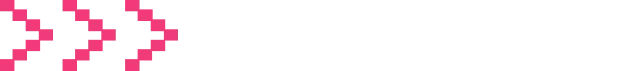
蟻鄉
——【終夜:憂傷的奶水】(節選)
撰文:林戈聲
趙夢鶴二十歲時被診斷患有巨物恐懼癥。一開始他只是表現為對微小事物的偏愛,從動漫手辦、口袋書與迷你包裝零食開始,逐漸發展蔓延,在十五歲生日前夕,他向父母提出生日願望,想要養一只螞蟻作為寵物。比起養貓養狗、養爬寵,這要求完全不過分,立刻得到滿足,趙夢鶴給螞蟻起名「福小姐」,父母未知這名字的由來,也許問過但也很快忘記,只觀察到趙夢鶴與福小姐的關系很快變得親密,便認為這是兒子熱愛大自然的一種良好品性,絲毫沒聯想到病癥上面。
趙夢鶴十六歲,張光亮接到學校班主任電話,得知兒子已經連續一周獨自坐在教室的角落聽課,但鑒於趙夢鶴平時學習中等,性葛文和,同學關系融洽,父母與老師再三溝通後,只得接受兒子「體驗人生的不同角度」這一牽強理由。從此趙夢鶴帶著他的小板凳坐在教室垃圾桶旁邊聽講,學習成績未上升也未下降,同學們盡管一開始好奇,慢慢地也習以為常,甚至把他的行為視為某種少年英雄式的叛逆,竟還得到了不少人的欣賞。
十七歲趙夢鶴視力下降,原因是他迷上微雕藝術,課余時間都用來鉆研在粉筆、鉛芯與蛋殼上構築誰也看不清楚的精神世界;他的走路姿勢也出現異常,總是低著頭,佝僂著背,有時會停駐下來,盯著一個點看上好幾分鐘。這種事情總是逐步發生,當做家長的發現這一現象,他的脊柱已經出現輕微的側彎,需要戴矯正器,好在這總還是一個溫順的孩子,除了專註於自己的小愛好,對於外界施加於他的好意並不拒絕。
十八歲趙夢鶴考上一所還算過得去的大學,由喜憂參半的父母一路送去報到。張光亮此時已經是個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身量的闊氣程度甚至比大部份同齡人還略勝一籌,他倒並不貪杯,只是愛吃饅頭、糕點一類的米面點心;夢遊程度已有所減輕,只在某些誰也不明緣由的日子裏,家人們偶爾會在客廳飯桌上發現一瓶放過夜的奶汁,家裏早就沒有嬰兒奶粉與奶瓶,因此奶瓶就以保溫瓶替代,奶粉變成面糊。
張光亮的身材讓他在高鐵二等座車廂裏受了不少窩囊罪,但好歹一切順利,最後父母與孩子在陌生城市的大學宿舍裏告別。母親絮絮叨叨許多衣食住行的細節,最要緊的是叮囑兒子要天天喝牛奶;父親透過六樓宿舍的窗戶俯瞰校園,剛想要感嘆,凸出的肚腩已先一步抵上了窗台。
軍訓結束,趙夢鶴便遇到一個追求者,女孩子大膽表白,趙夢鶴落荒而逃,一路逃進學校的樹林,藏身於一片稠密的灌木叢中。
灌木叢是微型愛好者的小小樂園,小石子、小昆蟲與枝葉間細小的簌簌聲都讓人心曠神怡,趙夢鶴在其中蜷縮手腳,想象自己只有新生嬰兒的大小,或者更小,變成魂入螞蟻國的南柯太守,剛才的女孩子只讓他記住了一個能產生頎長陰影的輪廓,與一把洪亮自信的嗓音,趙夢鶴此時無比想念福小姐。

電影【少年斯派維的奇異旅行】
大二下學期,趙夢鶴被學校勸退,至此,父母才知道他已嚴重曠課,並在宿舍與同學大打出手,原因僅僅是同學不小心踩斷了他的一根粉筆。
父母急匆匆把兒子接回家,又急匆匆把他拉扯到醫院,幾番檢查、哭鬧與爭吵,趙夢鶴終於說出自己對物體的恐懼,一切正常形體的事物在他看來都過大過密,而高大的建築或加大尺碼的任何東西(大號衣服、寬屏手機、三層牛肉漢堡)則讓他直接感到心臟疼痛,有時甚至會誘發短暫的窒息。
此病超出了現有醫學能力範圍,醫生給出的意見與對待癌癥晚期的患者一樣:想幹嘛就幹嘛,萬事不要勉強。
父母一開始萬念俱灰,認為兒子從此將成為一個廢人,沒想到休學一個月之後,趙夢鶴已能賺取小筆收入,半年後,他在網路售賣微雕作品的生意趨於穩定,月收入能與父母的收入之和持平,父母轉憂為喜,甚至加入這項買賣的外圍工作,幫助收發快遞,充當臨時客服。
趙夢鶴二十三歲,福小姐死亡,享年八歲零九個月,作為一只工蟻算得上高壽。此事無人知曉,一個月夜,趙夢鶴放下微雕工作,把福小姐放進一只玻璃小瓶,蓋上軟木塞。玻璃瓶只有成年人指甲蓋大小,是專門訂制的,平時用來盛裝昂貴的微雕藝術品,它們的材質包括但不限於翡翠、沈香、蜜蠟、珍珠。
趙夢鶴把裝有福小姐的玻璃瓶放進口袋,從床底下拖出背包,走出家門。他把福小姐埋在小區花壇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在玻璃瓶旁邊種下一粒芝麻,最後把土壤輕輕抹平。之後他起身。蹲得太久,小腿酸麻,他站了一會兒,等酸麻勁過去,便背著背包走出小區大門,再也沒有回來。他留給父母一間收拾整潔的臥室,與一張大額存款單。
趙夢鶴知道他將給父母帶來不解與悲慟,但一個投身於微渺的人無法向生存於宏大的人們解釋清楚對於世界的不同想象,哪怕物件是父母。
這之後的許多年,趙夢鶴從許多城市與鄉村穿行而過,有些地方百廢待興,有些地方已經垂垂老矣,趙夢鶴都一視同仁,不作感想,因為經過他仔細縝密的考察,這些地方都不適合一個巨物恐懼癥患者生活。

電影【壞孩子的天空】
這趟出走其實早有端倪。它萌芽於一個初秋的傍晚,那天,趙夢鶴和所有養寵物的人一樣,晚飯後例行出門。鄰居們遛貓、狗、鳥和養殖鱷魚,趙夢鶴遛福小姐。他走走停停,耐心等待福小姐探索環境,和路遇的螞蟻互相揮動觸角,就像寵物狗互相嗅聞屁股,此時人的心情最為放松,腦子裏沒有特定的念頭,耳聰目明。
晚風裏送來一些聲音。
它們是一些最為細微瑣屑的語詞,同傍晚的光線同樣曖昧,同晚風同樣疏散,它們像死去的人被時間沖洗幹凈的骨殖,懶洋洋愜意地攤在松軟的泥土裏,對意義與目的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千萬個人裏面,只有趙夢鶴一個人碰巧遇到它們,又碰巧把它們撿拾起來,湊到耳邊。
趙夢鶴不知道這些絮語來自何處,一開始他甚至不確定它們是彼此關聯的同一類聲音,但他發現,當他側耳傾聽的時候,福小姐也頓住腳步,一對纖細的觸角敏感地在空氣中微擺,幾次三番,趙夢鶴就明白這不是幻覺。當晚,趙夢鶴在床上輾轉反側,想的是他自己當時也無法說清的東西,直到天色蒙蒙亮時,他依舊沒有想清,如此迎來第二天,又度過一個月,來到下一個月、下一年。不知不覺間,趙夢鶴開始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福小姐待在一起,但絕不是出於對自然、生物、昆蟲或生命的興趣,他只是常常在腦海裏回想起福小姐觸角在微微旋擺的那個傍晚,秋風初起,晚霞溫柔,螞蟻觸角這樣過於微細的事物,世間只有他和福小姐心知肚明,這事的確毫不重要,但它發生於那一秒。
過後的幾年,趙夢鶴、趙夢鶴的家庭與整個世界,都發生了一些大事,譬如趙夢鶴高考、鄭欣愛榮升護士長、人類首次登陸火星、全球極端天氣的比例上升、一種犀牛從地球上消失、養老金政策調整,而趙夢鶴記得的有:
雞蛋殼小頭的部份厚,大頭的部份薄;
比起糖水,福小姐更愛喝牛奶,酸奶更好;
有一個網友想要購買他的微雕作品。
被診斷為巨物恐懼癥之後,趙夢鶴感到如釋重負,病癥名稱像一個容器,說不上合適,但至少容人暫居其中,再圖以後。自此,趙夢鶴關上房門,一心沈浸於微雕工作。福小姐陪伴他左右,她已步入老年,不再熱衷於在石膏巢穴裏鉆孔,大部份時間,她都趴在一個水槽旁邊一動不動。
趙夢鶴賣得最好的作品是福小姐的等身像,用黑紫色淡水珍珠雕刻出來的福小姐完全能夠以假亂真。這些用特制的高倍放大鏡才能看清的作品在網路上傳播,隨發達的物流系統來到買家手中,他們付給趙夢鶴錢,並在閑談之間透露只言片語的訊息。由此一個小小的圈子在不經意間形成了,他們以巨物恐懼癥來辨認彼此。一開始只是網路交流,漸漸地,胃口變大,這些人不再滿足於虛擬交往,而是組織線下聚會,聚會時他們席地而坐,親近地挨著地面而彼此間空出較大的間隔,他們使用白酒杯喝茶,用茶碗蒸的小盅涮火鍋,旁觀他們像一群木楞楞的癡呆患者,但實則他們表情豐富,只是他們使用微表情。

電影【如晴天,似雨天】
一次聚會上,一個剛剛旅遊歸來的同伴說起一樁見聞。她這趟旅行是不得已,是被家人硬拖出去的,地點是紐西蘭。她一路暈飛機、暈汽車、暈輪船,這些龐然的工業造物全都叫她腸胃難受。記不清哪一天了,她渾渾噩噩地被帶到一片河岸邊,坐船參觀兩岸風光,這地方是著名奇幻電影的拍攝地,為增添神話氣氛,導遊故作神秘地介紹兩岸高矗的石壁:夾岸相對的山巖如果發揮想象力,可以附會成執劍相向的巨人騎士,在故事裏,他們具有人類無法理解的生命性質,久遠的年代裏曾有旅行家時隔五十年故地重遊,發現五十年前昂首挺立的巨人之一,竟在五十年後微微彎下了腰。
假如石壁巨人生活在人類無法企及的時間尺度裏,那人類在它們看來就屬於極其微小之物。這位同伴進而想到,盡管尺度如此不同,石壁巨人卻和人類生存在同一個世界,正如人類和螞蟻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而彼此仍可以相安無事。
聚會的巨物恐懼癥患者們接連放下白酒杯,喃喃地回味著同伴的用詞,「相安無事」。
趙夢鶴接著她說道:「我一直能聽到一種聲音,像電流一樣,比電流還輕。」
「我能看見絲織品上經緯線之間的空格,」另一個人說,「有時候我不好意思上街,大家跟不穿衣服也沒什麽兩樣。」
「我不愛吃東西是因為味道在我嘴裏是分離的,酸、甜、苦、辣,一樣是一樣,所以我只愛喝白開水。」
應該有一個地方能讓巨物恐懼癥患者按自己的喜好生活。應該找到這樣一個地方。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趙夢鶴不是第一個脫離舊有的生活去找尋新棲息地的人,但截至他離開父母的那個夜晚,這樣一個地方還沒有被同伴們找到。這早在意料之中,巨物恐懼癥患者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和標準,他們大多也比較耐心,因為許多叫普通人心浮氣躁的事物或事件,在這些人看來卻是另一番光景,是許多微渺之物、細小邏輯的俏皮組合。
也許趙夢鶴最終找到了那樣一個地方,也許他的旅行還在繼續,我們作為外人無從知曉。哪怕趙夢鶴真的找到這個地方,這地方就在張光亮、鄭欣愛夫婦樓上,他們倆很可能也察覺不到,那畢竟是另一個尺度,既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之中,又遊離於我們的知覺之外。
對張光亮和鄭欣愛來說,兒子是徹底失蹤了,他們再也沒能找到他。
作為母親,有時鄭欣愛也有種古怪的感覺,她覺得趙夢鶴就生活在她身邊,甚至於就住在她樓上,吹進窗欞的晚風中捎帶著似有若無的氣息,夜深人靜,天花板傳來熟悉的腳步聲,但一切都只是感覺,感覺又轉瞬即逝。甚至在趙夢鶴剛失蹤的那段時間,有時候,剛生下兒子的記憶重回心靈,手臂跟著精準地感受到一個嬰兒的重量,十五天與二十天都有嚴格的分別,鼻子也能嗅到孩子那股溫熱微酸的奶味。
也並不能說全都是捕風捉影。
離開家以前,出於一種愛屋及烏的心理,趙夢鶴在工作台的角落與窗台各放了一點牛奶,福小姐雖然去世了,他擔心還有未收到訊息的朋友來串門。牛奶加了紅糖與蜜,盛在兩盞小小的隱形眼鏡片裏。
後來牛奶被喝掉了一些,剩下的變酸了,幹結在眼鏡片底部。最後鏡片也風幹皺縮,不知所終。
▼
有時很龐大,有時很瑣碎
【紛紛水火】簽名本現貨發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