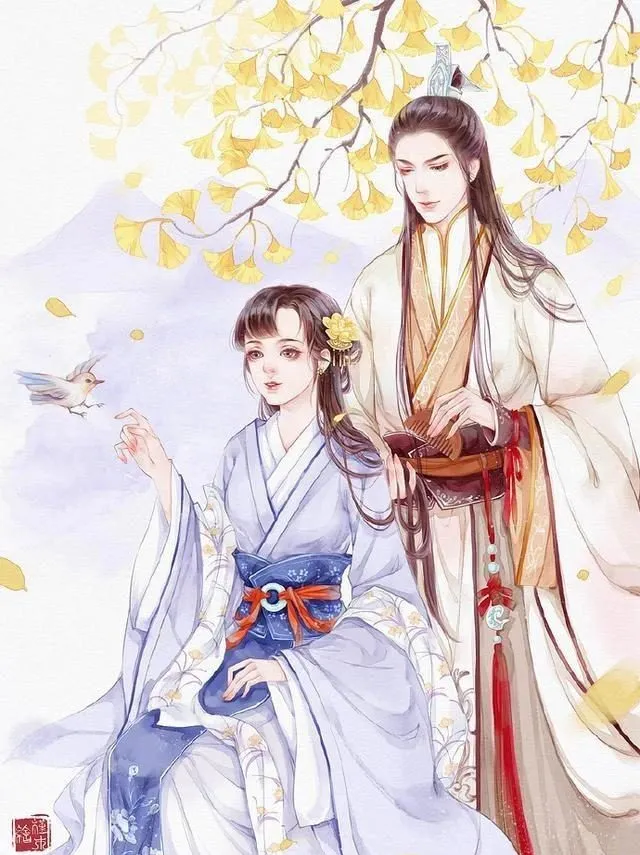易鳴鳶驟然睜眼,呼吸緊促。
她捂著鈍痛沈重的腦袋從樹邊坐起,碧波那頭一望無際的草原外是無數巍峨又雄壯的高山。
腳邊在風的吹拂下一浪接著一浪彎折,微黃的草發出沙沙的響聲,喚醒易鳴鳶的思緒。
長達三個多月的行路顛簸讓她眩暈不止,身體散架般難受,整個人幾欲昏吐作嘔,每過幾個時辰必須下車走上幾圈,不然完全吃不消。
最近情況愈發嚴重,就如同這次,只是到河邊洗把臉醒醒神,結果一陣天旋地轉,她已暈倒在離河邊約一百米的胡楊樹邊。
待易鳴鳶醒來,仰頭觀察天色之後,她稍稍定心,看樣子昏迷的時間不算太久,否則隨行的婢女或差役早就找過來了。
許是因為這三個月的時間裏易鳴鳶這個和親「公主」都表現得乖順又配合,所有人都變得對她極其放心,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嚴防死守,生怕她趁機逃走,到現在允許她可以獨自離開隊伍,去到稍遠一些的地方。
走回車隊的路上,易鳴鳶擡頭望向遠處的群山,霎時間仿佛看到了庸山關隘之外漫山遍野的火絨草。
隔著搖曳的火絨草,是疼愛她的父母兄長和原始的自由,那裏有她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易鳴鳶木然提裙邁步,可惜……一切都已成為夢中泡影。
昔日恣意張揚的少女一步一緩的走近車架,離得近了,哭泣中夾雜著抱怨的聲音愈加響亮,是一個小太監在哀鳴著此次送嫁驚險無比,不知還有沒有命回來。
這一切的緣由都是因為四月前匈奴勾結西羌組建了一支軍隊,如同破風的長箭般在短短半月內連破三城,只差二百八十裏就能探擊到大鄴的皇都廣邑。
大鄴傾盡全國之力才堪堪險勝,是以無力應付之後的戰爭。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向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匈奴竟派使臣入廣邑覲見陛下,表示願與大鄴休戰,並結成兄弟之邦。
只要大鄴承諾每年給他們提供繒絮酒面,粟米藥材,另外還討要了一位和親公主。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是何等的氣吞山河,雄鎮宇內,而今時過境遷,竟要送過去巨額的禮物和一個女人,實在是奇恥大辱!
金鑾殿上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了三天,最終還是梗著脖子應了下來,施舍般同意了。
然而難題又出現了——送哪個公主過去?
陛下子嗣艱難,皇後多年無子,只有一個當眼珠子疼的嫡公主,自然死活不肯撒手,鬧著要交還皇後金印。
淑妃也育有一個女兒,可今年還不滿四歲,實在難當和親的重任。
照理來說,接下來人選理應出自宗室之中。
偏偏此時,有人想起了大鄴那個名存實亡的郡主,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
那日易鳴鳶獨自面聖,頭頂傳來壓迫感十足的話語,那道聲音先是訴說了在朝廷爭議中力保下她性命的艱難,望她感念隆恩浩蕩,接著言明匈奴人造謀生事,霍亂百年,使大鄴尊嚴顏面盡失。
最後,稍染上些語重心長,令她為萬民排憂解難,像從前的父兄為國征戰一樣,全力效命於朝廷,並叮囑她永遠不要忘了自己身體裏流淌的是大鄴人的血。
下跪拜伏的少女別無選擇,沈默著叩首應下。
***
易鳴鳶正要提裙上馬車,忽然感覺到地下一陣顫動,就如同某一年大鄴境內地龍翻身的模樣。
所有人驟然安靜下來,有經驗的當即握緊武器,俯身趴到地上,耳朵貼上沙土聆聽附近的動靜,他神色一變,「馬蹄聲很雜亂,不好,可能是截道的!」
另一個士兵聞言卻松了口氣,擡腳踹上他的屁股,不屑的呸的一聲,「這裏是構通大鄴和草原的雲直道,安全得很,怎麽可能有小賊流寇,你瞎說什麽?」
送親隊伍走的是最寬闊易行的雲直道,每隔百裏都有守兵夾道護送,穿過邈河馬上就要進入草原的範圍,幾乎沒人敢在這個地方惹是生非。
易鳴鳶隱隱有些不安,在此地遇到踏馬而來的陌生人終歸不是什麽簡單的事,她吩咐左右提高戒備,又準備派一支輕騎向前探查。
還沒等她說完命令,東西兩邊的林子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出幾百個繩套,勒住守在裝載著金銀糧食的馬車旁的兵卒,用大力將他們在短時間內拖入林中,消失不見。
那些隨行人員在掙紮間的動作戳傷踢到了馬,馬撒開蹄子跑向各個方向,頃刻間易鳴鳶的身邊大亂,擔憂性命的從屬只顧自身逃命,來不及分給易鳴鳶半點多余的眼神。
十幾個鷹鉤鼻凹眼窩,身高八尺有余的胡人操著一口易鳴鳶聽不懂的胡語,在眾人都沒註意到的時候舉起鋼刀闖進了人群裏。
他們砍人頭比砍瓜果還要幹脆,被抓住肩膀的小太監沒能發出最後一聲哀鳴,手起刀落,就被一刀穿過了喉嚨,徹底沒了聲息。
猩紅的血液四處飛濺,在地上漸漸匯成一條血河,鮮紅充斥著易鳴鳶的雙眼,她後撤數步,從袖子中掏出前不久她偷偷藏起來的尖銳匕首,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細弱單薄的脖頸。
再等等,還沒到庸山關,還沒到,她暫時不能死。
易鳴鳶腳步急促,短暫的反應後立馬伸手拽掉頭上繁瑣的發飾和最外層阻礙行動的加厚裙衫,以最快的速度開始逃亡。
最前方的兩個胡人在人群中搜尋到了她的蹤跡,互相交流了一番後,其中左耳墜著銀耳鉤的男人點點頭,朝著易鳴鳶的方向襲來。
他一雙墨綠色的眼睛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陰森恐怖,讓人毛骨悚然,易鳴鳶只是回了一下頭,差點嚇得一個踉蹌跌倒在地。
她咬緊牙關埋頭向北邊跑去,腦後的腳步聲逐漸逼近,仿佛下一秒刀就能落下來,她不敢再回頭確認對方與自己的距離,只祈禱能夠死在離父兄的屍骨更近的地方,哪怕只近一步。
胸膛裏的空氣被擠壓殆盡,易鳴鳶感覺到自己的喉管好像在被世界上最滾燙的火焰灼燒,可即使如此,她也一刻都不能停頓。
遠遠的,她仿佛聽到了駿馬的咆哮,汗血寶馬揚蹄飛奔,前方一個黑點漸漸變大,馬的噅噅嘶鳴也愈發響亮。
易鳴鳶心生絕望,以為前方還有胡人接應,卻在下一秒聽到了夾雜著馬蹄聲的大鄴官話。
「閃開!」
易鳴鳶下意識閃身躲避,余光裏看見馬上的男人搭箭在弦,把一張畫漆牛角弓拉得如同滿月一般,輕輕松松瞄準,下一秒背後追趕自己的胡人應聲倒地。
她正欲轉身道謝,馬上的男人卻伸手將她撈起,摟著腰按到馬上,易鳴鳶驚呼一聲,身後與男人相貼的部份熱辣滾燙,不待她掙紮,男人側身用弓抽打了馬屁股,兩人在顛簸下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易鳴鳶雖會騎馬,但從沒有試過這樣快的速度,她在馬上沒有支點,又不想與那人緊緊相貼,只好俯下身抱緊馬脖子穩住身形,確保自己不會跌落下去。
汗血寶馬在林間疾馳,這匹馬像有靈性一般,自己避開了樹枝,朝著寬廣平坦的地方奔去。
現在已是秋日,易鳴鳶在馬背上不久就被吹得雙手僵直,渾身哆嗦不止,她感覺體溫在飛速流逝,吸了吸鼻子,用盡所有的勇氣大喊:「義士,能不能騎慢一點,我冷!」
男人悶聲發笑,掰著她的肩膀讓人坐直,在馬上解開自己的獸衣,「拿著穿去。」
易鳴鳶在呼嘯而過的勁風中躊躇,陌生男人的衣物她一個閨閣在室女怎麽能用呢?
她咬著下唇猶豫片刻,最終還是伸手接過,正起上半身穿好獸衣,將自己包裹於略帶粗野氣味的皮料裏。
「後面有人在追,慢不了,你抓緊點。」說著雙腿狠夾了一下馬腹,吃痛的駿馬立即加快了速度,也讓馬背上的兩個人緊緊相貼。
易鳴鳶渾身肌肉頓時緊繃起來,臉上也泛出羞怯的紅暈,男女授受不親,從前就是哥哥教她騎馬,也是站在馬旁伸手牽著韁繩,像這樣半個身體與陌生男人緊密相接還是第一次。
不過現在是在逃亡途中,即使是心裏有再多的不願與抵觸,暫時也只能這樣。
她沈下心思考自己當前的處境,聽聞草原部落中女少男多,婚配很不均衡,所以很多匈奴男人會南下搶掠,除了糧食以外,最多搶奪的就是女人。
還聽說,草原人不顧搶來的女人的意願,通常是兩三個男人共妻,更有甚者,一個女子要被迫服侍四個男人。
身前的獸皮帶著一點原始的牛羊膻味,在男人體溫的烘烤下溫暖著易鳴鳶的身軀,她動作盡可能輕地抽出匕首攥緊,如果身後這個男人是想要把她搶回去當媳婦,她立刻在這裏自戕,也不受這等屈辱。
雪亮的匕首泛著冷冷的光,倒映出她果決而悲戚的雙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