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遠親不如近鄰。可大部份時候發生矛盾就是在鄰裏之間最常見。
古訓曰:窮不失誌,富不張狂。但有的人偏偏做不到,感覺比別人強點就「天王老子老大、他老二」了,說話從來不考慮後果。
玉潤村是坐落在華北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這個村住著二十多戶人家,同是李姓的占90%,其中有幾個單門小姓據說是村上老姑奶奶寡居後,其後代在姥娘家繁衍紮根的緣故。
因為祖輩有著絲絲縷縷的血緣關系,說起來還都是親戚,所以村上倒也沒出現過所謂「欺生」的現象,但各人有各人的脾氣秉性,雖然不在一口鍋裏吃飯,可也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時候,這其中就有李貴賢和何文昌兩家。
這兩個人一文一武:李貴賢家世代為農,除了認識鈔票,那只會寫自己的名字;而何文昌是「老三屆」畢業生,後來在村中學當教師。
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偏偏是鄰居,經常一言不合就「擡杠」,誰都不服誰,被村裏人戲稱為「蜈蚣見不得雞」。
下面就聽聽李貴賢敘述他們兩家人的故事。

口述人:李貴賢 74歲 農民
其實我這輩子不願跟人結冤作仇的,除非遇到那種不講理的斤斤計較之人。
我們村雖說不大,但民風淳樸,尤其是在大集體時候,真的可以講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形容。
因為村裏人往上推兩三代,都有拐彎抹角的親,相互間稱呼最多的就是「表叔、二大爺」,所以沒有啥大的矛盾發生,即使有啥摩擦,村長三句兩句一調解,很快就和好了。
但也有另類,就是那種自命清高、好為人師的人,而我的鄰居何文昌就是。
每次我跟何文昌發生口角後,我心裏就遷怒我父親,想當初我們哥四個分家,他偏偏將我的房地基分到村最東頭,不在村中心不說,關鍵給我「配備」了何文昌這樣「烀不熟、砸不爛」的難纏之人!
何文昌比我小2歲,他本來不是我們村的人,印象中他父親沒了,在他十多歲的時候跟隨他母親投奔他幾個舅舅來的,後來就在我們村紮根了。
因為何文昌有四個舅舅,他們兄弟幾個在村裏也是「一踩地亂晃」的人,所以別看何文昌是孤兒寡母,但在村裏一點沒受到委屈,因為有幾個舅舅「罩著」呢,村裏老少幾代人都統一稱呼何母叫「老姑奶奶」。

老姑奶奶一輩子性格很剛強,她身上缺少老人該有的慈祥,估計跟她年紀輕輕就守寡有關系。
女人身後沒有男人保護的時候,都習慣把自己偽裝成「刺猬」,這些當然可以理解。
可話又說回來,剛強可以,但不能不講理。當年老姑奶奶跟我們家做鄰居時,因為家禽家畜亂跑,經常跟我妻子嗆嗆,從而發生口角戰。
有一次我家有只下蛋的老母雞經常不趴窩下蛋,我妻子跟蹤發現,原來這只老母雞每天只要從雞籠裏放出去,肯定是拍拍翅膀順著兩家的過道,就從何文昌家院門那個洞裏鉆進去了。
原來,何家有只大公雞,都是它把我家這只老母雞招擺過去的。
那天我妻子就蹲守在何家門口,看到老母雞進了院子,終於在雞窩裏逮了個「現行」。
當我妻子把老母雞從老姑奶奶家的雞窩裏拎出來時,老姑奶奶和她家兒媳婦婆媳倆追著跟我妻子吵。

俗話講:打架沒好拳,吵架沒好言。那天也怪我妻子說話不中聽,本來是自己家的雞硬是往別人家跑去下蛋,怎麽能怪別人呢。
但婦女吵架都是「一塘荷葉拉的滿塘轉」,吵著吵著就不是單純的雞丟蛋的事了,把許多陳芝麻爛谷子的事都抖摟出來,什麽哪天把牛拉到田埂上吃了一溜秧苗啦,什麽曬在墻頭上的紅薯藤少了一大半啦,等等。
我一開始是在家沒出來,可她們越吵越厲害,引的村裏人都圍過來看熱鬧,作為一家之主的我,自然要出來調解一下,可誰知道被老姑奶奶一通呲噠,她指著我的鼻子訓斥道:「人家都是‘當面教子,背下教妻’,你倒好,任由你家這個不講理的婆娘出來亂嚷,現在才出來裝好人!」
我聞聽可不樂意了,憑啥不分青紅皂白連我都兇,所以我回懟道:「你真是豬八戒倒打一耙!」
就這一句話,可捅婁子了!老姑奶奶一下子癱坐到地上,又是拍巴掌,又是詛咒,說我罵她了!但我認為我沒罵人。

可能是看我們兩家人鬧的不可開交吧,有人就跑到離村不遠的學校送信去了,不大會兒何文昌風風火火的趕回來了。
看到他母親坐在地上,何文昌趕緊上前把老太太攙扶起來,憤怒的盯著我說:「作為一個男人,欺負老人和婦女你不覺得臉紅嗎?」
但我不甘示弱,我就說是老太太不講理。
看到自己家兒子回來了,老太太又哭訴上了,說我罵她是豬。
我辯解說豬和豬八戒是有區別的,我沒有罵人。
好不容易何文昌總算聽明白過來了,他勸她母親道:「媽,這種人別跟他一般見識。老話不是講嘛,‘三代不念書,等於關一院子豬’!」
很明顯他嘲笑我沒文化,不單單把我罵了,連我我們家老少幾代人都順帶罵了!叔可忍嬸嬸不可忍,性情暴躁的我上前就給何文昌一拳,他頭一偏,正好打到他鼻子上,頓時血流如註……

那天確實是我先動手的,何文昌也是掛彩了,但我知道他少年時期就是「沙鼻子」,動不動就流鼻血,其實我下手不重,而且也就那一拳。
但老姑奶奶不依不饒,她跑到村幹部那告狀,讓他們要主持公道。
最後沒辦法,為了息事寧人,我只好跟妻子倆拎了20多個雞蛋,登門給老姑奶奶和何老師賠禮道歉,就這樣這事才算過去。
但從此兩家人頭碰爛了都不說話,正如老話說的那樣:被虎老蛇咬了,毒氣在心裏。
所以我們這鄰居各的,就像是「仇人」,誰也別想幫助誰:我們家電線斷了,明明何文昌會接線,他看到電線耷拉下來也不管;暴天下雨了,何文昌家平頂房上曬棉花,何文昌不在家,就他媳婦一個人在家爬上爬下澆的渾身濕透,我坐在屋裏也不想幫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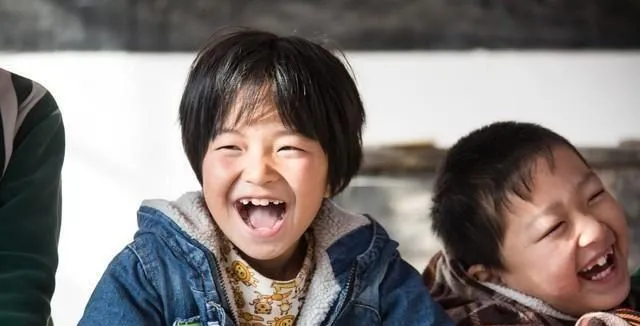
再說說我們兩家的下一代讀書的情況吧。
我家是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可能天生就不是塊上學的料吧,這幾個孩子除了上學成績不行,其他方面也是玲瓏剔透的,有時候我也是真著急,自己就吃了沒文化的虧,總希望他們有出息吧。
可這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還是有區別的,就好比挑200斤重的擔子走上坡路,雖然累,但咬咬牙也就上去了!
但讀書不行啊,書拿到跟前,它們認識你、你卻不認識它們也是沒辦法。
就這樣,我家這四個孩子沒有一個讀到初中畢業的,女兒只上到小學三年級。
可何家兩個兒子就不一樣了,每天放學回來就往屋一鉆看書,根本不像村裏那幫嘎小子們追出打鬧淘氣。
結果人家兩個不吭不哈都上了縣一中,先後都上了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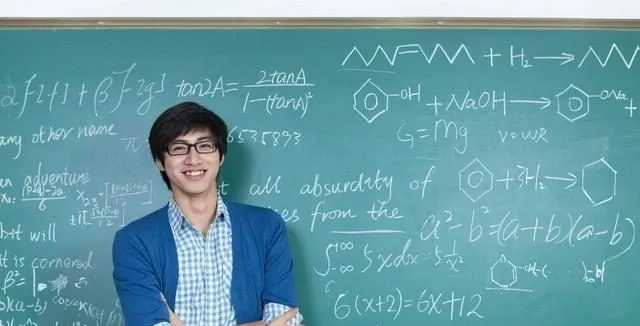
其實一個人的成功與否,關鍵就是看孩子發展的怎樣,這一點我跟何文昌比自嘆不如,但我想的開,不鉆牛角尖,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既然走讀書這條路行不通,我就早早讓三個兒子學手藝,其中兩個木匠、一個瓦匠,我們家後來蓋的樓房就是三個兒子帶著他們一幫師兄弟完成的。
我是知足常樂的心態,可何文昌卻處處拿他兒子的成就故意顯擺,尤其是人多的地方,看他每次端著水杯,搖著蒲扇,搖頭晃腦的皮笑肉不笑的樣子,我就來氣!
更可惡的是他倚仗自己每個月幾千塊錢薪資,一到農忙時倒背著雙臂在村口大道上溜達來、溜達去,看到人就故作關心的虛情假意道:「別幹了!這麽大年齡了還那麽累幹啥?兒孫自有兒孫福!」
大夥兒聽聽,這叫什麽話?農村人沒有養老金,只要有一口氣都舍不得歇著,他這純粹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每次大老遠看到他來,我寧願挑著擔子繞道走,也不跟他碰面!

老話講的好: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
何文昌妻子蘭英也是個呱呱叫的女人,當初跟「小腳婆婆」老姑奶奶也有矛盾,這婆媳倆一爭論,何文昌簡直就是:老鼠鉆風箱____兩頭受氣。
後來老姑奶奶去世後,他們家的日子總算消停不少,可那個蘭英也不是省油的燈,雖然何文昌每個月有好幾千塊錢薪資,但蘭英也舍不得歇著,自家地少,她就去開荒種些五谷雜糧,可開荒地都是公家的,有時候別人家的雞鴨進地了,她也扯著嗓門大呼小叫,惹得村裏很多人背後都埋汰她。
就是這樣有福又要強的女人,也敵不過命運的安排,在她58歲那年,大清早在地裏摘綠豆時倒在地裏,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才被路過的人發現,身體都僵硬了。
現在雖說都是火化,但也有石棺,而且也安排8個「擡重」的人,而我每次都是村裏擡重人之一。
都說生死不記仇,逝者為大,我也準備好參加「擡重」,可結果這個何文昌居然重新找人,也不找我這個鄰居!
為這事我氣的幾天心裏都不舒服,老伴就勸我道:「你真是神經!為別人家的豆子炸碎了鍋,何苦呢?不找你更好!」
就這樣,我們兩家無形之中又結下梁子。

何文昌老伴去世後,他那兩年也老實低調不少了,因為後來學校合並,家裏就剩他一個人,所以他幹脆就住學校不回來了,因此我們倆更照不上面,有時候寒暑假聽到那邊院子裏有動靜,我看都不看一眼,把他當空氣。
後來有一天我跟何文昌表弟遇到一起了,不知道因為說啥,居然把話頭引到何文昌身上,聽他表弟說,何文昌還有一個月就要辦退休手續了。
這才讓我想起來,我們居然都不知不覺的步入了花甲之年,時間過的真快啊,我跟何文昌不和也有十多年了。
何文昌退休並沒有回到老家住,估計是他兩個兒子不希望他一個人孤孤單單吧,總之,到老有七八千退休金,肯定會受兒子兒媳們歡迎的。
至於到底享不享福,只有他自己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談兒色變」,害怕兒子多了到老受罪,其實我用切身體會告訴你們:沒有那麽嚴重。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父母也就給了我三間土墻瓦頂的房子,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起步都一樣,都是從一窮二白開始,尤其是像我們這樣孩子多的家庭,更是如此。
好在咬咬牙也挺過去了,我三個兒子都沒念多少書,隨後都自謀職業,連物件都是自己搞的,我們家孫子孫女好幾個,但我和老伴早就放話出去:需要我們帶,那就別心疼,送回到老家來,我們是不存在往誰家跑著照看的,路多踩不死草,別把我們累死累活的到時候還落埋怨。
所以我三個兒子也就老二孩子放在家時間長一點,後來上幼稚園都接走了。因為也就逢年過節兒子們回來團聚一下,所以不存在婆媳矛盾。
可能是我們家風比較正的緣故吧,她們妯娌之間也相處和睦,每年回來各家都給我們老倆口幾千塊錢生活費,老伴的衣服鞋襪都是幾個兒媳包了,不誇張的說,相處的跟母女似的。
所以說,不要被社會不良風氣帶偏了,任何時候都是兩好隔一好。

轉眼又是幾年過去了,有段時間謠傳說我們村要規劃,很多家都偷摸的蓋房子,等著拆遷。
我當然也跟兒子們傳話過去了,問問怎麽打算,後來兒子們都說,沒必要把錢財往這上面投,有老房這個「老根據地」就行了!房多累主人。
我一聽他們都想的那麽開,那我就更不用操心了,好好保重身體,多享幾年福是真的。
有一天我從地裏回來,剛在水龍頭下洗洗手,就聽到隔壁院子有動靜,我猜想:是不是何文昌這家夥回來了呀?這鼻子倒挺尖,是不是回來看看、打聽拆遷訊息的呀。
雖然各這麽多年鄰居,但始終不和氣,他不搭理我,我還不想睬他呢,於是我就洗菜做飯,那幾天老伴被女兒接走了,就我一個人在家。
等我吃完午飯,準備去村裏棋牌室玩麻將。
我鎖好院門就往外走,在路過何文昌家門前,看到一個人蹲在院子廚房墻根在抽煙,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原來不是何文昌,而是他的大兒子何歡。

何歡就住在省城,好像在哪個研究所工作,以前他媽媽蘭英在的時候,他時不時的回來看看,但也不久留,最多吃頓飯就走。
而他弟弟何佳在深圳工作,我幾乎就沒咋看見過,據說何文昌一開始在小兒子那,後來不習慣那邊快節奏的生活,又回到省城大兒子那。
可如今為啥大兒子回來了,他自己沒回來呢?我有點納悶,不過也不多想,回不回來跟我沒多大關系。
我麻將結束時已經快5點了,那天手氣不錯,贏了十多塊錢,夠買兩斤豬肉了。
當我剛進家門還沒等喝口水,聽到門外有人喊我名字,回頭一看,是何文昌大表哥能興大哥,而他身後跟著何文昌兒子何歡。
我有點納悶,想著能興大哥來了也正常,怎麽何家大兒子也跟過來幹啥?就是房屋拆遷,各家是各家的,也幹涉不到其他人啊。
我一邊想,一邊笑著招呼他們,何歡緊走幾步,從口兜裏掏出香煙往我面前遞,嘴裏還喊著「表叔」。
我雖然跟他父母有點過節,但對他兒子我當然不能抱成見,何況伸手不打笑臉人呢。

不等我問話,能興大哥笑著對我說道:「貴賢啊,跟你商量個事啊,」
我趕忙說道:「大哥你有啥事盡管說。」
「唉,這不何歡回來了嘛,是為他爸的事,上禮拜文昌表弟突然腦溢血了,在醫院搶救好幾天,但還是下了病危通知書了,估計也就這一半天的事了。」
能興大哥語氣沈重的說道。
我當時一聽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文昌比我還小2歲呢,平時也沒聽說他有毛病啊,怎麽突然會不行了呢。
我接著問道:「哦,真是想不到啊,有啥事讓我幫忙就說吧。」
「貴賢表叔,我上午跟我家幾個表叔去墳地那看了,我爸生前就有遺願,說百年之後要跟我媽合葬。所以送我爸骨灰進墳地時,要經過你家那塊玉米地,可能到時候要毀壞不少莊稼。」
我一聽原來是為這個事啊,其實那塊地當初不是我家的,後來農村不是又進行了二次分地嘛,何文昌老伴蘭英墳地就在這塊地的南頭,如果到時候送葬的人多,那這片玉米不但礙事,還會被踩的東倒西歪。
我再看看何歡,只見他40多歲的男人,此時像個無助的孩子,眼巴巴的等著我表態,嘴裏不斷的說:「表叔,玉米能打多少斤,你說一聲,我補償你。」

聽何歡這麽說,我大手一揮,道:「什麽錢不錢的!我現在又不是窮的不能混!這樣吧,我明天起早就去把玉米稭砍了,你們不用操心了,回去忙你們的吧。」
何歡聽我這麽說,激動的說話都有點磕巴了,他不停的朝我作揖,嘴裏說著「謝謝表叔!謝謝表叔!太麻煩您了!」
就這樣,我晚上打電話讓老伴第二天早點回來,我們倆把一人多高的玉米稭砍了大概有5公尺寬的路,一直到蘭英的墳頭,還用三輪車把稭稈拉到路邊,不能誤老何家辦事。
幾天後何文昌的骨灰盒回來了,我自告奮勇組織了「擡重」班子,又幫著料理後事,雖然他有兩個兒子,但年輕人好多老規矩不懂,而我現在也算是村裏的老人了,能幫一把是一把吧。
其實鄰裏之間哪有什麽深仇大恨啊,就是一些雞頭鵝腳的瑣事,和那不值錢所謂的面子!
看我這次一點沒為難何家,村裏人都誇我有格局。何文昌三天「完煙」後,他的兒子們也該回去工作了,何歡哥倆臨走跟我道謝,還給了我一個用毛巾包裹的東西。
我們這白事是有回禮的,我當時也沒多想。
結果等何歡他們車開走有十多分鐘後,我的手機響了,一看是個陌生號碼,我接通後,聽到電話裏的人說道:「叔,我們走了,這次多虧您的幫忙!毛巾裏有點錢,那是我和弟弟給你家玉米的補償,謝謝了!」
我一聽忙推辭著,但那哥倆說是應該的,讓我務必收下。
如今我常常感嘆道:
人,只有今生,沒有來世,之前我們真是太想不開了,為啥不能好好相處呢?只可惜時間不會倒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