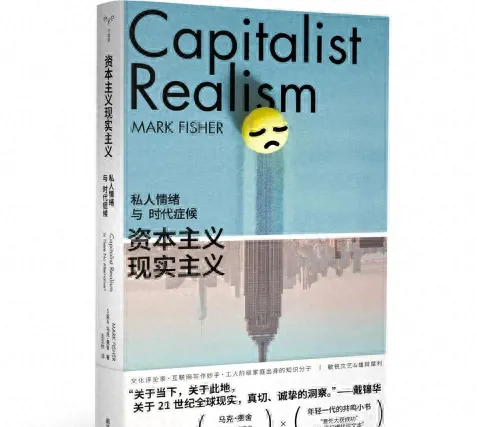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作者:馬克·費舍,譯者:王立秋,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
與當下現實「短兵相接」的教育之書
2011年,美國上映了一部名為【超脫】(Detachment)的電影,導演東尼·凱耶透過主演阿德萊恩·布羅迪扮演的代課教師亨利,展示了一幅極為陰郁的美國教育圖景。亨利難以走出童年創傷經歷導致的陰影,他心靈破碎且封閉,特意選擇代課教師這樣臨時性、流動的工作來避免與周遭世界產生情感聯系。他所代課的社群高中因問題學生反叛、風評不佳從而面臨絕境,學生們肆意挑釁和頂撞教師,陷入令人絕望的社會底層再生產而不自知;亨利的同事們以種種個人化方式去應對艱難處境,或是犬儒玩世,或是情緒崩潰,而這種極端無望的公共教育處境,反而激發了亨利沈睡的天賦,他以某種深重的悲哀風格(如閱讀課上他給學生朗誦愛倫坡的【厄舍府的倒塌】所喻示的),和學生、同事建立了情感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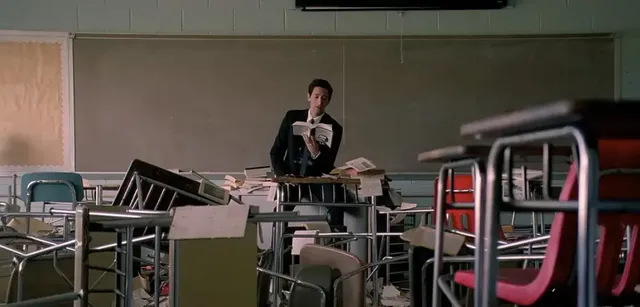
【超脫】(Detachment)劇照。
實際上,這樣一幅陰郁的教育圖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艾倫·布魯姆(Allan D. Bloom)出版的暢銷一時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早已有了思想層面的診斷和預示,只不過,布魯姆在書中對美國大學的犀利抨擊,容易被指認為持精英立場的知識分子對美國大眾文化及「政治正確」的民主文化的反戈一擊。顯然這是錯失了要點。如【超脫】中劉玉玲飾演的心理輔導老師多麗絲面對無動於衷的學生,在近乎悲憤的狀態下喊出的:無心(careless)是輕而易舉的,真正難的、需要勇氣和性格力量的,是關心。
只要在教育領域中有過哪怕短暫執教經歷的人都知道,教育工作中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放任不管、按部就班的機械式工作是最容易的事(我的一位大學同事對此有過辛辣的點評:「我假裝講課,學生們假裝聽課」);一旦秉持「天職」觀念,希望在官僚束縛的框架下有所作為,事情就變得棘手。進一步地,如果對學生有所期待和塑造,同時又試圖小心翼翼地呵護學生的獨創個性、成就自由靈魂而非專家學者,那麽,此時的教育就進入精妙的藝術範疇。考慮到現實當中的階層分化以及種種政治經濟力量對教育場域的「爭奪」,對教育的探討實在是人類社會一個重大恒久的課題。
在這個意義上來探討英國學者馬克·費舍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癥候】一書,我們可能發現,這是一部與當前現實「短兵相接」的教育之書,費舍堪稱二十一世紀初罕見的教育者。
在對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實進行診斷時,費舍表現得像一個高明的偵探,帶領讀者穿越思想的重重迷霧。費舍無疑是歐洲左翼理論滋養的當代掌旗官,西方馬克思主義自葛蘭西、薩特、艾爾都塞、福柯、德勒茲、布迪厄等人以來,已發展為星叢式的宏大思想體系,費舍並未被這一宏大體系遮蔽,他巧妙地借助影視評論、文化分析以及後現代理論(從詹明信、齊澤克、讓·鮑德裏亞到德勒茲、加塔利和拉康),以令人驚異的清晰方式,告訴我們為什麽當前的資本主義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所謂「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即通常所稱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幅「景觀巨幕」,它籠罩一切、無遠弗屆,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系統,而且就連想象其替代選擇也變得不可能——費舍參照詹明信和齊澤克的話說明了這一點: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末日更容易。

【超脫】(Detachment)劇照。
在教育領域,
尋找存在意義上的真實
這種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究竟是怎樣一個怪物?費舍至少從兩條線索上給出了說明:其一,從深度上說,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接近尼采所說的,讓一個時代陷入一種「危險的、針對自己的反諷情緒」乃至更危險的犬儒情緒,由於這種情緒的裹挾,某種超脫的旁觀主義、「世界主義的指法」取代了介入和參與,舊的資本主義信仰體系崩潰,剩下的是在廢墟審美中盲目遊蕩的「消費者-旁觀者」。費舍以精神健康為範例,討論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如何在看似高效、突飛猛進的運作過程中導致日漸嚴重的壓力和痛苦問題,精神痛苦的增長率(尤其是抑郁癥,費舍本人即長期承受抑郁癥的痛苦)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實踐密切相關。此外,對後福特主義社會中勞動力的臨時化、勞動環境的網路化分析表明,工人的對抗已經不再是階級陣營之間的搏鬥,而是內部對抗,即工人的「心理鬥爭」;欲望被資本充分動員後的工人再也找不到一個「可辨認的外部敵人」,費舍在此評論道,這種情況將左翼打了個措手不及,至今左翼未能從中恢復過來。
其二,就廣延的「裝置」層面而言,資本主義現實主義被德勒茲和加塔利描述為某種先前所有社會系統均無法擺脫的「黑暗潛能」,其所構築的實體(即資本主義系統)具有無限的可塑性,其界限並非由法令固定,而是被務實地、即興地定義,這種拆解規則並且隨時重建的做法表明,資本主義不受制於任何超越的法——費舍此處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似乎可概括為「無結構的結構」,相較於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筆下的例外狀態和「神聖人」結構分析,費舍的分析突出歷史含義,但這幅步步為營的資本主義動態演化圖景同樣陰郁得令人窒息。例如,費舍探討了深入到無意識層面的資本主義文化,這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甚至可以對具有顛覆潛能的材料加以「預納」(precorporation),也就是說,對於人們的欲望與希望進行預先設計和塑造,這其中尤其包括對「另類」和「獨立」的反叛文化的預先設計:涅槃樂隊和科特·柯本的極度倦怠和憤怒,他們的每一個舉動,甚至在發生之前就已被預料,被追蹤,被「買賣」。即便柯本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景觀的一部份,意識到一切都有劇本和套路,他也無力逃出這個系統。同樣的例子還可以從好萊塢對革命者切·格瓦拉精心地浪漫化、讓他成為時尚文化的標誌這點看出(見2004年發行的電影【摩托日記】)。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已經走到了仰賴反資本主義這個「否定的結構」來誘使人們安心消費的地步。

【摩托日記】(Diarios de motocicleta)劇照。
如此一來,我們看到費舍描繪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執行得天衣無縫,而目前可見的抵抗形式則毫無希望,那麽,反抗還有可能嗎?有效的挑戰來自何處?在「資本主義與真實」一章,費舍試圖從拉康、齊澤克的真實(the Real)與現實(reality)區分入手,來回答上述看起來幾乎不可能的問題。費舍認為,在拉康那裏,真實遭到壓抑,現實透過這種壓抑將自己構造為「自然化、無可置疑的」現實;但真實是「只能在表象現實場域的斷裂與矛盾中窺見的創傷性的空洞」,換言之,質疑看上去「別無選擇」的現實,破除其中虛假的必然性(如資本主義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系統),才有可能啟用現實之下的各種真實,這是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策略。同樣的道理,後福特主義控制社會所強調的「靈活性」「遊牧主義」和「自發性」,看上去似乎正是反抗僵化體制與集中化的「68」一代所欲求的目標,在費舍的分析下,這些恰恰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的詭譎現實,它非但不新,反而是階級權力和特權的回歸。而尤其令人驚異的是,費舍考察了新自由主義政治與國家、官僚制的密切關聯:自詡反官僚制的新自由主義管理,官僚措施竟然得到了強化。費舍采納齊澤克對拉康「大他者」概念的闡釋,以精彩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說明後福特主義官僚制當中,大他者如何以一種巧妙的、類似卡夫卡的迷宮結構的安排來虛擬變形並強化自身。
由此可見,如果說反抗還有可能,首先應該邁出的一步就是借助理論分析對現實的「爆破」,發現存在意義上的真實。費舍探討真實的領域正是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領域,即教育。費舍在英國一家延續教育學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任教長達10年,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形成的困局有親身經歷和深度觀察,而教育領域是分析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作用的「完美起點」。在費舍看來,英國學生表現出的「反身性無能」(reflexive impotence)連冷漠和犬儒都不是,而是某種聽天由命:知道自己處境糟糕,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這種情況的外在表現是,費舍接觸的許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是學習障礙,但這些問題都因私人化而排除了政治化和社會歸因的可能;這些青少年陷入某種「抑郁的快樂」狀態,費舍將其精確定義為「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由於控制社會取代了福柯所說的規訓社會,網路—手機—雜誌等資訊平台構成的娛樂矩陣把學生吸進後,導致學生在集中註意力或是專註上的無能。教師的情況可能更糟:英國教育標準局的檢查發生的變化是,以永久性的無處不在的測量取代了定期評估,甚至越來越重視學院的自我評估系統——費舍參照福柯的話說明了這些測量和評估的驚人效果:監控的位置上不必真的有人,被監控者會自動進入自我審查狀態;在教師身上就是不斷進行象征性的自我貶低,這是一種「後現代資本主義版的懺悔主義」。
教師實際上困在誘導者—招待者和規訓者—權威這兩個身份之間。如果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則來理解教育,那麽學生和家庭自然是消費者,學校和教師則是提供教育服務的招待者(費舍不無諷刺地說,考慮到資金來源,英國的學院不能開除學生);但在家庭被高速執行的資本主義壓垮後,教師越來越需要代行家長職能,扮演某種規訓者和權威的角色,甚至為學生提供情感支持。整體而言,教育早非隔絕於真實世界的象牙塔,而是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再生產的「引擎室」,種種矛盾匯集其中,無怪乎費舍稱其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文化的前沿陣地。

【超脫】(Detachment)劇照。
逃逸的力量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後福特主義下「日漸低幼化」的文化的出現,導致原有的反規訓的鬥爭都行不通了。如前文所述,依照現實和真實的劃分,破除現實的看似自然、「無可選擇」的表象後,就應該跳出積極進取與消極怠工這個二元對立並尋找新的出路,我們可以理解為,尋找「逃逸的力量」(語出福柯對勒貝羅爾繪畫的評論:從戰栗的沮喪和被忍住的悲傷傳向希望的閃爍,傳向飛躍,傳向這只狗的無盡的逃逸……)。
費舍確定這個尋找過程中,首要的一點就是對控制程式的不認同。當意識到「創造性」和「自我表達」(這恐怕是教育系統最強調的特質)在控制社會已經變成勞動的一部份時,原子化的個體突進和反抗也變得不可能了;青年尼采受叔本華的激勵,認為人應該以英雄式生存之姿拋棄塵世幸福、與極其嚴重的困難搏鬥並不求報酬,直至為真理奮不顧身地犧牲——在費舍眼裏,這種清教徒般的高貴理念無疑契合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需要,與馬克斯·韋伯曾經指出的早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別無二致。放棄政權,退入情感和多樣性的「私人空間」同樣不可取,在齊澤克看來這正好構成新自由主義統治的「完美補充」。費舍認為,唯有在出現一個新的集體政治主體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跳出這種宿命論;但是新的政治主體如何出現,以及是否需要建立全新的政治組織,費舍認為這仍然有待回答。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費舍所指出的方向:懸置現有的結構,在恢復公共性(例如讓教育回到公共服務的軌域,擺脫商業本體論)的前提下,策略性從管理主義配置的勞動形式、監督機制中撤回,以及將普遍的心理健康問題從醫學話語中抽離出來,將其轉化為有效的對抗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費舍以某種審慎樂觀的方式引導讀者尋找新的有效反抗形式,這些引導如歷史幽暗處的微光閃爍不定,但引發的思想共鳴和連鎖反應將是深不可測的。在書的末尾,費舍以情感激揚的文字指出,鑒於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壓迫無處不在,哪怕是替代性的政治經濟可能性(也包括思想的可能性)的微光,也會產生巨大影響;恰恰是什麽都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讓「一切又變得可能」。這就是說,必須把歷史終結的漫漫長夜當作一個「巨大的機會」來把握——我們會想起,韋伯在【以學術為業】的演講末尾,也曾經參照【舊約·以賽亞書】的一段話來表達「黑夜」的隱喻:
「守望的人啊,黑夜還要多久才會過去呢?」守夜人回答說:「黎明就要來了,可黑夜還沒過去。如果你還要問,那就回頭再來。」
很明顯,教育者韋伯在告訴年輕人,不要期待先知和救世主,真實就在於每一個人面對黑夜的思考和行動(而非徒然等待)。費舍與韋伯在激發行動的氣質和精神主旨方面完全一致,只不過,費舍的文字更加激進,這或許是相比資本主義,這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一巨大、全新的事物已經在理論上被錨定和顯影。尼采-韋伯式的英雄生存或許在今日仍然閃耀著激動人心的色彩,但在現實幾乎轉為「無物之陣」、反抗已經預先被設定的當下,費舍開啟的尋找「逃逸的力量」並與生成纏鬥的路徑,讓身處黑夜的人們重拾信心、看到更多可能。
撰文/張美川(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