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探討的核心,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如何從自身出發,如其本然地、不被歪曲地顯現或綻現出來。分析海德格爾「在世存在」思想的結構內涵及其蘊含的生態審美意蘊,是理解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的重要一維。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此在被海德格爾置於存在論上的「優先地位」,以至於人們對隱含在其中的「人類中心論」立場頗多微詞。而在海德格爾看來,「一個‘人類中心論的立場’恰恰唯一地竭盡全力去指明:處於‘中心’的此在之本質是綻出的,亦即‘離心的’(exzentrisch)」[1](P189)。所謂「此在之本質是綻出的」,意思是說作為此在的存在方式的生存是「綻出之生存」(Ek-sistenz)[1](P380)。綻出之生存意味著「站出來」、「出離自身」,而到存在之真理(存在之澄明)中站立。此在之綻出又是先行在「此」的綻出,這個「此」即世界。也就是說,此在作為綻出之生存是從世界(此)中來,到世界(此)中去的生存。在這裏,可以看出海德格爾是以某種頗具危險性地站入「中心」(作為「中心」的此在)的姿態來反「中心」(作為「中心」的主體),由此展開了他的生存論分析,即此在 「在世存在」、「向死存在」及「四方遊戲」的基本結構分析。

【存在與時間】——[德]海德格爾
一、「在世存在」:此在的整體性生存論結構
「在世存在」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英譯Being-in-the-World)的簡稱,是海德格爾用連字元將四個德文單詞連線起來一個具有整體性的概念,對這一概念的闡釋和論證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最具啟發性之處,也是海德格爾此在分析的核心問題。在海德格爾看來,「‘在世界之中存在’源始地、始終地是一整體結構。」[2](P209)這個「在世」的概念整體「總是已經」先行設立,是此在的先天機制。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此在的存在就是一種「先行於自身的已經在(世)的存在就是寓於(世內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2](P222)理解海德格爾「在世存在」的整體性生存論結構,須從以下三個構成環節來把握,盡管這三個環節原本不具有可分性:1、何謂在世界之中的「世界」?2、「誰」在世界之中?3、「在之中」本身意味著什麽?對於環節2的問題,我們已經知曉這個「誰」正是此在本身,因為此在「向來已經」是在世的,此在之綻出是一種先行在世的綻出。此在之所以是一種「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因為只要它作為此在而存在,它的本質機制就包含於「在世界之中存在」中。由環節2勾連出的環節1和環節3,由於「在之中」又只能站出並同時站到「世界」中去,所以環節3又與環節1相連線,從而構成一個彼此相連的整一性概念。我們不妨先澄清環節1中的「世界」概念,進而透過環節2將環節3的「在之中」的意味揭示出來。
對於「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世界」,我們顯然不能將之理解為一個外在於人的物理空間。實際上,它被作為「現象」描述出來的意義結構。「根本上是現象學的世界概念構成了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的橋梁。」[3](P97)現象學的現象描述方式是顯現的,且「世界」概念與世界之內的存在者(包括物、自然物和各類價值物等)根本不相關聯。也就是說,盡管存在者就在世界之內,卻不能把「世界」看作是存在者之規定。對世界之內的存在者,無論是從存在者層次上加以描述,還是從存在論上加以闡釋,都無法觸及到世界現象的邊際。「世界」在這裏並不指一個作為各種存在者之和的共同世界,不是指此在被拋入其中並在其中與世記憶體在者打交道的日常世界,也不指加上了我們對現成之物總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的主觀世界,而是指一般「世界之為世界」。「世界之為世界」是一個存在論概念,它構成一個生存論的環節,因為「在世」是此在的生存論規定,而「世界」是此在本身的一種性質。在海德格爾看來,笛卡爾哲學由於將「世界」解釋為「廣延物」(resextensa)而走到了世界存在論的極端。笛卡爾的「廣延物」是空間性的,未回到更本源的世界之為世界的「世界性」,遂成為二元論思想的開端。
惟有回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間,而在「在世界之中存在」這一規定中,「‘世界’根本就不意味著一個存在者,也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存在者領域,而是意味著存在之敞開狀態。」[1](P412)我們已經指出,作為此在的存在方式的生存是「綻出之生存」。人(此在)站出到存在之敞開狀態之中,存在本身就作為這種敞開狀態而存在。「‘世界’乃是存在之澄明,人從其被拋的本質而來置身於這種澄明中。」[1](P412)當然,作為存在之澄明的「世界」也不是單純一成不變的沈寂狀態,也就是說,它絕不是擺在我們面前可供我們打量的物件。相反,「世界」是活生生的、動態化,它像七彩的光束一樣不斷變化、重組、分散、聚集,又時時刻刻照耀著世記憶體在者,使其得以顯現並獲得意義。
以上透過對環節1中「世界」概念的闡述,我們同時也已經明確了環節2的那個「誰」,即作為此在的人在世界之中,並參與了世界意義整體的建構。接下來該對環節3,即這個「在之中」進行一番闡釋了。對於這個「在之中」(In-sein),海德格爾運用現象學與生存論的方法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在他看來,這個「在之中」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一個現成物在另一個現成物之中,這仍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論方法。就其源始意義而論,「之中」(In)根本不是指一個現成物在另一個現成物中的空間包含關系,而是包含著「居住」(innan-)、「逗留」(habitare)等含義。而「存在」(sein)的第一格「bin」(我是)又聯系於「bei」(寓於),因此「我是」或「我在」就是指:「我居住於世界,我把世界作為如此這般之所依寓之、逗留之」。而「存在」(sein)就意味著:「居而寓於……」,「同……相熟悉」。[2](P63-64)因此,作為一個生存論範疇的「在之中」(In-sein)意思就是「同……相親熟」(Vertrautseins-mit)。在此意義上的「在之中」就反撥了形而上學的主體—客體相分離的認識方法,因為此在與世界是源始統一的、親密無間的一體,此在源初地就同世界相「親熟」,「居而寓於」世界,「依寓於」世界而存在。這實際上挑明了人與自然環境親密無間、融為一體的源始生態關系。
由此可見,此在生存作為一個整體現象,是由三層結構構成的:一是「先行存在」,即此在先行於自身而存在的「生存」(即「籌劃」,意指此在作為一種「可能之在」總是不斷超越自身);二是「已然在世」,即此在「總是已經」在世界之中的「真實性」(也即「被拋性」,作為此在必然性的先天機制);三是「共存於世」,即此在與其他存在者(包括他人)共同「在世」,或者說此在「寓於世記憶體在者與他人共在」的「沈淪」狀態(現實性,日常此在的存在方式)。這三層結構構成了作為整體性的海德格爾「在世存在」的基本結構。換言之,存在者先天地就處在與天地萬物的原始關聯和往返交流中,這種與天地萬物先天的、本源的、相融相契的共存關系,不以任何意誌為轉移,也不依賴任何認識而存在。這實際上揭示出,人並不是把世界作為認識物件來認識、把握、籌劃、算計,而是把「在世存在」作為此在的一種原初的生存方式。不論是「先行存在」,還是「已然在世」,抑或「共存於世」,都在揭示這一點:「在世存在」並非時序上的先後關系,不是說人首先存在,此外再與世界發生另外一層的關系;也非空間上的包含關系,不是如同在一間大屋子裏似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又非時空上的跳脫關系,即不是說人有時處在世界之中,有時又能夠脫離於萬物、獨立於世界之外;而是人先天地、原本地就已經生存於世界之中了,並且這種在世存在的敞開狀態無所不在,它是人的本性,是人生存於世的本然處身狀態。
二、「向死存在」:此在「在世存在」的邊緣境域
基於此在「在世存在」的基本結構分析,海德格爾同時還引入了時間性的思考維度,透過在時間性維度下對此在進行分析,以達到從時間來理解存在的目的。這也就是【存在與時間】中從此在存在的意義(時間性)到一般存在的意義(時間)的前期基礎存在論思路。從時間性的維度上來看,此在存在於世的終結,就是死亡。正是由於與死亡有某種關系,確切地說,正是此在先行進入死亡的「向死存在」,它才能贏獲其「操心」的「整全」,如此這般的此在的生存也才能成為一個整體現象。
對此在在世的現象分析已經揭示出,此在生存是一個在世存在的整體現象。這一整體結構又可統而稱之為「操心」(Sorge,或譯作「憂心」、「煩」等)的整體結構。問題是,此在又如何具有「操心」的整體結構呢?也就是說,「操心」如何才能獲得並成為它的「整全」(Ganzheit)呢?這便涉及到了「向死存在」(Sein zum Tode,英譯Being toward Death)的問題。從時間性的維度上來看,此在存在於世的終結,就是死亡。正是由於與死亡有某種關系,確切地說,正是此在先行進入死亡而存在,它才能獲得其「操心」的「整全」,如此這般的此在也才能成為一個整體。這樣以來,死亡現象作為此在的終結,並不是簡單的停止生活,生命最後時刻的到來,或與生存無關的淪陷或結束——而總是別的某種東西,確切地說,它不是某種東西(不是「什麽」,即不是某個物件),甚至也不是死去的過程,而是朝向死亡而存在。「對於此在,死亡並不是達到它存在的終點,而是在它存在的任何時刻接近終結。死亡不是一個時刻,而是一種存在方式,此在一旦存在,便肩負這一方式……」。[4](P45)因此,死亡之於此在,並不意味著此在到了盡頭,到了它存在的終點,而是意味著這一在者處於為終結而存在的方式中。
死亡是此在的一種存在方式,並且,死亡是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中,此在必須親自把它擔負下來,它是不可讓與且無法替代的。任何人無法替我去死(它是我不可剝奪的財產),也沒有人能從他人那裏取走他的死。在死亡中,顯示出此在存在的「向來我內容」,即唯有自我會死去,且唯一會死去的是自我的這一「必死性」。「生就是死,而死亦是一種生。」對荷爾德林【希臘】詩中的這個詩句,海德格爾闡釋道,「由於死的到來,死便消失了。終有一死的人去赴那生中之死。在死中,終有一死的人成為不死的。」[5](P203)透過這一令人頗為費解的闡釋,我們可以捕捉到一種死的差異性:一種死與生相對,是生的終止、結束,而與此同時,另一種死則在這前一種死中剛剛起步——它是不死的。這一過程既不可能,又制造著可能性。「死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是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2](P297)在此意義上,死亡作為一種可能性就具有了其完整的概念:它是最本己又無所關聯的、確定又最不確定的、不可超越且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如此一來,作為此在之終結的死亡就是一種永遠開放的可能性。在這種開放性的可能性中,此在所具有的「操心」才以「向死存在」的方式獲得了整全。然而,在日常的「向死存在」狀態下,此在作為沈淪的存在卻在死前不斷逃逸著死亡。「此在只要生存著,它就確實是在走向死,但卻是以逃逸、衰退的方式走向死的。人們置身於萬物之中,並且從日常生活的萬物出發來解釋自身,以逃避死亡。」[4](P49-50)日常沈淪著的此在在死之前對死亡的逃逸和閃避被海德格爾稱之為一種「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實際上,此在經常把自己保持在一種非本真狀態的向死存在中,以盡可能減少死亡之可能性的顯示。但這種非本真狀態是以本真狀態為基礎的。海德格爾正是從日常存在出發,圍繞著「非本真」與「本真」的關系把分析推向對「畏」、「良知」、「決心」等此在的在世狀態,以探求此在如何向死亡存在而獲得其「整全」的方式。
「畏」(Angst)是此在的一種根本性的情緒。與「怕」(Furcht)根本不同,「畏」不針對任何具體物件,而是面向作為絕對超越者的存在(即「無」)。畏揭示著無。而這個「無」「既不是一個物件,也根本不是一個存在者。……無乃是一種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為這樣一個存在者得以為人的此在敞開出來。」[1](P133)此在正是基於「畏」而被嵌入「無」的狀態而完成自身的超越。在這種不甘沈淪的自身超越中,此在被一種「良知」(Gewissen)的呼聲所召喚而回到最本己的存在。此時,「決心」(Entschlossenheit)就作為此在的一種本真在世狀態,以大無畏的精神應和著「良知」的呼聲,「先行進入死亡」而去贏獲其「整全」。
經過對此在「向死存在」的一番分析,我們從中不難看出作為此在的一種生存現象的「死亡」,以及此在在面對這種死亡時的態度所具有的意義。「海氏強調個體的有限生存應當責無旁貸地擔當起自己的存在,並且無畏地直面自身的有限,這是有其積極意義的。」[6](P39)這一積極意義在於,一方面它使有限性的此在「責無旁貸地擔當起自己的存在」,以一種「向死而生」的邊緣境域提升生命的品質,從而超越非本真的生存狀態而進入本真的在世生存狀態,在不斷自我完善中獲得此在自身的「整全」。另一方面,這一意義還在於,此在只有擔負起對他人、對周圍存在者的責任,終結所意味著的死亡才是最本真的死亡。換言之,他人之死對我來說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我正是對他人之死負有責任,以至於我也投入到死亡之中。」[4](P44)由此引申開來,我對我生存於其中的生態自然環境也是如此。一種對自然之神秘所應有的「畏」的心態,一種發自心底的「良知」的呼聲和責任意識,一種先行進入死亡、從死亡出發而生存的「決心」,不正是一種生態意識和生態思維方式的體現嗎?確切地說,這種思維方式即一種整全性的思維方式,探求此在如何向死亡存在而獲得其「整全」的過程,也就是這一思維方式的生態意蘊所展現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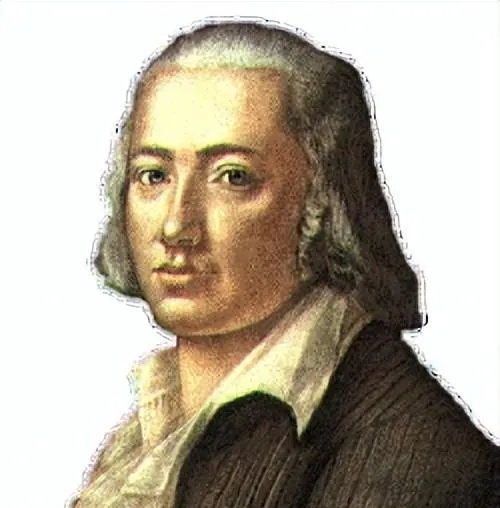
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
三、「四方遊戲」:動態建構的「世界」意義整體
對於「世界」的整體意義,海德格爾在後期所作的【藝術作品的本源】中進一步闡明:「世界世界化,它比我們自認為十分親近的可把握和可覺知的東西更具存在特性。」[7](P26) 「世界世界化」(Welt weltet)是海德格爾的一個獨特表述,其意在挑明「世界」作為一個意義整體的動態建構性。海氏後期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遊戲的著名隱喻,即是對這一「世界」意義整體的啟示。
在1950年6月所做的【物】這篇演講中,海德格爾最早從關於物及物化的討論中引出了天地人神四方世界遊戲說。在海德格爾看來,傳統形而上學與現代科學將物設立為物件的表象思維方式是對物的掠奪,在這種思維方式統治之下,物之物性不但未得彰顯,反而被遮蔽和遺忘了。那麽,何為「物之物性」呢?早在1930年代的【藝術作品的本源】這篇演講中,海德格爾對藝術作品的物性因素做了探討。在那裏,他著重批判了三種傳統與流俗的物觀念,企圖透過物之物因素經由器具之器具因素的中介而通達作品之作品因素。但這一道路顯然受阻,因為從物到作品並不能揭示藝術作品的本源與藝術的本質。而到了50年代,海德格爾從存在之運作方式,即Logos(聚集)的意義上重新思考了物。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從30年代對傳統‘物’觀念的批判到50年代對作為聚集方式的‘物化’所作的詩意運思,這之間有一個思想的演進、深化的過程。」[6](P232)
在【物】這篇文章中,海德格爾以我們常見之物「壺」為例,指出 「壺的本質乃是那種使純一的四重整體入於一種逗留的有所饋贈的純粹聚集。壺成其本質為一物。壺乃是作為一物的壺。但物如何成其本質呢?物物化。物化聚集。」在「物化」之際,天空、大地、諸神與作為終有一死者的人這四方從它們自身而來統一到四重整體的純一性之中。這四方中的每一方都與其它各方相互遊戲。「天、地、神、人之純一性的居有著的對映遊戲,我們稱之為世界(Welt)。」[8](P188)世界的對映遊戲又被海德格爾形象地稱之為「居有之圓舞」(der Reigen der Ereignens)[8](P189)。這個世界遊戲中的「世界」與前期此在「在世」、人可與世界劃一的「世界」有所不同,在這個「世界遊戲」中,天、地、神、人四方聚集為一體。
在這一四方整體結構中,大地(die Erde)承擔一切,承受築造,使我們人類得以居住;同時,它滋養著果實和花朵,蘊藏著水流和巖石,庇護著植物和動物。但大地並不是孤立的大地,當我們說到大地時,我們已經思及了作為整體的其他三方,即它是天空下的大地,服從諸神的命令,並且由人在其上來築造和圍護。天空(der Himmel)是太陽之蒼穹,也是望朔月行之處。人在大地上居住,他擡頭仰望時看到的正是天空。天空是神的居所,這一「擡頭」就包含了對諸神的期待、對超越的向往。諸神(die Gottlichen)即暗示著的神性使者。從對神性隱而不顯的支配作用中,神顯現而成其本質。正是神性之維使處於大地之上的人擡頭仰望天空,進而張開了天空與大地之間的無限生存空間。「神乃人之尺度,人之為人必與神同在,必以神性尺度度量自身與萬物,並由此獲得生存的根基,真正與天地萬物同在,屬於天地人神的世界家園。」[9]人以此神性尺度度量自身與萬物,才能獲得生存的根基並真正與天地萬物同在。而人類作為「世界」各方中的一方,被稱作終有一死者或有死者(die Sterblichen),這是因為與一般只是消亡的動物相比,人能夠赴死。「赴死(Sterben)意味著:有能力作為死亡的死亡。」[8](P187)也就是說,人作為有死者並不意味著人被死亡所侵襲,而是人有能力赴死,人的存在就是承擔起自己的死亡,惟有承擔起自己的死亡,人才作為人而存在。人的居住、人的生存就是「向死而在」,在向死而在、向死而生中人築造著自己的一生。所以只要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諸神面前持留,人就「不斷地赴死」。由此也可見,作為有死者的人是不能離開也離不開天、地與諸神的,這四者源初地成為一體而彼此不可分離。
由此可見,海德格爾的「世界」概念有一個前後變化發展的過程:在早期的【存在與時間】中,「世界」指的是人存在於其中的那個世界,即人的生存世界;後來他把這個概念加以豐富並納入了歷史維度,將民族發展的歷史在內的生存世界包括其中;而到了後期,海氏更是把這個生存世界的結構概括為「天、地、神、人」的四重整體世界。世界(Welt)又透過世界化而成其本質,但世界之世界化又是無法透過某個他者來說明或論證的,因為這種說明和論證還停留在形而上學的表象思維方式上,而「當人們把統一的四方僅僅表象為個別的現實之物,即可以相互論證和說明的現實之物,這時候,統一的四方在它們的本質中早就被扼殺了。」[8](P188)這四方相互依偎、達乎一體,構成一個柔和的「圓舞」式的世界遊戲。這一世界遊戲以及遊戲中的各方又是由語言所聚集和指示的。「但是,四元卻是一語言的世界,如果它是被語言所指示的話」。[10](P245)正是語言使人作為天地人神這四方中的一方而居住成為可能。這裏的語言指的是在源初意義上的自然語言。在自然語言中,自然而然的物「物化」,自然而然的世界「世界化」,如此這般的情景才構成了渾然一體的和諧的「世界遊戲」,人也才能在其中(大地之上、天空之下、諸神面前)找到詩意棲居的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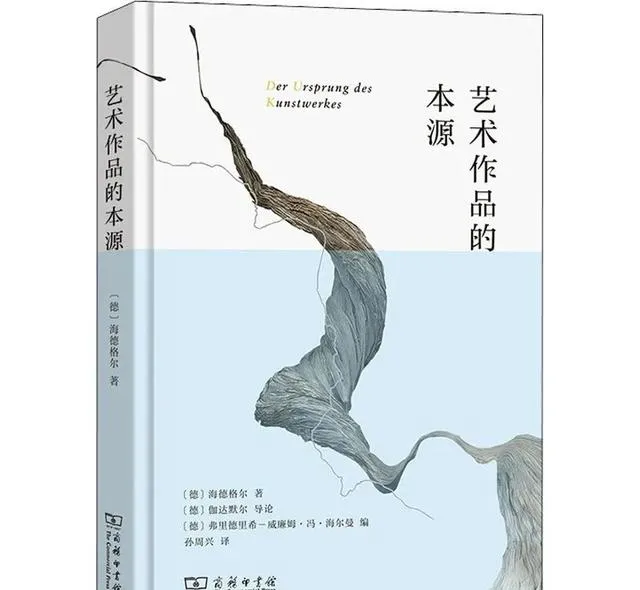
【藝術作品的本源】——[德]海德格爾
四、「在世存在」思想的生態審美意蘊
自蘇格拉底確立了理性的至高無上地位之後,西方傳統哲學與詩學便出現了理性與感性的爭執、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感性在主流哲學與詩學中往往被貶抑,而理性則受到高度尊崇。與此路向不同的是,海德格爾以其對存在問題的獨特追思,以其中貫穿的解釋學的現象學方法的運用力圖實作對主客分離的超越,從而超越主體中心論和邏格斯中心主義。
在前期的【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關於此在的生存論分析,雖然賦予此在在領悟存在上所具有的十分觸目的「優先地位」,但正如他所聲稱的那樣,「關於存在之為存在的問題處於主體—客體關系之外」[11](P826),是一種「離棄了主體性的思想」,並且「一切人類學和作為主體的人的主體性都被遺棄了——【存在與時間】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1](P400)。作為海德格爾思想中的最具啟發性之處,「在世存在」模式強調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原生地依賴於將世界整個囊括其中的意蘊的指引關聯。而對「在世存在」與 「向死存在」整體結構與具體環節分析,則旨在消弭此在在世界中的主體的優先性,並以「在之中」思維(整體性思維)和整全性思維,實作從實體性的認識論思維模式向關系性的存在論思維方式的轉變,這其中已然包含了與形而上學認識論不同的生態思維方式。首先,「世界」不是作為現成物的存在者,不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可供我們打量的物件,而是一種具有動態建構性的意義整體。這便是一種非物件性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其次,「此在」在世界之中,此在「向來已經」是在世的,此在之綻出是一種先行在世的綻出,這一點也已經打破了主體形而上學主客分離、人與自然對立的知識論世界圖式。再次,作為此在的一種存在機制的「在之中」,進一步挑明了此在不是與物質實體(客體)相對立的思維實體(主體),而是與「世界」打成一片、與世界相「親熟」、渾然一體地「依寓於」世界的此在,這實則是一種整體性的關系性思維方法,是從實體性的認識論思維模式向關系性的存在論思維方式的重大轉變。
而到了後期,海德格爾將作為此在的人納入到「天、地、神、人」四重整體(das Geviert)結構中,大地、天空、諸神和終有一死的人這四方從自身而來,出於統一的四重整體的純一性而共屬一體。人並不居於具有決定其它主體的中心地位,人只是四重整體中的一重,四方遊戲中的一方。並且,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人是自然的看護者:人不僅生活於自然之中,而且具有守護天、地、人、神四方的職責。這裏的守護或看護並非主宰或主導,而是一種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的相對平等關系。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諸神和護送終有一死者的過程中,人的棲居發生為對天、地、人、神四重整體的四重保護。這一思想進一步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使得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關系獲得了重新審視和定位,並對科技理性的無限膨脹和現代科學中物件性思維方式的盛行進行了深刻反思,滲透其中的非物件性思維、平等性思維、整體性思維等思維方式蘊含著濃郁的生態審美意蘊。
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思想還可與儒家、道家思想相互參照。如儒家【易傳·系辭下】雲:「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這裏的「三才之道」既是高揚人道之道,將人放到與天、地並舉的突出位置;又是註重人與自然休戚與共、和諧發展之道,天、地、人並非各行其道,透過法天正己、尊時守位、知常明變,人道可與天道、地道會通,達到與天地合一、與自然和諧的的境界。【禮記·中庸】亦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思想,認為達至「中和」之境,天地便各得其位,萬物自然發育。而在道家那裏,人與世界的先天關聯則得到更深入的探究。莊子將先天不與天地相分離的「聖人」視為「天人合一」的集中體現,將其在世界中本真的生存方式喻為「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遁而皆存」(【莊子·大宗師】),而聖人無限開放以至與萬物冥然合一的心境則是「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莊子·逍遙遊】),達到了與天地六氣融為一體的本真生存境地。莊子還提出「藏天下於天下」的思想,與「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這種人為地藏小物於大物之中相比,「藏天下於天下」則把天下萬物藏於天下萬物之中,讓天下萬物自然而然地存在,莊子認為這才是「恒物之大情」(【莊子·大宗師】),才是與道合一的本然狀態。
可見,中國先秦的儒家尤其是道家,在探尋道的問題上已經與海德格爾探尋存在的問題走在了相似或相近的「林中小路」上,「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前者比後者踽踽獨行的足跡竟早了兩千多年。他們都試圖把人的認識從物件性思維、心物對立、沈陷於現成存在者的思維模式中擺脫出來,去探尋更為本源的東西,讓人回歸到其賴以生存的根基之處。這既是本性的回歸,因為人天生就在世界之中存在,人與自然萬物是天然的一體;也是認識的超越,即超越心物對立、主客對立,以非物件性思維、整全性思維觀照萬物和世界。海德格爾作出這番關於「在世存在」思考之的同時,還曾於20世紀30年代發出了「拯救地球(大地)」的號召。盡管當時並未引起太多認同,但20世紀後半葉以來,隨著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生態問題日益成為現代社會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問題,海德格爾的思想也成為當代生態美學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海氏本人甚至被冠之以「具有生態觀的形而上學理論家」「生態哲學家」等稱號。我們不妨把海德格爾視為早期中國智慧在兩千多年後的異域回響,這種回響和共鳴反而有助於我們在比較與互鑒中,為當今時代解決生態危機問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
[1] [德]海德格爾. 路標[M]. 孫周興,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2] [德]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M]. 陳嘉映, 王慶節,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06.
[3] [德]克勞斯·黑爾德. 世界現象學[M]. 倪梁康,等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03.
[4] [法]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 上帝·死亡與時間[M]. 余中先,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1997.
[5] [德]海德格爾. 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 孫周興,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0.
[6] 孫周興. 說不可說之神秘——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1994.
[7] [德]海德格爾. 林中路[M]. 孫周興, 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8] [德]海德格爾. 演講與論文集[M]. 孫周興,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05.
[9] 余虹. 詩人何為?海子及荷爾德林[J]. 芙蓉, 1992(6).
[10] 張賢根. 存在·真理·語言——海德格爾美學思想研究[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4.
[11] [德]海德格爾. 尼采(下)[M]. 孫周興,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