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介於西漢盛世與三國鼎峙之間的東漢,在兩盞鎂光燈之間,顯得黯然失色。東漢成了西漢與三國的附庸朝代,其時代意義與獨特性長期受到忽視。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偉傑的【東漢的崩潰:西北邊陲與帝國之緣邊】(The Collapse of China’s Later Han Dynasty, 25—220 CE: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s and the Edge of Empire),是寥寥無幾以東漢為研究主題的專著。這部專著源自謝教授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呈交的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出版英文原著,中譯本於2023年由東方出版中心推出。謝教授透過分析帝國中心與西北邊緣之間的政治環境、軍事狀態、文化素養、族群觀念、自然地理等區域差異,論述飽讀儒家經典、掌握洛陽朝廷的東部文人與長期對羌作戰、被政治邊緣化的西北武人之爭,如何導致東漢帝國的衰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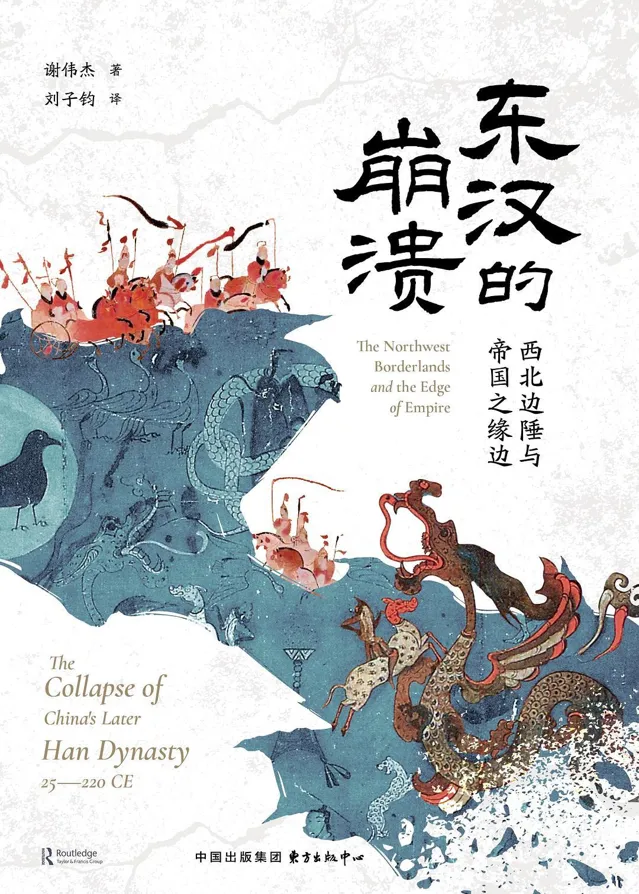
中譯本序中提到,您本來是以魏晉南北朝史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後來開始上下求索不同歷史時期,並在陳學霖教授的啟迪下,最終選擇了東漢史。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尤其是與西漢相比,東漢有何獨特之處,以至於吸引了您從事東漢史研究?
謝偉傑:在修讀歷史本科時,我本來對隋唐史抱有興趣,後來察覺到隋唐史的諸多問題,其實需要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決定以魏晉南北朝史為主要的研究方向。然而,如果不是從漢代開始,甚至從上古時期開始求索,我就無法完全理解魏晉南北朝史。於是,我陷入了一次信心危機。當時,陳學霖教授說:「你的讀書範圍可以無邊無際,但是你要有專精的研究範圍,不能夠永無止境地探索。」就此,我有數個想法。第一,秦、西漢前期和東漢末年是秦漢史學界的焦點所在,至於西漢後期及東漢前中期,則關註相對薄弱。從這個方向鉆研歷史,會比較容易提出新觀點。第二,我們普遍對東漢政治發展有籠統而典型的刻板印象:皇帝壽命短促—中期戚宦相爭—後期黨錮之禍。不過,除了這些故事外,東漢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深入探討。例如,我們在比較東西兩漢的國力時,一般認為東漢是一個非常衰弱的時代。可是,如此龐大的東漢帝國,即使面對各種內憂外患,就如超過百年的漢羌戰爭,也沒有馬上崩潰,而是存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證明東漢絕對「不是省油的燈」。第三,東漢是早期帝國模式的終結,是關鍵的時代。第四,這本英文書需要考慮如何吸引英語世界的讀者,如何為海外漢學界作出貢獻,而東漢史恰好長期受到忽視。因此,我選擇了從事東漢史研究。
長期關註您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您有一個別具一格的歷史寫作習慣——除了中文著作外,您還會參照大量英文及日文著作。能否請您分享一下,中國、西方及日本學界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擁有什麽特征,三者又有何長處?
謝偉傑:研讀歷史應該在能力所及之處,盡量多看原始史料和近人研究。歷史是一門累積的學問,需要累積大量史料和別人的研究成果,才能創造學問。做學問的人倘若能夠掌握更多語言工具,必定獲益良多,我甚至惱恨自己精通的外語太少。在中國文化、語文的熏陶下,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史料的掌握,當然是相對優秀的。但是,從本國史的思維探討中國史,卻可能會出現盲點。西方和日本學者研習中國史,其實是研習外國史。透過對比本國史與外國史,他們能夠以別出心裁的角度探索中國史。當然,這些角度是否言之成理?我覺得是另一個問題。另外,外國學者撰寫中國史,面向的是英語或日語世界的讀者。他們的表述方式與我們截然不同,常常以新角度思考歷史,或是利用比喻說明歷史。相較之下,日本學者閱讀中文史料是用心仔細的,他們開辦了大量史料研習班,以集體的力量精讀史料。至於西方學者,他們除了擁有世界史的基礎外,還具備社會科學的知識。此外,容我參照博士論文導師金鵬程(Paul R. Goldin)教授的說法:「西方學者讀中國史料,沒有中國人那麽快,可是中國學者讀中國史料,卻沒有西方人那麽慢。」這個慢讀,是很有意義的。

謝偉傑
您在書中以西北地方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作為背景式鋪墊,其中提及西北地方深受北邊區文化的影響。那麽,北邊區與西北地方有什麽共同的文化?與北邊區相比,西北地方又有何種個性?
謝偉傑:近年,中外學者都討論到北方文化帶的影響。亞洲內陸文化是透過北方文化帶傳入中國的。它不但影響了西北地方,也影響了漢帝國的北邊區。西北地方與北邊區相比,即涼州與幽、冀、並州相比,西北地方的地理位置更接近西域,與西域的聯系自然相對密切;反之,北邊區的地理位置比較接近蒙古草原。所以,兩者之間有著具體而微的文化差異。整體而言,它們都受到外來風習的影響。然而,西域既有遊牧群體,又有定居的綠洲國家,那麽涼州郡縣與西域各國之間的交流接觸,就或多或少培養出獨有的區域文化。漢帝國的西北發展事業,是先穿越河西走廊,進軍西域,繼而邁進中亞,建立屯田據點。這種發展模式與北邊區截然有異,因為北邊區一到了蒙古草原的某條界限,就不是早期中華帝國能力所及的地方。兩者顯然踏上了不一樣的發展路徑。
文化興盛的關東洛陽朝廷與尚武的關中西北邊疆,顯示出東漢帝國東文西武的形勢。根據【史記·貨殖列傳】及【漢書·地理誌】,所謂關中,亦即秦地,其實也包含巴蜀地區。然而,為什麽是西北地方,而不是巴蜀地區,成了文武之爭的舞台?
謝偉傑:你提及大關中地區,即秦地,其實包含巴蜀地區。雖然巴蜀地區是秦國在戰國後期經營所得,但是從長時段的角度看西北地方發展,關中核心地區卻早在西周時期,已經與亞洲內陸文化建立直接的聯系。當時,周人從亞洲內陸引進了戰車、青銅武器等物質文化,孕育出「西土之人」的西土意識。與西北地方不同,巴蜀地區擁有自成一格的區域文化。作為一個發揮後勤作用的糧倉,秦國在向南開發的過程中,吞並了巴蜀地區的資源;漢高祖也在進入巴蜀漢中後,帶走了當地的資源,還定三秦。至於為什麽西北地方成為了文武之爭的舞台?第一,西漢定都關中,使西北地方變成舉足輕重的戰略要地。第二,漢帝國無論是進軍亞洲內陸,還是築起防禦,西北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緣地帶,而巴蜀地區則只應付對關中地區威脅較少的西南夷。第三,西漢西北地方尚武,成為了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後來文武情勢逆轉,便演化成關東與關中之間的文武沖突,而不是巴蜀與關東之間的地域沖突。
在西北邊疆政治邊緣化的過程中,東漢王朝湧現了一批染上東部士大夫色彩、允文允武的西北精英,譬如涼州三明皇甫規、張奐和段颎。身處在帝國中心與西北邊緣當中,遊走在東部文人與西北武人之間,請問他們是如何立身處世的?
謝偉傑:我對允文允武的西北精英及其立身之道很感興趣,但在史料的限制下,相關問題是難以深入挖掘的。例如涼州三明,我們只能依靠【後漢書】的傳記追溯當時情境。論及他們是如何立身處世的?站在邊緣人的角度,他們在西北地方當然是精英分子,但在東漢朝廷眼中,他們仍然是邊緣地區出身的人,在東漢朝廷主流中不占有重要席位。例如,張奐打算將戶籍所在地改為內郡;段颎被士大夫排斥在外,只得勾結宦官;皇甫氏與關東文化的接觸相對密切,但仍然無法躋身一等士族之列。這些事例證明兩地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的差異,導致了文武之間的對立。對於涼州三明這類身份模糊的人而言,如果別無所求,尚且安之若素;如果心有所求,便會處於矛盾困難之中。就算他們主動討好東部士大夫,東部士大夫也不一定接受好意。如此的話,應該如何是好?以涼州三明為例,他們有不同的取向,就如段颎,選擇勾結宦官勢力,從而攫取更高的權力,又如皇甫規,選擇表現出自己是關東士大夫的同情者。我認為邊緣精英分子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除了涼州三明外,其他人也可以是個案研究的物件。
您在書本中提到,文化差異與政治忠誠是區辨漢羌的重要標識。例如,當西北羌人與漢人都是帝國政府的敵人,並在關東士大夫眼中是「不屬於我們一分子的西方人」時,他們之間便沒有鮮明的差別。請問這種區辨民族的方法,放之於其他民族如匈奴、百越,又是否合適?
謝偉傑: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雲:「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在此基礎上,我認為:胡漢之分,不僅僅在衣食住行等表面的生活文化,而在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雙向的,既要自我「認可」,也要他人「同意」,單方面的「認可」是存在缺憾的。此外,我認為古代沒有近代的民族主義概念。在此背景下,政治忠誠便是區分胡漢的重要標識,效忠物件將決定個人的族群身份。與服飾和飲食習慣相比,政治忠誠明顯實在得多,因為服飾和飲食習慣可能是因地制宜而產生的最佳生活方式。我曾經撰寫了一篇論文【在外圍政權中制造合法性:前涼統治下西北邊陲的帝國忠誠主義和地方主義(301—376)】(Fabricating Legitimacy in a Peripheral Regime: Imperial Loy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Under the Rule of the Former Liang [301—376]),談及一種多層次身份認同(layered identity)。人可以有不同和多重的身份認同。政治忠誠也是一樣,既可以效忠自己的社群,也可以效忠某一位君主,因此歷史實況一定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復雜。不過,我反對以單一標識分辨胡漢,文化差異與政治忠誠等標識應該作一整體考量。至於這種區辨民族的方法,放之於其他民族如匈奴、百越,理論上是可行的。只是匈奴、百越沒有留下文字材料,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漢人所說的故事。
涼州人口由本土居民、各地移民及蠻夷部落共同組成,其中更充斥著士兵、免官者、政治流放犯、特赦犯、流民、冒險家、傭工等。有趣的是,在這樣文化多元、身份多重的群體中,卻逐漸整合出以「涼州」這一行政區劃為單位的身份認同。為什麽呢?
謝偉傑:涼州人口除了有本土居民外,還有大量自漢初開始不斷遷入的關東及南方移民。我在書本中沒有仔細分析移民有否落地生根,以及戍卒完成守邊後會否離開駐地,確是我的不足。透過簡牘,其實可以一窺本土居民及戍卒的人口組成。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各地移民與本土居民產生了一種文化取向,繼而逐漸整合出一種身份認同。然而,我不打算強調他們整合出以「涼州」為單位的身份認同,以涼州為單位只不過是方便說明研究的地理範圍。他們不一定有作為涼州人的意識,而是有屬於這一區域,作為西北人的意識。鄭泰與董卓的對話,就劃分了東西兩地居民。對於知識階層而言,州部身份可能相對重要,因為察舉制度包含州舉名額;對於平民而言,「涼州」則不是必要的身份認同。

董卓
在中譯本出版後,您對這本書有沒有產生新的看法?
謝偉傑:第一,利用簡牘材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因為我當時計劃撰寫一個概括性論述,從西北地方說明中心與邊緣的矛盾、文武之爭、身份認同等問題,而降至地方層面上,簡牘其實能夠提供更多資料。當然,西北簡牘尚未能夠細致描繪社群內的畫面,清楚刻畫時人如何定義自己,如何看待東漢中央朝廷,但我相信如果利用西北簡牘,故事內容將會更加豐富。第二,結尾收束過於草率。董卓死後,關東群雄如何續唱余韻?漢末英雄人物又有何種身份認同?我一直希望撰寫以呂布為中心的個案研究,作為我對東漢歷史研習的真正結尾。此前,就著對西漢後期的看法,我也出版了一篇以陳湯為研究中心的論文【公元前1世紀中國外交事務中的冒險機會主義:陳湯、他的同伴及其支持者】(Opportunism in Foreign Affairs in First Century BCE China: Chen Tang, His Fellows, and Their Patrons)。第三,直到現在,我對漢代東西文武之爭的看法仍然基本不變,但我認為可以進一步探究東漢文武價值觀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不單是東漢涼州,其他時期其他地區也是可行的研究物件。
最後,請向讀者介紹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寫作計劃。
謝偉傑:剛才我提到的呂布研究,是一個不日上映的方向。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英文書,本來打算論述上古至魏晉南北朝的戰爭、政治與社會關系,但在撰寫過程中發現,如果內容橫跨上古及魏晉南北朝,時間維度將會過闊,書本將會過厚,而當下條件不適合出版一本這樣的英文書籍。現在計劃先完成上古至秦漢的再說。雖然西方學界討論秦漢歷史的英文書層出叠見,但是有關魏晉南北朝政治與軍事的英文專著,卻少之又少,這個領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盡管葛德威(David A. Graff)教授撰寫了【中古中國的戰爭】(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但是他主要研究唐代史。在此,我必須強調這本書對我影響深遠。這本書一出版,我就在【漢學研究】撰寫相關書評,葛德威可以說是我的偶像。另一個計劃是寫一本關於漢代邊緣群體的英文書籍,是從任教生活史期間引申出來的題目。以上是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寫作計劃。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