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白·馬什出生在牙買加,曾在倫敦、直布羅陀和梅諾卡島留下痕跡,她到訪過非洲之角和裏約熱內盧,探索過印度次大陸,還曾被囚禁在摩洛哥蘇丹的深宮。她參與了美國佛羅裏達州的土地投機和國際走私,數次被卷入奴隸制度之中。她的一生也是宏大歷史的一部份——18世紀的啟蒙運動、帝國戰爭、洲際貿易、奴隸販賣與航海移民深刻改變著世界,也重塑著她的人生軌跡。這是【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一個女人的世界史】(以下簡稱【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所講述的故事。作者琳達·科利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原著於2008年出版,即頗受好評。近年隨著微觀全球史研究在中國的普遍接受和流行,相關著作、譯作接連出版,琳達·科利培養的一批青年才俊,如馬婭·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其著作【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國與大英帝國的東山再起】【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也先後推出了中譯本。今年二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推出了【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的中譯本,這部著作被歷史學界視為微觀全球史的奠基之作,此次中譯本的面世於讀者而言可謂「相見恨晚」。3月2日,由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教授陳丹丹創辦的全球學術平台「全球研究論壇」(globalstudiesforum.com)特邀蘇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魏濤策劃召開「全球微觀史」圓桌論壇,邀請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吳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旭鵬、維吉尼亞州倫道夫-梅肯學院(Randolph-Macon College)副教授張德文,以及台灣地區「中大」副教授蔣竹山,一起以【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為切口,探討了微觀全球史研究的方法和意義。

幸運的小人物:發現伊莉莎白·馬什
伊莉莎白·馬什不是名門貴族,也沒有做出什麽重大的歷史貢獻,一個小人物何以能得歷史學家之青眼,專門為其寫一部書呢?在圓桌論壇的開始,主持人魏濤對琳達·科利的學術經歷做了介紹。
琳達·科利治英國史,早期的代表作有1982年出版的 In Defiance of Oligarchy The Tory Party 1714-60 ,研究的是1714年到1760年的托利黨。第二本專著是1992年出版的 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中譯本【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2】由商務印書館於2017年出版),討論的是英國人的自我認同。之後,又有2002年出版的 Captives:The Story of Britain's Pursuit of Empire and How It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ere Held Captive by the Dream of Global Supremacy ,這本書以俘虜為研究物件從海外視角研究英國史,正是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科利接觸到了伊莉莎白·馬什。
馬許本人留下了兩份文字資料,一是以她被俘摩洛哥的經歷寫成的回憶性文字——【女俘虜】,二是以她後來在南印度的旅行經歷寫成的遊記。以這兩種資料以及馬什家族留下的一些資料,科利寫成了【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
伊莉莎白·馬什的幸運不僅在於歷史學家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發現了她,關註到她,並由此繼續深入,挖掘出關於她的更多的資料,更在於,伊莉莎白·馬什在她生活的時代,留下了關於自己的文字。
「相較於很多普通人來說,伊莉莎白·馬什是比較幸運的,她處在一個婦女地位已經得到提升的時代,18世紀中後期英國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閱讀,其中婦女的比例應該比較高。這也是她能夠留下資料的時代背景。但更多的女性,就像馬什一樣有著全球經歷的女性,我們根本是看不到的。」張旭鵬在發言中,談起了伊莉莎白·馬什的故事中那些在她身邊而無姓名的女人,「以馬什的母親為例,她出生於加勒比海地區一個跨種族的婚姻的家庭,當時白人和黑人的結合很多。馬什母親的第一任丈夫是一個白人,第一任丈夫死了之後,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馬什的父親。馬什的父親娶她,其實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因為她第一任丈夫是一個比較富有的船商,留了一筆遺產,馬什的父親從這個婚姻中獲得了這筆遺產。這也是當時很多普通英國人去加勒比海地區,或者去其他殖民地,實作身份躍升的一個有效途徑。其實馬什的母親也擁有一部全球史,但是她卻沒有任何留下任何東西,甚至在這本書中她的母親連名字也沒有。這些跨種族婚姻的女性盡管有全球性的經歷,但在歷史中,依然處於一個沒有歷史的地位。還有馬什的兒子,他在印度找了一個當地的女人也生了孩子——書中特別提到他找了印度的‘女伴’,這個女人在他的家族中也沒有名字,甚至馬什的孫子也找到一個印度女伴,也沒有名字,不僅沒有名字,他們生的混血女兒還被馬什的孫子遺棄了……也就是說,有更多具有全球性命運的人其實是沒有歷史的。」
伊莉莎白·馬什留下的文字使其成了幸運兒,但從歷史書寫的角度講,馬什留下的資料又是極其有限的。那麽,琳達·科利這部經典之作是如何完成的?
何以經典?——微觀全球史的寫法
在分享閱讀體會時,吳愁從四個方面對【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一書的特點做了整體評述。
「第一個特點是這本書是以一個人來帶動這個人所處的整個世界,將個體命運置於宏大的世界歷史行程中。這種研究或者說寫作呈現的方式,既很容易將讀者帶入閱讀,又把著作帶上了一個哲學的高度,探討了個體命運置於世界歷史宏大車輪的哲學命題。這體現了全球微觀史的魅力所在。
「第二個特點,這本書其實講述了一個女人的世界史,迎合了近些年女性史的整體發展,以及自下而上進行歷史書寫的取徑。另外,歷史中常見的女性,比如皇後或是重要人物的妻子,或是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修女等等,而馬什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個平民,被迫遷轉,流動於歐洲、地中海、美洲、北非、印度次大陸等。她一生的重大遭遇都植根於18世紀歷史的宏大潮流中。所謂‘宏大潮流’,比如說18世紀地中海的奴隸貿易,乃至在當下歷史書寫中都不為人所知的由海盜引發的白人奴隸貿易,還有七年戰爭、英帝國的擴張,等等。平民女人與大時代的風雲詭譎,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這也是本書極其具有吸重力的一點。
「第三,本書采用跟蹤擴充套件式的寫作手法,將個體與宏大世界之間的關聯處理變得平滑圓潤、不留痕跡。跟蹤式寫作手法,尤其被用於流動的人或物的寫作當中,琳達·科利在這本書中主要是跟蹤伊莉莎白·馬什的人生線,在具體的事件中,再擴充套件與事件相關的歷史人事。比如說講到第一次女主被俘虜於摩洛哥,科利就會分析,她所乘坐的船為什麽會被劫持?然後就會講到巴貝瑞的海盜,以及1755到1756年,英國和摩洛哥之間關系的惡化。摩洛哥國王出於自身的政治野心,蓄意劫持英國船只以此作為對英談判的籌碼。接著細化到伊莉莎白兩次被傳喚,單獨面見摩洛哥國王,尤其是第二次,科利進而展開書寫摩洛哥國王的個人魅力——穿衣打扮、個性特點,講述他的從政風格、政績以及政治野心,再進一步講述18世紀摩洛哥的地理政治和商業需求,等等。在這些擴充套件描述中,作者又不無高度地概括:摩洛哥國王是一個商人政治家,是那個時代的原始全球化的創新人士,並且論及原始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多中心現象,穆斯林也積極地參與、推動了這一行程。如此,一些歷史性的洞見躍然紙上。講完這些宏大背景,作者筆鋒一轉,再回到女主。
「本書的第四個特點,這是一個女人的世界史,這裏體現了大量的女性獨特的心理活動,以及女主的女性視角,就是說這本書的女性中心特征,以及比較強的文學性和故事性——這體現在書中大量的細節描述。對讀者而言,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感是比較好的。作者圍繞伊莉莎白·馬什的一生展開,基於史料以一種探案式的分析,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地呈現了女主的一生。基於史料,這本書雖然不能夠像真正的文學作品那樣去過度彌補和想象女主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但對於女主的婚戀情感、人生中的幾個大膽選擇和決定,作為讀者可以感受到,伊莉莎白·馬什的命運歸因於她所處的時代,同時,她經歷的磨難中,其個人性格和選擇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呼應了個體和時代命運這樣的主題。這樣的寫作和表達,令人耳目一新,讀起來非常具有吸重力,可以說是雅俗共賞的一本書。」
吳愁的評述,尤其是她所言的第三、第四個特點即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前面的提問——史料的解讀,寫作的技巧,以及適度的想象。其中,史料是最基本的。琳達·科利面對一個普通女人的有限史料,她完成的作品令人稱贊,但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張旭鵬在發言中針對史料不足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張旭鵬認為,馬什留下的資料,並不完全足夠支持歷史學家去進行一個全球性分析。首先,【女俘虜】是她事後十幾年的回憶,裏面有很多想象、創造性的成分,那麽,用它來進行分析,就缺少一定的客觀性。南印度遊記則是一個完全私人性的記錄,而且在印度南部的旅行,也談不上是全球史。伊莉莎白·馬什的故事,讀者之所以覺得精彩,在於琳達·科利作為歷史學家展開的分析和想象。
「馬什的第二段旅行,科利說她沖破家庭的束縛——這層含義是歷史學家賦予她的。琳達·科利花了很多筆墨去分析當時的背景,比如對於馬什丈夫的全球性移動的生活所展開的分析,我覺得這部份可能要強於對馬什的分析,因為她的丈夫就是一個真正從事全球性活動的商人,而且關於她丈夫的材料也比較多。還有,科利對時代背景,諸如七年戰爭、英國在全球範圍的殖民地,甚至包括獨立戰爭的全球性影響等等,這些分析都很出彩。正是這些出彩的分析,把史料上的不足沖淡了一些。這其實是很多微觀史寫作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史料過少,歷史學家就會展開想象,對於微觀全球史寫作中存在的過度詮釋的問題,張旭鵬認為,像【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一般「以個人為主體的微觀全球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個傳記,歷史學家在寫傳記的時候會與傳主共情,賦予傳主一些額外的東西,比如科利賦予了馬什很多現代女性意識,比如她獨立的個性,對婚姻的不滿,想尋找一個獨立的婚姻……」。
作為另一部微觀全球史作品【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沖突的世界】的譯者,張旭鵬以此為例進一步談到,「朱宗元被作者塑造成一個非常有時代意識的人,他有一個強烈的意識,要用天主教來重新詮釋儒家,他覺得這是他的使命。但這樣的詮釋,放在當時一個很普通的儒家知識分子身上,他是不是真的能肩負起這樣的使命,我覺得不一定,因為沒有更多的史料能夠讓作者去分析他的內心」。過度詮釋,是微觀史寫作要面對的問題,也是難以避免的問題。當然,想象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
何以經典——微觀全球史的意義
【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能夠引進到中文世界轉譯並出版,蔣竹山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從學術史的脈絡上回顧了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繼而到微觀全球史的轉向。
蔣竹山回憶說,在他讀碩博士的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當道的時代,不少相關著作都推出了繁體中譯本,而近二十年來,研究趨勢則轉向了全球史。「歐陽泰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三本書,有史景遷,有戴維斯,他們都在關註人物。史景遷是不是全球史書寫的取向,這很難講,大概他還是在文化史的書寫中關註人物,而過去,我們提到戴維斯,更是將其視為新文化史的戰將。那麽,他們是什麽時候開始發生歷史書寫的轉向的呢?」蔣竹山說,「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我們看到的是,在所謂的全球史的書寫中,關註的人物也是我們比較不熟悉的‘小人物’,但在小人物的跨大洲的移動中,人物的能動性被‘提’出來了。當然,在一些微觀全球史的著作中,這個人物也不一定要跨大洲,就是以全球的視角看微觀的人事。談全球史一般會被認為是談一個非常大的議題——不管是在空間或者是時間上,而比較忽略人物的能動性,那麽,微觀全球史就是重視起人物的能動性,在新文化史跟全球史中間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過去新文化史研究把‘社會’給丟掉了,微觀全球史就是把過去丟掉的社會經濟又‘拿’了回來。當然,過去年鑒學派也談大歷史,裏面有地理環境,有社會經濟,也有人,但人的能動性不是他們關註的重點。科利的書中,你感覺人是被大時代的漩渦帶著跑的,但這個過程中個人的意誌也很重要的,微觀全球史會強調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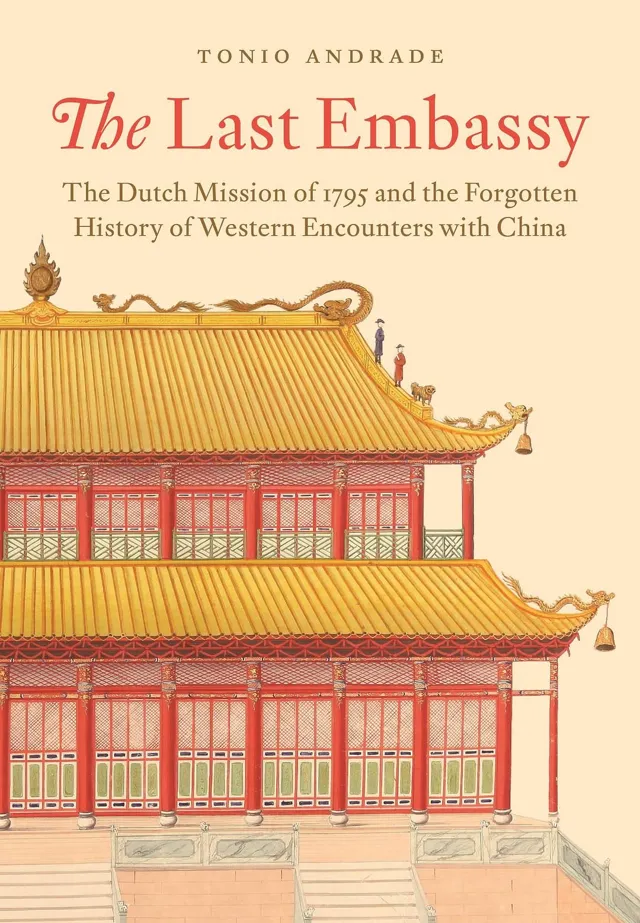
he Last Embassy: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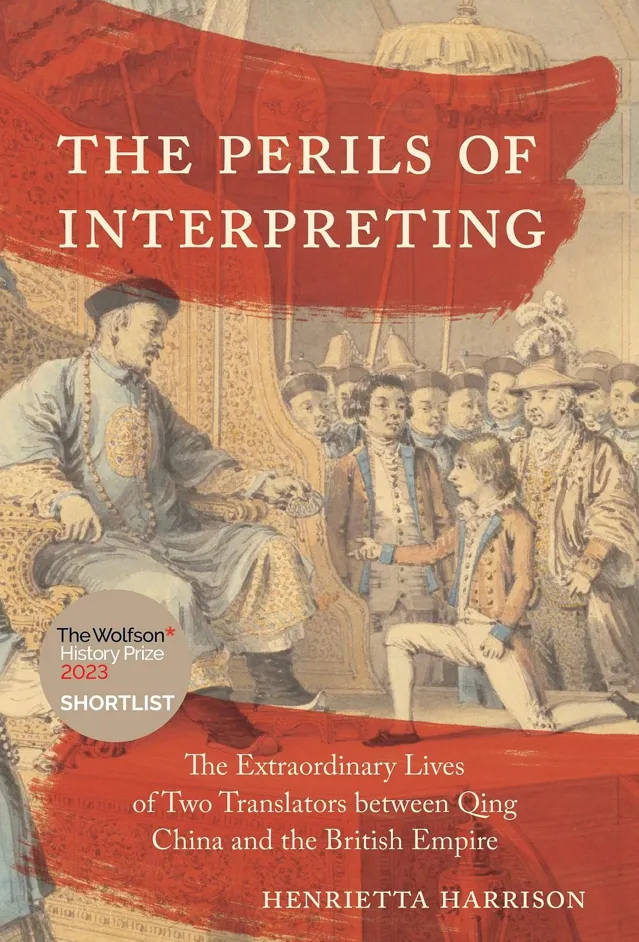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蔣竹山還與讀者分享了幾本微觀全球史的新近研究動態。「歐陽泰的新著 The Last Embassy: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講的是荷蘭的使團到中國的故事。類似的,還有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新著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她關註的是馬嘎爾尼使團中的兩個轉譯。此外,也有研究某一地的,比如景德鎮的全球史的。去年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期刊組織了一個關於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專號,邀請了幾位全球史學者講全球史中的地方。有興趣的讀者關註一下這個專號呈現的個案研究,就會比較清楚這些學者講的微觀全球史到底是什麽,研究方法是怎麽樣的。」
比較的視野:女性與女性的世界
張德文的研究更多關註婦女,她從比較婦女歷史的角度分享了她的閱讀體驗。她選擇性地參考了兩部八九十年代較為經典的歐美婦女微觀史著作及一部中國婦女史著作進行比對。微觀婦女史的代表性著作非常多,張德文的選擇是比較具有個人偏好的,她選擇了Laurel Thatcher Ulrich所著的 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助產士故事:馬莎·巴蕾德的生活】)和英國歷史學家Caroline Kay Steedman的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好婦人的人生景觀:母親和我的人生】)。Ulrich和Steedman都是上世紀較早關註微觀層面書寫女性歷史的研究者,兩者對材料的挖掘和重新發現都有方法論上的重大突破。Ulrich對生活在新英格蘭,生命跨越殖民地時期和美國初建時期的助產士馬莎·巴蕾德留下的日記進行顯微分析和解讀,重構了這時期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口出生、衛生、食物、經濟、貿易和農業活動的歷史。以往的歷史學家往往認為巴蕾德流水賬式的日記過於日常普通,對歷史分析用處不大。Ulrich則另辟蹊徑,在大量細致入微地閱讀和分析中,讀到了助產士日記中反映出來的人口出生變化趨勢、嬰幼兒死亡率、日常家庭生產貿易、食物配給、氣候變遷、地區交通運輸概況等等這些往往深受年鑒學派偏好的重大議題。作者Ulrich也因此書而獲得學界矚目。Steedman自傳性質的對母女兩代人的書寫則依靠回憶和人類學式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解構了一個倫敦工人階級家庭的母女兩代人生活,從而揭開成長的階級密碼。文章的精彩之處是對母親這個人物的描述:始終貫穿母親一生的對物質的追求,作為女兒的作者寫道,來自母親童年時代的物質匱乏。母親來自一個紡織工人家庭,她的童年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一直到晚年,母親保有物件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的渴望。作者Steedman分析自己與母親長年失和、無法互相理解的深層社會歷史原因,用馬克思主義女權分析方法解釋階級情感和欲望的構成。她筆下的工人階級女性並不是革命的,而是將社會已有秩序和資產階級的物質欲望內化,並終生處於望而不得狀態的一個女工。Steedman的分析直接有力,將母親和自己作為研究物件,不可謂不堅強倔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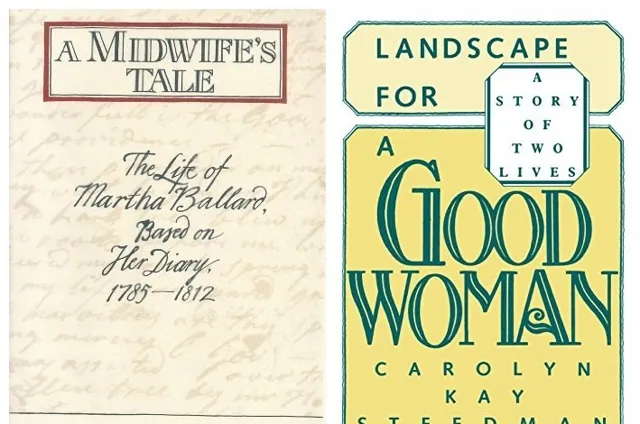
Ulruch 和Steedman 這兩位學者發表於上世紀末聚焦於地方社會的微觀婦女史作品和科利的微觀全球婦女史作品發表前後相差二十年,形成了有趣的比較閱讀。正如幾位老師討論到的,此間歷史學界主要關註點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婦女史作為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難免不受歷史學轉向的影響。全球史研究和寫作的興起正是其中之一重大影響因素。如果說Ulrich和Steedman的地方性研究幫助我們從婦女史的視角更深入地了解了社會肌理的構成和社會各項因子的互動變化,包括情感構成的社會階級性及其傳承,那麽科利的研究則佐證了婦史角度研究全球史的可能及其啟示意義。科利對宏觀歷史的把握運籌帷幄,同時她對婦女史研究方法的把握也允許她對研究物件的家庭、婚姻和個人旅行有精準的敏銳度,是一部將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典範之作。
就中國婦女史的比較閱讀而言,科利的著作和曼素恩(Susan Mann)的【張門才女】( The Tak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也可作為有趣的比對。兩者關註的女性生活在大致相當的世紀,生命大致落於18、19世紀之交,生活在當時最大的兩個東西方帝國中。討論的內容也都涵蓋了女性的成長(母女、父女情感皆有著墨)、女性的旅行、婚姻、家庭生活、婦女寫作等內容。盡管曼素恩的研究沒有全球史的中心維度,而將重點置於晚清時期圍繞科舉制度而形成的男性、女性生命周期,但是她也關註到十九世紀歐洲崛起鴉片戰爭等因素對中國江南女性生活形態的深度影響和重構。
張德文指出,兩部關註地域範圍截然不同的作品在組織形式上卻有異曲同工之處:比如都是沿著女性的生命發展歷程——出生、成長、婚姻、家庭、寫作、旅行、子女——這些線索展開討論,從而達到在揭示女性微觀層面的生活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歷史學家進行對更大議題(社會、經濟、階級、文化)等在普遍意義上的分析和討論。比如就婚姻這個問題,曼素恩著墨於晚清理想婚姻物件的選擇是確保家庭地位得以在科舉制中的成功中得到延續。女性與男性的學識在晚清江南社會也因此各具特點,都受到重視。父母在子女的婚姻中扮演重大角色,對女兒的情感之深亦體現在對她的婚姻的細致周到的思慮及安排上。科利的著作同樣有對十八世紀英帝國中產階層婦女婚姻安排的詳盡論述。馬什對女兒伊莉莎白的婚姻有同樣的思慮:囿於當時的境況(由於帝國戰爭伊莉莎白被摩洛哥所俘,與一同被俘的男子同關押數月),伊莉莎白的貞潔及其名聲及社會地位如何得以保障?馬什為了女兒有一個妥當的安置,甚至放棄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以趕赴到女兒身邊。若對這一議題有興趣,兩部作品還可就晚清帝國和英帝國婦女史研究與寫作進行更多的比較思考與分析。它們都對帝國婦女研究寫作提供了重大啟示,科利的全球微觀婦女史寫作對二十世紀婦女史寫作的意義也深遠,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婦女全球活動更加頻繁活躍的世紀。
可以說,在微觀全球史的書寫中,其核心是以微觀的個體來回應/體現全球性的某些重大議題,從這個目標上說,也許【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尚有可討論之處。而作為一部經典著作,【伊莉莎白·馬什的磨難】無疑是成功的,它包羅永珍,可以闡釋、解讀的角度有很多,始終給讀者和學者以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