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公眾號「人間the Livings」釋出了一篇非虛構推文,作者姓名標示「張湯圓」。文章以一個女兒的視角講述了自己暗淡的家庭與母親的悲劇人生,質樸而又真誠,閱讀量迅速突破10萬+。在結尾,張湯圓回憶了自己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夜裏,母親在半睡半醒中喃喃地說道,考上大學的女兒是自己唯一值得驕傲的事情。
然而在未完待續的現實中,走進大學校園的張湯圓卻沒有如母親驕傲的想象中那般一片光明。失去了高考目標的牽引,曾經引以為傲的成績不再是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尺,茫然與無力又以新的形式降臨在了她面前。更何況她所就讀的廣東F學院,在國內3072所高校中,只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存在。
在寫下那篇文章之前,張湯圓申請了一個課題,她想回到自小生長的村莊,去了解那些和母親一樣的媽媽。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她找到了學校財經傳媒系的老師黃燈。此前她從未上過黃燈的課,但就在2016年春節,她讀到了黃燈那篇引發網路討論的爆款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其對鄉村親人的回望與剖解讓她認定,這就是最適合自己的計畫導師。
而當張湯圓敲響辦公室的門時,黃燈也在構思著一個題目。自2005年起,黃燈在這所學校的十年時間裏已教過4500多名學生,持久的接觸與交流中,她不僅見證了不同代際的青春面貌,也窺見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的命運軌跡及其背後的時代變革。她想把她所了解的這些成長故事寫下來,同時提出自己的追問與思索,標題已經擬好了,就叫「十年從教記」。

四年以後,構思變成了20萬文字,以【我的二本學生】為名面世,隨即引發廣泛共鳴與討論。但黃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本書就像一個孩子,它的模樣是自然長成的,事實上其所展現的內容只是「十年從教記」的一個部份。所以她的筆沒有停下來,直到【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在近期出版,所有的表達終於得以完滿。
走到講台的背面
寫作【我的二本學生】期間,黃燈和張湯圓的母親在學校見了一面,更早一些,她還去了一趟張湯圓的老家。不過後來的成書中,張湯圓並沒有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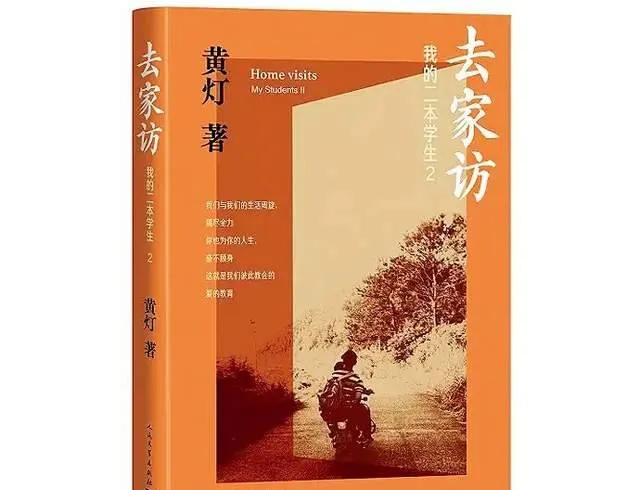
沒出現的不止張湯圓一人。在那前後的五年時間,黃燈去過許多學生的家裏,不少人的故事都沒有被寫出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共性或者過於特殊,而是在黃燈心裏,這些具體而鮮活的相處值得被作為另一種單獨的表達:「寫‘二本學生’不能只寫講台上看到的東西,一定要走到講台的背面,去了解他們為何會成為他們,這才是一個立體的觀察。」
在粵西丘陵起起伏伏的懷抱中,黃燈見到了張湯圓的家,一幢其母親為了方便女兒上學而親手建起的二層小樓,墻壁裸露著紅磚,除了廚房能看出裝修的痕跡,所有房間都是毛坯狀態;也見到了女孩的父親和哥哥,此前聽到的講述中,他們一個不負責任、一個無所事事。很長時間以來,這是張湯圓日常生活的全部,更彼此撕扯著構成了她的精神世界——她刻苦讀書,拼盡全力走出去,既是為了讓媽媽驕傲,也為了逃離爸爸和哥哥。
她還見到了張湯圓保存的一個紙箱,裏面放著一摞證書和獎狀、以及一堆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用過的圓珠筆。黃燈數了數,證書四十一個,獎狀四十九張,圓珠筆近兩百支。「我第一次意識到家訪的意義,第一次深刻地感知到,如果不抵達現場,這些湮沒的場景,這些正敏永遠不會提及的細節,將遮蔽在我的視線之外。」在後來寫下的文字裏,黃燈這樣描述著自己當時的感觸,她所稱呼的「正敏」,便是張湯圓。
不過,並非每一個走訪的家庭都如正敏家一樣暗淡和傷痛。許多學生還是在關愛與溫馨之中長大的,並經由樸素、本分的價值觀言傳身教,生長出了踏實、充盈而從容的性格與生命狀態。對黃燈而言,這與其在寫作【我的二本學生】時常常感受到的沈重截然不同,她發覺「囿於校園的狹隘和對年輕群體理解維度的單一」,自己對二本學生的認知過於悲觀了。「他們作為個體所彰顯出的自我成長願望,讓我清晰地看到,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並由此散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這也讓她回想起了自己的青春。1995年從嶽陽大學畢業後,黃燈被分配到一家紡織印染廠,工作了三年以後,因為廠子經營困難而下崗,每月只有80塊錢的補貼,最難的時候全靠朋友借錢度日。即便如此,黃燈卻從未焦慮過,總覺得人要活下來沒有想象的那麽難:「我也覺得很奇怪,我為什麽就那麽不怕?這個(勇氣)到底來自於什麽?我覺得童年時候形成的篤定很重要。小時候,外公外婆、爸爸媽媽都對我們很好,家裏比較寬松,我就像野馬一樣長大的,很自由,個性沒受到過壓抑。童年的安全感足夠,面對困難的能力就會強很多。」
於是在2022年5月,黃燈開始動筆寫下一個個的家訪故事。她希望透過這些記述能夠補全【我的二本學生】缺失的那部份,即在學校教育的維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被疏忽和漠視的教育資源,平凡的青年是否可以擁有更多途徑去獲取滋養、安放自我。同時,區別於【我的二本學生】有意從整體角度來透視和行文,這一次黃燈給每一個學生都安排了單獨的篇章:「我願意從一些個案上去發現個體的能動性。」
初稿寫了整整7個月,花費的時間是【我的二本學生】的三倍,是黃燈迄今為止投入最久的一次創作。又做了7個月修改,最終定稿為如今的這本新書【去家訪】。
黃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一年多的創作過程中,她的內心也隨之獲得著某種程度的療愈:「2018年時,我總是為我的學生抱不平,覺得他們太難了。他們現在也很難,但是我的心態改變了很多,(變得)特別心平氣和。」
打破沈默的沖動
黃燈最初產生將學生寫進文字裏的想法,源自一次偶然。
2006年是黃燈任教廣東F學院的第二年。一次課上,她布置學生當堂完成一篇作文,當天的廣州恰巧台風過境,她索性便以「風」作為命題。沒多久,一個喜歡坐在教室左側座位的小個子女生就交卷了。讓黃燈沒想到的是,窗外的陣陣呼嘯在這個孩子的筆下成了淒厲的哀鳴,滿紙字句所抒寫的盡是苦悶與無助。
這與黃燈自己的成長經驗也完全迥異。在相同的年紀時,她的生活充滿了快樂、美好和理想,「整天寫著那些風花雪月的東西」,絲毫不像這個女孩一樣,被種種煩惱籠罩和束縛著。
從那之後,她開始有意將關註的目光聚焦在這些青春的生命上,盡可能地增加自己和他們交流的機會。漸漸地,她發現女孩並非特例,其所表達的焦慮原來普遍地存在著。這些「出身平凡,要麽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麽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的孩子,雖然各有各的窘迫,卻因為一個彼此相同的身份——二本學生,面對著共有的困境。
「我的學生總是不斷地在我面前說‘我們二本的’,我其實以前還沒這個概念。」1992年黃燈參加高考的時候,全國的高校錄取率僅25%,而且那個年代,所有的大學生都同樣享受著生活補貼和畢業分配的待遇,彼此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盡管黃燈最終去到了當時尚為專科的嶽陽大學,依然心生自豪、滿懷夢想。
可在她的學生們那裏,黃燈看不到這樣的激情了。在高校擴招的形勢變化中,這些年輕人已隨著學歷的整體貶值失去了天之驕子的光環,市場化就業日益激烈的現實也將生存競爭的殘酷更早地拋擲在他們面前。「他們踏進校門,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的行列,他們安於普通的命運,也接納普通的工作,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
重重壓力與差異之下,黃燈從這些孩子身上看到的更多是與年齡不相稱的馴順,以及讓人心疼的卑微。對此,她理解,因為類似的情緒反饋她也曾偶爾有過:大學時,因為閨蜜在北大讀書,黃燈了解到一所名校所具備的氛圍和條件,第一次生出些許的挫敗感;讀研時,班裏的許多同學畢業於名校,他們所表現出的水平、見識和自我規劃,又讓她覺得自己身上有一種掩飾不了的社會青年氣息;即使後來從教,在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時,她仍然能從一些名校學者那裏感受到另眼相看的目光。
她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是一種持續蔓延的沈默。這種沈默不僅來自學生本身,更來自於外部社會的忽視。在黃燈看來,這個數量龐大的學生群體是和腳下大地黏附最緊的生命,「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命運、前景,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以及他們實作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然而,「那麽多年以來,這樣一個重要的話題沒有人正正經經地討論過。」黃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不過書寫的念頭甫一形成,艱難的糾結卻又隨即在心底生出。黃燈不確定她的觀察是否能夠代表所有學生,也不確定她的理解是否準確。而且,她自知無力去解決那些困境,所以表達反而顯得殘忍而又虛弱。
然而,打破沈默的沖動終究無可抑制。2018年,只用了2個月的時間,她便完成了初稿,然後發給了自己在中山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林崗。林崗看過,給她回了一條很長的微信:「……你是罕見的能回頭看回頭關心那些在你身後的人,不論他們願或不願、能或不能跟上你,你都在他們身上傾註熱情和關懷。做這些事,比你僅僅做教師來得更有意義。你已經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20年,經過仔細的斟酌、修改,書稿正式出版。原本的後記被黃燈拿掉了,她從不否認自己在這一次的書寫之中始終充斥著一股強烈的情緒,卻還是覺得應該盡量讓學生成為敘述的主角,因為「在找不到確定性和結論以前,傾聽更有力量」。這本書就是後來被廣為討論的【我的二本學生】。
無盡旅途的新一程
創作【去家訪】的過程讓黃燈對很多人與事都有了更為全面、冷靜的認識,下筆時的情緒也不再如當年那般感性或者激憤難抑。不過她也清楚,家訪所帶來的這些新的感受和體悟,不意味著現實已經發生了某種本質性的改變。【去家訪】一共寫了12個故事,但這12個學生絕非二本學生整體的面貌,事實上在發出拜訪的詢問後,不少學生給出了明確的拒絕,還有一些人願意接受,但要求黃燈不要把自己寫進書裏。「能夠邀請我、能夠接受我去家裏面的孩子,相對來說他的內心(本來就)更強大一些。」
同時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二本雖然不在高等教育學歷鏈條的頂端,卻也不屬於末端。無論如何,它至少跨過了「本科」的門檻,達到大部份企業的招聘起點,也擁有考研、考公的資格。相對而言,專科學生的天花板還要低矮得多,而且群體規模更為龐大——2023年全國高校913萬的招生人數中,專科占據了483萬人——他們一樣需要被關註。
2019年夏天,黃燈在廣東F學院以班主任身份帶過的第二個班級也畢業了。送走了37個學生之後,她做了一個決定,辭去了在這個學校裏擔任了15年的教職,轉投去了深圳的一所專科職校。
說起這個選擇,黃燈忍不住笑了起來。她說自己的選擇其實非常隨意,因為恰巧有一些朋友在那裏上班,隨口問了一句願不願意來,結果便過去了:「有機會多去觀察一些學校蠻好的,我對重點大學也很感興趣,要是有機會也會去待幾年。像以前魯迅他們那代人可以幾年換一個學校,我覺得對教育觀察是特別好的。」
這所職業院校90%都是工科專業,沒有中文系,黃燈只能面向全校開設公共選修課,講授非虛構寫作。課程每學年一期,只招二三十個人,沒有教材,也不點名。多數時候,黃燈連講台都不站,而是走到隨意落座的學生中間。
學生對這位新來的老師並不陌生。又因為是小班教學,師生之間的交流也比大課密切許多。有學生問過黃燈,到這裏任教是不是為了寫【我的職校學生】,她回答:你們自己寫,會比我寫得好。
「去職業院校是想了解職業院校的學生,確實有這個意識在裏面。(而且)職校孩子的故事更奇特,我的學生講他的成長經歷,都是你無法想象的,寫出來絕對吸引眼球。(但)我覺得寫完二本學生就不用寫職校了,我想表達的觀點已經表達得差不多了,再去寫職校就是換個題材、寫一些不同的故事,但我對故事的興趣沒那麽大。」黃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還是會有一些時刻在不期然間撞擊著黃燈的內心。一次她在一個學生的作文裏讀到這樣一段文字:「在度過無數教育機構拼命渲染的各個分水嶺後,時間終於還是到了初三。該分的水都分完了,‘源頭活水’們老師們一直很放心,到時我們這群‘工業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看似戲謔的自嘲之中,隱藏著令人心痛的自我貶抑,濃烈的茫然和頹喪無疑遠遠甚於那些默默接受平凡命運的二本學生。
所以也許黃燈還是會寫下去的,就像她在【去家訪】結尾處留下的最後那句話:「歸途列車抵達處,是我無盡旅途的新一程。」對她而言,對於學生的關註永遠沒有終點。
黃燈說,她對教育的熱愛與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我爸是一個中學老師,他表面上不是那種正統的好老師,但他是一個對教育有理解的人,是一個有教育家情懷的人。」就在之前幾年的家訪中,黃燈還時常會在眼前浮現出父親的身影,曾經每一年的開學前後,他都要堅持去學生家看一看。
有時候,黃燈還會回想起一幅動人的畫面。小時候,父親的學生一放學就會跑到她家的地裏,一群人像鴨子一樣成群結隊,七手八腳地幫忙插田、收割、侍弄莊稼。「你會覺得那種師生關系是特別美好的。」
發於2024.3.25總第113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黃燈:當一個老師決定去家訪
記者:徐鵬遠
編輯:楊時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