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人類歷史上長期是小眾活動。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火車汽車蒸汽機船等先進交通工具相繼投入營運,旅行才逐步大眾化。19世紀中葉,當近代旅遊業先驅、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創辦者英國人湯瑪斯·庫克,開始在他們國家提供火車遊覽行程時,首批遊客多至六百人。
現代美國著名的文學派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遙想當年這一變化時說,那些曾經享受著旅遊特權的上流人士大概會被這樣的人潮嚇退。(參見[美] 彼得·奇爾森、[美] 喬安妮·B.馬爾卡希【旅行寫作指南】,文匯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
但布爾斯廷生前恐怕未曾想到,他謝世後一二十年裏,在東方的中國,旅行成為人民大眾生活的組成部份,甚至是一些人的剛需。從前出國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而今幾乎每天有許多人在說,「世界這麽大,我想去看看」。
自有旅行,便有記錄旅行的文字。旅行文學從來是不少作家、旅行康寶而為之、雅俗共賞的文學品種。文旅消費的日益增長,促進了新時代中國旅行文學的日趨繁榮。
文匯出版社近幾年推出的旅行文學書籍,如劉子超的【失落的衛星 深入中亞大地的旅程】(2020年7月第1版)、【午夜降臨前到達】(2021年8月第1版),及彭英之的【絲路北道】(2023年8月第1版)等,都頗受出版界和讀者好評。劉子超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作家、記者,而彭英之出身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多年從事編程建模工作。這位「理科男」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

2017年,彭英之和他的旅伴行走的絲路北道,經過中亞五個「史坦國」,也是劉子超七年前的遊歷之地。
中亞地貌壯觀,歷史厚重,文化燦爛,故事動人。他倆在書中都展示了所到之處現實經濟社會狀況和自然人文景觀,追述歷史事件、人物,聊發思古之幽情,更多是當下之思考。兩者內容各有側重,論作者的心氣,作品的藝術性、思辨性,在伯仲之間。
彭英之的自序,提及英國人愛德華·吉本當年坐在古羅馬遺跡中沈思時產生的沖動,激勵他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彭在絲路旅行期間,也曾試圖找到讓他決心寫一本書的時刻。「在這一場不停向西的遊歷結束之前,我已經決定為這條名為‘絲綢之路’的古路留下一份屬於當代的記錄」。
劉子超說,旅行文學要「以精致的文字書寫異域」。文學作品的文字表述風格不同,都應該是「精致」的。劉子超強調這一點,旨在將旅行文學跟「旅行攻略」、旅行記錄「流水賬」相區別。
與【失落的衛星】相似,【絲路北道】文字之精致也並非仰仗華麗辭藻,而是憑借觀察力和文化底蘊,融敘述、描摹、抒懷與議論為一體,貌似平常的話語中顯露微言大義。筆者在閱讀這份「記錄」的過程中,油然感覺到:「精致的文字」每每透過各種對話留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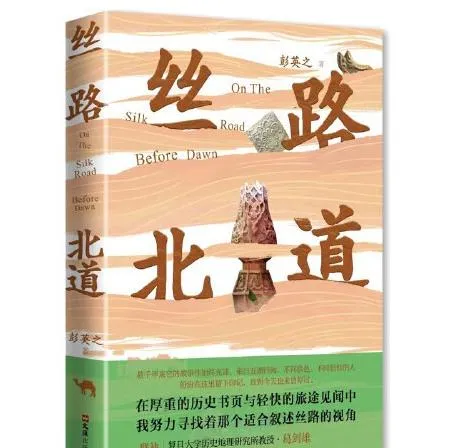
這裏所謂「對話」「交流」,英語中communication可作其對應詞,emotional communication指情感交流。旅行文學中的對話和交流大致包含旅行者與山川對話,與人文景觀對話,與當地人對話。
【絲路北道】中的對話、交流內容豐沛;值得一提的是旅隊內部的交談溝通,為一般旅行文學作品所罕見。限於篇幅,擷取少量例子為證。
與天山雪峰「神性」的交流
在劉子超的書裏寫到他遇見的一男一女兩位來自瑞士的大學生,他們來到「中亞的瑞士」吉爾吉斯作「文化之旅」,他們覺得這裏的天山比艾爾卑斯山更「野性」,像幾倍年前的艾爾卑斯山,沒有房子,更沒有現代化的舒適裝置,但他們看到了閃山水之間的馬群。

吉爾吉斯境內的天山,選自【失落的衛星 深入中亞大地的旅程】
彭英之對精靈所言「吉爾吉斯的山是最棒的」,起先並不很以為然。但當他近距離見到天山雪峰時,不由得與曾經相遇過的乞力馬紮羅山、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安第斯山脈作了比較:
「……吉爾吉斯北部的天山雪峰要隨和得多。它們在草甸前一字排開,溫和坦誠,無處不在,像睿智和藹的長輩,什麽困惑都可以說。」
擬人化修辭延續到進山後述寫的感懷:
「我抑制不住內心的贊美,甚至帶著剎那間的虔誠……這或許是大山的氣場。當你擡頭看著山,山也低頭望著你。這份凝視沈重而安靜,叫人不得不將被瑣事扯到支離破碎的靈魂重新擰在一起才敢應付……」
這不就是八百多年前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中「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當代天山雪峰版嗎? 「野性」「隨和」,蓋因比較物件不同而見仁見智也。
著名作家陳丹燕在其【我的旅行哲學】(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中指出,在大山大海中,人與自然處在自然本源的秩序裏,自然的壯麗與嚴酷並存的本色及其豐富性,會自在地呈現,「能治愈人類心智中的委頓與迷茫」。她把這種「治愈」功能稱為自然的「神性」。彭英之對天山雪峰的感受,乃是對「神性自然」的一種演繹。
中國古典文學中,不只是散文,在詩詞中相似的案例也不勝列舉。如李白【獨坐敬亭山】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杜甫【青山】的「我問青山何日老,青山問我何時閑……」句,都可作如是觀。「神性」無疑是作者所賦予的,他們以自己的情感、思想,發掘了自然景觀蘊含的人文精神。彭英之體會到了一直在身邊的大雪山簡直是「仙境」,天山是吉爾吉斯的靈魂,書寫時便多次對它「賦能」。
情感互動在碎葉城遺址與撒馬爾罕
古代中亞先後出現的汗國、帝國,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漢唐時期的中國與這一地區有過不同方式的交集。整個19世紀,英帝國和沙俄在中亞的 「大賽局」,是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歷史樣本。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絲綢之路,銜接歐亞大陸中部不同地區。它不是一條具體的路,而是「一整套貿易道路網路」,當年,「像一條大動脈為不同地區的文明提供新鮮血液」。
星轉鬥移,天災人禍,中亞地區的歷史遺址保存得不如人意。當地政府致力於建造博物館以搜藏、展示歷史遺跡。中國遊客到訪吉爾吉斯,地處絲綢之路兩條幹線交匯處的碎葉城遺址總是要去憑吊的。漢朝在碎葉設立西域都護,唐朝經營西域設「安西四鎮」,管理該地區軍政事務,碎葉是其一。

碎葉城遺址
在彭看來,「盡管學界不能認定李白生於碎葉城,但這不妨礙國人把思念寄托在這座異邦城市身上……」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座後來落入異邦的名城,早已融入大地,遺址只是土堆,內城僅剩地基。此刻,彭英之覺得天山「不僅看著我們,還看著我們腳下的廢墟,似乎在告訴我們它掌控著一切興盛淪陷」。
無奈、沈痛,心情似南宋時黃機站在長江邊北望淪喪的國土:「草草興亡休問」(【霜天曉角·儀真江上夜泊】)。然而,當轉頭看到中國使館的「幾位同胞走上遺址裏的小山坡,同樣帶著期待,做足想象」。他舒了口氣,「有中國人在,碎葉總不會太寂寞」!
離開碎葉遺址,旅隊的小車向山裏急駛,彭的思路繼續勾連著歸於塵土的「足跡和故事」:
「遺忘本是宇宙的常態,記憶才是奇跡般的存在。但擁有長情的記憶正是人類與其他動物間最不同是地方之一。在湮滅一切碾壓萬物的遺忘面前,與過往建立聯系的努力好像無邊黑暗中的熒光:微弱,但頑強,仿佛意見最有人性的掙紮。我越來越覺得,‘原來你還記得’是這樣動聽的情話。我拿出筆記本,記下眼前的情景,留下那些撲閃的微光。」
長情的記憶微光仿佛也在我眼前閃爍,我想:無奈和舒心,都不應僅視為作者的自嘆。所有當年與碎葉城有交集的先輩,一定正在聆聽這位21世紀中國青年的傾訴,為他的這份感慨而欣慰。
有2500年的歷史的烏茲別克第二大城市撒馬爾罕,是古代帖木爾帝國的首都,「古絲綢之路明珠」。現在是中亞文化重鎮、旅遊勝地。

烏茲別克撒馬爾罕的列吉史坦廣場
【絲路北道】用了四章的篇幅,介紹了中亞最古老城市之一撒馬爾罕古往今來的事與人。城裏恢弘的列吉史坦廣場的「形狀由三座傳統高等學院主宰」。「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座中心廣場邊的建築是學校……」。列吉史坦廣場「或許從一個側面解釋了這座城市在歷史上的光環,也解釋了為什麽它能讓路過的旅人不自覺地感到渺小」。
作者認為帖木爾「是個不輸於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的征服者」,「他一生未嘗一敗,殺戮無數」,但他對本國的文學藝術家「無比寬容積比重視」,撒馬爾罕的建築「就連痛恨他的敵人都不能不折服」。內戰和征伐使撒馬爾罕失去了中亞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它作為世界級歷史文化名城,使彭英之們為之傾倒,以至朱總都臨時抱佛腳,聚精會神地讀起了【孤獨星球】雜誌中亞特輯裏的歷史部份。
「建築可閱讀」,撒馬爾罕的廣場和地標讓他們不由自主地融入了這裏的文化。老城裏建築物的不同藍色,因「它歷史的氣質散發著近乎金色的光芒」。城郊的皇陵又一次讓他們感嘆不已:「這裏沒有絲毫哀愁,卻有說不出的溫馨和靜美」。「從未見過生死界限如此不明確的長眠之地」。「橙色的光籠罩著一切,把我們也納入了他們的時空……」
「不自覺地感到渺小」「納入了他們的時空」,凡此種種心緒,不就是旅人與景觀的情感互動嗎?
地毯店裏與織毯人的心靈交流
中亞地廣人稀,從無人機視角看來,「……人是見不大到的……大山、大水、大沙漠和人造地標,雄偉高大,像歷史的骨骼,構成一切故事的背景框架。」「但它未能記錄到多少個體」。「個體」即人,構成了「絲綢之路血液和肌理」。 當地人的生存狀態及與他們的交流溝通,是【絲路北道】重要的「記錄」物件。該書正文後附有「人物索引」,這在旅行文學作品中還未曾見過。其中出境前後一路上打過交道的當地人有名號的共20個,有一位是地毯店店員薩爾多。
烏茲別克的布克斯奧羅,也屬中亞最古老城市之列,彭英之帶了幾位旅伴在一家地毯店做成了幾筆交易。他記錄的不只是砍價和付定金,地毯店模樣、店員薩爾多的外貌與做生意的老成相,顧客對地毯的辨識、鑒賞,薩爾多與他們聊起「想去中國看看」的願望……顯現了異域文化和常人心理。
「薩爾多是店內唯一站著的人,其他人慢慢匍匐到地毯上,都叫色彩迷了眼……不同粗細的手指慢慢劃過地毯的表面,順滑地畫出弧線,碰觸著成千上萬個線結。那些線結是一個素未謀面的人花了好幾個月的生命打出來的,背後隱藏著另一個時空的喜怒哀樂……使用者的指尖能夠觸碰到創作者觸摸過的同一個點,兩個陌生的生命間就此形成一種奇妙的聯結。」
與薩爾多是語言的交流,匍匐到地毯上觸碰其線結,是與織毯人的心靈交流。
旅隊內部隨時隨意的閑聊
2015年,彭英之的同窗和後來的同事耐森與他開始謀劃這場中亞之旅。耐森是個學了多年中文和中國文化,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他對中國文史的了解,勝過他的華人太太。耐森在工位上給一直對中西亞歷史文化「極度癡迷」的彭英之發了份提議中亞之行的信件,措辭近乎謙恭。
彭對這一提議「喜出望外」。次日,半睡半醒的彭在手機上看到耐森發來的「自駕可行性調查」和一些具體設想時,「贊嘆不已,想到既然他把寶貴的周末拿出來做研究,我就可以放心偷懶了。於是我放下手機,毫無羞恥地睡了回去」。
耐森的紳士風度和處事認真的品格,彭對同事的信任和欣喜中自嘲的灑脫,都躍顯紙上。我對他倆的第一印象,在後文中發現獲得了他們旅伴的共情。隊員小葛說,跟彭英之出來旅遊「會不知不覺接受很多新事物」;「我一直覺得耐森是我們這個旅途裏最大的gentleman……」彭問:「你倆要不要擁抱一下……」「他們勾肩搭背地碰了一下,耐森開懷地笑了」。

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新華社
旅隊十一個男女青年的文化背景不同,行為習慣無疑會有差別;他們中多數人過往的旅行體驗都來自已開發國家,對中亞相當陌生,他們的觀感會不一樣;陸路行很辛苦,有可能身體不適、心情焦慮。彭英之是旅隊內部的「融合劑」,不時鼓勵、啟發大家「多聊聊」,這個「小社會」內部相互關心,樂於記錄這個「小社會」內部隨時隨意的交流和觀念碰撞。
有位在共享單車公司工作的朱總,是虔誠的行者。他在旅途中不時透過手機處理業務,讓旅伴感到不解:「他是在休假呀!」朱總開電話會,「在電話裏談論著效率,談論著策略,談論著一些宏大的目標,看上去是世界上頂頂重要的事。
天山在他背後一聲不吭,風呼呼地吹,野草發出共鳴,感覺馬上要召喚出一些在這萊恩排過大事的人,可旋即又悄然停息」。對如此「永遠在工作」的狀態,作者借風和野草的動作,表達了隊友們對朱總的調侃。這段描述既可看作自然與人的交流,也可視為隊員間的對話,兩者水乳交融,樸實而內建幽默。
此行最後一站是土庫曼的阿什哈巴特,在這裏旅隊成員將各奔東西,回家或另赴他國。分手前,大家談論最多的一是依依不舍之情,很溫馨;二是走了這些國家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裏,以及遭遇的趣事鬧心事。

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特的獨立柱。新華社
對此,彭英之感喟良多,他寫道:「能夠走進他人生活並且分享一場獨特記憶的,都是宇宙以某種極細微的機率牽上的線,能遇見這些人對我而言,無比珍貴。」年輕人因孤獨感而對漫長旅途中的相遇深感慶幸和珍惜,我完全能理解。
錢鐘書的【圍城】借趙辛楣之口說過一段廣受讀者稱道的話:
旅行最試驗得出一個人的品行。旅行時最勞頓麻煩,叫人本性畢現。經過長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討厭的人,才可結交做朋友。
【絲路北道】中,旅隊成員一路上的communication,生動地印證了錢先生的這句名言。
久蓄氣芳始得精致
錢谷融先生在詮釋「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時強調,文學作品應該富有情致和詩意,能夠激起人們的某種憧憬和向往,文學的這種詩意美的來源,是「對人的信心」。
旅行文學當然也不例外。
旅行文學不僅僅是景觀的描述、考古成果的介紹或地理的踏勘,它更需要記錄本文提及的人們在旅途中的各種對話與交流,揭示、描述、探索多層面的人性。唯其如此,才能達到關懷人、關懷人性,透過具體的審美形態表現人性的各種情感,並以此來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品質這一文學的核心目的。
旅行文學沒有時效性要求,作者有足夠時間對資訊作後期處理,在客觀事實中融入由表及裏由此及彼的主觀思考,並以想象加持。如資深媒體人邵寧在【不帶相機去旅行】(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中所言:「旅行筆記,必須在一個閑暇的時刻,在一個安靜的角落,提筆書寫。這時,經過沈澱之後的印象、體驗,才會慢慢浮上心頭。」
彭英之懷著已有的閱讀所得,在絲路北道上行走,身不離筆記本,在遊歷中溫故知新,歸來5年之後【絲路北道】方告殺青。之前五年裏,作者審視整理旅途筆記、視訊,重溫相關典籍,透過網路繼續搜尋新材料。寫作是他再次遊歷這條通路,並「不斷感受到它無窮大魅力」的過程;是他更深入地觸碰到了那些活在絲路歷史和現實中的人,透過他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過程。所有相關資訊經過篩選沈澱、發酵,久蓄氣芳,文字方臻「精致」,審美價值更大,認知功能更強。
精致的旅行文學,除了在人們閱讀文本時起到審美、認知作用,還能為旅遊業提高服務品質、遊人養成對話交流意識帶來啟示。
郁達夫有詠西湖詩雲:
樓外樓頭雨如酥,
淡妝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蘇。
雖然傳媒已從「讀圖時代」進入短視訊稱霸的新階段,但精致的文字仍然有著照片、視訊無法替代的功能。希望有更多大眾喜聞樂見的旅行文學作品誕生!
作者:青山
文:青山編輯:郭超豪責任編輯:邵嶺
轉載此文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