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观经过周秦及汉初的几次实质性转变之后,至汉武帝时成为了汉王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董仲舒在【春秋】的公羊学诠释中,将「奉天法古」与成为圣人紧密结合起来,使这一理想化的政治图景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实际政治中的国君可以成为儒家理想中圣人的模样,若非如此,则天会以灾异的方式予以谴告。

在董仲舒思想中,圣人与先王等同,现世的国君亦为圣人,若背离圣人之道则会受天谴以改正之,或者另立「新王」予以取代。董仲舒把「【春秋】之道」概括为「奉天而法古」,继而得出「圣者法天,贤者法圣」的成圣准则,从这一角度来看,【春秋】的编写目的就是为后王提供思想行为上的借鉴,使之向圣人接近。
「奉天」与「法古」,表面上为成圣的两条通道,其实质还是指向「奉天」,因为「法古」所效法的仍然是「先王之遗道」,而「先王之遗道」同样源于「奉天」。

公羊学与汉初政治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导,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加上整体的文化环境较差,儒学发展缓慢,儒者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黄老思想虽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但外戚和诸侯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匈奴对北部边疆的侵扰并未根绝,公羊学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彰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力,适时地突显出了自身的实用性,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
【公羊传】和【春秋繁露】是公羊学推进中出现的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对【春秋】笔法的探讨极为深入,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经战国齐地学者再度阐发后,于景帝时著于竹帛;后者从理论的角度指出了孔子寓于【春秋】中的「笔法」,使公羊学达到了理论上的成熟。
此外,【公羊传】的思想突显出战国称雄时代,学者们希望以「文王之正」来实现大一统的理想政治格局,而董仲舒的理论阐发则是在统一政权已经形成的背景下进行的。

公羊学的形成
【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以口授的方式传播,「【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最为根本的原因可以视为「免时难」。

值此之故,对于【春秋公羊传】的源流,经学史上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纬书认为源出子夏,「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何休解云「孔子至圣,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
董仲舒以为源出孔门诸弟「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此外还提及子夏、世子、子池、曾子等人。

在这里,纬书和董仲舒将【公羊传】的作者指向了孔门弟子。但蒋庆否认了这一说法,「从学理上推之,【公羊传】必为孔子所作。孔子自作【传】以解释【春秋】之经,【公羊传】当是孔子自传」,并进一步列出缘由,概而言之,一为【春秋】深奥,实非一般人所能知,二是形式上的一问一答类似于原始的课堂笔记,三是【春秋】诡其实、变其例,除孔子本人外无人可知晓。
蒋庆认定孔子作【公羊传】的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若果真为孔子所作,就不会以此来命名,提及的三点缘由也多臆测之辞,正因为【春秋】深奥才有了后来的【传】和对【春秋】义法的阐释,而一问一答的写作体例并非单见于【公羊传】。

战国时的诸子已经参与到【春秋】的解释与传播中,「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当为最早的两部公羊学著作,翻检二书可知,【春秋繁露】所提及的经师不曾见于【公羊传】,反之亦是,二书几无重合之处。

虽然公羊学传授谱系的记述相对清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生都著于竹帛」。
但这一说法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徐复观直言其为凭空伪造,「只是出于因【公羊】、【左传】在东汉初的互相争胜,【公羊】家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来,以见其直接出于孔门的嫡系单传」,黄开国解释为「【公羊传】的得名始于公羊寿与胡毋生将其著于竹帛,公羊寿与胡毋生有师生关系,胡毋生尊其师,而著名为【公羊传】」,并进一步认为「【公羊传】并不是公羊氏的家学相传,而是战国【春秋】齐学的传本。

在战国时的齐地,无论是【春秋】学说的口传,还是文本的传承,【春秋】齐学都应该有一个较为公认的版本,而这个版本数代相传,并不断得到修补」,这一解释也印证了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对【春秋】义的阐发。
将【公羊传】看作战国【春秋】齐学传本的说法,符合齐地的学术品格,也同公羊学的内在理路相一致。「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陈丽桂认为齐地的地域环境因素决定了齐学的两大特点,即「能深思,多智谋」和「荒诞的遐思」,这里的「智谋」与「荒诞」可以视作是对先秦正统或原始儒学的突破。
公羊学的一大鲜明特点就是反对君主制度的绝对性、永恒性和神圣性,公羊学家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时就十分明确地把王置于天之下,将天和王进行了区分,所主张的三世学说和大同思想也是彻底否定了君主制度的永恒性。

与思孟学派的心性儒学相比较,公羊学更加关注现实政治,公羊学的核心理念和论述目的并非成己成德,而是指向政治领域的改制立法。
汉初的公羊学
刘邦在掌权初期并不认同治经儒生的存在价值,「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对劫后余生的儒家经学也是幸灾乐祸,「吾遭乱世,当秦焚学,自喜,谓读书无益」,直至叔孙通制定朝仪后,才意识到儒学的重要性。
汉初政治虽多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尚清静无为,但公羊学的势力也在逐渐增强,鲁地两位儒生对叔孙通的指责和辕固生、黄生对待汤武革命的态度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汉五年刘邦废除秦朝的繁苛礼仪后出现了下不尊上的乱象,叔孙通适时提出与鲁地儒生共制朝仪以显现皇权尊贵的建议,获得刘邦许可。

叔孙通在鲁地征召的过程中遭遇了两位儒生的批评,「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儒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叔孙通个人品质的怀疑和否定,认为他以阿谀奉承的方式获取政治权力,丧失了儒者的品格;二是「起礼乐」不合时宜,依照旧传统,礼乐的制定是在「积德百年」之后,而不是在政权草创之初、生民未养之时。

叔孙通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两位儒生是「不知时变」的「鄙儒」,最后依然和其余诸生共同商定礼乐。显然,这两位儒生是以个人的德性和对寻常百姓的关怀为出发点,去看待制礼作乐这一事件的,力求「合古」。
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其余诸生则更加倾向于制度的设定和皇权的维护,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注重「时变」,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就具有了一定的公羊学倾向,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学才能够登堂入室,逐渐获得政权的认可。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件是辕固生、黄生在看待汤武革命上的分歧。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在于「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为?」。
他否认汤、武革命的合理性,明「上下之分」,臣子的天职就是匡正、辅佐天子,若天子失德败政,臣子也难辞其咎。辕固生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认为汤武诛伐桀纣是民心所向,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争权夺利,完全肯定了汤武革命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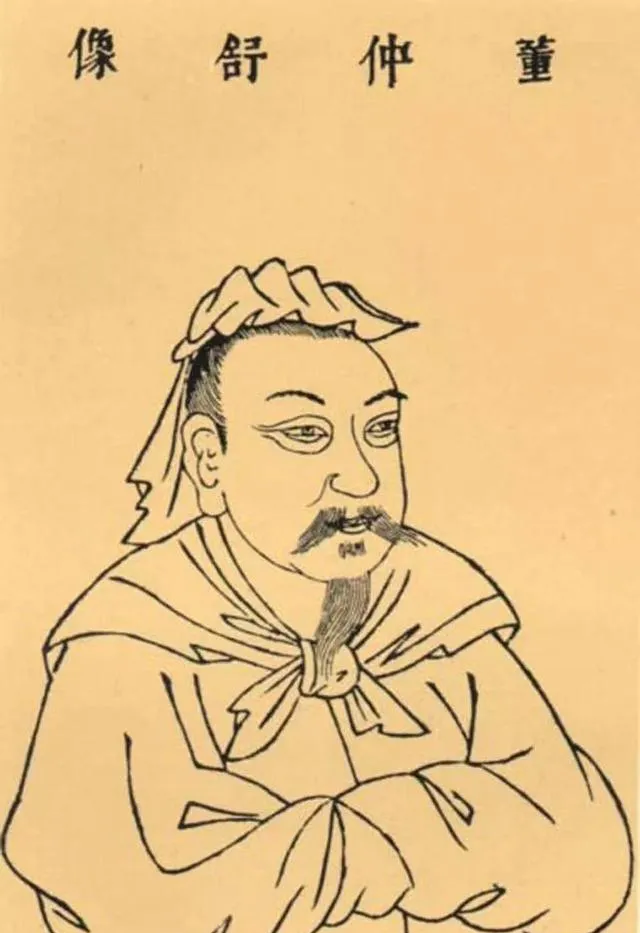
虽然黄生、辕固生都是从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出发去评论汤武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但黄生侧重于相对保守的现存秩序维护,而辕固生则从民心所向、天命论的角度论证了西汉政权的合法性,与公羊学的思想完全一致,以最为直接的论争方式将公羊学思想引入景帝的思考之中。
上述两例中出现的「合古」与「求变」、维持现有秩序与建立新制度,一则偏向于传统儒学,一则偏向于公羊学,就表面上来看,公羊学有着「背离」【春秋】主旨的意味,因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提倡复古、反对变革、效法先王是【春秋】对于世事的态度。

待公羊学理论成熟后,这一看似矛盾、对立,与【春秋】主旨相「背离」的论述,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在公羊学家眼里,「新王必改制」并非是「改其道」、「变其理」,而是「顺天志」以「明自显」,就是顺从天的志向来标识自己受命于天。
当然,公羊学思想在汉初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过很大的阻力,喜好黄老的窦太后因辕固生视【老子】为「家人言」而「使固入圈刺豕」,反对武帝任用喜好儒学的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以及儒生赵绾、王臧,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迟滞了公羊学的推进。
建元六年(前 135 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对策,置五经博士,就此推动了公羊学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因他的著述和思想对汉代政治产了重大影响,被司马迁、班固赞以「唯董仲舒明于【春秋】」、「为儒者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