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远亲不如近邻。可大部分时候发生矛盾就是在邻里之间最常见。
古训曰:穷不失志,富不张狂。但有的人偏偏做不到,感觉比别人强点就「天王老子老大、他老二」了,说话从来不考虑后果。
玉润村是坐落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同是李姓的占90%,其中有几个单门小姓据说是村上老姑奶奶寡居后,其后代在姥娘家繁衍扎根的缘故。
因为祖辈有着丝丝缕缕的血缘关系,说起来还都是亲戚,所以村上倒也没出现过所谓「欺生」的现象,但各人有各人的脾气秉性,虽然不在一口锅里吃饭,可也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时候,这其中就有李贵贤和何文昌两家。
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李贵贤家世代为农,除了认识钞票,那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何文昌是「老三届」毕业生,后来在村中学当教师。
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偏偏是邻居,经常一言不合就「抬杠」,谁都不服谁,被村里人戏称为「蜈蚣见不得鸡」。
下面就听听李贵贤叙述他们两家人的故事。

口述人:李贵贤 74岁 农民
其实我这辈子不愿跟人结冤作仇的,除非遇到那种不讲理的斤斤计较之人。
我们村虽说不大,但民风淳朴,尤其是在大集体时候,真的可以讲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
因为村里人往上推两三代,都有拐弯抹角的亲,相互间称呼最多的就是「表叔、二大爷」,所以没有啥大的矛盾发生,即使有啥摩擦,村长三句两句一调解,很快就和好了。
但也有另类,就是那种自命清高、好为人师的人,而我的邻居何文昌就是。
每次我跟何文昌发生口角后,我心里就迁怒我父亲,想当初我们哥四个分家,他偏偏将我的房地基分到村最东头,不在村中心不说,关键给我「配备」了何文昌这样「烀不熟、砸不烂」的难缠之人!
何文昌比我小2岁,他本来不是我们村的人,印象中他父亲没了,在他十多岁的时候跟随他母亲投奔他几个舅舅来的,后来就在我们村扎根了。
因为何文昌有四个舅舅,他们兄弟几个在村里也是「一踩地乱晃」的人,所以别看何文昌是孤儿寡母,但在村里一点没受到委屈,因为有几个舅舅「罩着」呢,村里老少几代人都统一称呼何母叫「老姑奶奶」。

老姑奶奶一辈子性格很刚强,她身上缺少老人该有的慈祥,估计跟她年纪轻轻就守寡有关系。
女人身后没有男人保护的时候,都习惯把自己伪装成「刺猬」,这些当然可以理解。
可话又说回来,刚强可以,但不能不讲理。当年老姑奶奶跟我们家做邻居时,因为家禽家畜乱跑,经常跟我妻子呛呛,从而发生口角战。
有一次我家有只下蛋的老母鸡经常不趴窝下蛋,我妻子跟踪发现,原来这只老母鸡每天只要从鸡笼里放出去,肯定是拍拍翅膀顺着两家的过道,就从何文昌家院门那个洞里钻进去了。
原来,何家有只大公鸡,都是它把我家这只老母鸡招摆过去的。
那天我妻子就蹲守在何家门口,看到老母鸡进了院子,终于在鸡窝里逮了个「现行」。
当我妻子把老母鸡从老姑奶奶家的鸡窝里拎出来时,老姑奶奶和她家儿媳妇婆媳俩追着跟我妻子吵。

俗话讲:打架没好拳,吵架没好言。那天也怪我妻子说话不中听,本来是自己家的鸡硬是往别人家跑去下蛋,怎么能怪别人呢。
但妇女吵架都是「一塘荷叶拉的满塘转」,吵着吵着就不是单纯的鸡丢蛋的事了,把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抖搂出来,什么哪天把牛拉到田埂上吃了一溜秧苗啦,什么晒在墙头上的红薯藤少了一大半啦,等等。
我一开始是在家没出来,可她们越吵越厉害,引的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作为一家之主的我,自然要出来调解一下,可谁知道被老姑奶奶一通呲哒,她指着我的鼻子训斥道:「人家都是‘当面教子,背下教妻’,你倒好,任由你家这个不讲理的婆娘出来乱嚷,现在才出来装好人!」
我闻听可不乐意了,凭啥不分青红皂白连我都凶,所以我回怼道:「你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就这一句话,可捅娄子了!老姑奶奶一下子瘫坐到地上,又是拍巴掌,又是诅咒,说我骂她了!但我认为我没骂人。

可能是看我们两家人闹的不可开交吧,有人就跑到离村不远的学校送信去了,不大会儿何文昌风风火火的赶回来了。
看到他母亲坐在地上,何文昌赶紧上前把老太太搀扶起来,愤怒的盯着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欺负老人和妇女你不觉得脸红吗?」
但我不甘示弱,我就说是老太太不讲理。
看到自己家儿子回来了,老太太又哭诉上了,说我骂她是猪。
我辩解说猪和猪八戒是有区别的,我没有骂人。
好不容易何文昌总算听明白过来了,他劝她母亲道:「妈,这种人别跟他一般见识。老话不是讲嘛,‘三代不念书,等于关一院子猪’!」
很明显他嘲笑我没文化,不单单把我骂了,连我我们家老少几代人都顺带骂了!叔可忍婶婶不可忍,性情暴躁的我上前就给何文昌一拳,他头一偏,正好打到他鼻子上,顿时血流如注……

那天确实是我先动手的,何文昌也是挂彩了,但我知道他少年时期就是「沙鼻子」,动不动就流鼻血,其实我下手不重,而且也就那一拳。
但老姑奶奶不依不饶,她跑到村干部那告状,让他们要主持公道。
最后没办法,为了息事宁人,我只好跟妻子俩拎了20多个鸡蛋,登门给老姑奶奶和何老师赔礼道歉,就这样这事才算过去。
但从此两家人头碰烂了都不说话,正如老话说的那样:被虎老蛇咬了,毒气在心里。
所以我们这邻居各的,就像是「仇人」,谁也别想帮助谁:我们家电线断了,明明何文昌会接线,他看到电线耷拉下来也不管;暴天下雨了,何文昌家平顶房上晒棉花,何文昌不在家,就他媳妇一个人在家爬上爬下浇的浑身湿透,我坐在屋里也不想帮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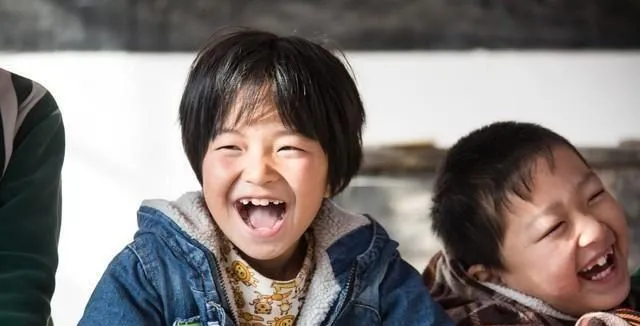
再说说我们两家的下一代读书的情况吧。
我家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能天生就不是块上学的料吧,这几个孩子除了上学成绩不行,其他方面也是玲珑剔透的,有时候我也是真着急,自己就吃了没文化的亏,总希望他们有出息吧。
可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是有区别的,就好比挑200斤重的担子走上坡路,虽然累,但咬咬牙也就上去了!
但读书不行啊,书拿到跟前,它们认识你、你却不认识它们也是没办法。
就这样,我家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读到初中毕业的,女儿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可何家两个儿子就不一样了,每天放学回来就往屋一钻看书,根本不像村里那帮嘎小子们追出打闹淘气。
结果人家两个不吭不哈都上了县一中,先后都上了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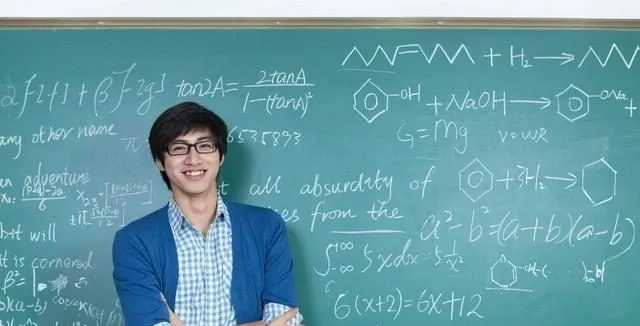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关键就是看孩子发展的怎样,这一点我跟何文昌比自叹不如,但我想的开,不钻牛角尖,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既然走读书这条路行不通,我就早早让三个儿子学手艺,其中两个木匠、一个瓦匠,我们家后来盖的楼房就是三个儿子带着他们一帮师兄弟完成的。
我是知足常乐的心态,可何文昌却处处拿他儿子的成就故意显摆,尤其是人多的地方,看他每次端着水杯,摇着蒲扇,摇头晃脑的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我就来气!
更可恶的是他倚仗自己每个月几千块钱工资,一到农忙时倒背着双臂在村口大道上溜达来、溜达去,看到人就故作关心的虚情假意道:「别干了!这么大年龄了还那么累干啥?儿孙自有儿孙福!」
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话?农村人没有养老金,只要有一口气都舍不得歇着,他这纯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每次大老远看到他来,我宁愿挑着担子绕道走,也不跟他碰面!

老话讲的好: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何文昌妻子兰英也是个呱呱叫的女人,当初跟「小脚婆婆」老姑奶奶也有矛盾,这婆媳俩一争论,何文昌简直就是:老鼠钻风箱____两头受气。
后来老姑奶奶去世后,他们家的日子总算消停不少,可那个兰英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何文昌每个月有好几千块钱工资,但兰英也舍不得歇着,自家地少,她就去开荒种些五谷杂粮,可开荒地都是公家的,有时候别人家的鸡鸭进地了,她也扯着嗓门大呼小叫,惹得村里很多人背后都埋汰她。
就是这样有福又要强的女人,也敌不过命运的安排,在她58岁那年,大清早在地里摘绿豆时倒在地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被路过的人发现,身体都僵硬了。
现在虽说都是火化,但也有石棺,而且也安排8个「抬重」的人,而我每次都是村里抬重人之一。
都说生死不记仇,逝者为大,我也准备好参加「抬重」,可结果这个何文昌居然重新找人,也不找我这个邻居!
为这事我气的几天心里都不舒服,老伴就劝我道:「你真是神经!为别人家的豆子炸碎了锅,何苦呢?不找你更好!」
就这样,我们两家无形之中又结下梁子。

何文昌老伴去世后,他那两年也老实低调不少了,因为后来学校合并,家里就剩他一个人,所以他干脆就住学校不回来了,因此我们俩更照不上面,有时候寒暑假听到那边院子里有动静,我看都不看一眼,把他当空气。
后来有一天我跟何文昌表弟遇到一起了,不知道因为说啥,居然把话头引到何文昌身上,听他表弟说,何文昌还有一个月就要办退休手续了。
这才让我想起来,我们居然都不知不觉的步入了花甲之年,时间过的真快啊,我跟何文昌不和也有十多年了。
何文昌退休并没有回到老家住,估计是他两个儿子不希望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吧,总之,到老有七八千退休金,肯定会受儿子儿媳们欢迎的。
至于到底享不享福,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很多人都「谈儿色变」,害怕儿子多了到老受罪,其实我用切身体会告诉你们:没有那么严重。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父母也就给了我三间土墙瓦顶的房子,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起步都一样,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孩子多的家庭,更是如此。
好在咬咬牙也挺过去了,我三个儿子都没念多少书,随后都自谋职业,连对象都是自己搞的,我们家孙子孙女好几个,但我和老伴早就放话出去:需要我们带,那就别心疼,送回到老家来,我们是不存在往谁家跑着照看的,路多踩不死草,别把我们累死累活的到时候还落埋怨。
所以我三个儿子也就老二孩子放在家时间长一点,后来上幼儿园都接走了。因为也就逢年过节儿子们回来团聚一下,所以不存在婆媳矛盾。
可能是我们家风比较正的缘故吧,她们妯娌之间也相处和睦,每年回来各家都给我们老俩口几千块钱生活费,老伴的衣服鞋袜都是几个儿媳包了,不夸张的说,相处的跟母女似的。
所以说,不要被社会不良风气带偏了,任何时候都是两好隔一好。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有段时间谣传说我们村要规划,很多家都偷摸的盖房子,等着拆迁。
我当然也跟儿子们传话过去了,问问怎么打算,后来儿子们都说,没必要把钱财往这上面投,有老房这个「老根据地」就行了!房多累主人。
我一听他们都想的那么开,那我就更不用操心了,好好保重身体,多享几年福是真的。
有一天我从地里回来,刚在水龙头下洗洗手,就听到隔壁院子有动静,我猜想:是不是何文昌这家伙回来了呀?这鼻子倒挺尖,是不是回来看看、打听拆迁消息的呀。
虽然各这么多年邻居,但始终不和气,他不搭理我,我还不想睬他呢,于是我就洗菜做饭,那几天老伴被女儿接走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等我吃完午饭,准备去村里棋牌室玩麻将。
我锁好院门就往外走,在路过何文昌家门前,看到一个人蹲在院子厨房墙根在抽烟,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原来不是何文昌,而是他的大儿子何欢。

何欢就住在省城,好像在哪个研究所工作,以前他妈妈兰英在的时候,他时不时的回来看看,但也不久留,最多吃顿饭就走。
而他弟弟何佳在深圳工作,我几乎就没咋看见过,据说何文昌一开始在小儿子那,后来不习惯那边快节奏的生活,又回到省城大儿子那。
可如今为啥大儿子回来了,他自己没回来呢?我有点纳闷,不过也不多想,回不回来跟我没多大关系。
我麻将结束时已经快5点了,那天手气不错,赢了十多块钱,够买两斤猪肉了。
当我刚进家门还没等喝口水,听到门外有人喊我名字,回头一看,是何文昌大表哥能兴大哥,而他身后跟着何文昌儿子何欢。
我有点纳闷,想着能兴大哥来了也正常,怎么何家大儿子也跟过来干啥?就是房屋拆迁,各家是各家的,也干涉不到其他人啊。
我一边想,一边笑着招呼他们,何欢紧走几步,从口兜里掏出香烟往我面前递,嘴里还喊着「表叔」。
我虽然跟他父母有点过节,但对他儿子我当然不能抱成见,何况伸手不打笑脸人呢。

不等我问话,能兴大哥笑着对我说道:「贵贤啊,跟你商量个事啊,」
我赶忙说道:「大哥你有啥事尽管说。」
「唉,这不何欢回来了嘛,是为他爸的事,上礼拜文昌表弟突然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好几天,但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估计也就这一半天的事了。」
能兴大哥语气沉重的说道。
我当时一听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文昌比我还小2岁呢,平时也没听说他有毛病啊,怎么突然会不行了呢。
我接着问道:「哦,真是想不到啊,有啥事让我帮忙就说吧。」
「贵贤表叔,我上午跟我家几个表叔去坟地那看了,我爸生前就有遗愿,说百年之后要跟我妈合葬。所以送我爸骨灰进坟地时,要经过你家那块玉米地,可能到时候要毁坏不少庄稼。」
我一听原来是为这个事啊,其实那块地当初不是我家的,后来农村不是又进行了二次分地嘛,何文昌老伴兰英坟地就在这块地的南头,如果到时候送葬的人多,那这片玉米不但碍事,还会被踩的东倒西歪。
我再看看何欢,只见他40多岁的男人,此时像个无助的孩子,眼巴巴的等着我表态,嘴里不断的说:「表叔,玉米能打多少斤,你说一声,我补偿你。」

听何欢这么说,我大手一挥,道:「什么钱不钱的!我现在又不是穷的不能混!这样吧,我明天起早就去把玉米秸砍了,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去忙你们的吧。」
何欢听我这么说,激动的说话都有点磕巴了,他不停的朝我作揖,嘴里说着「谢谢表叔!谢谢表叔!太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晚上打电话让老伴第二天早点回来,我们俩把一人多高的玉米秸砍了大概有5米宽的路,一直到兰英的坟头,还用三轮车把秸秆拉到路边,不能误老何家办事。
几天后何文昌的骨灰盒回来了,我自告奋勇组织了「抬重」班子,又帮着料理后事,虽然他有两个儿子,但年轻人好多老规矩不懂,而我现在也算是村里的老人了,能帮一把是一把吧。
其实邻里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就是一些鸡头鹅脚的琐事,和那不值钱所谓的面子!
看我这次一点没为难何家,村里人都夸我有格局。何文昌三天「完烟」后,他的儿子们也该回去工作了,何欢哥俩临走跟我道谢,还给了我一个用毛巾包裹的东西。
我们这白事是有回礼的,我当时也没多想。
结果等何欢他们车开走有十多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我接通后,听到电话里的人说道:「叔,我们走了,这次多亏您的帮忙!毛巾里有点钱,那是我和弟弟给你家玉米的补偿,谢谢了!」
我一听忙推辞着,但那哥俩说是应该的,让我务必收下。
如今我常常感叹道:
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之前我们真是太想不开了,为啥不能好好相处呢?只可惜时间不会倒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