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履不停】劇照
✎編輯 | 譚山山
2023年12月30日,在萬聖書園新店,舉行了「巨浪中的個體:歷史寫作中的‘小人物關懷’」主題分享會。
這是廣東人民出版社旗下的「萬有重力」出版品牌、新周刊與萬聖書園聯手舉辦的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分享會的第二場。分享會由萬聖書園主理人劉蘇裏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特聘教授趙世瑜、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擔任嘉賓。
「我對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非常感興趣,但最重要的是發現和理解形成這些思想、情感和行為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個人應對環境的方式。在我的書中,那些做決定的人、‘塑造’歷史的人不一定身居高位,他們可能是,而且往往只是碰巧出現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反映的是時代的光亮和悲歌。」
浦洛基教授如此闡述自己的歷史觀。在他關於人類命運的宏大敘事中,總有那麽一些重要的時刻,留給了那些無法留名史書的普通人。
時代的一朵小浪花,足以成為淹沒你我的滔天巨浪。幸運的是,有些人,在為我們記錄。
本文即摘自該分享會的對談記錄。

「巨浪中的個體:歷史寫作中的‘小人物關懷’」主題分享會主持及嘉賓(左起):劉蘇裏、趙世瑜、孫歌、宋念申。(圖/萬有重力 提供)
時代的巨浪與不確定的個體
劉蘇裏 :這個題目起得非常好。巨浪中的個體,講的是個體在歷史大勢當中的命運。「命運」,拆開看,是「命」和「運」。命沒辦法,爹媽把我們生下來,沒辦法改造,沒辦法復制;運就很玄妙,跟今天我們談的歷史節奏有很大的關系。孫老師雖然是研究思想史的,但是對個體在歷史中的命運,相信有長期的觀察。
孫歌 :2011年9月底,我去了京都,得以近距離觀察「3·11」核災難之後日本社會是如何擺脫創傷的。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做思想史的人都會重視本雅明的著名命題,即歷史只有在危機飽和的那個時刻,才會突然展示它真實的面貌。
作為只能存活幾十年的個體,我們都希望一生無病無災;但是作為思想史學者,我們必須意識到災難不僅是災難,也是一次近距離進入歷史的機會。怎樣抓住這樣的機會來觀察看上去很正常的那種生活方式當中的反常部份,這是我給自己確立的一個思想課題。
核能作為戰爭武器被發明,即便後來被和平利用,仍然攜帶了巨大的風險——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風險,還包含了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經濟的,甚至是人的各個層面的因素。【原子與灰燼】把核實驗和核電廠的事故放在一起討論,這是很有意思的排列方式:前者是戰爭,後者是和平利用,但是作者告訴我們兩者有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

攝於日本千葉縣,橫幅上書「核能是能源的未來」。(圖/Arkadiusz Podniesinski 攝)
劉蘇裏 :浦洛基的【切爾諾貝爾】,講到切爾諾貝爾核災難當中的小人物。趙老師是研究歷史人類學的,也叫社會史或微觀史。你是怎麽進到這個領域的?
趙世瑜 :我不懂核能,但是核能的利用或者一系列悲劇性事件,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行程中,不管相隔千裏還是萬裏,我們都會馬上有直接的感觸。
核危機給每一個人,尤其是受到災難損害的人的心靈和肉體帶來不可磨滅的創傷。這種創傷會帶來沈重的記憶。西方國家的歷史研究中有一個主題,專門研究創傷記憶。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在美國接觸過這方面的研究,最開始它集中在二戰後幸存的猶太人的苦難記憶。我們老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創傷記憶就是「後事之師」當中很重要的一點,但是我們做得很少,值得反思。
劉蘇裏 :宋念申老師是我定義的「中生代學者」,我們來聽聽就這個主題他想說什麽。
宋念申 :浦洛基的寫作方式讓我感覺特別熟悉。他寫的不是傳統的歷史研究作品,而更像是新聞寫作。【原子與灰燼】中,那艘日本漁船在比基尼核爆之前,船長一心想的就是,「我的網壞了,要多撈點魚,再多走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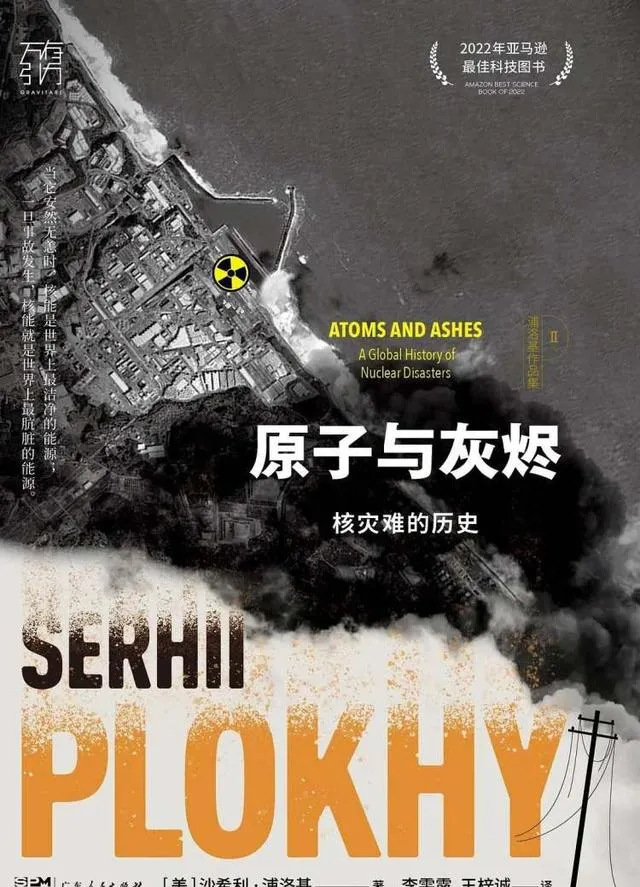
【原子與灰燼】(2023年10月版)封面。
2001年9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完全不知道三天後會發生什麽。「9·11」當天,我去看了冒煙的五角大廈,然後開始做街頭采訪。我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麽,我只知道我在經歷一件事情,這就是一個普通人正常的反應——在真正發生歷史轉折時的那種不確定性。
於是,我去學歷史。只有在歷史裏,才能體會那種經驗性的感覺給你帶來的東西。歷史寫作和新聞寫作,我認為是很接近的,都是站在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的基礎上去揣測事件發生前的結構是什麽樣子的。對於一個人文學者來講,把握不住的那種命運感比確定性更有魅力。
在歷史寫作中尋找普通人
劉蘇裏 :浦洛基跟史景遷還不太一樣。史景遷寫小人物,就是寫他們的故事;浦洛基是寫一個大的主題,把小人物放在其中展現他們的命運。
趙世瑜 :他這三部書和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化的歷史著作不同,它們非常像新聞采寫或者紀實文學,不是典型的歷史學家的作品。我相信這樣一種敘述方法一定是作者有意而為的,他希望讓更大範圍的群體——尤其是那些覺得這件事情離我們很遙遠,跟我們沒太大關系的人,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及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巨大傷害。
找一些根本沒有文獻資料的人群做研究,背後的理念是:在敘事可控的範圍內,盡可能不讓那些在歷史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或者經歷過重要事件的人,被歷史忘記。浦洛基的三部書中,除了提及戈巴卓夫、堅尼地、赫魯曉夫等重要人物,也提到了很多親歷者,消防隊員、逃難的人等,這在新聞采寫或紀實文學中常見,而在學術著作中是少見的。
今天我們的觀念、價值觀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關註重大事件、重大危機當中的那些個體,也包括日常生活當中的個體。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生老病死,這對個體來講都是危機。這些危機難道不該關註嗎?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
在重大危機中的體驗和日常危機體驗可能有很大差別。朱令去世,在座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我的好朋友談起這個事情的時候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無奈、無力,憤懣又沒辦法。這不是大事件,但今天有那麽多人在討論這件事,說明我們進步了。我希望這類事情能進入歷史學者的視野。

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圖/萬有重力 提供)
孫歌 :中國的歷史學傳統,一向是有面孔的、有人的。但近代以後學西方,歷史學開始社會科學化、非人格化。今天,在主流的歷史敘述裏可以看到事件、找到知識點,但是你沒有辦法找到歷史的不確定性裏若幹在場之人的感覺。
這三部書的強項就在於,它寫的是最嚴重的時代危機,但同時它有面孔——既有大人物的面孔,也有小人物的面孔。
我們在看歷史、看同時代各種危機時有兩個視角。一個是國家視角,那是傳媒、教養給我們的,也是我們用邏輯不斷復制、不斷再生產的視角。另一個是生活人的視角——作為小人物,人們面對的是生老病死這些具體的生存問題,掙紮在生存的困境裏面,他要活下去,他該怎麽辦?
浦洛基的作品中有一個細節,我在日本也強烈感受過——在危機來臨的時候,面對危機的人並不知道它來了。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提示,它有點像今天我們面對AI時的感覺:帶著一點興奮,覺得與己無關,又覺得有點危險。
第二個細節,科學家在面對核這樣一個無法完全掌控的能量的時候,是用三七開的邏輯來對待的。比如現場負責人在核危機來臨時,認為小劑量的輻射可以忽略。小劑量的輻射會置人於死地,但這些在國家視角裏是忽略不計的。

福島核泄漏區,被遺棄的教室。(圖/Arkadiusz Podniesinski 攝)
回到人的主題
孫歌 :今天所有人都認為核能源是安全的,核電廠只要建在海邊就安全。日本有個反核科學家叫小出裕章,到2011年為止,他任職於京都大學核物理研究所,但他一直反核。他說核電廠是「不修廁所的高級公寓」,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2011年之前,還沒有人知道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智慧,比如福島、福井這些有核電廠的地區的姑娘,很難跟東京的男孩結婚,家長不同意。老百姓不傻,他們只是不說而已。小出借2011年的核危機,把它說出來了。
小出後來說,60歲以上的人,吃點帶核輻射的東西問題也不大,因為輻射損害身體需要一個積累過程。他還提出了一個很不討巧的建議,建議商店裏能建一個60歲以上老年人專櫃,專門放那些被汙染的食材。
劉蘇裏 :周其仁說過,每個人都想喝新鮮牛奶,要原汁原味、好喝,還能保存一定時間,這件事以傳統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完成,然而大家又對添加劑有意見。所以這到底是廠家、消費者還是社會的問題呢?
孫歌 :小出是個誠實的科學家。科學思維的特征,即設定一個目標,之後向它不斷推進。但人文思維要照顧到人這樣一種多面、復雜的,有內在矛盾的生命綜合體,這跟科學思維是有矛盾的。小出的行為體現了科學思維的典型缺陷。

小出裕章。(圖/Wikimedia Commons)
當我們把科學意識形態化,強調必須用科學思維來主導一切時,其實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因為這意味著人在科學思維中要退居到邊緣。透過核危機及它牽引出的無數個相互矛盾的個案,我們獲得了另一個契機。
近代以來,科學被神聖化、絕對化、意識形態化之後,我們忽略掉了更為重要的——看上去拖泥帶水且不那麽光鮮的——和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另外一些要素,而這就是趙世瑜等學者在田野裏打撈的、小人物生命中核心的東西。當然,我並不是在挑戰科學,而是挑戰科學意識形態的絕對化。
宋念申 :歷史寫作要關註小人物,個體的視角非常重要,在主流歷史學界,這一點不需要再討論。近兩年來,這種寫作方式並不少見。以前主要在近現代史領域,因為材料夠,有底層人物留下來的日記、口述材料;像趙世瑜老師他們那樣,從鄉村的碑刻、家譜裏也能找出很多材料。作為一種方法,現在甚至追溯到中古史乃至上古史。
歷史寫作要尊重敘事的完整性。關註底層的話語,對國家話語而言是有效的補充。二者是一種非常微妙的共存關系,是相互構建的。
從【切爾諾貝爾】到【原子與灰燼】,浦洛基的關註點更復雜、更宏觀。核危機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延伸到孫歌老師所說的人類的現代生存問題。對小人物的書寫,它的目的在於揭示歷史裏更微妙、更復雜的層面。

【王氏之死】(2011年9月版)封面。
趙世瑜 :對於小人物關懷或者「巨浪中的個體」,國際史學主流並沒有太多分歧。但在中國學術界還是有挺大的不同,我自己就經歷了很多同行嘴上不說,但內心不以為意,或者覺得我標新立異。
而在2023年,我看到了變化。央視一套播出的一部考古紀錄片,在證明秦簡史料價值的時候選擇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魯西奇教授寫過的【喜】的故事,另一個是秦簡裏一封小人物的家書。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兒童的世紀】作者、法國學者菲利浦·阿利埃斯曾說,經濟史能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無聞的群眾是怎樣生活的。在法國學者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體的東西——巴黎街巷或者威尼斯市場的生活場景;一家人在廚房裏一起吃飯。布羅代爾透過這些東西來講食品價格等經濟學概念。
從學術上講,如何回到人的主題,依然任重道遠。就讀者來講,當他們無法共情,並把自己的經歷代入歷史作品時,也就很難理解作者所描述的那些事物。
劉蘇裏 :很多事情是這樣的,一定是文學家走在前面,準文學家走在中間,然後才是學者。近兩年比較有名的,像【張醫生與王醫生】【東北遊記】等,就是準文學家作品。學者呂途就「中國新工人」主題寫了幾部書,說明我們的學者已經意識到這件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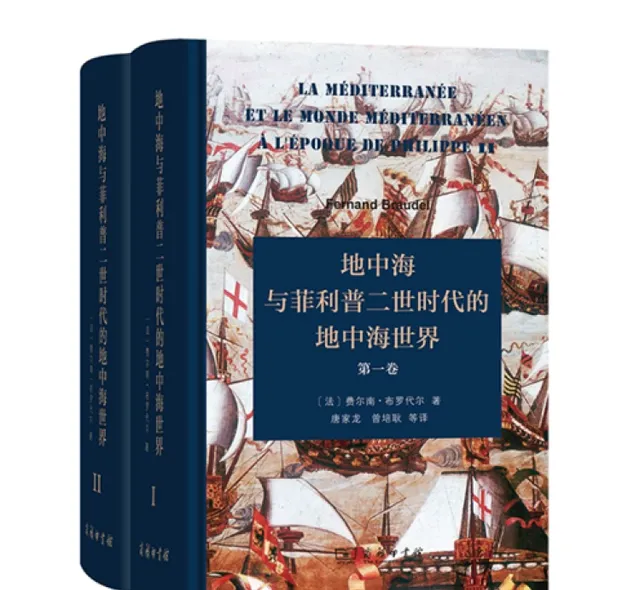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2017年1月版)封面。
小人物如何對抗時代的巨浪
現場提問 :趙老師提到「集體創傷記憶」,我們缺乏集體創傷記憶,也缺少相關教育。如果我意識到自己是巨浪中的渺小個體,想努力記住巨浪下的時代記憶,應該怎麽辦?
趙世瑜 :孫歌老師提到的日本科學家小出裕章,像他這樣的人很多。他一開始唱反調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後來會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我們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雖然不見得有他那樣的專業知識。
浦洛基給了我們一個提示。為什麽他的書裏能寫這些東西?因為他可以獲得的資料變得豐富了。過去為什麽資料少?除了技術手段、修史者的史觀問題,或者是孫歌老師講到的科學意識形態化問題,還有很多復雜的原因。
如今,透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小人物能夠發聲的機會比過去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不僅僅是記錄我們的一點一滴,也要記錄父輩的一點一滴。

「巨浪中的個體:歷史寫作中的‘小人物關懷’」主題分享會大合影。(圖/萬有重力 提供)
比如,可以給父輩甚至爺爺奶奶輩錄音,或者讓他們自己寫;很多家裏留下的老東西,不要隨便當垃圾廢品扔了。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人民公社時期,每一個人民公社的辦公機構門口都掛了牌子,某某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黨委等。後來國家文物局想搜集這種牌子,發現全中國只剩一個了——而在過去,全國可能有數以十萬計這種牌子。可想而知,我們平常會不經意地損失多少記憶。
我們需要多留點心,多帶些主動意識,去留下這樣的東西,記住這樣的歷史。未來因此可能會不一樣——不僅僅是每個個體會不一樣,甚至我們國家都會不一樣。
· END ·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 | 楊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