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棄的靈都
鄧曉芒
從表面的思想傾向上說,王朔和張承誌似乎是對立的兩極,前者是看破紅塵後與世俗同流合汙、痞,後者是堅持最徹底、最純潔的道德理想,是極端的純情。然而從精神實質來看,他們兩人卻有著原則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們都想完全無保留地使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與最底層的民眾融為一體。這與「紅衛兵精神」、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確是一脈相承的,他們使一種圖騰式的大眾崇拜帶上了大眾固有的痞性。
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種「民粹」意識,它歷來主張知識分子要懂得民眾的疾苦,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當年俄國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穿草鞋、吃粗糧、幹農活一樣,「五四青年」到農村去,60年代上山下鄉,「文革」的發動群眾、憶苦思甜,結果使知識分子不但大眾化、平民化了,同時也痞子化了。王朔難道不是知識分子、文化人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模範嗎?當代痞子文學只不過是首肯了這一方向,主張要想為民眾說話,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為地道的民眾,即最底層的痞話。一切社會都有痞子,但中國的特點是痞成為通行的規則(盡管痞本身意味著無規則、胡來、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時感到自己真正純潔,他回歸到了自然本性。張承誌同樣拒斥對這自然本性的一切文雅和教化的提升。
當代中國人的靈魂掙紮中左沖右突,最後總是回歸到了原始和兒童的純真。人們說,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動物。真是這樣嗎?非也!王朔把人的動物性的痞理解為純情,這無異於一種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為了動物,他會有種內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卻感到怡然自得,超然灑脫,自我欣賞,以為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莊和憚悅的境界。這只是一條自造的逃路,他的無出路正在於沒有異化感,沒有要擺脫非人狀態的內在沖動。人們又說,張承誌追求的是「清潔的精神」。真是如此麽?非也!
張承誌把人和動物之間的生存狀態作為精神保持「清潔」的條件,這種精神拒絕和害怕一切文化的發展與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這是一種停滯、倒退、心懷嫉恨的精神,一種遏制精神的健康發展的精神。他的無出路在於這種精神骨子裏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淪陷性。世紀末的中國人,要尋找的絕不是這樣的靈魂。
由此可見,王朔和張承誌所表現的,是痞和純情的兩種不同的結合方式。他們各自立於自身的立場,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和對方的立場已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各有自己尚不徹底、尚未看透的地方。真正看透了中國人的人心、人性的,是賈平凹,特別是他的【廢都】。
賈平凹80年代即以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在中國新時期文壇上雄踞一時,人們欣賞的是他在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文化味」。它是「地主的」,但卻是大地主,是其他一切小地方的發源地和根。它既不同於現代知識分子的浮光掠影的理想追求,也不同於對大眾生活的如實反映,而似乎是深遠悠久的歷史本身在現代發出的沈悶回音。他對歷史掌故、鄉土風俗和民間禁忌、國民心理的韻味和理路的熟悉程度及生動描繪,是超出旁人之上的。
然而進入90年代,他忽然有了一番深沈而痛苦的反省,想起「往日企羨的什麽詞章燦爛,情趣盎然,風格獨特,其實正是阻礙著天才的發展」,而自己已到了40歲,「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長官發財、吃喝嫖賭,那麽搔禿了頭發,淘虛了身子,仍沒美人出來,是我真個沒有夙命嗎?」他發現自己「幾十年奮鬥營造的一切稀裏嘩啦都打碎了」。於是,當他要在「生命的苦難中」、在這部40萬字的「苦難之作」中來「安妥我破碎了的靈魂」時,他便搶劫了以往的寧靜、雋永和娓娓道來的文風,變得慌亂而急促;當他下決心要切實地透過寫作來尋找自我、把捉自己的靈魂時,他看到的恰好是自己的失落,即失了魂;或者說,他發現原先自以為圓滿自足的那個自我只是一個假象,他的真我其實是分裂的——他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莊周還是蝴蝶了。
小說的主人公莊之蝶,曾經是一個真誠、純潔的青年,12年前曾與本單位一位女性景雪蔭戀愛,竟「數年裏未敢動過她一根頭發,甚至正常的握手也沒有」;後來另娶了一位名門閨秀牛月清。成了知名作家以後,在西京城裏地位極高,是文化界「四大名人」之一,市人大委員,人人都以能一睹容顏為快,真是如魚得水,要什麽有什麽。然而,正當他功德圓滿、輝煌燦爛之時,他卻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他看透了知識界文化界的無聊和空虛,識破了一切官樣文章和紙糊桂冠的虛假;但他並不像王朔那樣憤世嫉俗、倒行逆施,而是「大隱隱於朝」,逢場作戲、以雅就俗。
他深知自己早已喪失了一切理想主義的道德信條,但他無法起來指責任何人,因為這個社會的墮落也正是他自己墮落,他就是這個沈淪著的社會典型代表和「精英」。因為他唯一能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充當這個已經腐朽了的倫理體系身上的蛆蟲,尋求著這個封閉的實體上的裂縫和「破缺」,以維持自己那尚未被窒息的最後一點原始生命力;用孟雲房的話說就是:「一切都是生命的自然流動,如水加熱後必然會出現對稱破缺的自組織現象」。
當然,這種倫理體系上的「破缺」現象主要集中體現在愛情或性關系上。莊之蝶身為名人,有那麽多人讀他的書,據說他的書又尤其寫女人寫得好,身邊自然就聚焦攏來一批女性崇拜者。這些女子一個個形容姣好,聰明伶俐,風情萬種,善解人意。他們仰慕莊之蝶的知識、文化、氣質和藝術家作派,更陶醉於他作為一個性夥伴的豐富的想象力和實際操作能力。這是一個真正的「自然人」,他不做作,不虛偽,遇到一個靈魂的女子,他總是能夠做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並順順當當的成其好事。不是憑他的外貌(他的外表很一般),也不靠花言巧語,更不憑借暴力,而只憑他一腔誠心、真心,他便同時占用好幾個如花似玉的女人。這簡直就是一個使男人暗中羨慕的當代賈寶玉。
因此,現實中的莊之蝶盡管顯得那麽玩世不恭,整個一個玩弄女人的痞子,但在理想或夢幻中莊之蝶卻自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天才,能將除去一切道德面紗的赤裸裸的痞性、獸性變得如此優雅和溫情,甚至使之顯出一種自然天成的純潔和美來。
當然,這種美決不是精神上的,而是一個有精神的人對肉體的崇拜和迷戀,是精神放棄自己更高的目標而回到肉體的家園,直言之,是精神的頹廢和沈淪。當精神無論如何也看不到自己頭上的天光、無法引導自我超升至神明般的至福境界時,唯一能使靈魂感到「安妥」的便似乎是向肉體沈淪。
這種沈淪是如此愜意、如此甜美,毫無罪感和觸犯天條的恐懼,因為精神的唯物主義知道,沒有上帝,也沒有死去的靈魂。人生如過客,如蛆蟲,亦如夢幻。而最真實的夢幻是蛆蟲的夢幻,只有蛆蟲的夢幻才使得蛆蟲不只是蛆蟲,而有了「文化」,成了天道和自性。可見,理想和現實、精神和肉體、夢幻和蛆蟲畢竟還不是一回事,精神對肉體的崇拜雖不是「精神上的」,但畢竟是「精神性的」,亦即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最高級的文化,否則莊之蝶就和那些無知無識的流氓沒有區別了。莊之蝶並不屑於普通誘奸者的禽獸行,他向來看不起杯水主義,他是懷著一腔純情的真誠去和人通奸的,他痞得瀟灑,痞得有水平。他水性楊花、隨時可移情別處,但每次都忠實不渝、全心投人。

孟雲房說他「別人在外面玩女人都是逢場作戲罷了,莊之蝶倒真的投入了感情!他實在是個老實的人」。他要天下一切美妙女子,但只是為了將自己的純情無私地賜福於她們,因而一點也不顯得「個人主義」。可是到頭來,他在把這些普通女子從粗痞提高到「純情」的層次上來、因而「造就」了她們的同時,也就將她們毀了。正如柳月說的: 「是你把我、把唐宛兒創造了一個新人,使我們產生了重新生活的勇氣和自信,但你最後又把我們淪陷了!而你在淪陷我們的過程中,你也淪陷了你,淪陷了你的形象和聲譽,淪陷了大姐和這個家!」
這些女人,雖然庸俗一點,可都還是些好女人,即使有些越軌行為,也是壓迫下的自然反抗。如唐宛兒跟周敏私奔,阿燦不惜賣身而給妹妹報仇,柳月看孩子給吃安眠藥,都是情有可原。但她們都並覺得理直氣壯。一旦遇到了莊之蝶,她們就一個個忽然都鮮活起來,迎風招展起來。是莊之蝶給了她們精神力量,使她們看到人生中還有些可以問心無愧地追求的東西、新鮮誘人的東西,但又是絕對高級的東西,因而都死心塌地跟了他,心甘情願地成為他精神王國中的奴隸和泥土。唐宛兒曾激情洋溢地對莊之蝶說:
「我想嫁給你,做長長久久的夫妻,我雖不是什麽有本事的人……但我敢說我會讓你活得快樂!因為我看得出來,我也感覺到了,你和一般人不一樣。你是作家,你需要不停地尋找什麽刺激,來啟用你的藝術靈感」,「我相依我並不是多壞的女人,成心要色相你,壞你的家庭,也不是企圖享有你的家業和聲譽……不是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為一個搞創作的人,喜新厭舊是一種創造欲的表現!」「我知道,我也會調整我來適應你,使你常看常新。適應了你也並不是沒有了我,卻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反過來說,就是我為了我活得有滋有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會厭煩。女人的作用是來貢獻美的,貢獻出來,也使你再有強烈的力量去發展你的天才」。
這番話,不是一個從小縣城來的普通女子能說得出來的,無寧說,它直接說出了莊之蝶或賈平凹本人對女人的看法,從唐宛兒嘴裏說出來,至少也是鸚鵡學舌。一般說來,賈平凹筆底下的女人都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的,她們的一點思想只能從男人那獲取。幾千年來中國的女性的確就是這麽過來的。而一旦男人的思想崩潰,女人在思想上就越發一瀉千裏,往往比男人更顯得激進(如今天中國的一些「女權主義者」),行動也更加大膽(陰盛陽衰)。
清虛庵的尼姑慧明師父便是這種女人的一個典型代表。她年紀輕輕便削發為尼,深研佛理,但決不是為了遁入空門,而是為了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向男性世界挑戰。她與多名男子發生關系,但卻始終能保持一種聖潔和高深的氣質。她向牛月清介紹她的經驗之談:「在男人主宰的這個世界上,女人要明白這是男人的世界,又要活得好」,「女人就得不斷地調整自己、豐富自己、創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動,才能立於不會消失的位置」,「女人對男人要若即若離,如一條泥鰍,讓她抓在手裏了,你又滑掉……所以,女人要為自己而活,要活得熱情,活得有味,這才是在這個男人的世界裏,真正會活的女人!」
這種中國式的「女權主義」,歸根結底是以男子的絕對統治為前提的,哪怕這種統治並不以暴力、而是以「純情」的方式、以「文化」,「文雅」的方式實行。女人只有以男人為標準才能「創造」自己,這種創造便沒有什麽創造性;女人「為自己而活」、「對自己好一點」也只是為了更好地適應男人,則她們是否真能「取得主動」、成為「真正會活的女人」,也就不取決於自己,而取決於男人的興趣和能力。如果男人興趣轉移、能力有限、女人的一切「創造」和自信自憐便毀於一旦。
所以,當莊之蝶以「文化」的名義將他的女人們的原始生命力激發出來時,由於他實際上並不具備皇帝那樣強大的「痞力」來無條件地擁有她們,控制她們,他就只能無可奈何地眼看著她們一個個走向淪陷,並清楚地意識到這整個是一場罪孽、一片地獄的煎熬,他內心一點也「瀟灑」不起來。因此盡管這些女子在遭到淪陷時沒有一個對他心懷怨恨,反而對他更加頂禮膜拜,但他越來越感到困惑的卻是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個壞人嗎?」這其實也是作家賈平凹的自我發問。
要好,想作個好人,為此而不甘屈從於世俗的虛偽;但世俗中充滿著虛偽,因而他極力要尋求現實中的破缺,以顯露真實,然而最真實、最實在的竟是人的動物性的情欲、痞、不管你如何美化它、「文化」它,在偽善與道貌的反襯下頌揚它,它仍只不過是盲目的痞性,其最高代表就是皇帝,其純粹體現就是一夫多妻制!然而,這痞性不正是出於純情、「要好」,歷經磨難,幾經錯過而終於求得的嗎?莊之蝶深為後悔:「多年前與景雪蔭太純潔了,自己太卑怯膽小了,如果那時像現在,今天又會是怎樣呢?莊之蝶狠狠打了自己一拳,卻又疑惑自己是那時對呢,還是現在對呢?」
其實,【紅樓夢】中警幻仙子早就說過,那「意淫」和「皮膚濫淫」盡管「意雖有別」,畢竟「淫則一理」。純情的回到本心,與痞的從本性出發,恰好成了兩極相通。當賈寶玉的「紅樓夢」破滅後,莊之蝶再也不能把夢幻當現實了。但夢幻又始終纏結著他,使他以為那裏還有一個「真我」完好如初;他淫亂,但他在幻想中貞潔;他痞,但他付出和是真情。他不知自己是誰,是好人還是惡人,但他沒有力量、不敢、甚至不願意擺脫這種雙重自我的混沌狀態,因為要他弄清這個問題,就等於要他直面醜惡的現實和靈魂的骯臟,放棄一切自欺來懺悔。他寧可自恃純情而怪罪於他人。例如,「為了擺脫困境,他開始用關於女人的種種道德規範來看唐婉兒,希望自己恨起她,忘卻她!可莊之蝶想不出唐婉兒錯在哪裏,哪裏又能使自己反感生厭?」
他竟然援用他自己首先破壞的傳統道德來為自己開脫罪責,怎能不陷入自相矛盾!
要麽,他就必須徹底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幹一番驚世駭俗的事,哪怕像皇帝那樣公然妻妾成群。但他不能徹底,他既無能力,也無膽量。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實作他作為男人的動物性功能,只在幻想中使自己成為一名男子漢。當他的結發妻子正式向他提出離婚後,他就真正崩潰了,他的一切憤世嫉俗和返潮流的故作瀟灑都脫落下來,顯出他骨子裏不過是數千年傳統文化的一種變態標本。無論他如何激進、如何超前、如何解放,他的根是家庭,這個家庭盡管不能給他帶來任何生機活力,還日復一日地消磨他男人的自尊自信,幾乎使他成了一個不能人道的廢人,但他仍然不能離開它。一旦被連根拔起,他就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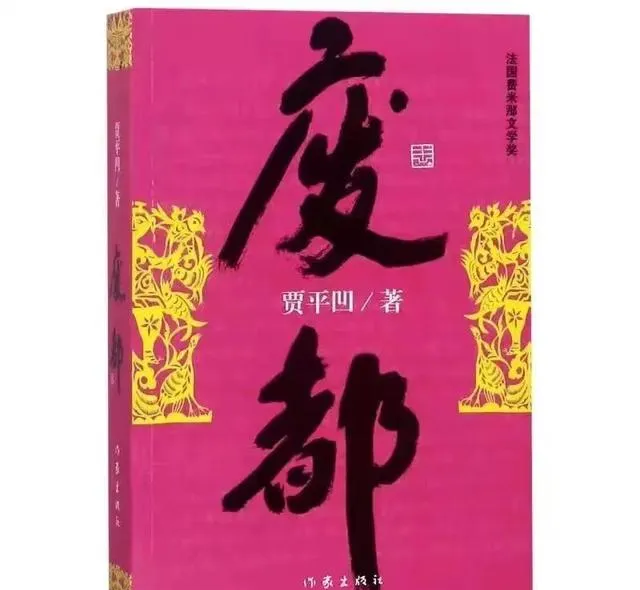
莊之蝶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車站候車室裏,他到底要到哪裏去?為什麽出走?這些都沒有明確的交代。莊之蝶決不是一名戰士,而只是一個逃兵,不僅是逃避社會和現實,而且是逃避自己。他以自己內心的赤誠為據點去尋求社會的「破缺」,可是當他發覺這破缺不在別處,正在他自己內心深處時,他便膽怯了。他可以承受別人的指責和輕蔑,但他無法直面自己罪孽。他的一切真誠和純情到頭到都成了虛偽,都成了勾引女人滿足自己動物性情欲的手段。不論他的出發點是如何要「好」,他都擺脫不了成為「壞人」的宿命,因為人性本惡。
但賈平凹還沒有反思到這一層,否則他的靈魂就永遠也得不到「安妥」了。靈魂之所以是靈魂,就在於它永遠不能在物質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安妥和歸宿。真正自由的靈魂是註定的格拉斯哥流浪,只能居住在虛無之鄉。它與物質或肉體的區別就在於它是「無中生有」,是憑空創造。莊之蝶的悲劇並不在於他與社會反腐敗抗爭的失敗,而在於他的靈魂的軟弱無力、打不起精神,無法戰勝自己的劣根性。
賈平凹的悲劇也不在於他只能在這種絕境中、在中國當代靈魂的毫無希望的生存狀態中「安妥」自己的靈魂,而在於他無論如何也還是想要使自己的靈魂在世俗生活中尋得「安妥」這一強烈的願望本身。這也就是對那曾經一度那麽妥帖輝煌、而今早已被廢棄的靈都的無限留戀、無限傷懷。只有在這種留戀和傷懷中,他才感到自己內心仍然保留著一股溫熱的血脈,一種人性的赤誠,一番超越當下不堪的現實之上的形而上的感慨。
在【廢都】中,我們除了看到男主人公和一個個的女人的曖昧關系之外,還看到一種整體的氛圍,一種文化氣氛,這才是作者真正要渲染、要標榜的東西。說到底,莊之蝶憑什麽能夠引得一個個不同的層次、不同身份的女人如燈蛾撲火般地趨之若鶩?不正是憑這種妙不可言、深不可測的文化涵養嗎?與這種文化涵養相比,世俗生活的一切,包括人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生活享受,都顯得那麽低階庸俗、虛幻不實。
尤其是對那些自我感覺頗好、尚未被自卑心理引入對生活和命運不公的憤懣嫉妒,尚未泯滅對人生理想目標的追求的女子來說,莊之蝶無異於一個實實在在的精神寶藏,在他那裏有著一個五彩斑斕的華嚴境界,顯示著生活應有的本相。
然而,莊之蝶的文化涵養之所以顯得深厚、玄妙、醇香四溢,並不是由於他的積極進取和創造性的自我陶鑄的結果,而恰好是由於他的頹廢、傷懷、念舊和反璞歸真。這也是整個小說所著力強調的思想傾向。在西京城裏,莊之蝶代表文化的最高層次。古今中外一切激動過、誘惑過人類心靈的玩意兒他全都看過了,聽過了,領教過了,欣賞過了。但最終,他看不出這裏面有什麽真正新鮮的東西。
他的目光越來越沈浸到那些遠古的、代表人類蒙昧時代的精神家園的東西中去,從中體味人的本真的存在和意境,就像他從那早已失傳了的「塤樂」中聽到的那樣:「……你閉上眼慢慢體會這意境,就會覺得猶如置身於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嗚咽,有一點磷火在閃;你步入黑黝黝在古松林中,聽見了一顆露珠沿著枝條慢慢滑動,後來欲掉不掉,突然就墜下去碎了。你感到了一種恐懼,一種神秘,又抑不住地湧動出要探個究竟的熱情;你越走越遠,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的瘴氣,又看到了陽光透過樹枝和瘴氣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卻怎麽也尋不著了返回的路線……」
在一個遍地物欲洶洶的年代,莊之蝶這種閉眼沈吟顯得那麽獨出一格、超凡脫俗。他並不是一個迂夫子,相反,他體現了每個世俗凡人在感受到生命痛苦時(如果凡人也有痛苦的話)所自然而然地夢想回復的那種懵然無知的原始狀態。尋根就是尋求純情之痞或蠻痞之真情,它是對現代生活否定人的本性的抗議。
然而,正因為人類生活的成長和進步、人的歷史和文明行程不能不以這種人類本性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為根本動力,因而這種尋根實際上又是對人類的現實本性(即要長大、要發展)的一種逃避,它註定是感傷的、悲劇性的、軟弱無力和沒有希望的。它沒有承擔自己苦難的勇氣和力量,只徒然呈現了人的心地的純凈和善良:一種極其狹隘、絕望、幼稚和不切實際的純凈和善良。它在被作為自覺的目標刻意追求時往往顯得可笑和虛偽,在付諸實際時則又變得可怕和殘忍,因為它想用已死的虛幻回憶來強行摧毀雖已患病但畢竟沒有死滅的生活本身。
幸好,莊之蝶只是一介文人,他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將他的理想和情感在布衫中推行,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一種象征性的舉動驚世駭俗地表達他回歸自然的理念,即像一只牛犢一樣趴在奶牛肚子下直接用嘴吮奶。在【廢都】中,那頭借給莊之蝶以奶汁、其實毋寧說供給他以精神上的奶汁的奶牛正是莊之蝶良心的象征(同樣,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大青馬是章永璘的良心的象征。
這些作家總喜歡用馴良的牲口來表現人的靈魂)。這奶牛大智若愚,雖然不會說話,卻有比人類更加深刻透徹的思想。「牛的反芻是一種思索,這思索又與人的思索不同,它是能時空逆溯的,可以若明若暗地重現很早以前的影像。這種牛與人的差異,使牛知道的事體比人多得多,……所以當人常常忘卻了過去的事情,等一切都發生了,去翻看那些線裝的古書,不免浩嘆一句‘歷史怎麽有驚人的相似’,牛就在心裏嘲笑人的可憐了」。
這牛真是天生的「後現代主義者」,它堅信「人與所有的動物是平等的」,「人也是野獸的一種」,「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卻將他們的種族退化了」。於是操著法蘭克福學派和羅馬俱樂部的口吻把人類在20世紀所幹的一切荒唐事如環境汙染、人口爆炸、水源危機、生物鏈破壞……一一罵了個遍。
人類的養尊處優已使人種退化得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個七星瓢蟲。「牛在這個時代,真恨不得在某一個夜裏,闖入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家裏,強奸了所有的女人,讓人種強起來野起來!」奇怪的是,這恰好是當今那些到處尋找「真正的男子漢」的女人們所暗中渴望的。當然,這種男子漢如果不是采取粗暴的獸性,而是像莊之蝶那樣采取文化的、純情的方式,將更得女人們的歡心。中國人需要的並不是真正獸性的陽剛之氣,而是一種具有陽剛之氣的文化。但很可惜,這文化恰好是陰柔的、扼殺陽剛之氣。於是眾多的小說家便發揮自己天才的想象力,捏造出了像莊之蝶、章永璘這一類既有高雅的文化情致、又具有令人羨慕的效能力和 「野性」的男人形象,其實不過是一種畫餅充饑的空想罷了。
因此,莊之蝶的虛假,並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缺少這樣的例項,也不是賈平凹刻意構想出來的那些情節(如頭一次見面一個文化人就可以和一個陌生女人兩相情願地上床)如同天方夜譚,而是根本上的不可能。中國文化是這樣一種文化,即越是真誠的文化人越是表現出性無能(其結果是怕老婆、「妻管嚴」),只有那種「兩面人」,才能在「文化」的面具底下為人的本能和野性(獸性)留下一席之地;再就是那些缺少文化教養的村夫村婦,他們的野性較少受到殘害和壓抑,反而有一種輕松自如但痞裏痞氣的表露和發揮。

中國文化人在性心理上的這種心理障礙,不是透過文化上、思想觀念上的「回歸原始」可以消除的,正相反,當他把這種回歸當作一種高超、純凈的文化來追求、來標榜時,他只是突現了自己已被這個文化本身禁錮的毫無出路的絕望狀態,從而更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負擔,導致虛火上升而底氣不足。這正是當今文人們以各種方式冒充陽剛之氣的內心根由,也是許多文人不僅在作品中、而且是生活中「渴望墮落」、玩味粗野、流於鄙俗的最終根由。我們看對莊之蝶和阿燦做愛的描寫,就深感文化人對轟轟烈烈的愛的想象是何等可笑。
所以在【廢都】中,莊之蝶對現存文化的一切否定的憤激之辭都帶給人一種「理念先行」的、無的放矢的印象。人們不明白,對這樣一個他在其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的世道,他為什麽那麽深惡痛絕。我們倒是能夠合理想象:這只不過是當今文人的一種姿態,一種憤世嫉俗的時髦,仿佛不如此便顯不出文化的高超和思想的先鋒似的。
莊之蝶把哀樂捧為最上乘的音樂向人家推薦,說「只有這音樂能安妥人心」,就顯得有幾分做派;唐婉兒說別人不講究是邋遢,「他不講究就是瀟灑哩」!倒是點出了莊之蝶故意邋裏邋遢的本意。當今世界真如牛月清的老太太說:「讓帶面具不帶,連妝也不化,人的真面具怎麽能讓外人看了?」其實老太太的擔憂是多余的。真誠如莊之蝶,也是有自己的面具的,只是他並不自覺罷了。不帶面具就是面具,而且是更隱秘的面具;否定文化也是一種文化:這就是我們民族數千年來真正的睿智之所在。
莊之蝶並沒有表露出真正的內心矛盾和沖突,盡管他滿臉一副「苦莫大焉」的模樣,作者和許多讀者都會不由自主地對他的生活羨慕得要死,覺得他哪怕做了「花下鬼」,也不枉風流瀟灑了一世。從作者對莊之蝶的這種欣賞和美化中,我們不難猜到事情背後的真相:這一切手到擒來的風流韻事和要死要活的感情糾葛都是作者胡編出來的,現實中的莊之蝶實際上被周圍社會和自己頭腦裏的傳統觀念束縛得一動也不敢動,即所謂「有賊心無賊膽」。這才能解釋他對這個社會所通行的倫常規範的深仇大恨。
人與人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麽容易溝通的,尤其不容易以「文化」為媒介溝通。讀過莊之蝶的書就想和他上床的女人也許不是沒有,但那只屬於「意淫」的範疇,從那裏進到「皮膚濫淫」還有著漫長的路,而且往往是半途而廢。因為這兩者潛伏著內在的矛盾,即「意淫」是以對方的貞潔為基礎的,一旦實作性愛,便是對這基礎的破壞;理想一旦破滅,便將「文化」降格為「痞」了。當賈平凹自以為他可以用勞倫斯的審美眼光來看待這種痞,來把性愛上升為一種人類生命最美麗的花朵時,他似乎忘了,查泰萊夫人既不是看中梅樂士的名氣,也絲毫沒想到對方的文才,而僅僅是坦然而對自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對一個健康有力的男人的自然需要而已。
而這正是我們的文化、也就是莊之蝶身上吸引女人的那種文化所極力鄙薄和斬殺的。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個像莊之蝶這樣誠實的文化人,身處當今這樣一個四處埋伏著物欲、情欲和陰謀的社會,怎麽可能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像真正的兒童那樣動輒敞開自己隱秘的心扉,不但未遭暗算反而屢屢中的、消遙法外呢?怎麽可能輕易就獲得眾多女人死心塌地的真情、獲得那麽多「以心換心」的摯愛(這種摯愛甚至超越於正常的嫉妒心之上,使莊之蝶被當作人人為之獻身的神來崇拜)?作者最後讓他悲悲戚戚地死於心臟的不堪負擔,正如那頭奶牛死於現代文明一樣;但其實,使他淪陷的並不是外在的環境,而是靈魂的絕癥。
顯然,是賈平凹「尋根」的理念制造出了這一切幻覺。他陶醉於中國幾千年來文人士大夫夢寐以求的回歸理想,而未發覺這一理想一開始就是既不合邏輯也不合生命自身的規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將來更不存在退回到原始人類如同赤子般互不防範的社會狀態中去的可能。人們歷來用遠古大同理想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貼金,不過是利用了大眾文化的不成熟、不獨立以便理所當然地充當家長罷了。在這方面,文人士大夫千篇一律地成為了這個大眾文化的幼稚性和依賴性的代表或代言人。
這不僅使他們在權力面前本能地作赤誠狀、純潔狀和嬰兒狀,而且使他們即使在拒斥和遠離權力、甚至成為世俗社會的憤激的批判者時,也顯得那樣幼稚天真,充其量是一個兒童的自暴自棄。如果說,當年屈原的自沈還表明了一種真正兒童式的真純的話,那麽當今文人所標榜的「陸沈」則更多的是一種市儈的狡獪。
人們現在已經知道,「不活白不活」,對世俗的反抗居然也可以用來作為自己在世俗生活中謀取平日被自己和社會所壓抑著的世俗欲求的誘餌,使這種世俗欲求成了冠冕堂皇的「個性解放」、「思想啟蒙」,成了最先鋒的濟世和救世宣言。似乎當人們在一天早晨醒來,發現一切文化都只不過是鬼話,人們只要赤條條一絲不掛地走在大街展示赤誠,就既可以使自己獲得為所欲為的快樂人生,又使社會民風淳樸、不生機心,真是不費吹灰之力!莊之蝶只不過是率先身體力行了這一理想而已,屬於「先赤起來的」一部份人。
可見,對「廢都」的懷念絕不是一種進取的思想,更不是什麽啟蒙思想(盡管它以西方最激進的文化批判為參照),而是放棄主動思想,聽憑自己未經反思的情感欲望和本能來引領自己的思想(跟著感覺走)。從這種意義上說,所謂「安妥破碎的靈魂」雲雲只不過是對一切思想的解構,使自己的靈魂融化於那充塞於天地間、如怨如訴的世紀末氛圍之中,以自造的幻景充當自欺欺人的逃路而已。中國人其實並沒有靈魂的本真痛苦,一切「我好痛苦好痛苦、好孤獨好孤獨」的自訴都只是在撒嬌做派,意在求得他人的呵護和愛撫。
當代作家的靈魂何時才能真正振作起來、奮發起來,不是陷入陳舊的語言圈套頁走失語,而是努力為自己創造新的語言呢?
(引自【靈魂之旅: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生存意境】,鄧曉芒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簡 介

鄧曉芒(1948年4月7日-),中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批評家。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德國哲學】主編。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德國哲學,亦研究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創立「新實踐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積極展開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行程和精神建構,在學術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張力】【文學與文化三論】【新批判主義】【實踐唯物論新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