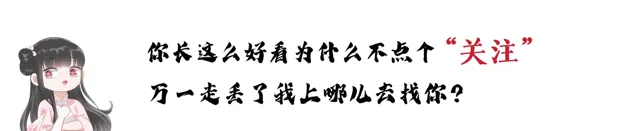1934年10月,陳奇涵將軍生了一場大病,朱老總連夜親自探望。
那時,他得了非常嚴重的關節病,膝蓋腫得像饅頭。
即便如此,他也硬扛著走出了草地。
朱老總見到他的時候,說這個老表有股頑強勁。
事實上,那時的陳將軍正經受著更大的痛苦,朱老總也是得知此事後特來安慰的。

陳將軍與朱老總認識得很早,朱老總的夫人康克清女士曾說,陳將軍是朱老總最早的戰友。
他們的友誼跨越將近半個世紀,長達49年,在南昌,他們曾一起創辦軍官教育團。
那麽,當年過草地發生了什麽,他們是如何認識的,又如何維持了這麽久的友誼?

堅定信念
陳奇涵將軍過草地的時候,他從江西軍區的參謀長,降為了紅軍總政治部動員部的科長。
這一職位的變動,實際上是拿掉了他的軍事指揮權。
那時,得到訊息的他深受打擊,但他並沒有氣餒,堅定信念堅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那麽究竟是因為什麽事情,他才被突然降職了?
1930年初,中央蘇區掀起了一場「肅反運動」。

黨內素來有自我批評的活動,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然而隨著運動的擴大化,運動當中出現了一些很不好的現象。
在贛西南根據地,有一大批根據地創始人被汙蔑成了「AB團分子」
這個AB團是什麽東西呢?其實,最開始這就是老蔣為了破壞大革命,搞出來的一個特務部隊。
但在紅軍的鬥爭中,這支部隊已被基本擊潰,但有不少幹部受到了錯誤的思想路線影響,認為組織中,仍有這類人存在。
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才在蘇區中掀起了一場運動,而陳將軍也陷入了這場風暴之中。
那個時候,跟著他一起參加革命的二弟、三弟,都遭到了汙蔑,還沒有把事情調查清楚,他們就被無辜地殺害了。

面對這樣的風暴,陳將軍絲毫不懼,他對組織內不正常的現象,十分不滿,並大膽地提了出來。
那時他說:「運動是好的,但不能那樣沒有節制地亂搞。」
正是因為他站出來說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汙蔑他,他差點被當作「AB團分子」處決。
好在有朱老總出手相救,他聽聞陳將軍被捕後,立刻找到那些同誌,要他們刀下留人。
當年他說:「陳奇涵我是了解的,他怎麽可能會是‘AB團分子’?
「1927年的時候,我們就在南昌,一起堅決打擊了‘AB團’。」
面對一些激動過頭的幹部,朱老總耐心地說,搞革命不能只靠一兩個人,一定要大家齊心協力,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這就是說,要相信同誌們,不能隨便亂冤枉人,要實事求是,講證據。

這是他的這一番話,才救下了陳將軍。然而,好景不長,1933年,博古首的領導同誌進入了中央蘇區。
他們再度掀起了一場風暴,首當其沖的是毛主席,主席那時被迫離開了中央中心,無法指揮軍隊,賦閑在家。
而陳將軍堅定維護毛主席的思想路線,還是一如既往地,敢於站出來指出問題。
正是這樣,他才被有心人給利用了,被突然降職,失去了軍事指揮權力。
1934年4月,他加入了長征的隊伍當中,並擔任紅一軍團司令部教育科長一職。
透過草地時,他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病。
膝蓋腫的高高的,像饅頭一樣,他幾乎已經到了命懸一線的地步。
但他如無數紅軍戰士一樣,他有著鐵一般的意誌。
在重病的情況下,他堅持走出了草地,抵達了班佑地區。

那以後他放松了一些,發起了高燒,燒得神誌不大清楚。
大家都以為他快不行了,朱老總得知這個訊息後,立馬趕過來看望老戰友「最後一面」。
然而陳將軍十分頑強,醫生將他肚子裏的野草和12條蛔蟲全部打出後他,他奇跡一般地恢復了。
朱老總看老戰友從死亡線上活過來,他心中自然是高興的。
那時,他站在陳將軍的病床邊,眼裏含著眼淚打轉,笑著說:「陳啟涵,你這個老表,有股頑強勁兒。」
這段艱難歲月好在有朱老總幫忙,陳將軍才順利度過,而在為將軍辯駁時,朱老總提到了南昌的一件往事。
這件事,對他來說意義非凡,同時也是他們兩人友誼的起點。

那麽,在南昌時,他們兩人是如何認識的呢?

初識戰友
1930年的時候,朱老總提到了一件南昌往事,這也是他和陳奇涵將軍友誼的起點。
在南昌他們是如何認識的,又是什麽契機使他們成為戰友?
1925年2月,陳將軍經過陳賡、許繼慎同誌的介紹,成為共產黨人。
第二年夏天,他帶著一批黨員,以國軍總政治部指派員的身份,回到了江西。
在那裏,他建立起了組織,並在贛南、贛東開展工農運動,掀起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革命。
又一年,1927年初,朱老總按組織的命令列動,借由他以前在滇軍的戰鬥經歷。
利用自己在滇軍中的聲望和同僚關系,到江西南昌工作。

他借著與朱培德的關系,被安排到了第五方面軍,擔任參議,並兼任第3軍官教育團團長。
彼時,陳將軍也在軍官教育團,他擔任參謀長和黨組織負責人兩個職位。
那時軍官教育團雖然在名義上屬於國軍第三軍,但實際上,這一支軍隊接受中共中央領導。
朱老總在滇軍中很有聲望,是非常有名的戰將。
大家聽聞他創辦了軍官教育團,滇軍中的進步軍官紛紛前來報名。
不僅如此,當地也有一大批青年誌士,棄筆從戎,報考加入軍隊,所以這支部隊的招生工作非常順利。
而軍官教育團也成了朱老總和陳將軍,認識並成為戰友的契機。
他們兩人了解到對方都是軍人,身經百戰,並且他們的性格比較相近。
在思想上,他們也很投契,很有話題。

巧的是,他們先後都曾在雲南講武堂中學習,算上來,還是前後輩學長學弟的關系。
正因如此,他們兩人在工作時配合十分默契。
軍官教育團下屬有3個,一共有1000多人,這些學員大多數是朱培德將軍手下的下級軍官。
他們大多數是行伍出身,家庭貧困,靠著打仗補貼家用。
3營又被叫做「學生營」,部份是北方宣傳隊隊員,剩下的都是當地的進步學生。
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把教育團當作一支普通的軍隊來訓練。
他們希望,未來能從這個教育團內走出一批優秀的革命幹部。
那個時候,他們還和方誌敏同誌創辦的訓練班一起教學,這兩個組織都是那時,江西省培養革命幹部的基地。
朱老總和陳將軍十分關照他們的學員,不愛擺架子,和他們同吃同住。

而且,他們對教官的要求也很嚴格,讓他們改掉舊軍隊的習慣,不許打罵學員。
一到出操時間,他們總是準時到達訓練場地,還親自給學員示範動作。
那些學生都知道,這兩位首長,住的房子裏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還有數把椅子,十分簡陋、樸素。
他們這樣以身作則,也極大感染了學員,讓他們嚴格要求自己,逐步成長。
部隊的教學內容非常豐富,包含軍事和政治兩個方面。
朱、陳兩位,除了進行嚴格的軍事教育以外,他們還非常註重政治思想教育。
他們經常請到全國有名的進步人士到講堂講課,提高他們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他們除了講政治形勢、軍事策略以外,還教育大家,不要只想著個人的利益。

打仗並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要為了革命,為民族復興而奮鬥。
他們講課時從不講晦澀的理論,而是從自身的經歷出發,用淺顯的語言解釋理論。
朱老總授課語言幽默風趣,逗得學員們開懷大笑,而在這樣輕松的過程中,他們學習到了知識,進一步提高了思想。
陳將軍則重視黨員的發展工作,在他的努力工作下,到學期結束時,每個連都有十幾名黨員。還有的甚至發展到了全連的一半。
正是在這樣的教育下,他們才能齊心協力,面對老蔣的背叛,成功搗毀了「AB團」的陰謀。
教育團的這一段時光,使陳將軍和朱老總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而他們的戰友情誼也一直持續到了新中國成立。在和平年代,他們又是相處和交往的呢?

晚年時光
1927年,在南昌的軍官教育團中,朱老總和陳奇涵將軍相遇。
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們又是如何在繁瑣的事務當中,保持深厚的友誼的?
1954年1月,中央成立了軍事法庭,陳將軍被任命為軍事法院院長,他來到北京工作後,二人就有機會互相看望了。
1960年的春天,中央軍委舉行了宴會。在會上,領導同誌提出了掛名休息的建議。
因為有好幾位老將軍年事已高,再工作下去恐怕對身體不利。
而這,正合陳將軍的心意,他早就希望將自己的工作,交給年輕的同誌繼續延續下去。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和朱老總之間的來往更加頻繁了。

周末的時候,他們就會互相串串門,比如康克清同誌有時候就會打電話給他,請他去吃紅燒肉。
那時,她說的是,朱老總要請他跟衛彬夫人到家裏吃肉。
朱老總喜歡養蘭花,陳將軍到他家拜訪,他總愛把自己種植的蘭花展示出來。
而且他還特意送了幾盆給陳將軍,從那以後,養蘭花也成了陳將軍的愛好。
1962年的一天,他們到江西等地進行視察工作,晚間閑散步時閑聊,他們便談起了南昌工作的往事。
他們仍對南昌起義段時間的經歷,難以忘懷,講到南昌起義,他們認為南昌起義失敗是缺乏建立根據地的經驗。
他們對於這次失敗,也感到非常惋惜,因為那時的江西農村條件非常好,倘若他們起義成功了,就在江西發展。

或許,情況也就和那時大不相同了,但歷史沒有如果,不到那個時候,又怎麽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後來,他們又聊了很多,在路上,他們又把江西的問題梳理了一遍。
視察工作結束後,他們將這一次談話寫成了一篇文章,收集到了朱老總的文集中。
而這,也成了朱老總生前最後寫成和發表的一篇文章。
陳將軍把朱老總送了兩盆蘭花當作珍寶,秋天,蘭花謝掉的時候,他會把這些花兒,葉子都制作成標本。
不僅如此,他還貼在紙上,題寫詩句。
而在動蕩年代,陳將軍仍保持以往的態度。他敢於提出組織的問題,從不冤枉其他的同誌,敢於幫那些被汙蔑的同誌說話。
就在朱老總被打倒的時候,有人問他和朱老總到底是什麽關系?

他就說:「我和老總是南昌起義時的老戰友,他是我尊敬的老總,你們不能打倒他!」
面對氣勢洶洶的小將,他絲毫不怕,還和這些同誌們多讀書,要多認識歷史唯物主義。
而他身邊的警衛員怕他講太多,惹得那群小將鬧事,就以陳將軍身體不適為由,把那些人打發走。
1976年7月6日,朱老總病逝,陳將軍聞訊悲痛萬分。
後來他接受采訪,多次回憶起和朱老總共同戰鬥的日子,他時常思念著朱老總。
5年後,陳將軍也離開了人世,就在他彌留之際,朱老總的夫人康克清同誌曾多次去看望他。

後來,她講到朱老總與陳將軍的深厚友誼,她說自己是看在眼裏的。
朱老總曾評價,陳將軍工作踏實,為人真誠。
他是個資歷很深的老同誌,卻從來不講自己。
朱老總和他一樣都是久經考驗的無產主義戰士,他們之間幾十年的友誼記錄了戰火紛飛的革命時代,到和平的建設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