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
32歲的雜貨鋪老板,患了一種無法治愈的疾病。在徹底惡化前,他用一次次的流浪與自我放逐,對抗命運的虛無。在蠻荒之地,他找到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我已經三十二歲了,準備到山裏建個四合院隱居釀酒。
我太愛喝酒了,喝醉了醒著不是醒著,夢也不是夢,懸浮在一個高於現實又低於夢的維度裏。可現實總跟理想過不去。疫情雖然沒有帶走我的命,但是帶走我不少錢。
九月份,我終於把經營多年的兩個雜貨鋪轉讓了,滋味很復雜,即是解脫又是失落。
我和箱子們一起擁堵在三姐家的小屋裏,撐得小屋要吐。屬於我的只有眼前這些箱子,裏面具體裝的啥我也忘了,反正都有用,不過沒有也沒關系。
我用屁股使勁擠了擠床上堆滿的雜物,呆坐在床邊看著箱子們,抽根煙吧。想想這些年旅遊和玩的花銷在這小城換個兩室一廳是夠的,再想想今後何去何從?總不能無所事事吧?再抽根煙吧。
馬向平的電話結束了我的多愁善感。他是北京的藏文化學者,也是苯教弟子。他要去阿裏尋找古象雄遺址和壁畫,也知道羌塘能讓我魂牽夢繞,問我去不去?我讓他等我考慮考慮。
「弟呀。姐都快急死了,你還得幾天能把樓上貨架給姐裝上啊,貨都到家了。再不擺出來就過季了。」三姐愁眉苦臉地站在門口說。
這活兒我已經磨蹭兩天了,按照現在的速度起碼還要一周。我很不情願地拿起手中的小錘兒,有點沈,比劃兩下又放下了,總覺得平板手機上有點什麽得看看,屁股一下就被椅子吸過去了。
馬向平發來了這次長途旅行的文案,看著那些誘人的西藏地名我不知不覺地笑了。摸摸良心問問自己想不想去?相當想!盤算著買房蓋房錢不夠,跟他走,夠!
小錘兒再次上手分量就不一樣了,它又輕又敏捷。小鋸兒鋸一下木板心裏就念叨一遍:羌塘!阿裏!
兩天一夜幾乎沒睡,幹完啦。
出發前我媽有點擔心。以前催婚,我說再催我就出家當和尚,她說我神經病。前段時間,我說想獨居山裏,潛心釀酒,她建議我去山裏出家,起碼寺廟人多安全,我沒幹。
「媽。我要走了你不說點啥麽?「
「嗨!你現在走我都不在乎了。」她忽然想到什麽,接著說:「媽跟你說讓你去當和尚是跟你鬧著玩呢,你去了可別真留那不回來。」
「我神經病啊,我才不出家呢。」
「那我就放心了。」
同行四人一車,北京出發。另外兩個我都不認識,一個搞攝影的姚旭東,還有一個比我大一歲的天津朱玉海。

進藏後,我們先去馬向平皈依的寺廟,他把這當成第二個家,想在這裏多住幾天。我跟他來過一次,被這裏的氣質深深打動。

圖 | 水鳥
到了海拔四千多的寺廟,我高反了,頭很疼,眼睜睜地看著玉海像野牦牛一樣各各山頭撒歡,還讓我看它在山頭光膀子的照片,他的胸毛茂密的像黑胸罩,讓我更加斷定它就是沒前進演化好的野牦牛,不然哪來這麽強的身體素質?
畫滿壁畫的屋裏,六人有三個時不時吸一會兒氧氣,走路都吃力何況爬山。晚上玉海又說外面的星星超好看,我讓他離我遠點,以免我的腦袋爆炸崩著他。
很冷。我是穿著羽絨衣褲進羽絨睡袋的,高反入睡是個技術活,加上另外五個老爺們打呼嚕磨牙放屁和高反的呻吟聲,我放棄強求不來的睡眠,只想撐住,撐著撐著就昏了過去。
好在第二天頭就不痛了,看到的天也藍了,雲也白了,誦經聲也神聖了,還在風裏聞到了酥油燈的藏味兒,甚至挑起了給十幾個內地弟子做飯的要務。接過這個要務後我就為難了,調料只有油和鹽。硬著頭皮幹吧,他們說熟了就行。
「師兄。這個米最多只能洗一遍,菜也是,好像之前老姜都不洗的,這裏的水實在太珍貴了。大部份是從山下背上來的。」瑤瑤心疼地看我把第二遍洗米水倒掉說。
瑤瑤是一名上海醫生,牙白眼亮溫柔善良,在美國留學期間接觸過很多種宗教,最終皈依在本寺師傅門下。她每年都會攢假到這裏修行一段時間。
缺水是大問題,外來的弟子都很自覺地盡量不用水,臉也不用洗,沒人笑話,這裏人都這樣。可我必須用濕巾擦擦腳,我很慚愧。
「兄弟。要不你還是洗洗吧,我頭太疼了。」我對床的於大哥說。
之後幾天,我是唯一夠資格泡腳的。有人看我泡得舒服也想泡,被拒絕,他不夠臭。
於大哥在我們前一天到,高反非常嚴重,可怕的是還伴有高燒,他的同伴周律師多次想帶他下山休整好再上來,他堅決不下山。來一次寺廟不容易,死不了就挺著。可屎尿挺不住,他艱難地把小便放進大瓶裏,又順手放在我倆床頭。
「大哥,你要是不把它拿走,我就把腳調過來。」我看了看尿桶又看了看憔悴的他,不忍心也說了。
他一聽,艱難地坐起來,桶挪到床尾。
在這裏,屎尿很讓人頭疼,廁所離我們住處有兩百米遠,旱廁通風不好,那味道的沖擊力簡直是一種酷刑。尤其晚上入睡前,總是憋到不得不才去解決。第三晚我就很掙紮,那種感覺介於不去不得勁兒,去了不值得之間。
「一起吧。有些事兒是拖不了的。」周律師看懂我的意思說。
幾年前,周律師因非法持有槍支被拘留,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在貴州支教期間認識一位師兄,之後被寺廟的一切感動,做了一個多月義工後成為師傅弟子。他對這裏很熟,在他的帶領下,我們爬到山腰拉野屎,一邊拉一邊看星星。
「你不能總蹲在一個地方,適當換個位置更好一些。」周律師說。
「嗯。你真有經驗。」
「在環境中成長和學習嘛。你得去適應環境,不能讓環境適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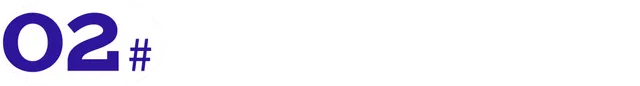
我的身體狀態越來越好。第四天跟著玉海還有一位香港的女師兄去轉山。她在山上住了有些日子,我請教她有信仰是什麽感覺。她說不清,但是覺得很神奇,是種緣分。她去過很多寺廟,一直找不到想皈依的師傅。偶然到這裏,被師傅的博學和仁慈打動。
母親去世時,她在自家佛堂為母親誦經超度,怎麽也找不到誦經的感覺,想到遠在西藏的師傅,想到寺廟的艱苦環境,突然有了感覺,她嚎啕大哭,然後迫不及待奔赴西藏找到師傅皈依。
轉山回來後,過了中午吃飯時間,我和玉海迅速抵達廚房,用高壓鍋壓了一鍋面條。著急了,沒等放完氣就開蓋了,高壓鍋吐了,半鍋面條掛在鍋沿和煤氣竈台上。我相當愧疚,在這個忌諱浪費的地方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浪費。
在寺廟吃飯餐具都是內建的,不用洗,這裏的習慣是舔幹凈,不會舔就用紙擦。婷婷姐說:「碗好舔,師傅那喝酸奶的杯子才難舔,太深了。」
幾天裏,我沒做出一頓讓我滿意的飯,可他們都贊不絕口,尤其李師兄(女的),還特意送我幾雙襪子以表謝意。李師兄本次來是將自己九歲的兒子送到寺廟出家的,聽說她的女兒在歐洲上學。這覺悟讓所有人欽佩。
傍晚,我坐在廚房門口的長木板上發呆。索巴益西微笑著撩起僧服坐在我旁邊。彼此友善的笑意讓我們相談甚歡,臨別時,他約我晚上去看月亮,那天是九月正中。
皓月當空,我們悠閑地走在轉山路上。
「心裏有佛是一種什麽感覺?佛真的存在麽?」我問。
「你是真實存在的麽?」他笑著問我。
我想了想說:「也許吧。」
索巴益西指著星空問:「那裏有多遠?」
我點點頭說:「沒有邊際。」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麽?」
「也許吧。」
「還有真實存在的,你看不到也摸不到。」
「什麽呢?」
「你的心。」
我楞住了。心裏想著,二十一歲的他平時都學了啥?單單臉上淡然的微笑就是一門學問,這裏的僧人幾乎都有同款微笑。
路過天葬台時他笑著建議我過去躺一會兒,我沒去。繼續往前走。靜靜的夜空沒有風,遠處傳來兩個轉山女孩高唱的八字真言,嘹亮的歌聲回蕩在群山中,在鐘聲的映襯下格外動聽。
「你有夢想麽?」我問。
「有的。就是好好念書,現在念書是最重要的。」
「做一輩子和尚麽?」
「是的。」
「怎麽看我們俗人?」
「很可憐。」
「嗯。被欲望逼使著不斷追求,永遠滯留在不斷追求的過程裏。」
「你們什麽都沒有。」索巴益西保持微笑地說。
「你不想住大房子,開豪車吃大餐麽?還有很多想得到的東西。」
「我們吃穿都是喇嘛供的,什麽都不缺,只有學習好才是最好的。」
「對外面的世界不好奇麽?」
「我去過拉薩,林芝,很吵,我不喜歡。我回到村子都覺得吵。」
「所以你們是要把欲望修沒了麽?」
「要有知足,知足才會幸福。」
「那生理上的欲望怎麽修?」我問完不好意思地笑了。
「念經,還有一個咒語是可以的。」
不論我問什麽,他臉上始終掛著淡淡的,滿足的微笑,這狀態讓我感覺新鮮又陌生。
「我最後是要修成無我,那非常難,非常非常難。」他說完不好意思地笑了,又仿佛觸碰到遙遠的夢想。
「那是什麽狀態?」
「就是只為別人好。」
「你避免不了被傷害。」
「沒關系的,只要他好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難,我現在還不行。」
我不是被他的話打動的,而是他真誠的態度。
「我能為你做點什麽?比如生活用品之類的。」
「真的不用的,我什麽都不缺。我爸爸說你該換個手機了,我覺得沒那個必要,還可以用,可是他就給我買了。家裏也會供我,真的什麽都不缺。」
我們又走到一座山後,不遠處一個人背著手一動不動地仰望月亮,像是在沐浴月光。他是即將成為堪布的巴登思根,堪布相當於佛學院的研究生或博士學位。我們三個約好了明天他們下課後去爬山。
第二天下午,我們用了一下午的時間在山頭感受那未必是真實的存在和預料之外的幸福感,慵懶地躺在草地上,閉上眼睛,每人叼著一根草棍,笑容久久綻放。
晚上,我被邀請到索巴益西的寢室作客,我帶了一些零食,準備繼續追溯他們幸福的理由。
索巴益西的房間光線很暗,兩張很窄的鋪蓋就鋪在地上,看起來很不舒服。我到的時候,他和室友紮西正在煮掛面,面裏有幾根青菜。我猜他一定把所有的零食都擺在茶幾上了,因為這房間裏貧瘠得除了經書和一面念經用的鼓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幾顆蘋果是李師兄今天送給他的。他還用一瓶廉價的維生素E護膚品招待我,也是別人送的。
紮西說他之前住的房間有一只老鼠。趕過幾次老鼠不走,於是裝進盒子裏騎摩托送到山的另一邊,幾天後老鼠又回來了,索性用鞋帶拴在柱子上成了室友。
我們聊得很開心,可我心裏百感交集。這心情直到離開很久才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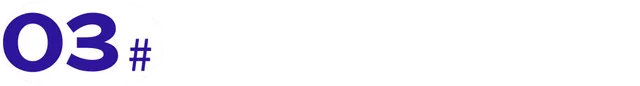
漫長的旅程,我每天都會被荒涼的奇特風景震撼,後來就麻木了。更多時間,那些壯美的景色都在車窗外匆匆流過,每天十個小時左右車程,疲乏的時候會質問自己為什麽要走這一遭?明明早知道很辛苦。
陌生的蠻荒之地,意外是一直提防的,但能防住也就不叫意外了。馬向平透過關系找了位僧人去尋找修行洞。
天氣和心情都風和日麗。附近有很多山洞,路過就進去看一眼,偶爾被飛出的野鴿嚇一跳。最大的洞口有點像女人的生殖器,陸續飛出很多鴿子。我有點擔心在我頭上拉屎,萬萬沒想到,後來竟能肆無忌憚地躺在屎上享受。

圖 | 旅行途中
在洞裏的岔路口,僧人淡然地用手畫了一個圈,語言不通,但我懂,走一圈唄。通道逐漸向下越來越窄,先彎腰再跪下,退?有點難,繼續?又不想趴著爬。
我還是跟上了,鉆下去的過程,我在心裏講臟話了。沒想到鉆出的不是出口,是一個密閉小空間,手機燈一關伸手不見五指。僧人手指的出口看起來特別扯,洞口小得頭插進去就堵死了,我有幽閉恐懼癥,一下就炸了。馬向平先後試了幾次,都被卡在洞口,急得我很想上腳蹬。很快呼吸開始急促。
「快點!缺氧了。」我驚慌地喊。
馬向平終於不顧相機死活,隨著「啊」地一聲,洞口吞沒了他的兩只腳。
「玉海!拉我一把。」馬向平首次發出兔子急了會咬人般的吶喊。
最後剩下最胖的我,沒有退路。我已經忘了爬出來的過程,記得一直在拼命。三四米的隧道像極了產道。掙脫後,我躺在出口的鴿子屎上盡情呼吸卷起的幹屎灰。大腦酥麻,渾身癱軟。
第二次刻骨銘心的經歷是轉岡仁波齊神山的兩天。我期待過頭失眠了,淩晨四點出發,而那裏九點才亮。我們的攝影師沒參加。
說好了我和玉海不等馬向平,他有腳傷太慢,我們在一起就是現實版龜兔賽跑,等我們到了再開車接烏龜。可是走進荒原後,我們有點擔心烏龜被狼當早餐,就走走停停地等。
好在有星空,幹等不無聊,時不時還滑過幾顆流星。不知道是不是我視力的緣故,感覺這兒的星星特別大,特別多,有一種果樹大豐收的感覺。
「星星大跟你眼神兒沒關系,我看也大。」玉海仰著頭說。
天還沒亮我就困懵了,不敢有半點走神,手電的光圈之外很有可能是懸崖。因為馬向平是苯教所以我們反轉,陸續迎面看到很多轉山的藏民。等待是寒冷的,好在有熱帖貼在屁股上才抑制住痔瘡長大。等著等著,玉海的手電光就消失在山邊了。我也暗下決心,天一亮就拋棄這只老烏龜去追玉兔。
我低估了轉山的難度,中午困得走路不走直線。坐在大石頭上按了一百多下打火機也點不著煙,三步一趴朝拜的藏族小夥全看在眼裏,扔給我一個打火機。我遞給他煙,他搖搖頭只顧念經繼續朝拜。他們爬過的土路有明顯的一道道曲線,不追風,不趕景,一點點向前移動。
到了下午,我有點害怕心臟停止跳動,它太微弱了。幹草地被陽光曬得正暖,索性一頭紮在上面一動不想動。第二次紮在草地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眼看著草地不錯,心裏卻不停強調著堅持,一不小心就栽倒了,一不留神又睡了半小時。到營地的最後一公裏我大概用了三個小時,五步一喘十步一歇,艱難前行。
營地的住宿條件很差,平常可能倒給我錢也不會住那麽臟亂差的多人房,可是只有這裏能保命。電話裏,馬向平的聲音奄奄一息,很抱歉我無能為力,只能加油。

圖 | 房間
等馬向平的時候,房間就住滿了,最後換了雙人標間,是個倉庫,沒有燈,墻縫和門縫能擠進來月光,捎帶一縷縷寒風。
馬向平的狀態很糟糕,他發燒了。我讓他多喝熱水,他不好意思喝,因為我得給他倒尿瓶。黑暗中我們也不聊天,我在想這一切圖個啥?估計他在想著活下去。
一只大老鼠在房間裏跑來跑去,我很想趕走它,花一百塊錢都行,但是我沒動,竟然睡著了。
那一夜無夢,是個好覺,第二天滿血復活。馬向平也奇跡般地恢復正常了。我背著包,依然走走停停地等他。爬上海拔五千八的埡口不是件容易的事。
「兄弟。你最好在那邊繞過去,坡度會減緩很多。畢竟只有兩條腿,不是四驅的。」一個內地轉山人對我說。
我看了看不止多走一倍的路程,舉起兩支登山杖大口喘著氣說:「我四驅的。」
在埡口等了馬向平半個多小時,我挨個給家人發了影片慶祝勝利。不妙,頭越來越痛,燒紙和供香的煙加速頭痛。馬向平坐在石頭上,用大口呼吸的方式給命充電,充完電,他還要燒香,還有掛經幡等儀式要做,我知道務必快點下到海拔低的地方,沒等他。
後來,馬向平說看到我蜷縮在草地上一動不動的時候嚇壞了。我只是睡著了,醒來後才發現,頭頂不到一米處有一坨人拉的尚未風幹的野屎,媽的!記得睡前還吃了塊壓縮曲奇和一罐紅牛。
下午在補給點喝甜茶等馬向平的時候遇到一個內地遊客和一個藏族精靈。他們準備翻過埡口到我昨晚住的地方,我極力勸他明天再出發,以我的親身經歷,天黑之前是不可能到的,可他的精靈卻說兩三個小時就可以抵達。遊客看到我的痛苦陷入糾結,不知道該不該走。後來我走了,他還在糾結。
那晚我發燒了,玉海要開夜路上來接我們,我虛弱地堅決沒讓,實在太危險,我不能為了保命拿他的命去冒險。

進藏一個月了,我對廣闊的藏地越來越習以為常,心情不會為風景有過分激動。每天依舊是十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卻感覺很休閑。
我們去了很多寺廟和古遺址,去過唐卡畫師的畫室,見過幾位活佛,吃了很多牦牛肉和羊肉,甜茶、酥油茶。麻木到昨天還在尼泊爾邊境看雪山,今天忽然就在和印度接壤的湖邊餵鳥了。直到進入羌塘領地才回憶起無數個夜晚聽著楊柳松獨自橫穿羌塘的那本書【北方的動地】。
兩驅的車不要妄想走進羌塘,我們試了,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推車是件很炸肺的事。油一定要加滿,不然心裏空落落的。別指望導航,它也懵,有一天我們是淩晨十二點半才找到水泥路的,那是一陣豁然開朗的歡呼。
環當惹雍錯途中我們的車在一片軟沙上失去控制,直奔溝下沖去,萬幸那一段溝不深。要不是我平生經歷過兩次翻車也不會這麽鎮定,劇烈的顛簸中我已經做好了翻車準備。好在玉海開車本領強,它沒翻。
車停以後,馬向平堆在座位上,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前排的靠背。
「摸摸毛嚇不著。」我摸著他的頭說。
他笑了,笑了事兒就不大。
我曾無數次幻想過從羌塘的此端走向彼端的過程,那一定是和孤獨最近的接觸,在生存的邊緣感悟人生,找尋極端的邊緣。當我身臨其境,這裏的荒蕪遠遠超出我浪漫的想象,我是如此渺小和脆弱。
區間測速讓我們不得不在荒野裏等一個小時。下午羌塘的風很大,我獨自站在風裏遙望羌塘的遠方,於是走了進去,走到車只有火柴盒那麽大的位置。躺下,感受和這片土地接觸的感覺。心裏想著「爸。你放心,咱倆最在乎的就我媽,其它追求都次要。」想到這很快起身往回走。
「你幹嘛去了?走那麽遠。」玉海問我。
「剛神經病犯了。」
「太危險了,遇狼怎麽辦?你都看不清。「馬向平說。
「神經病會怕狼麽?竟說那讓人後怕的事兒。「我又回頭看了眼荒原。
接近孤獨需要莫大的勇氣。我該如何把承受孤獨扭轉成淡然接受呢?它離我那麽遙遠又觸手可及。
五月份,我帶著三年前的病例又去醫院了,大夫看完我的病例好奇我又來幹嘛?很遺憾,醫學發展趕不上我視力惡化的速度。但這次我知道病名了——Stargardt(一種少見的眼底黃斑變性)。
這病是一點點變差,已經十幾年了,才混上視力三級殘疾證,讓我無事可做,但距離真正的糟糕還很遙遠。更讓我難受的是整天躺在床上思考我該幹什麽?還能幹什麽?想這些比感冒還難受,是正經八百的精神病。
張大笑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有病——胰臟癌。我知道這事兒後心情很不好,他就用誇張的大笑安慰我沒事兒。旅行出發前我們喝了點酒,在他家二層樓的天台上爭論我是不是神經病?我說我不是,他咬死了我有病。
「你這眼神兒你找死去啊。你不是神經病是啥?」張大笑說。
「我就是不想被安逸活活給溺死。」

圖 | 寺廟老僧
回到家後,張大笑點了一桌子豐盛的菜給我接風。他是個大忙人,想在癌細胞擴散之前多給家人攢點錢,他不太關心我都去了哪些地方。
「玩完之後打算做什麽?總不能啥也不幹吧。」張大笑一臉嚴肅地問。
「學習釀酒。」我絲毫沒有猶豫的回答。
「神經病。」
「我現在知道我真正想要什麽。釀酒是個體力活,感覺上生活質素下降了,但我接受現實。」
「你接受個屁。」
「以我現在的視力狀況起碼體力活我還能幹幾年。一想到余生喝的都是我釀的好酒,還有啥能比這更讓我興奮的呢?我不會因為無所事事失去生活重心。更何況,酒越老越值錢,而我越老越瞎。」
「你根本不了解釀酒,沒你想得那麽簡單。」
「我之前也覺得難。但我相信我能愛上釀酒的過程。造酒曲就是受孕,發酵是在胎中的過程,蒸餾是分娩,入窖才是成長的過程。我要給它們創造一個純凈的世界,遠離喧囂,在最單純的環境裏成長。等我想喝的時候就跟它們融為一體,在我體內完成終極前進演化,我們的融合會產生一種神奇的感受,它叫幸福感。」
「呵。」張大笑不屑地瞥了下嘴。
「不給你喝。我的酒只給有能力讓自己幸福的人喝,那些糟糕的人喝了我的酒我會很心疼,因為酒能讓美好更美好,也能讓糟糕更糟糕。你得好好表現才給你喝。」
「等你酒釀出來給我揚墳頭上吧。」張大笑冷笑著說。
「沒發生的都是未知,只要對未知還有期待就沒有絕望。活著就想好好活著的事。」
我很慚愧剩了很多菜,以前沒有這麽慚愧。之後的兩天還是跟不同的朋友胡吃海喝,他們都過著有房有車卻想換房換車的生活。每次結束後,看到剩下的美食我都能想起那個清晨寺廟老僧人的背影,他安詳地坐在崖邊打坐,面對一片雲海和經幡。(紀永生)
(摘編自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