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張煒先生積澱了多年的長篇力作【去老萬玉家】正式推出單行本。在釋出會上,施戰軍先生從「少年中國」入手,圍繞這部小說的「詩性」與「魅性」展開了一段精彩的評論。施戰軍先生認為, 「大歷史是一種多解的寓言,必須得穿過暗夜當中的驚濤駭浪、崇山峻嶺,才能顯影」 。而張煒先生,就是那個 帶我們穿過暗夜的人。
(本文摘編整理自【去老萬玉家】釋出會上 施戰軍先 生的評論內容)
我在筆記中最早寫的四個字是「少年中國」,舒莞屏到底和「少年中國」是一種什麽樣的關系?但是在小說裏面他數次寫到巨獸,海邊非常罕見的災難性天氣的描繪,大風來了以後把冰坨子掀起來,面對這些東西我想到,就像一匹健壯的小鹿,或者一個非常健碩的、非常俊美的小駿馬,是那樣一個形象。當這樣的小馬、當這樣的小鹿遇到怪獸,他寫的是這樣一種東西。所以【去老萬玉家】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生靈要去巨獸家,就是這種感覺。
這部書從少年的視角開始,其實他寫的是少年也好、民族也好、還是作為人也好,他究竟應該怎麽活,或者說一條命是怎麽撿出來的、是怎麽活出來的。 所以它不僅僅是帶有少年氣、英雄氣的作品,它是充滿煉獄感的,充滿人生磨難感、挫折感的一部書。 盡管有很多美好在安慰著你,在治愈著你,但是告訴每一個「傻白甜」那樣履歷的人,生活其實到處都是黑洞,到處都可能是危險。比如有一個細節我記得非常清楚,大家趕跑了亡靈,終於把那個亡靈趕下海了,「將軍們的臉色比亡靈還黑」。這一句非常有意思,其實是告訴你,在我們的歷史執行當中要戰勝很多魑魅魍魎。

最後一章開頭一段,真是希望大家好好讀讀,十九章開頭這一段是這部小說巨大的交響樂中最重要的華彩片段,它是這部作品真正的高峰書寫,而這個高峰書寫用那樣平靜的語調包容了一切,這裏面到處充滿象征:
「水道初開,海灣裏的冰坨還未化盡。最後一批搭乘冰坨的海豹即將離去。海牛從未知的深處傳來哞哞聲,震蕩未能融盡的冰塊和凍土,讓其發出嘩啦啦的碎裂聲。沙堡島又出現了巨獸」——巨獸在這裏又一次出現,前面就有一次出現,非常明顯的——「它們踏出了陌生的蹄印,一溜溜凹坑裏堆積了鳥毛和雞肋。沒人識得這蹄痕,只從深度和尺幅上猜測體重,判定這是一頭水陸兩棲動物,於大荒之年出來溜達。它吞噬了陸地上的一些生靈,深夜潛回大海。」
嶺南也好,膠東也好,到處充滿了水陸兩棲的、水和陸地交接的地貌。跟歷史的選擇一樣,你到底是選擇水,還是選擇土?水土相接的地方,就是歷史的交匯點,膠東的巨大象征意義就在此。
我剛才說大的方面看它是生命小說,這個生命怎麽完成?它是魅性和詩性互為表裏完成的。魅性部份就是歷史,這個歷史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巨獸,充滿魅性的巨獸;而詩性部份就是水道。自然和歷史就在魅性和詩性之間來回地轉換、生成。所以每個人的成長,包括美少年的成長,都是在圍困和執念之間不斷搖擺突破的。
所以大歷史是一種多解的寓言,必須得穿過暗夜當中的驚濤駭浪、崇山峻嶺,才能顯影。 所以大歷史無處不在,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也是在大歷史中。

【去老萬玉家】
第十九章(節選)
水道初開,海灣裏的冰坨還未化盡。最後一批搭乘冰坨的海豹即將離去。海牛從未知的深處傳來哞哞聲,震蕩未能融盡的冰塊和凍土,讓其發出嘩啦啦的碎裂聲。沙堡島又出現了巨獸,它們踏出了陌生的蹄印,一溜溜凹坑裏堆積了鳥毛和雞肋。沒人識得這蹄痕,只從深度和尺幅上猜測體重,判定這是一頭水陸兩棲動物,於大荒之年出來溜達。它吞噬了陸地上的一些生靈,深夜潛回大海。
沙堡島周邊幾十裏鬧起了饑饉。因為冰天雪地封鎖了訊息,所以整整一個冬天島上沒人得知噩耗。在村鎮街巷和小徑旁,死去的人變成一具具冰坨。雞狗鵝鴨和貓倒在路旁、冰面、人的身側。凍土融化了訊息,山地和平原傳來十年罕有的恐懼:人們吃掉最後一把糧食,又尋找糠末和樹葉,吞下被子裏的絨絮、軟細的泥土,啃焦幹的冰。夏天和秋天並無大災,人們都記得結實的玉米和大片搖蕩的麥穗,記得一群群麻雀在飽滿的籽實上捲動,見過渠裏的魚蟹喧騰躥跳,怎麽一下就變成吃喝無著?知情人捂著嘴巴相告:大城池入冬前把囤裏的糧食全部拉走,藏下一點隔夜糧又被將軍搜光。所有人都在熬冬,有幸熬過來的,就眼巴巴等著賑災了。春天就是這樣的日子,府上會派出賑災大人,這些人手持刀劍押送救命的吃物:成袋的米糠、地瓜屑末、魚的下水和一桶桶稀湯寡水。
府上大人除了全力賑災,還要帶頭辟谷,讓大藥堂的老道以身示範。一沓沓石印的「大公縮食歌」和度過饑饉的「四十六字訣」隨賑災物品一起發放。緊急時刻來臨,大城池的巡督分批派出,去海邊獵場和種植場,甚至是火器營調撥物資。種植營的六十石糠末、漁獵場的二十車魚下水和帶魚尾巴、火器營的十幾個大湯桶,都在催促之下姍姍來遲。小棉玉走出熱氣尚濃的冬房子,戀戀不舍地換下新娘嫁衣上路了。她是首屈一指的巡督,說一不二,所以每逢困局必要出行。一行人由車馬衛士組成,說不上浩浩蕩蕩,也算得上威嚴齊整。他們身著厚厚的禦寒冬裝,捆紮皮帶,手持刀械,直赴巡地。這次巡行首去漁場和捕蜇場,那裏的春捕即將開始。巡行是為了督促調集大宗應急食物,以解大城池周邊燃眉之急。
舒莞屏與夫人小棉玉同乘一輛騾車,一路神色冷峻。舒莞屏聞聽十余年來最為嚴重的災情,悲傷沮喪,跟隨身負重任的新婚妻子急急上路,不再顧及其他。當他得知要將漁場剖下的雜碎悉數運回,連剪除的細繩般的帶魚尾巴也要收起,忍不住問:「為什麽不取走整條帶魚?」小棉玉答:「獵場是銀庫的最大進項,捕蜇場和種植營也是一樣。府中開銷、購買火器,所需銀兩都出自這裏。」「死人的事最大啊!」「正是。銀庫空了,什麽都空了,那會死更多的人!」
寒風正烈,海邊的春天總是遲緩。隨著接近大海,無數鷗鳥揚在半空,各種水禽追逐呼鳴。蟄伏結束,半截入土的窨子前,漁人扛著抓鉤爬上高坡,翻皮帽的護耳在風中像鷹翅一樣扇動。海邊人除了要穿厚厚的蒲絨衣褲,還要圍裹油布,一個個都像傳說中的食人獸。離海岸幾十丈遠,高大的窨子一排排出現,這是為即將開始的春獵搭起的主營。營中主管是說一不二的魚把頭,手下有三個副頭領,還有一支火銃隊,個個都是兇神惡煞。魚把頭相當於軍營總兵,一年四季都是這裏的國王,漁人是奴隸。小棉玉和舒莞屏一行直奔主營,離那排窨子近了,魚把頭率人迎來,連呼「巡督大人」,躬身行禮。
「災情諸事想必你已知曉,獵場須按府中牒令辦理,不得有一絲差池。」小棉玉直言不繞,表情冷肅。魚把頭仰頸答道:「大人放心,咱這裏一根魚腸子都不會扔。」小棉玉瞥瞥他隆起的肚腹,問:「這個冬天過得還好?」「稟大人,托府上大人的福,今冬還好,只未聞南面饑饉之事。」小棉玉轉身看忙碌的人群,他們正扛著舢板,喊著號子往浪湧那邊挪動。海中不斷推上沙岸一些綠的紫的海菜,它們被勞作的漁人踩到了沙子裏。小棉玉說:「所有海菜都不得踐踏,要堆在一旁,待車子運去賑災。」魚把頭略有驚色,說:「好的大人!」
午餐時所有人都在車中用過。食盒開啟尚有余溫,蒲絨隔層裏是幾只盅缽和蓋碗。災年飲食,不過是薯片醬瓜、幾片鹹魚、一點甜粥。「比起饑號之人,我們也該感恩府上了。」小棉玉說。舒莞屏喝下一口甜粥,小聲問:「我在想,淩晨時分冷大人還喝咖啡?還有,萬玉大公還用海參魚膠盅?」小棉玉看他一眼,未語。餐後車馬急急上路,奔往下個漁場。預計要在那裏過夜,再沿水道往南,過河向西,去捕蜇場。
後半程風小了些,天空雲朵散開,頭頂出現了鳴唱的百靈。「有點春天的樣子了,提調大人。」舒莞屏說。小棉玉囑一聲:「這不像夫君之言。」「是的,大人諒之,我不過是叫慣了。」他為自己的失言感到抱歉。出行前言定:在人前須有夫妻模樣。好在這是車中對話。下車時,舒莞屏不忘攙起小棉玉,而她則摟緊了那條屬於自己的左臂。漁場一夜甚是愜意:天氣晴好,月亮升空,全然沒有酷寒之象。餐後夫婦二人走到野艾叢生的營地空場,身後一兩丈遠是三個衛士。他們相攙而行,小棉玉貼緊夫君,呼吸噴上他的臉頰。因為營中頭領招待了烈酒,二人盡管淺嘗輒止,還是有些燥熱。小棉玉望一眼月亮,說:「我的公子,我的夫君,一匹拴不住的馬兒。」舒莞屏說:「你是我認定的純良之人,沒人比你更溫順,也沒人比你更仁善。我夜裏難眠,總在想一件事。」「何事?」「我在想,既是姐弟,為何不能一起出逃?」小棉玉急速抽手:「不可!公子,我是不會離開的!」「為何?」小棉玉低頭:「我已是紮根在沙堡島上的一棵樹,拔脫了會死。」
夜晚他們宿在一間稍為潔整的窨子裏。這裏火炕溫熱,還有一座土爐。小棉玉依伏在他的身旁,半夜仍無睡意。舒莞屏對著她的耳廓說:「小棉玉,我無時不在謀劃那件大事。這裏的春天來得太慢了,等連翹花謝了,我就上路。」「公子,求你今夜不再說它,可好?你知道我多盼一起出行!我覺得這裏比婚房更好,不是嗎?」舒莞屏的手撫著她的額頭、眼睛,說:「所言甚是!我們逃出了那間囚牢,也就舒暢許多!」

×
張煒 【去老萬玉家】

此書寫了大變局將臨的19世紀末:從廣州同文館回半島探親的青年舒莞屏,回程突遇風暴,借輪船延誤之期完成恩師重托,前往聲名遠揚的萬玉大營,由此開啟步步驚心之旅。從熱血沸騰的崇拜到摧肝裂膽的悲絕,從無法抗拒的誘惑到深冤凝結的仇讎,九死一生,舒莞屏最終沖出魔窟羅網。
這是一個韌忍和藐視、周旋和看破、決絕和撞碎的青春故事,一部艱難完成的世紀驕子傳奇,一場遲遲到來的男子成人禮。 此旅之後,未來將不存任何奢望和僥幸,更不再膽怯和畏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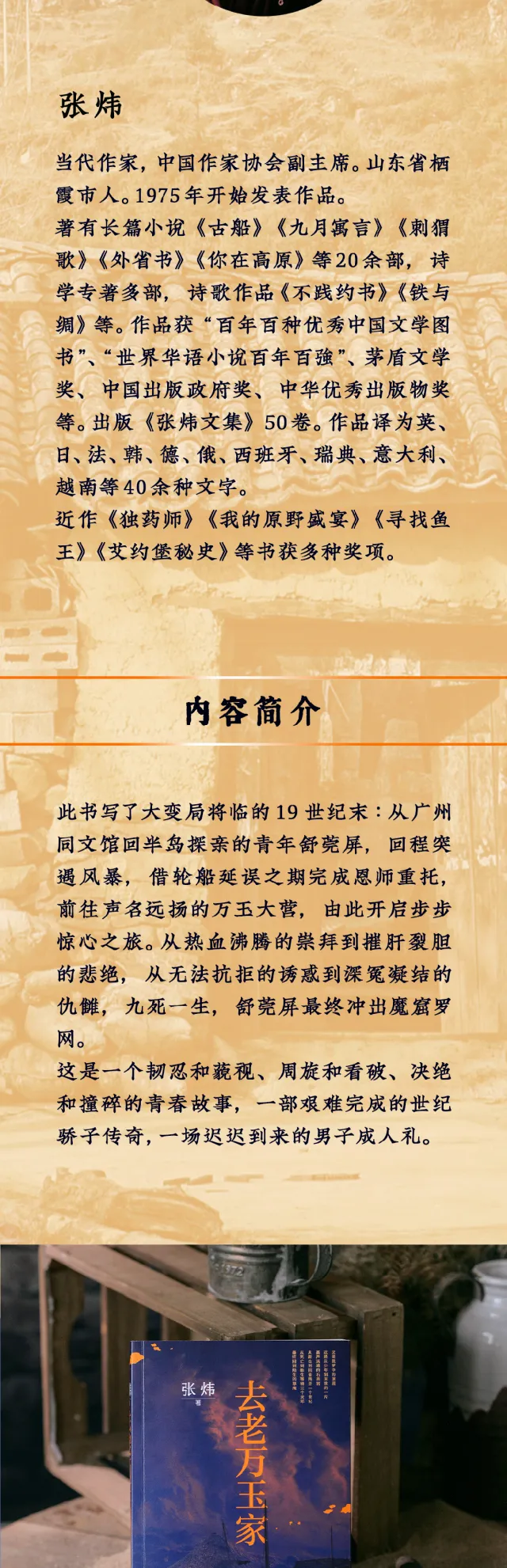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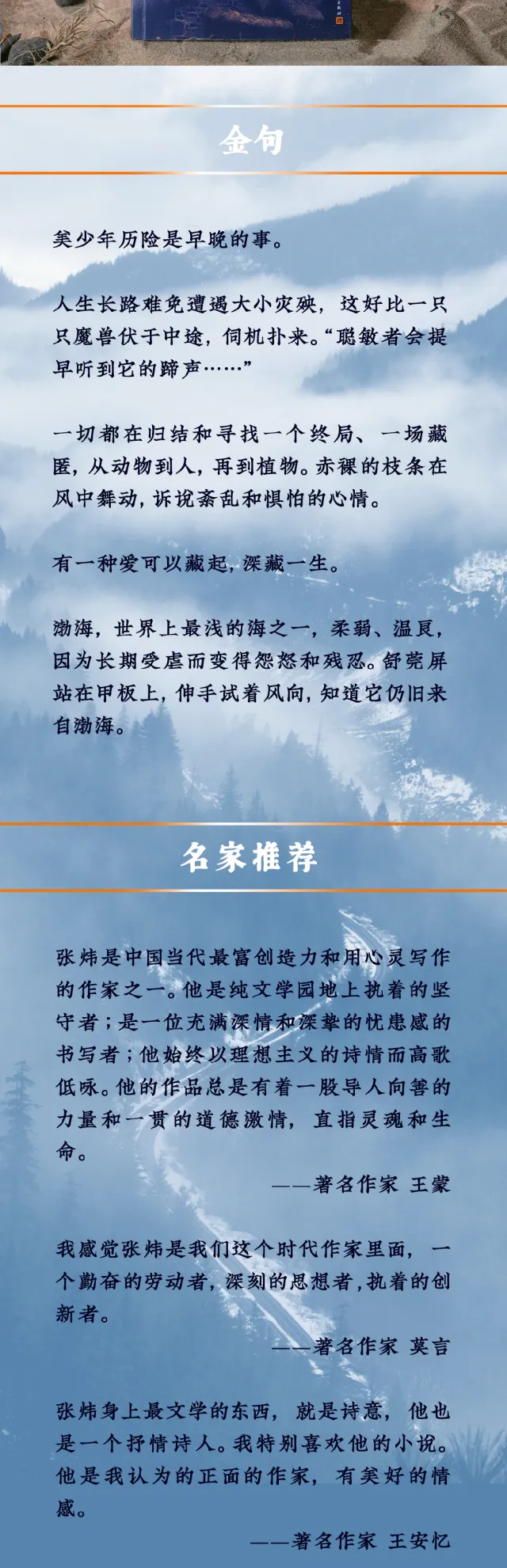

稿件初審:周 貝 張 瑤
稿件復審:張 一
稿件終審:王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