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第一人稱寫故事,故事來源於生活,請別過分解讀!所有作品皆今日頭條原創正選,抄襲、搬運、洗稿者可恥!)
文/白鷺湖姑娘 素材/張力輝
昨天,我和妻子去出席發小鄭玉軍的兒子 鄭壯壯的婚禮,本來應玉軍妻子王蘭和孩子們的請求,讓我當證婚人的,但我這人比較感性,怕到時候我情緒失控。
因為壯壯的婚禮,缺了玉軍的身影,一想到這,我鼻子發酸,眼淚就會止不住的流,本來是孩子大喜日子,我不能那樣。
望著台上一對新人甜蜜的四目對視,我在心裏默默念道:玉軍,我的好兄弟!你看到了嗎?孩子長大成人了!你在那邊可以放心了!
下面我來給大家說說我和發小鄭玉軍之間親如手足的故事

我叫張力輝,今年56歲,出生在江淮流域的一個小村莊,家裏姐弟3個,我上面有2個姐姐。
我父親早年在縣城一家機械廠上班,但找的物件、也就是我母親,是農村姑娘,婚後生下我們三個孩子的戶口自然隨母親,也在農村。
我們是典型的「一工一農」的家庭,即:父親一個人在縣城上班掙薪金,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在老家種地,雖然那時候日子過的不寬裕,但跟別人家相比,我們還是挺幸福的。
父親是個顧家好男人,只要有空就會從城裏坐車往回趕,給家裏添置生活用品,給我們買零食、水果。尤其是分田到戶後,一到農忙季節,父親還得請假回來,因為那時候我還小,才十幾歲,家裏沒有男勞力不行。
記得那時候我們家總共有7畝多地,分田的時候抓鬮,我們家跟其他兩戶人家搭幫飼養一頭老黃牛,三家20多畝地,就指望這老黃牛耕地。
我父親雖然是農家子弟,但種地並不內行,更不會犁田打耙。我倒是有個親大伯,但他家地多,而且大媽心胸不開闊,偶爾找一回大伯犁田,好酒好菜招待著,還把大媽叫過來一起吃飯,那大媽也不樂意。
有一次我母親無意間聽到大媽跟別人抱怨說:「有錢咋啦?有錢就能使鬼推磨?咱不稀罕吃他家那頓飯!‘年三十的砧板’,誰樂意往外借?」
言下之意,找大伯幹活,大媽不高興。
那怎麽辦?涼拌!自己學唄!
於是,當工人的父親半路出家,開始學犁田。也幸虧我家分的是黃牛,性子溫順,如果是大水牛,估計我父親也不敢。
如今一想起父親當初學犁田,我們都忍俊不住,真是出盡了洋相,連使喚牛的口令都說錯了!
沒在農村生活過的朋友們大概不知道,牛犁田也是從小要調教的,在我們老家叫「告使」(這裏的「使」方言讀suǐ),即小牛長成後,由老農帶著下地幹活,教它們聽口令,「駕~」就是走;「臥」就是停下,跟草原上套馬桿馴馬是一個道理。
可能是我父親電影看多了的緣故吧,他不按套路出牌,「駕~」口令喊的對,老黃牛聽的懂,那是讓幹活呢。可讓停下來,我父親不知道喊「臥」,而是扯著嗓門大聲命令道:「立定、立定~~」
天吶,老黃牛哪裏聽的懂,它從小沒人這麽教它呀,所以還往前走,氣得我父親用牛鞭子使勁抽它!
老黃牛被抽的後背生疼,哪有不走之理?於是加快步伐走的更快!氣的我父親吹胡子瞪眼睛,把我和姐姐在田埂上笑得前仰後合,然後被父親罵了一頓,我們這才乖乖走開,躲到旁邊接著笑。
總之,每年大忙季節一過,把父親曬成「非洲小白人」。所以當有人再說「一工一農,快活賽洋熊」時,父親把詞改了,叫「一工一農,累的精慫!」
累是累,但地必須還要種,因為那時候農民每年都要上繳農業稅,公糧都是裝揚場上風籽粒飽滿的稻谷,把下風稻留著自己家吃。

我小時候淘氣,學習成績也不好,每次作業完不成,我就讓跟我家住隔壁的鄭玉軍幫我寫。
鄭玉軍只比我大10個月,我們倆是同一年出生,也都是各自奶奶帶大的。老人們那時候也不是專職帶孩子,還得貪著忙家務,所以我和玉軍打小關系就好,一睜眼就聚在巷口那棵老槐樹下玩耍,什麽「慣響炮」啦,「扇畫牌」啦,「彈玻璃球」啦,等等,都是我們每天要上演的節目。
可若論家庭條件,鄭玉軍差我一大截,他父母就是靠土裏刨食的莊稼人,爺爺是個「藥罐子」,常年有病,為了生個男孩,鄭玉軍上面有3個姐姐。
孩子多的農村家庭,條件大多不太好,所以每次看到我拿著蘋果橘子吃的時候,鄭玉軍都眼巴巴的瞅著。
每到這個時候,奶奶就讓我切一小塊給玉軍,我當然不吝嗇,我怕玉軍不跟我玩。
玉軍雖然是家裏唯一的男孩,但父母並不嬌慣他,所以小小年紀的他,地裏許多活都會幹,而且他有把子力氣。
記得有年我家種了8分多地的春玉米,母親帶著兩個姐姐把玉米棒掰回去後,玉米稭稈還杵在地裏呢。
一場雨過後,旱地棉花急需鋤草,母親她們忙不過來,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母親就讓我去砍玉米稭。
玉米稭用途多,不單單能當柴火燒,還可以挑直溜的編成竹笆,用來曬棉花。
所以我一上午大概砍了一半,中午回去的時候,正碰到玉軍坐在門口聽廣播劇。
於是,我開玩笑的說道:「玉軍,你這曉得快活哎,還能聽廣播,下午陪我去砍玉米稭唄。」
其實我當時就是說著玩的,結果還沒等我吃完飯,玉軍就拿著鐮刀找我來了,他真的要陪我幹活去!
就這樣,那天下午我們不但把玉米稭砍倒,隨後看看天還早,玉軍又跟我一起,把玉米稭抱到田埂上,用板車拉到家門口。
望著我們倆累的滿頭大汗,母親心疼的跟啥似的,誇贊說:「還是要養兒子,力氣大。」
那天晚上母親特意炒了幾個菜,把玉軍爸也叫過來一起吃了晚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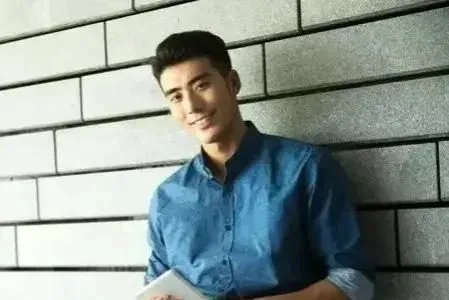
轉眼我和玉軍初中畢業了,但都沒考上高中,按我家的條件,完全可以復讀一年再接著考的,但我對上學不感興趣,說啥也不去。
就這樣,我和玉軍正式回鄉務農了,記得有人建議我們去學個木匠,但那時候我們才16歲,父母覺得有點早,說再等等。
不久我大姐出嫁走了,二姐去學裁縫,家裏的地基本就我和母親在家種,這時候我開始認慫了,覺得種地太累,正好縣城有幾個廠在對外招工,可以花錢買城市戶口,被安排工作。
就這樣,父親花了3500塊錢,讓我農轉非,進了一家肉聯廠上班。
其實我父親也跟玉軍爸媽說了買戶口的事,但他們家拿不出這麽多錢,就這樣,我和玉軍分開了,我當了工人,他還是農民。
只不過縣城離的不遠,我基本保持一個月回家一趟。每次回去,我都要去找玉軍玩,送他嶄新的工作服,紗手套,給他講外面有趣的事,他還陪我一起去釣魚,我們倆絲毫沒有生疏感。
自打我二姐出嫁後,考慮到家裏沒勞動力,母親身體也不好,後來我們家只種了一畝多地的口糧田。
正好這一畝多地跟玉軍家是上下埂,每次只要犁田,玉軍順便就把我家的給犁了,母親就按「帶莊稼」的標準給玉軍錢,結果玉軍生氣的對我母親說道:「二媽,我也就是順帶手的事,憑我跟力輝之間的感情,給錢太見外了!」
當然,玉軍所做的一切我們都記著呢,只不過換其他方式去表達。

89年春天玉軍的女朋友就談好了,年底結婚的,憑著我跟玉軍多年的感情,我特意請假回來,送了他一盞精致的台燈和一套玻璃茶具,母親還隨了10塊錢的禮。
這些在當時的農村,也算是重情了。
玉軍的妻子叫王蘭,長的眉清目秀,性格也好,婚後第二年生下大女兒文靜,但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嚴重,兩年後二女兒婷婷出生。
那個時候農村計劃生育已經開始嚴抓了,但為了生兒子,王蘭和玉軍也成了超生遊擊隊,東躲西藏最終生下兒子壯壯。
這期間因為被罰款,莊稼也被耽誤,玉軍家的日子一落千丈,「因生返貧」。好在穩定後,玉軍回家承包了養魚塘,我還借給他2600塊錢買魚苗。
本以為我當上工人,就是端上了「鐵飯碗」,殊不知更嚴峻的考驗在等著我呢。
我是93年結婚的,妻子是幼稚園老師,婚後第二年兒子張沛出生,母親那時候風濕性關節炎已經非常嚴重了,連帶孩子都勝任不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不久我所在的肉聯廠開始裁員,我屬於是第二批下崗職工。而父親的機械廠也沒撐多久,隨後也解體了。
兩個工人全下崗在家,母親一個農村婦女,哪經歷過這些?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
不知道誰把我和父親下崗的訊息傳到村裏,有天一大早玉軍兩口子來了,玉軍扛了一袋子米,手裏拎著一只塑膠水桶,桶裏用水養著七八條活蹦亂跳的大鯽魚。
王蘭胳膊上挎了一大籃子菜,還有一個紙盒子裏裝了幾十只雞蛋。
玉軍安慰我說:「別著急,慢慢找活幹,不用擔心其他的,我在農村種地,不會讓你們餓著。」
那一刻把我激動得差點流眼淚,人在最脆弱的時候,有一句暖心的話,足可以銘記一輩子。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父親跟兩個關系要好的同事開了一家修理廠,如此一來,至少解決了工作問題。
說實在話,改革開放那會兒,只要你有魄力,敢幹,幹啥啥掙錢。
沒幾年的時間,父親的修理廠規模擴大了,除了賣農機配件,還經營各種農用車,尤其是2003年後,生意再上一個新台階。
但母親沒福氣,病情不斷反復,於2010年冬天去世了。
因為常年不在老家,母親的喪事也幸虧有玉軍的幫忙,他跟著忙前到後,真的比親弟兄都給力。
但厄運正悄悄的向這個善良的人逼近。
2012年的3月份,有天上午我正在公司卸貨,口兜手機響了,當時正忙著幹活,我沒理會,直到把活幹完,掏出手機一看,是玉軍打過來的,我趕忙回撥過去,問問什麽事,結果接電話的是玉軍的妻子王蘭。
簡單問候幾句,王蘭向我打聽,問縣醫院也有沒有熟人,玉軍這段時間不舒服,到醫院檢查一下,不過已經掛上號了。
我當時有些緊張,說這就去看看,但王蘭說暫時別去,他們檢查完就回去,連讓他們留下來吃飯都不肯。
我只好作罷,但心裏還是惦記著玉軍,正打算抽時間回去看看時,王蘭電話打來了,哭著說玉軍檢查結果出來了,是肝癌晚期!
我當時一聽傻眼了!半天說不出話來,於是我安慰說,檢查不一定準,我開車回去接他們再復查一次看看。
其實我有一種預感,玉軍情況肯定不好,因為他爸就是肝病去世的。等我著急忙慌的趕回去後,玉軍反而比我鎮定,他笑著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為了進一步確定病情,我讓妻子打電話給她在省立醫院的哥哥,幫著聯系專家號。
後來結果出來了,跟縣醫院一樣。
本想著瞞著玉軍,怕他有思想負擔,但眼神出賣了內心,在玉軍的再三追問下,我只好說肝部有囊腫,不過大夫說沒事,配合治療就行。
玉軍苦笑著點點頭,便不再說話了。

怕治療費不夠,我給了王蘭2萬塊錢。
但再多的錢,終究買不來健康,幾個月後,玉軍病入膏肓,為了節省開支,玉軍轉院到了縣醫院。
其實這幾個月來,我和玉軍之間從來沒正面談論生死,都在刻意回避這個問題,更希望奇跡的發生。但有天下午,等王蘭出去買牙膏後,玉軍拉著我的手,含著淚說道:「力輝,其實我倒不怕死,只是擔心往後我不在了,這三個孩子怎麽辦?兩個女兒還好說些,就是壯壯要給他娶妻安家,王蘭一個女人,沒這個能力啊!」
聽到玉軍說到這,我眼淚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玉軍在準備托孤啊!
我用力握緊玉軍已經沒有血色的手,安慰道:「玉軍,先不想那麽多,安心養病吧,車到山前必有路。」
玉軍苦笑著搖搖頭,輕輕的嘆口氣,接著說:「我知道這個病沒希望的,就是孩子還小,真舍不得啊……」
不等玉軍說完,我們兩個大男人已經泣不成聲……
在玉軍的一再要求下,不久他就出院了,這意味著回去等死。
一個星期以後,44歲的玉軍帶著滿腹的遺憾走了,留下妻子王蘭和三個孩子,當時大女兒21歲,二女兒17歲,兒子壯壯才14歲。

玉軍的兩個女兒挺懂事,在玉軍走後更加知道替母親分擔家庭的重擔,但兒子壯壯正趕上逆反期,有段時間不太省心,我只要有空,就和妻子一起開車回去看看,鼓勵鞭策壯壯要好好學習。
壯壯也挺爭氣,後來上了一所師範大學,王蘭卻為日後學費發愁,雖然有兩個女兒幫襯,但她們自己也有小家庭,總是貼補娘家,怕女婿有看法。
我那時候已經把父親的公司接受過來了,每年效益都不錯,於是我對王蘭說:「壯壯上學的費用你就別操心了,有我呢。」
就這樣,壯壯四年大學,每年學費都是我資助。
轉眼間壯壯大學畢業,在縣城一所高中任教,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後,接下來就考慮買婚房。
自打玉軍去世後,王蘭一個婦女哪有能力掙錢,後來在我的建議下,把魚塘轉租出去,這樣每年也有一筆收入。
前幾年王蘭就想給壯壯按揭一套房,但那時候房價太高,我建議再等等。
前年壯壯的女朋友也談好了,買婚房成了當務之急,也算走運,房價降了下來,去年壯壯婚房也買了,一切水到渠成。
昨天在婚禮現場,王蘭領著兒子兒媳走到我和妻子面前敬酒,當著眾人的面,王蘭說:「壯壯,以後改口叫大伯為‘大父’,沒有他,就沒有你的今天!」
「大父」在我們老家可是對最敬佩的父輩人的尊稱,可見我在他們一家人心目中的份量!
未來的日子裏,我希望壯壯一路順遂,我也可以告慰玉軍在天之靈了!
半生兄弟,一世情緣!
(本文寫於2024年5月15日早上6:06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立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