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絕成為天才鸚鵡】是美國作家賓·勒納首部引進國內的作品,也是一部半自傳成長類小說。小說故事跨越四十余年,記錄美國高中生亞當的成長歲月,及其心理治療師父母莊拿芬與簡的人生,探討當代美國社會多種困境、癥結。
何謂「天才鸚鵡」?它源自小說人物簡的童年往事:在母親簡年幼時,她的父親只願購買一元店餐巾紙盒作為禮物,為掩蓋禮物本身的寒酸,父親虛構了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裏,人類選拔有潛力的動物,例如猴子和鸚鵡,訓練它們說話畫畫,父親聲稱,簡收到的這個餐巾紙盒,就是由一只天才小狨猴創作的。

這段記憶以人物意識激流的方式出現。事實上,當我們閱讀這部作品時,人物的聲音常變換「時間錨點」:簡可以從描述紅州極右翼人物,跳轉向自己的童年陰影,再跳轉向亞當的辯論賽現場。而敘述者的聲音,常被淹沒在人物大量的內心獨白中,幾乎難以區分,共同自由地穿過時間屏障,在當下、過去間反復橫跳。
時間被切碎,成為萬花筒中的紙屑,隨著人物意識的流動,組合不同花樣。非線性時間結構——這樣的創作手法曾在福克納的意識流經典之作【喧嘩與騷動】中熠熠生輝,讀者常常會有不知身處何時何地的陌生感,需要重新慢慢適應摸索。在這兩部小說中,空間的變化皆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過程,這與難以琢磨的時間元素相互制衡:在福克納筆下,隨著美國南方經濟的沒落,地主康普森家族的大宅被分割成小格子間出售;在賓·勒納的書中,亞當父親工作的「基金會」——心理研究療養院,在亞當成年後被廢棄,被破壞。空間的變化錨定了漂移的時間,也指明了兩部小說各自的主題:美國南方的挽歌、美國當代社會頑疾何解。
除卻時空處理的相似性,以白癡作為主要人物的創作手法,令【我不是天才鸚鵡】與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顯得極為親近。

論及白癡這一文學符號,不得不先從【喧嘩與騷動】的書名出處說起——莎士比亞名劇【麥克白】。全句為:「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台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福克納也的確創造出了一個文學史上著名的「愚人」——班基明,33歲的他僅有3歲的智商,被母親視作家族衰落的征兆。除了姐姐凱蒂和管家迪爾西,沒人愛他。但諷刺的是,被所有人厭棄的班,是一個巨大純凈的嬰兒,保持著人類最初蒙昧的狀態,未沾染一絲世俗塵土。他有著上帝的銘印,能聞到厄運,他的嗚咽度量著家族的悲劇:「接著班又嗚咽起來,絕望而悠長。它什麽都不是。只是聲音。似乎是行星交會令所有時間、不公和苦難頃刻間化作語聲」。這個寓言式人物與基督緊緊相連:班的33歲與耶穌的33歲重疊,後者在這個年紀被釘在十字架上。班的生日為1928年4月7日,是神聖禮拜六。只有班能夠嗅到凱蒂身上樹的清香味,即使在她陷入性的「墮落」時,他依然確認她的純潔;只有他能在這沒落家族奄奄一息的陰郁氛圍中,從火焰的明亮形態中獲取慰藉;而也只有他能夠從現實的浮塵甚至自身的皮囊中進行自我剝離,守護記憶中的三個摯愛——凱蒂、火焰、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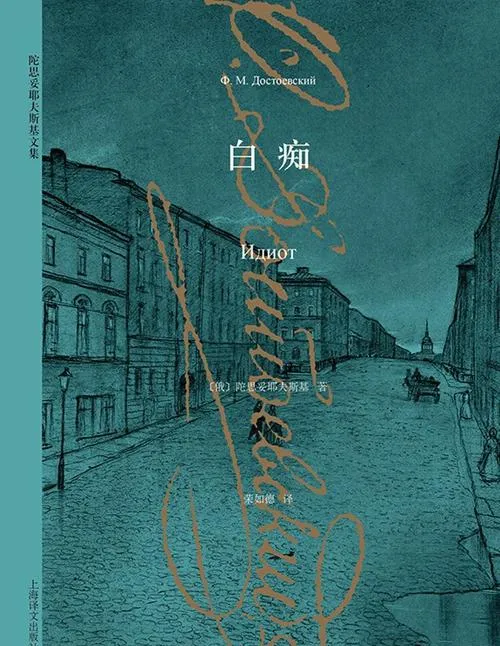
班有著明顯的「聖愚」特質,而聖愚曾於19世紀的俄羅斯文化及文學作品中非常活躍。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梅什金公爵便是最著名的一位。巴哈金認為作為主要人物的瘋癲或癡傻之人,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另一種處理方式,意即另一種視角、另一個聲音,有跳出既有框架點撥他人的功效。在中國古典名作【紅樓夢】中,瘋癲的一僧一道也是類似的文學符號。
【我拒絕成為天才鸚鵡】中的白癡戴爾,雖和班一樣,處於自己的邏輯中,但依然對外界的沖撞極為敏感,他介於兩個世界之間。作者以跳躍的記憶碎片再現戴爾那不受控的混亂大腦。不同於班那至純的回憶,柔美又遙遠的童年之夢,戴爾的記憶充斥著現代社會的殘忍冰冷、焦慮恐慌,神經質的怨憤隨時爆發。他無法精準接收現實,但能夠感應到現實中的憤怒微粒:他遭受同學的欺辱,頻繁光顧亨通街上的軍品店,常年穿軍用工裝褲,吸收店老板斯坦的種族歧視言論。成年後的他佩戴槍支,成為憤怒的紅脖子。如果說書中其他人物是當代美國大眾的縮影,那麽戴爾則既是縮影的縮影:一個貨真價實的男人—男孩綜合體;也是縮影的鏡子,投射他們無法吐露的內心,正如賓·勒納所言:
帝國特權臣民的變態形式。如果他是女人或另一種族或另一形式的他者的身體,他就立刻面臨性侵犯和警察帶來的致命危險。正是他與那些占優勢者的相似才使得他成為可憐人和挑釁者……他離規範太近,其他人無法用他的不同來證明自己,於是那些真實的男人——他們自己其實是永遠的男孩,因為美國就是無盡的青春期——就只能用暴力來顯示自己的不同。
白癡戴爾雖缺乏班動人的聖潔,更接近一個社會邊緣人物,但依然保留著寓言式人物的特質。戴爾也有屬於他的超驗場景:在許願召喚龍卷風後,風暴的到來令他驚覺自身的「法力」,這當然是偶然性助長了這個四歲孩童的幻想與精神冒險。但另一方面,戴爾雖錯亂、笨拙,但也直覺敏銳,在不自覺中,洞察現代社會執行模式的脆弱、現代社會荒謬的空洞:當一件商品掃不出來碼,需要人工核對價格時,戴爾意識到他「無法解釋為什麽註明價格的標簽會等距離處於兩種相似但卻不同的罐頭之間」,「只有當他這樣站在貨架前渾身冒汗時,才意識到1996年整整一年狄龍超市都在迴圈播放著背景音樂」。
在這兩部小說中,白癡這一文學符號皆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而,不要誤解,作者並非將整個虛構的世界置於一個人物的視角之下,多視角敘述是兩部作品的重中之重,極大擴充套件創作的深度與廣度。
【我拒絕成為天才鸚鵡】分為7個章節,以亞當、莊拿芬、簡的視角敘述,每個章節之間以白癡戴爾的視角敘述連線。構成「十」字型結構,復調書寫——同一個現實被多元視角分割為多面向立體物質。人稱的豐富多樣增加作品的層次感:作者賦予父親莊拿芬、母親簡第一人稱,亞當的章節則和白癡戴爾一樣,是第三人稱。直到小說的末尾,人稱在一個自然段內悄然扭轉:在一場亞當參加的辯論賽現場中,簡與丈夫莊拿芬坐在觀眾席上觀看,就在亞當即將登台之時,簡的第一人稱敘述「我」突然扭轉為第三人稱「她」,而登台的亞當則占據了第一人稱「我」的位置。這種人稱的扭轉可以被視作人物主體性的更叠,這種代際更叠在小說的最後一個章節【主題統覺:亞當】得到全面終極的蔓延。
多人物多視角描寫的手法,是【喧嘩與騷動】的拿手好戲。但細看之下有所相異,這種不同不僅來自所書和所述的時代的相異,也體現在人物創作上。這涉及作者對人物塑造的看法,以及作者本身與人物之間距離的拿捏:賓·勒納在不同人物的各章節中,保持同質的敘述音色、語氣緩急,根本原因在於,作者將夾敘夾議——昆德拉式的小說創作手法進一步內化,將作者自身想要輸出的觀念與批判,內化到人物的內心獨白中去,筆法不再完全服務於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由大量觀念組成。相比之下,福克納的筆法更傾向於賦予人物實在的血肉,他註重創造人物的語氣,因為語氣是性情和價值觀的延伸:超驗的班,神經質的昆頓,市儈冷酷的傑森。雖說福克納以文學技法和晦澀著稱,但他的小說在復雜中有著極為嚴謹的細節設計。一個動作、一個地點都能夠勾起班的回憶;現實的片段無法阻止班繼續沈浸在過去的回憶中,於是現實讓位於記憶。讀者只要熟悉這種模式的韻律,那麽班的篇章就會從晦澀轉為明晰,一個白癡的錯亂大腦也就變得有跡可循。而昆頓那些不帶標點符號的意識流長句,其波浪的匍匐形態和班的碎片跳躍感形成美學上的對位。第三章,則由傑森小市民的低下感構建,為這個家族的終結打下基礎,最後一章以家仆迪爾西的悲憫視角為整個康普森家族的消亡進行哀悼。

福克納的動人筆調,有流淌的大河慟哭,其作品憑意象驅動,描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Yoknapatawpha)世系。而賓·勒納則以智性收集和剖析橫亙在眼前的世界:女權主義、兒童虐待、階級對立、郊區暴力、難民和人道主義問題、種族主義、語言的社會功能問題,乃至外交關系一應俱全,但不顯臃腫。這些議題被散落在小說的三大面向中——一位少年的成長史、其家庭的動態走向、家庭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系,賓·勒納以此入手,探討自我認同、身份探索,全方位觀察整個時代。這樣的創作思路與美國導演林基利特十分相似,後者在其代表作【少年時代】中,亦是從這三個面向,展示職業與家庭的動蕩、種族問題的復雜,酗酒家暴陰翳之下的社會壓力,將人物境遇與內在掙紮融入到故事中。同時,賓·勒納與林基利特都註重描繪細碎的商品:從說唱歌手圖帕克、喜劇【宋飛傳】,到相容iPod的音箱、GameBoy、Xbox遊戲機。正是這些琳瑯滿目的文化消費品,與社會問題,一同構建人們的生活。
在這幅完整的當代美國社會圖景中,關於語言的社會功能的討論貫穿整部作品。眾所周知,演講、辯論,是美國政客的基本素養,更是美國政體的關鍵基石。賓·勒納借人物簡之口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演講和辯論的技巧是否已卓絕到脫離了它的初衷,它們借由如「語速壓倒」(意即辯手提出盡可能多的論據,讓對手無暇應對,而這些因瘋狂速度而無法被回應的論點,無論質素好壞,都將被承認)這樣的技巧鉆了空子,令價值討論和有效思辨不復存在:「人們學會了用資料來點綴一個演講,就如政客使用統計即數據一樣——達到一種權威的效果,而非澄清一個問題或者確認一個事實。」作者又借由人物莊拿芬的「言語遮蔽」實驗,揭示語速壓倒的盡頭是語言系統的最終坍塌,引發主體的崩潰;接著,透過亞當之口指出:語速壓倒和盲目致力於經濟增長有著相似性,是時代的癥結,「兩者都有賴於不加批評地相信擴張,相信越多越好,癡迷於積聚」;同時,語速壓倒式的伎倆涵蓋了所有商業規避風險方式:商品推銷、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等等。
亞當在演講激動之處會不自覺地點頭,辯論賽教練伊文森嘲笑他並想要剔除掉這種個人習慣。社會縱容荒謬如語速壓倒這樣的手段,卻容不下一個小小的個體化特征。從這樣一個細節出發,整部【我拒絕成為天才鸚鵡】的宣言浮出水面,何謂「拒絕成為天才鸚鵡」?意即自我意誌的伸張:約定俗成的框架也好,高位者的暴力壓制也罷,都沒有權力抹殺個人個體化經驗。
「但是伊文森想要剔除的那個小小的身體動作卻代表某種更加個人化的東西——我兒子獨特的標記時間的方式——又更加超越個人的東西——標誌著他的個體性正融化進一種純粹形式的體驗:就是這樣平凡的語言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