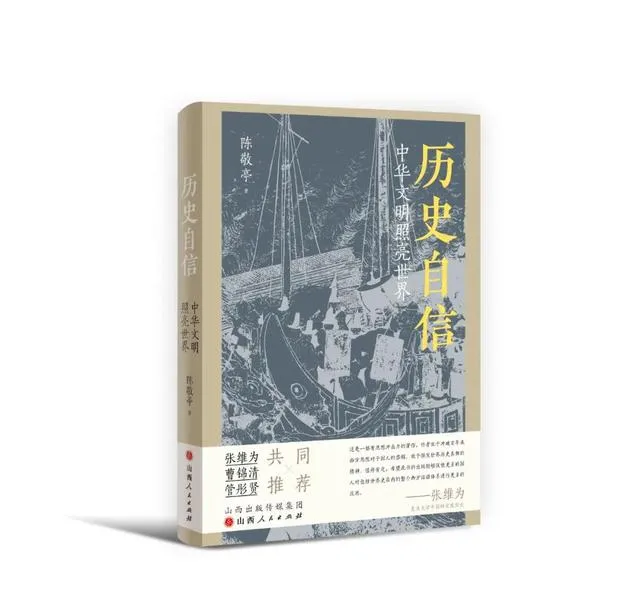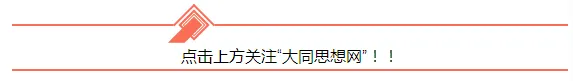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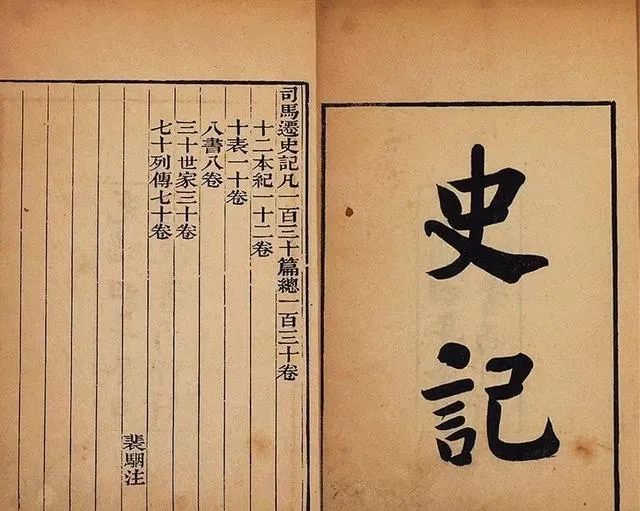

精神突破、生存真理 與中國思想的超越性問題
陳赟
原載【東嶽論叢】2023年第11期
摘要: 世界哲學視域中的精神突破運動以超越性意識的興起為標識,其核心是突破自然節律所體現的宇宙論秩序以及與之關聯的宇宙論王制所指向的集體主義生存樣式,由此產生了以精神傳承為核心的歷史意識。
在中國思想中,超越性並非指向以心靈體驗作為位點敞開去身體化、去社會化、去宇宙化的作為終極根據的絕對者,而是走向歷史過程中文化宇宙的綿延,道體透過體道經驗而被納入歷史文化世界,參與超越性根據就是參與歷史文化宇宙的賡續。
人性的自我理解並沒有拋開作為天地萬物整體的宇宙論視域,對人之區別於其他存在者的特異性的強調與人作為會通萬物整體的宇宙論結構的凸顯被整合到一起,構成人性理解的背景。而作為根據的天道則被分化為不同層次,太一之天、乾元之天與在人之天,對於它們的結構化理解,避免了「逃離」的形而上學。
在精神突破運動中,由宇宙論風格的真理分化出以啟示為特征的救贖真理(以色列)和以哲學為符號的人學真理(古希臘),二者分別側重神極與人極中的一極,以其中的一極為主去連線會通另一極,構成了兩種不同的超越性類別;而中國思想則發展出以居間性、均衡性為內核的中道真理,構築了獨特的超越性品質。
關於儒家思想的超越性問題,比較流行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如下觀點:儒家思想並沒有發展出經驗與超驗、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分離性架構,因而它缺乏變革世界的激情,其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對現實世界秩序的適應【1】。然而,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其 軸心時代理論 中強調,正是在希臘、印度和中國三個地區發生了精神突破運動,其實質是從「自然民族」到「歷史民族」的昇華,而作為這一突破之核心的則是超越性意識的興起【2】。
沃格林在其「天下時代」的論述中進而將精神突破運動進行擴充套件,並將其置於帝國征服對具體社會摧毀的背景下,這一背景使得人們在具體社會內部展開的自我確證不再可能,而不得不投向與權力分離的精神領域,這一領域在人那裏的敞開位點是人的心性或靈魂,而不再訴諸與宇宙節律的合拍【3】。
無論是軸心時代理論,還是天下時代學說,都將超越性意識的顯發與人類文明的多元平行進展關聯起來,只不過在雅斯貝爾斯的普遍歷史架構中,這種平行性是時間上的共時性,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這600年時間中人類歷史在三個地區顯現出來的共同性;而在艾歷·沃格林那裏,這種平行性更多地被視為意義上的等價性。
歷史地看,那些精神突破的擔綱者們由於與他們所置身其中的具體社會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間距甚至難以調和的沖突,這反而使他們擁有了超越性的視域和批判性的態度,實作了與具體社會的分離,本傑明·史華茲就以「後退一步,向前觀望」(stand back and look beyond)表述這種視域【4】。
所有這些都突破了韋伯關於儒教中國缺乏經驗性與超越性張力的觀點。問題並不在於儒家傳統是否具有超越性的向度,而在於如何理解超越性意識的不同類別,尤其是當這些類別以多樣化方式出現時,無法以其中的一種類別化約其他類別。接續他們的洞見,則可以從貫通軸心時代理論與天下時代理論共有的精神突破運動來刻畫中國思想超越性意識的開顯問題。
一、超越性與歷史性的交構
所謂的精神突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從捆綁它的給定性條件中掙脫而獲得獨立自主,這種獨立自主可以在人類經驗的符號形式中獲得表達,從而具有了本己性位置。
就中國語境而言,從「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秩序轉變,首先意味著「治出於一」到「治出於二」的權力與精神的分離格局,地上的君主不再有壟斷通天的特權,人人皆可以在其本有的心性中通達天道,這也就是何以在「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轉折時期人性論興起的根源【5】;
與此相應,人性、人心、人情成為秩序的根據,它們在「三代以上」則渾淪於宇宙論秩序中,消融在高高在上且不近人情的神聖性天命意識中,精神突破則將其解放出來,成為秩序根據的獨立一極,人由此而成為與天、地並列的一極,中國思想中天地人三才之道意識的出現,正是人成為秩序之獨立一極的表現【6】。
當雅斯貝爾斯將精神突破運動與超越性意識的興起關聯起來時,構成其前提的是自然與歷史的區別,而沃格林則將這一區分延展為宇宙與歷史的區分。宇宙即自然,它們構成與歷史的對峙,這是雅斯貝爾斯與沃格林理論背後的共同預設。神話時代的人們深感自身被卷入到大自然節律所呈現的宇宙論秩序中,而與宇宙節律的保持一致,則是太古存有論的根本取向;與此相應,歷史作為對自然的宇宙節律的否定,被等同於宇宙節律之不規則的偶然和意外。
與此相應,米爾恰·伊利亞德所刻畫的上古社會中,泯除歷史意識深深地隱藏在神話敘事的核心,唯有如此,宇宙論秩序中的「神顯」才不會受到幹擾,因為在精神突破之前,神被視為宇宙內最高事物,而精神突破則將神從宇宙內事物中解除,使之成為世界及其內事物的終極根據。宇宙論秩序中的「神顯」關聯著神聖的開端或創生,對絕對起源、萬物開端的全神貫註是精神突破之前的上古心靈所特有的意識,宇宙誕生的神話則是上古宗教/神話的核心內容。
這種神聖開端關聯著歷史的抑制:以宇宙秩序確證其生存的那些「宇宙人」與後來的「歷史人」不同,他們「或者定期性地泯除歷史;或者不斷地尋求超歷史範例與原型而貶抑歷史;或者賦予歷史某種後設歷史的意義(迴圈理論,末世論的旨歸等等皆是),若此種種,其宗旨皆是認為歷史事件本身沒有價值。換言之,他不認為歷史是他人自身存在模式的一個特殊範疇」【7】。基於自然的宇宙論秩序,總是要麽回到太初整體,要麽重復宇宙誕生,以保持人們歸屬其中的集體主義生活形式具有一種宇宙論的結構(cosmological structure)【8】。
生存的宇宙論結構與精神突破之前的宇宙王權關聯在一起,對於那些在宇宙論王國中被統治的民族而言,掙脫宇宙論王國的統治就同時關聯著掙脫宇宙論秩序,因為那些王國將自己支配的社會秩序以神話等符號深深地嵌入天地萬物組成的宇宙論秩序中。由此精神突破運動在於將人與更高的神,甚至是比宇宙的創世神更高更絕對的上帝關聯在一起,畢竟宇宙的創世神還可以是宇宙論王國秩序的潛在支持者,甚至是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
那麽,新的上帝唯有與這種絕對神關聯起來,生存本身才能超越王權及其連通的宇宙論節律,這樣的超越性,向上就是構建超越宇宙論秩序的絕對神,向下就是分離人的身、心以凸顯純粹的精神性——靈性,超越性的實質就是在純粹精神性(靈性)與絕對神之間建立溝通——這就是在猶太—基督宗教中可以引申出來的具有古典靈知主義特色的超越性。
擺脫了宇宙論秩序的天道就以絕對者的身份向人的靈性敞開,而超越者本身則以絕對自由和純粹創造為內容。敞開絕對者的方式來自靈性的啟示,後者建立了個體內在性與天道絕對性之間的無中介連通。這種超越性方式采取了從身心結構中分離出身體,從宇宙和社會中剝離出宇宙節律和社會禮法,因而超越性表現在對身體、社會和宇宙的否定。
在中國思想中,超越性意識的誕生同樣與三代的宇宙論王國的失序——禮壞樂崩相關。當人以歸屬於宗法集體主義的方式而歸屬於宇宙論秩序的三代生存方式不再有效時,每個人以盡心—知性—知天的方式而與天道直接相通,便打破了宇宙論王國中王者對通天權的壟斷,於是與天相通的德不再被限定在政治層面,而是通向了人性內在固有的品質,不再被王者或統治階層所獨占,而是面向每個人敞開,不再僅僅以「同姓則同德」「異姓則異德」(【國語·晉語】)所表達的集體生存方式的倫理風尚顯現,而是轉向以內在的道德開放自己。當人可以透過內在心性而直通天道時,心性自身成為秩序的根據之一,而對人所顯現的天道本身也內在於人性之中。
中國思想雖然發展出了具有超越性意義的天道概念,但這一概念並非以對身體、社會和宇宙的否定為前提的,相反,一種在個人、社會、宇宙之間的張力性結構主導了對道的理解,個人沒有被化約為去身體化、去社會化、去宇宙化的純粹精神化或智性化個人,以這種個人的理性或精神性(靈性)對宇宙內事物進行分割和定義以達成秩序的方式並沒有得到鼓勵。這使得道在具有創生性品質的同時更具有調節性特征,道者導也,引導性的內涵規定了道以道路為象征,它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參與。
道的這種引導性品質同時構成了道的創生性品質的限定,道的那種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的一面雖然被引出,但生而不有、為而弗恃、長而弗宰的另一維度也被給出。這兩者構成了道的生生向度與無為向度,二者並列不悖。這就導致了道雖然生天生地,但卻並非從虛無中按照自身意誌創造天地。道的創生性乃是「物固自生」(【莊子·在宥】)的根據與引導。道並不主宰萬物,而是給出了物之自為主宰的根據;道不是生出了萬物,而是給出了萬物之自生自成的根據。
既然天道之生物,實即物之自生;天道之成物,即物之自成,那麽,天道的意義在哪裏呢?萬物之自生自成本身卻是源自天道。【論語·陽貨】:「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與【大戴禮記·哀公問】中孔子貴天道之不已意思相通:「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孔穎達曾將天地的精神(天地之心)理解為「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9】,在其之前也有對天道、天命的無為表述:「無為為之之謂天」(【莊子·天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 萬章上】)。郭象以「物各自生」「物各自造」解釋天道,這就是將天道的角色理解為引導者而不是支配者【10】。【論衡·自然篇】:「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朱熹也說:「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妝點得如此!」【11】
天道並非世界的最終決定者,也並非一個虛無主義世界中的意義授予者。天道並不直接介入萬物的自生自成,而只是這種自生自成的根據。於是,按照一個終極絕對而獲得支配天下及其萬物的正當性的構想失去了基礎,那種根據能夠把握這種絕對者的理性或靈性來進行分割、定義世界內事物及其秩序的方式也失去了正當性。
萬物各自據其源自天道的性命而生活,這種性命自身又是本己性的,但又是天道在此物那裏的分殊化展開。萬有各有其天命,這一天命即隱藏在其性命之中。即便是治理天下的統治者,也必須以引導者的角色出現,引導人們正定性命而已。「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管子·法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卦·彖傳】),正是儒家思想基於其超越性的天道而構建的秩序原理。
各正性命的秩序成了天道在生活世界的展開,它支持的是融入和參與世界,而不是否棄世間:「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禮記·哀公問】)這使得中國思想傳統中的超越性意識並沒有導向從世間的逃離,而是走向世間萬有的協和共生。
相比之下,這種逃離在猶太—基督宗教中卻被鼓勵,以【出埃及記】的象征被靈知主義者擴充套件開來,不僅世界,而且歷史,都成了必須從中逃離的「埃及」意象,惟其如此,才能保證世間性的生存本身乃是一種朝聖之旅,而世間性的家國天下乃至身體,最終都不只過是臨時性的驛站,人被刻畫為大地上的異鄉者,世間及其一切都僅僅具有臨時性的意義。儒家思想在發展超越性意識的同時,卻對世間性生存予以肯定,但這種肯定並不等同於將人與世間性建立在給定性捆綁關系中,而是建立在對世間性生存的轉化與提升上。
精神突破運動的結果,是對於被拋地與一個具體社會或政治共同體的給定性捆綁,個人有了選擇結束的可能性。因而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出處、進退、隱顯成為儒家思想視野中的生存的不同樣式。然而,與西方古典靈知主義不同,從具體社會及其禮法秩序中的結束或出離,並非轉向一切非世間性的超驗性絕對,而是投身於歷史中展開的文化,正是文化保證了不同的社會與政治共同體的連續性,任何社會與共同體都將如有機體那樣面臨生老病死、興衰成敗的命運,但文化透過歷史記憶卻可以被傳承、被延續。
文化的核心又是具體社會中的人對天道的體驗,天道自身無所謂歷史,但其對人的顯現必須透過人的體道經驗,後者是歷史性的,前人的體道經驗匯聚為歷史中的文化,文化作為道之顯者,構成人類歷史之本質,與道相通的超越性意識在中國古典思想中被引向參與歷史文化之賡續的活動,於是,孔子所謂的「與於斯文」,構成「對越上天」的方式【12】。
「斯文」意味著歷史過程中的精神傳承,透過斯文,個人得以突破或超越他所置身其中的具體社會,而得以進入跨世代性的歷史文化世界,這並非純粹的超驗之域,但卻透過向著過去和未來的開放而突破並提升作為生存處境的當下。由此,當下不再受制於自然的宇宙節律。道(天道)與文(斯文)在歷史中交會,人之參與道體,即被轉化為參與「斯文」。
歷史性在中國的超越性意識中由此而獲得了基礎性的意義。一個人超出他自身的社會和時代的方式,並不是在心靈體驗中朝向非時間性的永恒,而是進入歷史、參與和推動歷史、成為歷史的一部份。這就導致了歷史對於中國人而具有的宗教性意義,或者用趙汀陽的話來說,一種歷史為本的精神世界在中國思想中被建立【13】——這在追求非時間性的永恒的希臘傳統與猶太—基督宗教中是難以想象的。
在西方,歷史與哲學的張力,或者說經驗與先驗的張力與沖突始終存在,以至於尼采慨嘆「缺乏歷史感是一切哲學家的遺傳缺陷」【14】。古希臘世界對確定性的非世間性的理念世界的執著,與基督教末世論思想結合在一起,導向了對歷史的如下理解:歷史只是以克服歷史為目的,歷史終結所開啟的永恒才是歷史的終極目的。
因而時間與歷史自身毫無意義,只有透過一種終極目的,歷史才被給予了意義。「假如歷史的意義在歷史事件已經自明,那麽,就根本不存在關於歷史的意義這個問題。但另一方面,只是就一種終極意義而言,歷史才可能表現為無意義的。」【15】借助於末世論的與目的論的終極目的,西方思想剝奪了歷史自身的意義。
但是,對中國思想而言,歷史承載著跨世代的體道經驗,這些體道經驗表達為能化之「斯文」,後人的體道無以繞過「斯文」,而只能以參與「斯文」的方式展開,「斯文」不但連線了人與道,而且溝通了作為生者的人和作為死者的鬼神,因而「斯文」本身就具有神聖性的意義,道之生生透過歷史過程中「斯文」之延續而實作。歷史與天道便不再是兩個互不相關者,而是相即相入的,天道必然透過歷史而向人敞開自身。這就是天道在人那裏的歷史性。
歷史在中國文明中的位置,相當於神話之於西方文明 ,它是表達人類經驗的原初性符號形式【16】,正如在西方文明中哲學、宗教、科學等都是從神話中分殊而來;中國知識譜系的三支——經、史、子,都是從「原史」的分化,不僅六經皆史,諸子皆史,而且後世的史學也是從「原史」中分殊而來, 史在中國,一如神話在西方,構成最為古老的符號形式,可謂百科學術之母體 【17】。
在經、子、史從「原史」中分化以後,經、史雖然被分殊開來但又具深層聯系,即經即史,即事即道,歷史被賦予了顯道的超越性意義。道體透過歷史過程中人對道體的參與而自我顯現,但這種顯現既是不完全性的,也是相對性的,並且最終都要轉化為歷史中的體道經驗,人之體道或參與道體,透過與歷史中的他人的體道經驗的貫通的方式而展開,這就是歷史文化世界對於道體開顯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
正是這一點使得中國思想更加註重天道的歷史性,與此相應,超越性意識不再如同希臘那裏構成對歷史的否定,相反,超越性與歷史性的相即相入、相涵相攝,才使得歷史對於中國思想而言本身就具有超越性向度,一切類別的道之體驗或神顯經驗,最終都透過歷史中的經驗而轉化為人文的教化形式,從而被納入人道範疇,這就使得中國古典思想的超越性意識與歷史性之間具有某種深層的互補性和共構性。於是,我們看到,中國思想中超越性意識的如下取向:不是拔離地面、朝向真空,而是轉向歷史中的文化宇宙,在世間,在歷史過程中,以參與文化宇宙的綿延而指向歷史為本的精神世界。
二、人性的自我理解及其超越性根據
在雅斯貝爾斯與沃格林那裏,歷史與自然的對立,關聯著歷史與宇宙的對峙。精神突破意味著歷史意識的發生以及對自然的宇宙論節律的突破。歷史意識關聯著精神事件所界定的紀元性意識——人類歷史此前紀元與此後紀元被區分的意識,而宇宙作為自然事物整體則是精神突破運動之前的秩序樣態。泯除歷史以回歸永恒,不能采用「轉投自然而跨越歷史」的方式,雖然這樣可以獲得「復歸無意識的生命,更深刻地復歸無生命的自然力的清晰性」的體驗,「引向靜謐、雀躍和無痛苦的統一」,但那卻被雅斯貝爾斯視為「逃離了人類和我們自身」【18】。
中國思想在精神突破之後仍然保持著對宇宙論秩序的敬意,因而被沃格林視為突破不完全性之表現。但沃格林的復雜性在於,他看到了以神話符號表達的宇宙論風格的真理與精神突破之後以哲學、啟示這兩種符號表達的生存真理具有意義上的等價性質,這意味著不能再以落後與先進、野蠻與文明來看待精神突破前後的狀況,人類探尋生存真理的形式和符號可能有所不同,但就其意義而言卻不分軒輊。
將人視為宇宙人,乃是各種神話所表達的古老的真理。人同於其他生存者的地方,在於其是眾多的生存者——萬物——之一,但人又因位居生存者鏈條的頂端,具有其他生存者所沒有的「東西」——譬如仁、義或禮而不同於其他生存者;更重要的是,人是萬物鏈條中的集大成者,會通萬物,從而具有一個世界性的視域,將互不相知、互不相與的生存者納入世界整體視域。
【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對人的理解具有雙重內涵:一方面人具有其他生存者所不具有的「義」,這是人能夠進行分工並進一步組建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其他存在者的內容,如水火之「氣」、草木之「生」、禽獸之「知」,皆在人那裏匯聚,並與人所獨有之「義」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人的本性。前一方面呈現的是人性之自我定義的種差,它往往透過人禽之辨的話語得以被辨識;後一個方面,則將人作為一個復構,由於人會聚了生存者的各個層級因而具有了感應萬物、會通萬物於一身的能力。
這個意義上的人不再是一物,不再是生存者,而是具有非生存者的特性,它是生存者全體——宇宙——的一個縮影:「天便脫模是一個大底人,人便是一個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19】天既是包舉萬物之宇宙總體【20】,也是宇宙萬物的根據,作為根據的天道內在於宇宙萬物之中,同樣也內在於人性之中,人可以透過理解人性來理解宇宙,也可以透過理解宇宙來理解人性。
人性的以上兩個維度共屬一體,但二者之間並非給定的和諧或一致,相反,這兩個維度始終處在一種結構性的張力之中,人因此而具有了選擇與決斷的自由。
其一,人作為與眾不同的萬物之一而與萬物隔離,生存在人所獨有的特異性之中,並以此自我界定。帛書【五行】雲:「循草木之性,則有生焉,而無好惡。循禽獸之性,則有好惡焉,而無禮義焉。循人之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不循其所以受命也,循之則得之矣,是侔之已。故侔萬物之性而知人獨有仁義也,進耳。」人與草木一樣皆有生,但區別在於草木無好惡;人與禽獸一樣有好惡,而人有禽獸所沒有的禮義。由此,人侔同萬物之性但又有萬物所不具有的特異之處。由此而來的「盡性」,就是不僅不能放棄、而且必須堅持並充分發揮人之區別於其他存在者的特異性。
其二,人作為一個微型宇宙,而與天地萬物構成的大宇宙相涵相蘊、聲息相通,這就是人可以在其生存體驗中渾然與物同體的根源。這個意義上的實踐已經不再可以為「盡性」所含,因為在這裏人的生存體驗所連通到的不再是每一物各有的與形相連但同時也為形所限的獨有之「性」,而是人與其他生存者在根源處的相通,因而它被視為「至於命」的實踐,這種活動由於超越了「大體」與「小體」的區隔,而能「踐形」,即在形色上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能性,在人的這種可能性中,與天地之承載萬物的品質具有相似性。
如果說朱熹業已指出了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並不具有貫通宇宙全體的能力:「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21】,那麽,董仲舒明確肯定只有人這種生存者才能貫通天文天地萬物,從而成為與大宇宙相應的小宇宙:「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春秋繁露·人副天數】)貫通天地萬物的能力也可以理解為人的特異性,但這一特異性與人之具有禽獸所不具有的特異者(如仁義等)並不在同一個層面。
仁義這種特異性,是人區別於其他生存者的品質,而會通天地萬物則是人連線溝通天地萬物的能力。從前者出發所導致的人的定義,是排除人與其他生存者的相似性【22】,而彰顯人的獨有的特異性,因而在這裏要求給出的是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界限,透過這個界限所理解的人,則最終往往被導向「大體」,即道德性、精神性、理性等,它是在排除「小體」即 生物性 、感性等過程中達到的。
換言之,以區分大小體的方式,將人的自我界定交付給大體,而對自己與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小體特征加以否定。從後者出發所導致的則是人與萬物的一體性與貫通性,在這裏人得以界定自己的方式並不要求排除相似性,得以彰顯的乃是更高層面上的一體性與貫通性,因而人不再是排除了生物性與感性的道德性、理性或精神性,而是小體與大體一體貫通而大小區別不再成立的統一整體。人並不是單憑他的理性、精神性、道德性才貫通天地萬物,而是他的所有方面本身就與宇宙具有最深層意義上的同構或相似性,因而共同參與了人顯現宇宙的復合能力。
人的自我界定的上述兩種可能性,邵雍將前者稱為「人亦物」,即人作為物種之一的可能性,將後者稱為「物之物」,即人不再是萬物之一,而是作為一種「存在區域」,在這個區域中,萬物得以被感知、被會通,從而成為同一個世界的不同事物,而人並非與物有別的獨立事物,而是這個宇宙顯現自身的一種場所:「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23】
人異於萬物者並不僅僅在於人擁有物所不具的仁義等現成品質,而是一種貫通萬物使之納入宇宙整體的能力,「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23】。人的能力使得人對宇宙整體的經驗成為可能,而這種體驗本身卻是其他生存者所不具備的:「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23】人之靈於萬物並不在其獨有的道德性與理性,而在於其能通達萬物整體。
王船山將這個意思表達得更為清楚。就天地萬物自身而言,它們各為形象而不相知、判然區分而互不相與,在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置身其間的宇宙整體似乎缺乏感知自己的感官中樞,但這種「不相與,不相知,皆其跡也」,就「跡」而言,可以說「天地之無心可矣」;然而人正是「天地之心」,即宇宙感知自己的感官中樞,「及觀於人,而後知其心在是已」。彼此不相知、不相與的萬物,透過人的「斟之酌之,會之通之」,而成為同一個宇宙中的不同事物,因此,「天地之靈,以人而靈」【24】。
在人的究極境地,「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23】在這個意義上,人是宇宙的縮影,這意味著,人是天地的雙重代表,在萬物那裏代表天地,在天地那裏代表萬物,人因而位居天地的核心位置,即那種使得天地萬物得以會通為一個整體的特殊場所。當然,這裏的「人」乃是「大寫的人」,即【荀子·王制】所謂的君子:「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人是天地的參與者,不是與物區隔的萬物之一,而是萬物之全體。
在亞里士多德、赫爾德乃至沃格林那裏,可以看到對人的後一種理解,即人並非僅僅是某個東西,而是一個「實在之域」(a realm of reality, Seinsbereich Mensch),它匯聚了完整的存在鏈條,因而不再僅僅是一種存在者。只不過對於人的這種理解,在他們那裏,更多地與人的靈魂學相關,即靈魂成為人經驗完整的存在整體的「感受中樞」。這樣一種理解,凸顯的仍然是人之相對於其他存在者的具有辨識度的特異性,只不過這一對人的定義不同於第一種人性定義,其對人的理解不再著眼於人物之辨的層面,而是提升到人與宇宙關系的層面。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回到人的原初宇宙經驗,它同時也是原初秩序的經驗,其核心是人與宇宙渾然一體的體驗,「大人」與「宇宙」的互動滲透、彼此涵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為原初秩序經驗的顯著特點。不僅人不將自身區別於萬物,而且,人自身也與天渾然不分。在這種渾然一體的經驗中,人依然在宇宙整體中獲得自己的身位,不是透過突顯特異性、采用區隔化方式達成的,而是人與宇宙萬物在交織疊構中的共生、互融。人在這裏獲得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即人自身作為一個存在整體或一個生態系,就是一個小宇宙或縮微宇宙,人並不是一個存在者,而是存在整體的映現【25】。
精神突破運動意味著原初宇宙經驗的分殊化,它展開為天與地的分化、人與神的分化、世界與社會的分化,更重要的是世界及其根據的分化,分化了的社會與人、事物不再以渾淪未分的原初宇宙經驗的整體作為生存的意義,而是以世界的超越性根據作為意義的源頭。這個意義之源在原初宇宙經驗中是作為宇宙內事物的最高存在者——在西方是「神」,在中國是「天」。伴隨著原初秩序經驗之分化的,是宇宙論風格的真理被生存真理所取代,生存真理是朝向根據的生存,譬如「在天之下的生存」或「在神之下的生存」。
根據本身的分化有不同的形式:其一,當根據作為具體事物的根基時,它內在於事物的本性中,成為內在於事物中的「天」,譬如在人之天、在物之天,人性與物性的概念由此而產生。這裏的根據就是本性的概念,它指向事物的自身規定。
其二,當根據作為世界之根據時,它指向存在者整體的根據,作為世界整體的終極目的或終極原因或終極意義而被領悟,但它本身卻並非實體,並非宇宙內事物,因而無法以把握事物的方式把握它,它將事物的生存導向與自然宇宙節律的合拍,根據在這裏被分化到這樣一個特定位置,即萬物整體的世界——漢語的表達是「天地之間」或「天下」。這樣的根據意味著主導一切具體事物的普遍根據,在儒學語境中,它是「乾元之天」,「乾元之天」與「坤元之地」的交合而化生萬物,構成具體事物及其整體的根據。
其三,當根據不再被局限於宇宙中,甚至也不是產生宇宙的根據,它有著並非可以從事物的根據乃至事物整體的根據來加以理解的深邃內涵,它不是被領悟為創造世界的造物主,而是被領悟為創造世界的造物主之根據,也就是比造物主更高的神。此時,它只與造物者關聯而不直接作用於具體事物,這樣的根據就超越了宇宙的節律,超越了事物的整體,而是純粹的「在天之天」或「天之自身」,它構成根據的根據。
「在天之天」也就是「太一」「太虛」所表達的更原初的「天」,與「天地」之「天」不同,前者是「太一之天」或「太虛之天」,後者是「乾元之天」。「太一之天」自身分化出乾元之天與坤元之地,兩者的交通對具體事物的生成負責,因而人與萬物都是乾坤之子。但作為乾元之天、坤元之地之來源的「太虛之天」或「太一之天」,不倚靠其他事物或資源,自生自化【26】。
在基督教語境中,太虛之天就是比造物者更高的絕對者,是根據的根據,保羅傳統的「神顯(theophany)經驗」,就是對之的體驗,這種神顯不再訴諸宇宙節律,不再與任何特殊的事物相關,相反,它是對宇宙的徹底逃離,以徹底逃離達到徹底超越。
在中國的語境中,「根據的根據」就是所謂的「太一之天」或「太虛之天」,它雖然與「乾元之天」同樣具有創生性,但卻是本質不同的創生性,「乾元之天」創生的物件是天下的萬物,創生的方式是與坤元之地相交,在具體事物的創生上,「乾元之天」並不具有自主性,必須透過與「坤元之地」的結合才能創生萬物。
然而「太虛之天」或「太一之天」創生的物件不是具體事物,而是「乾元之天」與「坤元之地」,它創造的不是物,而是造物者;其次,它的創造僅僅透過它自身而展開,並不借助於其他事物,因而其創造即其自由之表現。
既然有了根據的分化,朝向根據的生存真理也就有了不同的層次:其一,本於人性的生存,謹守人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存在者的本性,安於人在宇宙中作為萬物之一的位置,人禽之辨、人物之別都是這一層次的生存真理的構成部份。根據所帶來的超越將人引向以人的人性(精神性、道德性、理性、歷史性)對人的非人性(生物性、感性、自然性、本能等)的超越。
原初宇宙經驗中的植物生長節律、四時更替、天體的執行等,不再被作為秩序的唯一基礎;在「天下時代」或「軸心時代」,人性論的興起,構成一道新景觀。如何理解人性?通常的取向是透過人禽之辨分離出人的自主領域,以減法的方式獲得人性的界定,其方法是不斷地排除人與動物的共有內容,而將人所獨有而「非人」(如動物)所無的特異性,作為人性的本質規定。其結果便是人性的內容被理性、道德性、精神性、社會性等所占據,而欲望、激情、感性、生物性、自然性等被排除在外。
由此,「人」的確立必須透過排除「非人」維度,「人」由此被視為生存在「人」與「非人」的對待張力中的存在者。當人禽之辨視角涉及對人自身的剖析時,人本身也被分為「人」(其內容為理性、道德性、精神性、社會性、歷史性,等等)與「非人」(其內容為感性、生物性、自然性,等等)兩個部份。
其二,本於「造物主」之神的生存或「本於乾元之天的生存」,它把人與萬物聯系在一起,共同遵守宇宙的節律,乾坤父母、民胞物與就是這種意義上的生存。它的超越性展開在對以宇宙視域對社會視域的超越、以方外視域對方內視域的超越。
其三,本於「太一之天」的生存,就是不僅超越一切具體事物,而且超越社會與宇宙,達到純粹的虛靜或絕對的創造、自由。
在第一種生存取向中,人與根據是以分離的方式達到統合,被突出來的是真正意義的人之所以為人的特征,但這種方式卻以離開最高根據(太一)與次級根據(乾元之天)及其造物(天地、萬物)為代價的,人類是世界中的孤獨者。第二種方式中,人與根據的關系是達到與其所有造物的統一,人擁有整體的世界,並融合在世界之中,與物為春;人是天地萬物之友。第三種方式中,人不僅逃離萬物,甚至逃離天地,只是與最高根據的「太一」合一,人不再被視為萬物之一、不再被視為宇宙內事物,而是被視為純粹自由與創造性或純粹精神化人格化身。
普通的個人在成為自主君子的修養過程中,采取的是第一條道路,君子在人禽之辨、人物之辨中將自身確立為人性的體現者,在這個意義上是「大寫的人」,這是與普通人(庶人)相比的「大寫的人」,大寫的人或者是理性主體,或者是道德主體,或者是精神性主體。這種大寫的人,是人類政治社會秩序的積極參與者,但對於包含萬物的宇宙秩序卻沒有興趣。
因而第一條道路是政治社會中的人透過大體(精神、理性、道德性)與小體(自然、感性、生物性)的分層而達到的自我確證,這種確證本身也是構建社會分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方式。這主要是因為人性界定的方式,本質上是突出人的特異性的方式而構造區隔性,這種區隔性本來存在於人與其他存在者(「非人」)之間,但現在被引入人與人的關系之中,這就達到了社會分層的效果。
當孟子區分「大體」(心之官)與「小體」(耳目之官)時,他意在匯出「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的社會分層,如此,不僅「勞心者」與「勞力者」「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的分層有了合法性,而且,前者對後者的支配也有了正當性基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在羅馬法系統中,人禽之辨以所有者與所有物的內涵充實「人」與「非人」,「人」意味著自權者的身份,而「非人」則意味著他權人,自權人以「人」的身份可以正當地將「他權人」(被視為「非人」的人)合法地視為自己的財產,譬如家主對妻子、奴隸擁有所有權,後者只能被作為非人之物對待,當人格被界定為所有者時,我們進一步看到了這種支配活動的法權化形式。
以人性為根據的生存,構建了一種支配性秩序。這種支配性秩序在人的內部,體現為理性、精神性、道德性、社會性等對感性、生物性、自然性的支配,「人」往往因此而被視為司法主體,即一個能夠控制其動物性維度(「非人」)的主體(如雅各·馬里坦),或歸責主體(如康德),或者歸罪主體(如基督教),這樣人就被視為與「非人」相對待的「人」。人禽之辨一旦進入世界歷史秩序中,就導致了目的論視域中「人」的符號化現象,「人」被抽象化為某種理念或理想,與此相應的是如下的理念,「‘人類’在歷史上的過去還從未存在過,也不可能在任何一個當代中存在……‘人類’是一個理念和一個理想。」【27】
當人禽之辨以突顯特異性達成人性的界定時,必然會造成人格(person)與人類(human being)的分離,在齊斯特拉姆·恩格爾哈特【生命倫理學】中我們看到了這一觀念:並非所有的人類都是人格,並非所有的人格都是人類;甚至,某些現實的人類只能是潛在的人(potential person)或非人(non-person)甚或反人(anti-person)【28】。
不符合「人」的特異性者,作為「非人」,在道家哲學視域中便是「棄人」「棄物」。一旦承諾了「棄人」和「棄物」的合理性存在,那麽,對之所施加的泯除或排斥就具有了正當性。在近代的文明等級論與國際法語境中,一旦某個民族與文明聲稱自己配得上人類符號,它實際上就是在宣示擁有了代表人類的法權,從而獲得了對作為棄人或棄物的野蠻民族的正當的殖民權和支配權。
要想達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的世界秩序,就必須超越第一種秩序,即基於人性的秩序,而達到萬物一體的視野,這就是第二種秩序。事實上,早期政治社會的王者采用的是第二條道路,他必須以造物主意義上的根據自我顯現。亞述箴言傳達了早期人類具有普遍性的統治經驗,統治者必須作為一種大人,走向以造物者為根據的生存:「大人是神的一個字,而(其他)人是大人的影子;大人是王,猶如神鑒。」
王借助於天地神奇力量而達成的統治,被視為神的影像。拉貝特在其【亞述—巴比倫王權的宗教性質】(1939)中強調:「王在神人之間有著特殊的地位,他在某種程度上是聯結人的世界與崇高的神界的力量」,而且「他被神選中,他本身不是神,而是特別的人」【29】。此言可與維柯關於人類歷史階段中的「神的時代」的刻畫相互印證。
軸心時代或天下時代進行的精神突破,就是實作了宇宙秩序與人性秩序的分離、世界與其超越性根據的分離,這一分離的核心便是人性的獨立,人性與超越的直接關聯的實作,而不必透過王者這一中介。因而分化之後,克服第一種基於人性為根基的秩序在帶來秩序的同時也帶來棄人和棄物的問題,必須朝向第二種根據下的生存真理,這在莊子那裏是從宇宙的視角超越政治社會的禮法秩序,達到「磅礴萬物以為一」(【莊子·逍遙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層次;在張載那裏,則是「民胞物與」的層次:天地是人的父母,他人是人的兄弟,萬物是人的夥伴。
這樣的生存真理的根據,不可能再是在人禽之辨、人物之別中構建的人性,而是人與萬物共同的根據,就是乾元之天,所以張載有「乾坤父母」之說。這種以乾元之天為根據的秩序一旦與王權結合,王將自身作為天的代表,以實作帝國征伐的意識形態工具,那麽以此為根基的生存也會帶來問題。
第一種生存真理在社會內展開,第二種生存真理在宇宙內展開,它們都建立在對社會與宇宙信任的基礎上。一旦社會處於極端創傷而在社會內部不可能得到撫平、且在政治社會的支配被上升為宇宙秩序時,第三種生存真理就出現了,它不僅是對社會的反抗和逃離,也是對宇宙的反抗和逃離,人脫離在世者的身位,而達到「未始有物」的新層次:以「太一」為根基則指向天地渾淪性的超越性,以保羅式的上帝為根據則走向創造性與自由性本身。由此而被界定的生存,一方面只能是完全個體性的,另一方面只能是純粹精神性的。
就前者而言,它必須拒絕一切服務於世間性的共同性,如果存在著共同體的話,那麽也只能是「相與於無相與」的類似於保羅傳統開發出來的「靈性共同體」;後者的特性是在世而不屬世,其在世的目的就是為了棄世,以達到純粹的非世界性的生存。
這種生存真理可以為帝國征服下的人類提供反抗帝國支配的慰藉,但同時也攜帶著對世間秩序以及對人的敵視,因而構成一種徹底逃離的形上學。逃離是反抗的方式,但卻不以建構天地之間的秩序為目標。因而它包含著對一切實質性的秩序的顛覆,是人類文明的「負經」;正如第一種秩序與第二種秩序雖然有著自身的問題,但卻是人類文明的「正經」。
如果說在西方,三重根據的分化,是以斷裂的方式達成的,而在中國思想中,以三重根據的分化為前提,走向的卻是其連續性。個體性的超越性生存,上達至作為人之根據的「人之天」,進而上升到作為人與萬物共同根據的「乾元之天」,立足於「人之天」「乾元之天」來會通「太一之天」,這就使得作為突破當下現成性為目標的超越運動,具有一種上升性和連續性。
三、生存真理的分化與中國思想的中道真理
我們可以從宇宙論風格的真理到生存真理的分殊化的視角回看對人性的兩種定義:一種將人放在人物之別、人禽之辨語境中加以理解,它是一種以減法為方式的定義,減去人與物的共同性,凸顯人的特異性——這種特異性被視為人性。這樣的人性界定將人視為萬物之一,但又不同於所有其他萬物。另一種界定則將人視為小宇宙,即宇宙的縮微性的相似物,人身上會通了所有存在者的特性(如前引荀子的界定,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正如宇宙包含了所有的存在者。這兩種界定中;一者將人視為一物,作為萬物之一的某物;一者將人視為會通萬物的小宇宙。
人的第二種定義,在人與宇宙的關系層次展開,宇宙並不是一個具體的存在者,因而人也就不再是一種可以由物件化方式加以把握的客體之物。只要在客體之物上加以把握,將這種定義視為人之不同於其他存在者的特異性之所在,那麽,這種特異性就會被視為一種本質主義意義上的現成內容,其實這種人性定義只是人的一種有待展開的潛能,它需要人透過自己的生命存在顯現。即便是對第一種人性定義,也不能作為人已經擁有了的現成內容來看待。畢竟,人的自我界定的可能性,並不是一種作為客體之物可以經驗方式發現的現成品質,而是必須以參與的方式將其生存投身其中,而後得以證成的生存真理。
生存真理不同於客體化真理的關鍵所在,是其不能以意向性(intentionality)方式加以把握。由於意向性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它所把握的只是意向世界(外部世界物件的感性知覺)中的客體這一結構性層次,在這一層次中意識本身被作為對應性的意向主體,即意向性客體的對應相關項。
然而,在意識指涉意向性客體的同時意識自身還有一種「顯亮性」(luminosity)的結構層次,它本質上是對各種實在領域的參與,實在並非意向性客體,而是包括意識以及意向客體等在內的存在共同體,其核心是天(神)、人、社會、世界的相互參與。意識的以上兩種層次,對應於沃格林所說的兩類實在,即物-實在(the thing-reality)和它-實在(the it-reality)【30】。
值得註意的是,「它-實在」的經驗具有「被動」性質,不能還原為某種先驗主體的建構,意識在此並不屬於作為軀體之功能意義上的人,而是人遭逢作為存在根基之天的力量之牽引、並被其穿透,在其指引下自身運作,進而言之,意識之顯亮性就位於軀體中的人類意識與被作為事物來意向的實在「之間」【30】。
意向性的經驗或可解決認識論批判以及對外部世界的客體化物件經驗的認識,但它並不是意識結構的所有可能性,它不能解決與求索根基的經驗相關的超越問題。當將之運用於參與實在的人時,人也就被現成化為客體之物。關於事物性的語言和認知主體把握客體的語言,訴諸概念(concept);但顯亮性的體驗無法被概念壓縮或還原,而只能以符號(symbol)加以象征。
對人與實在的實體化的根源正在於以意向性方式解釋面對人與實在,以至於顯亮性意識層次無法透顯。「經驗之恰當理解的最嚴重障礙」是「實體化嗜好」,「感性知覺的世界之客體物件,已經如此強有力地變成‘事物’的模型,以至於不經意間闖入到非對客體性經驗的理解,那些經驗不是關乎客體物件,而是關乎實在之奧秘」【31】。
實在的奧秘只有在符號化象征的顯亮性經驗中才能被開啟。意識就不再是對人的意識之外的實在有知覺的人類意識,而必定是參與性的純粹經驗的居間實在,雖然具有不可描述性,但卻可以透過闡釋性的方式來理解【32】。在顯亮性的意識層次,主體與客體的經驗模式不再有效,那只是意識參與實在的敞亮性經驗被誤置在意向性經驗層次而產生的混淆。進一步地,如果沒有顯亮性的意識層次,甚至意向性經驗自身也是不可能的【33】。
意向性意識與顯亮性意識都是原初的純粹經驗中的分殊化形式。原初經驗將神、人、社會與世界經驗為一個存在共同體,神與人、社會與世界作為宇宙內事物,以類比的方式被關聯在一起,在各自的層次上彼此參與互涵,世界既不是一個去神性的內在物理世界,神也不是一個宇宙之外的神,相反它是宇宙之內的「事物」。就此而言,神與人、世界與社會之間作為生存真理的兩極結構而被體驗為類比所建立的同質性(consubstantiality)關聯。
在這種宇宙論風格的真理中,宇宙是以全體的方式被納入生存張力結構中去的,這種張力將自身表達為宇宙內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等級秩序。但原初經驗所傳達的宇宙論風格真理往往透過神話的符號表達自身,當哲學這一符號承載的智性意識與啟示這一符號承載的靈性意識出現以後,宇宙論風格的真理就以分殊化方式解體為生存真理,宇宙被分解為內在世界及其超越性的神性根基,在這種語境中,天(或神)雖然仍然可以被視為萬物之總體,但更重要的則是被視為世界的超越根基,原初宇宙體驗退藏為生存真理的隱性背景。
盡管人類生存的經驗有從緊湊到分殊的進展,這一進展只是使得經驗本身對意識而言變得更加清晰,並沒有改變生存真理的張力性結構。就生存結構而言,生存展開在兩種力量的結構性張力之間:一端是人的探尋、求索,另一端是根基的推動或牽引,這個根基或者被符號化為天,或者被符號化為神,但這並不重要。
因為,所謂的天(或神)並不是外部世界中的實體,而是生存張力結構體驗中的極點,孟子曾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來拒絕將天實體化為某物的經驗,「天」或「神」只是根基的不同符號,根基本身是生存體驗中對人而言具有向上牽引作用的力量復結(power complexs)【34】,它常被表述為各種形式的「超越者」,但其實是一種沒有「超越者」(不能在意向性層次加以實體化理解的自足性)的超越性力量,它在人的權能範圍之外,對於人的知行而言都具有無法透明的特征。人自身其實也不是一種現成的固化實體,而是透過在超越體驗中與天的力量復結有所區分的另一種力量;並不存在一個被天的超越秩序普照、不越雷池半步的人的秩序;在一個更廣大的存在秩序中運作、互動的力量,則是透過模糊人類與超人類的界限者這種方式來達到人自身的【35】。
人在其求索根基的生存運動中被來自根基的力量(它並非生存者,而是無定意義上的非生存者,構成生存者的本源)所穿透、所照亮而向上提升自身,而這種向上的提升正是參與實在的要求,任何一種生存真理的參與都伴隨人的向上的轉化,即超越自身的現成狀態;但同時生存張力的另一極中還存在著來自作為生存者的人這一極點的反拉力、反牽引,只要這種反拉力、反牽引占據上風,人就會被墜落為意向性客體,世界因而也會成為與人的參與實在的運動無關的外部世界。
實在經驗的兩極作為體驗的兩個極點,有著多種多樣的符號化形式,譬如生與死、圓滿與缺陷、時間與永恒、秩序與失序、真理與非真理、生存的覺解與生存麻木、愛上帝(amor Dei)與自愛(amor sui)、開放心靈(l’âme ouverte)與封閉心靈(l’âme close)等等【36】,它們作為張力體驗的兩極,是向上與向下的兩種力量,人就生存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之中,對張力的意識並不是一個由某一認知主體接收到的物件化資訊,而恰恰是實在得以在其中顯明自身的那個過程【37】。
在個人那裏,並不存在一旦得道就自此達到了人性的最高可能性——被設想出來的完成了的人,即便是瞬間綻放的永恒體驗也仍然無法脫離生存體驗兩極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就社會而言,並不存在一個原初的伊甸園式的開端性的美好社會或末世論意義上的絕對終極的地上天國,社會本身也永遠處在張力之中,為了任何一種絕對王國而瓦解張力的動員最終都走向社會失序。
生存的真理就開放在生存體驗的兩極之間的張力性結構中,而無法消除其中的任何一個極點,也無法將其實體化(客體化)為內在世界或超驗世界中的某物,因而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時時刻刻的戒慎恐懼,都是面對張力的必要態度。任何試圖消除兩端中的任何一端極點的做法以及將任何一種極點實體化的取向,都將導致生存真理的畸變,從而造成個人乃至社會的失序。
在生存體驗的兩極力量的互動作用中,實在對其參與者呈現自身。將兩極保持在張力結構中的生存真理因其著眼於不同的極點,而有不同的類別。沃格林指出:從緊湊的宇宙論真理的分殊化進展已經解析出兩種生存真理:
一是以希臘為代表的著眼於人的探尋的人學真理(anthropological truth),這一真理類別包含了以心(靈魂)作為感受超越之中樞相聯系的全部範圍內的問題,它對應著原初宇宙體驗的智性分殊化,其符號化形式是哲學;二是在猶太-基督教中出現的「救贖真理」(soteriological truth),它對應著原初體驗的靈性分殊化,其符號化形式是啟示【38】。
緊湊性(compact, 意為渾淪而易簡)與同質性(透過類比來聯系相似的兩者,如人與神、世界與社會)是宇宙論風格真理的不同特色,而無論是人學真理還是救贖真理,都是經由分殊化進展而達致的非同質化真理。在宇宙論風格的真理中,根基被作為宇宙內最高事物;但是生存真理激發的卻是超越性體驗。
在古希臘的人學真理中,根據被辨識為神性努斯,求索生存根據的超越體驗,正是人的努斯與神性努斯的合一、相互參與( metalepsis )的體驗。其內核是人的智性意識,即努斯,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本心,被經驗為感受生存張力的神性根基的感受器官。人學真理一旦喪失了來自根基的推動,那麽智性意識就會蛻變為作為主體的人的內容,努斯的邏各斯化、邏各斯的邏輯化,邏輯的數理化,數理的數量化(數據化),就是必然的,隨之而來的是哲學不再承受生存張力而是下降為智者的論辯技術。
伴隨著智性意識而展開的生存真理,將人體驗為「既體驗著存在秩序、又在自身秩序中向存在秩序調諧的存在」【39】,「人類本性核心之點在於,對根基以追問著的知曉與知曉著的追問這種形式敞開。透過這種敞開,秩序從存在根基直接流入人的存在。——這超越一切內容、形象、以及模型。」【39】知曉與追問本身刻畫出的是智性的體驗,它不是對某物的體驗,而是對追問本身的體驗,是人在這種體現中向著存在根基的生成的體驗。當孟子以盡心的方式知性、以知性的方式知天時,孟子給出的也是基於人的探尋以敞開生存根據的「人學真理」。
而對救贖真理而言,對於生存的根據已經無法基於人的主動探尋來實作,相反,人必須變成完全的被動者,接受來自更高存在或力量的恩典或啟示。這是以徹底放棄屬人性的機制以開放屬神性、屬天性的機制的方式。屬人機制的充分放棄,不僅消除任何我性者,而且消除人性者,這時候天(在保羅那裏是上帝)對人的作用就會呈現;重點不再是從內在於人體與內在於世界中的人性與人心出發來貫通天道,而是人心、人性從世界中徹底逃離、脫離,人作為人與世界剝離之後的純粹剩余物——剩下來的只有純粹精神,以等待上天的啟示或恩典。因而,救贖真理是被超越性俘獲的體驗,是完全被「根據的根據」完全牽引的體驗。以意向性經驗敞開的只是「物-實在」,意向性認識已經不再能接近它,而是只能以顯亮性意識來敞開的「它-實在」【40】。
沃格林以其深刻的思辨,將現象學的意向性體驗奠基於顯亮性體驗的基礎上,拒絕了以先驗主體名義發動的去世界化的誘惑。他以智性或靈性接納生存張力,由此而區分上述兩種生存真理,這就使得在他那裏,他拒絕並避免了將永恒與終末拉入時間與歷史之內的靈知主義思辨,而是將並非時間中而且也不受歷史影響的永恒在時間-歷史中的臨在,視為導引此世生存的定秩化力量,據此將人之此世的生存轉化為一種具有末世論性質的朝聖之旅——確切地說是朝向神之下的不朽之生存。這是一種在實體化了的上帝之死後,那種全知敘述主體退隱之後采取的沒有超越者的超越性道路,這是為西方的生存真理所做的最偉大辯護。
然而,中國思想對生存真理的探尋,卻既無法被化約為人學真理,也無法被等同於救贖真理。儒家思想透過「仁」突破了三代宇宙論秩序,將禮法秩序奠定在對人性的展現理解——仁——的基礎上,同時又以中道的思想將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貫通起來,從而形成了生存論上的中道真理,這一真理的核心是兩極的互動內蘊和彼此平衡。
不同於人學真理將承受超越根基的感受中樞理解為作為智性意識的靈魂(努斯,Nous),也不同於救贖真理將之理解為作為靈性意識的靈性,儒家思想將人的全體作為感受超越體驗的中樞,由此我們看到在儒家的表述中,並非人心是天地之心,而是人是天地之心,即不是人透過心——無論是作為意識還是精神,而是透過人整個的生命存在,來貫通超越性的天道——盡管這種超越性並沒有實體化的超越者,而只是生存的根基。
這就使得生存張力中的兩極並沒有被限制在意識經驗中,而是在身心一體的生命整體中回應天人兩極之間的上升性與下拉性的力量。換言之,在沃格林發現的兩種生存真理中,一個共同的特點是身心分離,二者被對應為自然與精神、自然與歷史、感性與理性等等多重對立,真理只是顯現在精神、歷史、理性的場域——這明顯不同於儒家之身心合一。
不論救贖真理還是人學真理,實質上都是精神突破的結果,人不再透過宇宙內事物,而是透過人性意識中的生存張力來透顯實在。人在其關於人性的意識中發現人生存在居間性的張力結構,一方面是意識中作為根據的「天」之牽引,另一方面則是來自「人」的力量。人之所以不再是宇宙內現成性事物,就在於他生存在意識中人與天的居間張力中,其生存形式展開為兩者之間的運動。
來自天道的牽引,使得人處在一種以超越當前的現成狀態及其結構為目標的運動中;而來自人的力量往往意味著一種下拉性力量,它將人導向現成性,即將人視為一種當下完成的宇宙內事物。作為處於天人的居間性張力結構中的存在者,居間性構成了人之存在的本質特征。而這種居間性正是中道的內核。
中道真理就是將天人之間的居間張力作為其精神實質的「元真理」。所謂「元真理」,可以理解為:它是第二序的生存真理,相對於作為第一序的救贖真理和人學真理,它更為原初。中道真理在現實世界中往往不得不發生變形,而人學真理和救贖真理可以視為生存真理的不同變形:一者突顯生存張力體驗中的「天」,一者突顯張力體驗中的人。畢竟在經驗世界中,中道真理的顯現往往是采取變形的方式。譬如,在沈陷於人性的社會中,救贖真理就成為實際的中道;而在出世取向成為潮流的時代裏,人學真理就成為承載中道的真理形態。
當然,中道真理也可以被視為與救贖真理、人學真理共處同一平列層次而不同於二者的第三種真理。畢竟,生存真理的內核是天人之間的居間張力,而所謂天與人,並非兩種客體化事物,而是人在自身意識中發現的張力性結構的兩個極點。人總是會超出作為宇宙內某一事物的定位,尤其是其心靈,並非物件化事物,而是連線自我與他者、自我與世界等的一種結構性網絡。人在人性意識中發現,人不僅僅總是朝向人之所以為人的極點運動,而且也總是奔赴作為根基的天,人的生存總是展開在意識中的人極與天極之間的互動運動。正是這種運動彰顯了實在與真理的內核,這就是生存張力結構中的兩極張力。
而中道真理之所以為中道真理,就在於它直面這一內核,並將之視為超出一切歷史中發生的生存真理類別。當莊子在【大宗師】篇中強調真人的品質在「天人不相勝」時,就是將中道視為真理的類別,天不勝人,人也不勝天,這裏的核心是天人之間保持一種張力性的平衡,從而區別於「遊方之外」者所體顯的「畸於人而侔於天」的「救贖真理」。
如果說在宇宙論秩序中,人透過人與天地萬物所展現的宇宙節律的協調來構建自己的生存形式,那麽經由「軸心時代」或「天下時代」的精神突破,生存形式所基於的深層協調被轉換為人性意識中的天人兩極,也就是人與超越性的根據的協調,成為實在及其經驗的根本性結構。而中國思想強調的是人性意識中天人兩極之間的居間張力與動態平衡。
由於作為根據的「天」在人性意識中發生了進一步的分層,因而這種居間平衡表現為更加復雜的結構,展開為四個維度:其一,三重根據(人之天、乾元之天和太一之天)的平衡;其二,個體內部的身心平衡;其三,個人、社會、宇宙與根基的平衡;其四,超越性與歷史性的平衡。所有這些都區別於沃格林在古希臘和以色列看到的人學真理和救贖真理,展現了中國思想對生存真理的不同理解,以及超越性的獨特形態【41】。
更重要的,中國思想的中道生存真理及其體現的超越性,並非以存在的名義拒斥變化,而是以變化的普遍性為出發點。儒學和道家所突出的世界理解,具有「化則無常」(【莊子·大宗師】)、「唯變所適」(【周易·系辭下傳】)的取向,在那裏,一切皆流,萬物皆化,沒有既定的目的,也沒有末世論的方向。
作為根基一極的「天」,在儒家思想脈絡中被分殊化為:(1)不可測度而時時刻刻都在潛移默化的「天之體」,此即「為物不貳」之天;(2)在日月星辰中呈現但從來不能被固定拘泥的「天之象」,即法象之天;(3)唯有對人而言可以與之統合的「天之德」。儒家對生存根基的理解,著眼於人的生存張力,無論是「天之體」,抑或是「天之象」,都在無常之化中,不是人的生存根據,而人所納入其生存根基的則是可以使人貞定的「天之德」,「天之體」無法顯化,「天之象」在氣化之五常中運作;在萬物生生不已的過程中所顯發的「天之用」中,則可以體驗到「天之德」。
中道的生存真理直契「天之德」,將其化為生命生活的一部份,但「天之德」卻無法以語言方式充分符號化,也無法被意向性意識所客體化,因而,天在人那裏所表現出來的就不是創世的言說,譬如【約翰福音】所謂的「道成肉身」,而是不言之默。人在四時執行、百物化生中感受到不言之天德,體之於身,因而人可以自己生命的「文」與「德」來顯現並確證中道真理。
由於有確實的德行作為依據,因而不再如沃格林那樣在意識-實在-語言的復合組構中打轉,而是以生命之文與生命之德體驗天人之際的中道真理。作為中道真理的代表者,儒家的聖人不再是超越性的先知與哲人,他們在與凡俗的生存抵抗中彰顯其來自根基的吸重力,而儒家的聖賢則超越了超越性,因而能夠即凡而聖,化聖於凡,因而聖賢追求的不是理念化或純粹靈性的生存,而是即出即入、在入世與出世之間達成了真正的平衡。
沃格林所呼喚的生存真理張力體驗之兩極的居間或在意識中的均衡,出現在作為未來思想之可能性的儒家哲學中,在那裏,已經不再需要預設非時間性的永恒與全知敘述主體的末世期待視域;在這個不變的只有變化的宇宙-歷史的洪流中,人所據以自我貞定者,不是「天」之「體」「象」「用」,而是「天」之「德」,中國思想的超越性以及生存真理最終落實到「天人合德」上。
總體而言,天下時代的精神突破,本質上是對宇宙論秩序的突破,這一突破意味著超越性意識的誕生,即從宇宙論體驗向著超越性體驗的轉變。在這一轉變中,古希臘和以色列分別建立了哲學和啟示的符號形式,以表達超越體驗。而中國則以經史作為其超越性體驗的符號表達形式。
超越性體驗展開為人性意識中的生存張力意識,在生存張力的天人兩極中,對天的突顯導致了以色列式的救贖真理,對人的強調則走向希臘式的人學真理,中國思想則致力於在人極與天極之間保持張力性平衡的「中道真理」,後者意味著沃格林所謂的「居間」的機制化,這一機制化本身當然是將超越性意識引向歷史中的文化宇宙,人類立足於歷史中綿延的文化宇宙以與自然宇宙彼此協調,從而實作了對超越性的居間性轉化。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人學真理、救贖真理還是中道真理,作為生存真理的不同形態,各有局限,各有優勝。
它們都遵循著生存真理的視角主義顯現原理,沒有任何一種生存真理類別可以占據真理本身,從而達到真理的一次性、完全性呈現;相反,每一種類別的生存真理都是真理的不完全性、相對性、視角性顯現,這就決定了只有透過不同生存真理的互鑒和互釋,才能理解自身局限,從而向其他真理形態開放,消化並吸收其他形態的生存真理,以此方式豐富和提升自己,這本身就是一種在歷史中展開的自我超越。
註釋
1陳赟:【馬克斯·韋伯與儒家孝道倫理的超越性問題】,【道德與文明】,2021年第3期。
2陳赟:【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與歷史意義問題】,【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3陳赟:【沃格林論「天下時代」的秩序轉換】,【社會科學】,2022年第12期。
4Benjamin Schwartz,「The Age of Transcenence」,Daedalus,1975,104(2),p.17.
5陳赟:【「治出於二」與先秦儒學的理路】,【哲學動態】,2021年第1期。
6陳赟:【天經·地義·人情:具體普遍性的結構】,【中山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
7米爾恰·伊利亞德:【宇宙與歷史:永恒回歸的神話】,楊儒賓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7頁。按:楊儒賓將作者譯為「耶律亞德」。
8米爾恰·伊利亞德指出:「每一次危機的關鍵時刻,在每一個透過儀式裏,人們再次重演太初世界的戲劇。共演出兩次:一是回到太初的整體,二是重復宇宙的誕生,也就是打破原始的統一性。……個人與集體的生活具有一種宇宙論的結構:每一個生命都構成了一個迴圈,它模仿著世界永恒的創造、毀壞和再創造。——達雅各神話賦予了太初的整體性以極其重要的意義。幾乎可以說,達雅各人癡迷於神聖的兩個方面:太初和整體。世界因神聖而善、而有意義,它來自生命樹,也就是說,來自完成的神性。只有太初的整體,其神性才是完美無缺的。——神聖的歷史發生了,歷史必須透過周期性的重復而獲得永恒,將實在固化在胚胎狀態,如同在一開始那樣淹沒在太初的神聖整體裏面,是不可能的。……每一個神話都表現出前後相續的、連貫的一系列太初的事件,但不同民族以不同方式對這些重大行為做出判斷。」(伊利亞德:【探尋:宗教的歷史和意義】,晏可佳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98、99、100頁)
9王弼、韓康伯註,孔穎達疏:【周易註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註疏】(整理本)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10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1、105頁。
11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5冊【朱子語類】第4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5頁。
12陳赟:【中庸的思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9頁。
13趙汀陽:【歷史為本的精神世界】,【江海學刊】,2018年第5期;趙汀陽:【歷史·山水·漁樵】,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1-2頁。
14佛烈德利赫·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獻給自由精靈的書】,楊恒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頁。譯文根據英文本略有改動。
15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李秋零、田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16陳赟:【「原史」:中國思想傳統中的原初符號形式】,【船山學刊】,2022年第6期。
17陳赟:【「治出於二」與中國知識譜系的建立】,【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
18卡爾·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李夏菲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74頁。
19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6冊【朱子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7頁。
20郭象註【莊】雲:「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1、51頁)羅君章【更生論】雲:「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梁釋僧佑撰,李小榮校箋:【弘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頁)清人黃叔琳【硯北易鈔】卷12雲:「又觀向秀所註【莊子】有雲‘天者萬物之總名’,尤超出意表。」明末哲人劉宗周繼承了向郭的這一說法。
21 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四書或問·中庸或問】,第551頁。朱熹:「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絶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3冊,第2854頁)
22相似的問題,在朱熹哲學中得以表達,這個表述的重點在於強調人的品德與天地之德之間的相似性:「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卷95【程子之書】,第3178頁)「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朱子全書】第15冊【朱子語類】卷36【論語】,第1357頁)
23 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頁,第4頁,第6頁,第7-8頁。
24 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3冊【船山經義】,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692-694頁。
25陳赟:【秩序與渾沌的居間性平衡:論莊子的秩序形上學】,【孔學堂】,2023年第1期。
26陳赟分殊了「太虛之天」與「乾元之天」,參見陳赟:【氣化論脈絡下的身體與世界】,收入林月惠主編:【當代中國哲學的議題:以氣論與身體為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年版,第161-215頁。
27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第47頁。
28「不是所有的人類都是嚴格意義上的人,不是所有人類都能成為道德主體的人。……嬰兒在這個意義上不是人。極其衰老者和嚴重智障者從這個重要方面來看都不是人。」(齊斯特拉姆·恩格爾哈特:【生命倫理學】,轉引自羅伯托·埃斯波西托:【人與物:從身體的視點出發】,邰蓓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頁)
29保羅·利科:【惡的象征】,公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頁,第214頁。
30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18,Order and History V,In Search of Order,edited by Ellis Sandoz,Columbia & London:University ofMissouri Press,1999.p.29,p.30.
31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28,What is History?And Other Late Unpublished Writings,edited with an introducation by Thomas A.Hollweck and Paul Caringella,Baton Rouge &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184.
32艾歷·沃格林口述、桑多茲整理:【自傳體反思錄】,段保良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頁。
33對沃格林關於顯亮性經驗與意向性經驗及其分別的探討,參見朱成明:【沃格林意識理論與東西知識傳統的深度對話】,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29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92-115頁;陳勃杭:【艾歷沃格林對意向性和啟明性的區分】,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29輯,第142-173頁。
34這一術語來自沃格林對荷馬史詩中的諸神的解析(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15,Order and History II,The World of the Polis,edited by Athanasios Moulakis,Columbia & London:University ofMissouri Press,2000.p.170)。
35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15,Order and History II,The World of the Polis,edited by Athanasios Moulakis,Columbia &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170.
36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12,Published Essays 1966-1985,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lis Sandoz,Baton Rouge &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119.
37艾歷·沃格林:【秩序與歷史】第4卷【天下時代】,葉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頁。
38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5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nfred Henningsen,Columbia &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p.149-162.
39艾歷·沃格林:【記憶:歷史與政治理論】,朱成明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頁,第197頁。
40Eric Voegeli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18,Order and History V,In Search of Order,edited by Ellis Sandoz,Columbia & London:University ofMissouri Press,1999.p.51.
41陳赟:【「中國」作為「中道之國」——基於儒家仁性論的視角】,【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10期。
作者簡介:陳赟(1973—),男,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文明視域中的中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