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讀書日,這是一個關於人與書的節日,也是關於書與人的節日。
書與人的相遇,看似是人單方面的找尋,但書也在默默地等待。比起那散發著簇新氣味的新書,舊書更有一番深沈的情意。波赫士將書比作人類最嘆為觀止的工具,其他工具都是身體的延伸,唯有書是想象力的延伸。但舊書不僅是想象力的延伸,更是時間的延伸,與情感的延伸。舊書暗黃的書頁與脆韌的紙張,是歲月的痕跡,而書頁的折痕和書邊的批註,則是情感的銘印。從舊書中讀出的不僅是書中的內容文字,細膩的眼睛,更能從中看出往昔歲月中前任主人給它留下的獨一無二的標記——那字句下的劃線,曾經讓一顆心靈產生共鳴;那書頁上的折角,曾經讓一雙手再三在那裏停留。書中的一張字條,是一段舊日的回憶,字裏行間的批註,記錄著靈感閃現的一刻。

4月中旬,在天津鼓樓舊書市選書的人們。(新京報記者 李陽 攝)
在本文中,我們請歷史學家楊念群、王東傑等書評周刊老朋友與大家聊一聊「書與人」。以下為他們的口述整理。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年4月19日專題【舊日書】中的B04-05版。
楊念群:舊雜誌上的舊文章,讓我沖破舊觀念的束縛
人的一生可能會讀過很多書,也接觸過許多文字,這些書或者文字到底對其人生的成長有多大意義往往是模糊的,不容易那麽確定。我的讀書經歷也是如此,我記憶力並不好,所以特別忌諱談什麽讀書經驗,因為在我的閱讀生涯裏,並沒有哪一本一定印象最深,或者帶有決定性的人生指南著作留在了記憶中。唯一有一篇文章卻是個例外,那就是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寫的一篇演講詞【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這篇文章被轉譯過來最早發表在1980年的【外國文藝】雜誌的第5第6期合輯之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正逢改革開放初期階段,對外國小說或者社會科學理論的轉譯相當稀少,轉譯成中文的西方短篇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也不多。所以當我讀到這篇演講時有一種突遭觸電的震撼感覺。

1980年的【外國文藝】雜誌,這本雜誌曾經開啟了許多年輕人的視野。
這篇演講詞是薩特為了回應學界對【存在與虛無】這部存在主義經典著作的誤解而寫,演講中提出的一個最重要命題即「存在先於本質」,這是個哲學命題,同時也是一種做人的基本態度。大意是說,以往人們做出人生抉擇往往要依賴上帝的睿智,因為上帝有權決定一個人所度過的人生意義的「本質」。而作為無神論者的薩特卻認為,「人」作為一種存在主體,應該先於各種外在規範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和行動邏輯。原來大家遵循的是「本質先於存在」的原則,現在反而應該倒過來強調「存在先於本質」,就是真正建立起人類的「主體性」。
記得當時閱讀這篇演講時並非是把它當作一篇純粹的哲學文章來看的,也不是為了參與「存在主義」哲學觀的討論。而是「存在先於本質」這個命題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因為在我上大學時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才剛剛起步,各種新思潮不斷湧入,讓人目不暇接。而各種過去遺留下來的舊觀念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還是相當嚴厲的,新思潮的出現不時受到打壓和質疑。如何發揮人的主體性,沖破陳舊思想的網羅,特別是已經僵化至極的各種教條化思維的束縛,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必須回答的一道難題。而薩特這篇文章的啟示是,作為年輕一代,不就是要沖破那些作為「本質」的官樣教條思想的束縛,大膽把自身主體的「存在」意向作為優先考慮的選項嗎?不就是要用自己的思考(存在)去替代那些早已過時的「本質」規定性嗎?
這篇文章還指出,要讓每個人一旦做出選擇後就要勇敢地承擔起責任,如果把這個命題轉換成每個中國人的現實考量,那就是當你做出人生選擇時,有可能會遭遇困難和各種抵制,但是必須提前把可能發生的各種後果,包括好的和壞的後果都盡量考慮在內,當遇到各種生活的阻力和障礙時,面對可能發生的後果,要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責任。這為我確立沖破舊思維網羅的勇氣和信心,提供了一個很恰當的理由。回首這段閱讀經歷,我有時會自問,在當今日益喧囂浮躁的復雜社會氛圍裏,你是否仍然保持著那顆「存在先於本質」的選擇初衷呢?是否慢慢被各種新的「本質化」教條所侵蝕腐化,喪失了自我「存在」的感知能力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又在三十年後重讀了薩特的這篇文章,目的不僅是為了懷舊,更是想重新確認自己仍然還有選擇「自我」存在方式的能力。
王東傑:本不必有什麽「必然」
我想起一本英文舊書,以賽亞·伯林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歷史的必然性】),一本薄薄的精裝小冊子,是他1953年一次演講的稿子,以後收入了鼎鼎大名的【自由四論】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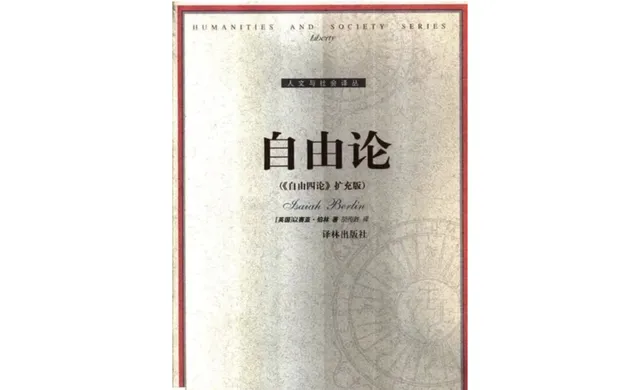
我最終沒有找到那部原版的【歷史的必然性】,但好在,這本書在2003年轉譯成中文,收入【自由論】中了。
這本書是我讀碩士時候淘到的,正好三十年前的事。有一度同濟大學圖書館出賣英文舊書,我不太清楚那些書是怎麽來的,一屋子都是,滿坑滿谷,隔三差五就會換一批,似乎都是從美國海運過來的。很便宜,復旦很多同學都跑去淘。我經常跟哲學系的朋友、現在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的王瑞鴻教授搭伴兒。
淘英文書不容易,早期有很多障礙。一個是學術上的:很多人的名字聞所未聞,不知道哪些書重要;一個是生理上的:書脊上的字是橫排的,不像中文書是豎排,讀起來很方便,英文書得把頭側過去念。英文水平糊學術水平都有限,淘得很累。後來慢慢摸出點門道:不看大開本的,不看封面花裏胡哨的,那很多都是教材,或者流行小說。
就這麽著,歪打正著,淘了一些後來才發現很重要的著作,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其實買它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以賽亞·伯林是誰,我只是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所以我很幸運。讀了之後,大受啟發,知道「歷史的必然性」隱含了對個人道德責任的排除: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是被身外的某種無可抗拒的因素所決定的,我們當然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然而這是很荒唐的。它很容易導致一個人為所欲為。自由包含了責任,歷史的必然性和自由相矛盾。我就是從那時起,在我的認知字典裏刪除了「必然性」這樣的字眼,以後我寫論文、寫書,從不使用這個詞。
那時候,我們住在復旦南區,來往於校本部、文科圖書館和我導師朱維錚先生家,都要穿過很多居民區——復旦很多地盤,是和校外的人混雜在一起的。常常,在夕陽西下時回宿舍,要經過一片菜市場,我都看到一個老太太在撿爛菜葉。我不知道她的經歷,是不是一位剛下崗的工人?夕陽映在她的白發上,一片燦爛,令人眼花——我不大清楚腦海中的這幅畫面是我的記憶還是想象。
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起飛,很多人一下子有錢了,很多人還是很窮。很多有錢人說:那有什麽辦法?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原始積累當然很殘酷,但都要經過這個階段,這是歷史的必然性啊!那時候我已經讀了伯林的【歷史的必然性】,我對說這些話的人說:胡扯!我不相信這幾個字。後來在課堂上講「史學概論」,談到歷史的必然性,我總會說起那個撿菜葉的老太太。我想,我還會說下去。
胡成:我等在舊書攤前,依然希冀著那曾經的求之不得
類似少年聽雨與而今聽雨的不同,不同階段對於舊書的取舍亦不相同。
少年,不但沒有歌樓,書也很少,城裏只有一家新華書店,所以一應不是當下出版的舊書,都極難得。也沒有固定地址的舊書店,行蹤飄忽的幾處舊書攤,便成獲取「過去出版物」的唯一渠道。
學校附近,那時地屬郊區,街後連排的平房,幾條窄巷,我記憶最深的舊書攤就在某條窄巷路口。一輛平板車,木凳撐起車把,擺平的板車上雜亂無章地擺著各種舊書。
攤主,一個老頭兒,就住在窄巷深處,大約做著收購舊書廢紙的營生。附近拾荒的,或者蹬著三輪走單幫的收廢品的,會把舊書轉賣給他。他給的價格,自然會比廢品收購站論斤約的價格高一些。
漸漸地,知道這處舊書攤的人越來越多,去晚片刻,好書便無蹤影。
大約晚我一兩年,有個矮胖的總是剃著平頭的男人總比我先到書攤,而自從他出現,我幾乎再也沒有買著像樣的舊書。
又過一段時間,平頭男把老頭的底細打聽清楚,索性也不在巷口等待,而是經常直接登門,先把有價值的好書一掃而空。但他並不看書,只是也想做點兒舊書生意,於是就在我住的小區附近租下一間平房,作為他的庫房。
有天,梅雨後初晴的日子,他招呼著路過的我進門去看他的戰利品。門前碼著一地的書,曬曬太陽,褪褪潮氣。真是有很多我求之不得的好書,比如我只買著兩冊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精裝版【巴爾錫克全集】的其余幾冊。

【巴爾錫克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是傅雷先生轉譯的。
他自然可以轉賣給我,但是要價卻比老頭兒貴上五倍都多,而我卻是囊中羞澀的學生。
後來老頭兒的舊書攤我去得越來越少,因為再難買到什麽好書。除非平頭男偶爾幾天沒有過去,還能有幾本漏網之魚,比如中華書局初版的【柳河東集】,但這希望已經渺茫得近乎於無。
而今雖然鬢已星星也,好在那些原本求之不得的舊書,卻已唾手可得。
但是求之不得,才有意願搜藏,唾手可得,也便無所謂擁有。於是終於醒悟,我或者我們以為自己愛的是舊書,實際上愛的終歸還是求之不得。
於是現在的搜求舊書,卻已不再是那些普通的現代印刷出版物,而是古籍,無所謂有用還是無用,有所謂的還是珍貴、罕見與難以搜求,比如稿本、抄本。
當然,清代以前的善本價格也非我等可以接受,生平買過最貴的一冊稿抄,若幹年前購自甘肅省定西市,清光緒年間的【續修隴西縣誌稿】,彼時隴西士紳編撰是書,卻因時局動蕩,地瘠民貧而未得付梓,僅存此稿抄本一冊。我曾試圖點校此書,卻因所記內容許多有違當下民族政策,因此半途而廢。
不過每每看見,我總還會想起少年的梅雨初晴後,那間平房裏曬著太陽的幾冊【巴爾錫克全集】。那時若是可得,我會逐頁讀完,而現在我若得著,哪怕昂貴千萬倍的古籍,也只是草草翻過,然後束之高閣。
黃博:舊書堆裏的寶藏
書的生命,當然不以新舊而論,不過舊書如老酒,越久越醇,越久越有故事。
還記得十歲左右,彼時尚在讀小學的我,因為暑假無事,已正在家中發了幾個星期的呆了。有一天突然收到住在重慶市區的舅舅來信,邀我去他那裏小住幾天,並說他家裏有一批閑置的舊書打算送給我。聽到有免費的書可拿,我欣喜若狂,不等父母放假,執意要馬上去重慶。我家當時住在離重慶市區有八十多公裏的長江邊上的一個棉紡織廠裏,從那裏坐船去重慶,因為是上水行船,最快也要七八個小時。這麽長的路途時間,父母當然不同意一個小孩子獨自出遠門。不過賴不過我的軟磨硬泡,加上托了幾個正在跑船的熟人,我終於坐上了去重慶的夜航船。
這次重慶之行,我從舅舅那裏背回了二十多斤重的一大堆舊書,整個暑假都浸泡在文字的海洋裏,這大概是我最早體會到閱讀樂趣的一次機緣吧。在這批舊書裏,當時最吸引我的是周振甫的【詩詞例話】,這是一本談論如何鑒賞古典詩詞的小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62年初版,我得到的是1979年的第二版,這書的年齡比我還大啊!書中摘選了許多古代詩話和詞話的原文,輔以作者精妙的解題和點評,讓我第一次發現,在記住作者和詩詞的創作背景,轉譯文句大意、提煉中心思想等語文課的詩詞讀法之外,詩詞還可以這麽讀!後來我才知道,這本書的作者周振甫,乃是有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大家。

【中國古代笑話選註】【詩詞例話】【兩宋後妃事跡編年】,好在當初在舊書堆裏淘出了這些寶藏。
讀大學的時候,我晚上最喜歡去閑逛的是學校附近的一條專賣舊書的大街。那時一到傍晚八九點鐘,路上全是擺地攤賣書和買書的人。不過因為囊中羞澀,我常常是去湊個熱鬧而已,只看不賣,過過幹癮。不過,有時見到一些十分奇妙的書,也甘冒著苦一苦肚子的無奈,豪擲「巨款」將書拿下。現在放在案頭經常還會翻翻的【中國古代笑話選註】,就是當年花了五元錢,餓了一頓飯買下來的。這本書是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在我讀大學的2000年左右,已是有十多年歷史的舊書了,到今天,則已足足有四十年之久的歷史了。本書從古籍中摘錄了許多搞笑的片段,然後輔以註解。一邊可以學習文言文,一邊又可以放松心情,真是一舉兩得。說實話,書中的許多選段,如果按某一個主題串聯起來,再添油加醋地用現在流行的歷史小說的筆法重新寫一遍,完全可以做成一本讓現代人看古人笑話的暢銷書。
說起這個,其實舊書裏不乏很多因為各種原因而被埋沒的暢銷書種子。比如【兩宋後妃事跡編年】,就是這樣的一部被遺忘的寶藏書。這本書是巴蜀書社於1997年出版,作者從宋代史籍中摘錄出了有關後妃的紀事的原文,再按年編排匯為一編。雖然不免有許多疏漏之處,但也算是比較完整地呈現了宋代後妃的大事紀年。我知道這本書,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在學校的圖書館裏第一次見到此書時,它已是一本出版約有十年的舊書了,但仍然讓我就眼前一亮。可惜因為出版太久,當時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
幸運的是,多年之後,我竟然白嫖到了這本心心念念多年的老書。2011年,當時我剛博士畢業留校工作的時候,在巴蜀書社工作的朋友說社裏有一批庫存的舊書可以相贈,我就厚著臉皮向朋友要來了這本【兩宋後妃事跡編年】。不過,因為純是史料組譯的體例,這本書其實並不適合拿來作消遣式的閱讀。入手之後,一直放在書架上已經多年,很少仔細品讀過裏面的內容。因為當時的我,其實沒有理解到這本書真正的價值。這幾年宋代宮廷劇流行起來後,才發現完全可以在這本書的史料基礎上,將兩宋後妃的事跡重新整理鋪陳,搞出一部現代古偶大劇,也不是不可能啊!事實上,宋代後妃們的故事,相當符合現在最流行的所謂宮鬥大女主的爽文題材,而這本書裏類似的素材簡直不勝列舉。
朱琺:【一千零一日】,是的,我沒寫錯書名
「一千零一日?」沒錯。依照【一千零一夜】的格式,也譯作【天夜日譚】。此外,還有第三個名字叫「Hesarlek pus」,意為「千日談」。據說,十七世紀時候,法國學者彼狄斯·迪·拉·克羅依克斯(Pétis de la Croix)最早將【一千零一夜】譯成了法文,然而不曾付梓,手稿至今猶保存在慕尼黑圖書館。據說,正是他,還將【一千零一日】譯介到歐洲,卻直到百年之後的1785年,才由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還有【一千零一刻:韃靼故事】(1712)和【一千零一時:秘魯故事】(1759)這樣的傳奇故事集,把【一千零一日】視為這種時代風氣的產物,似乎並無不妥;可以透過本書來觀察經典的叢生、故事的演變,以及真跡與偽作之間、敘事者與作者之間微妙復雜的關聯。書中記有一些敘事母題,或者為今人援以為典故,譬如:所羅門王的指環,圖蘭朵公主的難題,以及作為故事集主線人物的「克什米爾公主」。本書結構與【一千零一夜】及【五日談】相近,克什米爾公主的奶媽蘇特魯美妮(一譯毛姬·芭赫爾)是故事的朗讀程式。但它貫徹自書名而起與夜譚相悖的形式,連故事主線的設定都是相反的:【天方夜譚】是緣起於不忠及厭女癥;而【天方日譚】的動力卻是在厭男癥的治療過程中產生的渴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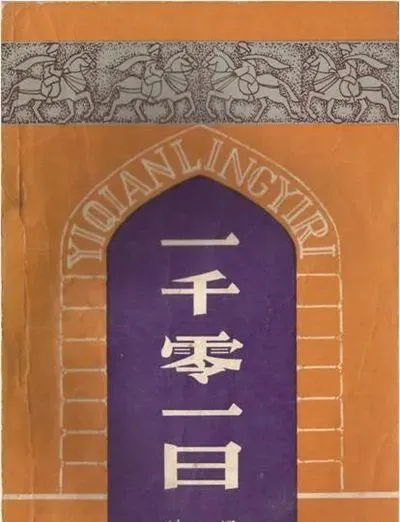
【一千零一日】,不是【一千零一夜】。
兩本書在影響力方面當然也一顯一隱,大相徑庭。1981年,【一千零一日】才有了一個節譯的200頁中文本,被視為【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由香港轉譯家杜漸自英文選本轉譯而來。我上世紀末讀大學時在圖書館裏看到,還以為是自己熬夜眼花或者出現幻覺看錯了。九十年代初,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從阿拉伯原文17卷本150萬字直譯而來的10冊【一千零一日】。書號各冊獨立,而前五冊首印六萬,後五冊僅有萬七。我花了數年時間,有在網上覓得,存館藏章和索書標簽;有在打折書店偶獲,數冊封底粘有條形碼和價格貼紙難以除去,不知是書店、書商或是出版方所為——終於攢全了十冊,又花了幾年時間,才陸續讀過一通。
盛文強:那條叫「唇唇」的魚遊向了圖冊深處
山東半島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加吉頭,鮁魚尾,鱽魚肚皮唇唇嘴。」這句諺語說的是四種魚類的美味之處。加吉頭,是指真鯛的頭部脂肪含量豐富,香濃可口。鮁魚是指藍點馬鮫,鮁魚尾則是指鮁魚的尾柄,這是鮁魚遊動時的「推進器」,肉質結實而又鮮美。鱽魚指的是帶魚,鱽魚肚皮也即帶魚的中段,時人以此為美味。
這則諺語的難點在於最後的「唇唇」,據說這種魚的唇部味美,端上桌來,老饕先照著魚唇下箸。至於唇唇是什麽魚,卻一直沒能搞清。翻閱資料尋找,和相關研究者討論,也無所收獲,只能暫時擱置。事有湊巧,最近淘到一部出版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舊書【黃渤海習見魚類圖說】,是張春霖、成慶泰等老一輩生物學家編纂的魚類圖冊,裝幀頗精致,書脊包布,精裝小開本。翻到「黑鰭髭鯛」的頁面,赫然標註著「唇唇」的俗名。該書作者有大量田野調查的積累,所列的俗名頗能接續舊時傳統,且當時尚有豐富的黑鰭髭鯛族群,可以歸入「習見」之類,這個答案應該是較為可信的。
【黃渤海習見魚類圖說】,書中的魚,終於遊進了知識的深海。
由這部圖冊出發,又翻檢山東半島一帶的方誌資料,發現一種「重唇魚」,疑即「唇唇」的早期版本,由書面的「重唇」到口語的「唇唇」,或為音調的訛誤,無意中由莊變諧。清光緒【日照縣誌】的「嘉鲯」條目下附有重唇魚:「又有口豐者曰重唇」。嘉鲯又名加吉魚,學名真鯛,可見重唇魚和真鯛相似,只是魚口較為豐滿。民國版【萊陽縣誌】載:「重唇狀類嘉鲯,而色黑味次,唇部較腴。」這句記載是說重唇魚和嘉鲯形狀相近,但顏色黑,口味稍微遜色,但唇部豐腴。民國【牟平縣誌】亦載:「重唇,唇厚若二唇重疊,故名,其味之美在唇。」這是說重唇魚的嘴唇有兩層,味道鮮美。民國版【山東省漁民歌謠集解】的註解也提到:「重唇魚即鷹魚鯛,為鯛之一種」。綜合對比這些地方史料,重唇魚的形態特征也可與黑鰭髭鯛吻合。
黑鰭髭鯛是一種近海肉食性魚類,經常出沒在砂石底的礁區,喜食螺貝和小魚。黑鰭髭鯛和真鯛形狀接近,呈長橢圓形,背部有棘刺,最顯著的特征是其唇部層疊,故而又名重唇、唇唇。隨著漁業資源的破壞,如今已經很少見到黑鰭髭鯛,「唇唇」的俗稱更是少有人知了,乃至有人誤認為「唇唇」是唇部更為豐厚的淡水鯰魚。
一種魚類離我們遠去,與之相應的地方性知識也隨之晦暗不明。海洋愈發空曠,想來令人惆悵。
李子纂:念茲在茲者,終有讀完之日
大約在小學的時候,我不知從哪裏獲得一本關於辛棄疾的小冊子——【青兕英雄傳】。讀罷,我被辛棄疾的忠義和英勇打動。此後,辛棄疾的形象就久久不能去懷。而我也總想找到更多關於他的書來閱讀。
後來,在課本裏,在其他詞選中讀到辛詞,就更想擁有一本稼軒的詞集了。但我從小生活在大山裏,雖在縣城上了中學,但縣城無文化氛圍,要得讀一優秀版本,也不容易。上大學後,我有段時間在圖書館保存本室勤工儉學,在整理書架時,看到架上幾冊已經落灰的【稼軒詞編年箋註】。此書我已聽師友們說起,說是好註本,於是就在空余閱讀起來。我第一次擁有這部書,是在大學接近尾聲時,那時學校圖書館剔除了一些副本量巨大的舊書,放在圖書館大廳供師生低價選購。我就有幸選到一冊【稼軒詞編年箋註】,草綠色的封面,滿鋪花草紋樣,顯得極為雅致。雖是舊書,拿在手裏,卻顯得柔和極了。雖然略顯殘破,卻毫不影響閱讀。這本書在畢業時被我帶回貴州老家。而我久在外地,回家的時間很短,所以它又一次蒙塵案頭。

【稼軒詞編年箋註】,我還是喜歡舊版的小花紋,不會太惹眼。
不過,稼軒詞集總還需再購一冊,以便隨身閱讀。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稼軒詞編年箋註(定本)】,我又將它請回家中。這次的封面,顏色偏藍,紋樣更為粗大。與舊版相比,我還是喜歡以前那樣的小花紋,不會太過惹眼。不過新版本也有好處,內容上作了不少修訂,更為完備。
前些年擬作鉛山之遊,準備將此書再好生翻閱一回。而我讀書遲緩,直至鉛山之行後數月,方讀畢此書。鄧先生寫作此書,數易其稿;而我讀此書,不時中斷。但念茲在茲者,終有完成之日。
采寫/李陽
編輯/李陽 羅東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