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時間是一座可以精確計算,隨意控制前後行進方向請讓我們跟隨穿越時間的畫面的鐘,從反方向開始移動,回到當初大東山的時空,去看那一襲被淋濕的黃袍,那看那一柄烈劍,去看劍鋒所向的中年人,去看無數人,在雨中。
靜止,然後秒針輕輕掙紮,彈動了一下,越過了第一個格子。
隨著四顧劍的一並指,那柄一直懸浮在空中地長劍,倏地一聲飛了出去,繞著他地身體畫了一個半圓,直刺慶帝地後背!
此時,葉流雲已經來到了慶帝的身邊,平直伸出他那雙如金石一般的潔白雙手。
劍已經刺破了空氣,撕裂了大東山上或許有或許沒有的濃厚元氣,下一秒鐘便似乎要刺入皇帝的後背。然而那一雙潔白的甚至有些稚嫩的手,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輕輕向著那柄劍按了上去。
——大東山上宗師圍殺慶帝之局,在這一刻終於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葉流雲出手,向著那把劍而不是皇帝!
最先接觸到這把殺劍的,是葉流雲的袖子,麻布織成的廣袖,在這一剎那變得極其柔軟,就像是無雨東山山腰間時常飄浮著的雲朵,柔柔地層層裹疊在那把急速飛來的劍上。
雲絲寸斷,麻袖碎成蝴蝶在大東山頂上飛舞,而那把劍,卻在這樣溫柔的廝纏中消耗了精魄,身上所攜的寒意殺意,倏然間消失不見,變成了一把破銅爛鐵,黯淡無光,十分卑微。
這把劍勢來的太兇太厲。以至於葉流雲在念出一偈之後,不得不出護住陛下安危,然則當他顯示了自己的真實立場,卻無法尋到最關鍵的那一點進行伏擊,該如何應付接下來地局面?
葉流雲白須被雨水打濕,而雙眼卻是認真地看著自己手中的劍,沒有因為劍身的黯淡而產生絲毫的輕視,更沒有因為自己被迫提前出手,而不能伏殺四顧劍。有些許的不安。
他只是認真地看著這把劍,握著這把劍,似乎這把普通的劍身裏,蘊藏著無數的鬼神,下一刻便會跑出來,將山頂上所有的人吞噬幹凈。
那雙穩定如玉的手抱了一個虛圓,虎口相對化作一個圓環,而那柄啞然無光地天劍,就在這半空之中頹然淩空靜止著。
他是大宗師。所以他才知道,四顧劍的劍意全數蘊在這一劍中,若自己此時再不出手,劍身便會全數刺入陛下的身體。
他於四海遊走若幹年,為的便是這一刻,然則,卻被迫提前動了。四顧劍不是真的白癡,正如事後長公主所料想的那般,他與苦荷雖然沒有想到葉流雲會站在慶帝一方,但是這二位北齊東夷的大宗師。對於慶國人的陰險狡詐,有著最深刻的認識,不到最後一刻,他們絕對不會讓自己陷入險地。
那個戴著笠帽地矮小身體裏,其實蘊藏著與歷史名聲截然不同的大宗師智慧,他只用了這一柄身外之劍。便破了慶帝的局,逼出了大東山上真正的殺著——葉流雲!
就在葉流雲像一輪明日般護在慶帝身前,雙手抱圓,強行鎮住淒厲一劍時,四顧劍的身體抖了起來,身上的麻衣就像是被電流襲過一般劇烈震動著,此時他的劍已淩空飛去,停駐在葉流雲那雙穩定的手掌之間,而隨著他身體的震動,一股驚天的劍意。蕩蕩然刺透了他身上所穿地麻衣,直沖天際。
受此劍意感召,葉流雲**雙手所控的那柄劍,也劇烈的顫抖了起來,在空中嗡嗡作響,重放光彩。
此時大東山上的雨還在嘩嘩下著,只是在這樣的片斷時光中,雨滴似乎在用一種奇慢的速度,細膩地感知著大地地吸重力。不再成絲成傾盆之勢,而像是一粒一粒晶瑩透明的珍珠。
就在重重珍珠玉簾之後。穿著麻衣的矮子以身為劍!勢破天地,就這樣須臾橫縱十余丈,像一道電般殺到了葉流雲的身前,伸手一摁,摁住了自己佩在身邊數十年,早已心意相通的那把普通劍枝!
四顧劍的手掌重新握住了自己的劍,劍上芒尖狂吐,如銀蛇亂舞,氣勢逼人。
而就在層層雨簾像靜止般被麻衣四顧劍生生撞破之時,葉流雲的眼瞳裏驟然間大放光芒,有如流雲裹日,生生吸取了太陽中的能量,悶哼一聲,拱成圓環無極的雙掌,向內一合!
啪地一聲脆響,空無一物的空氣卻像是堅硬的金屬,片刻後被這雙潔白的手生生壓碎,合在了劍身之上!
對於大宗師來說,沒有什麽局,即便慶帝設了一個局,將葉流雲隱藏到了最後,可依然讓四顧劍簡簡單單一劍挑破了重重迷霧,而緊接著,四顧劍卻利用了這個大好的機會,將自己的全部劍勢,重新灌入到這把劍當中。
葉流雲的身側是慶帝,當此淩厲一劍,卻是避也無法避,只有用雲手硬抗,然而無上劍勢與肉身相敵,葉流雲的散手身法卻無法盡情施展,四顧劍搶的便是這個先機!
大宗師之戰,偶一動念,便天地變色,只需要一絲偏轉,大勢便已偏移!
四顧劍淒厲瘋狂地叫了起來,一身狂戾地劍氣全數湧進了手中的這把劍上,劍氣湧入地速度是這樣的快,以至於手掌握著的劍柄處竟倏然間變得高溫起來,倏地一聲蒸發了草繩上的所有水滴。
令人恐怖的金石磨擦聲音響起,長劍在葉流雲緊緊合著的雙手間,往前突進了一寸!
葉流雲依然微低著頭,雙臂上的廣袖早已化作了身周空中飛舞的蝴蝶,世上最穩定的那雙手臂死死夾著那柄劍,片刻後,手上的皮膚……開始寸寸裂開,就像是得了某種皮膚病的患者。皮膚老去,邊緣翹起,看上去就像是慶歷五年地那場大旱中的土地,龜裂開來,異常恐怖神奇。
他的眼中全是寧然的目光,看著掌中的劍一寸一絲地向自己的身體靠近,卻沒有一絲情緒吐露,而只是吐了一個字。
「雲!」
兩只已經被
氣激地皮膚寸裂的手臂,隨著這一個字偈。猛然間來。比海水更深。比湖水更柔。比江南女子的眼波更溫純。是那天上地雲。雲中地絲絲僂僂。如牽掛一般。一僂一僂地系在了驚天一劍上。讓那強大到了極點地劍勢驟遇溫柔。不得不在途中暫歇。
哢地一聲,就在這短短地一秒間。天公極為湊趣地賞了一道閃電,照亮了被烏雲遮蓋。顯得格外陰暗地山頂。
閃電。照亮了四顧劍笠帽下地臉龐。只見他雙眼裏全數盈滿了如野獸一般地狂野氣息!
他沒有說一句話一個字。只是淒厲地尖嘯著。嘯聲回蕩在大東山上。不知道震昏了多少人。他是用劍地大宗師。他用地是四顧劍。顧前不顧後,一往無前!
劍勢隨著嘯聲全數湧了出去。逾發的暴戾不可阻擋。無窮無盡地殺意,暴戾的氣息。盡在這一劍中。
這是四顧劍出世以來刺出地最強一劍,是他整個人地生命。精神,信念凝結成地一劍。劍勢之淩厲暴戾。已有逆天之跡。在這片大陸上。以前從來沒有人刺出這樣地一劍。以後估計也沒有。
沒有人能夠阻擋。即便是葉流雲也不能!
局。往往是分不清局內人。局外人,謀局定勝地人們往往在事情結束地那一刻。才會悲哀地發現,自己算來算去。反將自己算了進去。誤了朕及卿家性命!
事情地發展,永遠和控局者最初的算計,會漸行漸遠,如果知道此時時鐘停滯地這一秒發生地一切。或許慶帝在最開始的時候,寧肯選擇將虎衛收攏於山。以慶國兩大宗師與苦荷四顧劍正面相敵。有五繡在旁,在百名虎衛於兩敗俱傷之後揮刀而斬,何至於會出現眼前地情況?
四顧劍在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裏。完美地展現了一位大宗師地智慧與決斷,只用了一劍,便逼出了葉流雲。更完美地利用慶帝布下的局以及慶帝地生命,將葉流雲逼入了絕境之中。
如果四顧劍不是在上東山登天梯之時,一劍斬盡百余虎衛,消耗了他部份心神,此時那驚天地一劍,或許早已經刺入了葉流雲地小腹之中。
當然,如果不是用上百名慶國高手地鮮血去祭這把劍,去蘊積無窮地血腥殺意,四顧劍或許也使不出來如此絕情絕性,暴戾動天地一劍。
葉流雲有三個方法可以應付這一劍。正如那個世界中三十六計地最後一計,當事態發展到了極端之時,最好地方法往往就是最簡單地方法。
以這位慶國宗師地無上身法和流雲散手,面對著四顧劍的驚天一劍,在最開始地時候,他可以選擇後退逃離。以散手雲海暫封劍鋒一剎,只需要一剎,他便可以離開那道劍勢籠罩地範圍。
然而皇帝在他的身側,如果他避開了,皇帝只怕會在這柄天劍下變成漫天肉屑。所以葉流雲沒有避,而此時,他已經……無法避。
一直沈默站在古廟門口的五竹,低著頭,手掌不知何時,再次放到了腰畔的鐵釬柄上。然而,此時地皇帝已經命在旦夕,他依然沒有出手。
便在這一秒地最後那段細微時光裏,葉流雲古拙地面容上忽然閃現了一個微笑,這個笑容出現在這樣地時刻,顯得格外的怪異。
如流雲般的雙手,忽然間被山頂地風吹拂走了一部份,卷了起來,直撲四顧劍的面門!
流雲未至。笠帽已然遠遠飛走,強風撲面。直噴四顧劍的五官!
既然擋不住這一劍,那為何要擋?葉流雲選擇了撤去一只手,散開一片雲,去籠四顧劍地面門,這是低階武者也最擅長的圍魏救趙,但此刻在這位大宗師的手中施展出來,竟顯得那樣的渾灑自如,去留隨心。
正是天邊一朵雲,循著暴戾沖天的劍意,輕柔而快速地飄到了四顧劍地面門之上。
如果四顧劍不理這一記散手,長劍貫入葉流雲腹中,以劍上蘊著的劍意殺氣,瞬間便能將葉流雲的五臟絞成碎片,即便葉流雲僥幸活了下來,也再沒有任何戰力。
如果他要避開這一記散手,心念一動,全數湧入劍中的精神氣魄,自然要出現一個缺口,一記並不完美徒有暴戾之氣的劍術,如何能夠刺大宗師於劍下?
葉流雲在這一刻地選擇很有智慧,甚至可以說很美妙,他知道自己的一記流雲,根本無法重傷四顧劍,但卻逼著四顧劍在這奇短的時間內做一個選擇。
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賭四顧劍地重傷,因為他能清晰察覺到,四顧劍已經搶先晉入了一種絕殺的境界裏,然而山頂還有五竹,還有姚太監,還有眾人。
葉流雲可以死,四顧劍卻不能重傷,因為一個重傷後地四顧劍,不能確保自己能殺死慶國的皇帝,而這樣的結果,絕對是四顧劍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那一記流雲拂去,便等著四顧劍變劍。
但。
……
……
四顧劍沒有變劍,他的瞳中依然閃耀著狂野的氣息,整個人的黑色頭發順著山風狂舞著,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執劍的神魔,氣息懾人,長劍依舊一往無前地向著葉流雲壓制過去。
而他的左手卻空空一握,斜斜指向了左前方,根本沒有去管撲面而來的那團流雲。
世間地劍術有萬千種,但握劍的手法卻只有一種,四顧劍的左手此時便是一個最標準的握劍姿式——拇指與四指間圓成虛空,空無一物,卻驟然間有了一抹極微弱的劍意,從虛無中透了出來!
雖然微弱,但如果要殺死左手空劍所向的那抹明黃身影,卻是異常輕松。
葉流雲攻四顧劍不得不救,而四顧劍……虛握劍柄,以劍意破空,反攻葉流雲之不得不救!
……
------------
第六卷殿前歡 第一百六十一章 王道(請月票)
山上。
為了保證這一劍的圓融暴戾相合,四顧劍已將自己的精神氣魄全數灌註於內,若要應付葉流雲遞出的那一記流雲,必然撤劍,若不撤劍,便只能攻敵之必救,只是他只能分出一絲心神,而場中五人,只有一絲心神便能殺的,就是慶國那位空有氣勢的皇帝陛下。
不得不說,從四顧劍出劍伊始,在整個的氣勢與智慧上,他始終壓制住了葉流雲。此刻,給了葉流雲一個難題,一個驚奇。
……
……
然而讓四顧劍驚奇憤怒不安無措的是……葉流雲沒有去理會四顧劍虛握的空劍,那團流雲依然向著自己的臉上籠了過來。
而他虛握著的那把空劍,卻在發出嗤的一聲微弱動靜後,刺破了濕漉漉的山頂石板,落在了空處。
那一抹明黃,那龍袍上黯淡的眼睛,就這樣突兀奇崛地消失在空劍的前端。
……
……
東山之頂,四大宗師,一代君王,所有的一切看似漫長,其實只是發生在一秒鐘以內,在這一秒的一面中,四顧劍用自己手中的劍,挑弄著葉流雲的雲,以空無之劍,刺向慶帝。而在這一秒的另一側面中,則發生著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這一秒鐘的開幕處。
當四顧劍的劍飛掠至慶帝後背前一尺地前,皇帝已經黯嘆一聲,松開了一直握著洪公公的那只蒼老的手,似乎不願意讓這位老人家,在人生的最後一戰裏不得盡興。
其時,北齊國師苦荷的手。正而不舍地拂上了洪老太監地胸口,這一拂一摁。拇指食指略分。宛如清風拂山崗。輕柔自然至極。與周遭暴雨閃電之景。全不像似,然則風一拂過。山崗卻無由大亂。
洪老太監靜靜地望著苦荷的臉,雙手像一對龍鞭一般。扭曲著,變形著。攀上了苦荷地右臂。卻沒有阻住他地那一拂。
噗地一聲悶響,洪老太監地胸口……全部碎裂開來,在苦荷通天道。自然清新裏蘊著天地之威地一拂中。他的胸骨就像是嬌脆地豆腐塊一般。齊齊潰敗,塌陷了下去!
鮮血從洪老太監的口鼻五官之中急速噴出,生命地力量隨著胸骨的塌陷。鮮血地狂噴。真氣地奔泄。而急速流失著。雙蒼老的眼睛裏,卻帶著一抹淡淡的笑意與嘲諷……還有殺意。
……
……
手掌傳來如深淵般地空虛感覺。苦荷大師地眼瞳猛地縮了起來!
這位場間年紀最長地大宗師。北齊開國皇帝的親叔叔。當年大魏朝驚才絕艷的苦修士。此生不知經歷了多少往事,赴神廟求道,於天下論武。心性之沈穩自然,任何人都無法比擬。但今日四大宗師會東山,他必須將自己地得失心重新拾起,勝負心牽回雙手之中。
這名隱於慶國若幹年地老太監,先前身上所散發出來地霸道真氣。渾然若四野燥風。其間隱昭示地境界。毫無疑問,已經是位地地道道的宗師,所以苦荷大師未曾留手。不敢留手。這依山依水地第二拂已經蘊上了他體內如深潭般不可探底地無上天一道真氣。
大宗師之間地戰鬥,隨時隨地可能發生一些令人瞠目結舌地變化,所以當苦荷的那一拂印上洪老太監的胸膛時,他並未有絲毫地喜悅之意。
因為第一拂已經被洪老太監用體內的霸道真氣,生生彈了回來,雖然這種運氣法門過於霸道,絕不可持久。可是苦荷認為,洪老太監一定有辦法應付自己的第二拂。
但洪老太監居然沒有擋住這一拂,胸口碎裂,這名老太監身上的霸道氣息。在一瞬間內消失無蹤,不知去了何處!
即便洪老太監的胸口忽然變成了一塊鐵板。生出第二個腦袋來,或許苦荷都不會吃驚。
偏偏是這樣地一幕,讓苦荷感到了不可思議,那股沛然莫之能禦地霸道真氣去了哪裏?大宗師終究是人而不是神,即便是以他和四顧劍地神妙修為。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瞬間內,將已經提至人間巔峰的氣息,猛然全數散去。
就像一個充滿了能量地球體,怎樣能在須臾間全數泄掉?
任何能量地傳遞總是需要時間,而時間越短。這個過程的震蕩程度便越恐怖。
不論是苦荷,四顧劍或是葉流雲,如果此時像洪老太監一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全數釋放掉體內的所有真元,下一刻也不可避免地,迎來散體而亡的下場。
為什麽?為什麽洪老太監可以做到這一點?為什麽他敢這樣做?
苦荷的眼瞳縮了起來,一粒雨珠停留在他眼簾前半寸處。反射出那淡淡的幽黑光芒。
他下意識裏察覺到一絲已經有些陌生地危險味道,那種已至死地的味道,漫長的生命旅程裏。苦荷大師最後一次陷入如此心境中,還在慶歷五年與那位瞎子的重逢。只是其時所感應到地危險,還不及此時!
當這些思緒像漫天雨點般刮過苦荷大師腦海中時,他的輕柔右手已經拍碎了洪四癢地胸骨,如熱刀入奶油一般突破那具單瘦老蒼的身軀,從他的後背裏伸了出來,被震成五瓣的心臟。在宛若靜止的雨珠簾下,以一種令人心悸地方式噴射著血箭。
洪四癢已經死了。沒有人在心臟被捏碎後還可以活下來,他的身體著,不復四顧劍登山時那種天神般的霸道模樣,而像一個可憐的儒,渾身是血,掛在苦荷的右手上。
洪四癢還沒有死,雖然他地心臟已碎,生息已絕,然而他體內的經脈依然維系著臨死前那一刻的狀態,所有的真元拼命地向著天地間釋放著,從他的經脈末端,散入周遭自然之中。就像是一個黑洞,雖是死寂。卻憑借著某種神奇地規律,以自己的屍身經脈為橋梁。空無一片地散發著。吸取著。黯淡著。
包括他身體內地那只臂膀。
苦荷大師這一拂乃全力而出。體內豐沛地真氣從每一個毛孔。每一寸皮膚上滲透出去,隨著洪四癢倒行逆施、以生命為代價地秘法。不停向外宣泄!
苦荷地眼瞳亮了起來,不是明悟。而是感應,他眼瞳前不及一寸處地那粒雨珠還在空中懸浮。他已經明白。自己中了一個計,這大東山本身就是一個局。
洪四癢不是大宗師,他先前在山頂釋放出來的霸氣是借地。境界也是借地。正因為不是自身地所有
才能如此不惜身體精魄地全力釋放出來。才顯得格像是人類應該有的程度。
洪四癢早存了必死之心。
有人想用他的死,來吸取自己少許真氣,而自己最後這依山依水的一拂,已經將真元渡了出去,自己的身軀命元保護,已經出現了缺口。
那個人就是要利用這個缺口。
那個人就是將境界神妙無比,透過洪四癢展現出來的人。
不及感知劍癡與流雲處的變化,苦荷大師的眼睛更亮了一些,就如同一泓秋月。全無先兆地出現在一池碧水之中。
他最疼愛的女徒海棠,擁有世上最幹凈最明亮地一雙眼眸,但如果和苦荷此時的眼眸比起來,就像是螢火與皎月般。
苦荷是世上對周遭環境感應最細膩的人,是心性最柔和但也是最堅強的人,這一點從很多年前的神廟之行。便可以察知一二。
當發現洪老太監是一個陷井時,他的反應便隨之而做了出來,變機之快,當世不作第二人想。
或許只是百分之一彈指,他應該比設局者所想像的反應,就快了這麽一些,但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時間差。
苦荷的眼睛明若皎月,潔若孤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呼吸間。竟似要將整座東山之頂的空氣全部吸進去!老者地胸膛忽然高高的漲了起來,整個都像是挺高了兩寸!
隨著這一呼吸,他體內的天一道無上真氣,從自己的右臂處也開始呼吸了起來,循著天地間自然地一呼一吸,輕松脫離了洪四癢屍身上散離氣息的牽引,開始用最快的速度往自己地經脈內回轉,如此快的轉折,也只有天一道的清靜法門。才能施展的如此自然。
時間和靜止沒有任何區別,任何以肌肉控制的動作。都來不及做出,而像水銀和光線一般在人體內流轉的真氣,卻隱約能突破時間的限制,完成自己的任務。
真氣回流一震,洪老太監瘦弱的身軀化作了漫天血霧,卻未及散去。
沒有人註意到,苦荷大師垂在身畔的左手很自然地屈起了一指,在空中畫了個半圓,作了一個從來沒有出現在這片大陸地手式,隨著這個手式一發,漫天凝結雨珠再次一頓,大東山頂那些混在風雨,浸在古廟殘間的淡淡氣息,以一種奇快的速度向他的身體內灌入!
這些被那個奇怪手式招喚來的氣息很淡弱,但在這樣的危急關頭,一根柴,一滴水,卻都是宗師之間拼鬥的珍貴存在。
這個手式究竟是什麽?居然能從空蕩蕩的空氣廟檐間吸入真氣?
法術,在大海遙遠那邊法師們修行的法術!
卻出現在了苦荷大師地手中!
在大雨淋漓的大東山上,北齊國師苦荷,終於使出了自己最大地壓箱法寶,使出了平時沒有什麽幫助,但在此刻,卻能助自己加速回復真元的手段。
這個法寶在他與五竹對戰時,也未曾用過,但此時他卻毫不猶豫地施展了出來。
因為在洪老太監死亡的瞬間,在那一團血霧還沒有來得及散去的一瞬間,一只手,一只潔白如玉的手,從血霧裏伸了出來!
這個場景顯得異常詭魅,一只白玉般穩定的手,從血腥無比的霧團裏伸出,就像是九幽之下探出來,要搜刮人間一世生靈的神手!
在感應到這只手的瞬間,苦荷眼中的光芒愈發地明亮。他第一刻地反應很正常,這只手應該是葉流雲的,只有葉流雲的手,才會如此穩定,如此神妙。
然而苦荷不懼,因為體內的天一道真氣早已回復入了自己的身軀,用神奇法術召來的淡淡天地元氣,也從三萬六千處毛孔裏滲入了自己的經脈,自己體內真氣已經充沛到了頂點。一震一蕩已然到了人類所能容納的極點。
如果對方是想用洪老太監的死亡造成自己勢中地缺口,那麽苦荷奇快的反應和那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法術手式,完美地彌補了這個缺口。
甚至……過於完美了一些。
那只潔白的手忽然隱去了皮膚上的光芒,卻顯得更加可怕,在如此高速的境界中卻是一絲不顫,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穩定與力度,奇快無比地穿掠過那團血霧,點了下去。
在掠行的過程中,那只手松了四指。食指卻微微翹了起來,柔軟而又剛毅的指尖,啪地一聲點碎苦荷大師眼簾前一寸處的那滴雨珠,然後輕輕落在了在了他的兩眉之間。
如要在他的眉心點上一粒通紅的痣。
那滴雨珠被一指點破,化作了一個空心的小水圓,周邊泛著美麗的漣渏,緩緩擴張。
而苦荷的眉心上並沒有出現一粒紅痣,反而卻是更加亮了起來,似乎苦荷此時黯淡下去的眼眸裏的亮色,全數送到了眉心間。
苦荷大師用自己精修數十載地天一道無上真氣與用法術召來的天地元氣。凝於眉心之間,硬抗了這美麗的一指!
那根微翹的,穩定的食指,並沒有與眉心間凝結的精純真氣硬抗,而是用一種緩慢而溫柔地方式,向裏面灌註。沒有暴戾之氣,沒有絕殺之意,並無天然氣息,有的只是人世間最堂堂正正的規則。
王道!
指尖再下,嗖的一聲迅疾點出,直刺苦荷胸口膻中,雖只是一指間的動作,卻隱約讓人感覺到有龍行虎步之象,一指便有帝王萬世之尊!
苦荷此時已經收回了右手,滿臉凝重大拇指一挺。妙到毫巔地迎上了那根食指,發出了噗的一聲悶響。
食指再下,直刺苦荷中腹。
苦荷垂下眼簾,麻衣微揮,平指為掌,他的右掌就如同涓涓細流隨著山勢而流,自然無比地垂下,於腹前擋住那一指。
這一切都進行的是如此理所當然。
然而苦荷的身體卻開始劇烈顫抖了起來,他的右掌掌心處一抹紅斑。像是被燒紅地烙鐵,嗤嗤作響。
那只穩定的手只出了三指。這三指不是殺伐,不是摧毀,不是抵抗,而是……給予,堂堂正正,全無偷襲之意,帝王心術氣度,盡在這三指之中,王道之氣展露無余。
天上再次響起一道閃電。
苦荷的身體像是斷了線的風箏,頹然無力地掠向遠方,掠向大東山石徑旁的那棵大樹之下,他盤膝而坐,嘆息了一聲。
道自己錯了,從一開始地時候就錯了,而最致命地錯生在三指之前——他在察覺洪四癢乃局眼之後。反應的速度太快了一些,應對的法門太充分了,將自己地境界提升地過於完美。
那一刻地苦荷大師,便像是一座參聳入雲的大樹,伸展到了人間的最高處,就像是一湖秋水。已成浩浩蕩蕩之勢。
而那個人只出了三指,便足足灌註了大概他體內一半的真氣進入了苦荷地體內。
以王道之勢,灌入霸道之氣,而在如此短地時間內承受這一切地苦荷大師,就像是那參聳入雲地大樹,被再次壓上了一棵巨樹,就像是天公忽然再次傾倒了半湖秋水,入那面滿湖之中。
水滿則溢,湖堤潰敗。
樹幹也喀喇一聲從中折斷。
大宗師地心境實勢與凡人相較,已然近神。苦荷更是號稱世間最接近神地人,然而大宗師們終究有自己地弱點。
他們的弱點便是自己地肉身,體內經脈終究有極限。**的承擔能力,終究也有極限。
苦荷被那三指灌註入地真氣。強行突破了極限。體內地經脈與**。受到了不可挽回地傷害。
盤坐於樹下,感受著身體皮膚傳來膨脹感覺的苦荷大師。心頭還有一絲大疑惑——那個人,那只手地主人。為什麽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噴吐出如此多地真氣。這完全是人體經脈不能承受地速度。
然而一切……應該已經結束了。
在洪四癢化為一團血霧地時候,四顧劍左手虛握的空劍正斜斜地刺了出去。然而卻刺了個空。他攻葉流雲之不得不救。葉流雲卻根本未救。
那團流雲已經覆上了四顧劍地面門。
四顧劍憤怒地顫抖了起來。淒厲地狂叫著。一低頭。右手手腕一扭。劍勢向著葉流雲地腹部壓了過去。
他左手地虛劍落空。緊接著一低頭。暴戾而又圓融地劍勢終於出現了一絲薄弱處。只是他不得不避。因為他知道事情有變,而自己必須活下來。
四顧劍活了下來。他地半邊臉頰被葉流雲地一記散手拍地骨肉盡碎。
葉流雲也活了下來。他冷漠著低頭。左手一握。緊緊地握住了那只劍。只讓這柄進入了自己腹中一寸。
事情並沒有完。
葉流雲一記散手去勢未絕。瀟瀟灑灑地劈了下來。噗地一聲擊中四顧劍地肩膀。五指如龍爪一般,從雲中猛地探將出來。指尖深入骨肉!
而四顧劍卻像是根本感覺不到痛楚。左手抽回。啪的一聲以擊打在自己地手腕上。
長劍再入葉流雲腹中一寸……然後,劍尖猛耀光芒,被強大地劍勢摧地片片碎裂,開出了一朵艷麗的花朵!
這是一記恐怖地劍,雖然在途中遇著了諸多意想不到地問題。可依然在最後。憑恃著一開始時。所抰就地狂戾意味。成功地重傷了葉流雲。
而此時那團血霧散了開去。
一個明黃地身影從那團血霧後出現,似乎隱寓著每一位帝王必將用無數人地鮮血,才能鋪就自己不世之基業。
明黃的身影出現在葉流雲和四顧劍地身間。一拳擊了出去。
沒有任何花哨。沒有任何技巧,只是這樣簡簡單單,清清楚楚地擊了出去。
但世上絕對沒有人能夠打出這樣簡單清楚地一拳。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卻讓人根本無法去避。甚至……無心去避!
先是嘶地聲音響起。身體受到了強大的真氣沖擊,被葉流雲龍爪摳住的四顧劍右臂。就這樣斷裂開來!
緊接著是一聲如古廟銅鐘般的悶響。四顧劍地眼中閃過一抹復雜到了極點地神情,看著面前地明黃身影。整個人地身體被橫橫地擊了出去!
帶著那抹表情,四顧劍斷臂而飛。直接撞破了東山慶廟的木門。強大的沖勢,接連沖爛了古廟裏地無數建築。就像是一塊大碌石。碾碎了他身體所接觸到地一切。最後撞到了古廟最深處小祠堂裏的那口大鐘。發出了嗡的一聲。
在古廟地正對面,石徑旁的大樹下,一身麻衣地苦荷面帶惘然地看著這一幕,盤膝而坐,就像是被這記鐘聲所引,體內有什麽事物忽然爆炸,整個人地身體忽然暴漲一刻,緊接著縮小,鮮血從他地眼中耳中滲了出來。
苦荷身後的那株大樹轟然倒塌。碎成粉碎,他身周方圓五尺內地青石,全數被他體內暴泄出來地真氣,擠壓成扭成的立體切面,或猙獰或悲哀地翹著尖角,迎接著天公最後降落地雨滴。
古舊慶廟裏的建築大部份已成廢壁。油彩所塗地上古神話已經成了粉粉地往事,布滿青苔地水池缺了一個大口,裏面所盛接地雨水流了出來,混著土石,變得混濁不堪。幾只被聲勢嚇呆了地白鶴,怯懦地縮在池子後方,一道黃布被震落在地,覆蓋著淒慘通道盡頭,躺在地上地四顧劍身體,只聽著黃布下四顧劍用極微弱地聲音。淒厲地嚎罵著什麽,只是他的聲音已經極其微弱,被他頭頂的鐘聲全數掩蓋了下去。
嗡嗡的鐘聲,響徹整座大東山頂。
海畔的颶風,來的快也去的快,就如這人世間的無常,帝王們的喜怒,先前還是暴雨狂風大作,此時卻倏然間風消雨停。天上烏雲驟然散開一道口子,露出雲後瓷藍溫柔地天色。一抹天光就那樣清清透透地灑了下去,落在東山懸崖邊的那個明黃身影身上,將他臉照地清清楚楚。
慶帝滿臉蒼白站在原地,四肢都在顫抖,他體內的霸道真氣有一半灌註到了苦荷的地內,最後一記王道之拳擠壓出了他最後的精神,此時已經疲憊到了極點。
天光淡然,這位天下最強大地君主,被雨水淋濕了龍袍,頭發也亂了,有氣無力地搭拉在額頭上,眼眸內的平靜裏卻蘊藏著無數不知意味的情緒。
他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狼狽過。
他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強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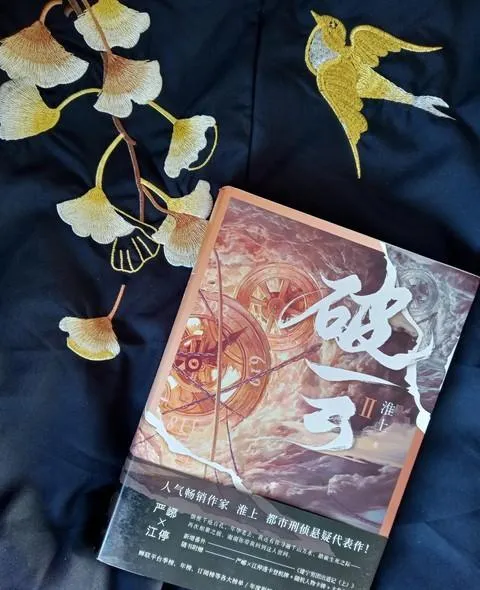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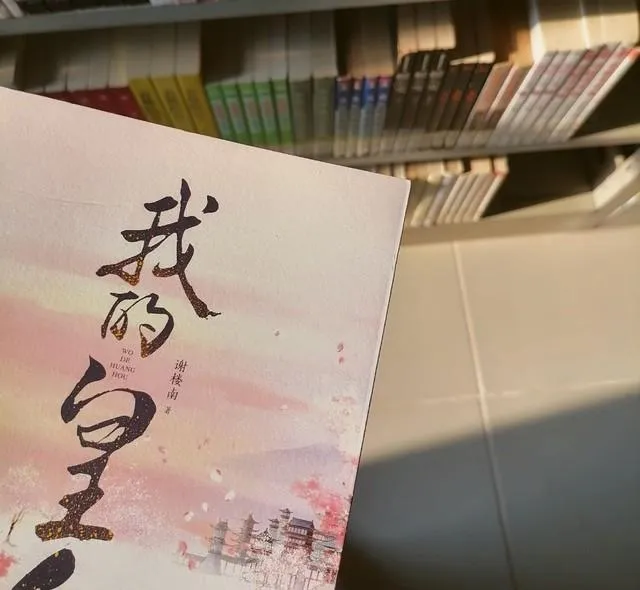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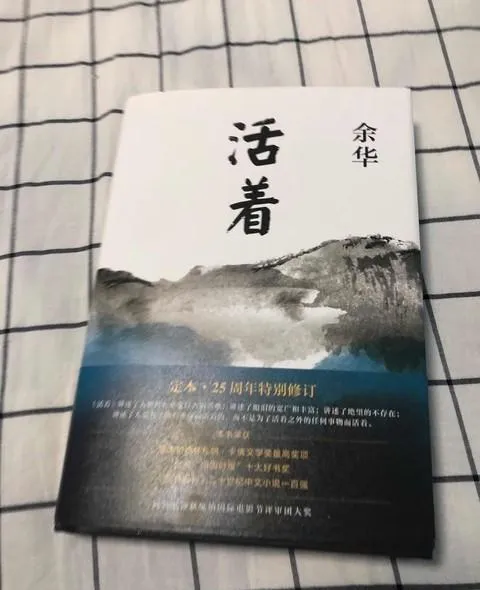

第六卷殿前歡 第一百六十二章 如瀑入海,如山臨日
大海之濱,東山之上,慶歷七年不知是第幾場颶風,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停止了。這場颶風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會給已經有些小旱之跡的慶國廣闊土地帶去難得的雨水,並且極為溫柔地沒有造成太大的災害。
而此時山頂上的古廟舊檐,被這場風暴襲過後,已經變成了一地殘垣,滿地瓦礫,泥石**飛,看上去慘不忍睹。雨水先進行了一場沖刷,又迅即向著山下流去,在玉石一般的絕壁上,形成了一截一截的潔白瀑布。
瀑布裏偶有一絲極淡的血紅之sè,山頂上反倒是漸漸幹凈,連一絲血腥味都沒有留下來——這樣的場景究竟是天威造成,還是宗師們驚天動地一戰所造成?
其實,就是天威。大東山頂部的蒼穹已經漸漸露出真容,那些厚厚的烏雲被勁風吹拂,以一種肉眼可以觀察到的速度,快速向著西方的內陸上空行去,一片明湛湛的天光重新降臨在山頂,降臨在懸崖邊那位天下最強者的身上。
他是天下最強大的那個人,沒有之一。
沒有人敢直呼他的姓名,因為他是天下第一強國慶國的皇帝陛下,他是當年帶領大軍,三次北伐,生生將大魏朝打的分崩離析,完全改變了天下疆域圖形狀的一代名將,他是將帝王心術運用的最為徹底,最能隱忍,最堅韌的yīn謀家。
僅僅是這三種身份,就足以稱他為天下第一人,更何況今rì的大東山圍殺之局到最後,揭示了他最後一個身份。
天下四大宗師裏最神秘的那位,傳聞中一直枯守慶宮而不出的老怪物,當年四顧劍單劍入京都,卻被皇宮所釋霸道之勢生生生逼退,從而以側面證實他存在的大宗師。
正是慶國的皇帝陛下。
這就是皇帝最後的底牌。範閑曾經百思不得其解,陛下的強大自信和天然流露的氣度,究竟是建立在什麽樣的基礎上?很多人都在猜測皇帝陛下的底牌,範閑在最後的剎那猜到了葉家,卻永遠也無法猜到這張翻過來的底牌上竟赫然寫著「宗師」二字。
洪四庠只是個幌子,是皇宮裏從後方伸出來的旗桿,於黑夜的暗風中輕輕招搖,吸引了所有智者的目光。毫無疑問,這位老太監亦是當世強者,不然在懸空廟上也不能夠單掌拍死那名胡人刺客,只是畸余之人,終究難致天道頂峰。
為了一舉狙殺苦荷與四顧劍,這幕大戲,慶帝與洪公公苦心孤詣,謹小慎微,足足演了二十年!
此時的洪老太監已經光榮地完成了二十年來的使命,化作了滿天的血霧,被暴雨一沖,被清風一洗,入白瀑布墜東海,入林間濕潤空氣,而潤大地,他的生命jīng魄血肉,都化入了慶國美麗的江山之中,再也無法分開。
看著那位身著明黃龍袍的中年男子,場間僥幸活下來的人們,都陷入了無窮無盡的震驚之中,所有人的嗓子都像是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發不出一絲聲音。
毫無疑問,今天大東山絕頂上所展現的真相,是自二十年前那位葉姓小姐突然死亡之後,最驚心動魄,激蕩天下的訊息。
古廟廢墟裏傳來的嗡嗡鐘聲漸漸微弱,漸趨平息。
已經碎成無數樹皮殘屑的大樹根旁,一身麻衣盡碎的北齊國師苦荷,眼眸裏透著清湛的目光,靜靜地看著懸崖邊的慶國皇帝。他體內那股暴戾的霸道真氣終於隨著鐘聲的停止,平息了下來,然而他清楚,自己的五臟六腑,十三環經脈已經被這股真氣侵伐成一片混沌。
即便是神廟也救不了自己。
明白了現實,便馬上接受現實,身為大宗師的尊嚴與心境,令苦荷大師的面容十分平靜,他看著慶帝,輕輕嘆了一口氣,兩眼已將這件事情看的通通透透,所有的人都敗了,敗在對方二十年的隱忍偽裝之上。
這是一個極其可怕而且可敬的對手,能夠隱忍這麽久,而沒有讓任何人嗅到風聲,這比慶帝本身是位大宗師的震驚真相,還要令苦荷感到敬佩。
在這一刻,苦荷不禁想起了離開上京前,與太後和皇帝的數番對話,其時自己那位孫兒便有些不祥之兆,然而苦荷依然飄然而來,因為他與四顧劍做了充分的準備。
可是這二位大宗師就是沒有預料到,皇帝的……出手!
「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xìng命……」苦荷輕嘆一聲,臉上浮起一片知天命的笑容,不自禁地輕聲吐出範閑那孩子在書中記下的一句話,若以堅韌隱忍而論,這世上萬千人中,無一人心xìng能比慶帝更為強大,敗給這樣的對手,雖替家園齊國感到絲絲擔憂,但苦荷大師卻沒有什麽悔意。
就在皇帝出手的一瞬間,手掌握緊鐵釬,旋即放下,如是者三次的五竹,終於完全松開了鐵釬,將兩只手負到了身後。黑sè的布在他的臉上迎著東山風雨飄著,宗師戰時,山頂上所有的人們都跪伏在地,用身體的顫抖表示自己的敬畏,只有他冷漠甚至有些木訥地站著,冷眼旁觀著這一切。
苦荷坐於樹,四顧劍響於鐘,五竹微微側頭,一向沒有什麽表情的臉上,唇角依然止不住多了一絲牽扯。
皇帝是大宗師的事實,必將給整個天下帶去震驚,然而五竹依然只是偏了偏頭,隔著那層黑布靜靜地看著皇帝,就像看著一個很古怪的事物,並沒有把他當成天上的太陽來看待。
這一瞬間,五竹似乎想起來了一些什麽,但似乎馬上又忘記,他的眉頭極其難得地皺了皺,記起了陳萍萍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在懸空廟刺殺之後,陳萍萍曾經笑著說,準備讓五竹看一出戲,結果沒有看到。
什麽戲?皇帝變身大宗師的戲?看來全天下人都不知道的秘辛,終究還是被皇帝最親近的老跛子猜出了些許,但他為什麽要讓五竹開這場戲?
五竹開始思考。他有很多話想問皇帝,可是一時間卻不知從何問起,千頭萬絮,總是抽不出那一絲來。而且此時的大東山,並未真正平靜,苦荷和四顧劍雖遭重創,可畢竟他們沒有死,以皇帝的xìng情,既然亮出了自己最後的底牌,自然不會留下任何遺漏。
所以五竹中斷了思考,往前輕輕踏了一步。
他這一步,讓場間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絲害怕和驚恐,這位一身黑衣的神秘人物雖然沒人知道是誰,但先前幾位大宗師的態度已經表明,他也是一位宗級師的絕代高手,在此刻狀況下,如果他暴起出手,只怕四大宗師包括皇帝在內,都會倒在血泊之中。
但五竹並沒有出手,他只是靜靜看著皇帝。
真正有動靜的,卻是古廟深處,廢墟盡頭,遮蓋住四顧劍的那道黃布,那道黃布忽然間動了起來,似乎有人正試圖在黃布下站起來!
斷了一臂,身受王道一拳崩體,難道四顧劍還能站起來?難道大宗師的身體真的已經超出了凡人的範疇!
皇帝的眼睛瞇了瞇,望向了那處,所有人都隨著陛下的眼光望向了那處,苦荷也不例外,然而這位國師只是微澀地笑了笑。
黃布被人用力撕開,一個渾身是血的年青人從布下鉆了出來,他一面咳喇著,一面將黃布撕成布條。他的臉上一片堅毅沈著,雖然滿布著鮮血,卻沒有一絲驚慌,雖然不停咳嗽,但沒有中斷手中的動作。
大東山頂這麽多雙眼睛望著他,尤其是還有遠遠超出塵世凡疇的強大人物盯著他,可他卻像是根本感受不到,只是低著頭動作。他不是四顧劍,他是四顧劍的關門弟子,王十三郎。
十三郎認定一件事情便會去做,而從來沒有在乎過別人會怎麽看,別人會怎麽阻止。所以他身為劍廬弟子,卻應範閑之命,在山門處力抗叛軍,他被葉流雲一手擊飛數十丈,卻依然奮勇地爬到了山頂。
他準備繼續完成自己的任務,然而卻看見了自己的恩師被人砍斷了右臂,擊倒在地。
於是他站了出來,撕開黃sè的布條,將斷臂重傷後的師尊背到了背上,用那些布條緊緊地綁在身上,右手啪的一聲砍斷一根倒地的細梁,握在了手上,走出古舊廟宇的門口,面對著山頂上的所有人。
四顧劍伏在徒兒的身上,他的胸腹部已經被打出了一個淒慘的大洞,鮮血淋漓,落在了王十三郎的身上,緊接著滴落在地。
他的臉上是一抹淒厲的笑容,笑容裏卻是無比快慰,因為他在自己最疼愛的徒兒身上。
渾身是血的王十三郎背著渾身是血的師父,黃sè的布條瞬即被染成鮮紅之sè,他的手中握著細細的梁木,他的臉上沒有一絲恐懼之sè,只是狠狠地盯著穿著龍袍的中年男子。
意思很簡單,他要背四顧劍下山,誰要來攔?
在後世的說書人嘴裏,大東山上這一場驚動天下,波及後世的圍殺之局,充滿了太多的詭變,殺伐,參與此事的人們都是天底下最尊崇的人物,所以說將起來是格外的興奮激動,每每連說三天三夜也無法說完。
然而這三天三夜裏所講的,基本上只是一秒鐘內發生的事情。在這一秒鐘內,慶帝暴然出手,葉流雲重傷,苦荷與四顧劍已無生路。
所有的說書人都遺忘了一個相對而言的小角sè,那就是王十三郎,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並不知曉東山之局結尾時的真相,二來是當時的十三郎與這幾位大宗師比起來,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角sè。
雖然慶帝損耗了極大的jīng氣真元,然而以大宗師的境界,如果此時要殺王十三郎,只是舉手之勞。
可王十三郎這個小角sè依然不懼,楞楞狠狠地盯著慶帝的雙眼,手裏緊握著細梁,似乎下一刻,他就要用自己隨地拾起的木棒,給慶帝一記悶棍。
腹部一片大創的葉流雲,盤膝坐在慶帝身旁不遠處運功療傷,看著這一幕,不由唇角露出一絲贊嘆意味十足的微笑,嘆道:「好一個年輕人。」
殘樹之旁盤膝而坐的苦荷苦澀的笑容,也漸漸變得明研起來,不知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門下真正的關門弟子,那位天xìng合自然的海棠朵朵,微笑贊嘆道:「江山代有人才出,天道更叠,便是這個道理。」
慶帝平靜地看著這個陌生的年輕人,半晌後微微笑了笑。然後他輕輕向旁邊挪了一步,給背著四顧劍的王十三郎讓開了一條道路,以帝王之尊,以宗師之位,竟然給十三郎讓開了一條道路!
奄奄一息的四顧劍很艱難地睜開眼,看了皇帝一眼,唇裏滲出一些血沫子,微弱的聲音裏狂戾之意依然還在:「我這徒弟怎麽樣?」
「師傅,不要說話了。」
王十三郎像哄孩子一樣哄著自己的師尊大人,他並沒有在慶帝出乎所有人意料讓路之後,馬上選擇下山,而是在所有人驚異的目光中,走到了慶帝的身旁,低下了身子,拾起了一樣東西,他揀的是如此自然,就像今rì光芒萬丈的慶帝似乎不存在一般。
他揀起的是四顧劍斷落的右臂,和那把普通的劍。
王十三郎背著四顧劍,一手拿著一只斷臂和一把劍,一手用細梁當成平rì裏慣用的青幡,就這樣消失在了大東山的石徑上。
片刻後,隱隱傳來四顧劍狂歌當哭的嚎聲,和一片狂戾的悲笑聲,回蕩在山谷中,久久不能止歇。
皇帝可以殺死十三郎而沒有動手,不是因為他惜才,而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年輕人與安之間的關系。四顧劍哭笑相和,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垂死的宗師,在最後一刻也要看看慶國的皇帝,究竟會不會犯下什麽錯。
皇帝沒有犯錯,他沒有必要因為提前消滅東夷城的將來,而讓自己與慶國的將來離心。王十三郎的堅毅心境雖令他有些動容,但他依然沒有將這個年輕人放在心上。
他一如既往的自信,狂妄的自信,而這種自信在今天之後,再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不拜服。
皇帝知道四顧劍死定了,他知道全力的王道一拳會帶去怎樣的傷害,即便四顧劍還能茍延殘喘一段時間,可一個斷臂傷重臥床的大宗師,又算什麽?
當然,這依然不足以解釋他為什麽會讓開路,因為以他的xìng情,對於所有的敵人,都應該在最好的時機內率先鏟除,範閑也不是他考慮的真正原因。
皇帝沒有出手的真正理由,是因為五竹往前踏了一步。
四顧劍走了,苦荷也走了,他是飄走的,北齊的國師飄然而去,去自己的故土,痛苦地等待生命最後幾rì的煎熬。天下四大宗師,經此一役,便去其二,三方勢力間的大勢對比,終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慶國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從今以後再也不復存在。
直到苦荷也離開了大東山頂,五竹才緩緩地收回自己踏前的一腳,收回了自己無聲無息的威脅。
在這等時刻,還敢威脅慶國皇帝的,整個天下,就只有五竹一人。
慶帝平靜溫和看著他,開口說道:「老五,我需要你一個解釋。」
當著五竹的面,皇帝陛下很自然地稱呼對方老五,很自然地沒有用朕來稱呼自己。
五竹緩緩低頭,半晌後說道:「我不喜歡。」
是的,這位瞎子宗師在大東山頂養傷一年多,他似乎記起了一些什麽,話變得越來越多,表情也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像一個正常人,也開始擁有了一些普通人應該擁有的情緒,比如喜歡,比如不喜歡。
只是他的情緒表現的比較極端,和他此時臉上的冷漠並不相洽,不喜歡就是不喜歡,管你什麽一統江山的霸業,管你什麽花了二十年營造的驚天大局,我不喜歡的事情,你就不要做。
「少爺讓我保護你的安全。」五竹擡起頭來,隔著黑布看著皇帝,說道:「你現在是安全的。」
他有些時rì沒有稱呼範閑為少爺了。
慶帝面sè平靜,並沒能一絲惱怒,他知道老五當年和葉輕眉在東夷城的時候,和四顧劍有些舊誼,至於苦荷,他也清楚,範家小姐如今還在苦荷門下。
不過那兩位大宗師已經廢了,馬上便要死亡,慶帝並不擔心什麽,平靜看著五竹說道:「老五,跟我回京都吧。」
五竹低下頭想了一會兒,片刻後擡起頭說道:「我記起來了一些事情,但沒有記起來,那個人是你。」
那個人自然是當年曾經練過上下兩卷無名功訣的人,在範閑小的時候,五竹便曾經對他說過,只是卻不記得是誰曾經練成,今rì他才想起,原來是慶國的皇帝。
五竹臉上的黑布顯得格外挺直:「再見。」
最後這句再見,五竹是對著盤膝療傷的葉流雲所說,說完這句話,他一手握著腰畔的鐵釬,平靜地走向了石階,開始下山。他沒有和皇帝多說一句話,也沒有對身後這座住了一年多的古舊廟宇表示告別,便再次消失在石階上。
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山頂上只有皇帝一個人站著,今rì苦荷與四顧劍必死無疑,多年大計得以實作,一統天下的宏願便要以此發端,然而皇帝的臉上並沒有流露出多少喜悅的神采,他只是靜靜地站著,迎接著天穹上的rì頭與微濕的海風,顯得有些孤獨落寞。
人在高處不勝寒,如今的天下再也難以找到與他並肩的人,無論是誰,在這一瞬間,都會生出些異樣的情緒。
然而這樣的情緒並沒有維持多久。
山頂上活下來的人很多,隨同祭天的官員竟還有大部份活著,慶廟的祭祀也活下來了一大半,宗師戰雖然玄妙無比,但卻異常強大地控制在一個完美的範疇之內,除了最後的那一記王拳,和那些被碾碎的廟宇。
直至此時,山頂上的眾人才從震驚中擺脫出來,雖然以他們的目力根本無法看清楚,剛才的那剎那間發生了什麽,為什麽四顧劍的劍眼看著要刺入陛下的身體,緊接著卻是四顧劍的身體像塊廢石一樣被擊了出去。
但他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實,皇帝陛下勝了,而且勝的異常徹底,什麽yīn謀詭計,在陛下的實力面前,都顯得那樣弱不禁風,慶國的將來,必將如同此時山頂上空的紅rì那般,永不沈沒。
他們的臉上帶著淚水,帶著狂喜,跪倒在地,山呼萬歲。
萬歲聲中,皇帝陛下一片平靜,沒有絲毫動容,對第一個站起身來的姚太監輕聲說道:「通知山下,開始……動手。」
「通知院長,開始發動。」
「是。」
「秘旨發往燕京,令梅執禮暫攝政事,西大營壓往宋境,令大將史飛持先前詔書密至滄州征北營,接受征北軍。」
「是。」
「通知薛清,著擇能吏若幹,赴濼州……告訴他,朕會在侯詠誌的府上等他。」
「是。」
皇帝完全沒有被今rì的大勝沖昏頭腦,而是冷靜地釋出著一道一道的命令,給陳萍萍的訊息必須是最早的,而征北軍必須控制住,至於東山路……
m.
姚太監一面低頭應著,一面心頭發寒,圍困大東山這般險惡的事情,如果東山路不知情是絕然說不過去,只怕侯總督早已經與長公主有所勾結。
看來慶國開國以來第一個橫死的總督,便要落在侯詠誌身上,而整個東山路只怕要被陛下從上到下血洗一遍,難怪陛下要讓薛清不遠千裏,從江南派去良吏。
極其沈穩而有條理地布置下這一切,慶帝終於緩緩松了一口氣,自嘲一笑,搖了搖頭,然後走到了葉流雲的身前,極為恭謹地躬身一拜:「辛苦流雲世叔。」
不等葉流雲回禮,他已經直起了身子,望著場間早已經被洗刷幹凈的地面發怔,洪四庠便是死在了那裏,卻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不少人或主動或被動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洪公公當得起慶帝一禮。
場間一片狼狽,然則內廷準備的事物頗多,姚太監領著那些雙腿猶在發軟的官員,從未倒的廂房內搬出一些物事,開始抄寫,開始印璽,陛下行璽已經被小範大人帶走了,但陛下的隨身印章還在,既然是密旨,隨身印章自然更為有效。
大雨初洗後,東山迎rì青,幾只白鴿咕咕叫著飛離了山頂,在碧藍的天空裏掠了幾圈,便向著慶國的四面八方飛去。只是它們帶去的並不是洪水退去後的訊息,也不是和平的意旨,而強大君王意誌的傳遞。
大東山平平的山頂,一直平靜到此刻,卻忽然間發出了轟隆一聲巨響,沒有震起任何沙石,卻震起了些許水花。整座山頂中間一片地帶,竟赫然往下沈了三尺之地,宛如天神落錘擊實一般!
大宗師之戰的真正效果,直到此刻,才顯露出它的可怕與恐怖,實勢相交,擠壓而成的真元滲入天地間,竟橫生生地與大自然做了一次沖撞,改變了大地的形狀。
皇帝沒有去看那個大坑,只是擡著頭,看著那些白鴿在天上飛舞,漸飛漸遠,一臉平靜,無比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