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個村,名字叫做呂公堂。相傳是呂洞賓曾來過,後人修建廟堂,來往者祭拜,得名。
曾聽說有個孩子坐在廟裏的鐵牛像上,坐上去,下不來,老人來給燒了把紙錢,才好。
自小年,迎來竈王爺爺,吃餃子,年來了。接著,做年豆腐,蒸餑餑,年豬肉,三道功夫活。我家老媽打下手,老爸做事細象,手藝漂亮,是主要負責人。
年二十九,爸媽煮肉,我再回村裏。今年他們做了四大鍋,全誠為了讓我和老姐吃夠。老爸還特地學了個大腸包小腸,耐嚼,香嘞。下午,媽媽請仙客,在炕上擺好桌子,九道菜,要有魚有豆腐,有香煙,有酒,然後說道些什麽。大致是祈求來年連年有余,風調雨順,平平安安。

今年是大進年,年三十上午去祭祖。挎著垸子筐,裏面五個餑餑,四盤菜,三道紙,兩份水果,一瓶老酒。以前,還讓帶上幾支鞭炮禮炮,現在管得嚴,入口處派人看守,不讓放了。
大伯說,已經連續幾年小進年了,今年是大進年。
立春時,下了一場大雪。陵園墓地裏的泥土路混著雪水,比冰堅硬。我們順著攀上去,路邊地裏長著麥苗,上面鋪著雪,老爸說今年這好,麥子長得好了。大伯說,年五更不下雪就行。我問得知,年五更下雪,來年地旱。
爬上坡,找到碑,壓好墳頭紙。從同治年間第十世老祖,從右往左,十一世、十二世、十三十四十五世,再散葉,一代代生枝,成家成族。
到了我爺爺奶奶那兒,老爸明顯變得柔軟,給我介紹啊,然後自己悄摸地對著說話,給爺爺奶奶喝酒,給奶奶點上顆煙,最後叫我跪拜。記得爺爺去世時挺年輕,很突然,我小,長大我聽我姐描述,老爸那時候整夜睡不著,眼睛裏布滿血絲,通紅。
整個山上生滿了側柏,我站那兒,望天的視野唯獨留了個空處,燒紙熄滅後升起了煙,我一擡頭,剛好看到了旺盛的太陽,陽光穿過,吵鬧之間,肅穆安靜,我鼻子一酸。
路上也有女性,這裏沒有那麽嚴格的男女區異,只要帶著思念。
回家,貼對子(對聯)。我要先去姥姥家貼,這是我和小姨家表弟的習慣。今年姥姥姥爺還沒來得及熬仗子(面黏糊),去了我給現弄,很快就好,我也貼好,貼正當。和表弟同他們說會話,後天再來,別牽掛。
年三十中午,吃大米幹飯。老媽用大鍋做了笨雞燉粘窩子(牛肝菌),肥腸豬肉粉條。伴著昨天熏好的豬肉,昨晚做好的肉凍、賀菜(胡蘿蔔絲)和香椿。姐夫他們家沒有這習慣,老姐姐夫小外甥一並來吃。吃得很香。
吃罷,姐夫老姐他們一起收拾好碗筷,我偷懶帶著小外甥玩,老媽老姐在沙發上聊天。她告訴我姐,一年裏面最好的日子一定是年三十晚上,沒有比這時候更好的時候了,叮囑他們發動一下汽車,說一些祈福的話。
三十下午,收拾家裏,然後躺著,直直腰。休息好,給客廳茶幾、廚房竈桌、院子裏的台子擺好魚餑餑、花餑餑或錢袋,眾多水果,還有大三元筷子三酒碗,一座香爐。客廳還要更豐富,有些熟食,會一直續燃蠟燭。
將近八點,全家出動,炒菜上肴喝酒。十二點,最愛的菠菜豆腐素餡餃子上桌,帶著面制的「錢串子」(類似面條),包著錢幣,另配有紅燒黃花魚與煎豆腐。拜年,收第一份爸媽的壓歲錢。夜裏,從大門到裏屋,各個門口放上攔門棍,我去天井院子裏踩芝麻稈,應著早以來那句謠話「踩芝麻稈,當大官」。
朋友問我為什麽吃菠菜豆腐餡,我問媽媽。她說,要論起來,菠菜是一種蔬菜,然後各自寓意(豆腐:都福;菠菜:有菜——有財);還有說道就是過年年五更守歲,不吃肉類,吃素,同菩薩同佛一樣,吃素,不傷「歲」(動物)。朋友回復到,講究。三十往後,新年伊始,就是我小家習慣。初四基本歇下,上山,拾柴(拾「財」)之余,並呼吸新鮮空氣,健康身體。老爸開車,路上沿途村莊,會一路介紹。有些名字起的好,福祿並,滿堂峪,光明村。

民間是一個實踐的概念。民間故事經由傳與說,不停地完善,民間故事是最偉大的文學母本。
初一到初四,是我在村裏和小學同學、親戚朋友聚會的時刻。大家講話,從前往現在,各村子,各個人,說在了「命」上。
痛事。癌癥大致是農村裏來勢最兇最快的病。癌癥,誰也無法抵抗,把人身體煉幹,並把人硬生生地疼死。在以前,村子裏將這種病隱晦地稱為「不好的病」。現在普遍了,直言說癌。具體到什麽癌。
今年,又聽到這樣的事。一位老人活到了八十歲,一輩子健康,突然吆喝身體疼,去醫院一查,肺癌,晚期,已經擴散到淋巴。整個人以極快地速度從能站著、勉強站著,躺著,再到爬不起來。聽說兒媳婦照顧,婆婆偶爾嘩嘩地流淚,是在說著抱歉。
還有一對兄弟,都七十多歲,一位一輩子從醫高明,一位一輩子種地辛苦,同一年得癌,並隨著同一年死去。成家立業後,他們的交集不多,上天卻安排地如此默契。
不止老人,還有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一位母親,肝癌,走後,結婚的女兒被婆家認作怕有「遺傳」,「擡不起頭」。還留下一兒子,丈夫帶大。
除了癌癥,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病。折騰著錢。
一壯男力,父親早走,只剩母親。成家立業,有了一對孩子。就突然地腎不好。家人借錢,十幾萬。他的母親為他捐腎,楞是說哪怕我疼死了,我也不能讓我兒子一家就這麽敗了。好在成功,老人和這男人身體都挺好,可以幹活掙錢。還完債,孩子也健康地長大,一家很好。
也有相似的故事,父母沒有為孩子捐腎,男人身體慢慢地塌了,兩天一做透析,他的妻子從相伴到不伴,帶著孩子在另個屋子裏住。公婆管著這個男人。人們做出理解,天長日久得,誰能熬住呢?誰又有資格說這是必須去做的呢?該當的命運。還有人說他們剛結婚沒多久,丈人車禍離去,這個媳婦和這個地沖著,命裏壓不住福,不該來啊。

玄事。說起來怪,玄,很多地方都和不同的人沖著。史家莊的去不了姓「朱」的;朱家莊去不了姓「史」的;郭村店子發不了姓「鄭」的。還有姓「解」的去不了大婁村,聽傳當時孫臏把這兒給封住了,沒有下地水,都從面上流,換到河西村,就好很多,「解」(蟹子)找到水,奮生。還有村子都有著自己的謠傳,柳樹溝出「瘋漢」,小管莊吹嗩吶,但流傳被人坑害,給地主家的狗出殯去吹,沒有人再用了。
我問咱村呢,我媽說咱們村這都發,以前是廟,來來往往。
還有些人家沖路,家裏不旺,各種出事。是風水,找人破。這些人有些會算,有些人會看事,有人有「陰陽眼」,能通著。我問為什麽,他們說天定。但這些人一定不會算的全準,時準時不準,話也是七八分數,否則,這是傷天理。
還有事關墳地(林地)的故事,有位老人去世,放骨灰盒時,有同族別家兄弟偷偷在棺材裏放了一個秤砣,那幾兄弟緊接著靠販菜賣菜發了家,在那時候一大車薯仔掙一兩千塊錢。但是後來,沒幾年也就敗落了。
還聽他們說很久以前,村子裏有道士,每到過年都用符,老鼠都來進盆裏,他灑糧食給它們,說道著過年了。道士都是半夜行事,雞鳴回家,不看回頭路。還有個厲害的道士被請去不知道做了個什麽事,再也不做,很快也逝去。
這些民間故事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歷代傳說。聽聽就好。
人事。說回現在,姥爺今年八十歲,知道村子還有九百多口人,四百多戶人家。四大間平房再怎麽好也不惹人喜歡了,人人都奔計住樓。
村子裏以前周圍是田地,現在全是工廠。村前的「場」早已經全是挺拔的楊樹,等著被占,等著賠錢。大地永遠都在奉獻。
和小學同學們每年見一面,現在,他們有些已經工作,太大的壓力,太多嘆氣聲。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大都是沈默。我們只好回說著以前,那片「場」,我們跳樹樁,我們在土地上奔跑,沒管轄。接著有網,各種遊戲豐富我們跑在田野,走上學路上的玩法。
工廠成為人們的生活,村子裏除了極少數老人留戀大地,沒人想去種地。但工廠也累,男人一天兩百左右,女人一天一百二十左右,算是不錯。以前的爭在田間地頭,現在爭在工廠。為了錢,為了活輕快,人性的「壞」極具在此。我還聽說一些,同村的落戶的人將同村的孩子在那年冬天撞死,賠不起錢,坐牢。同村的人給同廠子裏的人下藥,賠不起錢,坐牢。這個世間總是濃郁著一些傷感,中和著希望的美麗。凝成一個民間常說的字,就是「命」。

之前老師發過一首詩,開頭:
以前我在農村,
和村裏人格格不入。
後來我在城市,
和城裏人格格不入。
孤獨像烏鴉的雙翅,
不離左右,統籌兼顧。
我評論:為什麽,我總是體悟到,我既是農村人,又是城市人,格格都入,是假象還是真相?
老師說,你是百搭,我是白搭。各順其不自然。
現在我想,這不是假象與真相之爭,這是喜怒哀樂,這是我生長在農村、所擁有的天然的情感。
這是一個個風俗習慣,經歷了眾多的手;這是一個個村子裏的故事,經歷了眾多的口。
每個人都是最後一代。大致去年,我深刻地意識到,我是周圍同齡人知道這些的「最後一代」。隨後,我便有意識地聽他們說,而這說的,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今年,能去往拜年的人家越來越少,拜年越來越簡單,老人也越來越少。
在廣袤的大地,大地苦得真實,讓人生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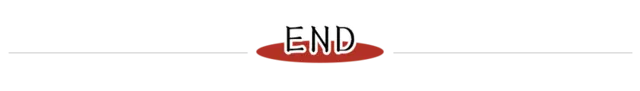
張濤
壹點號一食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