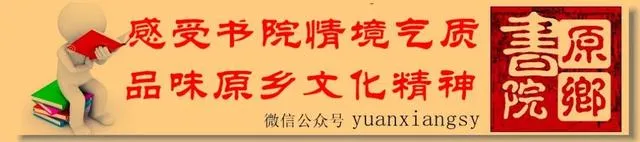
陪 同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作 徐德宽译
我想他看到我走过来了,可不知何故,就是不露声色。我站在打开的汽车后门旁,等着他抬起头。他折起报纸,钻出车门,瞥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憎恶。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惊讶得浑身直抖,身体仿佛都被掏空了。或许这并非憎恶,只是烦躁而已——根源在于对逃不掉的无聊存在有着躲不开的挫败感——只是不满而已。可就是感觉像憎恶。他微微翘起下巴,请我说明来意。我说出那家旅馆的名字,他点了点头,仿佛这不是太过分的要求,仿佛他之前以为我会说出一个不可能的去处。我不惧这头巨兽,在汽车前排挨着他坐下,目的是让他明白我并不像他最初认为的那样,活该遭人憎恶,但这也算是承认了我的外表似乎有惹怒他的潜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对他的愤怒视而不见。
汽车座椅笨重坚硬(而且是绿色的),塑料垫子已有些年头,裂痕随处可见。汽车突然转弯,冲出了出租车站,座椅锋利的棱角像生牛皮一样卷起,穿透了我的衬衫,刺得我皮肉生疼。汽车仪表盘上尽是窟窿和缠绕的电线,里面原先可能有打火器、收音机或者杂物箱。这些窟窿也不能说是空无一物:小纸卷塞满各个角落,从一个窟窿里垂下一块用得灰不溜秋的抹布,等着晾干。
我们在午高峰的车流中缓缓前行,他瞥了瞥我双腿夹着的公文包,然后抬起眼,盯着我的脸,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从哪儿来?」他问道,调节着自己的声音,使提问不那么唐突,但仍然试图让人听着像是在厌恶地咆哮。不管怎样,他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好像期待我会尊重他提这个问题的权利。「Unatoka wapi?」 【斯瓦希里语「从哪儿来?」的意思。】 他又猛然加速,身体后仰,把翘起的胳膊肘支在车窗上。他身形清瘦,肌肉紧绷,双腮凹陷,满脸不屑的期待。至少我在仔细琢磨他的问题时是这么认为的。那张肌肉灵活的脸上有种阴森而痛苦的神色,我不由觉得这是过着危险生活的人,有可能故意施虐,以减轻自身的痛苦。我对自己的好奇心感到恐惧和厌恶,希望旅程尽快结束。我应该一看到他的怨愤脸就立马走开。他又瞟了一眼公文包,脸上掠过一丝嘲弄的微笑,似乎在暗示我太自以为是。这只不过是一件便宜的塑料制品,提手硬而粗糙,拉链歪七扭八,我估计也就能挺上三五个月,不值得如此苛刻地审视。
「从哪儿来?」他问道,这一次,他冲那公文包点点头,表示他注意到了那东西。
「尤因格雷扎」 【斯瓦希里语「英国」的说法】 。我答道。英国。我心不在焉地小声搪塞他,以表明我对这场谈话没有兴趣。
他也轻轻哼了一声。「学生?」
很多人本想出门做大事,临了却只带回诸多故事和一个廉价的公文包;他的意思是问,我是否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有些人虽然干着令人羞耻的下贱工作,却频频传回自己如何好学上进、左右逢源(遇上好形势注定能发一笔小财)的神奇传说。我是否也是这样的窝囊废?他满脸愉快的坏笑,等着看我会如何羞愧难当地回答。他开口说这些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听到他说,其他人都跑光了,自己必须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家人,师长们在他年轻的时候曾对他给予厚望,可他也就只能这样了。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老师,他又轻蔑地哼了一声,这一次毫不掩饰。就这些?
午高峰时,人群总是行色匆匆,汽车只要稍有犹豫,他们就横穿马路,犹如不息的川流。
眼前这位出租车司机俨然受到这些放肆家伙的冒犯,每当前面的车礼让行人,他就狂按喇叭。
一群十几岁的印度小学生在汽车之间闲庭信步,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惹得他长长地按了一声喇叭,嘴里骂骂咧咧的。
「肮脏的屎刮刀。
他们在搞什么把戏?
」靠近邮局时,交通最为拥堵。
成群结队的人在人行道上走,一些身穿衬衫、打着领带的人急三火四,而另一些人则慢慢悠悠,时不时停下来看看地摊上的劣质商品。
「尤因格雷扎。」他一边哼哼着,一边左转拐向码头——我住的酒店就在那儿。「尤因格雷扎,」他重复道,「奢华之地。」
「你去过那儿?」我问道,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带着惊疑。你?为了抵制那厚颜无耻、自我陶醉的文化,我可是拼尽了全身气力,才能小有进展,可是这家伙谈起那个糟糕的地方竟会如此漫不经心。奢华之地。
出租车司机野蛮地按着喇叭,要叫挡在前面的一辆水罐车让路。他按了有一分钟左右的喇叭,似乎被水贩子的冒犯彻底激怒,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在车窗外挥舞着右臂,仿佛随时都会跳下车,掀翻水罐车。码头工人在路边的小亭里买午餐,他们也是水贩子的顾客,此时兴高采烈地朝出租车司机挥手。他开着车绕过水罐车,然后又长按了一下喇叭。
「你在英国有亲戚吗?」我问道。我无法想象,一个脾气这么坏的人,开着一辆快要报废的出租车(我们正坐在里头)谋生,怎么能够挣到钱,在那奢华之地的一张臭烘烘的床上睡上一晚,吃上一顿早餐。
「我以前在那儿住过。」他猛速转过身来,看着我,咧嘴一笑。我们现在已经下了大路,到了码头仓库和停泊机车的场地后面,在酒店前的最后一段路上迂回行进。路面上一会儿是峡谷般的坑洞,一会儿是陡峭的铁道线的路基——在这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他不得不集中精力。他刚开口讲话,但路面上的危机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他摇摇头,不想中断自己的故事。在这儿开旅馆本来就是疯狂至极,院子另一边又到处都是废弃的机器和工人丢弃的垃圾,但在码头和铁路变成肆意蔓延的废墟之前,在马路荒废之前,旅馆就已经在那里了。

「我有过一个马来亚女人,那是欧罗巴人种的妓女。她带我去过英国,还有法国,甚至澳大利亚。我们哪儿都去。都是她出钱。要是有人讲这样的故事,你会觉得他们肯定在说谎,幻想着卖身给有钱无脑的欧罗巴妓女。在遇到这个马来亚女人之前,我也这样想。」说话间他已把车停在了旅馆外面,挂在空挡上,车子抖个不停。「斯利姆。她以前叫我斯利姆,」他一边收钱一边说着,脸上洋溢着沉浸在回忆中的微笑,「其实我叫萨利姆。我一直都在邮局旁边的出租车站。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
我找到这家旅馆纯属偶然。移民局官员对我解释说,我必须在申请表上明确写上目的地国家的地址,否则不能发给我签证。他说这话时带着歉意,因为先前他看过我护照上的出生地后,不禁热情地说起桑给巴尔,还说他也有亲戚住那儿。他给我看一张写着旅馆名字的单子。「随便选一个,」他说,「你不必真在那儿住。填表而已。」 【原文为斜体英文,作者很可能想暗示移民局官员在用斯瓦希里语与「我」交谈。】 于是我就随便挑了一个。当我在机场外找到一辆出租车时,唯一记得的就是这家旅馆。这旅馆很难找,停泊机车的场地和仓库在工作时间之外静得吓人,这些都正合我意,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来拜访我,要是我住在城市另一边那带有赌场和游泳池套间的华丽宫殿里,也许就会有人来打扰。
可第二天晚上,总台打电话告诉我有人来访,这让我吃惊非小。来人正是萨利姆。我从未料到他会来,可这会儿他就在我面前,让人觉得我一直都知道他会出现。他上身穿了一件绿色丝质短袖衬衫,图案是白色花朵和配有舷外支架的蓝色独木舟,胸前口袋里露出太阳镜的一条腿。一件宽松的灯芯绒牛仔裤绕在腰上,系着一条宽大的带扣皮带,裤腰在皮带下折了好几层。他坚持要请我喝一杯,要请酒保喝一杯。大堂酒吧里空空荡荡,除了正在招待朋友的一对比利时夫妇(这家旅馆的老板)之外,再也没有别人。「Ces gens sont impossible.」 【法语,意思是:「这帮家伙真是无药可救。」】 女客人恼怒地说。在她提高的嗓门里有着不受外界影响的自信。这帮家伙真是无药可救。这个女人四十多岁,身材苗条,穿戴整洁,打扮时尚而又不失庄雅。萨利姆瞥了一眼那三个欧洲人,好像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可人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她给我买的这些,我的马来亚女人。」萨利姆说,小心翼翼地扯了扯自己闪亮的衬衫,然后又使劲捏了捏蓝色灯芯绒牛仔裤。他微笑着——这一次没有讥嘲的意味——毫不介意酒保也加入进来。「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上我的吗?」他等着,直到我和酒保都点点头,「那好,我告诉你们。她那天在北海岸塔姆碧丽酒店外等车。知道那儿吧?我看见她站在入口附近的一棵树下,好像在等什么人。通常都是酒店服务员把我们领到车道上后,客人才会从店里出来。你们见到过他们怎么打扮那些狒狒 【指酒店服务员】 吗?他们将那些狒狒从山上带下来,给他们围上黄围裙,扎上黑领结,然后管他们要服装费。这些我都知道。」酒保穿着白衬衫,打着黑领结,腰上围着黄围裙——他可能也得为自己的服装买单,但他尽量装作若无其事。
「不管怎样,」萨利姆继续说,「我猜她在那里等人来接她,可我想,不管咋样,我该试试。她不年轻,也还没那么老。她听我说了一会儿……呃……我照例跟她聊到在政府关税处的游览经历,于是,她上了我的车。我整天载着她到处逛,远的地方到过马林迪、怀塔姆、塔卡温古 【马林迪、怀塔姆、塔卡温古三处皆为肯尼亚地名】 。每到一地,我就跟她介绍当地的情况。要是我高兴,或是她问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就顺口胡诌一番。傍晚时分,我开车送她回宾馆,经过海滩时,她让我把车停下来,我们就在那里做那事。在户外的沙滩上,像两条狗。每天都这样。我早上去接她,拉着她到处逛,给她讲故事,天黑后带她去海滩。几天后,她告诉我她要带我一起去乌拉亚 【斯瓦希里语「欧洲」的说法】 。她把一切都弄好了。机票,护照。钱都是她来出。」


「你在海滩上肯定十分了得。」我很不情愿地没话找话说,因为我不相信任何女人,随随便便勾搭一下,就会看上萨利姆,而且看不到其中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再听到疯狂的欧洲人渴求非洲大鸡巴的故事了。酒保无声地笑了,萨利姆看看我,又看看他,似乎有点小受伤。
「叫我斯利姆吧,」他说着喝掉了杯中酒,轻轻地把杯子朝我推过来,「要是从外币换算成本币,也没多少钱。你知道的。不管怎样,她很有钱。」
我付了他的酒钱,坐着听他继续讲他的马来亚女人的故事。那女的离了婚,拿了自己的那份钱,决定到处旅游。她带他去了利物浦,她在那儿出生,还是婴儿的时候,父母就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对他来说困难吗?和她在一起?他耸耸肩。她负责一切,带他看各种东西;那母狗每天都要做爱,有时一天两三次。这并不难。他们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他交了两个住在附近的朋友,都是穆斯林,一个是索马里人,另一个是毛里求斯人。他们教他如何领取失业救济金。他和马来亚女人过着奢华的生活。英国政府是个大蠢蛋。利物浦到处都是黑人,粗野的混蛋,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政府就只管给他们钱。英国女人们总是爱抚摸他,摆弄他的头发,往他身上挤,给他买酒喝。过了几分钟,我跟他说再见,起身离开了。我有几封信要写,我说。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换了另一件花衬衫。我之前告诉过总台,说我不在,可也许接待员受制于我不能理解的情义,没有帮我的忙。我本想在走过总台时扭头留下句话,可此时值班的是另一个年轻人。「这是在澳大利亚买的,」萨利姆扯着他的衬衫说,「我们在法国待了几天后就去了那里。贝蒂。她的名字叫贝蒂。教名叫贝瑟尼,但她自称贝蒂。明晚你想去夜店吗?你还要在这里待一晚上,对吧?马坚戈 【肯尼亚地名】 那边有个好地方。不像这里,尽是些旅游垃圾。我们明天去那儿。澳大利亚女人总想要那个,可她们的男人性欲 【原文为nyege,斯瓦希里语】 不足。所以,那帮女人总是热情似火。炽热地燃烧。马来亚女人并不介意我和她们搞在一起。」他还讲了很多细节:女人们为了搞到他先是各种精心设计,而后便是不知羞耻恣意淫乐。
「你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呢?」我最后问道,强行要把故事拉到结尾处。
「总得有停下来的那一天,不能老玩儿,」他轻蔑地说,「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在其他任何地方,你终究不过是个小丑。」
这似乎是说再见的好时机,可萨利姆不让我走,显得非常严肃。他一边抓着我的手腕,紧紧攥住不放,一边又点了一轮喝的,记在我的账上。酒保上了酒水,让我签了账单,退了下去,目光小心地避开萨利姆抓住我手腕的手。酒吧里没有别人了。酒水一放到我们面前,他就笑着放开了我,在他抓着我手腕的地方,留下了一圈淡红色的肉痕。我起身离开,看到他想说点啥,却又改变了主意。「你的酒怎么办?没关系,我喝了。那我们明天见。」他说,「你没忘记那个夜店,对吧?」
一整天,我都竭力不去想要是他再出现,我该怎么办。这一天我专门用来充实前一周积累的一些参观和采访笔记。萨利姆的造访临近了,这会儿做这些事再糟糕不过了。充实笔记既非善行,也无痛苦,既不能转移注意力,也不能令人精神振奋,只是意味着疲惫地追溯那些影响已经消退的陈年旧事。傍晚来临时,我已经说服自己,我如此小心谨慎,真是愚不可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位鲜为人知的诗人潘杜·卡西姆的情况,世纪之交时他住在这里,我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信息,而马坚戈那边的夜店则与此毫无关系。可去一趟又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还可能有点帮助。之前并没有寻访到任何关于潘杜·卡西姆的有趣信息;而去一趟萨利姆经常光顾的夜店说不定会带来意外的收获。去这样的地方绝非我愿,再说要了解这座城市,也并不一定非得看清它油腻的下半身,可除了让我感到恶心之外,去看一下倒也并无大碍。我并不期待走进萨利姆的朋友圈,因为我料到他们和萨利姆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在返回英国之前,我就只剩下不到两天时间了。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找上我。笔记可以留待以后再去整理。我可能不得不花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去听那些用床上功夫征服极易上当的女人的乏味故事,可这难道不比竭力赶走萨利姆,成为他怨恨和气愤的对象要好吗?
所以,萨利姆到达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甚至认为他可能不会出现了,作为我怀疑他的故事的惩罚。我下来的时候,他正闷闷不乐地坐在车里。咕哝了一句问候语,他就开车上路了。这种神奇的问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打了个寒颤。为什么不干脆叫他走开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没有注意我们要去往何处,尽管我很清楚我们身在何处。我想刚才肯定走神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萨利姆已经离开了大路,在一条崎岖不平、没有灯光的小道上行驶。灌木林从四周向我们压来。车灯的水平光线使这种感觉更显压抑,就好像在地底下一样。这本该是一个微风习习、心旷神怡的夜晚,可在这隧道里,空气潮潮的,弥漫着湿泥土的味道。萨利姆扭头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咧开嘴笑了。「就快到了。」他说着哼唱起来。一条狗在夜里尖叫,不一会儿,汽车穿过的动静搅得黑暗的灌木丛枝叶乱动。又过了一会儿,萨利姆开足马力越过一个小土堆,进入一片被漆黑的大树包围的空地。已经有一辆车停在其中一栋房子前。肯定还有三四栋房子,只是光线太暗,很难看清楚。他把车停在那辆车旁边,我们下了车。
夜店原来是一座用板条和泥巴盖成的房子的前厅,挂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有两个人早来了,看见我们,就站起来打招呼,显然是在等我们。「这是从尤因格雷扎来的贵客。」萨利姆笑着说。
其中一名男子和萨利姆年龄相仿,有着犹如毁容一般的相似长相。另一个更年轻,块头更大,他瞥了我一眼,嘴角不自觉地飘过一抹得意的笑。他叫马吉德。一开始我没听清那个年纪更大些的男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叫布达。)还没等我们在那张粗糙的旧桌子前坐好,马吉德就大声喊着要啤酒。从里屋走出来一个中年模样的妇女,穿着一条磨破的紧身裙,腋下被汗液染成了黑色。她头上裹着和衣服同样材质的头巾,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肯加。她强颜欢笑,和这些家伙胡乱打趣了一会儿,又走开了,去准备我这些快乐同伴点的饭菜。
桌上放着空啤酒瓶,这些瓶子将作为饮酒壮举的勋章放在那里。马吉德和那名男子每人拿着半瓶啤酒,时不时喝两口;喝的时候,往往把冒着啤酒沫的瓶子往嘴里倒,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这些瓶子真大。屋里看不见杯子。那天萨利姆说要去夜店,我当时想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帮男人聚在树林中的黑房子里偷偷喝酒。
「还会再上一些的。」布达以劝人放心喝的口吻说道。他的表情复杂,一半是勉强抑制的愠怒,一半是与愁闷相伴的怨恨,这表情我之前在萨利姆脸上看到过。也许是因为喝了酒。在这样一个穆斯林小镇上,一个人对成为酒鬼这类问题,必须慎重,甚至要时刻念念不忘,毕竟在这里,谨慎行事是不可能的,被发现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对不当行为的内疚产生了愤怒的自卑,或许是在贫瘠文化中对破坏性毒药的消费需求造成了他们痛苦的表情。抑或是无法平复的愤恨驱使这帮男人不顾一切去饮酒取乐。我怎么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们这帮家伙今天都懒得去做昏礼 【穆斯林每日五次祈祷中的第四次,日落至天黑前进行】 了。」萨利姆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一边对着桌上的空瓶子点点头。那两人并不在意他的讥嘲,萨利姆勉强挤出笑容,紧绷的脸上一时间起了皱纹。他看上去气得够呛。
布达又矮又胖,身体滚圆,但给人很结实的感觉。好像这一身肥肉并不是因为他纵欲放荡,而是因为他有着比纯粹享乐更深的图谋。他朝我挤眉弄眼,一脸怪相:「给我们说说尤因格雷扎的新闻吧。那儿真有在水下行驶的火车吗?」
「瞧这个野蛮人说的,」萨利姆喊道,「你从来没听说过地铁吗?」
「你这么一来,会让这个英国人觉得我们都和你一样无知。」马吉德说道,声音里没有一丝调侃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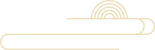

一个女孩从里屋走了出来,穿着又脏又破的长筒连衣裙,手里拿着两瓶啤酒。她眼里空无一物,似乎能够把眼前的一切看穿。她把一瓶啤酒放在我面前。她向前探身时,我从她连衣裙的腋下裂口处看到她年轻丰满的身体。她把另一瓶酒放在萨利姆面前,萨利姆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退缩了。
「阿齐扎,我们从乌拉亚来的朋友想要你。」马吉德突然说道,大笑着叫了两声。
她转过脸来,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然后站在那里等着,好像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跟她玩玩。」萨利姆说道,同时,像尸体一样朝我咧嘴笑着。我看到她又退缩了。
我看着那女孩,看着她尖尖的小脸和苗条的年轻身体,她没有任何反抗。我摇摇头,她垂下眼睛。马吉德大笑着,站了起来。女孩转身向里屋走去,双手已经撩起了连衣裙的下摆,马吉德大摇大摆地跟在她身后。布达温和地笑了笑,开始问我有关英国的问题。萨利姆回答了大部分,时不时会跟我确认一两句。我想有一瞬间我听到了一声尖叫,煤油灯的火焰闪了一下。马吉德似乎在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出来时乐呵呵的,光滑的面庞焕发着健康的光泽。
「渴死我了。」他说着,拿起还剩着酒的酒瓶。他一口气喝光了瓶里的酒,带着征服的微笑放下了瓶子。「轮到英国人了,我想。」
他们喊阿齐扎,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眼睛和以前一样空洞无物,嘴角向下耷拉着。我为他们点了啤酒,并对萨利姆说,等他喝完后,我就走。我们点的吃的怎么办?布达问。我还有活儿要干,我说。女孩端上啤酒后,布达站起身来,轻轻地跟在她身后走了。
「什么事儿?」马吉德面无笑容地问。「你不喜欢女人?去那里面干事吧。还是说,你不喜欢女人?她和他没任何关系,」他说着朝萨利姆抬了抬下巴,「你把她怎么了?」
萨利姆喝了一大口酒。「我们得去参加一个婚礼,」他喝完酒说,「你们留下来玩那肮脏的游戏吧。」
「你把她怎么了,你这个变态?」马吉德问道,咧嘴笑着,享受着生命中纯粹的快乐。
我们到婚礼现场时,正好赶上新郎家人和朋友陪同他到新娘家门口。两个年轻人在敲鼓,他们瘦得皮包骨,长相相仿,脸上表情紧张、冷漠,在震天的喧嚣中,似乎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内心。房前立着棕榈叶拱门,房子的正墙上搭着彩灯装饰的花环。从屋里传来了女人们唱歌的声音,新郎一走到门口,歌声突然变成了愉快的欢呼声。人们围着新郎转圈,跟他大声开着下流的玩笑,新郎被请进屋时,他们突然大喊大叫起来。年轻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即将要上桌的食物。萨利姆嘲弄地哼了一声。「新娘是我妻子的亲戚。」他说。
我没想到他有妻子。「你在和贝瑟尼私奔之前就结婚了吗?」他开车送我回旅馆时,我问他。贝瑟尼是个好听的名字,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提到它。
「是的。」他说。我们正在那条通往停车场的灯光昏暗的路上行驶,但即使在那暗淡的光线下,我也能看到他脸上的怨恨和愤怒。「我和她结婚好长时间了。」
「你回来是因为她吗?」我问。
他轻声地笑了。过了一会儿,汽车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轰隆作响时,他开口了。「最终她给了我一份豪礼。那个马来亚女人。我和她干那事时,流血了。她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不碍事,可她说我不能留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可我一和女人干那事,就会流血。」
我们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汽车停在旅馆外面。「你回来后看过医生吗?」
「什么医生?这里没有医生。」他说,眼睛盯着前方。然后他转向我,带着忸怩、温和的微笑。「明天带我一起走吧。到那儿我可以去看医生。带我走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他向我靠过来,那张脸紧张、兴奋到了怪异的地步,笑容里竟然主动多了哀求的意味。
第二天他来找我,尽管我头一天告诉他,我会自己去机场。他说话时带着平日里的恶意和傲慢,对看到的一切都嗤之以鼻。尽管我一再让他放下我就走,可他停下车后,在我旁边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张卷起的报纸。「像这样的公文包要多少钱?下次给我带一个来。要不寄一个给我,我保证少不了你的钱。我并不是说你在奢华之地需要我的钱。不过,很快你就会玩够了,要回到故乡来。」他说,「每个人都得这样,要不然,就会在异国他乡沦为笑话。」
我和他握握手,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当地钞票都给了他。他吃惊地看着那一大捆钞票。「希望你能好起来。」我说。
「你说什么?」他笑呵呵地问道。他把钱揣进口袋。「下次你可得留下来呀。」他说道,然后走开了,挥挥手,没有回头。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余静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