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位作家,在探寻自己历史意义的道路上似乎显得有些迷茫,然而,这种迷茫与另一位作家丁玲的迷茫,虽形式不同,却颇有相通之处。

浩然,这位来自河北的农民作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才,迅速在文坛崭露头角,其作品层出不穷,这在当时已堪称奇迹。
然而,他和丁玲一样,都生活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我们不能否认,【艳阳天】这部作品在浩然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意义。它热情讴歌了英雄人物肖长春,赞扬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同时也对马之悦和「地主」马小辫进行了批判。
这部作品明显带有斗争的鲜明烙印,是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动体现, 作家孙犁甚至说:「浩然的每部作品都自带原罪,自诞生的那刻起,充满了血与泪。」

随后,浩然又创作了【金光大道】,这部小说在【艳阳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了斗争的主题。在创作过程中,他更加自觉地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贯彻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将个体人物形象的意义与作家的本身体验紧密结合,共同融入了他所认同的历史叙述之中。
然而,正是在这种被改造、被强化的文化背景下,浩然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左」的印记。这并非单纯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但问题在于,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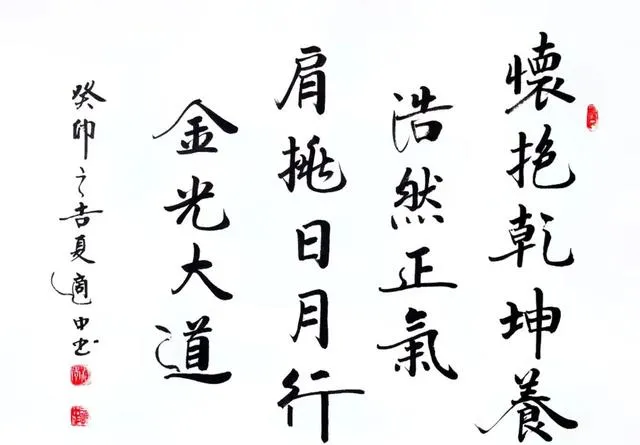
在新的历史时期,全民大反思的思潮涌动,人们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过去的问题,寻求新的思想解放。
关于浩然及其作品【金光大道】的争议,实际上是他自己挑起的。我们并非要完全否定这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我们必须指出其中存在的「左倾」印记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也是作家进步的契机。
如果浩然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这些争议,他或许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他选择了固步自封,以曾经的耻辱为荣,这无疑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损失。

浩然的「荣辱颠倒」,虽然与丁玲的「荣辱颠倒」形式不同,但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作品中,似乎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明,以她那俯瞰一切的上帝视角,无时不刻地统御着全局。她不仅掌握着人物生存的外在环境,更是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用她那充满智慧的目光洞察一切,实际上成为了真理的传递者和捍卫者。
整个文本仿佛是在权威眼光注视下进行的,那些来自这个眼光的信息被精心处理成英雄所需要的「神谕」,在他们困惑时给予指引。

英雄的成长历程,相较于普通人的奋斗史,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外在的、由更高权威选择的结果,而非仅仅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只要他们自觉地遵循感召,就能步入寻求真理的坦途,即便面临困难,也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在这种「神谕」的协助下,英雄们与困难抗争的价值更多地成为了展现「神谕」正确性的舞台,他们自身的人格魅力也主要来源于对「神谕」的坚持,而非通过自身挣扎矛盾的痛苦蜕变。
这是一种安全的「英雄历险」,它弘扬了「好人必有好报」的朴素道理,同时也强调了谨遵神谕的重要性。

从两部作品的结尾处理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主动营造史诗性质的努力。英雄的胜利和「神谕」的昭示,必然要以昂扬的姿态加以展示,文本也必须在各个方面体现这一成果。
在【金光大道】的结尾,罗旭光慷慨陈词,再次重申了「神谕」的精髓,引发了芳草地人民的狂呼和掌声,将胜利的喜悦升华为群体的狂欢。
在【三里湾】的深邃世界中,王玉生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的「技术革命」之中,那份对集体的执着让他毅然决然地与自私自利的妻子小俊划清了界限,离婚的决定彰显了他心系集体的高尚品质。

然而,玉生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很快便陷入了情感的纠葛之中。中学毕业的团支书范灵芝,如同一株真正的灵芝,美丽而聪慧,她的眼神中逐渐流露出了对玉生的倾慕。
然而,玉生那不高的学历——仅仅高小毕业——让灵芝在玉生与富农马多寿的儿子马有翼之间陷入了深深的犹豫。

马有翼,身为中学毕业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让灵芝忽略了他的富农家庭背景,长久地驻足在他的世界里。这种选择背后,无疑隐藏着耐人寻味的价值判断方式。而马有翼在经历个人的挣扎,成功通过「家庭革命」使父母转变思想后,最终与金生、玉生的妹妹玉梅结成了姻缘。
这种先进与落后的结合,恰似「人民内部矛盾」最为浪漫而温情的解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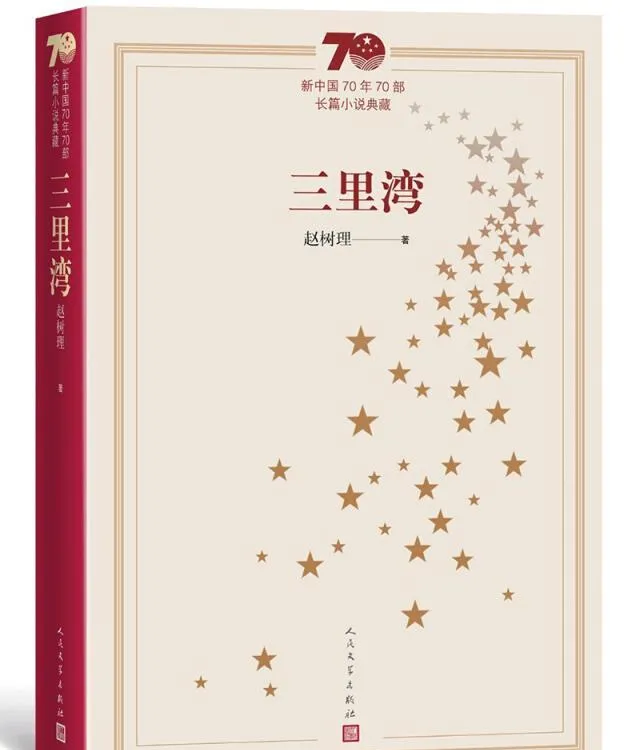
相较于玉生的情感纠葛,【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则经历了更为曲折的婚恋历程。他的童养媳因病离世后,他与「汤河上顶俊的女子」徐改霞之间那份久经磨砺的情感终于迎来了绽放的契机。
然而,徐改霞的身边同样有一位追求者——郭世富的儿子郭永茂,他身为中学生,家境富裕。但改霞从未因永茂的学历而动摇,她对他的自私自利思想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的情书交给了代表主任。
郭永茂的遭遇与【三里湾】中的马有翼形成了鲜明对比,它揭示了阵线已经日趋严密,知识分子已无法再凭借「知识」来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尽管郭永茂除了书信中的自私自利外并无其他劣迹,但他在爱情中的挫败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梁生宝最终选择了放弃与徐改霞的爱情,有意无意地促成她进城工作,离开了他们共同生活的蛤蟆滩。他转而与一位「红赯赯的脸盘」、高大强壮、手脚粗大的农村妇女刘淑良确立了恋爱关系。
叙事者通过这一选择,将爱情婚姻的选择视为革命者成熟的重要标志,合作社主任的妻子必须是庄稼好把式。然而,这种对革命理性的过度强调,对于源自肉身的感性需求却显得过于强硬和冷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革命的向往。
事实上,即便是叙事者,在描述改霞离去时,也流露出了一丝惋惜之情。

与梁生宝形成鲜明对比,【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与童养媳的关系深厚,两人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这一细节不仅彰显了萧长春坚定(而非梁生宝对童养媳的疏离所折射出的「个性自由」追求)。
当童养媳不幸离世(这恰好是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之际,或许叙事者有意无意地借主人公的婚变来展现这一法律所带来的社会解放意义),萧长春并未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悲痛之中,而是赢得了东山坞最动人的姑娘、团支书焦淑红的青睐,两人确立了深厚的恋爱关系。

相较于梁生宝的婚姻无奈,萧长春的爱情故事无疑更加圆满,这种叙事安排无疑进一步增强了「革命」在读者心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有人质疑:「假若没有斗争这条贯穿始终的动力线,浩然能否将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巧妙地融入到‘东山坞’这个宏大的叙事框架中,其创作又能否从狭隘的视野走向广阔的天地?」
然而,实际上,正是浩然无条件地接受了以斗争观念指导创作的原则,使得【艳阳天】的艺术世界显得略显单薄。

这种单薄主要体现在人物外部关系和内心世界的简化上,进而导致了作品第二、三卷与第一卷之间的艺术落差愈发明显。
一方面,为了「把英雄放到阶级斗争的场景中去表现」,浩然刻意简化了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其简化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萧长春和马之悦成为了正、反两大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其他角色则不可避免地被嵌入到这一斗争的「典型环境」中,用以展现和印证「斗争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的「本质规律」。

因此,萧长春等农村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排队伍」,「为自己调兵遣将」。当这种布局完成后,作品的第二、三卷便完全以两大阵营之间的生死冲突为主线,而形象的刻画和性格发展的描写则被淡化。
另一方面,斗争的模式也必然导致对人物内心世界描写的冲淡和简化。我们不难发现,在【艳阳天】的后期创作中,浩然对农村生活的真实体验与对阶级斗争观念的信仰遵奉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他内在的理性自觉。

因此,韩百安的小农心态、焦二菊的泼辣直爽、哑巴的内秀憨直等性格特质,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本质的外化形态。同样地,阶级斗争的规律和要义也必然会在情节中有所体现,如马小辫持刀杀人、弯弯绕放鸡糟蹋集体的庄稼、马老四用自己的口粮喂集体的牲畜、马翠清和韩道满因阶级出身时而和解时而冷战等。
这些情节虽然试图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但由于浩然对生活本质和现实人物的片面理解,使得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显得有所局限。
浩然在工农兵文学方向中的独特贡献,是研究其文学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现代文学兴起以来,文学大众化的追求便成为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课题。延安文艺讲话之后,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学要服务于工农兵,但这一理念在现实中遭遇了不少困难,知识分子与平民、农民之间的阅读鸿沟始终未能完全弥合。
尽管赵树理的创作曾被视为大众化的典范,但其作品更多地还是吸引了有知识背景的读者。而浩然,却以其独特的魅力,让【艳阳天】这样的作品深入到了广大农民的心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艳阳天】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当时农村合作社间友好往来的象征。它像是一面旗帜,引领着农民们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为了更贴近农民读者的阅读习惯,浩然在创作过程中精心删减情节,使语言更加通俗易懂。

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艳阳天】的第一卷农村版,随后便收到了数以万计的读者来信,足见其影响力之广泛。这部作品后来还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甚至在中央广播电视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使得更多不识字、不读书以及偏远山区的人们也能一睹其风采。
更为动人的是,据扮演【西沙儿女】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回忆,他曾去青岛崂山的一个村子,那里的支书夫妇因为读了【艳阳天】而结缘,成为了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吃饭时,书记念出书中的一句,妻子便能自然地接出下一句,这种默契和共鸣让人深感震撼。

浩然作为一位从工农兵业余写作者成长为专业作家的典范,他的创作具有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统一的独特性。他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成长为作家的一名农民,更是为新中国的主体对象——农民服务,他的作品被农民所接受,这种三位一体的统一性使得他的创作在工农兵文学方向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当今社会,虽然「农民写」的底层写作逐渐受到关注,但与浩然当年的地位和待遇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从自豪、自信到心酸、自卑的农民写作变化,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工农兵文学」的真正含义。

在农民依然处于社会底层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深入挖掘浩然的文学意义,思考他笔下的农民理想主义情怀对当今实利社会的启示。在普遍心酸的底层生存状态中,他那种昂扬向上、受人尊重的农民情怀,无疑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深入探讨浩然的作品与文学贡献,对于理解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初期文学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意义。浩然的创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生活的窗口。
鉴于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背景,关注占据国家主要人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农民群体,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浩然以「写农民、为农民」为宗旨,其笔下的农民形象构成了新文学农民人物长廊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仅如此,在同时代的农村小说创作中,浩然的作品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色。因此,对浩然及其作品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个人的文学成就,更是为了清晰梳理和认识这一段文学史的发展历程。
关于浩然的研究,历来是当代文学领域持续不断的话题。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浩然,必须以一个全新的、客观的视角来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