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年:1947
现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主要著作:【人生天地间】【沉默的视野】【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当代哲学问题九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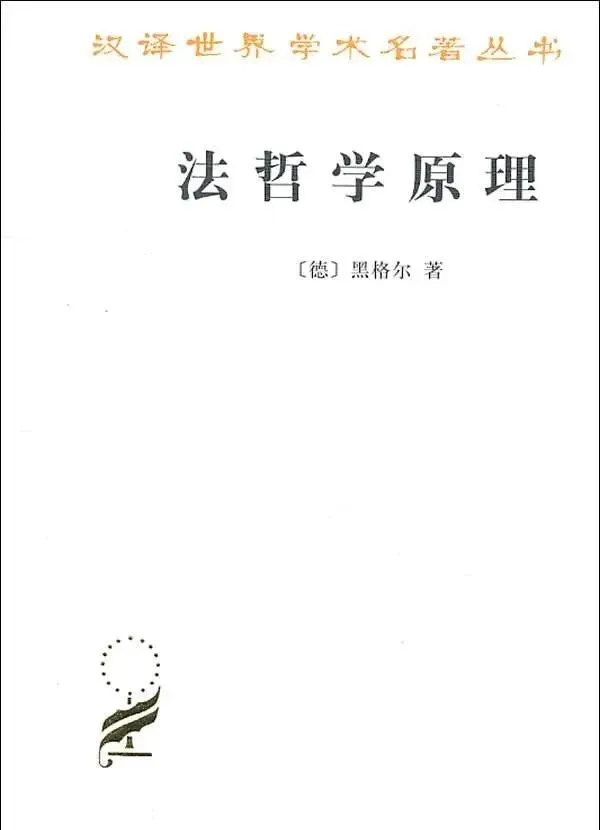
【法哲学原理】,[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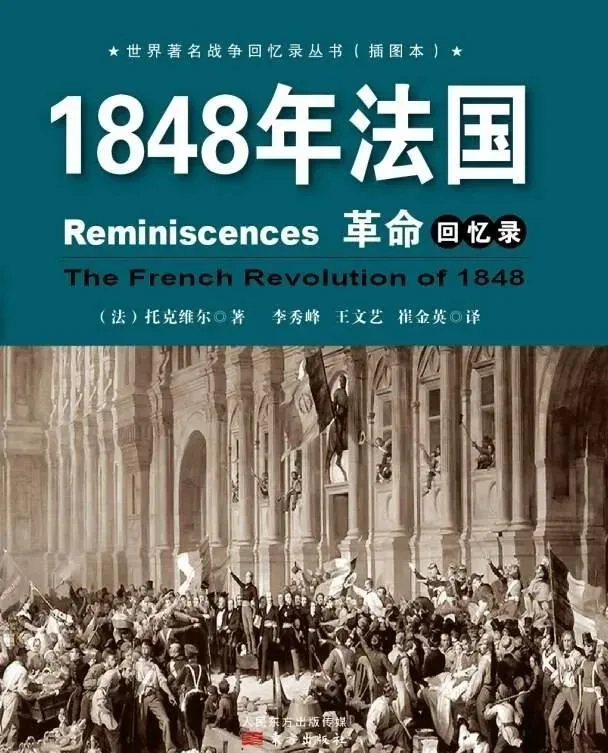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周炽湛、曾晓阳译,上海人民,2005(【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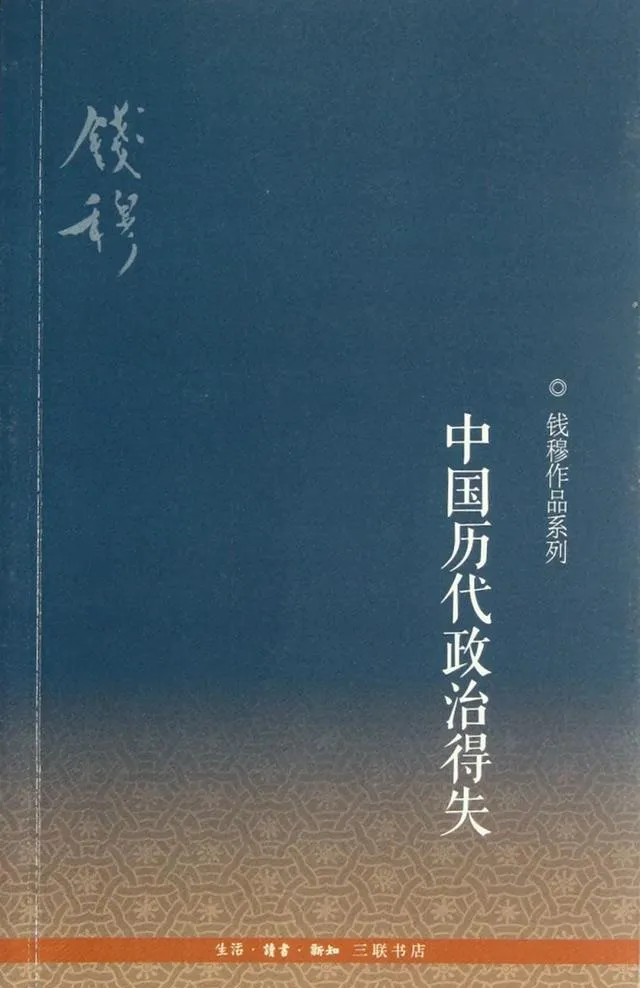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北京三联,2002
「开卷有益」是一句很小就知道了的话,那时候的家长和老师常用这句话鼓励读书,后来,就知道了只有「好书」才让读,才「开卷有益」;再后来,有了「读书无禁区」的讨论,那该是【读书】杂志创刊时由李洪林的一篇文章所引发的,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说是要读「社会这本大书」,其实是支持「读书无禁区」。
但不管有没有禁区,人其实都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而且,一旦发现那些不大容易看到的书,是一定会拿起来看看的,这倒不是因为那些书就是「好书」,而是纯粹出于「好奇」——好奇是人的天性,是一切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一开始就说:求知是人的天性,而求知则起于好奇。
当我也开始步入老年的时候,对「开卷有益」却有了许多新的体会。一是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开卷有益」的「效果」,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已经读了许多许多的书,而且总在思考,总在想表达什么;只有在此前提下,任何一本书,甚至偶尔随便翻翻的报纸、杂志,才谈得上「开卷有益」,因为总有所触动,而且马上联想到另外的问题,于是就要把这些触动赶快记下来,怕过后忘记。这样很苦,也失去了书籍本来所带给自己的乐趣,这时的「有益」,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我很想回到过去那种散漫地、无所用心地读书状态,可惜一时回不去。因为某种可以被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已经深入内心,即使自己不知道,其实只能在这种「范式」的指导或引导下阅读。
其次,所谓的「开卷有益」,并非指的只是「新书」、以前没看过的书。真正「有益」的,倒往往是重读时的感受。但人为什么会去重读一些书呢?无非是因为要用了,这才重新翻找。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就我而言,写一篇文章,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翻阅过去看过的书上了。为了找到某段话或某个意思,真是费尽周折:明明记得在这本书里,而且似乎记得在左面,但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就无法下笔,卡在那里。但,往往也正是为了寻找某段话而在一本早已看过的书中有了新的另外的收获。这说明人心中的「范式」是网状的,就如蜘蛛网一样,随时可能捕获一个偶然的闯入者。自然,「网状」越密集,也就越「开卷有益」。
由此可见,「开卷有益」的「益」,本身总免不了功利的目的,而收获却在那直接性的功利目的之外;所谓「之外」,无非是为下一个或另一个功利目的提供了准备;当然,为了实现那一目的,又会意外得到许多超出那一直接性功利目的之外的收获。
人生与书结缘,大约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而且总在那种直接的功利性目的的满足与不满之间。
但毕竟,有些书是真的可以称得上「开卷有益,百读不厌」的。
我这里首先举出两本书:一本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要给研究生们上「原著精读」,所以自己先要不断地看。这本书从我自己读研究生算起,至少总读了不下十遍。现在给别人讲,再读,而且每次都有新的体会,甚至可以做到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同一段话,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几种理解,再加上对时代、作者当时的心境、具体的语境、几个不同的译本或译法、面临的问题的转换、在后人那里所引起的不同反应等等因素,于是就会说出几套完全不同的话。一篇【法哲学原理·序言】,不过15页纸,但里面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仅「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作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这一句话,就需要讨论一个到底「什么才是哲学」的问题;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质上无非是对希腊伦理的本性的解释,而且他已经意识到一种更深刻的原则正在突破这种伦理原则,于是就想借助于某种外在的形式来压制住这种渴望,「殊不知这样做,他最深刻地损害了伦理深处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人格」;以及那三段广为流传、几乎人人皆知的隽语:「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密纳法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就能让人有多少感慨、多少议论可发!它不但要讲到你所理解的哲学,讲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希腊伦理的本性及那种伦理深处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人格,还要讲他所理解的「现实」与「合理」,讲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为什么要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他为什么会认为「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等等),当然,在这些话后面,是对中国当下哲学状况的认识,包括对启蒙或「再启蒙」(也就是思想闪电)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和感受,是我十几年前万万想不到的。
以前谈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认为这是他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一本书,现在我却认为这是他最深邃、最成熟的奠基之作,这期间所发生的转变到底折射出了什么,是时代的变迁?还仅仅只是我个人从心态到观念上所发生的转变?这里面的差异,其实也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历史观(绝对精神、时间中的理性)与海德格尔的历史观(生存论、时间性的情绪)的区别。而我们,恐怕又只能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解释。
至于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就不多说了,仅就那种把理论思索转变为一种叙事结构的体裁就足以使人陶醉;而且这是一种我心仪已久、并多次试验(如我的【沉默的视野】)的方式。要知道,正是这个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论断: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是今天的人们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你可以控制或减缓它,但却不能战胜它;第二,世界上所有社会中,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就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复存在的社会(想想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就知道被我们所误解了的「封建社会」,难道不是一个逐步消灭「贵族制」和确立皇权至上的过程吗?);第三,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这更严重了,因为在专制政府中,人们之间已经没有种性、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于是专制制度也就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等于把人禁闭在私人生活之中……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将永远不断下降(冯棠中译本,前言)。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说出过这样显然是真理但却完全不被人所意识到的话呢:「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第210页)这几乎可以称之为托克维尔的一个基本信念,因为这本书的第一、二两编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第64页)
至于说到一本国人自己所著的书,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钱穆老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些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精彩不在历数中国历代政治变迁的过程,而在历数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悲凉与无奈。秦汉以后,奴隶制度早已推翻,至此再无贵族承袭,只有皇室一家世袭,这是一;在古代中国,皇室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但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倘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只一个皇帝独裁,用来讲明清就可以叫名副其实,这是二;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有制度无宪法,有法制(一个制度有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治它)无法治(法治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是谓民主),有职责(须尽力践行之道义)无主权(自由意志之权利意识),有士人政权与部族政权间的交替(于是很可能事事出于部族、某特定集团之私心),无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间的更迭(二者不易区分,贵族多为军人,军人掌权便为贵族),有造反(每到政治极端腐败,造反的结果就是换一批人,重修制度)无革命(变法派与革命派在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革命之对象上争论不休,反倒使宪法、言论等革命性政制建设无法成型,即摆脱不了「不成文法」的惯常模式),此其三;最后,就是因对清朝政权之不满而扩展为对全部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的不满,进而再表达为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于是,我们也就在钱穆老先生这里隐隐看到了一种与黑格尔和托克维尔相似的东西。
有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基点,于是一开始所说的那个「范式」,便在暗中导引着人的读书生活;而一个人在朦胧中所期待的,无非是对这个基点的深化或摆脱。
(2007.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