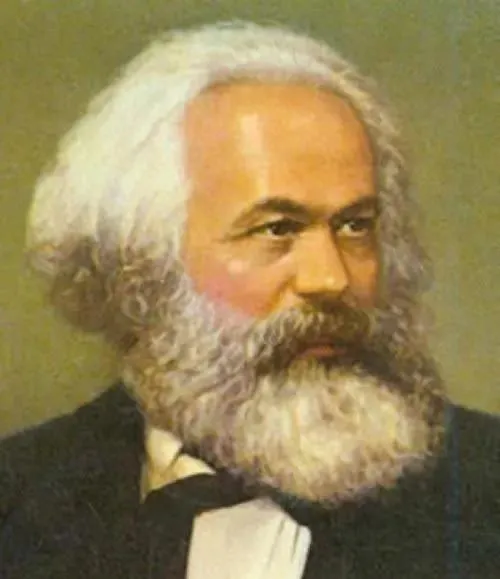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影响,激进的地理学家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纳入文化地理学科体系,生发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兴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相互作用促成马克思主义风景观。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景观的探讨尚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足够关注。1989年的论文集【地理学新模式】首次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地理研究,地理学研究的新模式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论文集里仅有少数作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展开人文地理学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史蒂芬•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关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和风景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并未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风景的内涵和思想脉络。
此外,【劳特里奇风景研究指南】(2019,第二版)零星提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风景研究的几位学者。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怀利(John Wylie)在【风景】中在论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和风景互动时,对风景作为「面纱」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地理研究中的表征和象征意义做了简要概述。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风景观的研究更少见,【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发展】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地理学的影响表现在静态和动态两方面:一在静态的意识形态构造上,景观呈现的结构是垂直的。景观作为面纱,掩盖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差异和不公平。二是作为生产实践的风景聚焦风景的物质层面,关注景观的劳动生产过程,揭示风景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动态结构。
本文拟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在思想脉络上的相互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风景观的内涵和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索,旨在为国内外文化风景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的相互影响
从历史轨迹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正是新旧文化地理学争论正酣之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其中,美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学者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nis Cosgrove)和丹尼尔斯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家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启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研究风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和空间生产模式。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被界定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观点、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地理问题的研究。 尽管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社会,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地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70年代激进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产物。
1977年【激进地理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激进地理学高潮时期,激进地理学家几乎对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的地理问题进行了反思,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对地理学的影响,批判人文地理学家忽略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女性、流动工人以及贫困、犯罪等城市和乡村社会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被现代地理学所接受,导致新兴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给文化地理学带来的新思路是: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超越了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更关注社会空间的塑造、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生产。
文化地理学家哈维也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张应用历史-空间-社会三维辩证法把空间生产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核心中,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开创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空间美学新模式。
1969年,哈维概括了地理学中空间概念的演变,揭示出空间概念的差异是与空间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密不可分的:「一个社会所发展的用来表示空间的概念框架不是静态的,自古以来空间概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般包括空间概念的变化,但有时通过科学发现突然需要对空间概念进行重新评价,这对现行的一套文化价值给予了猛烈一击。」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聚焦城市化理论,为此,他把社会正义引入到城市空间地理学研究之中。
同样,后现代地理学先驱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空间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空间和时间的生产,也同时生成了相应的社会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空间的生产,尤其是差异空间的生产是理解资本主义存在及其理论内核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地理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日益深入。 在哈维、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以及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等多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进一步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空间化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包括新文化地理学在内的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并被批评性地应用,这一时期的现代地理学受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例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影响,主张用结构主义的社会分析模式解读城市社会空间,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强调确定的分析范畴,如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强调各个重要链条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主张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来解读城市空间。总之,8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激进的风格重写文化地理」,引导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斯等地理学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新模式下,对新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风景」进行全新界定。
二、马克思主义风景观的内涵
1987年,科斯格罗夫和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方向】标志着新文化地理学登场。新文化地理「既聚焦历史也聚焦当代(但始终关注情景化和理论化),既探讨空间也探讨社会(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景观),既探讨乡村也探讨城市,既思考主导意识形态也考察文化的偶然性。总之,强调文化在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1989年,丹尼尔斯也强调新文化地理学应密切关注文化作为社会权力的媒介,在维护精英或官方权威中起到的作用。其原因是作为传统文化地理学核心概念之一的风景,不会轻易接纳权力和冲突等政治观念,甚至试图消解或掩盖风景的政治话题。可见,新文化地理学正是融合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交叉领域,对传统文化地理学中的风景概念重新界定。
早在1983年,科斯格罗夫就敏锐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地理学都关注文化生产和实践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地理学从同一个本体论观点出发,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或者线性的因果解释,坚持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定义为历史的。
这一点也是以卡尔•索尔(Carl Sauer)为首的旧文化地理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索尔在【风景形态学】中力主反对环境决定论,从概念上区分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概念,指出自然是文化实践的基础和产物,强调文化和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科斯格罗夫指出旧文化地理学存在的两个问题把文化地理学理论研究带入困境,一是没有从理论上界定文化产生的原因和文化的特性,二是忽略了文化中的阶级属性。
科斯格罗夫为新文化地理学总结了三大任务。第一,文化地理学家要揭示不同生产模式下,地方和风景所隐含的社会意义,并且把这种研究与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原因是每一社会和经济形态都有其具体特性,其生产和再生产都发生在具体空间例如风景之中,社会形态在空间中书写历史,社会形态的形成是风景在不同生产模式中的叠加。文化地理学的第二个任务是把空间并入文化生产的象征代码中,原因是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象征性权力,其空间的占用和再生产旨在维护阶级统治的合法化和长久化。
「风景既建构象征性权力,又被象征性权力所构建。」第三,作为革命性实践活动,文化地理学不仅要揭示人类行动在风景生产和维护中所起的象征作用,更要批判性地审视空间组织和风景中的新形式。总之,科斯格罗夫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纳入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之中,提出把空间生产、空间建构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形态列入风景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主题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1984年,科斯格罗夫在【社会形态和象征风景】一书中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风景观。 他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风景概念从15世纪开始的演变史进行梳理、概括,形成激进的文化风景观——「风景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它代表某些阶层的人们通过想象与自然的关系,表征自我和世界」。科斯格罗夫把风景概念的起源定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早期资本主义城市,「城市是资本主义和风景的发源地。」
这段高频引用正是对科斯格罗夫风景观的概括:「风景作为一种观看方式经历了自己的形成史,但其形成史必须置于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史视域下才能得以理解;风景有自己的假设和结果,但其假设和结果在起源和意义上远远超越对土地的使用和感知上;风景有独特的表现技巧,但这些技巧是与文化实践的其他领域共享的。」
总之,科斯格罗夫强调风景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活动。风景的形成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影响,风景既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重要的是主观意识的反映,风景背后是不同观察主体的观看方式,代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不同的表征方式和美学思想。在传统的文化地理中,风景被当作一种传统的视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有意掩盖了各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掩盖了平常百姓对自然风景的认知和体验。
科斯格罗夫在该书1997年再版引言里,对自己的风景概念再次进行阐述,他认为这本书的创新点是通过引用「社会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把风景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象、表述和意义挖掘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1995)一书中穿越时空,勾勒出一幅浩瀚宏大的风景隐喻的漫长历史,引导人们重新发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神话和记忆的脉络」。沙玛指出,风景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对于风景的规划、使用和改造由来已久,风景神话与人类历史、民族认同及国家身份紧密相连。风景是自然背后的文化,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例如「帝国、民族、自由、企业以及独裁——都曾借助地形学,将自然形式赋予自己的统治理念。」
沙玛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开启了记忆和风景研究的交叉领域。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指出,记忆和记忆再现是关乎国家身份、民族主义以及权力和权威的重大问题。对于沙玛的乐观史学观,萨义德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提醒学者们关注虚构在记忆和风景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建构社会、政治和历史记忆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和阶级纷争。
萨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虚构传统是当权者经常采用的一种实践。它是他们在大众社会中的一种统治工具。……虚构传统就是选择性地使用集体记忆的一种办法,其做法是篡改某一部分的国家历史,对其他部分进行压制,以及通过完全功能性的方式抬高特定部分的地位。这样,记忆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而是有用的。」萨义德多次用自己家乡巴勒斯坦作为例子,重申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耶路撒冷神话记忆至少意味着两种冲突的记忆、两种历史虚构、两种地理想象。
W.J. T.米切尔(W.J.T. Mitchell)也对沙玛的风景记忆观表示了不同,「我将风景当作一个记忆缺失和记忆擦除的地方加以研究,一个用‘自然的美丽’来掩盖过去、遮蔽历史的战略场所。」萨义德和米切尔警示人们要对风景记忆所涉及的国家身份、民族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评的态度,建构风景记忆的过程就是某个国家、民族和种族在某一地方或者空间所进行的空间生产、文化实践活动,就是权力维护、文化霸权和阶级冲突的过程,就是以隐秘、虚构的方式利用、误导集体意识,构建国家叙事的过程。
米切尔在关于「帝国的风景」中进一步提出作为一种权力的文化实践,风景是「人与自然,自我和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是它所隐匿的社会关系的象征,不仅仅象征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更是文化权力的工具,是社会和主体身份得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甚至是权力的手段,风景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构型,与欧洲帝国主义密切相关」,是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解放」「自然化」「统一」这个世界的手段和媒介。将帝国意识灌输到当地风景之中,实现风景的「自然化」。 除此以外,殖民者更多地通过风景的空间扩张推进殖民活动,其结果是,「在它们面前展现的‘前景’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场景,还是一个被投射的‘发展’与剥削的未来。」
科斯格罗夫和沙玛主要从历史层面探究风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地方文化传统,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弗雷德•英格里斯(Fred Inglis)对风景的概念界定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把风景视为高张力概念,其目标是直接打破统治阶级的幻想,原因是「风景位于几个概念的交叉点上,这些概念正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竭力区分的:‘机构’‘产品’‘过程’和‘意识形态’」。这种张力还表现在把风景当作精英阶级的「观看方式」与风景是日常的「生活方式」两种风景观的差异上。因此,不能把风景看作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鲜活的过程,风景创造了人,反过来又被人所改造。谈论风景时,人们必须考虑风景生产的实践过程:它被生产的同时其定义被接受和被解读。英格里斯对风景研究带来的启示是,对风景的解读阐释有助于理解和评判某一社会及其文化思想。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从文化唯物主义出发,分析产生于地理或者风景中各种文学和文化形式的变化,指出这些变化是英国社会斗争、阶级冲突及权力更迭带来的结果:「劳作的乡村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风景。风景的概念暗示着分隔和观察」;风景是英国贵族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通过风景绘画、风景写作、风景园艺和风景建筑的历史进行再现,而这些历史必须与「土地及其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威廉斯从丰富的城市和乡村主题的文学分析中得出结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家从不同视角描绘自己亲历或者记忆中的英国历史和现状:「不管过去的还是当代的意象,它们都是历史的建构,是不同政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不同观点所塑造的。这些意象没有一个不是没有实际的斗争和修辞争议的。」
英国左翼艺术史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同威廉斯一样,指出视觉艺术尤其风景画在揭示土地与人的关系时要考察更大的现实、历史、物质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服务的」。在【观看之道】(1972)中,伯格审视了西方风景画传统中资本主义策略在经济、社会和性别方面的操控和挪用。伯格首先指出过去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被神秘化,其目的是把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少数特权人物有意编造历史,使普通民众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的权利。
同样,艺术作品被上层人士收藏,脱离了大众,成为统治阶级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影像设备的普及、艺术复制品的大量出现,古代艺术被新的影像语言所替代,伯格提出新的问题,「谁在使用这种语言?目的何在?」约翰•巴威尔(John Barrell)在审视了1730年到1840年的英国风景画后得出结论:风景画是英国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安•伯明翰(Ann Ber⁃mingham)在【风景与意识形态】(1987)中也指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风景画是意识形态的工具,风景被以风景画的艺术表征方式符号化、具体化,被权力机构和统治阶层给予政治、文化和社会赋值。
总之,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影响,风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权力的文化实践过程,是历史、文化、地理、政治及经济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文化表征,是资本运作、国家立法、权力和社会公平作用于不同种族、性别及阶级等复杂关系的具象化。 风景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人类主观意识的体现,反映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立场的差异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景的研究主题
除了风景的内涵得到重新界定外,风景的研究主题也得到拓展,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风景与社会公平、风景与女性主义、风景与权力以及城市景观与空间政治。
第一,风景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系统化的思想,包括政治公平、经济公平、教育公平和民族公平。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公平的本质,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公平观进行了批评和否定。风景与社会公平正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关注最多的话题,涉及国家立法、司法、执法、社区、民族、种族及性别等方面。
马克思【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背后是真实存在的货币、资本关系,尤其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风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媒介和社会意识形态符号,成为了一种商品——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象形文字」及它所隐匿的社会关系的象征。由此,风景成为切入社会公平/不公平话题的途径。风景的社会公平性主要包括:一是法律、公平和政体,二是「风景民主」、公共参与和政体,三是劳工、阶级与生产,四是国家、种族与记忆,五是日常冲突和归属权。肯尼思•奥维格(Kenneth Olwig)主要通过「实体性」,考察风景生产、再生产(背后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实践过程)以及风景的视觉和文字再现过程中,风景是如何呈现社会公平的:「风景不必只从地域或者景色角度来理解,它还可以被看作社区、司法正义、自然和环境公平的一个连结点。」
乔治•亨德森(George Henderson)认为风景是一种社会空间,认识论意义的风景是一种人类实践和人类思想的物质再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风景的真实性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因为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尤其是一种很享受的凝视方式,通过有特权的透视法来宣称主权。这不仅仅是一种观看方式,而是地方的真实物质构建。」
温迪•达比(Wendy Joy Darby)也认为透视法凝视满足了商业资本主义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的需要,其运行模式有两个,一是能使观众体验真实空间的再现性,二是政策性,欧洲通过「掌握所有实际的和象征性的测量结果而实现了领土扩张」。唐•米切尔(Don Mitchell)多次重申风景主题的模糊性和隐晦性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和流通整个过程中,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权力,风景的政治性和公平问题是普遍的存在而非地方性问题。因此,唐•米切尔建议风景的概念和理论化需要把资本流通、资本的危机、种族、性别以及地缘政治和权力等因素考虑进去。
邓肯夫妇(James S. Duncan and Nancy J. Duncan)通过研究纽约市郊区贝德福德小镇的景观,揭示风景、阶级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权力关系。贝德福德小镇是特权阶层的生活场所,是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社会能力的反映,因此小镇的乡村田园风景、风景所象征的历史记忆和社区文化是小镇居民全力保护和维持的。
例如,为了保护位于小镇中心、被视为小镇象征的「贝德福德橡树」,社区和居民们多次通过立法和环境保护组织阻止开发商在橡树附近施工。该小镇的风景「被看作美学产物受到严格控制……居民们很自信地认为通过保持开阔的绿地,他们的审美利益就可以通过空间隔离得以保障,这样,居民们从空间和视觉上把自己屏蔽在令人烦恼的种族和贫困问题之外」。然而,风景政治涉及的阶级、种族、宗教和性别关系等话题,小镇风景的特权性和不公平性在全球化以及日益复杂的权力体系的当今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最主要的批评来自维护小镇景观的拉丁美洲工人,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被雇佣,却被特权群体排斥在外,被迫居住在小镇之外的廉价社区。
第二,风景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的「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章节里,指出欧洲裸像中往往女性为画作对象,画家、观赏者及收藏者通常是男性:「这不平等的关系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以致构成众多女性的心理状况。她们以男性对待她们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她们像男性般审视自己的女性气质」。在新旧文化地理学发展的任何历史时期,男性都是风景的凝视者,风景被女性化,是男性观察、评论的对象,对风景和女性的表征反映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温迪•达比直言,「风景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
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派的资助人或是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是拥有土地并管理国家的男人的附属物一样。」科斯格罗夫认为风景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其与父权制话语的合谋上,「文化被界定为‘男性’的属性,而自然则属于‘女性’的属性……这些‘女性特质’表现为非理性、任性和野性,有时也感性、温柔和驯服—但自然屈服于男性理性和独创性的控制力,则是一个一贯的比喻。」
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批评地理学被男性所垄断,所关注的空间、地方和风景是从男人的视角出发的。玛格丽特•菲茨西蒙斯(Margaret Fitzsimmons)指出在人文地理学话语中,自然被女性化,风景被女性化,风景与女性都被视为他者。因此,风景经常被认作女性的身体和自然之美:「诸位地理学家主要兴趣所在是大地母亲的外表和特征。为此,我们务必了解地质学的基本原则,如同画家要对人体或者动物的解剖有所了解……地表的特征和地球的内在特点值得学习、了解和领悟的是它们的美。」
女性主义学者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十分关注知识生产的政治性,她指出,地理学传统表现为「一种大男子主义凝视景观方式,这类凝视具有二元性,既有观者支配与掌握的主动性,也包括作为女性而建造的‘自然化的’景观的被动性;既有研究者所宣称的科学理性,也隐含了被压制的视觉愉悦。」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安妮特•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批评了环境叙事的主流视角是白人男性,土地被女性化,女性如何以花园作为自己的风景隐喻对抗男性话语。
1996年,路易斯•韦斯特林(Louise H. Westling)首次考察了美国小说中的性别与风景主题,指出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强化了美国田园思想核心的帝国主义怀旧——对待女性化风景和自然生物的自作多情的男性凝视掩盖了对于原始荒野的征服和破坏。
第三,风景与权力
权力与社会公平是紧密相连的社会话题。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达比认同米切尔关于风景是文化权力的工具,风景背后隐匿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之间的博弈等观点。他从18世纪英国的风景意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开始,考察了风景占有所代表的阶级冲突和矛盾,展示风景表征与政治表征之间的关系。达比把18世纪英国风景传统按照文化生产的形式分成风景与早期剧场、权力的印刷与印记、17世纪风景画与18世纪英国乡村别墅、18世纪舞台布景与全景画,从文化历史角度,揭示阶级概念是如何通过不同时期的风景表征得以传播、合法化。
在这一复杂的文化过程中,「地理空间和社会形态按高低有序的等级建构起来」,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的各种层次的象征性等级制度不断推进、强化或分解」等级建构。达比还以英格兰湖区(Lake District)和峰区(Peak District)两大风景区的立法史为例,揭示了隐匿在风景问题之中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呈现为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与互动等。
唐•米切尔以1913年到1942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农业风景和流动工人为探讨对象,揭示了「土地的谎言」。米切尔强调「风景的形塑是妥协的产物,是权力体系和政治经济学运行产生的多种权力状况的产物」,每一处风景都是人类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建构。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风景主要是来自不同移民国家的流动工人辛勤劳作创造的,他们为加利福尼亚乃至全美的农业综合体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被监管和被动隐形的流动工人、劳工营以及失业者、流浪汉留宿地的恶劣条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资本的占有和权力运作。流动工人在改造农业景观中的作用不仅被有意识忽略,他们应当享有的平等和社会权力被资本家剥夺。
第四,城市景观与空间政治
城市景观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城市景观的空间生产、区域划分、空间表征和象征意义等给予大量关注。哈维有诸多关于城市空间生产、资本运行等城市政治的论著。例如,在【公平、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中,哈维指出,西方世界卷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时空发展不平衡的全球过程,所有的新技术进步、快速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差异都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使。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哈维对城市的意义进行界定,在他看来当代城市是一种复合景观,一种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工改造的人工制品。
唐•米切尔在【城市权利:社会正义与公共空间之争】中回应列斐伏尔所说的「城市权利」,以美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实践为例,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拥有城市权利和公共空间?这种权利在法律层面和街区是如何被决定的?城市权利是怎样被监督、合法化或者削弱的?这种必须被限制和抗争的权利在美国城市中是如何被形塑为社会公平或者不公平的?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米切尔所关注的城市弱势群体,揭露无家可归者如何被国家立法排除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外或者受限进入公共空间。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的研究重点是工业化、消费社会以及审美经济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她多次引用哈维、爱德华•苏贾(Edware Soja)等人的理论学说,沿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认为以文化、艺术符号为代表的「象征性经济」起到了重塑城市的重要作用,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在城市空间生产和运作中进行了重组。
她在【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中分析了美国五种不同的城市市区类型,揭示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构建城市风景中的不同模式和形态,以迪士尼世界和亨利•福特产业综合体为实例探究强大的利益集团是怎样改造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规划的。佐金在对纽约苏荷区(SoHo)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变化以及纽约城市的变迁进行多年研究后发现,20年来该区已经被一些特权阶层通常是艺术家重新占领,他们改变了苏荷区的街景和生活。佐金指出,风景以一种物质形式表现权力关系,尤其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视觉意义上的不对称权力意味着资本主义吸取潜在的形象能量、发展真实的或者象征的一系列风景的巨大能力,这些风景界定着每个历史时期,包括后现代性,这颠覆了詹明信的权威论断——建筑对后现代性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的象征。相反,建筑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象征主义的资本。」
佐金直言在现代社会,风景早已超越了「实体环境」的地理学意义,而是物质与社会实践及其表征的复合体。狭义意义上的风景代表权力机构强加的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关系的体系结构;广义的风景涵盖人们所看到的全景:「有权有势者的地景——大教堂、工厂和摩天大楼——以及无权无势者附属的、抗拒的、或饱具乡土气息的地景——村落礼拜堂、贫民窟和廉价公寓。」因此,权力、压迫和集体抵抗把风景形塑为社会的缩影。对激进地理学家来说,风景是一块资本积累的白板,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历史阶段的空间性。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自主的还是被动的空间移动,经济力量是决定性因素,用哈维的话,「资本创造并破坏了自身的地景」。
结语
20世纪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中,风景的内涵得以延展,研究内容和视角得以充实。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庞杂,派别众多,文化地理学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景观仍然汇集了众多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和文化关系的深刻反思和激进的改良社会思想,其革命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多元性必将在未来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得到深化和完善。
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景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关注风景的历史、地理发生及发展史,又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政治及经济息息相关,背后是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空间生产、权力和社会公平等政治议题的表征和具象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冲击,城市化进程和流动性的加快,风景的文化、社会及政治属性将愈来愈强。风景与社会公平、风景与权力涉及民族、种族、性别及阶级等诸多社会因素,必将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探讨。此外,城市风景背后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政治随着后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和新焦点必将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城市景观将成为未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研究的重点话题之一。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精神和开放性大大促进了文化地理学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延伸,也将为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