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语义的转换并不需要任何可见的标识,只是在阅读过程中做一个极微细的停顿,悄悄换一口气,短到不必打一个标点,可是已在暗中滑向另一个议题。其步履之轻微,以至有些稍不经心的读者无所察觉。但一个好的阅读者当然就不只是留意段落划分、标点符号这些可见之物,还会关心那些看不到而只能感觉的成分。
同样的道理,观察历史,也不能只注意分期和事件,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悄然「换气」的瞬间。这在日常状态中的历史中并不少见,犹如金鱼吐出的一粒气泡,有些转瞬即破,有些寿命稍长,或因为和其他气泡发生结合、积聚,最后竟至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但追溯其开始时候,也不过就是金鱼偶然吐出的一串气泡而已。习史的人好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澜」者,当然不只是看波澜起伏、波浪滔天,还要知道它起始(或无始之始)的状态,以至那些终未成澜而消失无形的气泡。
近代中国是一个巨变时代,什么都在变,不同领域的变速不同,但总体来说可谓波涛汹涌,正是应该细观之澜。然而这种赏析的心情与可能只是事后才有,真正卷入时代的人,除了少数自认掌握了历史的通关密码而自信十足者,大多数人并不明所以,只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但是时代幕布上突然现出一条裂纹,让人从中窥见此前无法想象的另一种可能,必有人突破「常规」,做出此前无从想象的事来。倘或周边的人即或皱眉撇嘴,却到底没有发出怒喝,更未曾动手把裂口缝上,则时代风向已在悄然转换中。
下边笔者想引用两个出自近人回忆录的故事,展示民国初年历史中一些「换气」的瞬间。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三期
杨苡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李一氓
【李一氓回忆录】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天津,2023年1月27日逝世。著有【青青者忆】【雪泥集】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
诱拐女主人的男用人
第一个例子出自杨苡的口述自传。杨家是世家,杨父做过天津中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杨苡和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都是姨娘所生,大太太生的女儿叫杨蕴如,因为自小娇生惯养,我行我素,从不顾及他人,被家里人私下叫成「大公主」。大公主学业不成,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位姓孙的少爷,出自天津的另一名门,性情似乎也很温和。但大小姐此前完全不知男女之事,「看孙少爷书生模样,斯斯文文的,怎么晩上变成那样?就害怕得不行」。终于不能忍受,离婚了事。「离婚是在报上登了启事的,比结婚还轰动——那还是二十年代啊,离婚就是新鲜事,何况还登报。」

杨苡(右二)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左一)、姐姐杨敏如(右一)的合照。图片来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第二次婚姻是自由恋爱,大公主喜欢上燕京大学一位广东籍的赵姓男生。「大公主一直是没开窍的,和姓赵的在一起开窍了。」不久就同居。可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同居这样的事,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只有结婚一法。婚后二人回南,「家里的两个用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纪轻轻,跟着去的,也是陪嫁的一部分吧。过去嫁出去都会带用人过去,自己人,有照应,不让男方欺负着」。然而事情偏就出在这位男用人身上:
跟去的男用人叫小田,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当用人,老实巴交的,这时已死了。小田跟他爹完全两样,长得白白净净,学过点文化。他挑拨大公主他们夫妻关系,说姓赵的如何不好,一是说姓赵的长得难看,二是说他跟你结婚是图你的钱,还说,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大公主跟姓赵的原本还是真有感情的,就是没脑子,居然把他告上了法院,要离婚……
正闹离婚的时候,小田又撺掇大公主,让大公主跟他私奔。还说,有几万元钱在手,他们一辈子吃喝不愁。大公主不干,她跟小田没那种关系,小田是下人,她是特别有等级观念的,怎么可能跟他跑?小田就威胁她,他手里有不知哪来的一沓子照片,大姐夫私下里照的,也许就是现在说的「艳照」,说要散布出去。大公主急了,就打电报要家里派人去救她……
大概前后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大公主就又从广东回来了……婚也离了,善后的事儿是如何处理小田和那沓子相片。最后是给了小田一笔钱,让他走人,离开天津,当然也是利用杨家的势力,叫他闭嘴,这事一辈子都不准说出去。小田的确没再出现过,从此没了消息。
这里充满了各种八卦材料:富家小姐对性的无知和畏惧、大张旗鼓的结婚和离婚、未婚同居和再婚……无不可作为闲言碎语的好题目。不过,虽然这些事情在杨家视为耻辱,在二十年代的新潮青年中却也不算太过离谱。值得注意的倒是「小田」。虽然是用人,但是他「学过点文化」,又有几分姿色,先天和后天的条件给了他勇气,不但敢动手拆散女主人的婚姻,还先是诱拐、后是敲诈,皆非当时的普通人所能想见。
在一向「等级观念」森严的大公主眼里,这当然不可思议,其他人想来亦然:那位被派去处理此事的管家「潘爷」,根据杨苡提供的材料,向来是主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自然想都不敢想;小田「老实巴交」的父亲若是活着,也许会吓掉下巴。但在小田本人,却绝不认为这是痴心妄想,毫无可能。他事先就保留了一沓艳照,可见早有准备,预料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小田这么做,当然跟他自己的品行有关,或者也是因为杨家的大家长已经不在了,所以才有这副胆量,欺人孤儿寡母。然而,其中不也透露出世风转变的消息吗?时代不同了,旧的身份制度已在崩溃中。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小田有没有得手,而在于他的大胆:敢想敢为。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果: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否采取行动则大抵取决于个人,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更具象征意义。小田的形象和施蛰存在小说【追】里塑造的工人革命家鑫海颇有几分相似,都是无产者喜欢上资产阶级小姐的故事,不过小田本质上是个小流氓,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闹革命,求平等,而就是「色胆包天」。可是,一个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不安本分,又恰好遇到一个激变时代,想要脱颖而出,有点赌徒心态,敢于为旁人所不敢为,这里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估量。又或者他根本未曾多想,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行事。但这「本能」也还是时代的产物——他父亲老田的「本能」就并不如此。

【追】,施蛰存著,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藏。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这位小田后来不知怎么样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再过些年,地覆天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凭他这副身手和胆量,或许是一个弄潮的高手,也说不定。
和弟媳同居的老绅士
第二个例子出自【李一氓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1903年生在四川彭县(现在叫彭州),长期担任中共党内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不过那是后话。这里讲的是李十多岁,还是一个孩子时的见闻,从文中提供的信息看,大概是民国建立之后最初几年的事,比杨苡讲的故事早了十年。主人公是李一氓大姐的公公:
我们这位亲家叫杨西亭,是个老秀才(举人?),又是地主,多多少少还有点社会活动能力,当过多年的县劝学所所长。他就把我父亲请去当劝学所的庶务,两亲家,彼此都很信任……然而这个家庭也有一件怪事。老亲翁的亲兄弟死了,留下一个年纪轻轻的弟媳。这位弟媳,人长得很体面,我那时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都觉得看来顺眼。由于社会地位和封建礼教,年轻的寡妇不好嫁人。但成天住在家里,逐渐被大伯缠上,两厢情愿,顺理成章,这位亲翁就公然在弟媳妇房里过活了。杨家大院内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亲戚朋友之间,也就默认而无所避忌。封建制度虽然是祸根,但社会已开明到对这种事情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可见那个时代的特点了。
传统中国是个讲究礼法的社会,「男女有别」,即使是同胞兄妹、姐弟,长到一定年龄,按照规定,就不能轻易接触,更何况大伯和弟媳?实际情况当然比这要宽松,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农村,如果细心爬梳,各种打破禁忌的事件虽未必能和勒华拉杜里描写的14世纪法国小山村蒙塔尤的「性自由主义」相比,也绝非罕见。很多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谨守「看破不说破」的原则,只要还能维持体面,也就过得去。于是,纸面之上是一重历史,纸面之下是一重历史,纸面之外还有一重历史,将几重历史结合,彼此映照、折射和对比,看到才能更全面(注意,纸面之上的历史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不过李一氓所说的事确乎有些特殊,一是这发生在士绅之家,二是其举动如此「公然」,三是亲友也都「默认」。无怪乎李晚年写回忆录,还不忘提上几句,认为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李是过来人,对于「那个时代」的判断,当然不是只根据这一个案,即使他的判定未经严谨论证,只是一种感觉,有些随意,但历史当事人的感觉往往是对各种迹象加以消化的结果。作为一种整体的印象,仍具不小的参考价值。

电视剧【红楼梦】(1987)剧照。
和小田的故事不同,此处的重点并非是事情是否已经发生。传统上,即使是在士绅之家,出现这类违背礼法的丑闻也并非绝不可能(比如【红楼梦】里焦大揭发的「爬灰的爬灰」)。关键在旁观者的态度:二人的行为是「公开」的,亲友也都「无所避忌」(避忌二字重要),显然已不是为了维持颜面,而是「看破」也已「说破」(不必真「说」),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认可。然而这不是说旧的伦理规范已然失效——李一氓用的词是「开明」「宽容」,当然就不是鼓励、赞赏。然而,处在一个革命时代,连皇帝都没有了,此前的信条究竟孰是孰非,谁还说得清楚?于是,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还有可能,人人都在试探,等候尘埃落定,有些不知所措——或许因此就干脆「无措」。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吴虞。他在清末因为揭露家丑而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只好跑到乡下当袍哥的舅舅家躲藏。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他大摇大摆地回到成都——那时,通缉他的文告并未撤销,可是他已无需再为此忧心。革命突然在价值上造就了许多模糊空间——吴虞受益于此,杨西亭和他的亲友们也都主动或被动进入其中:二者走进的当然不是同一个空间,而是在同一或相似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许多平行或交叠空间之一,每一个都可能继续开放,但也可能因为什么事而重新闭合:比如,吴虞所在的空间就一直持续下去,杨西亭所在的空间虽未消失,但有一部分被关闭了。

吴虞(1872-1949),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制图:新京报)
三条界线
放在历史的潮流中,这两个故事都是再小不过的事,不过却提醒我们注意到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变化。第一个故事是对阶级的颠覆——这挑战被中途打断,秩序(暂时地)恢复了原状;第二个故事是对人伦的直接冒犯,周围的人却容忍了这一越轨,使不合法的事看起来「合法」了。两件事结果不同,却受同一种权力结构的影响:杨西亭得逞了,小田没有得逞,是因为杨在其权力场中处于强势,小田则是其所在权力场中的弱势,周边人对他们的态度当然不同。显然,至少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传统的结构仍在起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也泄露了传统衰落的信息。它们都破坏了伦理的边界:在小田的圈子中,大胆突破想象的暂时还只是他自己(不过在同时代更大的背景中,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私奔的事并非特例,至少在小说中如此。小田「学过点文化」,是否直接间接受到新文学或新思潮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杨西亭的例子中,虽然敢于行动的仍是少数人,但多数人的纵容不啻对此投下了一张赞成票。
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大家心头有数,都会把言行控制在安全的地带。但也有少数非凡人物(取其广义,无论褒贬,比如,赌徒也可以是「非凡」的),专做不一般的事业,行为尺度较常人为广,可是仍有限度,越过某条界线,就不再敢为,甚至不再敢想,这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终极边界。在边界沿线搜索,看到的当然都是一个社会中最偏颇的面相,不是常态;可也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确定某一社会道德水平的捷径。比如在有的社会,即使十恶不赦的人也会不齿于对手无寸铁的妇孺下手;在有的社会,许多「平常人」也会有各种理由论证这种举动合理合法,大快人心。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显然高过后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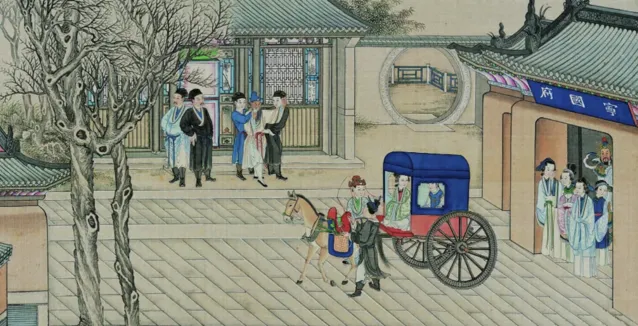
图片出自【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
不过,道德边界只是三条重要的社会界线中的一个,要理解它,必须将这三条界线合观。这三条界线,我们姑且称之为最高的道德指标线、道德底线和道德边界线。道德指标线是指大多数人做不到,甚至也并不努力去做,但对于少数能够做到的人却感到由衷敬服的标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最高理想所在;道德底线则是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违反的界线,比指标线的要求低了不少,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中最流行的言行尺度;至于道德边界线,则是连少数先锋或不法之徒也不敢逾越的界线,或曰底线的底线。
这三条线的距离往往相差很远,但它们都是可变的,彼此之间也总是处在互动之中。一般说来,道德边界线设定在何处,取决于社会普通的规范底线,后者又常常受到最高道德指标线的制约:有些要求虽高,难以落实,公众却能普遍认可其价值,这比如会导致他们将自己的日常行为锁定在尽量接近指标线的范围内;少数人既然生活在多数人中,即使「不一般」,却还是逃不过「一般」的影响。如此,这三条界线从高到低,形成了层层制约关系。反过来说也一样,道德底线乃至边界线也决定了一个时代最高理想的高度:少数人的边界线太低,「无法无天」,逐渐地会拉低全社会的言行底线,此时即使有「圣人」出来,也不能不向之妥协,标出的理想境界未免大打折扣。所以,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面貌,是这三条线随时「协商」的结果。
这三条线中,道德底线为多数人所遵行,是一个社会最稳固的部分,但也往往因为涉及面过宽而考索不易;道德指标线和实际情形相差太远,一不留神就容易模糊观测者的视线;要考察变局,从道德边界线着手不失为便捷之方,只要记住它们是边界即可。它们是极端的,因此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也往往是偶然的、边缘的,然而,「金风未动蝉先觉」,时代变迁的消息也往往就蕴藏在这些边缘事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