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探讨的核心,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如何从自身出发,如其本然地、不被歪曲地显现或绽现出来。分析海德格尔「在世存在」思想的结构内涵及其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蕴,是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重要一维。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此在被海德格尔置于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以至于人们对隐含在其中的「人类中心论」立场颇多微词。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个‘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恰恰唯一地竭尽全力去指明:处于‘中心’的此在之本质是绽出的,亦即‘离心的’(exzentrisch)」[1](P189)。所谓「此在之本质是绽出的」,意思是说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的生存是「绽出之生存」(Ek-sistenz)[1](P380)。绽出之生存意味着「站出来」、「出离自身」,而到存在之真理(存在之澄明)中站立。此在之绽出又是先行在「此」的绽出,这个「此」即世界。也就是说,此在作为绽出之生存是从世界(此)中来,到世界(此)中去的生存。在这里,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是以某种颇具危险性地站入「中心」(作为「中心」的此在)的姿态来反「中心」(作为「中心」的主体),由此展开了他的生存论分析,即此在 「在世存在」、「向死存在」及「四方游戏」的基本结构分析。

【存在与时间】——[德]海德格尔
一、「在世存在」:此在的整体性生存论结构
「在世存在」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英译Being-in-the-World)的简称,是海德格尔用连字符将四个德文单词连接起来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和论证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最具启发性之处,也是海德格尔此在分析的核心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世界之中存在’源始地、始终地是一整体结构。」[2](P209)这个「在世」的概念整体「总是已经」先行设立,是此在的先天机制。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此在的存在就是一种「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2](P222)理解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整体性生存论结构,须从以下三个构成环节来把握,尽管这三个环节原本不具有可分性:1、何谓在世界之中的「世界」?2、「谁」在世界之中?3、「在之中」本身意味着什么?对于环节2的问题,我们已经知晓这个「谁」正是此在本身,因为此在「向来已经」是在世的,此在之绽出是一种先行在世的绽出。此在之所以是一种「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因为只要它作为此在而存在,它的本质机制就包含于「在世界之中存在」中。由环节2勾连出的环节1和环节3,由于「在之中」又只能站出并同时站到「世界」中去,所以环节3又与环节1相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一性概念。我们不妨先澄清环节1中的「世界」概念,进而通过环节2将环节3的「在之中」的意味揭示出来。
对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世界」,我们显然不能将之理解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实际上,它被作为「现象」描述出来的意义结构。「根本上是现象学的世界概念构成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桥梁。」[3](P97)现象学的现象描述方式是显现的,且「世界」概念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包括物、自然物和各类价值物等)根本不相关联。也就是说,尽管存在者就在世界之内,却不能把「世界」看作是存在者之规定。对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无论是从存在者层次上加以描述,还是从存在论上加以阐释,都无法触及到世界现象的边际。「世界」在这里并不指一个作为各种存在者之和的共同世界,不是指此在被抛入其中并在其中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日常世界,也不指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之物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的主观世界,而是指一般「世界之为世界」。「世界之为世界」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它构成一个生存论的环节,因为「在世」是此在的生存论规定,而「世界」是此在本身的一种性质。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哲学由于将「世界」解释为「广延物」(resextensa)而走到了世界存在论的极端。笛卡尔的「广延物」是空间性的,未回到更本源的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性」,遂成为二元论思想的开端。
惟有回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而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规定中,「‘世界’根本就不意味着一个存在者,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而是意味着存在之敞开状态。」[1](P412)我们已经指出,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的生存是「绽出之生存」。人(此在)站出到存在之敞开状态之中,存在本身就作为这种敞开状态而存在。「‘世界’乃是存在之澄明,人从其被抛的本质而来置身于这种澄明中。」[1](P412)当然,作为存在之澄明的「世界」也不是单纯一成不变的沉寂状态,也就是说,它绝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可供我们打量的对象。相反,「世界」是活生生的、动态化,它像七彩的光束一样不断变化、重组、分散、聚集,又时时刻刻照耀着世内存在者,使其得以显现并获得意义。
以上通过对环节1中「世界」概念的阐述,我们同时也已经明确了环节2的那个「谁」,即作为此在的人在世界之中,并参与了世界意义整体的建构。接下来该对环节3,即这个「在之中」进行一番阐释了。对于这个「在之中」(In-sein),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与生存论的方法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这个「在之中」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现成物在另一个现成物之中,这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方法。就其源始意义而论,「之中」(In)根本不是指一个现成物在另一个现成物中的空间包含关系,而是包含着「居住」(innan-)、「逗留」(habitare)等含义。而「存在」(sein)的第一格「bin」(我是)又联系于「bei」(寓于),因此「我是」或「我在」就是指:「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之所依寓之、逗留之」。而「存在」(sein)就意味着:「居而寓于……」,「同……相熟悉」。[2](P63-64)因此,作为一个生存论范畴的「在之中」(In-sein)意思就是「同……相亲熟」(Vertrautseins-mit)。在此意义上的「在之中」就反拨了形而上学的主体—客体相分离的认识方法,因为此在与世界是源始统一的、亲密无间的一体,此在源初地就同世界相「亲熟」,「居而寓于」世界,「依寓于」世界而存在。这实际上挑明了人与自然环境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源始生态关系。
由此可见,此在生存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是由三层结构构成的:一是「先行存在」,即此在先行于自身而存在的「生存」(即「筹划」,意指此在作为一种「可能之在」总是不断超越自身);二是「已然在世」,即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之中的「真实性」(也即「被抛性」,作为此在必然性的先天机制);三是「共存于世」,即此在与其他存在者(包括他人)共同「在世」,或者说此在「寓于世内存在者与他人共在」的「沉沦」状态(现实性,日常此在的存在方式)。这三层结构构成了作为整体性的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基本结构。换言之,存在者先天地就处在与天地万物的原始关联和往返交流中,这种与天地万物先天的、本源的、相融相契的共存关系,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也不依赖任何认识而存在。这实际上揭示出,人并不是把世界作为认识对象来认识、把握、筹划、算计,而是把「在世存在」作为此在的一种原初的生存方式。不论是「先行存在」,还是「已然在世」,抑或「共存于世」,都在揭示这一点:「在世存在」并非时序上的先后关系,不是说人首先存在,此外再与世界发生另外一层的关系;也非空间上的包含关系,不是如同在一间大屋子里似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又非时空上的跳脱关系,即不是说人有时处在世界之中,有时又能够脱离于万物、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人先天地、原本地就已经生存于世界之中了,并且这种在世存在的敞开状态无所不在,它是人的本性,是人生存于世的本然处身状态。
二、「向死存在」:此在「在世存在」的边缘境域
基于此在「在世存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海德格尔同时还引入了时间性的思考维度,通过在时间性维度下对此在进行分析,以达到从时间来理解存在的目的。这也就是【存在与时间】中从此在存在的意义(时间性)到一般存在的意义(时间)的前期基础存在论思路。从时间性的维度上来看,此在存在于世的终结,就是死亡。正是由于与死亡有某种关系,确切地说,正是此在先行进入死亡的「向死存在」,它才能赢获其「操心」的「整全」,如此这般的此在的生存也才能成为一个整体现象。
对此在在世的现象分析已经揭示出,此在生存是一个在世存在的整体现象。这一整体结构又可统而称之为「操心」(Sorge,或译作「忧心」、「烦」等)的整体结构。问题是,此在又如何具有「操心」的整体结构呢?也就是说,「操心」如何才能获得并成为它的「整全」(Ganzheit)呢?这便涉及到了「向死存在」(Sein zum Tode,英译Being toward Death)的问题。从时间性的维度上来看,此在存在于世的终结,就是死亡。正是由于与死亡有某种关系,确切地说,正是此在先行进入死亡而存在,它才能获得其「操心」的「整全」,如此这般的此在也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以来,死亡现象作为此在的终结,并不是简单的停止生活,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或与生存无关的毁灭或结束——而总是别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它不是某种东西(不是「什么」,即不是某个对象),甚至也不是死去的过程,而是朝向死亡而存在。「对于此在,死亡并不是达到它存在的终点,而是在它存在的任何时刻接近终结。死亡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此在一旦存在,便肩负这一方式……」。[4](P45)因此,死亡之于此在,并不意味着此在到了尽头,到了它存在的终点,而是意味着这一在者处于为终结而存在的方式中。
死亡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并且,死亡是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此在必须亲自把它担负下来,它是不可让与且无法替代的。任何人无法替我去死(它是我不可剥夺的财产),也没有人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在死亡中,显示出此在存在的「向来我属性」,即唯有自我会死去,且唯一会死去的是自我的这一「必死性」。「生就是死,而死亦是一种生。」对荷尔德林【希腊】诗中的这个诗句,海德格尔阐释道,「由于死的到来,死便消失了。终有一死的人去赴那生中之死。在死中,终有一死的人成为不死的。」[5](P203)透过这一令人颇为费解的阐释,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种死的差异性:一种死与生相对,是生的终止、结束,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死则在这前一种死中刚刚起步——它是不死的。这一过程既不可能,又制造着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2](P297)在此意义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就具有了其完整的概念:它是最本己又无所关联的、确定又最不确定的、不可超越且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作为此在之终结的死亡就是一种永远开放的可能性。在这种开放性的可能性中,此在所具有的「操心」才以「向死存在」的方式获得了整全。然而,在日常的「向死存在」状态下,此在作为沉沦的存在却在死前不断逃逸着死亡。「此在只要生存着,它就确实是在走向死,但却是以逃逸、衰退的方式走向死的。人们置身于万物之中,并且从日常生活的万物出发来解释自身,以逃避死亡。」[4](P49-50)日常沉沦着的此在在死之前对死亡的逃逸和闪避被海德格尔称之为一种「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实际上,此在经常把自己保持在一种非本真状态的向死存在中,以尽可能减少死亡之可能性的显示。但这种非本真状态是以本真状态为基础的。海德格尔正是从日常存在出发,围绕着「非本真」与「本真」的关系把分析推向对「畏」、「良知」、「决心」等此在的在世状态,以探求此在如何向死亡存在而获得其「整全」的方式。
「畏」(Angst)是此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情绪。与「怕」(Furcht)根本不同,「畏」不针对任何具体对象,而是面向作为绝对超越者的存在(即「无」)。畏揭示着无。而这个「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1](P133)此在正是基于「畏」而被嵌入「无」的状态而完成自身的超越。在这种不甘沉沦的自身超越中,此在被一种「良知」(Gewissen)的呼声所召唤而回到最本己的存在。此时,「决心」(Entschlossenheit)就作为此在的一种本真在世状态,以大无畏的精神应和着「良知」的呼声,「先行进入死亡」而去赢获其「整全」。
经过对此在「向死存在」的一番分析,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为此在的一种生存现象的「死亡」,以及此在在面对这种死亡时的态度所具有的意义。「海氏强调个体的有限生存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自己的存在,并且无畏地直面自身的有限,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6](P39)这一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有限性的此在「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自己的存在」,以一种「向死而生」的边缘境域提升生命的质量,从而超越非本真的生存状态而进入本真的在世生存状态,在不断自我完善中获得此在自身的「整全」。另一方面,这一意义还在于,此在只有担负起对他人、对周围存在者的责任,终结所意味着的死亡才是最本真的死亡。换言之,他人之死对我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正是对他人之死负有责任,以至于我也投入到死亡之中。」[4](P44)由此引申开来,我对我生存于其中的生态自然环境也是如此。一种对自然之神秘所应有的「畏」的心态,一种发自心底的「良知」的呼声和责任意识,一种先行进入死亡、从死亡出发而生存的「决心」,不正是一种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方式的体现吗?确切地说,这种思维方式即一种整全性的思维方式,探求此在如何向死亡存在而获得其「整全」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生态意蕴所展现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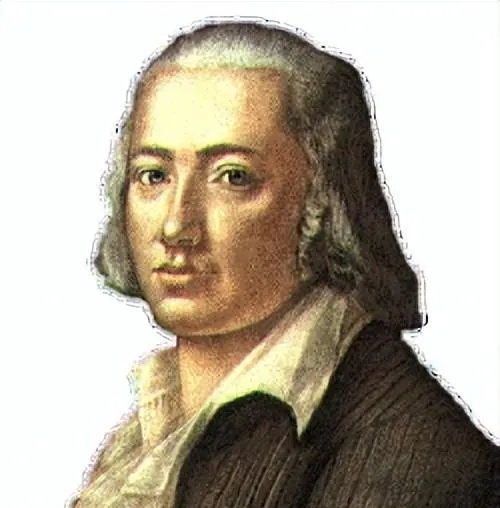
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
三、「四方游戏」:动态建构的「世界」意义整体
对于「世界」的整体意义,海德格尔在后期所作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世界化,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可把握和可觉知的东西更具存在特性。」[7](P26) 「世界世界化」(Welt weltet)是海德格尔的一个独特表述,其意在挑明「世界」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的动态建构性。海氏后期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著名隐喻,即是对这一「世界」意义整体的启示。
在1950年6月所做的【物】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最早从关于物及物化的讨论中引出了天地人神四方世界游戏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将物设立为对象的表象思维方式是对物的掠夺,在这种思维方式统治之下,物之物性不但未得彰显,反而被遮蔽和遗忘了。那么,何为「物之物性」呢?早在1930年代的【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物性因素做了探讨。在那里,他着重批判了三种传统与流俗的物观念,企图通过物之物因素经由器具之器具因素的中介而通达作品之作品因素。但这一道路显然受阻,因为从物到作品并不能揭示艺术作品的本源与艺术的本质。而到了50年代,海德格尔从存在之运作方式,即Logos(聚集)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了物。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30年代对传统‘物’观念的批判到50年代对作为聚集方式的‘物化’所作的诗意运思,这之间有一个思想的演进、深化的过程。」[6](P232)
在【物】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以我们常见之物「壶」为例,指出 「壶的本质乃是那种使纯一的四重整体入于一种逗留的有所馈赠的纯粹聚集。壶成其本质为一物。壶乃是作为一物的壶。但物如何成其本质呢?物物化。物化聚集。」在「物化」之际,天空、大地、诸神与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这四方从它们自身而来统一到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之中。这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其它各方相互游戏。「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Welt)。」[8](P188)世界的映射游戏又被海德格尔形象地称之为「居有之圆舞」(der Reigen der Ereignens)[8](P189)。这个世界游戏中的「世界」与前期此在「在世」、人可与世界划一的「世界」有所不同,在这个「世界游戏」中,天、地、神、人四方聚集为一体。
在这一四方整体结构中,大地(die Erde)承担一切,承受筑造,使我们人类得以居住;同时,它滋养着果实和花朵,蕴藏着水流和岩石,庇护着植物和动物。但大地并不是孤立的大地,当我们说到大地时,我们已经思及了作为整体的其他三方,即它是天空下的大地,服从诸神的命令,并且由人在其上来筑造和围护。天空(der Himmel)是太阳之苍穹,也是望朔月行之处。人在大地上居住,他抬头仰望时看到的正是天空。天空是神的居所,这一「抬头」就包含了对诸神的期待、对超越的向往。诸神(die Gottlichen)即暗示着的神性使者。从对神性隐而不显的支配作用中,神显现而成其本质。正是神性之维使处于大地之上的人抬头仰望天空,进而张开了天空与大地之间的无限生存空间。「神乃人之尺度,人之为人必与神同在,必以神性尺度度量自身与万物,并由此获得生存的根基,真正与天地万物同在,属于天地人神的世界家园。」[9]人以此神性尺度度量自身与万物,才能获得生存的根基并真正与天地万物同在。而人类作为「世界」各方中的一方,被称作终有一死者或有死者(die Sterblichen),这是因为与一般只是消亡的动物相比,人能够赴死。「赴死(Sterben)意味着:有能力作为死亡的死亡。」[8](P187)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死者并不意味着人被死亡所侵袭,而是人有能力赴死,人的存在就是承担起自己的死亡,惟有承担起自己的死亡,人才作为人而存在。人的居住、人的生存就是「向死而在」,在向死而在、向死而生中人筑造着自己的一生。所以只要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持留,人就「不断地赴死」。由此也可见,作为有死者的人是不能离开也离不开天、地与诸神的,这四者源初地成为一体而彼此不可分离。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有一个前后变化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世界」指的是人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即人的生存世界;后来他把这个概念加以丰富并纳入了历史维度,将民族发展的历史在内的生存世界包括其中;而到了后期,海氏更是把这个生存世界的结构概括为「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世界。世界(Welt)又通过世界化而成其本质,但世界之世界化又是无法通过某个他者来说明或论证的,因为这种说明和论证还停留在形而上学的表象思维方式上,而「当人们把统一的四方仅仅表象为个别的现实之物,即可以相互论证和说明的现实之物,这时候,统一的四方在它们的本质中早就被扼杀了。」[8](P188)这四方相互依偎、达乎一体,构成一个柔和的「圆舞」式的世界游戏。这一世界游戏以及游戏中的各方又是由语言所聚集和指示的。「但是,四元却是一语言的世界,如果它是被语言所指示的话」。[10](P245)正是语言使人作为天地人神这四方中的一方而居住成为可能。这里的语言指的是在源初意义上的自然语言。在自然语言中,自然而然的物「物化」,自然而然的世界「世界化」,如此这般的情景才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和谐的「世界游戏」,人也才能在其中(大地之上、天空之下、诸神面前)找到诗意栖居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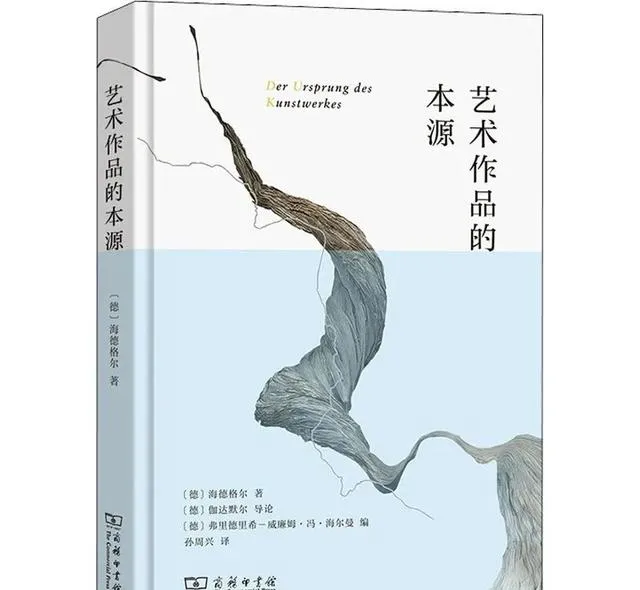
【艺术作品的本源】——[德]海德格尔
四、「在世存在」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
自苏格拉底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后,西方传统哲学与诗学便出现了理性与感性的争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感性在主流哲学与诗学中往往被贬抑,而理性则受到高度尊崇。与此路向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以其对存在问题的独特追思,以其中贯穿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力图实现对主客分离的超越,从而超越主体中心论和逻格斯中心主义。
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虽然赋予此在在领悟存在上所具有的十分触目的「优先地位」,但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处于主体—客体关系之外」[11](P826),是一种「离弃了主体性的思想」,并且「一切人类学和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都被遗弃了——【存在与时间】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1](P400)。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最具启发性之处,「在世存在」模式强调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原生地依赖于将世界整个囊括其中的意蕴的指引关联。而对「在世存在」与 「向死存在」整体结构与具体环节分析,则旨在消弭此在在世界中的主体的优先性,并以「在之中」思维(整体性思维)和整全性思维,实现从实体性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向关系性的存在论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其中已然包含了与形而上学认识论不同的生态思维方式。首先,「世界」不是作为现成物的存在者,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可供我们打量的对象,而是一种具有动态建构性的意义整体。这便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其次,「此在」在世界之中,此在「向来已经」是在世的,此在之绽出是一种先行在世的绽出,这一点也已经打破了主体形而上学主客分离、人与自然对立的知识论世界图式。再次,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机制的「在之中」,进一步挑明了此在不是与物质实体(客体)相对立的思维实体(主体),而是与「世界」打成一片、与世界相「亲熟」、浑然一体地「依寓于」世界的此在,这实则是一种整体性的关系性思维方法,是从实体性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向关系性的存在论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
而到了后期,海德格尔将作为此在的人纳入到「天、地、神、人」四重整体(das Geviert)结构中,大地、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的人这四方从自身而来,出于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共属一体。人并不居于具有决定其它主体的中心地位,人只是四重整体中的一重,四方游戏中的一方。并且,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人是自然的看护者:人不仅生活于自然之中,而且具有守护天、地、人、神四方的职责。这里的守护或看护并非主宰或主导,而是一种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的相对平等关系。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人的栖居发生为对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这一思想进一步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使得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获得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并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和现代科学中对象性思维方式的盛行进行了深刻反思,渗透其中的非对象性思维、平等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等思维方式蕴含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蕴。
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思想还可与儒家、道家思想相互参照。如儒家【易传·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里的「三才之道」既是高扬人道之道,将人放到与天、地并举的突出位置;又是注重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发展之道,天、地、人并非各行其道,通过法天正己、尊时守位、知常明变,人道可与天道、地道会通,达到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的境界。【礼记·中庸】亦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认为达至「中和」之境,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自然发育。而在道家那里,人与世界的先天关联则得到更深入的探究。庄子将先天不与天地相分离的「圣人」视为「天人合一」的集中体现,将其在世界中本真的生存方式喻为「圣人将游于物之所得遁而皆存」(【庄子·大宗师】),而圣人无限开放以至与万物冥然合一的心境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逍遥游】),达到了与天地六气融为一体的本真生存境地。庄子还提出「藏天下于天下」的思想,与「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这种人为地藏小物于大物之中相比,「藏天下于天下」则把天下万物藏于天下万物之中,让天下万物自然而然地存在,庄子认为这才是「恒物之大情」(【庄子·大宗师】),才是与道合一的本然状态。
可见,中国先秦的儒家尤其是道家,在探寻道的问题上已经与海德格尔探寻存在的问题走在了相似或相近的「林中小路」上,「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前者比后者踽踽独行的足迹竟早了两千多年。他们都试图把人的认识从对象性思维、心物对立、沉陷于现成存在者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去探寻更为本源的东西,让人回归到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之处。这既是本性的回归,因为人天生就在世界之中存在,人与自然万物是天然的一体;也是认识的超越,即超越心物对立、主客对立,以非对象性思维、整全性思维观照万物和世界。海德格尔作出这番关于「在世存在」思考之的同时,还曾于20世纪30年代发出了「拯救地球(大地)」的号召。尽管当时并未引起太多认同,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生态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海氏本人甚至被冠之以「具有生态观的形而上学理论家」「生态哲学家」等称号。我们不妨把海德格尔视为早期中国智慧在两千多年后的异域回响,这种回响和共鸣反而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与互鉴中,为当今时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1] [德]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3] [德]克劳斯·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 倪梁康,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4] [法]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 上帝·死亡与时间[M]. 余中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5] [德]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6] 孙周兴. 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
[7] [德]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8] [德]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9] 余虹. 诗人何为?海子及荷尔德林[J]. 芙蓉, 1992(6).
[10] 张贤根. 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11] [德]海德格尔. 尼采(下)[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