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
32岁的杂货铺老板,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在彻底恶化前,他用一次次的流浪与自我放逐,对抗命运的虚无。在蛮荒之地,他找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准备到山里建个四合院隐居酿酒。
我太爱喝酒了,喝醉了醒着不是醒着,梦也不是梦,悬浮在一个高于现实又低于梦的维度里。可现实总跟理想过不去。疫情虽然没有带走我的命,但是带走我不少钱。
九月份,我终于把经营多年的两个杂货铺转让了,滋味很复杂,即是解脱又是失落。
我和箱子们一起拥堵在三姐家的小屋里,撑得小屋要吐。属于我的只有眼前这些箱子,里面具体装的啥我也忘了,反正都有用,不过没有也没关系。
我用屁股使劲挤了挤床上堆满的杂物,呆坐在床边看着箱子们,抽根烟吧。想想这些年旅游和玩的花销在这小城换个两室一厅是够的,再想想今后何去何从?总不能无所事事吧?再抽根烟吧。
马向平的电话结束了我的多愁善感。他是北京的藏文化学者,也是苯教弟子。他要去阿里寻找古象雄遗址和壁画,也知道羌塘能让我魂牵梦绕,问我去不去?我让他等我考虑考虑。
「弟呀。姐都快急死了,你还得几天能把楼上货架给姐装上啊,货都到家了。再不摆出来就过季了。」三姐愁眉苦脸地站在门口说。
这活儿我已经磨蹭两天了,按照现在的速度起码还要一周。我很不情愿地拿起手中的小锤儿,有点沉,比划两下又放下了,总觉得平板手机上有点什么得看看,屁股一下就被椅子吸过去了。
马向平发来了这次长途旅行的文案,看着那些诱人的西藏地名我不知不觉地笑了。摸摸良心问问自己想不想去?相当想!盘算着买房盖房钱不够,跟他走,够!
小锤儿再次上手分量就不一样了,它又轻又敏捷。小锯儿锯一下木板心里就念叨一遍:羌塘!阿里!
两天一夜几乎没睡,干完啦。
出发前我妈有点担心。以前催婚,我说再催我就出家当和尚,她说我神经病。前段时间,我说想独居山里,潜心酿酒,她建议我去山里出家,起码寺庙人多安全,我没干。
「妈。我要走了你不说点啥么?「
「嗨!你现在走我都不在乎了。」她忽然想到什么,接着说:「妈跟你说让你去当和尚是跟你闹着玩呢,你去了可别真留那不回来。」
「我神经病啊,我才不出家呢。」
「那我就放心了。」
同行四人一车,北京出发。另外两个我都不认识,一个搞摄影的姚旭东,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天津朱玉海。

进藏后,我们先去马向平皈依的寺庙,他把这当成第二个家,想在这里多住几天。我跟他来过一次,被这里的气质深深打动。

图 | 水鸟
到了海拔四千多的寺庙,我高反了,头很疼,眼睁睁地看着玉海像野牦牛一样各各山头撒欢,还让我看它在山头光膀子的照片,他的胸毛茂密的像黑胸罩,让我更加断定它就是没进化好的野牦牛,不然哪来这么强的身体素质?
画满壁画的屋里,六人有三个时不时吸一会儿氧气,走路都吃力何况爬山。晚上玉海又说外面的星星超好看,我让他离我远点,以免我的脑袋爆炸崩着他。
很冷。我是穿着羽绒衣裤进羽绒睡袋的,高反入睡是个技术活,加上另外五个老爷们打呼噜磨牙放屁和高反的呻吟声,我放弃强求不来的睡眠,只想撑住,撑着撑着就昏了过去。
好在第二天头就不痛了,看到的天也蓝了,云也白了,诵经声也神圣了,还在风里闻到了酥油灯的藏味儿,甚至挑起了给十几个内地弟子做饭的要务。接过这个要务后我就为难了,调料只有油和盐。硬着头皮干吧,他们说熟了就行。
「师兄。这个米最多只能洗一遍,菜也是,好像之前老姜都不洗的,这里的水实在太珍贵了。大部分是从山下背上来的。」瑶瑶心疼地看我把第二遍洗米水倒掉说。
瑶瑶是一名上海医生,牙白眼亮温柔善良,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过很多种宗教,最终皈依在本寺师傅门下。她每年都会攒假到这里修行一段时间。
缺水是大问题,外来的弟子都很自觉地尽量不用水,脸也不用洗,没人笑话,这里人都这样。可我必须用湿巾擦擦脚,我很惭愧。
「兄弟。要不你还是洗洗吧,我头太疼了。」我对床的于大哥说。
之后几天,我是唯一够资格泡脚的。有人看我泡得舒服也想泡,被拒绝,他不够臭。
于大哥在我们前一天到,高反非常严重,可怕的是还伴有高烧,他的同伴周律师多次想带他下山休整好再上来,他坚决不下山。来一次寺庙不容易,死不了就挺着。可屎尿挺不住,他艰难地把小便放进大瓶里,又顺手放在我俩床头。
「大哥,你要是不把它拿走,我就把脚调过来。」我看了看尿桶又看了看憔悴的他,不忍心也说了。
他一听,艰难地坐起来,桶挪到床尾。
在这里,屎尿很让人头疼,厕所离我们住处有两百米远,旱厕通风不好,那味道的冲击力简直是一种酷刑。尤其晚上入睡前,总是憋到不得不才去解决。第三晚我就很挣扎,那种感觉介于不去不得劲儿,去了不值得之间。
「一起吧。有些事儿是拖不了的。」周律师看懂我的意思说。
几年前,周律师因非法持有枪支被拘留,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在贵州支教期间认识一位师兄,之后被寺庙的一切感动,做了一个多月义工后成为师傅弟子。他对这里很熟,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爬到山腰拉野屎,一边拉一边看星星。
「你不能总蹲在一个地方,适当换个位置更好一些。」周律师说。
「嗯。你真有经验。」
「在环境中成长和学习嘛。你得去适应环境,不能让环境适应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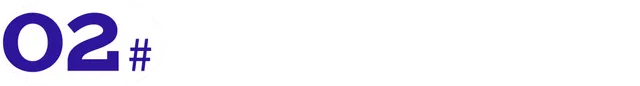
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第四天跟着玉海还有一位香港的女师兄去转山。她在山上住了有些日子,我请教她有信仰是什么感觉。她说不清,但是觉得很神奇,是种缘分。她去过很多寺庙,一直找不到想皈依的师傅。偶然到这里,被师傅的博学和仁慈打动。
母亲去世时,她在自家佛堂为母亲诵经超度,怎么也找不到诵经的感觉,想到远在西藏的师傅,想到寺庙的艰苦环境,突然有了感觉,她嚎啕大哭,然后迫不及待奔赴西藏找到师傅皈依。
转山回来后,过了中午吃饭时间,我和玉海迅速抵达厨房,用高压锅压了一锅面条。着急了,没等放完气就开盖了,高压锅吐了,半锅面条挂在锅沿和煤气灶台上。我相当愧疚,在这个忌讳浪费的地方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浪费。
在寺庙吃饭餐具都是自带的,不用洗,这里的习惯是舔干净,不会舔就用纸擦。婷婷姐说:「碗好舔,师傅那喝酸奶的杯子才难舔,太深了。」
几天里,我没做出一顿让我满意的饭,可他们都赞不绝口,尤其李师兄(女的),还特意送我几双袜子以表谢意。李师兄本次来是将自己九岁的儿子送到寺庙出家的,听说她的女儿在欧洲上学。这觉悟让所有人钦佩。
傍晚,我坐在厨房门口的长木板上发呆。索巴益西微笑着撩起僧服坐在我旁边。彼此友善的笑意让我们相谈甚欢,临别时,他约我晚上去看月亮,那天是九月正中。
皓月当空,我们悠闲地走在转山路上。
「心里有佛是一种什么感觉?佛真的存在么?」我问。
「你是真实存在的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了想说:「也许吧。」
索巴益西指着星空问:「那里有多远?」
我点点头说:「没有边际。」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么?」
「也许吧。」
「还有真实存在的,你看不到也摸不到。」
「什么呢?」
「你的心。」
我愣住了。心里想着,二十一岁的他平时都学了啥?单单脸上淡然的微笑就是一门学问,这里的僧人几乎都有同款微笑。
路过天葬台时他笑着建议我过去躺一会儿,我没去。继续往前走。静静的夜空没有风,远处传来两个转山女孩高唱的八字真言,嘹亮的歌声回荡在群山中,在钟声的映衬下格外动听。
「你有梦想么?」我问。
「有的。就是好好念书,现在念书是最重要的。」
「做一辈子和尚么?」
「是的。」
「怎么看我们俗人?」
「很可怜。」
「嗯。被欲望逼使着不断追求,永远滞留在不断追求的过程里。」
「你们什么都没有。」索巴益西保持微笑地说。
「你不想住大房子,开豪车吃大餐么?还有很多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吃穿都是喇嘛供的,什么都不缺,只有学习好才是最好的。」
「对外面的世界不好奇么?」
「我去过拉萨,林芝,很吵,我不喜欢。我回到村子都觉得吵。」
「所以你们是要把欲望修没了么?」
「要有知足,知足才会幸福。」
「那生理上的欲望怎么修?」我问完不好意思地笑了。
「念经,还有一个咒语是可以的。」
不论我问什么,他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满足的微笑,这状态让我感觉新鲜又陌生。
「我最后是要修成无我,那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他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又仿佛触碰到遥远的梦想。
「那是什么状态?」
「就是只为别人好。」
「你避免不了被伤害。」
「没关系的,只要他好就可以了,所以非常难,我现在还不行。」
我不是被他的话打动的,而是他真诚的态度。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比如生活用品之类的。」
「真的不用的,我什么都不缺。我爸爸说你该换个手机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还可以用,可是他就给我买了。家里也会供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我们又走到一座山后,不远处一个人背着手一动不动地仰望月亮,像是在沐浴月光。他是即将成为堪布的巴登思根,堪布相当于佛学院的研究生或博士学位。我们三个约好了明天他们下课后去爬山。
第二天下午,我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在山头感受那未必是真实的存在和预料之外的幸福感,慵懒地躺在草地上,闭上眼睛,每人叼着一根草棍,笑容久久绽放。
晚上,我被邀请到索巴益西的寝室作客,我带了一些零食,准备继续追溯他们幸福的理由。
索巴益西的房间光线很暗,两张很窄的铺盖就铺在地上,看起来很不舒服。我到的时候,他和室友扎西正在煮挂面,面里有几根青菜。我猜他一定把所有的零食都摆在茶几上了,因为这房间里贫瘠得除了经书和一面念经用的鼓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几颗苹果是李师兄今天送给他的。他还用一瓶廉价的维生素E护肤品招待我,也是别人送的。
扎西说他之前住的房间有一只老鼠。赶过几次老鼠不走,于是装进盒子里骑摩托送到山的另一边,几天后老鼠又回来了,索性用鞋带拴在柱子上成了室友。
我们聊得很开心,可我心里百感交集。这心情直到离开很久才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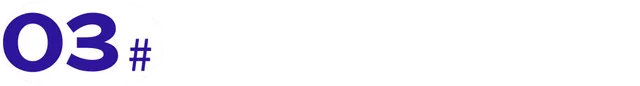
漫长的旅程,我每天都会被荒凉的奇特风景震撼,后来就麻木了。更多时间,那些壮美的景色都在车窗外匆匆流过,每天十个小时左右车程,疲乏的时候会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走这一遭?明明早知道很辛苦。
陌生的蛮荒之地,意外是一直提防的,但能防住也就不叫意外了。马向平通过关系找了位僧人去寻找修行洞。
天气和心情都风和日丽。附近有很多山洞,路过就进去看一眼,偶尔被飞出的野鸽吓一跳。最大的洞口有点像女人的生殖器,陆续飞出很多鸽子。我有点担心在我头上拉屎,万万没想到,后来竟能肆无忌惮地躺在屎上享受。

图 | 旅行途中
在洞里的岔路口,僧人淡然地用手画了一个圈,语言不通,但我懂,走一圈呗。通道逐渐向下越来越窄,先弯腰再跪下,退?有点难,继续?又不想趴着爬。
我还是跟上了,钻下去的过程,我在心里讲脏话了。没想到钻出的不是出口,是一个密闭小空间,手机灯一关伸手不见五指。僧人手指的出口看起来特别扯,洞口小得头插进去就堵死了,我有幽闭恐惧症,一下就炸了。马向平先后试了几次,都被卡在洞口,急得我很想上脚蹬。很快呼吸开始急促。
「快点!缺氧了。」我惊慌地喊。
马向平终于不顾相机死活,随着「啊」地一声,洞口吞没了他的两只脚。
「玉海!拉我一把。」马向平首次发出兔子急了会咬人般的呐喊。
最后剩下最胖的我,没有退路。我已经忘了爬出来的过程,记得一直在拼命。三四米的隧道像极了产道。挣脱后,我躺在出口的鸽子屎上尽情呼吸卷起的干屎灰。大脑酥麻,浑身瘫软。
第二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是转冈仁波齐神山的两天。我期待过头失眠了,凌晨四点出发,而那里九点才亮。我们的摄影师没参加。
说好了我和玉海不等马向平,他有脚伤太慢,我们在一起就是现实版龟兔赛跑,等我们到了再开车接乌龟。可是走进荒原后,我们有点担心乌龟被狼当早餐,就走走停停地等。
好在有星空,干等不无聊,时不时还滑过几颗流星。不知道是不是我视力的缘故,感觉这儿的星星特别大,特别多,有一种果树大丰收的感觉。
「星星大跟你眼神儿没关系,我看也大。」玉海仰着头说。
天还没亮我就困懵了,不敢有半点走神,手电的光圈之外很有可能是悬崖。因为马向平是苯教所以我们反转,陆续迎面看到很多转山的藏民。等待是寒冷的,好在有热帖贴在屁股上才抑制住痔疮长大。等着等着,玉海的手电光就消失在山边了。我也暗下决心,天一亮就抛弃这只老乌龟去追玉兔。
我低估了转山的难度,中午困得走路不走直线。坐在大石头上按了一百多下打火机也点不着烟,三步一趴朝拜的藏族小伙全看在眼里,扔给我一个打火机。我递给他烟,他摇摇头只顾念经继续朝拜。他们爬过的土路有明显的一道道曲线,不追风,不赶景,一点点向前移动。
到了下午,我有点害怕心脏停止跳动,它太微弱了。干草地被阳光晒得正暖,索性一头扎在上面一动不想动。第二次扎在草地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眼看着草地不错,心里却不停强调着坚持,一不小心就栽倒了,一不留神又睡了半小时。到营地的最后一公里我大概用了三个小时,五步一喘十步一歇,艰难前行。
营地的住宿条件很差,平常可能倒给我钱也不会住那么脏乱差的多人房,可是只有这里能保命。电话里,马向平的声音奄奄一息,很抱歉我无能为力,只能加油。

图 | 房间
等马向平的时候,房间就住满了,最后换了双人标间,是个仓库,没有灯,墙缝和门缝能挤进来月光,捎带一缕缕寒风。
马向平的状态很糟糕,他发烧了。我让他多喝热水,他不好意思喝,因为我得给他倒尿瓶。黑暗中我们也不聊天,我在想这一切图个啥?估计他在想着活下去。
一只大老鼠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我很想赶走它,花一百块钱都行,但是我没动,竟然睡着了。
那一夜无梦,是个好觉,第二天满血复活。马向平也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了。我背着包,依然走走停停地等他。爬上海拔五千八的垭口不是件容易的事。
「兄弟。你最好在那边绕过去,坡度会减缓很多。毕竟只有两条腿,不是四驱的。」一个内地转山人对我说。
我看了看不止多走一倍的路程,举起两支登山杖大口喘着气说:「我四驱的。」
在垭口等了马向平半个多小时,我挨个给家人发了视频庆祝胜利。不妙,头越来越痛,烧纸和供香的烟加速头痛。马向平坐在石头上,用大口呼吸的方式给命充电,充完电,他还要烧香,还有挂经幡等仪式要做,我知道务必快点下到海拔低的地方,没等他。
后来,马向平说看到我蜷缩在草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吓坏了。我只是睡着了,醒来后才发现,头顶不到一米处有一坨人拉的尚未风干的野屎,妈的!记得睡前还吃了块压缩饼干和一罐红牛。
下午在补给点喝甜茶等马向平的时候遇到一个内地游客和一个藏族向导。他们准备翻过垭口到我昨晚住的地方,我极力劝他明天再出发,以我的亲身经历,天黑之前是不可能到的,可他的向导却说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游客看到我的痛苦陷入纠结,不知道该不该走。后来我走了,他还在纠结。
那晚我发烧了,玉海要开夜路上来接我们,我虚弱地坚决没让,实在太危险,我不能为了保命拿他的命去冒险。

进藏一个月了,我对广阔的藏地越来越习以为常,心情不会为风景有过分激动。每天依旧是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却感觉很休闲。
我们去了很多寺庙和古遗址,去过唐卡画师的画室,见过几位活佛,吃了很多牦牛肉和羊肉,甜茶、酥油茶。麻木到昨天还在尼泊尔边境看雪山,今天忽然就在和印度接壤的湖边喂鸟了。直到进入羌塘领地才回忆起无数个夜晚听着杨柳松独自横穿羌塘的那本书【北方的动地】。
两驱的车不要妄想走进羌塘,我们试了,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推车是件很炸肺的事。油一定要加满,不然心里空落落的。别指望导航,它也懵,有一天我们是凌晨十二点半才找到水泥路的,那是一阵豁然开朗的欢呼。
环当惹雍错途中我们的车在一片软沙上失去控制,直奔沟下冲去,万幸那一段沟不深。要不是我平生经历过两次翻车也不会这么镇定,剧烈的颠簸中我已经做好了翻车准备。好在玉海开车本领强,它没翻。
车停以后,马向平堆在座位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排的靠背。
「摸摸毛吓不着。」我摸着他的头说。
他笑了,笑了事儿就不大。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从羌塘的此端走向彼端的过程,那一定是和孤独最近的接触,在生存的边缘感悟人生,找寻极端的边缘。当我身临其境,这里的荒芜远远超出我浪漫的想象,我是如此渺小和脆弱。
区间测速让我们不得不在荒野里等一个小时。下午羌塘的风很大,我独自站在风里遥望羌塘的远方,于是走了进去,走到车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的位置。躺下,感受和这片土地接触的感觉。心里想着「爸。你放心,咱俩最在乎的就我妈,其它追求都次要。」想到这很快起身往回走。
「你干嘛去了?走那么远。」玉海问我。
「刚神经病犯了。」
「太危险了,遇狼怎么办?你都看不清。「马向平说。
「神经病会怕狼么?竟说那让人后怕的事儿。「我又回头看了眼荒原。
接近孤独需要莫大的勇气。我该如何把承受孤独扭转成淡然接受呢?它离我那么遥远又触手可及。
五月份,我带着三年前的病例又去医院了,大夫看完我的病例好奇我又来干嘛?很遗憾,医学发展赶不上我视力恶化的速度。但这次我知道病名了——Stargardt(一种少见的眼底黄斑变性)。
这病是一点点变差,已经十几年了,才混上视力三级残疾证,让我无事可做,但距离真正的糟糕还很遥远。更让我难受的是整天躺在床上思考我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想这些比感冒还难受,是正经八百的精神病。
张大笑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有病——胰腺癌。我知道这事儿后心情很不好,他就用夸张的大笑安慰我没事儿。旅行出发前我们喝了点酒,在他家二层楼的天台上争论我是不是神经病?我说我不是,他咬死了我有病。
「你这眼神儿你找死去啊。你不是神经病是啥?」张大笑说。
「我就是不想被安逸活活给溺死。」

图 | 寺庙老僧
回到家后,张大笑点了一桌子丰盛的菜给我接风。他是个大忙人,想在癌细胞扩散之前多给家人攒点钱,他不太关心我都去了哪些地方。
「玩完之后打算做什么?总不能啥也不干吧。」张大笑一脸严肃地问。
「学习酿酒。」我丝毫没有犹豫的回答。
「神经病。」
「我现在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酿酒是个体力活,感觉上生活质量下降了,但我接受现实。」
「你接受个屁。」
「以我现在的视力状况起码体力活我还能干几年。一想到余生喝的都是我酿的好酒,还有啥能比这更让我兴奋的呢?我不会因为无所事事失去生活重心。更何况,酒越老越值钱,而我越老越瞎。」
「你根本不了解酿酒,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之前也觉得难。但我相信我能爱上酿酒的过程。造酒曲就是受孕,发酵是在胎中的过程,蒸馏是分娩,入窖才是成长的过程。我要给它们创造一个纯净的世界,远离喧嚣,在最单纯的环境里成长。等我想喝的时候就跟它们融为一体,在我体内完成终极进化,我们的融合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受,它叫幸福感。」
「呵。」张大笑不屑地瞥了下嘴。
「不给你喝。我的酒只给有能力让自己幸福的人喝,那些糟糕的人喝了我的酒我会很心疼,因为酒能让美好更美好,也能让糟糕更糟糕。你得好好表现才给你喝。」
「等你酒酿出来给我扬坟头上吧。」张大笑冷笑着说。
「没发生的都是未知,只要对未知还有期待就没有绝望。活着就想好好活着的事。」
我很惭愧剩了很多菜,以前没有这么惭愧。之后的两天还是跟不同的朋友胡吃海喝,他们都过着有房有车却想换房换车的生活。每次结束后,看到剩下的美食我都能想起那个清晨寺庙老僧人的背影,他安详地坐在崖边打坐,面对一片云海和经幡。(纪永生)
(摘编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