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人类历史上长期是小众活动。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火车汽车蒸汽机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相继投入运营,旅行才逐步大众化。19世纪中叶,当近代旅游业先驱、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创办者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开始在他们国家提供火车游览行程时,首批游客多至六百人。
现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派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遥想当年这一变化时说,那些曾经享受着旅游特权的上流人士大概会被这样的人潮吓退。(参见[美] 彼得·奇尔森、[美] 乔安妮·B.马尔卡希【旅行写作指南】,文汇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
但布尔斯廷生前恐怕未曾想到,他谢世后一二十年里,在东方的中国,旅行成为人民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些人的刚需。从前出国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而今几乎每天有许多人在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自有旅行,便有记录旅行的文字。旅行文学从来是不少作家、旅行家乐而为之、雅俗共赏的文学品种。文旅消费的日益增长,促进了新时代我国旅行文学的日趋繁荣。
文汇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旅行文学书籍,如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 深入中亚大地的旅程】(2020年7月第1版)、【午夜降临前到达】(2021年8月第1版),及彭英之的【丝路北道】(2023年8月第1版)等,都颇受出版界和读者好评。刘子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作家、记者,而彭英之出身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多年从事编程建模工作。这位「理科男」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

2017年,彭英之和他的旅伴行走的丝路北道,经过中亚五个「斯坦国」,也是刘子超七年前的游历之地。
中亚地貌壮观,历史厚重,文化灿烂,故事动人。他俩在书中都展示了所到之处现实经济社会状况和自然人文景观,追述历史事件、人物,聊发思古之幽情,更多是当下之思考。两者内容各有侧重,论作者的心气,作品的艺术性、思辨性,在伯仲之间。
彭英之的自序,提及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当年坐在古罗马遗迹中沉思时产生的冲动,激励他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彭在丝路旅行期间,也曾试图找到让他决心写一本书的时刻。「在这一场不停向西的游历结束之前,我已经决定为这条名为‘丝绸之路’的古路留下一份属于当代的记录」。
刘子超说,旅行文学要「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文学作品的文字表述风格不同,都应该是「精致」的。刘子超强调这一点,旨在将旅行文学跟「旅行攻略」、旅行记录「流水账」相区别。
与【失落的卫星】相似,【丝路北道】文字之精致也并非仰仗华丽辞藻,而是凭借观察力和文化底蕴,融叙述、描摹、抒怀与议论为一体,貌似平常的话语中显露微言大义。笔者在阅读这份「记录」的过程中,油然感觉到:「精致的文字」每每通过各种对话留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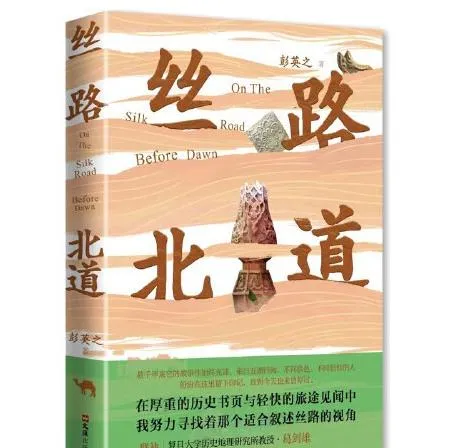
这里所谓「对话」「交流」,英语中communication可作其对应词,emotional communication指情感交流。旅行文学中的对话和交流大致包含旅行者与山川对话,与人文景观对话,与当地人对话。
【丝路北道】中的对话、交流内容丰沛;值得一提的是旅队内部的交谈沟通,为一般旅行文学作品所罕见。限于篇幅,撷取少量例子为证。
与天山雪峰「神性」的交流
在刘子超的书里写到他遇见的一男一女两位来自瑞士的大学生,他们来到「中亚的瑞士」吉尔吉斯斯坦作「文化之旅」,他们觉得这里的天山比阿尔卑斯山更「野性」,像几倍年前的阿尔卑斯山,没有房子,更没有现代化的舒适设备,但他们看到了闪山水之间的马群。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选自【失落的卫星 深入中亚大地的旅程】
彭英之对向导所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山是最棒的」,起先并不很以为然。但当他近距离见到天山雪峰时,不由得与曾经相遇过的乞力马扎罗山、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安第斯山脉作了比较:
「……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天山雪峰要随和得多。它们在草甸前一字排开,温和坦诚,无处不在,像睿智和蔼的长辈,什么困惑都可以说。」
拟人化修辞延续到进山后述写的感怀: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赞美,甚至带着刹那间的虔诚……这或许是大山的气场。当你抬头看着山,山也低头望着你。这份凝视沉重而安静,叫人不得不将被琐事扯到支离破碎的灵魂重新拧在一起才敢应付……」
这不就是八百多年前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当代天山雪峰版吗? 「野性」「随和」,盖因比较对象不同而见仁见智也。
著名作家陈丹燕在其【我的旅行哲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中指出,在大山大海中,人与自然处在自然本源的秩序里,自然的壮丽与严酷并存的本色及其丰富性,会自在地呈现,「能治愈人类心智中的委顿与迷茫」。她把这种「治愈」功能称为自然的「神性」。彭英之对天山雪峰的感受,乃是对「神性自然」的一种演绎。
我国古典文学中,不只是散文,在诗词中相似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如李白【独坐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青山】的「我问青山何日老,青山问我何时闲……」句,都可作如是观。「神性」无疑是作者所赋予的,他们以自己的情感、思想,发掘了自然景观蕴含的人文精神。彭英之体会到了一直在身边的大雪山简直是「仙境」,天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灵魂,书写时便多次对它「赋能」。
情感互动在碎叶城遗址与撒马尔罕
古代中亚先后出现的汗国、帝国,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唐时期的中国与这一地区有过不同方式的交集。整个19世纪,英帝国和沙俄在中亚的 「大博弈」,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历史样本。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衔接欧亚大陆中部不同地区。它不是一条具体的路,而是「一整套贸易道路网络」,当年,「像一条大动脉为不同地区的文明提供新鲜血液」。
星转斗移,天灾人祸,中亚地区的历史遗址保存得不如人意。当地政府致力于建造博物馆以搜藏、展示历史遗迹。中国游客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交汇处的碎叶城遗址总是要去凭吊的。汉朝在碎叶设立西域都护,唐朝经营西域设「安西四镇」,管理该地区军政事务,碎叶是其一。

碎叶城遗址
在彭看来,「尽管学界不能认定李白生于碎叶城,但这不妨碍国人把思念寄托在这座异邦城市身上……」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座后来落入异邦的名城,早已融入大地,遗址只是土堆,内城仅剩地基。此刻,彭英之觉得天山「不仅看着我们,还看着我们脚下的废墟,似乎在告诉我们它掌控着一切兴盛毁灭」。
无奈、沉痛,心情似南宋时黄机站在长江边北望沦丧的国土:「草草兴亡休问」(【霜天晓角·仪真江上夜泊】)。然而,当转头看到中国使馆的「几位同胞走上遗址里的小山坡,同样带着期待,做足想象」。他舒了口气,「有中国人在,碎叶总不会太寂寞」!
离开碎叶遗址,旅队的小车向山里急驶,彭的思路继续勾连着归于尘土的「足迹和故事」:
「遗忘本是宇宙的常态,记忆才是奇迹般的存在。但拥有长情的记忆正是人类与其他动物间最不同是地方之一。在湮灭一切碾压万物的遗忘面前,与过往建立联系的努力好像无边黑暗中的荧光:微弱,但顽强,仿佛意见最有人性的挣扎。我越来越觉得,‘原来你还记得’是这样动听的情话。我拿出笔记本,记下眼前的情景,留下那些扑闪的微光。」
长情的记忆微光仿佛也在我眼前闪烁,我想:无奈和舒心,都不应仅视为作者的自叹。所有当年与碎叶城有交集的先辈,一定正在聆听这位21世纪中国青年的倾诉,为他的这份感慨而欣慰。
有2500年的历史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是古代帖木尔帝国的首都,「古丝绸之路明珠」。现在是中亚文化重镇、旅游胜地。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列吉斯坦广场
【丝路北道】用了四章的篇幅,介绍了中亚最古老城市之一撒马尔罕古往今来的事与人。城里恢弘的列吉斯坦广场的「形状由三座传统高等学院主宰」。「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座中心广场边的建筑是学校……」。列吉斯坦广场「或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光环,也解释了为什么它能让路过的旅人不自觉地感到渺小」。
作者认为帖木尔「是个不输于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的征服者」,「他一生未尝一败,杀戮无数」,但他对本国的文学艺术家「无比宽容重视」,撒马尔罕的建筑「就连痛恨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折服」。内战和征伐使撒马尔罕失去了中亚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它作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使彭英之们为之倾倒,以至朱总都临时抱佛脚,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孤独星球】杂志中亚特辑里的历史部分。
「建筑可阅读」,撒马尔罕的广场和地标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融入了这里的文化。老城里建筑物的不同蓝色,因「它历史的气质散发着近乎金色的光芒」。城郊的皇陵又一次让他们感叹不已:「这里没有丝毫哀愁,却有说不出的温馨和静美」。「从未见过生死界限如此不明确的长眠之地」。「橙色的光笼罩着一切,把我们也纳入了他们的时空……」
「不自觉地感到渺小」「纳入了他们的时空」,凡此种种心绪,不就是旅人与景观的情感互动吗?
地毯店里与织毯人的心灵交流
中亚地广人稀,从无人机视角看来,「……人是见不大到的……大山、大水、大沙漠和人造地标,雄伟高大,像历史的骨骼,构成一切故事的背景框架。」「但它未能记录到多少个体」。「个体」即人,构成了「丝绸之路血液和肌理」。 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及与他们的交流沟通,是【丝路北道】重要的「记录」对象。该书正文后附有「人物索引」,这在旅行文学作品中还未曾见过。其中出境前后一路上打过交道的当地人有名号的共20个,有一位是地毯店店员萨尔多。
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也属中亚最古老城市之列,彭英之带了几位旅伴在一家地毯店做成了几笔交易。他记录的不只是砍价和付定金,地毯店模样、店员萨尔多的外貌与做生意的老成相,顾客对地毯的辨识、鉴赏,萨尔多与他们聊起「想去中国看看」的愿望……显现了异域文化和常人心理。
「萨尔多是店内唯一站着的人,其他人慢慢匍匐到地毯上,都叫色彩迷了眼……不同粗细的手指慢慢划过地毯的表面,顺滑地画出弧线,碰触着成千上万个线结。那些线结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花了好几个月的生命打出来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时空的喜怒哀乐……使用者的指尖能够触碰到创作者触摸过的同一个点,两个陌生的生命间就此形成一种奇妙的联结。」
与萨尔多是语言的交流,匍匐到地毯上触碰其线结,是与织毯人的心灵交流。
旅队内部随时随意的闲聊
2015年,彭英之的同窗和后来的同事耐森与他开始谋划这场中亚之旅。耐森是个学了多年中文和中国文化,在香港工作的美国人。他对中国文史的了解,胜过他的华人太太。耐森在工位上给一直对中西亚历史文化「极度痴迷」的彭英之发了份提议中亚之行的邮件,措辞近乎谦恭。
彭对这一提议「喜出望外」。次日,半睡半醒的彭在手机上看到耐森发来的「自驾可行性调查」和一些具体设想时,「赞叹不已,想到既然他把宝贵的周末拿出来做研究,我就可以放心偷懒了。于是我放下手机,毫无羞耻地睡了回去」。
耐森的绅士风度和处事认真的品格,彭对同事的信任和欣喜中自嘲的洒脱,都跃显纸上。我对他俩的第一印象,在后文中发现获得了他们旅伴的共情。队员小葛说,跟彭英之出来旅游「会不知不觉接受很多新事物」;「我一直觉得耐森是我们这个旅途里最大的gentleman……」彭问:「你俩要不要拥抱一下……」「他们勾肩搭背地碰了一下,耐森开怀地笑了」。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新华社
旅队十一个男女青年的文化背景不同,行为习惯无疑会有差别;他们中多数人过往的旅行体验都来自发达国家,对中亚相当陌生,他们的观感会不一样;陆路行很辛苦,有可能身体不适、心情焦虑。彭英之是旅队内部的「融合剂」,不时鼓励、启发大家「多聊聊」,这个「小社会」内部相互关心,乐于记录这个「小社会」内部随时随意的交流和观念碰撞。
有位在共享单车公司工作的朱总,是虔诚的行者。他在旅途中不时通过手机处理业务,让旅伴感到不解:「他是在休假呀!」朱总开电话会,「在电话里谈论着效率,谈论着策略,谈论着一些宏大的目标,看上去是世界上顶顶重要的事。
天山在他背后一声不吭,风呼呼地吹,野草发出共鸣,感觉马上要召唤出一些在这里安排过大事的人,可旋即又悄然停息」。对如此「永远在工作」的状态,作者借风和野草的动作,表达了队友们对朱总的调侃。这段描述既可看作自然与人的交流,也可视为队员间的对话,两者水乳交融,朴实而自带幽默。
此行最后一站是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在这里旅队成员将各奔东西,回家或另赴他国。分手前,大家谈论最多的一是依依不舍之情,很温馨;二是走了这些国家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以及遭遇的趣事闹心事。

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的独立柱。新华社
对此,彭英之感喟良多,他写道:「能够走进他人生活并且分享一场独特记忆的,都是宇宙以某种极细微的概率牵上的线,能遇见这些人对我而言,无比珍贵。」年轻人因孤独感而对漫长旅途中的相遇深感庆幸和珍惜,我完全能理解。
钱钟书的【围城】借赵辛楣之口说过一段广受读者称道的话:
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行。旅行时最劳顿麻烦,叫人本性毕现。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结交做朋友。
【丝路北道】中,旅队成员一路上的communication,生动地印证了钱先生的这句名言。
久蓄气芳始得精致
钱谷融先生在诠释「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强调,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文学的这种诗意美的来源,是「对人的信心」。
旅行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旅行文学不仅仅是景观的描述、考古成果的介绍或地理的踏勘,它更需要记录本文提及的人们在旅途中的各种对话与交流,揭示、描述、探索多层面的人性。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关怀人、关怀人性,通过具体的审美形态表现人性的各种情感,并以此来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品质这一文学的核心目的。
旅行文学没有时效性要求,作者有足夠时间对信息作后期处理,在客观事实中融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主观思考,并以想象加持。如资深媒体人邵宁在【不带相机去旅行】(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中所言:「旅行笔记,必须在一个闲暇的时刻,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提笔书写。这时,经过沉淀之后的印象、体验,才会慢慢浮上心头。」
彭英之怀着已有的阅读所得,在丝路北道上行走,身不离笔记本,在游历中温故知新,归来5年之后【丝路北道】方告杀青。之前五年里,作者审视整理旅途笔记、视频,重温相关典籍,通过网络继续搜寻新材料。写作是他再次游历这条通路,并「不断感受到它无穷大魅力」的过程;是他更深入地触碰到了那些活在丝路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通过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所有相关信息经过筛选沉淀、发酵,久蓄气芳,文字方臻「精致」,审美价值更大,认知功能更强。
精致的旅行文学,除了在人们阅读文本时起到审美、认知作用,还能为旅游业提高服务质量、游人养成对话交流意识带来启示。
郁达夫有咏西湖诗云:
楼外楼头雨如酥,
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苏。
虽然传媒已从「读图时代」进入短视频称霸的新阶段,但精致的文字仍然有着照片、视频无法替代的功能。希望有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旅行文学作品诞生!
作者:青山
文:青山编辑:郭超豪责任编辑:邵岭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