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眼中,音樂天才通常在早年就顯露出非凡的天賦,不僅精通各種樂器,而且在作曲、指揮等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展現出卓越的才華。不過,歷史上總有驚人的例外。不會彈鋼琴,沒有系統學習過音樂,甚至拿的是醫學文憑,就是這樣一位曾經的「業余愛好者」竟成了法國乃至歐洲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一代巨匠,他就是艾克托爾·路易·白遼士。如今,我們可以盡情地給他戴上眾多耀眼奪目的帽子,諸如「標題音樂奠基人」、「現代管弦樂之父」、「古今配器第一人」等,白遼士在音樂領域甚至引領了法國浪漫主義運動,從而與文學家雨果、畫家德拉克羅瓦並稱為「法國浪漫主義三傑」。幾乎憑借一己之力,這個放蕩不羈愛自由的音樂鬼才,為19世紀的法國音樂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

白遼士肖像
標題音樂奠基人
如果說魯迅的棄醫從文是由於國人種種令人悲哀的現狀之刺激,那麽白遼士的棄醫從樂更多地是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就像許多專制家庭一樣,白遼士在17歲那年被父親送到巴黎學醫,兩年後獲得學位。但相較於令他恐懼的解剖桌,歌劇院和音樂廳才是他心心念念的神往之地。在經過與父親的爭吵後,他發誓「不當醫生或藥劑師,而要成為一名偉大的作曲家」。當然,代價就是他被徹底停了生活費。就像如今的「北漂」一樣,漂在巴黎的白遼士不得不思考如何用音樂養活自己。然而,他連鋼琴都不會彈,靠樂器教學是不可能了。於是白遼士轉向了音樂評論——為雜誌寫評論和文章。就這樣,他成為了第一位以音樂批評謀生的作曲家。而恰恰是他的音樂批評,成了他余生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經歷了幾年私教和巴黎音樂學院的科班學習後,白遼士終於迎來了自己的命運之年:1827。是年,一個由英國演員組成的劇團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白遼士為莎士比亞作品中顯示出的人類洞察力、動人心魄的美和戲劇性情節所深深折服。更重要的是,他愛上了劇團中的主要女演員——哈利特·史密森,後者分別扮演了奧菲莉亞和朱麗葉。白遼士對她迷的神魂顛倒,寫了許多熱情洋溢的情書,使這位小明星受到了驚嚇,並斷然拒絕了他。然而,柏氏生性敏感且極富想象力,在被拒後進行了各種堪稱瘋狂的腦補:絕望的情緒,黑暗的幻象以及可能的死亡場景……都將成為他即將創作的那部非凡作品的關鍵因素。他為這部交響曲定下了「幻想」的主標題,輔以副標題「一個藝術家生命中的插曲」,並采用了前所未有的五樂章形式(他為每一樂章都寫了詳細的文字說明),這便是音樂史上劃時代的作品——幻想交響曲。憑借這部作品,白遼士成為了公認的「標題音樂奠基人」。對此,穆索爾斯基曾感嘆:「音樂中有兩個巨人:思想家貝多芬和超級思想家白遼士,所有現代標題音樂作曲家都以白遼士為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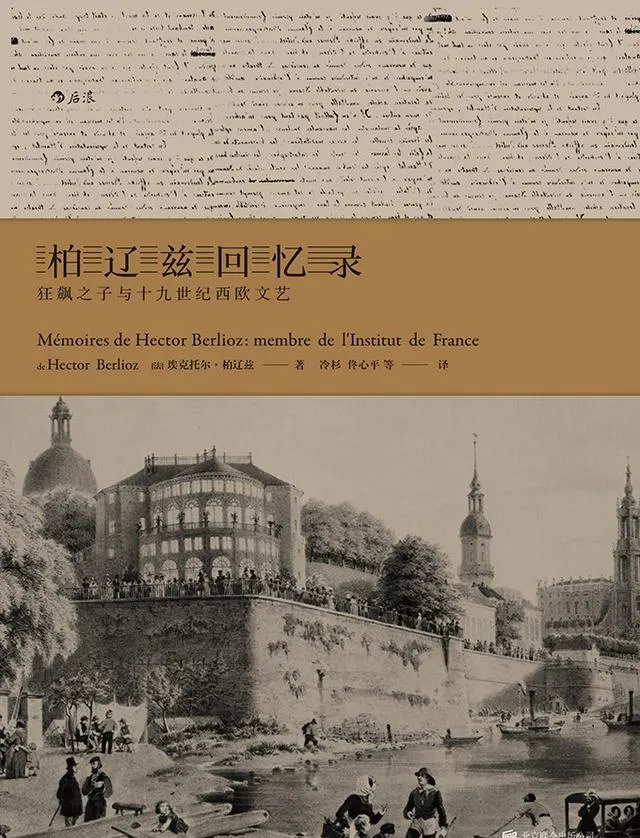
【白遼士回憶錄:狂飆之子與十九世紀西厄文藝】
首樂章始於一段緩慢的引子「憂郁的冥想」,它預示著夢中情人的首次出現,作為「固定樂思」它將在隨後的樂章中一再出現。接著,它被一些快樂的瞬間所打斷,並行展成狂亂的激情、憤怒和嫉妒,並最終返回溫柔、淚水,以及宗教的安慰。第二樂章的主題是舞會,開頭輕快的圓舞曲很快被突然闖入的「固定樂思」所打斷,當圓舞曲返回時,兩架豎琴增加了華麗的伴奏。第三樂章中,藝術家發現自己置身於傍晚的田野中,他聽到遠處傳來兩個牧人的笛聲:牧人之間的對話分別由一個英國管和一個雙簧管演奏,後者在後台演奏,以產生遠距離回應的效果。突然,固定樂思是在木管組中再次出現,暗示藝術家希望贏得他的戀人。然而,當牧人的曲調再次響起時,雙簧管卻遲遲沒有回應。留給聽眾的,只有定音鼓奏出的遠方隆隆雷聲。
第四樂章「赴刑進行曲」是白遼士的天才創意。在意識到他的愛得不到戀人的認可後,藝術家吞服了鴉片,由於劑量不足沒有致死,他在昏睡中夢見許多可怕的景象。他夢見自己殺死了戀人而被判死刑,奔赴斷頭台。低音弦樂器堅定的節拍以及沈悶的大鼓表現了行進的步伐。臨近結束時,單簧管再次奏出戀人的主題「固定樂思」,但很快被全樂隊演奏的一個極強的和弦突然打斷——斷頭台的鍘刀落下了。在此,白遼士的配器如此生動寫實,讓我們仿佛聽到了主人公的人頭落地之聲,這是音樂史上的一個偉大時刻。
末樂章的「女巫夜宴之夢」同樣精彩,藝術家在夢中看到自己在女巫的宴會上,被一群可怕的幽靈、巫師和妖怪所包圍,他們是為他的葬禮而來的。怪異的喧鬧、呻吟、狂笑,遠方的哭聲此起彼伏。戀人的旋律又出現了,但是已經失去了高貴而優雅的氣質,變得低賤、淺薄和怪異。她的到來引起了一陣歡樂的喧囂,緊接著加入了可怕的狂歡。在這個聲響龐大而怪異的末樂章中,白遼士創造了他個人對地獄的幻象。在通往地獄的道路上,一群女巫和妖魔鬼怪聚集在一起圍繞著藝術家起舞。
對於1830年12月5日觀看首演的觀眾來說,整部作品是難以理解的:新的樂器、新的演奏效果、在不同的調上同時出現的旋律、以及非傳統的曲式。但是,它們都很有效果,整部交響曲聽起來就像是在觀看一部恐怖電影,有著驚心動魄的畫面感。竊以為,即便白遼士再也沒有創作任何其他作品,他依然可以僅靠這部浪漫主義傑作而流芳百世。正是憑借這部作品,白遼士與史密森終於走到了一起。然而,兩人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藝術的幻想氣質與婚姻的務實風格從來都不是一回事)。白遼士抱怨妻子婚後體重增加,史密森則抱怨丈夫的不忠。晚年的史密森常常酗酒,漸至身體癱瘓,並於1854年病逝。白遼士一個人又繼續過了十五年,可謂晚景淒涼。白遼士與史密森以扮演羅密歐與朱麗葉開始,卻以哈姆雷特和奧菲莉亞的結局告終。人世間的愛情,多是如此。
現代管弦樂之父
作為一位只會演奏長笛與吉他兩項樂器的作曲家,白遼士在【幻想交響曲】中所展現出的驚世駭俗的管弦效果是驚人的。在交響曲的歷史上,白遼士是第一位在配器法層面真正超越貝多芬的天才。在交響樂創作的偉大探索中,他不斷試驗新的樂器:蛇形大號(大號的早期形式)、英國管(低音雙簧管)、豎琴(一種古代樂器,現被使用在管弦樂隊中)、短號(來自軍樂隊的一種有閥鍵的銅管樂器),甚至還有新發明的薩克斯管。1843年,白遼士寫下了音樂史上的不朽傑作【論配器法】,至今它依然作為配器課的教材在世界各地的音樂學院中使用,一直是舉世公認的經典教科書。

筆者收藏的不同版本的【幻想交響曲】
誰能想象,這個半路出家、不會彈鋼琴的醫學專業學生竟然在駕馭管弦樂隊上有如此驚人的天賦。在【論配器法】中所附十六頁的【安魂曲】總譜上可以遙想當年演出的大場面:一支管弦樂隊居中,四角上又是四支銅管樂隊。樂隊總指揮必須透過與四名副指揮的協同來控制音樂演奏。然而,這對他來說還只是有限的滿足,他真正想要的管弦樂隊是一種即使今天也不容易被實作的龐大規模:以小提琴一百二十,中提琴四十,大提琴四十五,低音提琴三十三的弦樂為核心,配以比例適當的管樂,另加豎琴三十,鋼琴三十,還要有管風琴。更「不同凡響」的是他還要添上罕見的古中提琴、超大提琴,還有十二副原型為龐培城廢墟出土的古鈸,等等。如此便組建成一支總計近五百人的管弦樂隊。對此,他這樣描述這種夢幻般音樂效果的幻想:
在這類巨型樂隊中,我們能獲得千萬種豐富多彩的配器手法……它安靜時,莊嚴得猶如微微入睡的大洋。它憤怒時,激烈得像是席卷一切的熱帶風暴……人們似乎聽到了原始森林的訴說……聽到了人民悲憤的吶喊、祈禱、凱歌。它的沈默會由於肅穆而引起恐懼,它的漸強會使人戰栗,有如頃刻間一片大火蔓延開來,把整個太空燃熾!
他是如此陶醉於前輩大師的配器藝術之中,盡管只會演奏長笛與吉他兩件樂器,卻對幾乎每件樂器的特性和效果都了如指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罕見的天才。對於他為之傾倒的大師格魯克的歌劇【伊菲姬尼在陶瑞德】(Iphigenia in Tauride,1779),他對其中中提琴的特性與妙用娓娓道來,令人擊節:
當奧勒斯特筋疲力盡為良心責備所折磨,昏昏入睡時,樂隊郁悶而緊張地發出嗚咽和痙攣似的嘆息,而從頭到尾響徹了中提琴不絕如縷的怨訴。在這個無與倫比的富於靈感的處理中,它之所以能使不少聽眾兩眼圓睜淚流滿面,主要由於中提琴聲部,特別由於第三弦那獨特的音色、切分節奏,以及由於它被低聲部攔腰一截時所造成的奇特的效果。
於是,當我們再次聆聽「赴刑進行曲」中那些驚人的片段,聽到那猶如赴刑死囚的幹咳般的一記陰森的鈸聲,或是似鍘刀斷頭般的極強和弦,我們或許將對那些神來之筆不再驚訝。因為白遼士把玩樂器就像魔術師把玩手中的道具,那接連不斷的神來之筆令人眼花繚亂,讓人嘆為觀止。再想想「女巫夜宴之夢」中的可怖場景:弦樂、高音木管和吹奏滑音的圓號不斷制造出恐怖的音響,然後一支高音單簧管開始吹奏「固定樂思」的可怕而滑稽的模仿,仿佛夢中情人此時穿著老女巫的醜陋袍子詭異登場。而在全樂隊爆發歡樂的音樂來歡迎她之後,全場突然安靜了下來。接著,出現了古典音樂史上最大膽獨創的時刻:我們聽到了黑暗哥特式教堂裏的鐘聲。在這樣莊嚴的背景下,大號和大管演奏出中世紀教堂中的葬禮聖詠——「憤怒之日」(Dies Irae)。突然間,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恐怖甚至死亡的窒息感向你襲來,那是一種關於音樂的極致體驗。後來,這首聖詠經常出現在眾多影視作品中,用來表現死亡、恐怖和黑暗。在電影【與敵共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 1991),【聖誕夜驚魂】(The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1993),甚至是美劇【美國恐怖故事】(American Horror Story, 2011)中,我們都能聽到這段詭異的曲調。
文學ⅹ音樂
在白遼士心中,音樂與文學總是聯系在一起的。他所奠基的標題音樂的最大特點正在於此,而他作為浪漫主義音樂代表人物的重要特點也在於此。在白遼士貫穿一生的創作中,文學與音樂是深度交融、緊密無間的,實作了兩者相乘所爆發出的巨大能量。當他還是學生時,就接觸了莎士比亞的作品,這種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莎士比亞悄無聲息地闖入我的生活,像閃電一樣使我愕然,他向我揭示了藝術的全部真諦。」白遼士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如饑似渴,並根據他的四部作品:【暴風雨】、【李爾王】、【哈姆雷特】及【羅密歐與朱麗葉】進行音樂創作。有人說在莎士比亞之前沒有戲劇家能夠在舞台上表現人類如此豐富的情感,而白遼士的創造性就在於用音樂來創造出如此寬廣的情感範圍。
讓我們再次回到【幻想交響曲】。這部傑作有著五樂章的不同尋常的形式(不是通常的四個樂章),這一結構安排極有可能是受到莎士比亞戲劇運用五幕形式的啟發。一方面,第一和第五樂章在長度和材料上相互平衡,第二和第四樂章也是如此,慢板的第三樂章是作品的中心。這使得整部作品在結構上非常對稱。另一方面,白遼士創作了「固定樂思」作為統一五章作品的手段,它在整部交響曲中總共出現了八次。它在故事中代表主人公的戀人,成為作曲家無法擺脫的東西,就像生活中的史密森一樣。有時對它的音高稍加改編,或是分配給不同的樂器演奏,不同的音色都代表了不同的情感。為了讓聽眾了解這些情感,白遼士為每個章節準備了一份標題,為聽眾在欣賞時閱讀。白遼士賦予了音樂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學性,色彩、強弱、節奏與文字、故事相互交織,難分彼此。
當然,這樣一種將文學與音樂高度交融的嶄新藝術形式的經歷註定坎坷。一方面,輕車熟路的慣性已經助長了無邊荒草,遮擋住人們的審美眼光;另一方面,功成名就的老一輩更是理所當然地占據了音樂中心的黃金地段,無情地擠壓著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的命運,白遼士一生才如此坎坷和貧窮(只能透過音樂評論來維持生計),要不怎會有帕格尼尼送他兩萬法郎以解燃眉之急的囧事,即使這早已成為音樂史上的佳話,卻也不由地叫人辛酸。幸運的是,叱咤歐洲樂壇的李斯特給了他極大的支持,這位同樣喜好標題音樂的大師(創立了「交響詩」這一具有高度文學性的音樂形式)在【幻想交響曲】的每個樂章中都看到了高度的文學性:
第一樂章我看到了情感的湧動,第二樂章看到了人物的交織,第三樂章看到了內心的獨白,第四樂章看到了氛圍的渲染,第五樂章則看到了白遼士自己所說的「周圍是猙獰可怕的精靈」。
李斯特敏銳地感受到這部劃時代的交響曲的獨特意義,它向一切傳統、法則、規範、教條,乃至陳腐、刻板、氣喘籲籲卻偏要說成美妙之音……向所有這些發出嘹亮如同軍號一般的宣戰。他直言白遼士是天才,後來特地撰文寫道:「在音樂的領域中,天才的特點在於,他是用別人未曾用過的素材,用新的、不同於過去的方式在豐富自己的藝術。」後來,李斯特還特意將【幻想交響曲】改編成鋼琴曲,和白遼士同台演出。上半場演奏白遼士的進行曲,下半場演奏他的鋼琴曲,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白遼士站腳助威。
除了在配器法上的偉大革新之外,白遼士之於音樂史的最大意義在於他第一次讓具體的個人成為音樂的主角。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幻想交響曲】視為「用音樂語言寫成的小說」。從此,交響樂不再如峨冠博帶般居高臨下,而成為像小說一樣的通俗藝術為大眾所接受,這是古典音樂接受史上的偉大一步。可以說,白遼士橫空出世的交響樂造就了新一代人聆聽音樂的耳朵。循著這條主線,我們再來聽他後來的三部傑作——【哈羅爾德在義大利】(1834)、【羅密歐與朱麗葉】(1839)和【浮士德的沈淪】(1846),便會心有戚戚焉。其實,無論是哈羅爾德,還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抑或是浮士德,都深深地刻印下白遼士自己心路歷程的軌跡。依然訴說著那個浪漫主義時代中一個藝術家的內心苦悶——他的天才,他的野心,他的叛逆,他的輕狂,他的為所欲為,他的不懼權威,他的生不逢時,他的痛不欲生,他的內心始終湧動著的對於音樂的至高呼喚,都凝結在這些作品中。

位於巴黎蒙馬特公墓的白遼士之墓
作為白遼士的異代知音,酷愛音樂的文學家羅曼·羅蘭給予了他最高的評價:「如果說天才是一種創造力,在這個世界中,我找不到四個或五個以上的天才可以淩駕在他之上。在我舉出貝多芬、莫札特、巴哈、韓德爾和華格納之後,我不知道還有誰能超過白遼士;我甚至不知道有誰能跟他並駕齊驅。」如今看來,這個評價並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