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作為一種烙印,作為一個文化土壤,是藝術家無法逃避的胎記。就好像米蘭·昆德拉雖然大半生都待在法國,並在創作生涯的中後期開始使用法語寫作,而且加入了法國國籍,可是,法國人還是會覺得他是一位東歐作家,經常會問及的就是捷克和他寫作的關系。人們總是試圖從他的寫作中分析他對母國的態度,即使他的專註點一再落在小說本體論(即小說是什麽,應該怎麽寫)上,一再深入地去探索現代小說的寫法,可人們還是不可避免地帶著一種眼光來看他的作品。我想一位哪怕在各個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中文作家,在英語世界中,也會遭遇這種「眼光」和「期待」,人們先入為主地希望這位作家能夠成為那個古老文明的代言人,能夠在作品中去分析、回顧和描繪他所成長的特殊土地,甚至有的讀者單純為了獵奇去讀一位可能在藝術手法和先鋒性上絲毫不遜色於西方任何一位同時代作家的少數族裔作家的作品,並希望那位作家能夠印合他們心中的文化想象……這是一種比「古老的敵意」更加深沈的「凝視」,一種無可避免的「他者」眼光。
作為一位伊朗詩人,芙洛格·法羅赫紮德就要面臨讀者對她的這種「凝視」。伊朗,一個率先進入人們視野的帶有政治性的標簽,「伊朗」這個詞的意思似乎比詩本身帶有更多的內涵和外延。基於這一獨特的「出身」,人們自然期待著這位詩人能夠寫出屬於伊朗的「反叛」(或稱為異端)詩歌。同時,作為一位女性詩人,人們又似乎更加期待著她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而這樣的「凝視」與「期許」不但有將詩人寫作工具化的風險,同時也會有失去辨認這位風格獨特的詩人那多姿多彩的詩歌藝術更多紋理的機會。妨礙了讀者進入到詩人多元豐富的詩歌內核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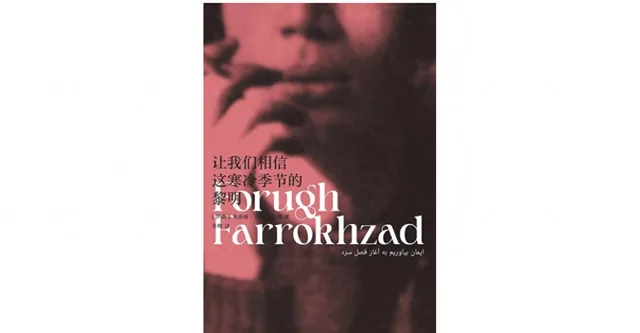
【讓我們相信這寒冷季節的黎明】,作者:[伊朗]芙洛格·法羅赫紮德,譯者:李暉,出版社:明室Lucida|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時間:2023年7月。
詩歌與生活的古老敵意
芙洛格·法羅赫紮德是一位短命的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31歲去世,蘭波活到37歲,海子25歲……歷史上還可以找到更多這樣的短命詩人。法羅赫紮德的生命結束在32歲,這是一個太早的年紀。對於寫作者來說,正是更多、更大的人生和文學沈澱準備去構建的時候,命運之輪的停擺,無疑扼殺了這位天才繆斯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似乎一直對於天才的創作者抱有敵意,而女性詩人比男性詩人往往需要承受來自各個方面的裂隙之威脅。1967年,命運的偶然性在法羅赫紮德身上上演了最殘酷、最戲劇性的一幕,一輛吉普車急轉彎中與一輛校車相撞,這一次看似偶然的機械性事件奪去了這位詩歌繆斯年輕而創作力豐沛的生命。在這最終的機械停擺之前,法羅赫紮德的創作生涯正處於高峰期,她正將自己詩歌之火燒得旺盛,寫出了自己的代表性詩集【重生】和【讓我們相信這寒冷季節的黎明】。

芙洛格·法羅赫紮德。
其實「敵意」並不十分古老,有時候它以變幻不定的面貌,如無孔不入的細菌和幽靈,鉆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1960年,法羅赫紮德出車禍去世的7年前,她就因為離婚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而導致抑郁,險些走上了自殺的道路,幸好那一次命運女神並沒有將她甩出人世飛輪,而是親手拽住了她。這樣的挽留,多給了她7年的時間用來寫出余下的生命詩篇。
芙洛格·法羅赫紮德是一位擁有西蒙娜·薇依一樣虔誠信仰的詩人,不同於薇依對基督教信仰的追索,法羅赫紮德的信仰是詩歌。縱觀她短暫的詩歌生涯,我們會發現一個燃燒的核心——那種逼人的創作激情。可以說,她全部的生活幾乎都是為詩歌創作而準備的,她是一個不但擁有著詩歌的虔誠之心,同時擁有著巨大的創作激情的女藝術家,一位為著詩歌藝術全力以赴的嚴肅作家。在一封寫給父親的信中,她說道:「詩是我的上帝。我愛詩到了這種程度。我日日夜夜都在想著要寫一首新的、漂亮的、還沒有人寫過的詩。」這是一位對詩歌有極高抱負的女性,她甚至將詩與上帝的地位等同,這無疑顯示了她對於詩歌藝術的癡愛。「我獨處而不思考詩歌的日子就算是虛度時光。」她無比斷然地說。有時候詩歌甚至是一種宿命,纏結著她,讓她既熱愛又無法掙脫,仿佛繆斯女神已經牢牢地預定了她作為自己的「愛女」:「為何上帝把我創造成這樣,把詩歌的魔鬼放進我的內心……」「我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除此以外,我沒有別的目標。」可以看到,詩歌在法羅赫紮德的內心當中作為一種雙重羈絆存在,一方面她熱愛詩歌,詩歌可以確證她的靈魂存在於世;另一方面她也意識到了詩歌與生活那古老的敵意,這一敵意有著雙重內涵,一是世俗層面的羈絆,詩人在精神王國當中的自我與生活中凡俗自我之間存在的裂隙與張力;更深的一層是,「詩在寫我」的創作宿命。在成熟詩人那裏,總能夠感覺到一種似乎處於「被動」的操縱,詩人仿佛是被某種「詩歌之手」操縱著寫下那些出乎意料的驚人詩行……透過這些發言,我們可以看到,僅三十出頭的詩人在創作上的高度自覺,這些議題,在我看來,一方面確認了法羅赫紮德致力於將詩歌道路作為自己一生誌業的決心,同時也反證了她作為「靈性詩人」的宿命:愛詩與被詩愛之宿命的纏結。
法羅赫紮德的詩歌擁有豐富的主題:存在問題、愛欲的問題、死亡、時間,民族的暴風雨……在她的全部主題中她都迸發出了巨大的激情,這令她的語言強悍、獨斷、刻骨而決絕,擁有著一種不可挑釁,不容置疑的果決。她經常使用主觀、奇崛的比喻,令她的詩歌突然上升到一種決斷的高度,與存在對話。譬如「你遠航在你自己的河上,拋下這土地——/哦,哢嚓折斷我激情風暴的樹枝。」(【悲傷】)「我的手指迸發出火花/點燃著空白紙頁的緘默。」(【愛的進行時】)這些極富主觀性的想象與語言的創造力激情相匯,讓她詩歌中的空間在場得到了提升,同時鐫刻她詩歌核心性的品質。
法羅赫紮德在【讓我們相信這寒冷季節的黎明】這本詩集中不停追問死亡、存在與未來。她的詩歌精確而雋永。例如,【你之後】這首稍短的抒情詩,這裏的「你」在詩歌開頭被揭開:「你,我的七歲」。而這一區分在之後被詩人稱為「奇妙的背離時刻」。仿佛這一時間前後是生命之界的一個分水嶺,鐫刻一種斷裂。詩人寫道:「你之後……我們和微風之間/和飛鳥之間/那明亮生動的聯結,破裂了,/破裂了,/破裂了/」。連續的三個「破裂」形成了三次怦然的音效,在我們心靈的腦海裏,折了三回。在之後的詩節中,詩人將這一隱喻進一步明確,又讓我們回到了「寒冷季節」這一象征世界,「我們成為彼此的謀殺犯」是對於「寒冷季節」的致命控訴與揭露,而在本詩的結尾,詩人不禁質問道:「一個人要付出多少?」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難於脫殼的悲愴。
同時,她的詩歌既指向豐富女性內在,又無限向外部的豐富世界展開。【讓我們相信這寒冷季節的黎明】是詩集中最長篇幅的詩,全詩籠罩在一種悲愴但堅忍的調子中,其中女性的敏感自我在這塵世上擺蕩,同時又延伸出對不合理周遭和世界的指控。全詩以「而這就是我,/一個孤獨的女人/在一個寒冷季節的門檻上。」
這一自白性質的抒情調子開始,融入了時間流逝的永恒主題,同時又以「水泥之手」對抗「無用無力的黎明」,將詩人放置在一種受挫敗的普羅米修斯的立場上來看待這一殘缺的世界,從而對存在和命運等復雜問題進行了精神上的追問。法羅赫紮德的詩歌語言多變、想象力奇詭,對於事物的認知機敏。「鳥兒想象的路線」「嫩葉的感性呼吸」「窗戶純凈的心靈」對意象進行了絕對原創的「再造」,充分體現了詩人對想象與語言的駕馭能力,是命令激情與一位女性詩人天然的感性創造力的完美結合。全詩透過歌詠的調子,仿佛在對一個未知的、獨一無二的朋友傾訴,支撐起由詩人不停編織的內心風景,並在其中節節遞進,全力實作著語言的表現力。「人們借著我的聲音祈禱」似乎在恢復一種詩人作為「古老先知」的部份能力。從而能夠在一個殘缺不全的「飽食死屍」的,充滿「腐爛果實」的生活狀態中「相信這寒冷季節的黎明」。
「在衰敗中繼續創造」
值得註意的是,芙洛格·法羅赫紮德一直將本質性探索作為自己藝術創作的核心。她說「我想穿透一切,盡可能地深入到所有事物中去。我想到達大地的深處。我的愛在那裏——種子在那裏生長,根系在那裏相接,在衰敗中繼續創造。就好像我的身體是這一活動的一種短暫的形式。」這一段話十分重要,令人震驚與側目,幾乎可以看作法羅赫紮德的詩歌觀,展現了她對自身存在問題的獨特思考。她將自身作為「大地種子」的一種形式(也許是短暫的),此時,藝術家將自我命運擺在「創造」背後,展現了作為一個「中介與手段」的決心,可以說,法羅赫紮德的寫作具有某種堅定自覺甚至獻祭的意味。
需要看到的是,法羅赫紮德的創作雖然紮根於繁冗復雜到讓人困窘無奈的社會現實中,但是她卻沒有拘泥於此種泥潭,而是朝向成為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她的所有「行動」都指向一個「藝術」核心。這保證了她的詩歌創作的純粹性。在我看來,法羅赫紮德給所有女性創作者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樣本,她從不標榜自己的天才性,而是在創作中不停地尋找和確認自身。這正是一個藝術家的真誠之所在。
在寫完第三本詩集之後,法羅赫紮德不免產生了一種自我懷疑:「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詩,我只知道那時候有很多我,她們都很真誠。我知道她們也很隨意。我還沒有成形,我還沒找到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形式和心智世界。」我們絕不能將這段話看作法羅赫紮德對自己作品的不自信,而應該看成一個真誠的、正在自己詩歌道路上摸索的藝術家的一種坦誠與自我決斷。
誠然,在我們身邊充斥著許多對自己的詩歌寫作十分「自信」的詩人,他們誇誇其談自己的詩歌,仿佛它們是已經成型的作品,他們的詩歌觀念是封閉而自大的,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流動的、逐漸成為的過程,而盲目地對自己與詩歌感到自信。實際上,從本質上說,所有詩歌都是未完成的,藝術家本身應當是一個不停更新的個體,自大狂註定與真正的藝術無緣。而法羅赫紮德不是這樣的人,她對自我藝術道路的商榷,正是對藝術的極大尊重與對人的發展的深刻認識,因為藝術是「正在發生」的,而不是「已經發生」的。這其中蘊藏著一個大大的「未來」,才是最讓人激動的,也因此值得我們一直為之辛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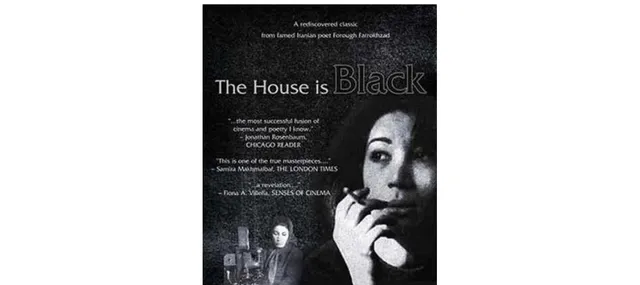
法羅赫紮德導演的紀錄片【房間是黑的】海報。
在我看來,芙洛格·法羅赫紮德是那種原創性的作家,這種型別的作家會在汲取了一定數量的材料之後,蓄積了足夠的能量池,然後開始自我的表達。在寫完第三本詩集之後,她真誠地談到:「因為閱讀一部又一部詩集,我已經飽和了,而由於我飽和了,並且好歹有一點才華,我就不免要以某種方式讓它們傾瀉出來。」這樣的一種態度,讓她的詩歌有一種深度和廣度,又不會流於「工具化」。在第三本詩集【反叛】出版之前,法羅赫紮德不得不離開伊朗,一方面這是因為她彼時對於電影制作產生了興趣,同時也是因為她的感性詩風加之自由派的生活方式與復雜的情感糾葛,在當時的伊朗文藝界引起非議與喧響。
法羅赫紮德始終處於裂隙之中,在我看來,她是在個體和社會兩種相互分離的境遇當中確立自己的詩歌的。作為女性,她坦誠地書寫著自己的個體經驗,但是她並沒有單純白描這些經驗,而是將之作為一個背景來提升在特殊制度下的人的精神尊嚴。
作為伊朗社會中的一名女性,法羅赫紮德當然在社會制度當中辨認著女性這一身份,體察著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女性的遭遇與困境。但是值得註意的是,她從來沒有將這種書寫當成一種特權或者取得文學合法性地位的便利手段,女性主義也從來不是用來標榜的文學地位說辭,它切實地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處境(戴錦華語)。這一處境,作為具有同構性社會境況的寫作者感同身受並有著切膚之痛。那是一種你無法擺脫、無法逃避的「宿命追殺」,無論你多麽想盡可能地擺脫這一社會和創作上的雙重束縛,你都始終在裂隙之中。
作為伊朗的女性詩人,法羅赫紮德卻幾乎是在一種自然狀態下寫作。她的心靈與精神與任何一個國度的女人無異。也就是說,她並沒有將自己的政治處境作為一個單獨的觀念性預設來建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而是將之作為生命整體性體驗不可避免的一部份來加以確認和體察的。我們也不應當單純將她作為一種特殊制度當中的特殊女性加以對待,而應該看到她內部蘊藏的巨大的女性創作礦藏,這儲備令她的靈魂在詩歌之國的沃土上方飛旋、盤桓。
為一個文明社會而寫詩
誠然,在政治與保守文化捆綁的社會形態當中,人的自由常常被限制,而藝術家作為信仰自由的群體,在其中經歷著兩種分裂,一種是外部環境對於經典和傳統的標榜會讓富有創新精神的藝術遭受重創;另一種則是藝術家在保守的傳統當中承受著普羅米修斯般的精神陣痛。即使不是十分反叛的藝術家,在這種環境當中也會成為異類,「顯得」十分反叛。
我們對世界的狀況通常有著共時性的看法,譬如不同經度、緯度的國家,共時性地存在於地球上。畢竟,在正常的情況下,你完全可以買上一張機票,第二天就出發飛往世界上任何一個你想去的角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看似共時性的國家、民族在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時間差異。也就是說,在一個充滿立法者與監管者的國家被視為挑釁的東西,在另外一些國家也許並不意味著什麽。這其中的悖論與張力時常讓人類的整體性在某一特定的時刻遭受重創。

芙洛格·法羅赫紮德。
「法羅赫紮德是為一個文明社會而寫詩。」這是同屬於一個民族與文明體系的詩人阿多尼斯對於法羅赫紮德的評價。在法羅赫紮德眾多的「頭銜」當中,有一個是「女性主義先鋒」還有就是「反叛」。這兩個詞都讓我覺得有些不適,「先鋒」一詞帶有著明顯的政治革命色彩,感覺下一時刻就需要拋頭顱灑熱血與資產階級鬥爭到底了。這是有些可怖的位置,仿佛一個女性在一個「不正常」的政體中寫詩、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就是「反叛」,就會被貼上「女性主義先鋒」的頭銜。這頭銜看似是一種褒揚,實際上,這一荊棘冠冕帶著血肉沈痛的背景,對於被放置在這樣位置的女性藝術家自身不安全,同時也不公平,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誰又會走上反叛的道路呢?更何況,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當中,哪怕是一個「文明國家」正常的需求、選擇與舉動都會被認為是一種「反常」。這正是法羅赫紮德們共同的境遇!
「為一個文明社會而寫詩」會讓我們想到很多詩人,這些詩人幾乎都在為著一個正常的、文明的秩序與社會寫詩,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米沃什、策蘭,王鷗行(越南詩人)……我甚至想到了李白,想到了屈原,想到了泰高爾,想到了哈維爾同時也想到了米蘭·昆德拉……這樣的名單可以無限列下去。有眾多人為著人類能夠在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當中生活而努力思考和寫作,為著人類精神的豐富性和獨特性與尊嚴而努力寫作。這些人不僅僅是為一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上的「文明」,更是為一個更好的「人類的未來」而工作。可以說,那些對於人類現狀的黑色反思與對人類未來的金色憧憬,全部都是指向一種「未來」,一個「更大更好的明天」。
從法羅赫紮德身上我們能夠看到詩人,作為人類靈魂真正的工作者,他們的希求無非是一個更加「人性」、公正的世界,如果他們不能身在那樣的世界,最起碼他們可以在詩歌當中去希求和構建一個那樣的世界!前述提到的眾多詩人,他們並不生活在不同一個時代,有的相差甚至千百年,然而從人類共同體的角度來說,他們卻是一個整體,一個實實在在的高度指向未來的整體。然而,無論生在何種時代,總有鐐銬拴系在這些精靈的腳上,無法騰躍。但是也許正是這樣吊詭的枷鎖,卻生出詩和文學的雙重羽翼——就像芙洛格·法羅赫紮德身後那對巨大的天使之翼。
撰文/袁永蘋
編輯/宮照華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