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中勝 贛南師範大學二級教授,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江西省「雙千計劃」人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計畫子課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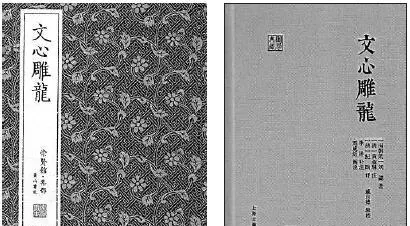
【文心雕龍】書影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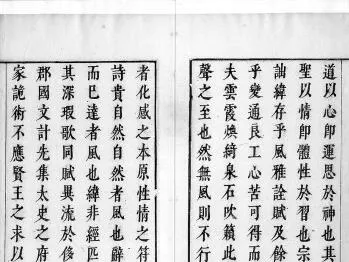
明五色套印本【劉子文心雕龍】。由明代萬歷年間吳興閔、淩兩大出版家族中淩雲、閔繩初合刻,五色套印源自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以紅、綠、青、黃、白五種顏色批點,版本價值極高。圖片來源:遼寧省圖書館(遼寧省古籍保護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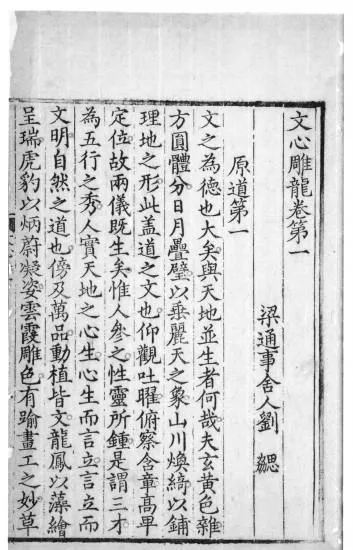
明弘治十七年(1504)馮允中刻本【文心雕龍】。資料圖片

劉勰像 資料圖片
學界一般簡稱「【文心雕龍】學」為「龍學」。在現代學術史上,關於一本書的研究被稱為「某某學」的委實不多,而「龍學」就是其中長盛不衰的專門之學。在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現代行程開啟之時,【文心雕龍】研究是如何融入這一行程,進而迎來百年「龍學」興盛的呢?回顧百年以來的「龍學」發展歷程,我們有必要從學理上思考「龍學」何以興、何以繼續興等涉及學科發展的重要問題。
開端:具備現代科學質素
五四運動前後,西方現代學術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國知識界傳播,中國學術的現代行程由此開始。當時學人受科學主義影響,認為一種理論是否科學、成熟的標誌,就在於其是否建立了嚴密的邏輯體系。正如梁漱溟所言:「科學是知識之正軌或典範;只有科學,才算確實而有系統的知識。」(【中國文化要義】)當時的文學研究也受這種科學主義的影響。如張相說:「近世研治科學,析類之事,目為至要。植物學家,部門科屬諸名,井井而談,屬隸無紊,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矧在文章,渠不若彼。」(【古今文綜】綴言)認為文學研究也像植物學一樣,要分門別類、條分縷析。徐昂也說:「無論字與文,研究宜用治科學方法,澈底分析。」(【文談】自序續)這種從自然科學移用過來的科學主義觀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學者們對【文心雕龍】的選擇。
五四運動前後,於中西文化的對比中,學者們想從幾千年的中國文論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論體系的著作,尋覓的結果就是,【文心雕龍】逐漸進入學者視野。如劉節說:「若彥和【雕龍】,則可以言文學原理矣。」【文心雕龍】是「純粹之文學體制」「說理精密,條貫有序」。(【劉勰評傳】,【國學月報】1927年第2卷第3期)梁繩祎說:「像萊辛(Lessing)、馬太·安諾德(Matthew Arnold)、泰恩(Taine)以及現代的喬治·勃蘭特(George Brandes),全是以批評名家的。他們評論的勢力都很偉大,有時單詞片語都要傳遍世界,不用說這種批評是文學前進演化極有關的助力。」反觀中國文學界,在古典文學批評傳統中,他發現了【文心雕龍】的當代價值:「在過去可憐的文學批評史中,尋一點萌芽,我們不得不推重千余年前的劉彥和。他著了一部專論文學的書,叫作【文心雕龍】。」(【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1927年6月【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梁繩祎是用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理論方法去解讀【文心雕龍】,他在文中提到義大利但丁的【神麴】、德國的尼采以及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國作家作品。
值得註意的是,五四運動前後,新舊兩派文化陣營在許多問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但是在對待【文心雕龍】的評價上,兩派意見卻出奇地一致。這是因為新舊兩派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觀察到【文心雕龍】的價值堪比西方文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掌旗官,魯迅評價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裏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集外集拾遺補編·論詩題記】)他認為,中西方文論都有邏輯體系嚴密的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和【詩學】分別對中西方文論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文化保守派的首領,章太炎早在20世紀初年就在日本開設「國學講演會」,講授【文心雕龍】。據學者考察:「章氏弟子們的記錄稿,至今還塵埋在上海圖書館。」(周興陸撰【章太炎講解〈文心雕龍〉辨釋】)而據【錢玄同日記】1909年3月18日載:「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與季剛同行。」由此我們可知,黃侃、錢玄同等章門弟子曾經比較系統地跟章太炎學過【文心雕龍】。黃侃認為【文心雕龍】是論文之「專著」:「敷陳詳核,征證豐多,枝葉扶疏,原流粲然。」(【文心雕龍劄記】)黃侃是從尊崇傳統文化的角度來推崇【文心雕龍】的,意在證明西方所謂的邏輯體系其實中國古人早已有之。誠如吳承學所指出的:「在清末民初,【文心雕龍】仍是傳統學者用來捍衛和發揚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
1923年,梁啟超在答【清華周刊】記者【國學入門書要及讀法】中,把【文心雕龍】歸為「隨意涉覽書類」(【讀書指南】)。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文心雕龍】,但實際上他是非常重視【文心雕龍】的理論思想和文學藝術的。1925年,梁啟超評價【文心雕龍】:「誠文思之奧府,而文學之津逮也。」(【範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序】)【文心雕龍】本身的文章辭采飛揚,是賦中佳作。更重要的是,其中確有符合現代科學體系的理論質素。在近百年來文學理論研究者們「尋例證己」的過程中,【文心雕龍】作為「中國文論也有邏輯體系」的一個重要例證被不斷提起,「龍學」由此開啟了百年的現代之路。
行程:融入現代學術
「現代的科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對「龍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後世眼光審視,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從正面影響來說,【文心雕龍】「體大思精」,被認為具備現代科學質素,可以進入現代教育體制、登上大學講堂,從此作為自成一體的一門「學問」融入現代學術行程。在實踐中,憑借現代教學機制培養出一代又一代訓練有素的研究者,最終實作了傳承有序地傳播及弘揚【文心雕龍】文化。百年來的學科化、課程化,大大推動了「龍學」的發展。過去人們只憑個人興趣愛好研讀【文心雕龍】,隨機性、隨意性較強,這並不利於科學研究的有組織推進。在進入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並成為有機組成部份之後,【文心雕龍】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它作為教材內容進入課堂,成為有組織有系統地開展研究、講解、學習、傳播的物件,進而由課堂到報刊、由學科知識傳播到社會文化宣傳、由國內到國外,從此【文心雕龍】的文化影響獲得了極大的拓展。
這裏我們就【文心雕龍】所受正面影響列舉幾例。林紓所撰【春覺齋論文】,是其在高師大學堂授課的講義,1913年6月起曾在【平報】連載。其中大量征引【文心雕龍】語段並申述之。在北京大學,姚鼐四世侄孫姚永樸稍早於黃侃在大學課堂上摘段講解【文心雕龍】,並在課堂教學基礎上精心結撰成一部文章學著作【文學研究法】,「其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體例仿之【文心雕龍】,頗具系統性、理論性」。這一時期,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最受學生歡迎者當為黃侃,其【文心雕龍劄記】是「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授課講義」。(見李建中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系·龍學檔案】)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學生因為【文心雕龍】課程問題要求撤換老師的事件:1916年,同為章門弟子的朱宗萊到北京大學任教,亦講授【文心雕龍】。推測可能是教學效果不及黃侃之故,結果引發學生上書蔡元培校長要求更換【文心雕龍】主講。(見朱懌撰【朱蓬仙生平事跡】)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論,但確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心雕龍】進入北京大學課程並深受學生們喜愛。這裏,我們再舉一個地方高校的例子。1937年福建協和大學的校刊【協大藝文】刊載【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步】一文,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說明:「本校中國文學系所開專書選讀一科中,【文心雕龍】適列其一,本系生與修者七人,采集體研究方式,由俞元桂先生指導。」(見耿素麗、黃伶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組譯·文心雕龍學】)這說明【文心雕龍】研修課在當時的地方高校中也有開設。
梳理「龍學」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許多「龍學」名著都是在大學課堂教學中誕生的。如劉永濟著【文心雕龍校釋】就是其在武漢大學給學生講【漢魏六朝文學】而寫的「講義稿」(見李建中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系·龍學檔案】)從教案講義最終變成學術經典,由此可見「龍學」之興離不開教學課堂之助。
【文心雕龍】走進課程教學為「龍學」培養了大批讀者、研究者,這是「龍學」此後百年薪火相傳的根本原因。「龍學」史上教學相長的佳話比比皆是,如詹福瑞先生師從詹锳先生:「從恩師詹锳先生學【文心雕龍】。一年間,先生一篇篇講下來,我一篇篇整理筆記,一篇篇背誦下來,終於有一天感到走近了這座精深的理論樓閣,雖不敢說登堂入室,卻似可窺其門庭了。」(【中古文學理論範疇】後記)李建中先生師從楊明照先生:「有幸從著名龍學家、四川大學楊明照教授研習【文心雕龍】。」先生感慨,我們要感謝劉勰,「有了他,摛文無虞」「有了他,余心有寄」「有了他,永不失語」。(【〈文心雕龍〉講演錄】附錄)這些年活躍於「龍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多有類似的求學經歷,往往師出「龍學」研究的老一輩大家。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們不斷將「龍學」推向一個又一個新境界。
展望:重拾詩性文章
從「現代的科學研究」帶給「龍學」的負面影響來看,由於過度強調【文心雕龍】的嚴密邏輯體系,學者往往把【文心雕龍】僅當作文學理論著作來看待,結果導致了兩方面的偏差:一是容易使學者忽視【文心雕龍】的詩性一面;二是容易使學者忽視其文章學的特質。
首先我們看其詩性的一面。【文心雕龍】固然有「體大思精」的特色,但其自身特質不僅有邏輯性的一面,還有詩性的一面。李建中先生指出:「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範,【文心雕龍】有其自身的質的規定性:詩性和邏輯性的統一。長期以來,海內外的龍學研究,常常過於推崇邏輯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她所特有的詩性智慧,從而遮蔽了【文心雕龍】的東方特色,遮蔽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不同於西方文論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龍〉講演錄】)【文心雕龍】的詩性智慧是由中國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所決定的。英國學者愛德華·泰勒曾用「文化遺存」的觀念來解釋這種文化現象:「它可能長期地影響到這些習俗或者技藝,如涓涓細流,綿延不絕,從這一代繼續傳到下一代。它們像巨流一樣,一旦為自己沖開一道河床,就成世紀地連續不斷流下去。這就是文化的穩定性。」(【原始文化】)無論是在文化資源、思維方式等深層次上,還是在言說方式、話語範疇等表面層次上,【文心雕龍】都彌漫著濃厚的詩性智慧。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者關註其詩性方面的內容。根據天津師範大學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紹,俄羅斯女漢學家卡·伊·戈雷金娜從【文心雕龍·原道篇】入手,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對劉勰文學觀念的影響。李建中先生認為,戈雷金娜的研究,其「入思方式及部份結論,對於我們探討【文心雕龍】的詩性智慧,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和借鑒意義」。(【〈文心雕龍〉講演錄】)中國台灣地區也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研究【文心雕龍】,為【文心雕龍】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大陸也陸續有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龍】,並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績。張毅認為,經學的陰陽五行學說對【文心雕龍】創作論有影響。(【陰陽五行與中國古代詩學】)閆月珍討論【文心雕龍】的「器物之喻」(【器物之喻與中國文學批評——以〈文心雕龍〉為中心】),把古代文論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維與先民們的生產生活經驗相聯系,具有人類文化學的方法論意義。夏靜分析【文心雕龍】與氣學思辨傳統的關系(【〈文心雕龍〉與氣學思辨傳統】),認為「氣學」獨特的思維方式並不能完全依靠現代理性思維進行理解和分析,具有明顯的詩性特征。研究【文心雕龍】與傳統詩性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回歸其真實的文化場景,展現出寬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廣的理論前景。
其次,我們要認真分析【文心雕龍】的文章學特質。五四運動之前,學者們普遍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文章學著作。如吳曾祺表示服膺【文心雕龍】,「極論文章之秘,識者以為知音。」(【涵芬樓文談】)章太炎說:「【文心雕龍】於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故經、傳、子、史、詩、賦、歌謠,以至諧、隱,皆稱謂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彥和之見高出於他人者也!」(【〈文心雕龍〉講演記錄稿】)他主張廣義文章學,這與【文心雕龍】的文章學思想一脈相承。五四運動前後,把【文心雕龍】視為文章學著作的人包括林紓、章太炎等,持此觀點的還有青年才俊劉師培、黃侃等。劉師培把【文心雕龍】視為文章學論著,並且認可其文章學思想體系。他說,我們要了解文學變遷,「非證以當時文章各體,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劉師培所謂「文學」實即包括「贊頌銘誄之文」等「各體文章」在內,是大文章觀念,而不是現代以來的純文學觀念。黃侃對【文心雕龍】的文章學特質判定是非常明確的,其【文心雕龍劄記·總術篇】雲:「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其書廣收眾體,而譏陸氏之未該。……案【文心】之書,兼賅眾制,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文心雕龍劄記】)文備眾體,黃侃揭示的正是【文心雕龍】廣義文章學的基本特質。
值得註意的是,五四運動以後,有不少受現代文學觀念影響的新派學者用純文學的標準去評判【文心雕龍】,認為【文心雕龍】的文學定義太寬泛、文體雜亂。如霍衣仙在談到【文心雕龍】的「失敗處」時說:「文學定義太廣泛,則議論必流於膚淺。……其文學定義,與章太炎氏‘凡以文字著於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之定義相同,故將經史子集、百家九流,冶於一爐而談之。內容既如此包羅永珍,議論之有‘搔不著癢處’,近於膚淺,為必得之咎矣。」(【劉彥和評傳】)又如楊鴻烈,一方面,稱劉勰是中國「第一個的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相當於歐洲文學上的「法定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心雕龍】全書的「根本缺點」:「在這樣文學觀念明了確定的時代,偏偏這位不達時務的劉彥和就來打破這樣的分別,使文學的觀念,又趨於含混!又使文筆不分!」「這樣一來,就把一個已經成就了的明白、具體、完全的文筆定義,攪擾得一個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了!」(【〈文心雕龍〉的研究】)
由此觀之,五四運動前後開啟的中國學術現代行程,對「龍學」此後的發展壯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但「以西釋中」「以西構中」也給「龍學」帶來了不小的損傷。今天看來,這種研究傾向最大的不足,就是把【文心雕龍】僅僅當作「文學理論」著作,而忽視其原本是文章學著作的特質。張少康先生認為,20世紀「龍學」的理論研究是「重中之重」,其主要成績突出表現在「重視了理論體系的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文心雕龍研究】)。單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研究【文心雕龍】,忽視了其中涵蓋面更廣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學特質。文學理論的研究物件偏向於純文學作品,而文章學研究的物件則包含各種文章創作,範圍要廣泛得多。從純文學文體入手,【文心雕龍】中許多文體就無法進入「龍學」研究的視野。
以純文學的觀念來看【文心雕龍】,更重視文學的審美功能,而輕視了文章學的實用功能。我們知道,【文心雕龍】是非常重視文章之功用的。劉勰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文心雕龍·序誌篇】)「五禮」「六典」「君臣」「軍國」,這些是軍國大事,在這些領域中,文章要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談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體如簿、錄、契、券、狀等,這些也是文章。劉勰的觀點是,大到軍國大事,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文章都能發揮重要作用。而如果從純文學的視角來看,這些文章都缺乏審美功能,都不屬於文學研究的範圍。所以,【文心雕龍】中許多文體沒有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的範圍,中國文章學久遠的實用傳統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章學既有理論,也有實踐,是基於文章創作實踐的理論,也是指向文章創作實踐的理論。豐富性和鮮活性是中國文章學的固有特點。因此我以為,純文學理論既涵蓋不了中國古代文章創作的豐富歷史,也指導不了中國當下文章創作的鮮活實踐。
純文學理論更重視「道」而忽視「術」,以【文心雕龍】為標誌的中國文章學既重「道」,也重「術」。【文心雕龍】有【原道篇】又有【總術篇】。文章學落實到文體、字法、句法、篇法的研究上,比各種所謂「理論」的研究更具體豐實。【文心雕龍】討論各式文體時,都本著「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文心雕龍·序誌篇】)的理路來闡釋,關註文體的源流、基本內涵、代表作品和體式規範。【文心雕龍】還有【镕裁篇】【聲律篇】【章句篇】【事類篇】【練字篇】等,關註文章的剪裁、聲律、用事、字法、句法和篇法。這些形式層面的講究相比抽象的純文學理論,更具體實在、更有可操作性。這些內容也是歷代文話涉及的主要方面,因此,也是中國文章學固有的傳統。但如果從純文學理論的角度審視,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術」層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視。
近些年,關於【文心雕龍】文章學特質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引起學者們關註。吳承學先生指出,在中國文章學史上,最早初步構建中國文章批評理論體系的,是「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六朝文章學」(【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我們當以這個基本認識為基礎,全面審視【文心雕龍】的文章學體系及其特質,從而推進中國文章學體系的理論建構。
回顧「龍學」百年歷程,我們得到幾點啟示:「龍學」要繼續發展,必須進一步融入當代學術行程,融入當代社會實踐,回應當代學術問題;必須加強學科建設,提升教學水平,嘗試用當代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龍學」文化,繼續培養一代又一代「龍學」的學習者、愛好者、傳播者和研究者;必須根植傳統文論的固有特色,以文化自信之姿,實作中西文論的互學互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