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無所歸!」在【帛書老子校註】中讀到這句話,格非揮筆寫下批註——「可做標題」。
「實際上‘登春台’討論的就是眾人和個體之間的關聯。【老子】第二十章裏還有一句‘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這是‘眾人熙熙,如登春台’的本意。」格非告訴南都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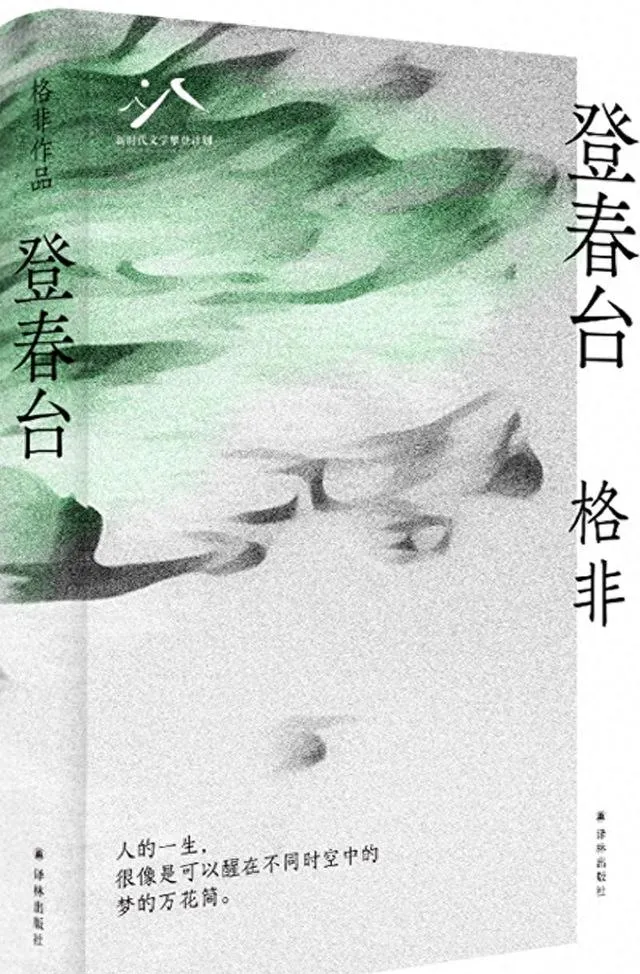
暌違四年,茅獎作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的全新長篇小說【登春台】近日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小說以坐落於北京海澱區春台路67號的一家物聯網公司為線索,講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四十余年裏,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四個人的命運流轉。在【登春台】中,人生的軌跡被偶然性推動,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變得不甚分明,無為即有為,親密即疏遠,萬物觸之可及、彼此滲透影響,而「孤獨」成為彌足珍貴的內心體驗……格非以他的精湛之筆,向讀者展示了理解、介入當代生活的另一種方式。
萬物互聯的當代景觀
「在這個作品裏,如果說我希望對某一個中國社會的特別的問題加以研究和表述的話,可以簡單地把它理解為‘連線’或‘關聯’。」格非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
小說【登春台】由四個章節和序章、附記組成。四個主要人物每人占據一章獨立的敘事空間,他們都供職於一家物聯網公司,人生經歷中有彼此鑲嵌或重疊的部份。格非下了很多功夫在人物內部建立起「復雜的關聯」,有時,相似的場景或情節反復出現,毫不相幹的角色互為「倒影」或「映像」……這些苦心經營的草蛇灰線,引導或等待讀者去發現隱藏在快速推進的情節之下更深層的哲學意味。
「我們共同處於時代的巨變之中,人與人之間是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格非說,「我想把四個人寫成同一個人。」

著名作家格非。
由小說主角之一周振遐掌舵的神州聯合科技公司,則是萬物互聯、資訊密織的當下世界的縮影。格非在小說中以驚訝的口吻描述了物聯網公司的電子地圖:「每一個純藍的光點,都標示出一輛正在路上行進的重型運輸卡車。在卡車數量比較密集的地方,純藍的閃光點自然連綴在一起,形成一條淺綠的光帶。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一帶,那些層層疊疊壘集的光帶,則向淡黃過渡,最後匯聚成一片晶瑩耀眼的亮白……」
這樣一種「連線」是侵入性的,它遵從商業資本的邏輯,炫目而誘惑,靈敏而高效,在生活中無孔不入,將我們餵養,將我們綁縛。然而在小說中,還存在另一種內在的、隱秘的、有益的連線,無關於人生的宏旨,可以從大隱於市、蒔花弄草、散淡無為中獲得。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民安贊道:「如今,物聯網不僅是一個公司,而且是一個新的世界法則。」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則認為,【登春台】是格非最近的一個高峰文本。「比江南三部曲更天人合一,他獲得了命運的語法。他不再那麽操心修辭。他更自由,更哲學,也更好看。」
格非對話陳嘉映:在喧囂的時代寫得很安靜
3月23日,「那偶然的和必然的使我們相連——格非長篇小說【登春台】新書分享會」在北京市萬聖·優盛閱讀空間舉行。作家格非與學者陳嘉映圍繞【登春台】展開熱烈的討論。
在分享會上,陳嘉映談道,在格非的小說裏,【登春台】是他讀過的最喜歡的一本,因為「故事性很強」,「寫的是當代的生活」,而且主要地點在北京上地一帶,「我差不多一輩子都住在海澱區,所以什麽東北旺,京城高速,一看就覺得很親切。」

分享會現場。
談及小說中的四個人物,陳嘉映坦言,假如從人物型別而言,他更喜歡周振遐的兄長蔣承澤,「我更喜歡那種生命力特別旺盛的人物。在周振遐的記憶裏,實際上一直是蔣承澤在推動他、溫暖他、給他熱量。我有一兩個朋友也屬於那種精力超級旺盛的,我看著一方面頭暈,一方面我又佩服。」與此同時,陳嘉映也認為【登春台】寫得很「安靜」,這種安靜的調性大抵來源於周振遐的性格。「雖然他居於董事長之位,但是那種不斷向上的時代精神,周振遐身上沒有。他反而說最好渺小一點,最好不為人知一點,這個我覺得感情上跟我比較相通。」
在提問環節,一個讀者問道,當下一方面每個人都想跟別人建立真實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會產生恐懼感,甚至「社恐」、「水泥封心」,不願與他人打交道,如何應對這種情況?
格非回答:「造成我們人生痛苦的非常大的一方面,來自於人際關系,這個從古代就有。當然現代聯系性更增強了,它會使得我們的痛苦變得更加復雜。」就個人經驗而言,格非坦言自己比較喜歡孤獨:「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獨處,透過控制我們現在到處泛濫的這種聯系性,找到那種真正意義上的聯系性。」

格非在分享會現場為讀者簽售。
南都專訪茅獎作家格非
在當代小說領域做一些新的嘗試
南都: 請談談您寫【登春台】這部小說的初衷。
格非: 我對當代小說已經很厭倦了。不管是看國內同行的作品還是看國際上的作家的作品。我上次跟畢飛宇在作協開會聊到這個話題。我說,現在很多人作品寫不好,不光是國內的作家,我覺得國際上有些大牌的作家寫的東西也並不好。這不是作家單方面的問題,主要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同質化的、了無生趣的現實。現實生活的可能性我覺得已經被窮盡了。閉上眼睛你就能知道兩年以後、三年以後、三十年以後會怎麽樣。因為大的趨勢是不可更改的。所有的東西都被規定好,朝著一個目標在往前發展,它的可能性也是可推測和可計算的。在這種情況下,生存本身的意義感很缺乏。這是一方面。如果你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摹仿論」,藝術是對現實的摹仿,那你摹仿的這個物件本身是有問題的。生存本身變得非常簡單和自動化,在這樣一種狀態下產生了厭煩感。
另一方面,從19世紀狄更斯、巴爾查克開創的所謂的寫實方法,它當然不是一成不變,它一直在發生很多變化,後來也經歷了現代主義運動對它的批判。但不管怎麽樣,一兩百年以來,寫實還是一種最主流的敘事手段。在中國,上世紀80年代作家們也做過先鋒小說的實驗,但到了今天,寫實又變成了鐵板一塊的東西。這跟市場化以及我們的認知、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甚至跟社會的變化有關。當下的社會不太願意讓人再去冒險了。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境遇裏,要遠離疾病,遠離危險,這樣的話所有的領域人們都不敢冒險了。因此,寫實成為文學創作中很重要的方法。但以這樣一種方法應對今天的現實我覺得是很無力的。我想,能不能再做一些新的嘗試?
南都: 【登春台】寫了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四個人物故事,每個人物的人生經歷相對獨立,最終因為神州科技公司而產生了關聯。為什麽采用這樣的敘事結構?
格非: 我不願意回到現代主義的老路上去,重新來透過作品的陌生化,透過形式的復雜變化,制造讀寫之間的疏離感。我不太願意很簡單地回到現代主義,回到卡夫卡、喬伊斯。但是,我也不願意再重蹈今天泛濫的現實主義的覆轍。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能不能在表層敘事上保持可讀性和可理解性,對讀者來說相對友好一些,但在結構上增加它的密度感和困難。寫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寫一個完美的傳奇故事太容易了。我想透過四個不同的人,在他們的內部建立起復雜的關聯,這是我在寫這部小說時首先考慮的問題。
實際上我在寫的過程中也采取了一些方法,比如增加了四個人物之間的「人物間性」。你大概也知道,因為社會的急遽變化,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但由於交通、資訊、傳媒的發達,每個人也都在變成同一個人。每個人的命運也都差不多。能不能透過四個不同的人打破這種同質化,然後再重新建立某種關聯。關於這個問題我不能講得太多,太多的話有點指導讀者的意思。
南都: 每個人物只寫了一章,組合起來會不會像四個中篇小說組合在一起?
格非: 完全可以這麽理解。因為實際上這也是我的一個考慮,你把它當成四個單獨的故事來看也沒有問題。因為有不同的讀者。我看已經有人回饋,認為這是四個人物的群像,或者四個人物的小傳,這麽讀我覺得也很好。四個人物表面上的聯系性也有,我比較看重的是內在的聯系性。但這種東西讀者是否能夠讀出來我並不知道。
南都: 這其實有點顛覆傳統長篇小說的固有結構。
格非: 【登春台】我認為介於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和系列小說之間。比如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當中每個故事都不相關,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他是透過這種辦法把它寫成了一個系列。但【都柏林人】的方法並不適合我,我不希望把它寫成一個系列,我希望在所有人之間建立關系,傳統鐵路索上的聯系,比如人物經歷彼此鑲嵌,同時人物和人物之間還有更內在的聯系,這方面我花了很多功夫,我覺得也比較隱蔽。比如說在第一章裏,沈辛夷的母親賈連芳,這個人做什麽事情都是失敗的。但是到了第二章,陳克明也在不斷失敗,但是每次失敗之後他都能站起來,到了關鍵時刻命運就會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四十年,有的人不知道怎麽就發財了,就成了幸運兒。有些人也並非沒腦子,也並非不勤奮,但他就是不能成功。這實際上是一個共同時代裏人類命運的關聯。小說裏有很多地方都是有暗示的,比如,賈連芳和陳克明兩個人都生在大年初一,他們還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在寫的時候有一個動機,把陳克明寫成賈連芳的「倒影」或者「映像」,這就形成一個很奇妙的聯系。
比如說第一章裏的廁所的故事在第三章裏也重復了;比如說寺廟,第一章沈辛夷父親幼年寄居在寺廟,他對寺廟的感覺和第四章裏周振遐對寺廟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人都是被寄養的,這種聯系在小說裏很多很多。我希望讀者能夠認真地讀出來。
為什麽四章之間密度感很強?正是這些細節增加了小說的復雜性,它與故事本身的流暢之間形成一種張力。
南都: 在小說的四個章節裏,第一章沈辛夷和第四章周振遐使用的是第三人稱,第二章陳克明使用的是第一人稱,第三章竇寶慶使用的是第二人稱,請談談您不斷轉換敘述視角的用意。
格非: 從技法上,與我剛才講過的對當代寫作的某種厭倦有點關系。我最近在思考,我們經常透過二元對立的方式來討論城市/鄉村,古代/現代,傳統/現代性的問題。從方法上來講,從修辭上來講,我們也會覺得,你使用的是這種或那種敘事方法。
第一章我想采取很簡單的第三人稱限制視角,就是人物視角。第二章變成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到了第三章我就用第二人稱,不是說非得使用不同的人稱,而是我感覺上認為應該做一些變化,我希望到了第三章與前兩章的節奏有所不同。因為第一章、第二章有人稱變化,但敘事的方法是一致的。我原來擔心第二人稱很多讀者不適應,但後來大家跟我反饋,其實第二人稱更好看。我也沒想到。到了第四章基本上是一個全知視角。
我想,我們曾經有過的所有方法,包括傳統的方法,現代主義的方法,在寫作的時候都可以拿來使用。我越來越傾向於這個觀點:我們不要在兩個裏面選邊站。不是說你寫當代的題材就一定具有當代性。也不是說你讀【史記】,讀【左傳】這些古代的東西就沒有當代性。有些遠久的東西也能激動我們的心,我們在讀的時候也覺得它在對我們當代人說話。我認為我們很多當代作家寫的就沒有當代性,寫的是一種遠去了的,早就過時了的東西。可是你讀先秦的散文,你可能會發現裏面有很尖銳的當代性。所以我認為,不要在兩個東西裏選,傳統和現代都可以用,你把它融入到整體的敘事策略當中就可以。這是我在用四個人稱時的考慮,所有的人稱我覺得都可以嘗試。
南都: 第一人稱的角色陳克明是您代入感最強的嗎?
格非: 也不是。你要想到,如果人稱不變化,全是他他他他,這是我不能忍受的,這就變成了四個獨立的故事。如果你在人稱中稍微做一點變化,這個變化裏是有聯絡性的,反而會透過人稱的變化把這種聯絡給勾連起來,這是一種直覺。透過人稱的變化,雖然變成了另外的故事,拉開了敘述的空間,但很奇怪的是,你會發現一種悄悄的聯系在敘事上被建立起來。就好像是同一個故事我用了四種方法來講。我剛開始寫這本書就有一個想法,我不知道有沒有實作,我想把這四個人寫成同一個人。
比如說,你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了財,我沒有發財,並不表示你跟我不一樣。你的發財是建立在我沒發財的基礎上的,我們倆其實是同一個人。這是我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在觀念上的考慮。這四個人其實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雖然他們的生存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一方面要拉開距離,這四個人有的是從江南過去的,有的人出生在甘肅,有的人出生在北京,每個人的生活背景和地域都不一樣,但在同一個時代裏,人的命運感是共同的。我們共同處於時代的巨變之中,人與人之間是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四個人是不能分開的。
中國的城市仍有「城鄉二元性」
南都: 小說裏的四個人物都原本都出生在鄉村(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肅雲峰鎮、天津城),伴隨著命運的推動和時代的分裂,他們來到北京學習、生活、工作,在大都市裏紮根。但無論怎樣,鄉村就是他們拖拽在身後的一片陰影,這片陰影裏有傷痛,有罪孽,也有慰藉。您為何如此關註「來自鄉村的城裏人」這樣一個群體?
格非: 鄉村問題我的看法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樣。中國現在的社會狀況,其實同時包含了鄉村和城市的因素。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上海這樣的國際化都市之外,你也可以說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當然中國有大城市,有人口很多的大都市,但它所奉行的基本倫理都是鄉村的倫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今天我們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但並不意味著這些人進入城市就真正變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我們今天在北京隨處看到的問題都是農業文明的問題,不是工業文明的問題。這二者是混雜的,也恰恰是中國目前社會狀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即兼有城鄉二元性。比如說,城市裏需要公共空間,需要獨立性,需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新的倫理秩序,你覺得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嗎?根本沒有。還是那種大家族,那種不打招呼就到你家來了,大家不遵守交通秩序,不遵守公共秩序,甚至不遵守一般的法律規定。這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哪怕在比例上很大程度上已經城市化了,但觀念上很多人也還停留在農業文明時期。
當然也有很多新東西,特別在沿海城市。你也不能說在中國社會裏就沒有孕育出現代的新的東西,當然有,而且因為是後發國家,有些東西它甚至走在西方前面。比如我們很多事情的效率非常之高,速度非常之快,更加沒有負擔,在某些領域裏面,中國的現代性又表現得非常典型。但是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始終籠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南都: 我的印象裏鄉村現在漸漸雕敝,城市在不斷影響鄉村。但在您眼裏情況恰好是反過來的。
格非: 對,實際上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很多好的方面可以從這樣一個二元結構當中得到解釋,所有不好的方面也可以從這個當中來找到解釋。我們混雜了現代都市、現代意識、現代性和幾千年延續的傳統農業文明。這樣一種混雜性我覺得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會結束,所以這也是我希望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的原因。不要以為你進了城就是城裏人了,同樣,你現在去到鄉村,你以為你走進了一個真正的鄉村,其實鄉村也已經城市化了。無論抽水馬桶、衛生裝置還是道路網路系統,鄉村都不缺乏,它跟城市有什麽區別?但是從人的價值觀和倫理角度來說,城鄉之間確實有很大的交錯性。
南都: 【登春台】這個小說讀下來,我覺得幾個主要人物在城市裏的成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透過勤勞聰明努力獲得的,這一點有別於大多數人的期待視野。為什麽這樣設計?
格非: 從實際的生存狀況來分析的話,我們以為一個人辛辛苦苦,努力打拼,一代人兩代人,就能夠在城市裏立足,但現實不是這樣。那些金融大鱷,那些取得很大成功的人,你覺得他是透過艱苦的努力,透過很好的教育,然後一代一代積累出來的嗎?比如說,我們講一個普通人,這個普通人的命運變化,你覺得可以像數學那樣列出算式來,一步步往前推進的嗎?生活中充滿了隨時隨地的變化。當然從階層的角度來說,我們也知道當前的階層在不斷固化,但這個東西也是一個表面現象。你要描述改革開放一個三四十年大的歷史運動,你會怎麽看這個變化?我認識的很多人就是成功了,而另一些人墜入了黑暗之中。從個體的角度來說其實也是如此。這種變化我覺得是隨時發生的。
當然,我們今天對於未來的可能性會看得比較清楚,因為這個社會越來越傾向於一個固定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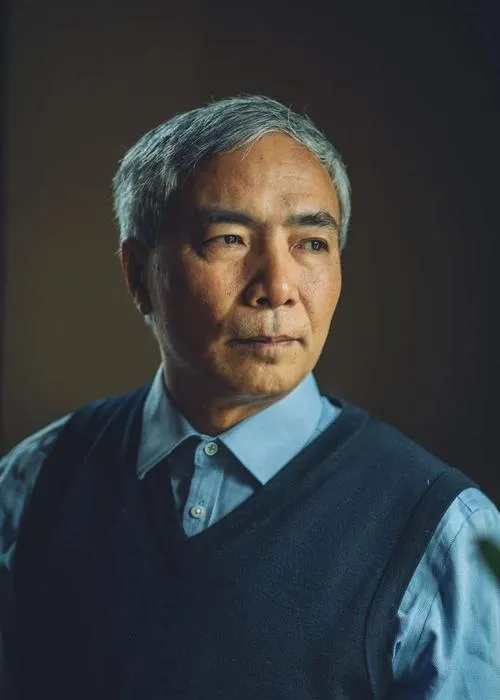
著名作家格非。
文明的發展傾向於將所有人「連線」在一起
南都: 神州科技聯合公司是一家市值600億元的物聯網公司,這家公司有現實原型嗎?您對於當代生活裏的「萬物互聯」有什麽感觸?
格非: 在這個作品裏,如果說我希望對某一個中國社會的特別的問題加以研究和表述的話,可以簡單地把它理解為「連線」或「關聯」。我會傾向於用一個物聯網公司來貫徹我的想法。
實際上,佛洛伊德問過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文明為什麽是沿著這樣一個路徑發展的?他考察了人從原始狀態,如何慢慢地建立起國家、政府、社會組織,這些組織如何越來越稠密,越來越趨向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把所有人都聯系在一起。文明為什麽要這麽做呢?比如說要強調愛,動物的話就是父親母親,父親的作用很有限,主要是母親撫養子女。人一開始也只有動物性,但他慢慢地發展出了非常復雜的社會系統。這個社會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就是希望把所有人聯系起來。中國的五倫當中,除了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外,還增加了一個朋友,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把兄弟關系擴大到陌生人。到了現代,這種變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佛洛伊德就問,文明何以這樣發展,它的目的是什麽?我們把文明看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的本質性規定是什麽?它為什麽這麽發展?佛洛伊德的解釋是,它的目的只有一個,把所有人連線在一起。我們從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化可以看出來,原來需要連線就必須有道路,中國的路修得很多。需要有資訊,當我們拿著手機在看的時候,所有人都聯系起來了。這是非常迅猛的。
我小時候生活在鄉村,我在十五歲之前沒有出過家門,連縣城都沒有去過。你就是被封閉在一個單獨的地方,你沒有聯系性,你就是傳統宗法制度的延續。你在村子裏犯了法,做了壞事,你的父母就會蒙羞。因為你就生活在那個群體裏。但是你遲早要走出來。這個小說的開頭放在80年代,那時候中國社會飛速發展,人從鄉村裏走出來,你從一個地方到了另一個地方,誰都不認識你,你和一些毫無關系的人建立起了聯系。而這種聯系性越來越頻密,馬路上那麽多的監控,那麽多的網路攝影機,所有人都處在電腦的、演算法的統治之下。這種聯系性變得越加突出。
悖論在哪裏呢,本來建立聯系性是為了更加有愛,能夠消除人的孤獨。但恰恰相反,你越是在人群之中就越會孤獨,而且這種無望感和無力感變得更強。這樣一種聯系性我覺得是需要思考的。這是現在的資訊文明導致的一個變化,這個變化在中國尤為典型。
我們現在雖然講個人空間,但實際上你所有的私人空間都被別人侵占了。開啟手機就知道,你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別人的思路別人的想法別人的愚蠢別人的睿智,這種侵入性非常厲害。事實上,有一種不太好的連線是外在的連線,透過工業化,透過商業,透過資本執行,透過欲望的擴大化,把人聯系在一起。
我去過幾家物聯網公司,我也很感謝他們給我提供的便利。透過朋友去參觀他們的公司,看他們的營運模式。比如車聯網是怎麽建立的,做了很多記錄。說老實話,我覺得非常震撼。當你看到車聯網的大熒屏,無數的光點在一個螢幕上閃爍,每一個光點代表一輛車,一下子在同一個時空裏,幾十萬上百萬在外面跑的車一下子呈現在你眼前,這些車正在去新疆、福建、台灣的路上……它形象地告訴你什麽是聯系性。僅僅透過運輸網路的車隊,你可以有一個極其直觀的印象。它是時實不斷變化的,連司機打盹兒都能監控得到,並且透過幹預進行批評警示。很神奇。每一個人都被納入到系統的監控當中,這是商業執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但我覺得同樣有另外一種連線,它是人與人之間高度的精神上的連線。這兩個主題作品裏都有描述。卡夫卡當年遇到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我是選擇個人性還是選擇社會性,我是選擇獨處還是生活在人群之中?如果獨處的話,你是毫無希望的,你被整個社會排斥。如果你在群體之中,你是同質化的,你會感到越來越大的孤獨。這個命題到了今天變得越來越典型了。所以我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考慮到兩種不同的聯系性。一種就是表面上透過商業資本建立的聯系性,這種聯系性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困擾。但同時,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嘗試一種新的連線。我們為什麽閱讀古典文學,你是否希望和杜甫建立心靈的聯系?你看起來在家裏獨處,但你同時不是在讀書、聽音樂,接受貝多芬嗎?你的心靈不是仍然在靠近嗎?所以孤獨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連線方式。因為你孤獨並不等於什麽都不幹,而是重新建立一種真正重要的聯系性。這是整個作品的中心。
南都: 小說裏的神州科技聯合公司位於春台路67號,主要人物也都是這家公司的員工或創始人,除了這一層聯系,小說的題目【登春台】是否還有更深的寓意?【登春台】跟您之前的【望春風】還有一點對仗的感覺。
格非: 疫情當中我在重讀高明那本書【帛書老子校註:新編諸子整合】,印象非常深。讀到第二十章,老子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二十章的內容很廣泛,它裏面其實討論了很多問題,其中還有一句話,「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當我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就在筆記本上註明,小說題目就用【登春台】。 實際上「登春台」討論的就是眾人和個體之間的關聯,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這是「眾人熙熙,如登春台」的本意。
但寫作的時候我發現了你說的這個問題,前面有【望春風】【春盡江南】,裏面都有春,我豈不是成了一個寫「春」的作家了?還會有人說,【望春風】【登春台】,是不是要寫成三部曲?這個我覺得不能忍受,於是改了個題目,叫【浮生余情】,具體來說就是浮生剩下來的一點感情。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它剩下來的一些東西。這也是這個作品裏的主題。這個作品裏寫了很多情感,母子之間,夫婦之間,周振遐和姚琴之間,我覺得用【浮生余情】也挺好,人生到了終結之時,剩下來一點東西,這個帶有強烈的對歷史的回顧的感覺。剩下來的感情,也就是殘留物。但是交到出版社,編輯認為【浮生余情】不如【登春台】好,【登春台】多麽簡潔有力。我跟他們講了我的顧慮,有人已經說我寫「春夢」了,我沒有寫春夢的意思。但出版社的編輯說,其實沒關系,好比說這個小說轉譯成英文,完全是兩個不同的題目,根本不用在乎題目有個春字。【登春台】不是因為故意要寫春,而是老子的話裏就是「登春台」,不用拘泥。
小說需要「熟悉」和「陌生」的轉換和再轉換
南都: 退休後的周振遐喜愛蒔花弄草,小說裏涉及許多養花的專業知識,您自己在閑暇時間也有養花的愛好嗎?養花給您帶來什麽樂趣?
格非: 我是一個喜歡養花的人。我在好幾個地方,只要有一個院子,我肯定會種花。不光是花,包括樹,我對所有植物都有感情。因為我是江南這個地方的人,對於山林、植物感情很深。看著植物長出來感覺會非常好。小說裏寫到的所有歐洲月季我都養過。但我現在不大養花的原因就是太累,它需要你付出的心血是難以想象的。比如盛夏季節一天要澆水兩次,早晨要在八點之前,晚上在太陽落山之後,兩次水都要澆,如果不澆的話花很可能就會死掉。我小說裏也寫到植物生長帶來的煩惱。我現在因為年紀慢慢大了,覺得耗費體力。可如果不好好侍弄的話,又覺得對不起它。所以我就不買花了。
我兒子原來小學有一次課外活動,他的老師給了他一盆朱頂紅。那盆朱頂紅我在清華養的,拿回來以後就放在我們家陽台上。那盆花我們從來沒有下過任何肥料,隨它去,也沒怎麽照顧。但是它不斷地長,不斷地開花,不斷地分枝,我們送給鄰居送了很多。那個花一直到現在還在開,在我們的北陽台分成了好多盆。朱頂紅有很多種類,它有幾個亞種是很漂亮的,我們家的那顆我覺得也很美。
南都: 小說裏有好多上地附近的真實的地點,包括周振遐經常去的金地花卉市場。用文學作品寫當代都市生活,尤其是大家較為熟悉的都市生活,您覺得作家面臨的比較大的挑戰是什麽?
格非: 一個方面,整個現代文學跟傳統文學的區別就在於自身的個人經驗的問題。這個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的,這是研究小說敘事的人的共識。傳統的文學、民間故事、傳奇史詩,都是歷史故事,全都是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現代文學寫的就是個體。這是必須的,你不寫個人經驗又寫什麽?
我有一個看法,文學首先第一步是把陌生的東西變成熟悉的東西,比如說物聯網公司,你需要去看的金地花卉市場,這個環境你不熟悉,你需要把它變成你熟悉的東西,這是你的經歷導致的。有的時候是透過調查走訪,把它熟悉化。但熟悉化了以後會造成你說的這個問題,你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會跟別人的經驗交叉。它缺乏陌生感,需要再度陌生化。作品裏寫出來的東西讓人家感到是一個熟悉的,我們的經驗是可以互通的東西,不能完全不具備交換性,那就是現代主義的寫法了。我覺得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具備經驗的可交換性,這是必要的。然後在可交換性的基礎上你去努力寫一點陌生感,也就是不可交換性,那就是獨特的東西。獨特的東西也不能太多了。
我覺得我跟你的不同可能很小,但是這點不同很重要,它是區別你和我兩個個體的最重要的特征的指標。這是我一貫的信念,我覺得小說需要某種熟悉和陌生的轉換和再度轉換。
小說裏重要的是文字能呈現出來的「無」(福柯語),文學中最重要的是它沒有寫出來的東西,需要透過你的想象去加以補足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停留在文本邊緣的,需要讀者去捕捉。我覺得這一點點光亮是極其重要的,小說裏有沒有這一點東西,是我個人區分一個作品的好壞最重要的標準。
「待訪性」是文學的固有特征
南都: 您現在的學生更偏好於哪一類的文學作品?原因是什麽?
格非: 我很難判斷。如果你挑出十個人,他們都喜歡現代主義的東西,這十個人裏面可能相當一部份是年輕人。年輕人為什麽有人傳統寫實,有人喜歡現代主義,還有人喜歡更庸俗的流行文學呢?我覺得取決於他在年齡別段讀什麽作品。人的閱讀趣味實際上是被塑造的,而不是天生的。所以我和我的朋友都建議,孩子在十四五歲或十七八歲這個年齡段,他讀的書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美國人當年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民意調查,為什麽某個區域的人特別喜歡讀經典著作,對於流行作品根本不屑一顧?為什麽集中在這一地區?他們發現,這個地區的父母可能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會引導小孩在關鍵的年齡段讀一些什麽樣的作品,然後孩子慢慢地會喜歡一些有深度的作品。如果從來都是被流行文學所餵養,慢慢形成了固定的趣味,再用這種趣味去接觸嚴肅文學就會出現一些問題。這個趨勢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體現的還蠻明顯的。我感覺這些年人們的閱讀趣味,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跟以前相比,正在變得越來越狹窄化,更多地受制於時尚的影響。獨立思考的人越來越少,有自己特殊趣味的讀者越來越少。當然這不是年輕人的問題,這是社會造成的。
南都: 在各種遊戲、短視訊、網文擠占人們的註意力的當下,您認為嚴肅文學怎樣才能爭取並留住自己的讀者?
格非: 我的看法是這樣,一般意義上我們心目中的比較有深度的文學,那種文學的傳播機制和流行文學是不一樣的,流行文學要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一下子占有大量讀者。所以他們會玩很多噱頭,他們會參照更多的時尚因素來吸引群體的關註。但是有深度的、相對來說偏向於純文學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傳播途徑我稱之為「待訪性」——等待別人存取。
現代文學的發生只有短短一兩百年時間,以前的文學,比如清代中期以前的文學,都是待訪性文學。一個作家寫完,作品還沒出版他就死了,無論杜甫還是曹雪芹都一樣,他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讀者。「待訪性」我覺得是文學的固有特征。好的文學就是你建立某個東西,你完成這項工作,然後就看它自己的命運了。它有它的隱秘的傳播渠道。好在現在出版一部作品越來越容易了。但是這樣的東西它能不能留下來,會不會有人閱讀,取決於很多因素,也取決於社會的變化,我覺得跟作品的好壞不是必然的關聯。巴哈活著的時候作品沒有幾個人聽,我們現在把他排在所有作曲家中的第一位,但那也是他去世後很久很久的事情。梵高也一樣,他一直就是等待存取的狀態。
對於作家來說,寫作過程中,他已經跟想象的讀者進行了某種交流,他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快樂和報答,而不是這種報答一定要具象化為多少銷量,多少版稅,或者讀者怎樣贊揚。實際上他在寫作的時候已經獲取了這一部份的收益,他在跟別人對話,也在跟另一個自我對話。作品的命運,作家沒有必要太關心,因為總會有人讀。
我自己是很相信緣分的。有的時候我會碰到一個特別特別喜歡的作家或詩人,原來很多年不讀的。但突然有一首詩擊中我,我就會不斷地買他的書,不斷重讀。比如說里耳克,里耳克的【杜伊諾哀歌】和【俄耳甫斯十四行詩】是他晚年的作品,我是在作協開會的時候,正好帶本書晚上閱讀,一下子讀進去了。從那時開始我對里耳克發生很大的興起,不斷重讀。其實里耳克本人未見得會知道有個人會在開會的間隙去讀他的詩。我覺得真正的讀者不在於多少,文學的命運還是很神秘的。
南都: 在寫作的時候會不會有未來將作品影視化的打算?
格非: 文學最大的魅力在於文字帶來的激發我們想象的力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裏有一句話:「她想死,但她還是想去巴黎。」這兩句話放在一個很小的句子裏。一個人想死的時候已經很絕望了,可是她還想去巴黎,她還是有時尚的虛榮心,她在臨死的時候還有巨大的虛榮心。這個句子很短,像詩歌一樣,呈現出極其復雜的內涵。強烈的對比帶給人的震撼極其巨大。這就是文字的力量,這種力量電影是無法呈現的。所以我是覺得,電影的改編其實跟小說沒有關系,它就是把小說的事實部份作為一個基礎,小說裏寫到的情節作為基礎,透過導演的再創作變成另外一個東西。但是小說裏僅僅有故事和情節嗎?當然不是。所以影視化這件事不必強求。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