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散文寫作這種體裁而言,作者太多,而優質名家少見。業內把劉亮程稱為「20世紀最後一位散文家」;而21世紀初,也有一名以書寫鄉村和自然領域題材而快速崛起的散文家——傅菲。
傅菲早年從事詩歌創作,十年之後擱筆。2002年四月,他的散文處女作【露水裏的村莊】發表於【人民文學】,此後開始了井噴式高品質散文創作。詩人、散文家黑陶曾說,「2006年中國散文應該叫傅菲年,在刊物隨處可見傅菲作品。」作為一名散文家和資深田野調查者,近些年來,傅菲專註於鄉村和自然領域的散文寫作,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元燈長歌】等三十余部。
【蟋蟀入我床下】是傅菲在長期而細致的野外觀察中,把自然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而創作的全新散文集。全書分「蟋蟀在堂」「自牧歸荑」「關關雎鳩」「愛有寒泉」「采采卷耳」五輯,四十余篇散文詩意叢生,極富自然趣味,以時序為時間緯度,視自然與鄉間時俗為經度,寫南方(贛東北)節令、物候變化、自然個體生命、人與自然的彼此貼近和關照。
傅菲擅從日常和平常入手,從生活的具體和層疊的煙火入手,深入事物的細理,刻寫自然萬物的風情、風度,傳遞自然、生命以及與生命發生的溫暖情感,並以中國式的智慧探尋中國人的自我安慰和超脫,將人在自然中的愜意和自渡精準地呈現出來。
傅菲的散文中,對山川草木植物動物的關註與表達占據了令人驚異的比重,這在當代中國散文作家的創作中並不多見。如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江子所言,「他字裏行間流布的風土與天色,哲思與情感,線條與節奏,喜悅與悲傷,是中國的,是當代的,是傅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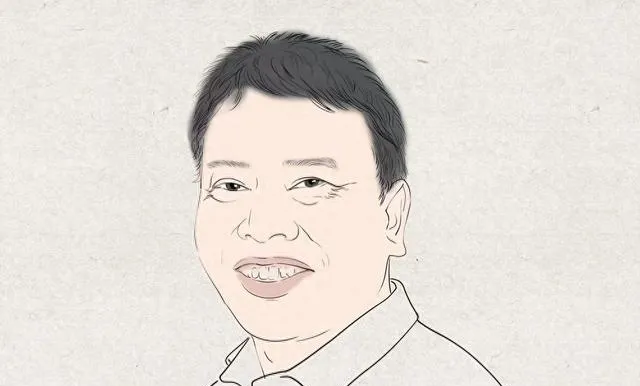
得益於田野調查,開始寫散文
「一個年過七十的大叔走在我前面,肩上搭一個棉布縫制的長布袋,低著頭往山上走。布袋裏不知裝了什麽東西,半鼓半癟。他腳上的布鞋半濕半幹,他的頭發半黑半白,他身上的衣服半灰半麻,他的腳步半輕半重,他手上的傘端舉得半斜半正,落下來的油桐花打在傘布上,滾下來,落在背上,滾下來,飄飄忽忽落在台階上。」
——【一些花開在高高的樹上】
記者: 您最初是先進行了十年的詩歌創作,又轉而寫散文。這個轉變的原因或者說契機是什麽?
傅菲: 習詩十年,1998年以後,我擱筆了。我寫不好詩歌,詩藝提高不了。當時我認為自己不會從事寫作了,我沒有寫作能力。
2002年4月,我抽調到「市嚴打辦」(臨時機構)編簡報。工作量不大,紀律十分嚴明。我在辦公室「塗塗畫畫」,寫了一組散文【露水裏的村莊】,投給了【人民文學】,並於第八期刊發了出來,這是我的散文處女作,自此我開始寫作。
記者: 您專註田野調查是從何時開始的?田野調查和散文寫作可以說是互相成就的關系嗎?
傅菲: 2013年10月,我開始專註田野調查。我在自然領域和鄉村領域的寫作,依賴並得益於田野調查。我的散文所呈現出來的生命力,來源於此。田野調查給予我豐富的寫作素材,給予我文字與生活現場相通,給予我鮮活、細膩、生活的細節,使得我開闊思路、深思當下,具有現實意義。
對我而言,田野調查是一項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可以認識形形色色的普通民眾,可以遇見各種各樣的物種,可以去往許許多多的偏僻之地。即使我不寫作了,我也樂意去田野調查,這是我最高級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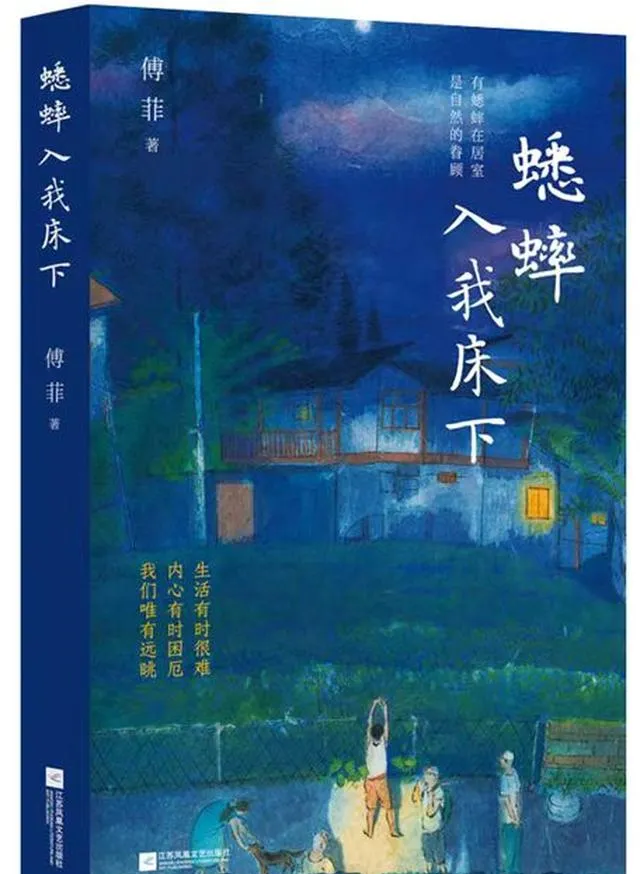
記者: 閱讀您的散文,這些充滿自然美學的文字會讓我想到陶淵明、孟浩然的田園詩,令人松弛、安閑。您也經常在文章中參照古詩。詩歌對您的散文寫作以及田野調查有什麽有益影響或有效補充嗎?
傅菲: 謝謝您的閱讀。在自然文學寫作上,我希望自己回歸本我、真我,從生活的羈絆中解脫出來。但並非「隱居」,並非逃避現實。
在青年時期,我有過十年的職業化閱讀。近十年,我很少閱讀小說、散文,大多看一些「雜書」,但一直沒有停止閱讀詩歌(包含古詩詞)。四十五歲後,我記憶力嚴重退化,能記下的古詩非常少了。詩歌,尤其是古詩,給我了古典的審美,給我了我濕潤的語感。詩歌對我的寫作影響很大,我的寫作得益於詩歌的閱讀。

長期訓練和寫作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字風格
在山中生活之後,我慢慢放下了很多東西,放下無謂的人,放下無謂的事,把自己激烈跳動的心放緩。其實,人世間也沒那麽多東西需要去追逐。很多美好的東西,也無須去追逐,比如明月和鳥聲。風吹風的,雪落雪的,花開花的,葉黃葉的,水流水的。
——【鳥聲中醒來】
記者: 在寫作的各類體裁中,散文應該是最容易入門卻又不容易寫好的體裁。您是如何形成「人與自然的同頻共振,並以詩性潔凈的語言,精準地表達出來」( 2019年度儲吉旺文學獎授獎詞)這種風格的?
傅菲: 散文易學難工。其實,所有文體都是極其難寫的。所有藝術門類的創作,都是極其艱難的。因為艱難,方顯可貴。
我不敢說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您所說的「人與自然的同頻共振,並以詩性潔凈的語言,精準地表達出來」這個特性,是我寫自然文學的特性之一。
我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有自己的腔調。這是長期訓練和寫作的結果,也與自己的審美、閱讀史、經歷、性格有關,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記者: 有的作家會覺得寫散文「很消耗」,大意應該是沒有充足的生活經歷,題材會很快枯竭。您已經創作了很多散文,是如何確保寫作素材源源不斷的呢?
傅菲: 這個問題,在田野調查部份已經作出了回答。當然,這部份的回答是「確保寫作素材源源不斷」的主要回答之一,還有其他,如閱讀、思考(認知)等。
深度挖掘寫作素材、「盤活」素材資源,是散文作家必備的能力之一。沒有這個能力,就無法從事散文寫作。散文寫作確實很內耗。
記者: 劉亮程老師被稱為是繼沈從文、汪曾祺之後20世紀最後一位散文家。在您看來,一個人的散文寫作要達到什麽程度,才能稱之為「散文家」?
傅菲: 我不是文藝理論研究者,更不是「散文權威」,我沒有能力也沒這個高度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散文作家。

更富哲思和自然氣的新作
蟋蟀叫著,兮兮兮。月影上來了,印在窗戶上,如一朵潔白的窗花。桂花樹在輕輕搖動,沙沙沙。這時,才突然想起,這是農歷十月十三了。我推開窗,月如水中白玉。扶著欄桿遠眺,山巒如失散的馬群,各自奔跑。安靜了,除了蟲鳴。
——【蟋蟀入我床下】
記者: 這本【蟋蟀入我床下】中收錄的散文寫作時間跨度是多久?比起您此前的作品,這本書又有了哪些新意和特色?
傅菲: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我大部份時間在自己老家(上饒市鄭坊鎮楓林村)居住,與村人一起生活。2021年8月,我從上饒市來到德興市大茅山北麓筆架山下客居至今。我喜歡去野外,河邊、深山、田野、荒野等都是我常去的。我的窗外就是稠密、無垠的針葉林、闊葉林。我的生活就是買菜燒飯、讀書寫作、田野調查。【蟋蟀入我床下】就是在這樣的日常情境下寫出來的。
【蟋蟀入我床下】相較自己此前作品而言,從篇幅角度說,多了短章;從取材的地域、地貌角度說,更有廣度,更豐富;從語體層面角度說,更富哲思和自然氣息。自2015年以來,我出版的每本散文集都有較為集中的主題。我註重挖掘主題的深度。【蟋蟀入我床下】的主題就是「生活美學之書」,主要寫時序之美、勞動之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作為一個熱愛書寫自然的寫作者,我生活的過程就是感受美、發掘美、提煉美的過程。
記者: 我在【蟋蟀入我床下】中讀到了很多快節奏生活的都市人不會註意到的大自然的細節。比如您觀察到的「露水悄悄地在草尖凝結」。在日常,您一定也是一個非常敏感、善於觀察的人?
傅菲: 應該這樣說,我是一個對自然非常敏感的人,對自然的感受力比普通人會強很多。這是我多年田野調查的實踐結果。善於觀察是一個作家必備的能力之一。對自然的變化、對自然的色彩、對自然的個體生命、對氣象的變化,我非常敏銳。
我的生活是慢節奏,我退守到屬於「自己的領地」生活,「自己的領地」就是與大自然相近、相親。我的日常應酬非常少,我專註於「自己的生活」。
記者:徐敏 漫繪:孫婷婷 編輯:徐征 校對:楊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