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心光明,是以恒言。
似乎很久沒寫信筆由韁的談心文,今天累了,隨筆寫上一篇——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篇文章最終會說到哪裏去。
這幾天,一直有朋友讓我就海南那位電台主持人因為一句日本大地震「活該」而當夜就漲粉七百多萬的事件寫篇文章。我苦笑說,我真的是懶得寫了——再說什麽好呢?關於這個問題,我之前的兩篇文,已經把該說的道理都說盡了。
可是道理這個東西其實是蒼白無力的。大學看傳播學的書,讀到過一句話讓我印象尤深:「 能用一句話說清楚的思想,一定不是好思想,但不能一句話說清楚的口號,一定不是好口號。 」
是的,傳播與做學問不同,它遵循的是短板原理——一個社會當中,最通俗的普羅大眾,他們的思維是怎樣的、能看的進多長的文章,決定了你的這個想法能不能傳播開來。你把說理搞的越精深、復雜,傳播效率就反而越低。所以做傳播與做學問,其行為邏輯是不同乃至相反的。
就比如日本地震這個事兒,你當然可以下筆千言,給大家講些道德和修養是遠見之類的道理。但你架不住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抱有的就是那樣一種「小日本全都死了活該!」的樸素心態,這種心態如此普遍,而且如此強大。就靠你寫個幾千字能扭得過來麽?
拗不過來。
所以我們這些吭哧吭哧寫文說理的人也許都是傻子,那些看到韭浪翻滾,就磨快鐮刀、急割勿失的人才是聰明人。
你看那位主播,就靠一句「日本人活該」漲粉近千萬,這件事的影響可不僅僅是塑造了一個新網紅,而是給想做這門生意的人傳達了一個訊號。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事情,一定還會有人嘗試做類似的極端表達。畢竟,這「潑天的流量」背後是潑天的富貴,誰不想要呢?
所以相比而言,我覺盧克文這樣的人其實也有他的可愛之處——明明喊句口號就能賺到的情緒流量,他大多數時候居然願意坐下來寫篇文章。這其實相比他的很多同行來說已經非常業內良心了,你看現在另一些跑這個民粹賽道的大V,寫的文和特殊年代的大字報也沒什麽區別,通篇全是咬牙切齒的口號。
而盧克文不,他居然還肯講故事、還說理。跟九邊爭論該不該造國產豪車的話題。
而盧大師也不知是誠心賜教還是說漏了嘴,居然把他的商業秘訣也說出來了。「月薪三千的人跟別人吹牛還能說什麽呢?當然要說我們也能造豪車了。」
是的,像九邊和我們這些人,當然可以批判這個想法很無厘頭。你個月薪三千的,為國產豪車這種這輩子都挨不上的宏大敘事吹牛——肚臍眼吹小號,你咋想的你?
可是你架不住這個社會的大多數普羅大眾,他們真的就是如盧大師說的一般這麽想的。
真的是這樣。
盧大師的優勢,就在於他「起身草莽」,他特別了解小鎮青年、中年、老年是怎麽想的,而這些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大多數。是讓你看不懂的那「一夜漲粉700萬」的人群中的一份子。
所以盧大師這句話,說的不是一個主張,而只是在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所以相比之下,我們才是可笑的——人家在實誠把流量密碼告訴我們了,我們卻說理寫文,論證這個流量密碼編的有問題。該反思的不是盧大師,是我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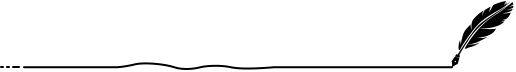
放棄諫言情節,尊重大眾意見。
寫文越久,我越深感到這句話應該當做座右銘刻到我桌子上,每天寫文前看一眼,提醒自己一下。
十年前剛畢業開始寫評論的時候我總有一種妄念,覺得自己可以靠一支筆和報紙這個平台,普及常識、讓更多人擁有理性、溫和而符合邏輯的思維方式,享受思維的樂趣。
可是,十年過去了,我越發覺得這個妄念是如此的可笑。
改變他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有限的普羅大眾的思想,是如此之難,遠非一篇千字文能夠做到。我在這十年中知覺到這種無力,但卻努力錯的方向,從周更寫到日更,從千字文寫到幾千字文,從幾千字文寫到萬字文……
但這一切真的有用嗎?
這可能是一種南轅北轍的努力。因為大多數人,文章越長,他們越是不看的。
他們固執的內心,可能只需要一句順他們心意的簡單口號而已,像海南那位主持人,給他們這句口號,他們就追捧他——目標使用者清晰,商品對路。
所以這個流量是我們的,是九邊的,也是盧克文的,但最終一定是盧克文的,甚至盧克文們也會最終把流量交出去,交給那位海南主持人式的新貴——理由無他,只因為人家的口號更簡短,更有力。
這個趨勢已經很鮮明了,你看盧大師當年那篇疑似洗稿的【文在寅的復仇】,雖然漲粉也很猛烈,但我想總不至於誇張到一夜700萬的程度。
一代新人換舊人,遊戲的邏輯又在變了。
說到底,普羅大眾看符合他們心意的爽文,就是圖個爽麽。與其聽盧大師那樣長篇累牘的論證為什麽可以這樣爽,不如就用十幾秒,把口號直接喊出來直抒胸臆。
也許有一天,盧大師們也會過氣,會被他曾經的粉絲謾罵,而我們會同情和懷念他,就像我們現如今經常同情和懷念退了休的胡錫進總編一樣。
而且這個過程,估計會比很多人想象的更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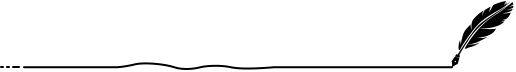
那麽在這個逆淘汰的市場當中,寫作,究竟還有什麽意義?
一年或是更久以前,我和一位同行朋友還真討論過這個問題。那段對話讓我想了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裏講述自己與錢玄同有過一段相似的言語:
「你抄了這些有什麽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抄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麽用。」
「那麽,你抄他是什麽意思呢?」
「沒有什麽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高中的時候學這篇課文,總覺得魯迅先生心態很消極、悲涼。但如今想來,我有覺得先生之心態,總還是有些奮進的——他的「吶喊」,總還是試圖去喚醒一些人。
而如今的我,卻連此念都不太有了。我還在堅持寫下去,心態更多是類似多年前讀過了另一則故事:
有人問點蠟燭的守夜人,說「你點它有什麽用?小小一根蠟燭,不能驅散這漫漫長夜。」
守夜人回答說:「我沒想過驅散這黑夜,我點起這根蠟燭,不是想改變黑夜,只是要讓黑夜不要改變我。」
嗯,多年過去,我已無心也無力去說服誰,我的公眾號、我的文章,更不可能像盧大師或海南主播那樣火爆。但我要堅持我的闡述、我的邏輯、我的底線、我的良心——為的只是不讓那日漸口號化、簡單化、情緒化、民粹化的洶洶之議,去侵染我,同化我。
盧大師、胡總編,或遲或早,面對越來越極端化的粉絲群,他們會被迫選擇——要不要被流量所裹挾,寫的更極端一些、更口號一些、更情緒,因為如若不然,他們就被那些崛起的「戰狼新貴」們所超越,所傾軋。
我卻幸運的沒有這份擔憂,我的主張、我的思想,決定了我本就不在這個生意場當中。那些不可被說服的韭菜庸眾,從不是我的目標讀者。
我就寫我默默的文,守我默默的常識。
至於您,我的讀者,您若看到這微小的燭光,願意圍聚過來,與我一同守護它。請接受我最真誠的致謝與敬意——我會盡力堅持為這些心靈相通的朋友寫作,當寒風呼嘯,我只守好這燭光不被吹滅。
我的寫作,已不再試圖去說服任何人。寫出來、寫下去,只是為了一份「我心光明」的堅守。
我心光明,是以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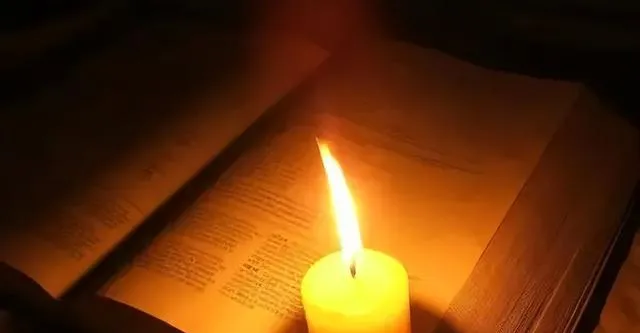
全文完
本文2500字,感謝讀完。今天累了,隨口跟大家談談心,聊做休整。
寫的比較短,想到哪兒說哪兒,望您見諒,願您喜歡,求一個三連,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