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十八世紀德國哲學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為世界哲學史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日本學者安倍能成曾說,康德哲學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學都流向他,後來的哲學又從他這裏流出。中國著名的康德學者鄭昕也留下了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時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義可以看作是應對當今時代平庸化的一劑良藥。在2024年——康德誕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聞同中國康德學會共同策劃,將陸續釋出對世界各地資深康德學者的深度訪談,再次挖掘這位哲學家的光輝精神以及對於現今世界的意義。
保羅·蓋耶(Paul Guyer)是近半個世紀英語世界最出色的康德專家之一,對當今康德學界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他於1974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匹茲堡大學、伊利諾-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大學職教。蓋耶教授對康德哲學各個分支均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入的研究。他已出版十幾本相關專著,包括基於其博士論文擴充套件而成的成名作【康德與審美的主張】(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1979),以及【康德與知識的主張】(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1987),【康德】( Kant, 2006/2014),【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奠基>導讀】( 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Reader's Guide ,2007), 【知識、理性與審美:康德對休謨的回應】( Knowledge, Reason, and Taste: Kant's Response to Hume ,2008),【自由的美德】( Virtues of Freedom ,2016),【康德的道德的理性】( Kant on the Rationality of Morality ,2019),【門德爾松與康德的理性與經驗】( Reason and Experience in Mendelssohn and Kant, 2020)。
蓋耶教授編訂的六本關於康德哲學的論文集當中,有三本屬於「劍橋指南」系列(Cambridge Companion)。他在1986至2016長達二十年時間裏與艾倫·伍德(Allen Wood)共同擔任劍橋康德英譯本(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Kant)的主編,也是其中【純粹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筆記和片斷】這三本的主要譯者。除了康德哲學,蓋耶教授在現代哲學研究領域(特別是其美學部份)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三卷本【現代美學史】(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2014)和【哲學家帶你看建築】( A Philosopher Looks at Architecture ,2021)的作者。

保羅·蓋耶在北京大學接受采訪
呂超: 您是在哈佛學院獲得學士學位的。我們很想知道您最初是如何被康德哲學吸引的,大學裏的哪些課程對您產生了影響,或者說您在中學時代已經開始閱讀康德了?
保羅·蓋耶: 在美國,高中生進入大學前的最後一年是第12年級。而在我讀11年級時,在一堂英語課(也就是每個人都要上的語言和文學課)上,老師給我們留了一份作業:找到一本你感興趣的文集,閱讀並撰寫一份讀書報告,然後在課堂上做一次口頭展示(oral presentation)。我們大致有兩個星期準備這項作業。我那時住在紐約市郊的長島。某個周末我到了市裏,乘火車回家前在車站書店裏看到一本平裝書,那就是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這本書很便宜,只有45美分,相當於現在的5美元或10美元。我買了這本書並在火車上開始閱讀,讀完時覺得它非常令人驚嘆,盡管它的結論中有一些瘋狂的東西(亦即我們對因果性的信念並不是合理的),它的論證看起來卻很棒,而這一點非常令人迷惑。我寫了一篇簡短的讀書報告,在課堂上做完口頭展示後,每個人(包括老師)都認為我瘋了,但我卻認為這很棒,是這一經歷真正讓我對哲學發生了興趣。
隨後的暑假我參加了為期六周的哲學課,這門課快速地介紹了各種哲學潮流,一個星期是關於分析哲學的,一個星期是關於存在主義的,我們甚至可能還上了一個星期關於中國哲學的課。當我進入哈佛學院讀本科時,我想要學習更多的哲學。實際上,那時我還在考慮成為一名建築師,但在入學的第一年我擁有了如此出色的哲學老師,以至於之後我就堅持做哲學了。我在本科之前就讀過一些康德,但讀得不多,我確實讀過叔本華,叔本華有一些基於康德思想的關於因果性的觀點,他在某種程度上試圖對休謨做出回應。當我進入哈佛學院時,我從不同的老師那裏對康德發生了興趣。本科第一年我們上了一門整整延續一年的人文學大課,這門大課是由兩名哲學系的老師講授,其中一人從前蘇格拉底哲學講到聖奧古斯丁,另一人則講授了現代哲學和更一般意義的現代思想。我在這門課中讀到的一篇文本是【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的第一部份,康德在那裏對自由意誌問題給出了他的解答。這門課有400多名學生,我們分成不同的小組,由高年級研究生帶領我們這些本科生學習康德的道德哲學。

康德
隨後的第二年,諾齊克開了一門【純粹理性批判】的課。自從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路易士(C. I. Lewis, 他也有點兒是康德主義者)於1955年退休後,哈佛已經有十二年沒人開設【純粹理性批判】的課了。路易士訓練了許多出色的康德學者,例如察爾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但他退休後,沒有做同樣工作的人接替他的位置。諾齊克當時還是一位助理教授,他之前沒有研究過康德,也不是哲學史專家。但諾齊克聲稱,對他來說現在是時候研究一下【純粹理性批判】了,而還有比開設一門課程更好的研究方法嗎?諾齊克不需要成為一位康德專家,他是我遇見的最聰明的人之一,是我遇見的最快的閱讀者和最快的學習者。諾齊克顯然在之前的夏天,或是花了幾個月時間通讀了【純粹理性批判】和當時已有的評註。那是1967年的春季,而這意味著前一年(即1966年)施特勞森的【感觀之縛】和貝奈特的【康德的分析論】已經出版了。這兩本書使康德在分析哲學看來變得有趣,而諾齊克也讀了這兩本書,在那個時刻進入康德哲學是非常激動人心的。諾齊克課上的一些學生正在攻讀第一學位,一些學生則在做博士研究。諾齊克再也沒有教過這門課,他並沒有成為康德專家,我或許是那門課上唯一成為康德專家的人。我發現康德的某些觀點有趣而可信,另一些觀點則非常瘋狂,比如先驗唯心論。【純粹理性批判】這部文本本身在我看來既迷人又充滿挑戰性,我在搞懂它之前都不願意放下它。其他學生繼續做其他事了,我則堅持研究康德。
在我進入研究生階段的第一年(即1969到1970年),羅爾斯開設了道德哲學的課程。他並沒有講授【正義論】,這本專著在之後的一年才出版。在【正義論】印刷之前,他分發給了我們一些其中的章節,但他實際上是用哲學史材料來授課的。羅爾斯在道德哲學課程中講授了亞里斯多德、休謨、康德,或許我們還讀到了密爾。羅爾斯在政治哲學課程上講授了霍布斯、洛克、馬克思,或許他並沒有把康德包括進來。但無論如何,羅爾斯都講授了康德倫理學。我開始對康德倫理學產生了興趣,而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在這上面做太多功課。當【正義論】在下一年出版時,位於全書中心的章節被稱為「康德式的解釋」(Kantian Interpretation)。羅爾斯用康德式的術語來解釋自己的工作,而這使很多人轉向了康德倫理學。羅爾斯當時已經有很多學生圍繞康德倫理學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工作了,這些學生大概比我年長六到七歲。在1960年代晚期,是施特勞森和貝奈特使康德的理論哲學變得激動人心並且與當時的哲學思考具有相關性,而在1970年代初期,則是羅爾斯使康德的道德哲學變得激動人心並且與當時的哲學思考具有相關性。
之後你可能會問我是如何開始研究康德美學的,這是我博士論文的主題,也是我在第一本書中以及之後一直在寫作的主題。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部份。首先,在我準備寫博士論文時還沒有真正研究過康德美學,而且那時候也沒有任何人深入研究過康德哲學中的這一部份。其次,我的父親是一位畫家。他主要靠做廣告藝術和設計為生,但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畫家。每次我回家度假時,父親都會立即把我拖到工作室,向我展示他最近的作品,並問我感覺怎麽樣。我那時想的是:「我喜歡這幅畫,不太喜歡那幅畫。」但當是你的父親提出這個問題時,你會想要談點更為實質性的東西,所以我就想:「或許從美學中我能找到一些可用的原則。」當然,你從美學史裏學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原則。你無法以在數學中找到規則的方式那樣,在美學中找到允許你對特殊物件做出判斷的規則。當然,關於藝術之於人類生活具有價值的不同方式,你可以得到更一般的觀念。一旦你擁有了這些一般的觀念,你便可以開始以一種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談論個別的藝術作品了。但你找不到任何「規則」,你無法「證明」你自己是正確的而對方是錯誤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父親是個思想開明的人。
呂超: 您是劍橋版康德全集英譯本的主編之一。我們很好奇如此龐大的工程是如何成功地完成的。比如不同的譯者會對術語有自己的偏好和各自不同的轉譯方式,您作為主編是如何協調所有這些譯者的?
保羅·蓋耶: 艾倫·伍德(Allen Wood)和我的確嘗試著制訂某種形式的指導規範。艾倫和我制作了一張主要術語表,並將它發放給所有譯者,同時艾倫和我也將自己作為譯者來看待。我自己堅持如下的轉譯原則,亦即譯本的讀者應當和原始文本的讀者擁有一樣多的、最好是同樣的解釋工作。如果某種東西在德語中是隱晦的和復雜的,那麽它在譯文中應當依舊是隱晦的和復雜的。如果某種東西在德語中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那麽它在譯文中應當依舊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否則的話,假若轉譯將原文中隱晦的東西變得清晰,它就會向讀者關閉解釋的可能性,譯者就是將自己的解釋強加在作品上。當然,譯者不可避免地總在把解釋強加在作品上,但他需要試著有意識地去克制。譯者應當盡量讓句子保持原樣,當原文中句子很長時,譯文也應當保持長句。當原文中句子很短時,譯文也應該保持短句。
當轉譯【純粹理性批判】時,艾倫和我首先做了第一份草稿,然後修剪,訂正彼此的工作,等等。我有時會回頭看看坎普·斯密的譯本,用他的轉譯來熱身。我發現斯密不僅把某些長句截成了短句,有時還會把短句拼成長句,因為斯密在英國長大時養成了某種我稱之為愛德華風格(Edwardian style)的寫作方式,他或是有意、或是無意地讓康德聽起來更像一位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作家。但我們不應當那樣做。我們發展出了一套指導規範,並試圖讓每一個譯者都牢牢記住它。
對於挑選譯者我們很有信心。大部份管理工作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挑選好的人來完成所有較低層面的工作。有時候這會涉及到協商,譯者或許不喜歡我們的建議,我們就會與其爭辯清楚,有時譯者會說服我們,有時我們會說服他們。我們或許會完全不喜歡譯者的工作,把稿子退給他們,要求他們思考如何修改。我們並沒有強加文體上的統一,盡管劍橋設計了這種型別的東西。假若我們能夠重做整套劍橋康德英譯本,它或許能比現在更加統一化,但它已經花了我們太長時間,而我們都太老了。
這件工程成功的關鍵在於我們真正在尋找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來完成盡可能多的工作。【判斷力批判】最早在由兩位英國哲學家進行轉譯,其中一人去世後我才加入了工作。任何一項延續了那麽長時間的工程都會遇到這類問題: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陷入了爭執,一些人則結束了。行程中總會存在某些調整,這有時會涉及到加入新人。至於【純粹理性批判】,除了我們自己,艾倫和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因此我們把這本著作留給了自己來轉譯。至於轉譯之後的修訂工作,我會做好某一部份的第一份草稿,把它交給艾倫。我們兩人當時都有其他工作要做,都在寫自己的書。當艾倫抽出時間時,他就會對我的轉譯提出各種建議,再把草稿返還給我,然後我繼續在上面工作,反之亦然。【純粹理性批判】譯本的成功在於我們兩人擁有不同的技巧。在選擇精確的詞匯(即「措辭」[diction])上,我認為艾倫遠比我要出色,當他建議用這個詞時,他幾乎總是對的。而當涉及「句法」(syntax)時——亦即在英語裏找到可讀的方法來保存康德的長句,使句子聽起來非常像康德本人寫的,但在英語中又是可讀的——我則比艾倫出色。我和艾倫是互補的,我通常更喜歡他的選詞,而他通常更喜歡我的句法。
劍橋康德全集要求轉譯全都是新的,而不直接使用過去的譯本。這部份地出於版權的原因。當然,瑪麗·葛瑞格(Mary Gregor)已經為劍橋先前出版的單行本做了一些轉譯,她按照我們的指導規範和艾倫的建議做了一些修訂,但在【實踐哲學】(Practical Philosophy)這一卷完成之前她就去世了,艾倫最終完成了這一卷的轉譯,所以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但瑪麗·葛瑞格本人卻無法對此做出回應了。然而在其他的地方我們的譯本都是全新的。我們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盡量少地依賴先前的英譯本。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困難的。如果你研究康德很長時間了,那麽斯密的【純粹理性批判】譯本將印在你的腦袋裏,你甚至能夠聽到它。而我們試圖在腦袋裏把它放到一邊,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並重新轉譯。康德有很多著作——包括他的一些科學著作和小論文——之前並沒有英譯本,而另一些著作的譯本則有些老了。我們盡可能多地從頭開始轉譯,有時碰到非常困難的段落時也會查詢其他譯本。對於【純粹理性批判】而言,我們不僅會查詢斯密的譯本,也會查詢所有英譯本,有時是麥克勒約翰(Meiklejohn)的1855年譯本,或者繆勒(Müller)的1881年譯本,甚至是【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個英譯本,即海伍德(Haywood)的1838年譯本。有時我們會發現這些譯者比斯密更為出色地解決了一些特殊的問題。
呂超: 您的著作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在中國也非常受歡迎。但對於一些讀者來說,您對康德的解讀並非完全沒有爭議。有時您似乎把康德的思想描繪成碎片式的,甚至是自己和自己相矛盾的。同時您使用了大量未出版的筆記,有時還會直接批評康德。某些讀者可能會更偏愛伊利森(Allison)或其他學者所采取的為康德進行辯護的立場,很多初學者或許會對您的進路感到一些不安。但非常有趣的是,隨著讀者深入了解您的工作,他們會對您的著作產生更多的同情和喜愛。
保羅·蓋耶: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猜測部份的原因在於我確實想成為一名哲學家,我並不僅僅試圖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從未想聽起來不客氣,但我並不致力於使康德在學生們眼裏變得清晰。我從一開始就想要發現:康德思想中有什麽在哲學上是可信的,有什麽在哲學上是不那麽可信的。我並不想說:這些是我們今天在哲學中所相信的東西,這些是康德哲學中與之相容的東西,那些是與之不相容的東西。我想說的是:康德對什麽觀點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對什麽觀點的論證不那麽令人信服,諸如此類。我想做的是內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我想要考察康德的論證,找出他的論證中哪裏出現了缺口,哪裏存在著假設,哪裏論證得好。
有些做哲學史的人真的把自己當成了歷史學家,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研究的作者必須對於當代哲學是有趣的。相反,這些作者僅僅作為過去的片段而是有趣的。我並沒有反對這些做哲學史的學者的進路,但我對此並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嚴肅地把康德當作一位哲學家來看待,考察康德的論證在哪裏是令人信服的,在哪裏並不令人信服。我認為康德是一個十分實驗性的哲學家,他持續不斷地嘗試著不同的論證,他隨著時間不斷地發展。康德並不像休謨那樣是一個早熟的哲學家(休謨在25歲時就想清楚了所有東西)。相反,康德花了很長時間來發展出他想要達到的結論,他試驗著通達該結論的最佳方法。康德嘗試了許多不同的論證,而這些論證並不總是整齊地嵌入一個單一結構內,有時這些論證甚至會彼此處於一種張力之中。康德的結論能夠嵌入一幅融貫的圖畫之中,但他的論證卻不能。
這就是我自己閱讀康德的方式,我的體驗說服了我采取這種方式,盡管並非所有人都贊同它。然而,如果你看看【純粹理性批判】中關於經驗的類比的第二個類比的文本,亦即康德關於因果性原理的證明,你就會發現在不同學者的計算中,康德論證因果性原理的次數也是不同的,比如坎普·斯密計算出了六次。康德甚至在出版的作品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論證著同一條結論,而這是為什麽呢?也許是因為即使在出版作品中,康德也沒有確切地找到正確的方式來建構他的論證,所以他才不斷嘗試不同的東西。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康德對觀念論的反駁,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才加入了這部份文本。康德很可能在修訂行程中比較遲的階段才加入了這部份文本。而在1788到1790年間,他又草擬了十二稿對唯心論的駁斥,這些文本偶然地幸存了下來。很顯然,康德對自己在已經出版的著作中的論證並不完全滿意,他依舊在試驗著建構論證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這正是康德的工作方式,那種關於他的每一步是如何嵌合在一起的、清晰的和單一的論證視野,從歷史角度來看恰恰是不準確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反倒是把自己當作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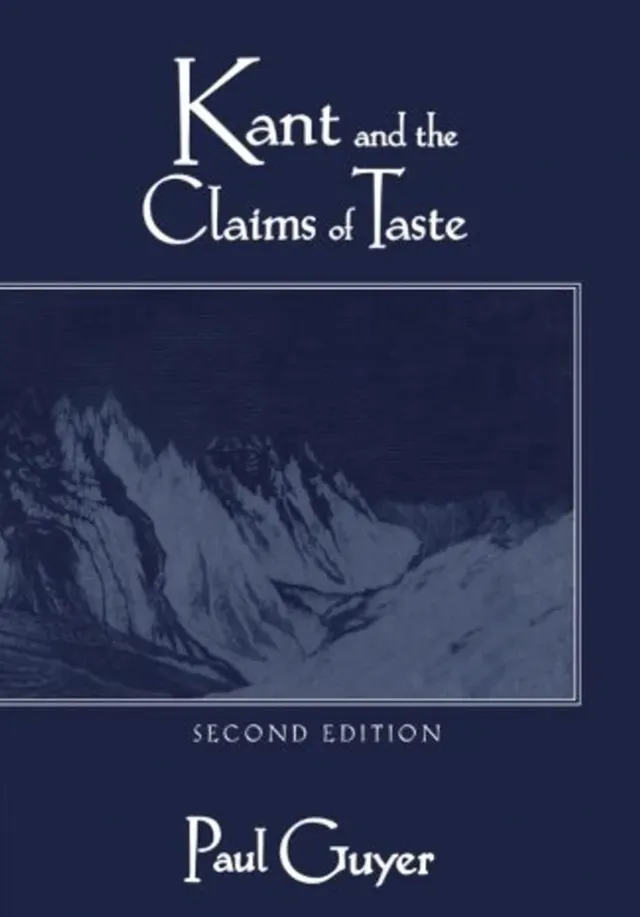
保羅·蓋耶的【康德與審美的主張】
呂超: 記得我多年前剛開始閱讀康德哲學時,就參考了您的大作【康德與審美的主張】(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現在距離這本書的出版(1979年)已經過去40年了,請問您認為在康德研究領域哪些要素或多或少還保持著和過去一樣,而哪些要素則發生了劇烈的改變?
保羅·蓋耶: 這四十年來未曾改變的是康德本人的文本。康德已經去世很長時間了,他的絕大部份(包括生前未出版的)材料已經在相當長的時間中為人們熟悉了,盡管近年來關於他講座的更多手寫稿被發現,而這是在所謂一手資料方面唯一的變化。
當我開始在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即Harvard University的本科生部)學習康德時,那是1960年代的後半段,關於康德的道德哲學只有很少的英語研究著作,比如路易士·懷特·貝克(Lewis White Beck)對【實踐理性批判】的評註。貝克是美國人,而說起英國人的著作,你就必須提到帕通(Paton)對【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的評註,還有坎普·斯密(Kemp Smith)1910年代末期關於康德理論哲學的比較老的註釋,以及帕通在1930年代出版的【康德的經驗的形而上學】( Kant'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
後來斯特勞森(Strawson)的【感觀之縛】( The Bounds of Sense )和貝奈特(Bennett)的【康德的分析論】( Kant's Analytic )突然問世了。我立即閱讀了這兩本著作,它們非常激動人心,它們以分析哲學的語言和特定預設來接近康德,尤其是在斯特勞森這裏。這些預設實際上並不屬於康德本人,但這卻突然使幾乎所有事情都變得可能了。之後在我的博士研究階段,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了。康德在這本著作裏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康德也在羅爾斯講授的課程中占據了很大的部份。羅爾斯在他的道德哲學課程中講授了康德,他從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建構出自己的哲學。出於某些原因,羅爾斯沒有太關註康德的政治哲學。那時很多人(主要在美國,但英國也有)開始對康德產生了熱情。康德突然在他自己的歷史中比在分析哲學對他的敘述中變得更為重要了。
我從博士論文關於【判斷力批判】(特別是康德美學)的工作開始研究康德,而這樣做是出於若幹原因。我本身就對美學感興趣,而且英語和德語學界那時並沒有多少關於【判斷力批判】的研究。因此這是一片開闊的領域,我可以直接對康德的文本進行思考和寫作,而不必過多擔心其他人說過什麽。在我完成博士論文並在幾年後將它重寫為一本書的這段時間裏,唐納·克勞佛(Donald Crawfold)的【康德的美學理論】( Kant's Aesthetic Theory, 1974)出版了,並且引發了細致的討論。在我1979年出版的【康德與審美的主張】中,我的某些修訂(這些修訂並未出現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就是在回應克勞佛所提出的問題。
我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階段的最後一年,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第一次成為哈佛的存取學者。他帶來了德語學術界的傳統,將我置於這些傳統面前。特別地在康德這裏,這意味著全方位地使用康德的材料,包括使用康德的遺作(Nachlass),亦即在他手稿中那些他生前無意出版、但此後卻被謄寫並長年累月印制出來的筆記,包括使用康德講座的手寫稿,這些是由在他課上的學生,或者甚至可能是由專職記錄員記錄的。所以,這就是說不僅利用康德的出版著作,並且也利用所有的材料來試圖對康德究竟在嘗試著做什麽獲得一種更充分的理解。我向亨利希學習,而如果我的記憶是準確的話,卡爾·阿默瑞卡(Karl Ameriks)(他當時是耶魯大學的學生)開始在德國學習了一段時間,他也開始使用上面提到的那些材料。我從【康德與審美的主張】開始的著作,以及卡爾幾年後從【康德的心靈理論】( Kant's Theory of Mind )開始的著作,都擡高了康德研究在美國的門檻。從那時開始你必須使用所有的材料。此外,我在博士論文中所做的一件事(盡管我並沒有將它放入第一本出版著作中)就是深入康德美學的歷史背景,特別是它的英國背景和德國背景。我一方面討論了哈奇遜(Hutcheson)和伯克(Burke)等人,另一方面討論了鮑姆嘉通(Baumgarten)、邁耶(Meier)、門德爾松(Mendelssohn)等人。大部份關於這個主題的英語研究都沒有真正使用這些材料,而當時的德語研究則更多地用到了它們。這擡高了在語境(Context)中研究康德的門檻。盡管聽起來這有點不謙虛,但我認為我和卡爾·阿默瑞卡改變了美國(或許也包括其他地方)對康德研究的期待值。
你或許會說,康德的出版著作當然應當享有相較於其他材料的優先地位,因為這畢竟是康德自己選擇出版的,而其他材料只是一些草稿和實驗,或許最終康德將它們放到了一邊,而它們僅僅是偶然地幸存了下來。這在某種意義上當然是正確的。但我想要說,我們從這些幸存的材料中獲悉了康德的工作方式。他持續不斷地勾勒出論證的輪廓,他持續不斷地嘗試著抵達同一結論的不同方式,而當無論出於什麽原因康德感到了現實地出版一本著作的壓力時,他就將這些材料放到一塊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出版著作中的論證必然優於其它他曾經嘗試過的論證。這並不是什麽著名的(或者說臭名昭著的)「拼湊物理論」(patchwork theory)。那種「拼湊物理論」說的是,康德字面意思地將所有手稿放在一起,剪裁、貼上、將其交給別人做成一份稿子,再送給印刷商。我說的可不是這個,而是康德持續不斷地嘗試著什麽才是通達他想要得到的結論的最佳路徑。你不能自動地假設他在某本書中安置的一個特定版本就是事實上最佳版本的論證。有時在他筆記中出現的某些版本的論證裏,我們發現了其他更有趣的路徑。
當然,這對康德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構成了挑戰。現在,你必須處理遠比我們當年起步時更多的材料,除此之外還有四十年間積累起來的研究文獻。英語和德語是康德研究使用的主要語言,義大利語作品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東西,但英語和德語仍然是主要語言。在世界各個地方——特別是就我熟悉的美國、英國、德國而言——人們感到身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必須越來越早地出版自己的作品。研究文獻不是以算數的方式,而是以指數的方式在增長。沒有人能夠全部掌握它們。在這個意義上,年輕學者面臨著比我們那一代人更大的挑戰。【康德研究】( Kant-Studien )每年都會出版一份過去一年裏關於康德哲學的文章和著作清單,而每一年都有數千的條目出現。沒有人能在一年之內將這些文獻全部讀完。因此人們需要挑選,而這又存在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閱讀最好的期刊,它們是 Kant-Studien , Kantian Review ,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等等。關註這些期刊,發現令你感興趣的東西。另一種方法則是相互交流,因為沒人能夠閱讀所有的東西,但某些人可能讀過這篇新文章,而某些人則可能讀過那篇新文章。
然而在這裏我還想說一件事,我認為對於老文本的每一種嚴肅而具體的哲學解釋,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與當前的哲學問題、當前的哲學話語、當下的哲學風尚聯系在一起。無論作者是否想要這樣做,這一點都是無可避免的。新的解釋者們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根據當前的哲學術語和哲學主題來解釋已經被研究了數年甚至數世紀的同一部文本。由於哲學術語和主題在不可避免地變化著,解釋者總會有一些新的工作可以做。如果你看一下近期康德研究文獻裏出現的認識論中的概念論(conceptualism)與非-概念論(non-conceptualism)之爭,關於康德是不是道德實在論者(moral realist)的爭論,以及道德實在論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之爭,(你就會發現)這些都是在新的哲學概念和術語層面進行的爭論。你會發現當年輕學者討論康德和其他作者時,他們會使用不同於50年前的康德研究中的概念。因為一般的哲學形勢(philosophical landscape)改變了,所以人們解釋文本的方式也會發生改變。這意味著,對某種形式的觀念論的特殊運用不可否認地是真的,亦即你總是從自己在地上的視角來觀看世界。你能夠調整你的視角,但你永遠無法全然脫離人類的視角而直接抵達客體。這一點對於哲學研究也是真的,它總是從某個視角出發寫成的,這個視角或是突然地、或是沒那麽突然地隨著時間而改變,由此解釋本身也將隨著時間而改變。
我認為自己十分地幸運,人們在【康德與審美的主張】出版40年後,在【康德與知識的主張】(1989年)問世30年後還在閱讀這兩本書。對於解釋性的著作來說,這就是一種很長的壽命了。這或許部份地緣於我有意識地並不將過多的當代哲學帶入進來,而試圖用康德自己的術語來思考。但這並不等於接受康德的所有論證。我將諸如一貫性(coherence)、合理性(soundness)等基本標準用於討論康德的論證。在某種程度上,我也並不回避引入一些其他的哲學假設。然而,我嘗試著並不簡單地將康德轉譯成當代哲學術語,因為那或許在十年之內在人們看來還是有趣的,但隨後事情將會已經向前發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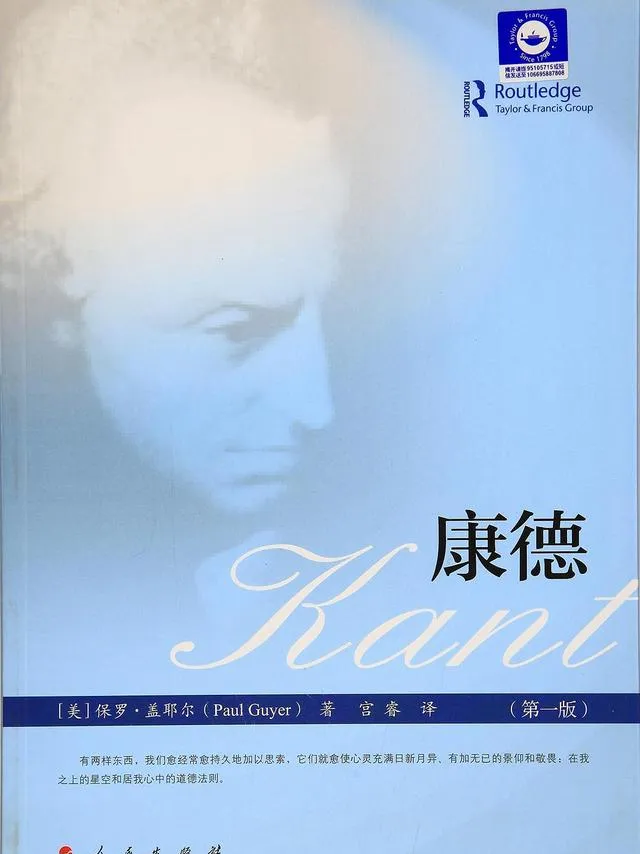
保羅·蓋耶的【康德】中譯本
呂超: 我們現在可能會感到用英語寫成的康德論文和著作甚至比用康德的母語寫成的作品更有影響力。在您看來造成這種變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麽?除了羅爾斯的貢獻之外,其他改變康德研究形勢的因素還有哪些?
保羅·蓋耶: 這裏有不同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完全不限於哲學學科內部,那就是英語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這部份地與大英帝國的地理疆域有關,部份地與二戰之後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位置有關。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都在學習英語,或是作為他們的母語,或是作為第二語言。當然對於這條規則是存在例外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人們都在學習英語,因此很容易把英語作為科學交流的語言,就如曾經的拉丁語和19世紀的法語一樣。
而第二點因素我認為是德國哲學的風尚。在過去四十年間,當康德在許多英美學生和學者眼裏變得越來越有趣的時候,德國卻越來越專註於當代哲學和分析哲學。和過去相比,真正研究康德和其他德國古典哲學家的人在德國變少了。德國人仍然擁有巨大的優勢,畢竟這些文本是用德語寫成的,他們能夠比其他大多數人更好地理解文本,即使後者已經做了很多年研究。但如果你看一下德國大學在過去四十年間的教授任命,大多數教授席位都給了做某些版本的分析哲學的人。這就是風尚的變化。近期在美國做一個優秀的康德學者,比在德國本土要更具聲望一些。
你還談到了羅爾斯的傑出貢獻,這一貢獻不僅在於他自己的著作,也在於他培養出來的數量龐大的學生。在羅爾斯事業開發中相對比較早期的時候,在他1960年代剛剛來到哈佛時就有很多學生:小湯瑪斯·希爾(Thomas Hill, Jr),奧諾拉·歐奈爾(Onora O'Neill)、凱瑞斯汀·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芭芭拉·赫爾曼(Barbara Herman)、安德魯斯·瑞斯(Andrews Reath)、安德魯·派普(Andrew Piper)(他至少在美國也是很著名的藝術家)等等。羅爾斯訓練了這些學生,但「訓練」(train)並不是一個確切的詞,因為羅爾斯並不制造門徒,而是啟發學生,然後後者就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工作,從而在英美兩地使得關於康德倫理學的研究變得生機勃勃,並且創造出了康德式的倫理學(Kantian ethics),亦即被康德啟發、但並不屬於對康德的解釋的這樣一種倫理學。許多人認為道德哲學有兩種基本範式,一種是康德式的倫理學,另一種則是功利主義或者後果主義的倫理學,而由亞里斯多德啟發的美德倫理學則有點緩慢地跟在後面。但康德主義成為道德哲學的一種基本範式已經超過四十年了,這極大地歸功於羅爾斯。康德哲學的其他部份,例如認識論,或許在美國就不是範式性的。然而也有很多人研究康德的科學哲學,例如蜜雪兒·弗瑞德曼(Michael Friedman),而我則在研究康德美學。現在一些學者也對康德的政治哲學感興趣,因此對康德哲學中其他部份的研究也是生機勃勃的。
呂超: 隨著二手文獻的急速增長以及康德哲學中各大領域已經得到探索,年輕學者做出新成績的壓力似乎越來越大。在您看來,康德哲學中還有哪些問題並未經過充分討論、但卻值得年輕學者進一步探索呢?
保羅·蓋耶: 我剛才說過,年輕學者將帶著不同於老一代學者的背景來接近文本。他們應當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提出在他們自己看來有趣的問題。同時,他們不應該自動地假設每一個變得流行的問題都真的值得被提出。年輕學者不應當僅僅關註最新的期刊文章和三年內出版的專著,而應當回過頭去看看一些經典解釋,比如貝克、阿默瑞卡、我、或許還有帕通等人的作品,然後他們或許會發現這些老一代學者已經提出了某些有趣的問題,所以他們可以告訴自己:不要被當代的問題轉移了註意力。
至於康德哲學中尚未得到充分關註的領域,我想說關於康德的政治哲學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特別是關於康德政治哲學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比如我正在完成一本關於康德和門德爾松的書。我考察的是他們之間貫穿兩人整個事業階段的學術關系。你或許會認為很多學者已經寫過這樣的書,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找到了一篇寫於1929年的試圖討論康德和門德爾松學術關系的德語文章,然而從那之後,就沒有人再寫過關於該問題的專著了,這有些令人吃驚。此外,學界關於康德從鮑姆嘉通那裏學到了什麽、拒斥了什麽的問題也沒有很好的研究。的確有一些研究康德和休謨、康德和哈奇遜的關系的,但這還不夠。而學界關於康德和沙夫茨伯裏(Shaftsbury)的關系也沒有足夠的研究。同時,關於康德的接受史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這是我最近在幹的另一件事。有些學者——特別是在德國和說德語的地區(如瑞士、義大利的一些地方)——在研究萊茵霍爾德(Reinhold)、邁蒙(Maimon)、和舒茨(Schulz)等第一代讀者對康德的接受,而英語著作中這方面的研究則很少。就我所知,以上提到的邁蒙等人的著作幾乎沒有被轉譯為德語之外的語言。此外,我發現昨天韓水法教授關於康德與人工智慧的開場演講中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因此在康德與當代科學、當代文化的發展的關系上也有很多研究可以展開。
呂超: 您在獨立的美學領域也有非常傑出的貢獻,比如那套關於現代美學的三卷本專著。我的問題是,當我們談及二戰之後的當代藝術(通常是後現代藝術)時,很多當代藝術作品似乎並不是優美的,反倒是醜陋的,它們無意於給我們帶來美的感受,而是僅僅想宣揚某種理念。請問這些作品可以被歸於審美的一般範疇之下嗎?我們想了解一下您對當代藝術的觀點,包括它們的潛在優勢和問題又在哪裏。
保羅·蓋耶: 首先讓我談一點關於作為一門學科的美學的觀念,然後再談談當代藝術。我不是藝術史學家或者藝術批評家,而將美學家的工作和這些人的工作區分開是很重要的。美學這個術語是由鮑姆嘉通在1735年作為和邏輯學並列的概念而創造出來的。美學和與理智活動(intellection)相對立的感觀知覺(sensory perception)相關。鮑姆嘉通意欲讓美學成為一門關於感觀知覺的科學,但他實際上並沒有解釋關於感觀知覺的一般性科學到底是什麽。鮑姆嘉通專註於對藝術的知覺,但確切地說「知覺」在這裏並不是一個合適的詞,因為鮑姆嘉通腦袋裏首先想到的是詩歌,而不是視覺藝術。然而,他並沒有把藝術的這些有趣內容限定在美上面,而同時也討論了崇高。當然,他並沒有用「崇高」(sublime)這個概念,而是將崇高稱為「感性的量」(aesthetic magnitude)。康德從鮑姆嘉通那裏學到了這個術語,但並非之後的每個人都直接使用這個術語。康德討論了自然和藝術中的美與崇高。崇高首先存在於自然中,因為康德並不認為藝術強有力到能夠產生出崇高感,但自然既可以產生出對崇高的體驗,也可以產生出對美的體驗。
美學中的重大轉折發生在黑格爾那裏。在美學講演錄的導言中,黑格爾想要論證說自然是沒有趣味的,因為它不是從精神誕生出來的精神,它不是人類的或者精神性的創造物。至於這裏的精神究竟意味著人類精神還是更高的東西,在黑格爾研究者那裏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黑格爾本質上說放棄了自然美,或者說把自然的內容從美學中排除了出去。因此透過這一排除,美學從黑格爾開始也就開始意味著藝術哲學。這並不必然地指哲學內部一種特別的理論,而僅僅是「藝術哲學」這門學科的名字。一些身處哲學領域之外的、其他學科的人(比如文學系的人)將美學等同於關於美的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等同於「藝術應當追求美」這一命題,由此他們得以談論「藝術的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 of art)(這種表達在哲學家聽起來卻是冗余的)。任何藝術理論都是美學的一部份,但當這些人談論藝術的美學理論時,他們聲稱藝術應當或者必須以美為目標,因此他們會認為二戰之後、甚至基本上始於杜尚(Duchamp)的二十世紀藝術都拒斥了美學、摧毀了美學,諸如此類。但在哲學家聽來,這些論斷毫無意義。藝術無法拒斥藝術理論或者藝術哲學,藝術只能反對某種特殊的藝術理論,而不是反對關於藝術的哲學言說這件事務本身。
因此從哲學的視角來看,二戰之後諸藝術領域內的發展——尤其在視覺藝術中,但也有一些音樂運動(如約翰·凱芝[John Cage]的作品)和一些文學運動——它們或許摧毀了「藝術應當追求美」這一觀念,但並沒有摧毀哲學美學(philosophical aesthetics)的實踐。如果你看一下美國1960年代以來哲學美學的發展——從亞瑟·丹托(Arthur Danto)1964年關於「藝術世界」(Artworld)的著名文章開始,也包括喬治·狄肯(George Dickie)在1960年代的一系列論文——你會發現哲學美學這一學科(或者說次級學科)試圖建構出一種藝術理論,這種理論可以適用於那種不再對美、而對其他東西感興趣的新型藝術。如果向前回溯一個世紀,我們還會發現卡爾·羅森克蘭茨(Karl Rosenkranz)的著作,這本著作的英譯名是【醜的美學】 (Aesthetics of Ugliness )。按照某種解釋,這個標題就是一種自相矛盾,因為美學僅僅關系到美。但羅森克蘭茨的意思是,這本書是一種展現醜的藝術理論,或者關於藝術為什麽必須既包括美,也包括醜的理論。在美國,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二、三十年間,美學作為藝術哲學的首要主題就是對藝術的定義,而不是對美的定義。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很多藝術是醜的,是和美不相關的,甚至是敵對於美的,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更為一般的對藝術的定義,從而囊括針對當代藝術的美學工作。
你也問到了我個人對當代藝術的看法。狄奧多·阿多諾聲稱奧斯維辛之後不可以再有詩歌,因為人類歷史中發生了如此可怖的事,詩歌創作,或者更一般地說,對美的物件的生產這件事本身都是粗俗的。相反,我們應當表達人類歷史中可怖的一面,因此藝術應當專註於醜,而不是專註於美,因為醜才表達了人類真正是什麽樣子,以及人類歷史變成了什麽樣子,諸如此類。這種「藝術應當專註於人類處境中的醜,而不是美」的情緒傳播得相當廣泛,即便人們並不知道阿多諾的作品,或者他們並沒有在參照阿多諾的原話。總之,這種傳播得相當廣泛的情緒是:人類處境是醜陋的,而我們應當致力於去表達真相。
然而,也有思考事情的其他方式。你可以說人類能夠做出、並且已經對彼此做出了可怖的事,人類生活的許多事實的確是醜陋的,因此我們在生活中比以往更需要美,難道不是這樣嗎?在2000年左右和在此之後,至少一些人開始以這種方式來思考問題了。人類生活中有許多醜的東西,我們必須認識它們、理解它們、改善它們。這件事很重要。而這意味著什麽?可能意味著將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加美麗,意味著透過創造美的藝術來幫助人們。所以我並不同意阿多諾的以下觀點,即奧斯維辛之後不應當再有詩歌,如果這個觀點意味著奧斯維辛之後不應當存在美的話。我同意「永不遺忘」的理念。我們不能假裝例如奧斯維辛之類的一切可怖事件從未發生,也許藝術所扮演的某種角色就是保持對這些可怖事件的鮮活記憶,向未曾在那裏經歷過這一切的下一代人表現和傳達這種可怖,因為藝術能夠強有力地傳達資訊,至少有時候能夠比枯燥的歷史書和一捆數據更為有力地傳達資訊。
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坐在一堆灰燼上,僅僅回顧著這些可怖的東西而不在生活中繼續前進。美的經驗對人們非常重要。看看這兒,看看四周(指北大人文學院)。人們維護著這些美麗的建築,種植樹木,照料花園和籬笆,因為美對人類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看來,堅持認為藝術不再以美為目標——這種觀點既是缺乏動機的,也是不正當的。或許並非每一種東西都應該被藝術當作合法的目標,並非每一件單獨的藝術品都應當以美為目標,但就我所理解的藝術來說,美的確是藝術的一個合法目標,除非人類種族出於對過去或當前之事的絕望而僅僅希望淪陷自身。我們的生活中需要美,自然能夠提供美,自然尤其在這方面能夠幫到人類,而當自然沒有幫到我們時,藝術又能夠提供美。
現在我特別地來談談一些各種藝術領域。我可能因為說這些話而陷入麻煩,因為我的姐姐是一位視覺藝術畫家(笑)。我認為繪畫活動在很多地方有些迷路了。亞瑟·丹托曾經論證說(而且很多人也承認這一點)繪畫是一種表象的活動(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所以一旦攝影術被發明出來並得到完善,繪畫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有一段時間人們嘗試著用繪畫去做一些別的事,由此我們有了非-表象性的(non-representational)繪畫,比如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或者更一般意義的非-具象性的(non-figurative)繪畫,就像始於俄國畫家馬勒維支(Malevich)的至上主義(Suprematism)。我覺得從1980年代起,雖然一些著名的畫家依舊擁有繪畫工具(如刷子、帆布、木頭等東西),但他們並不懂得如何使用這些工具。現在依舊有人在繪制肖像畫和風景畫,但他們不再得到關註了。因此我認為先鋒繪畫已經迷路了。然而這並不證明……誰知道未來又會發生什麽呢?
但對於其他藝術形式情況卻並不是這樣。現在的小說家和以往一樣多,甚至比以往更多。其中一些人在嘗試做實驗小說家,另一些人則幹著小說家從十八世紀起就在做的事,也就是講述虛構的故事,但這些故事捕捉到了關於人類生活之本質的深層真相,它們更為一般地或更為具體地描繪了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城市、特定的生活圈子、這一鄰裏或那一鄰裏的居民、這一社會處境或那一社會處境中的人,諸如此類。此外有人在寫詩,有人在做音樂,當然還有人在做電影、攝影、舞蹈和其他藝術,它們中的許多在我看來並沒有迷路。它們有時在尋求我們體驗為美的東西,有時在尋求我們體驗為驚悚的東西,有時在尋求我們體驗為崇高的東西。它們具有不同的目標。然而這些作品看起來和過去很不一樣。20世紀的小說讀起來不同於19世紀的英國小說、18世紀的法國小說、或者是【源氏物語】。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看起來非常地不同。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有很多角色,而在索福克勒斯的戲劇中只有很少的幾個角色和一支歌隊(chorus)。戲劇的結構也是完全不同的。索福克勒斯的戲劇推進得很快,僅僅描述了一天之內發生的事件,而莎士比亞的戲劇則能夠描繪在幾天、甚至幾個月時間裏發生的事件。然而這樣的不同又有些膚淺,因為在一個更深的層次,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亞在做同樣的事,他們都在捕捉關於他們各自世界的某些真相。希臘世界當然不同於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因此捕捉這兩個世界的藝術看起來也非常地不同。但兩者又在做同一項工作,這項工作允許生活在其中一個時代的我們從內部去理解另一個時代的人類生活,去理解那些人是如何感受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或者允許生活在這兩個時代之後的我們,對處於那些環境、那些時代的人類生活和我們自己的生活之間的相同與差異獲得一種理解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