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黃河這兩條中國的生命之流,各自發展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中國文化的整體,當然也應當包括長江、黃河流域以外的地區,我從江河講起,只是想要表達,我的陳述是追溯其源流始末之要者,是在形容各個地區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纏為一,終於建構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文化格局。 這一文化格局不是部落性的,也並非民族性的,不僅是國家性的,而且是「普世性」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天下格局」。 「天下格局」這個詞,並沒有「帝國主義」的含義,只是說明中國文化的內涵,乃是以「天下」為關懷,不受國界的限制,以萬民百姓為同胞,設定的即是【論語】所說「安人」「安百姓」——「百姓」指的是許多不同族群,並非任何一族而已。
相對於中國的特色,世界幾個主要的文化體系幾乎都從猶太教的根源衍生而成: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沒有一家不是擁出一個獨一真神,這個神對某一族類或其信仰者,有「偏愛的佑護」。這一套獨神教的信仰,基本上是排他的。相對而言,中國文化在形成過程之中,到了周代,以抽象的「天」作為宇宙的全體,天與人乃是相對相成、互相證明。 因此,中國文化是以大宇宙來定義一個人間,再以人間孕育下面各個層次的空間:國、族、親戚、鄉裏、朋友。 這一級一級由個人而至天下的網路結構,每一級之間,都是彼此關聯、前後相續的秩序——中間不能切斷,更非對立。
我曾把上述想法,寫成【萬古江河】一書,借此陳述中國文化本身發展的脈絡,及其從若幹地區性的文化逐漸融合為一個近乎世界性大國的歷程。那一書名,乃是形容中國歷史存續時間之長久。

▴
[美]許倬雲【萬古江河】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萬古江河】寫完後,我常常感覺這本書所討論的,其實大多是中國文化圈內部的演變。既然這一文化圈的特點,是一個大宇宙涵蓋其上,一個全世界承載於下,居於二者之中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這才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命意。本書的書名,確定為【經緯華夏】。我也是從許多考古遺址的分布,以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與轉折中覺悟:在長程演化之中,中國文化有許多個體的遺址可以排布為序列。誠如蘇秉琦先生所說:以「區、系、型別」作為線索,將似乎有個別特色的許多遺址,組織為古史的代表;從這種序列,也可以看到時間維度上某一個文化系統本身的演變。 我在本書中,將中國歷史歸納為時間之序列、空間之擴散,從而理解人類的移動軌跡,以及族群之間、國別之間互動的形態。 這就是將遍地開花的遺址,組織成有演變、有調節的整體敘事:將大面積、長時段、以其特征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這些個別的、有特色的群體——放在一區一區,也就等於以大型結構體的組合,敘述歷史上長時段推演的故事。在撰述本書以前,我對於中國考古時代發展模式的考察,相當程度上是依照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夷夏東西」的分野,在中國傳統的中原地區(也就是黃河大平原、關隴以至於渤海灣) ,陳述其延伸和擴充套件過程。最近,孫巖的新著【普天之下的多元世界:西周北疆的物質文化、認同和權力】(Many Worlds Under One Heaven: Material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E ) ,從最西的西漢水一帶(後來秦國的發源地) 開始考查,接著是西周的周原、涇水流域,再接下去是晉國在山西汾水流域的發展,以至於最後討論到燕山和草原交界處的燕國一帶。秦、周、晉、燕這四個區域的北向或西向,外面都有相當發達的草原文化遺址。孫巖從這些遺址遺留的文物入手,檢查其各別文化特色,發現每一區和草原文化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痕跡從出土器物上歷歷可見。這一說法,也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考古學所認定的「中原地區」,從西到東,其實都與草原文化有脫不開的關系。在本書中,我順著考古遺址展開再思考,發現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這兩個平行的地區,實際上各自發展、互相纏結。中國古代的發展基地,絕對不僅中原一處而已。尤其我想指明者為: 關隴以西,青海與賀蘭山脈、祁連山脈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超越了「西部邊緣」的意義,其實乃是東方與西方進退盤旋的空間。

▴
圖為陜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M26墓中的小青銅器
三星堆遺址引發的疑問,使我終於理解:陰山以下至於其東面,進而延伸至川北、長江上遊源頭,是農耕與遊牧的交錯所在;也正在此一地區,東亞內陸進行的諸多人類活動,必然波及東亞的主要地區——中華的本土。所以,我才將 「允姓之戎」 (早期文獻稱之為獫狁) 作為一個共同稱謂,以概括這一最東部的遊牧族群,他們與中華本土之間保持了長期互動;也因此註意到,從川北迄於長江口那一遍布山、陵、江、湖的天地,也是中國古代文明演化的地區。而四千年前從渤海灣到山東的東海岸新石器時代的族群擴散,使得長江與黃河兩個地區的發展,往往呈現了交纏疊合的復雜現象。
當黃海地區的族群擴散,聯系到東部沿海及至閩越地區,古代中國先民各種族群你應我和、交流合作,才創造出這片華夏天地。 這個大舞台上,進行著東方人類最重要的一場長詩大劇。至於幹擾中國歷史的因素,似乎主要是北方和西部內陸的牧人,一批批進入中國,有些竟就此融入中國。而到了近代,在從海上來的歐洲人和東亞其他族群沖擊之下,自中亞進入中國的絲綢之路,其重要性已經不復當年。這些從海上而來的刺激,確實對中國構成極大沖擊: 中國不再只是大陸國家,而必須踏著太平洋的洋流,參與全世界的人類活動。 這 才是本書下半部份,我必須陳述:中國如何因應海上來的沖擊。這一段陳述,是我的內心剖白。希望讀者能由此找到閱讀本書的線索。

▴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內的青銅神壇
余嘉 攝
二
在前面數章, 我嘗試將古代中國的演變,組織為三個核心區 ;每個核心區都有其發展的過程,也都有呈現其內在的特色。 而三個核心區之間的互動——或延伸、或演進、或轉接、或擴散,即是華夏文明本身從成長到成型的「詩歌」。
第一區在黃河流域,從關隴直到渤海:北面是「塬上」,這一遊牧民族的家鄉;南面則是「秦嶺—漢水—淮河線」以外,廣大的長江湖泊地區。 這個核心區域,一向被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原」。
第二區在西北的源頭是川北的岷江流域,南邊的界限則一直到南嶺,其最東端是長江口和太湖,「楚尾吳頭」,在此與中國沿海的第三區相接。整個第二區氣候溫暖、水分充足,地理景觀與生活條件確實比第一區更為優越。 這一區習慣上被視為南方,以及第一區的延伸 ——在歷史上的中國,第一區受北方遊牧民族重大沖擊時,其主體會撤退到第二區。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影印本書影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在寫作本書時,我才逐漸發現:從渤海灣兩岸起,也就是紅山文化越過渤海灣進入山東半島,這個「海岱地區」也應納入第一區;然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一沿海地區向南延伸,許多族群由第一區遷入第二區的「江湖尾梢」,再轉接上從良渚文化所在的長江下遊區域到廣東的沿海山陵地區。 這一沿海彎曲地帶,既與第一區、第二區相銜接,也與長江口以南整個沿海地帶密不可分,我們可以稱其為「第三核心區」 ——嚴格而論,尚不能稱其為「核心區」,但這一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重要。
這三個核心區,正是本書命名為【經緯華夏】的理由:山陵丘壑與河流湖泊,處處相疊相交,構成中華文明主流的廣大基地。當然,在此三區之外,還有另外兩片廣大的區域:一者為中國西北部,崇山峻嶺與沙漠、綠洲交錯,喜馬拉雅山、天山與陰山是中國許多河流的發源地;一者為中國西南部,山高谷深,民族成分復雜—— 以上兩區,都是中華文明逐漸延伸而擴張的腹地。 由於我著重敘述的是中華文明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主要討論的範圍也就集中在上述三個地區。在本書中,西北和西南地區尚未多加著墨。將來若有時間和機會,我想可以將這兩區的發展單獨論述。
讓我發揮一點想象力,將這三個核心區排列在中國的地圖上。第一區與北方遊牧民族有兩次個別的接觸,它們彼此同時發展,當然也有參差;在第二區又看見中國西北部戎族文化的影響,至少有一次延伸到四川,在那裏又與崇山峻嶺中出現的南方文化接軌。而在第一區,距今四千年前,已經存在相當發達的玉石文化 (從紅山文化到龍山文化) 。可是,在一次嚴重的氣候變遷之後,本來極為發達的大汶口到龍山的新石器文化,被迫擴散到第二區和第三區。這一個轉折,使得第二區獲得了極大的動力,也加強了第二區與第三區的互動,還彰顯了第三區以百越文化為代表的文化特色,促使其延伸到南方海岸。

▴
紅山文化玉豬龍
假若將這三大核心區作一個整體,放在圍棋的棋盤格上,當作已經排好的一條「大龍」:從大陸最高點喜馬拉雅山腳下,向東南開展,處處都有高山峻嶺,也處處都有湖泊河流;在這山河薈萃之處,清晨雲氣環繞山巒,黃昏暮靄渲染江湖——這些變化無窮的雲舒霧卷,都猶如飛龍滿天,在中國大地上翺翔。
在華夏大地上,凡有水源處,就可能有古人留下的遺址,也許是生活聚落,也許是墓葬。當然,更多的是他們留下的器用和生活必需品。在河邊、台地、山谷、平原,那些古人的遺留猶如星羅棋布,處處可見。於是,我們從這些文化痕跡,可以推測其來龍去脈,以及彼此間的交換與改變。 借用蘇秉琦先生的意思:同一文化的遺址,可以拉成一條條分布的線索,在這些遺址之中,如果有因接觸和適應而出現的變化,也就可以瞻見不同人群間彼此如何即時修改其生活形態及文化內容。
本書的前面數章,正是借了這些雲舒霧卷的古代文化遺留,才得以推演出:在這廣大的山巒峽谷之中,古代先民如何共同生活,又是如何來去移動。 這就是我經常以【易經】乾卦的「飛龍在天」為比喻,形容中華文明在這片土地「一天星鬥」「遍地開花」的實況 ——大家彼此映照、氣象萬千,無須任何一處作為主流,那是「群龍無首」最好的卦象。即使這些群龍飛入大海,也只是在臨海的泰山和玉山這兩座高山之上,在海潮洶湧之中遊戲自如。中華大地,雲氣彌漫,這些「飛龍」在半空噴霧吐水,使得處處都有足夠的水分,育成農作物以餵養萬民。這些善良而勤勞的農夫,日復一日靠著自己的努力養生送死,無須以掠奪和戰爭維持生計。但每逢外來侵犯,農夫們也會努力保護家園,依仗著星羅棋布的村落、田地和水塘,拿起刀劍弓弩,擋住胡人南侵的馬蹄。

▴
[南宋]陳容【五龍圖】(局部)
紙本 長卷 水墨,45.2x299.5厘米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如果北方農村聚落所構成的防衛系統,無法抵抗遊牧民族的沖擊,則華夏集合體的「神經中樞」可以立刻由第一區遷入第二區。 例如,永嘉南遷後防守的前哨站,就放在荊、襄、江、湖和江北淮泗。如果來自北方的壓力更進一步,還可以撤退到第二區所謂「吳頭楚尾」處。例如,靖康之亂後南宋遷都杭州,而仍舊以巴蜀、關隴作為右角的前哨,以荊、襄、江、湖作為後繼,延續了一百多年的政權。20世紀日本侵華,南京國民政府從沿海撤入巴蜀,以三峽外的長江作為第一道防線;又在西南的群山之中開出後路,通向外面的世界。
這三大區域之間的人群,彼此支持、互相移動也是常有之事。 人口密集之處,會將多余者分散到人口較為稀少的地區——當然,更常見的是擁擠的都市,將多余人口疏散到四郊及鄉野。世界歷史上的大帝國,如蒙古帝國、突厥帝國,以至於近來的「大不列顛尼亞世界」和蘇維埃共和國,其疆域都比中國大,但是所有上述帝國,其內部的充實和一致性,以及面臨外部重壓下的調節能力,都無法和中國歷史上呈現的彈性相比。

▴
瞿塘峽
1972年,沈延太 攝
在「東亞棋盤」上,「華夏棋局」所占比例應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間。假若以下圍棋的規矩而言,占據棋盤三分之一者很難號稱贏局。可是, 中國這條「大龍」所壓之處,處處是活眼;每個地區性文化,又都與鄰近文化常有接觸、互相影響—— 如此大的一條龍,盤踞三分之一的棋盤,沒有對手可以將其劫殺。整個中國的局面,自東往西、從南到北,區與區之間相互依仗、彼此掩護,是一個內部完足的整體。簡而言之,它有巨大的穩定性。可是,正因為這個完整的格局穩定性太高,當外來者釋放挑戰的訊號時,其下意識反應可能就是:「我不想要」「別惹我」。
這一特性也許正可以解釋,本書所討論的中國對於外來刺激的反應。 第一,刺激所傳遞的資訊完全因時而異。 有的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組織允許資訊迅速地傳遞到決策層,也就使得這條巨龍有內在的、充分的可能性,可以長存不敗。不幸在於, 中國歷史到近古以後,由於君權長執威柄,中間層的士族或官員回饋資訊的機會和能力都越來越弱 ——擁有的資源如此豐足,人民的才力也如此高明,中國在面臨挑戰時居然如此遲鈍,對於微小的挑戰尚能應對,對於近代以來西方的全面挑戰,卻是如此不堪一擊。
▴
仿宋相台五經本【周易王註】書影
願中國人在回顧華夏歷史時,有我們自豪之處,有我們覺得滿足之處。只是,我們如何能耐得、能忍受一條世界罕見的巨龍,卻要陷入沙灘甚至於泥濘中,停留在 「潛龍勿用」 的階段?
我盼望:中國能站起來,在世界上扮演一個大國應有的角色。 然而,中國不能落入白人霸權的窠臼,中國不要做霸主,而是做許多國家之中互相幫助的一員。 猶如【易】的乾卦六爻,如果一條大龍變為「亢龍」,就將面臨「有悔」的悲劇。我希望看見中國這條大龍,是滿天大大小小的飛龍之一,沒有帶頭人的壓制,眾多夥伴互相欣賞,大家自由飛行。這個卦象,恐怕是【易】卦之中無可命名的最高一階。
三
在本書之中, 我開宗明義,先從人種分類和東亞居民的定義開始。 其中提到在東亞地區出現的許多古人類,甚至「先人類」的大猿及原人。在本書中,我並未標榜東亞與其他地區的人類有何不同,只是為了說明:靈長類的人屬,究竟是在非洲走完全程,然後走向亞歐兩洲?還是在亞歐兩洲的長程跋涉之中,這些原始人類也在不斷地尋找適應的條件,以至於最後構成了今天全世界的我們?
我們有膚色的差別,形貌的差別,體態的差別。在種種差別之上,哪一點是我們相同的?這方面的內容,我在書中並未多加陳述,原因在於:第一,我所受的體質人類學訓練不夠,尤其對於基因的深入分析,還是一個尚待推進、極為復雜的科技計畫,我幾乎完全不能處理;第二,現有的資料及個案的數位,不足以歸納做出結論。我在此處丟擲這個課題,是為了提醒我們自己:現在古人類分類學上,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東方的丹尼索瓦人之間基因的差別究竟在哪裏?這種差別具有多少意義,還是只是一種內在更深的分層?【紐約時報】上有一篇文章提出同樣的課題,而且和我此處的說法不約而同: 我們還沒有能力對這個嚴肅的命題給出進一步的界定。

▴
16萬年前的丹尼索瓦人下頜骨化石
發現於甘肅省夏河縣白石崖溶洞
第二個階段,我又將中國劃分為幾個不同的文化形成區,它們各有自己分岔、相互融合的機緣。 中華文明並非由某個單獨的中心形成、前進演化,然後傳播到其他地區。我所列舉的三個核心區,都有各自發展的條件以及發展的過程;最後,它們在文化上終於構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上述幾個核心區的貢獻,最終都融合在這一整體之內。當然,融合之中還是有各自的特色,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是「圓頭方趾」的個體。然而,我們還是用【水滸傳】中的描述,來解釋如此現象: 「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崢嶸;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潔。」 畢竟,我們人類確實有許多的不同之處,也有很多相同之處。
在歷史上,中原王朝不斷承受草原民族的沖擊、融合。以我的觀察而言,東部草原是這些南下民族的主要來源地。進入中國以前,除了一些自有的農業基礎外,這些草原民族並未掌握其他文化的稟賦。於是進入中國以後,他們很容易就完全融入南部的人口。 在亞洲草原西部,我以陰山地區作為界限,而且以突厥及其分族作為例證,以觀察草原民族與中國之間的關系。 在歷史上,尤其南北朝和唐代,西方的這些兄弟民族一樣也進入中國。只是他們融合於中國內部族群的過程並不完全相同。

▴
[元]佚名【寒原獵騎圖】
絹本 立軸 設色,75x98.5 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歷史上的西部遊牧民族,常常在今天九曲黃河的陜、甘、寧一段著地生根,形成與中原政權相似而不同的單位;他們也可能更往西邊,在今日的新疆形成綠洲國家或草原遊牧單位。這些草原遊牧單位,例如匈奴與蒙古繼續向西發展時,一波又一波打進中東地區,甚至於最後狂飆卷入歐洲。他們所帶去的文化因素,卻不僅限於草原傳統:向往東方中國的地區,有長期成型的「桃花石」 (中古時代中國西邊的族群稱呼中國的別號) ;往西走,他們將這一模式及其約略知道的一些東方文化因素帶入歐洲。以上陳述說明: 中國歷史上不僅有南北之間的混合,其實有相當可觀的東西之間的差異。
中國文化在其成型時期,尤其從史前到西周及秦漢部份的歷史行程,竟能夠將許多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地方文化,彼此融合、交纏為一體。 以如此龐大的文化共同體,中國遂能長期穩定地應對外來刺激,自新石器時代以下,逐步修改自己或融合他者 ——中國文化的大格局,幾乎是個「金剛不壞之身」。可是,經過這些思考,我不能不提出一個疑問: 為何在宋以後,尤其明清階段,中國對外面的感應竟顯得如此遲鈍和保守,終於在清末,面對西潮的輪番沖擊時手足失措? 這一疑問,常常使我夜不成眠,苦思不得其解。
如今我覺得:中國在過去建構出龐大的文化體,可能做到了非常徹底的程度,以至於這個嚴密的文化體,終於趨向嚴重的「內卷」。最顯著的現象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沒有帶回任何新的觀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當時的中國往外面看,發現沒有值得學習之處——這一自滿,終於造成了對外嚴拒固守的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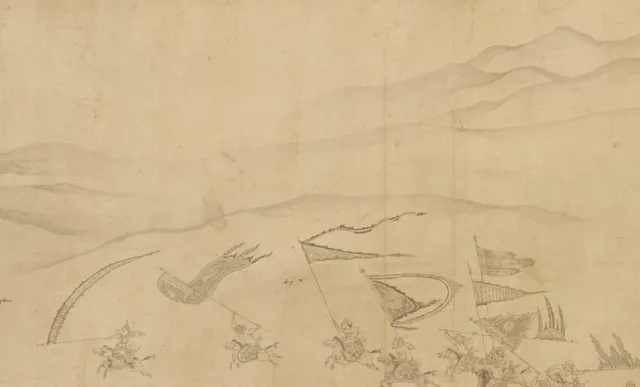
▴
[元]陳及之【便橋會盟圖】(局部)
紙本 長卷 水墨,36x774 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與西潮融合的巨大工程,我們必須要保持警覺:既不能照單全收,也不能全部拒絕;融合的過程,必須要留下許多修整的空間。而且我們必須要註意: 中國固有的文化性格,其實有相當重要的動態成分,例如【易經】的「變」,那一個永遠變化不斷的特色 ;而西方文化之中,卻有獨神信仰專斷的一面,也因此以為只有一種格局得神佑而長存。進行這種修改自身的重要任務時,我們要時常自省:任何改變,不應當囫圇吞棗,而應當註意到, 將他者的「變」與自身的「變」,合成一個陀螺旋轉式的動態平衡。 人類的歷史,本來就是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恒動過程。
本書所述各時代的特色不盡相同,每一時代所討論的計畫,也就不一定按照同樣的思路呈現。經由這些討論,我們可以理解每個朝代所面對的內憂外患,以及中國曾經受過多少的艱難和攪亂。
四
世界史名家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在【西方的興起】中,將「power」解釋成「權力」和「動力」兩種定義。若無各部份的反應機制和處理的回饋,權力中樞將沒有著力之處。 在這一課題下,我所註意的是人口、經濟、物質文明的發展。這些都是文化計畫,但文化體本身依靠這些計畫維持;這些計畫也反映那個特定時代文化能量的強弱。 我也考慮到各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差別,以此來區別承受外來刺激時這個意識形態或迎或拒,也以此來衡量其自我調節的程度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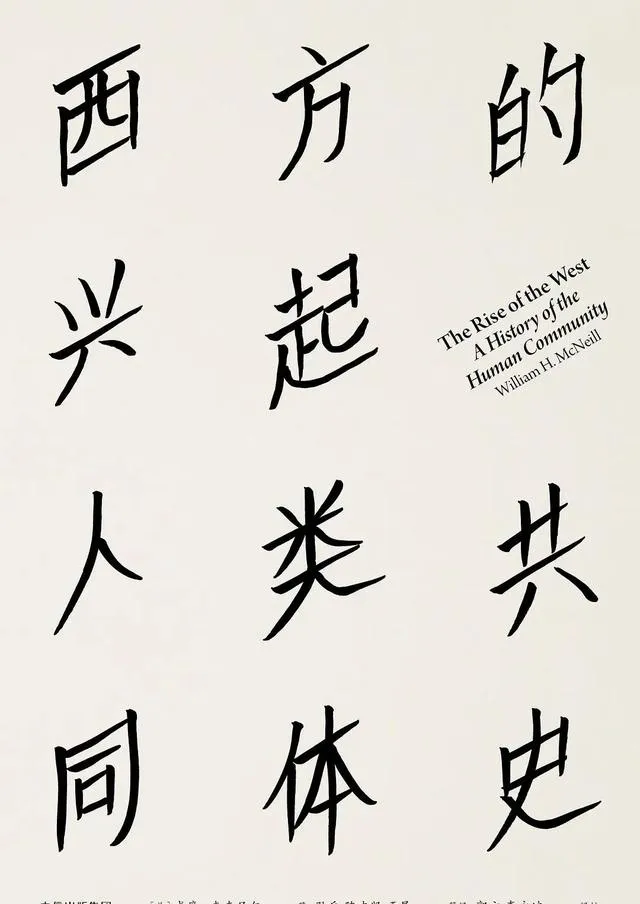
▴
[美] 威廉·麥克尼爾 著, 孫嶽 等譯:【西方的興起】
中信出版社,2017年
這些考慮,都是為了解答一個千古大問:為何到了近代兩百年來,中國面對著西方,無法抗拒那些乘潮而來的歐洲人?在奔入世界大海洋這一關鍵性的時刻, 為何中國文化的反應機制無法適當地感受變化,發展出應有的調節與更新?
這個大問題,才是我寫作本書的主要動機: 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 沒有這一番內外翻覆的嘔心吐血,我們將無法順利面對歐洲領導的近現代文明。沒有這一番自省,我們將無法采人之長,舍人之短,在我們源遠流長的基礎上,發展一個對於未來全人類有益處的選擇。只有全人類在這個真正東與西的沖突與疏離之後,熔鑄一個未來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階,才可以在更遠的未來繼長增高。
拳拳此心,以告國人。我的歲月有限,就望未來一代又一代,都有人願意參與這一個締造世界文化的大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