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發,當代代表性詩人之一,1967年10月生於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主要著作有詩集【寫碑之心】【九章】【陳先發詩選】,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系列)等二十余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草堂詩歌獎年度詩人大獎、英國劍橋大學銀柳葉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22春季大賽轉譯大獎等國內外數十種文學獎項。

陳先發
崖麗娟: 陳先發老師您好,感謝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訪談。在第八屆上海國際詩歌節上見面很高興。這屆詩歌節廣受矚目的原因很多,一是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先生等多位國際重量級詩人與會。二是詩歌節的主題設定為「詩,面對人工智慧」,非常具有前沿性和討論價值。聽了您主持的這場國際性研討會,獲益匪淺,能否簡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您在這個話題上的主要觀點?另外,上海國際詩歌節給您的整體印象是什麽?
陳先發: 我是第二次參加上海國際詩歌節,這次跟索因卡、墨西哥詩人奎亞爾等我喜歡的外國詩人見面,交流非常愉快。受趙麗宏先生委托,我主持了這場以「詩歌創作與人工智慧」為主題的國際詩人研討會,會中的諸多精辟見解讓我們受益。我們已經進入一個AI大模型時代,ChatGPT必將更深刻地改變人類歷史,顛覆既有認知方式,人工智慧在賦予我們時代一種全新定義的同時,也必將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我對詩歌乃至所有文學藝術的獨立價值,對詩歌在AI背景下的前景依然充滿信心。我不擔心AI的能力繁衍到如何強大,只擔憂AI產生一種東西:欲望!如果AI產生欲望,形成自我意識,也必將滋生對這個世界的征服欲。我的樂觀有兩個基本理由:一是詩歌最本質的東西是生命意誌力,而AI沒有體溫,它永不可能真正感受到一具肉身的短暫、茫然或狂喜。二是所有文學創作均基於個體生命體驗的深化,個體是基石。而AI只有整體,沒有個體。即使AI繼續發展,詩歌的尊嚴也將延續下去。也可能我低估了AI的自我生長能力,拭目以待吧。關於上海國際詩歌節,在與多位國外詩人的交流中,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它已成為世界上最為成功、影響力也最為顯著的詩歌節之一。趙麗宏先生是詩歌節的靈魂人物,因為他的持續推動,我們可以預期,上海國際詩歌節的文學史意義仍將進一步釋放。
崖麗娟: 您最近完成的長詩【了忽焉】,一時間成為了激發許多詩人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這首詩有個副題:題曹操宗族墓的八塊磚。首先引發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您是如何看待歷史這一主題的?或者說,詩的歷史意識在您那兒又意味著什麽?
陳先發: 謝謝麗娟。去年秋末我去安徽亳州,第一次在博物館目睹曹操宗族墓的這批文字磚時,先是被驚到了,繼之有喜悅、意外、惶惑等等,種種情緒一齊襲來。回來後,又找了些相關的拓片、字帖來看。這些文字磚對我的吸附力太強了。這首長詩的主標題及分節標題:「了忽焉」「作苦心丸」「澗蝗所中不得自廢也」「欲得」「亟持枝」「沐疾」「頃不相見」「勉力諷誦」,就取自其中八塊磚上的文字。我完全想不到兩千多年前的那些無名窯工,面對熊熊爐火,也可能是滿臉爐灰之時,手持細枝,在磚坯未幹之前,把「墓磚」這般可說是莊重、凝滯,或者說有點呆板之物,變成了一個自我抒發、感時傷逝、縱議時弊、吞吐塊壘的一個平台。兩千多年過去,磚上文字的活力、活性仍撲面而來。墓磚,當時他們想著是會永埋地下、不見天日的東西,一下子有了綿綿不息的生機。從資料上知道,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亳州市文物管理機構就對十余座東漢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發現了曹操祖父曹騰墓、父親曹嵩墓等宗族墓群,墓群占地約十多萬平方米,累計清理的文字墓磚有600多塊。我見到的磚塊,字型大多寫得隨心、灑脫,內容更是百無禁忌、大見性情。這就是一己之身面對自我時的誠實書寫,不求溝通,漫無目的,像某些特殊時刻「寫後即焚」的詩稿一樣。這些困頓、苦悶的窯工,也超越了他們的身份、階層、處境,觸碰到了人自身:這個過程本質上是詩性的。初看墓磚時,我腦中躍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詩人大沼枕山的兩句話:「一種風流吾最愛,魏晉人物晚唐詩。」這些窯工,算是最底層的魏晉人物了吧,這些斷磚殘瓦上,也確有一口真氣充沛激蕩、凝而不散。馮友蘭先生曾說:「魏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大致如此吧。那天,我俯身在展覽大廳的玻璃櫥窗上看了很久,其實我真想在這些磚前,靜坐冥想一日,最好是展覽大廳內空空蕩蕩。這些文字磚,我見到的不足百塊,最近還在尋些資料看,這個系列的詩,我或許還會再寫一些。

曹操宗族墓文字磚拓片
寫歷史主題的詩,最忌諱的是,順著史實的脈絡去描摹,那一定很糟糕。我們要寫出的,不是「歷史的面相」,而是「歷史的心象」,應該一巴掌拍碎了,成粉末了,再去塑形,再去重構,最好能呈現出一種與現實有著「共時性」的歷史。在我心裏,歷史不過是現實的加長版,歷史只是比現實多了一層時序結構而已。【了忽焉】中的窯工,可以是,或者說正是此刻的我。語言有著這樣的神奇能力。我們每時每刻都在使用著的日常語言,也首先是歷史的,哪個漢字沒有數千年了?這個不難理解——歷史透過語言作用於現實中的每一個人,我寫詩的語言,不僅反映了思想的現實、心靈的現實,事實上也要呈現歷史的「現實態」。換句話講,歷史其實是現實的一個特殊部位。雷蒙·亞倫(法國思想家)有句話講得非常精彩:「歷史是生者為了活著,不斷去重建死者的生活。」當曹操宗族墓的磚塊躺在博物館的聚光燈下,我們以即時的眼光、當下的身份、現代的理念在註視著它,它就是現實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混成現實」的一部份。它不是「扮演現實」,它就像古琴瑟聲、洞簫聲與當下的電子音樂合成了一個曲子,古琴聲是它自身的一個嶄新的創造。我們在內心默然闡釋著這些文字磚,我們與它的對話在展開,我們無疑就是它們在「活著時」的旁觀者,正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樣,這些文字磚所攜帶的生命資訊是沒有終結的,再過數千年,它依然能打動觀者的心,或者說,它的生命力是突破了時間和空間之有限性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通古今之變,語言和詩就是「通」的渠道、「變」的載體。從寫作的角度,從歷史的廢墟上來展開「物我關系」,又似乎更利於建構出詩中開闊的空間感。我覺得有必要同時強調的是,詩的力量,足以在任何事物上留下深深鑿痕,我對寫什麽題材從來沒有很強的分別心。換個說法,我對歷史題材、歷史元素在詩中的存在,也從來沒有任何執著。我寫歷史,但絕不是從中確立自己的文化立場,所以也不會因此而給自己硬扣上什麽文化保守主義的紙帽子。詩歌中的歷史、文學創造狀態中的歷史,不等同於史學意義上的歷史——它和我們常講的傳統二字,都是一種敞開的容器,它裏面所容留的一切,對我們來說,只是一種寫作的資源。舉個最通俗的例子,筷子,它無疑是種族的和地域的,我們以使用筷子而有別於其他族群;它也無疑是歷史的,我們的繁衍史有它獨到的貢獻;但它更是現實的,日用而不覺。對寫作而言,許多東西拿起來就用,只是一種資源、工具,就像筷子。歷史這個詞,既含奧義,其實也非常簡單而直觀:昨日之我即是今日之我的歷史,手再往前伸一伸,指尖就碰到魏晉的心跳了。歷史是個活體。阿萊桑德雷(西班牙著名詩人)說:傳統與反傳統是同義詞。我更願意聽到的評價是:「【了忽焉】是個新東西,它有了歷史的體溫,又洞穿了歷史。」
崖麗娟: 正如你詩中所說,是磚上的文字給了這些沒有生命的黏土磚「以汗腺和喘息」。那麽,您覺得文字足以揭示歷史的本相嗎?又該如何看待語言在一首詩中的使命?
陳先發: 說來挺有意思,我們的先賢大哲們,對語言是否具備呈現真理性內容的能力,其實是不信任的。不信任的痕跡處處可見。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講「不言之教,無方之傳」,禪宗六祖慧能講「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和「諸法美妙,非關文字」等等,充滿了對語言的疑惑。在先哲們那裏,老子的「道」、慧能的「本心」、王陽明的「良知」等,都是一種對語言的超越性存在,這跟維特根史坦所謂的「不可言說之物」是大致類同的。
這似乎是我們在語言中的兩難之境:一方面向往不立文字的心心相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文字來作永無止盡的闡釋。當然,禪宗講不立文字,也不是絕對地不寫些什麽,更多的是在隱喻「指月時,眼睛不要只盯著手指」。我一度在這個問題上是悲觀的,覺得文字不足以揭櫫歷史的本相,它所展開的,只是對歷史的想象而已。不光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在呈現所有的真理性內容上,文字乃至語言之力都是孱弱的。如果此處要為寫作二字新下一種定義,也許只能是這樣的:寫作即是一個人對上述能力孱弱的「自知」與「不甘」。
從這個維度,寫作的無力感,或者說寫作本身具有的消極意味,來源於我們總是企圖述說那不可言說之物。我們通常講一首詩好,是感受到了「在詩之內、言之外」,有那個不可言說之物的在場,甚至是你感覺到了冰山不出海面的那個龐巨的基座部份,感受到它的壓力、氣場、逼迫感。這種感受的傳遞,對一首詩的閱讀功效是關鍵的,但也沒有辦法說得過於清晰。此不可言說之物,是喧嘩之所以被聽見的、讓喧嘩現身的巨大沈默部份。我們寫詩,也因為深信詩有以言知默、以言知止、以言而勘探不言之境的能力。
你提到「使命」二字,我覺得大有意味。我舉個例吧。我曾被一張照片深深打動,很想為這一剎那寫首詩。1977年發射的旅行者1號太空探測器,於1990年2月14日在距地球67億公裏處,接收了人類最後一條指令,「回望」了地球一眼並拍下了如滄海一粟般、地球在深空的照片。據說在此一瞬後,旅行者1號便一去不返地沒入了茫茫星際。這個場景當然是人類實踐的壯歌,本質上它同時是一曲悲歌:是人以一己之渺茫之薄弱,面向宇宙之無垠時的向往、對峙和最終無望的和解。這次「回望」太動人了。因為它飽含了人之寄托,所以才談得上使命,負得起回望,但它的命運又終是杳不可測的。這就是一個詩人在無限的語言空間中,一首詩在無盡的時間旅行中的樣子吧。

旅行者1號在距離地球64億公裏處拍攝的地球
崖麗娟: 為了做好訪談,近期我集中將您2009年前後創作的五部長詩【白頭與過往】【你們,街道】【姚鼐】【口腔醫院】【寫碑之心】,重新都讀了一遍。雖十余年過去,仍為它們的精神氣象與心靈容量所震動。有詩歌寫作經驗的人深知,寫短詩可能更多憑靈感,而這種四五百行的長詩寫作,非常消耗心力和時間,更考驗耐力。我想了解的是,是什麽觸發您寫一首長詩的決心?您覺得在長詩寫作行程中,哪些東西是非常重要又難以把握的?
陳先發: 寫長詩往往是迫不得已。當一團面粉在你手中劇烈地發酵了,你不得不找個大點的袋子裝下它。長詩正是這種「大袋子」。你很難想象一種巨物要硬塞在一個微小軀殼中,聶魯達【馬丘比丘之巔】、艾略特【荒原】中的縱橫激蕩之思,豈能在一首短詩中得到舒展和盡興的表達?但我也總聽到有智者在說:長詩是可疑的。
確實,長詩寫作是個巨大挑戰。語言推進中的考驗當然很多,我覺得最難的是兩樣:個人語調的形成,以及,一口氣如何在巨大結構中自由呼吸。語言的基調和語氣的執行,是一首詩中根本的東西。這兩者也算是互為表裏的,語調關乎語言的呼吸、色彩、活力等等,詩之沈、之思、之宏觀建構,都需在這種語調中去層層呈現,走向縱深。語調與詩之所思不匹配,就會有不倫不類的感覺。有些詩,讀兩行,就讀不下去,為啥?語調不對——你這盤菜燒得味道不對,即便燒的是山珍海味,也沒用。語言的味道是第一驅動力。只有語言的快樂,可以破除長詩中容易形成的語言的疲倦。我在動筆之前,反復琢磨的東西和最費腦力的就是這個:語調。定了語調之後,就要考慮「一口氣」如何在各個部位穿行,如何在相對龐大的格局與建構整體中保持細節的生命力和柔韌性,如何讓這口氣在數百行詩句間自如貫通。難就難在,這口氣的自由接續。沒有了這口氣,長詩很容易淪入字詞的泥潭,必須有這口氣催動語言的靈性引導著你,往結構的深處走。沒有這口氣,數百行長詩焉能不讓人生出累贅、堆砌之感?有些長詩,思不可謂不深,力不可謂不沈,但看得出作者太想往詩中塞東西了,結果弄得面目可憎。詩的豐富性,不是靠充塞來完成的。
有兩點體會:一,「營造空白」很要緊,甚至可說是讓長詩活命的一招。在結構中設定大片的空白、空地,以容留閱讀的自如轉身,來促成寫與讀之間美妙的互動,是至關重要的。結構中的空白,往往是思想的充盈之處。在敘事、情感、語意演進的過程中,突然形成斷裂,帶來空白,這空白並不是「什麽都沒有」,而是讓空白說話。空白,在恰當位置上的表現力會出人意料的強大。二,讓長詩內部出現各類聲音的交響。長詩是個復雜的空間,也是個自足的生命體。它的內部,必須充滿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聲音。佩索阿說:「我沒有哲學,我有感官。」大家都明白,長詩重思。越是重思,越是要讓感官的體驗系統得到充足的釋放。從詩中「聽出什麽」,是種微妙的閱讀體驗。最美妙的感受是:從同一首詩中每次都能聽見不同的聲音,這並非你的耳朵特異,當代詩釋放的本即是一種變化、變量、變體。與其說你聽見了詩中的一種聲音,不如說你聽見了一種可能性。甚至是你聽見了什麽,來源於你想聽見什麽。寫作與閱讀間,橫亙著動蕩不息的戲劇性連線。好詩所創造的另一種奇跡是,它讓你聽見的聲音,根本不來源於耳膜。你的每一個毛孔、每一組細胞、每一根腦神經都有傾聽的能力。你能目睹自身的「聽見」。在好詩中,詞之間的碰撞也仿佛是有聲音的。詞與詞之間有一種奇妙的相互喚醒,有時與作者的寫作意誌並無關聯。寫作中所謂的神授,其實是一個詞以其不為人知的方式和氣息喚來了另一個詞。它讓你覺得你所聽見的聲音,出自你的生命而非眼前這首詩。
我過去的幾首長詩,累積了一些想法,但其實也攢存了許多力不從心的遺憾。【白頭與過往】意在從一對魔術師生平敘事中打通現實與幻相的關系;【你們,街道】展開的是對後城市化的反省以及對「破與立」的辯思;【姚鼐】是對我家鄉桐城先賢致敬並進而開啟一種命運圖軸的詩;【口腔醫院】其實是一首企圖精研語言與人關系的一首詩;【寫碑之心】是祭父之作,在我父親逝世兩年後才爆發而出。從語言能力而言,這些詩中精神的、情緒的、情感的、語言層面的能量,都不可能濃縮於一首短詩中。也可能一場大風雨,必須要在曠野上行進。當然,不是講短詩中不能有宏大的內在空間,說到底是能力的局限問題。
曾有詩人跟我討論過,長詩中如何處理繁與簡的關系。這個確實是個微妙處。我的想法是,細節宜繁,針尖上的舞蹈要足夠;大處宜簡,否則容易淪為空響。要看具體情況,繁簡並無高下之分。在【黑池壩筆記】中我曾寫過一段話來討論這個問題:「範寬之繁、八大之簡,只有區別的完成,並無思想的遞進。二者因為將各自的方式推入審美的危險境地,而迸發異彩。化繁為簡,並非前進演化。對詩與藝術而言,世界是赤裸裸的,除了觀看的區分、表相的深度之外,再無別的內在。遮蔽從未發生。」

詩集【寫碑之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崖麗娟: 我一直關註您在建立新的詩歌形式上的探索,比如讀到組詩【枯七首】,每一首都以「枯」為題,仿佛一部奇異的生命合唱,令人耳目一新。您是如何想到切入這個主題或者說因何耗費大量筆墨在這個意象之上?
陳先發: 枯這種鏡象,似乎只有中國人深得其中三昧。枯,既不是無,也不是死,以枯而生發的藝術創造力在各個領域澎湃不絕,從庾信的【枯樹賦】,到李義山的枯荷聽雨,再到王維畫大片的枯樹寒林,元代倪瓚更是畫枯成癖了,宋畫中諸家畫枯樹是各盡其妙。詩中的表達更是豐富,不全是物之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也是一種枯境。我寫枯七首,不過是我個人對枯之美學的當代演繹。
寫完組詩【枯七首】後,我在【黑池壩筆記第二卷】中對「枯」有著數十條解讀,這裏我就偷個懶了,順手摘錄幾條,作為對你這個問題的回答吧:
(1)作為一種起源,也作為一種目標: 枯,對那些有著東方審美經驗的人似乎更有誘導力。與其說多年來我嘗試著觸碰一種「枯的詩學」的可能性,不如說,作為一個詩人我命令自己在「枯」這種狀態中的踱步,要更持久一些——倘若它算得上一個入口,由此將展開對「無」這種偉大精神結構的回溯。枯,作為生命形式,不是與「無」的結構耦合,而是在「無」中一次漫長的、恍然若失的覺醒。對我而言,這也足以稱之為詩自身的一次覺醒。(2)枯,賦予人的「盡頭感」中蘊藏著情緒變化與想象力來臨的巨大爆發力。此時此地,比任何一種彼時彼地,都包含著更充沛的破障、跨界、刺穿的願望。達摩在破壁之前的面壁,即是把自己置於某種盡頭感之中:長達十年,日日臨枯。枯所累積的壓制有多強勁,它在穿透了舊約束之後的自由就有多強勁。(3)枯是詩之肉體性的最後一種屏障。它的外面,比它的生長所曾經歷的,儲存著更澎湃的可能性。對枯之美學的向往,本質上是求得再解放的無盡渴望。(4)我們對同一源泉存在著無數次的喪失:對枯的理解與解構,也不會是免洗的。(5)審美趨向的過度一致、精神構造的高度同構,是一種枯。消除了個體私密的大數據時代之過度透明,是一種枯。到達頂點狀態的繁茂與緊致,是一種枯。作偽,是一種枯。沈湎於回憶而不見「眼前物」,是一種枯。對生活中一切令人絕望的、讓人覺得難以為繼的事件、情感、現象或是寫作這種語言行動,都可以歸類到「枯」的名下進行思考,但對枯的思考,並不負責厘清表象:枯是這所有事物共有的、不可分割的核心部,也是從不迷失於表相的、或者說是根本就沒有面孔的「蒙面人」。(6)漢樂府和李白均有「枯魚過河泣」詩。八大山人畫脫水之枯魚。魚在枯去,河在虛化。撇開本義,離根而活,枯幹即是自由的達成。(7)所有必枯之物,仿佛生著同一種疾病,但它帶來的治愈卻千變萬化。面對某種枯象,我們在內心很自然地喚起對原有思之維度、原有的方法、原本的情緒的一種抵抗,我們告訴自己:這條路走到頭了,看看這死胡同、這盡頭的風景吧,然後我需要一個新的起點。所有面貌已經煥然一新的人,都曾「在枯中比別人多坐了會兒」。(8)當你筆墨酣暢地恣意而寫時,筆管中的墨水忽然幹涸了。你重蘸新墨再寫時,接下來的流淌已全然不同。枯是截斷眾流,是斷與續之間,一種驀然的喚醒。(9)人類的知識、信條、制度或感性經驗,都須經受「枯之拷問」。有多少廢墟在這大地上,多少典籍在我書架上沈睡:托克維爾的臉上蒙塵多深?陀思陀耶夫斯基在我案頭又荒棄多久了?在某個時刻、某種特定機緣下,我將在他們的枯中有新的驚奇與發現:仿佛不是我生出新眼,而是他們的枯中長出了新芽。
【枯七首】不是長詩,因為在這七首中,不存在內在的遞進結構。從表象上看,枯,是一種生命的困境,對枯的書寫是向此困境索取資源——它如此深沈、神秘而布滿內在沖突。人對困境的追索與自覺,毫無疑問,帶來了某種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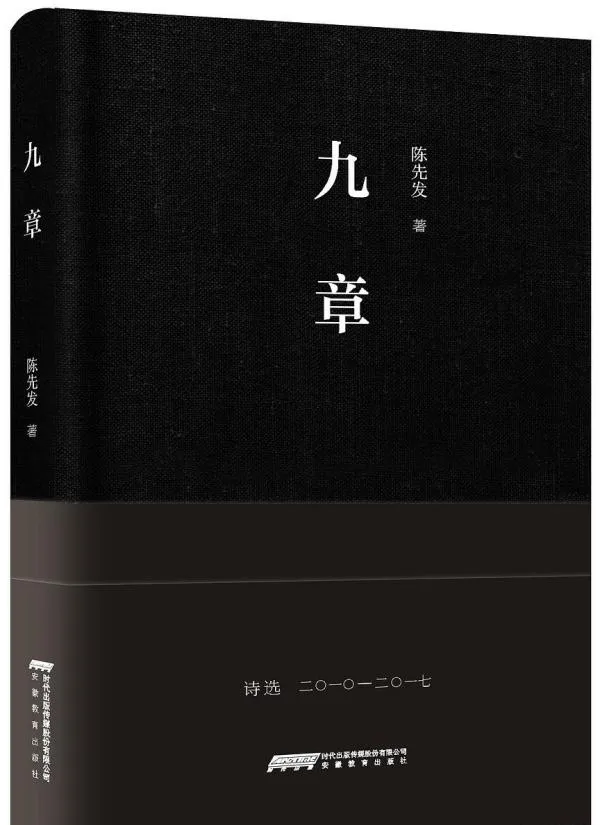
詩集【九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崖麗娟: 我和您一樣都曾經長期在媒體工作,我的體會是,做媒體能接觸相對寬泛的人和事,對所見所聞所觸的增益和開闊眼界確實有很大的幫助,這也引出一個可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您覺得現實與詩的寫作之間有一種正向推動關系嗎?一個人作品的豐富性跟哪些因素有關?
陳先發: 見得多,也未必就是增益。千個人、百座城,也可能重復的只是一種現實。我的想法是,詩與大家平常所講的現實沒有直接關系,它只跟一個人承擔的「內在現實」有關。這是兩個不同質、也不等量的概念。眼觀八方、內心卻一無所見的人,少嗎?記得博納富瓦在談論策蘭時,有句話說得好:「不蒙上雙眼,就看不清楚。」確實,真相與真正的纖毫之末,是心靈視域內的東西。詩源於閉上眼依然歷歷可覽的東西。當然,現實世界可以刺激與啟用人的內在空間,但真正詩性往往歸集在鬥室之中的萬水千山,芥粒之內的千峰萬壑。
一個詩人的豐富性與他所感受世界的維度和方式相關。參照一下我多年前寫的一段話:「在一顆敏銳的心靈之中,世界的豐富性在於,它既是我的世界,也是貓眼中的世界。既是柳枝能以其拂動而觸摸的世界,也是魚兒在永不為我們所知之處以遊動而洞穿的世界。既是一個詞能獨立感知的世界,也是我們以挖掘這個詞來試圖闡釋的世界。既是一座在鏡中反光的世界,也是一個回聲中恍惚的世界。既是一個作為破洞的世界,也是一個作為修補程式的世界。這些種類的世界,既不能相互溝通,也不能彼此等量,所以,它才是源泉。」
除了認知維度,詩人之豐厚,也獲益於他對語言的覺悟力。語言會慷慨饋贈他一些意外之物。詩歌語言的動力機制有神秘的一面,時而不全為作者所控。總有一些詞、一些段落仿佛是墨水中自動湧出的,是超越性的力量在渾然不覺中到來。仿似我們勤苦的、意誌明確的寫作只是等待、預備,只是伏地埋首的迎接。而它的到來,依然是一種意外。沒有了這危險的意外,寫作又將寡味幾許?
許多好詩是令人費解的。作品的豐富性,有時也出自讀與寫之間的復雜交織。好詩往往有迷人的多義性,它部份來於作者的匠心獨運,部份來於讀者的枉自多解。好的詩人是建構的匠師,當你踏入他的屋子,你在那些尋常磚瓦間,會發現無數折疊起來的新空間。當你第二次進入同一首詩,這空間仍是嶄新的,仿佛從未有別的閱讀打擾過它。
崖麗娟: 您在寫作中有沒有出現過難以為繼的停頓階段?怎麽度過這種個人危機的?
陳先發: 難以為繼、猶似身陷語言的泥濘之感,不僅在許多時刻有,甚至算是我的寫作常態之一。一些作品,往下寫不動了,就歇一歇,甚至直接撕掉,也並不覺得有什麽可惜。那種一氣呵成的、靈光一閃便揮筆而就的作品,當然也有,更多作品是在疙疙瘩瘩、漸行漸悟中寫成的,前者只有感謝老天,再愚鈍者也有暴雨直擊天靈蓋、靈魂出竅的那一刻,但我覺得後者才是正道、大道。難以為繼,甚至憂心如焚的時刻,恰恰是珍貴的,它構成了寫作中困境與超拔的原力,是錘煉人的好道場。慧能講得好呀:「煩惱即菩提。」
藝術說到底,是個體生命力的激發,是一個易朽與短暫的生命體,在孤獨時告訴自己如何去追逐那不朽的願望。我們對抗虛無的武器只有兩樣:我們的卑微與我們的滾燙。一己直如螻蟻,人面對無垠時之弱小,人面對速朽時有真情,是這兩樣,令我們拿起筆來。這桿筆,也唯有經過千錘百煉甚至是艱苦卓絕的一個過程,才能真正形成價值。
崖麗娟: 目前正在進行的作品有些什麽特點?您的自我期許,是在哪些地方獲得突破?
陳先發: 手頭最重要的活兒,是系列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的第三卷,爭取明年初出版。前兩卷是2014年和2021年出的,這中間的間隔拉得太長,我期待以後這個系列完成和出版的密度加大些,節奏加快點,一年出一新卷最好。這是一套百無禁忌的遊思錄,寫作的主體內容其實早已完成,現在是整理至第三本。整理,我並不視作是簡單地歸納,而是再造,重新為這些言說的碎片集確立一種內在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第三本如何突破前兩卷已經形成的某種慣性,是我正埋頭處理的一個要害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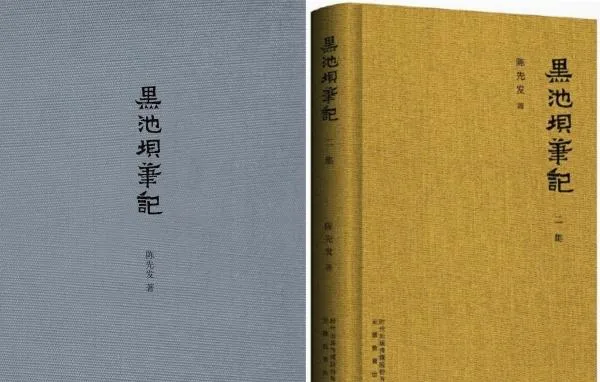
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系列
另有些列入寫作計劃的大體量作品,比如,一部有關量子纏結的長詩,是一個新的維度交織著新的難度,能不能最終寫成,還很難說。還想著手寫一本長篇小說,我在小說上的經驗積累較少,二十年前嘗試著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拉魂腔】,從淮河災難史中去寫宗法制度在中國底層的解構,東方式鄉村圖景的崩塌,我對這個向度的思考一直有興趣,也攢了些想法,有沖動再去觸碰一下。寫作是個人意誌力的左沖右突,什麽結果,難以預知。加上工作強度大,對個人時間和精力占用多,不敢說期待什麽突破,做做再說吧。
崖麗娟: 我註意到,今年8月份,幾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在廣州主持召開「詞的重力場——陳先發趙野作品研討會」,能否談談現場有關情況?研討會主題很有意思「詞的重力場」,該如何理解?
陳先發: 在這裏,再一次對詩人陳陟雲表達謝意,他費了很大心力匯聚多方資源,為詩人們召開專題研討,這個系列若持續下去,當是詩史上出彩一筆。本次研討,國內詩學理論界最活躍的一批名家都到場了,我理論根基薄弱,聽下來自覺獲益良多。這個研討,我是空著雙手去的,原想做個徹底的傾聽者,因為要互動,所以也談了點想法。
研討會主題的確有意思:「詞的重力場」。從文學角度觀察,資訊時代呈現的是「重力場」不斷消解的失重狀態。過去心懷壯闊的遠行,現在高鐵瞬間就抵達了;過去充滿意味的登臨,辛苦而得的一覽眾山小,如今纜車頃刻就瓦解了它。碎片式、即興式、戲謔式文化景象,讓「重」無所寄托,精神創造領域因之產生了巨變。恰是這種失重,令這個研討有了遠超出兩個研討物件本身的意義。
我想寫作者的一個基本願望,是喚醒一個更為內在的自我。這裏的喚醒,是指發現,是抵達一種語言的「場」,或說是「態」。它大致的特點有三:一是,更為凝神、凝視、專註的自我。可能再難找到比寫作更能將一個人全部身心凝聚於一點的勞作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受各種困擾、質疑、失敗,常常處在生命力的渙散之中,目光難以因凝於一物而到達生命意誌的深處。而寫作,逆轉了這種狀態,我們因凝神而捕獲了力量感,因專註而趨於某種超越。這個過程也是開放的、沒有盡頭的。諺語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從詩歌的維度看,它又是「羅馬是永不可能建成的」和「羅馬正是一瞬建成的」的疊加狀態。這個朝向單一、純粹的途徑是快樂的,所以對寫作者充滿了強大的重力。我的體會是,成詩的愉悅,再無一字可動的愉悅,勝過任何其他方式的愉悅。這是自我完善的道路。二是,如果寫作是有效的,它一定處身於一種多維的對話關系中。與時代的對話:這個不可避免,只能層層卷入,每個人都是具體時空中的生命體,經歷著時代賦予的、雞毛蒜皮般具體問題的種種拷問。不管你寫下什麽,只要你對自身是忠誠的,那麽你寫下的每一句,都是對話的繼續、答案的呈現。與自我的對話:人自身的缺陷帶來了內心生活的分裂、分裂,自詰同樣不可避免,寫作可以視作自詰的種種變體。人被自身的目的所蠱惑,也同樣對這種蠱惑抱有敵意,哪一個我,不是矛盾著的「眾我」的集合體呢?與語言的對話:寫作是語言的運動,對過往語言經驗積累的摹寫、審視、審判,對個體語言風格的向往,是寫作的原始沖動之一,要時時將語言實踐導向深入,那種一眼即辨的個體語言形象是如何建立的?個體生命體驗的復雜性是如何輸導至語言當中的?這都仰賴於寫作者與語言互信、互搏的對話關系趨於深化。當然還有與自然的對話關系,在我們的文學脈絡中,自然一度立身於神位之上,今天這個位置的空無,又能予今日之寫作什麽樣的啟示?總之,一旦動筆,我們就被迫在這多重的對話關系中,時而緊張、時而舒緩地進行各種再構與重建,語言的智慧與文學的行程也借此展開。三是,我們的詩歌仍需從對歷史的「吮吸」中審看自身。「來處」本是一個可疑的物件物,文學史自體的變幻中也留有我們對「去路」的建構。「重力場」三個字,它當然不是指趙野和我已經完成的某種詩學特質。詩趨向精神領域的重力,早已構成漢詩的傳統,從這個指向上去闡釋杜甫,我們已談論得夠多了,這個重力不是指某種分量重量,「輕」的風格,也可以達到審美效應上的重力,我倒是傾向於認為,人對內在自我的發現永不止步,才真正匹配得上這重力二字。時空的位移,不斷造就更新的、更深存在的自我,我們面對它永遠存在著新的「匱乏」,這個敞開的精神容器永不可被填滿,我們對此種「匱乏」的渴求甚於被餵飽的渴求,這是「詞的重力場」的真正要義。今日之現實,不再是歷史的某種線性延續,科學的突進讓人的視域由原子、誇克、量子的遞入而趨向令人窒息的精微,生活的現實,已陷於虛擬空間強行插入的「混合現實」「超現實」的多重圍困,我們一度棄置的文化態度中,我們對文化態度選取的兩難之境中,是否真的埋伏著可能新生的命題呢?這些是研討會上即席隨興的想法,肯定不夠嚴謹,留待以後的寫作實踐去延續吧。
(崖麗娟,壯族,出生廣西,現居上海,詩人,兼事詩歌評論。出版詩集【未竟之旅】【無盡之河】【會思考的魚】,其中【會思考的魚】榮獲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優秀作品獎。編著有10余部文史書籍,在各大報刊發表新聞報道、傳媒研究、歷史研究、文藝評論、作家訪談等各類文章100多萬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