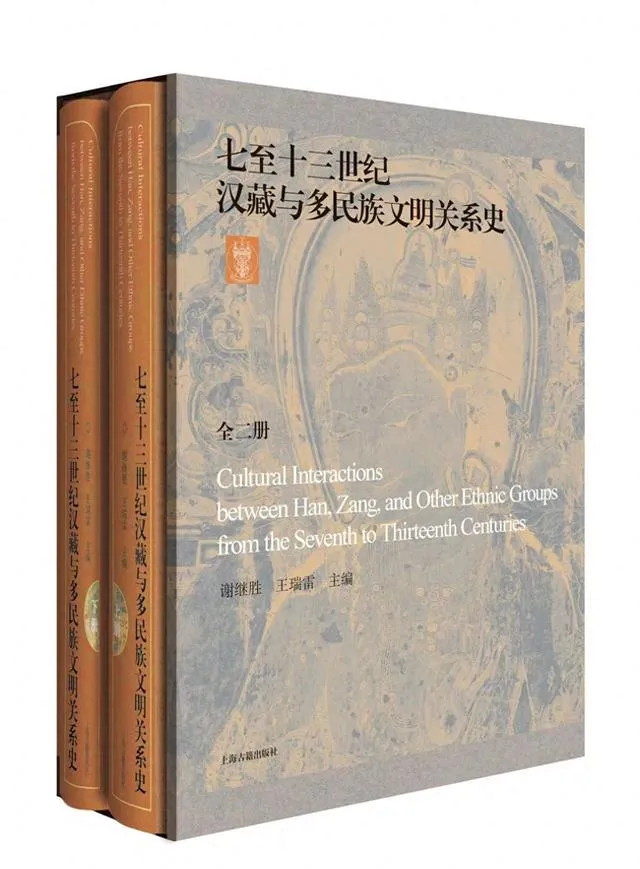
【七至十三世紀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關系史】,謝繼勝 / 王瑞雷 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月版,680.00元
「貓鬼神」是在西北農村廣泛存在的一種漢、藏、回、土、蒙等族均有信仰的邪神。「主要存在於甘肅、青海,尤其在青海河湟地區的漢、藏、土族當中信仰尤為廣泛,特別是:西寧市的湟中、湟源和大通;海東地區的平安、樂都、民和、互助、循化;海北的門源、海晏;海南州共和、貴南;果洛州的瑪沁。」「一般來說,養有此物的人家,被認為是不祥、不吉的,因而備受人們的鄙視和反感,一般沒有人願意和他們做親戚、朋友。」屬於介於神鬼之間的一種「精靈」信仰,也就是「妖」或者說「邪神」,一方面他們自己本身有很多缺陷:諸如都具有心胸狹窄,為害作惡,搗亂生災,形象邪惡等特征;一方面人們供養它們,多與個人利益有關,對它們的信仰也是懼怕多於崇敬,不屬於公開的信仰,多處在一種隱諱和禁忌的環境中。
現在流傳於鄉間的「貓鬼神」信仰中,供奉、崇拜的物件並不是其起源傳說中一脈相承的神靈,而是可以隨時生成的一種「邪神」,尤其從它的生成方法中可以看出其濃重的巫術色彩。「貓鬼神」的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從祖先手中傳承而來,貓鬼神就具有了一種家神的特征,影響供奉者家庭世世代代,連綿不絕;二是利用特殊方法現時生成,生成後「貓鬼神」即受供奉者的奉祀和役使。
【隋書·外戚傳·獨孤羅傳附弟陁傳】曰:
……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轉入其家……會獻皇後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貓鬼疾也。」……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貓鬼……其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陁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數日,貓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並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後所,使多賜吾物。」……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雲貓鬼已至。……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貓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
【隋書·後妃傳下·隋文獻皇後獨孤氏傳】記載:「異母弟陁以貓鬼巫蠱咒詛於後,坐當死。」
【太平廣記】卷三六一載:
隋獨孤陀,字黎邪,文帝時,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家」原作「甥」,據明抄本改。)高氏,先事貓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帝微聞之而不信。其姊為皇後,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貓鬼疾。」帝以陀後之異母弟,陀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由是疑陀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陀。言無有,上不悅,左遷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楊遠、皇甫孝緒雜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從陀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貓鬼每殺人,被殺者家財遂潛移於畜貓鬼家。帝乃以事問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陀夫妻,將死,弟詣闕哀求,於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訴其母為貓鬼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詔赦訴行貓鬼家焉。陀亦未幾而卒。
這幾則史料我們看到此物皆與「獨孤」有關,獨孤乃鮮卑大姓,吐谷渾本為遼東鮮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晉末,首領吐谷渾率部西遷到枹罕(今甘肅臨夏),後擴充套件,十六國時期,鮮卑勢力強大到擁有青海大部土地,征服了羌人,建立了吐谷渾王國,統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方的羌、氐部落,其疆域東至西傾山、白龍江流域,北接祁連山,西至巴顏喀拉山,南至川北阿壩、松潘一帶。至5世紀末6世紀初,吐谷渾達到全盛,東部疆體擴張至洮河流域,西部也達到了今新疆若羌、且末一帶,所統治的範圍恰好覆蓋了現在的安多藏區。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太平廣記】卷一三九「貓鬼」條載: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由「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余家」來看,當時貓鬼信仰的規模應該是很大的,是一個以往沒有引起人們註意的民間信仰。而且隋亡後,貓鬼神信仰並沒有消失,唐高宗時期由長孫無忌等所修【大唐疏議】第二六二條:「蓄造貓鬼及教導貓鬼之法者,皆絞;家人或知而不報者,皆流三千裏。」從此處侍奉貓鬼成為一個專門的罪名看,應該信仰者還是頗多的,而且朝廷對此打擊甚為嚴厲。
這幾則史料和上面的田野所得,至少可以說明三個問題:一,此類信仰至少在公元4世紀已經有之並且延續至今,主要傳播區域大致就在今天安多藏區所覆蓋的區域。二,主要史料記載都與「獨孤」鮮卑氏有關,暗合了田野中等所調查關於來源於吐谷渾的傳說。三,與巫蠱和靈異有關,與「忒讓」特征幾乎一致。
眾人口中所敘述的「忒讓」和史料中所記載的或者是學者們田野工作中得來的「白哈爾」「貓鬼神」的特征基本重合。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是同一種「靈異」在不同的具體地理環境下和族群文化基於自身文化內涵的不同表述。其顯著特征是與巫術和禁忌相關。
人們經常用「迷信」或「淫祀」來描述民間信仰,並將其定位成原始的、落後的、低階的宗教形態,但是對於民眾來說,動物信仰是與其生活緊密相關,並且與家族、村落、區域文化有密切關聯的民間信仰系統。「忒讓」「白哈爾」「貓鬼神」這些在不同的區域和社會文化環境中被賦予的不同名稱在實際內涵中卻驚人地一致,邊緣性的信仰廣闊放射線至青藏高原及其毗鄰的黃土高原和蒙古高原,放射線整個西北和部份西南區域,這就如巴斯(Fredrick Barth)及莫門(Michael Moerman)等主觀論者對客觀文化特征的看法:文化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經常呈現出許多部份重疊而又不盡相同的情況。以各文化特征而言,它們的分布大多是呈連續的過渡性變化,族群邊界似乎是任意從中劃下的一條線。此類信仰更多的是呈現出一種地域性特征,而不是屬於某個特定族群,藏族社會中的本教將之歸類為「贊」,而藏傳佛教將之認為是「白哈爾」護法神,藏族群眾在民間社會則稱呼它為「忒讓」,而其上述這些說法除了形象與「貓鬼神」有較大出入外,其他體征與漢、回、土族所描述的「貓鬼神」幾乎完全一致。正如筆者在第一部份的田野中調查所得拉蔔楞的「忒讓」傳說多來源於塔哇,眾人的猜疑也指向於那裏。而正如貢保草在對「塔哇」這種圍繞著寺院的建立而自動生成的村落進行系統研究後所指出的:「塔哇」文化不是屬於某一個民族的文化,而是在此地生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此類信仰來自多個族群混居之地,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有其大同小異的表述,但當我們將其不同情境下的「忒讓」「白哈爾」「貓鬼神」列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顯然它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地域性特征,而非族群性特征,而且從我們在上面三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此類信仰分布範圍遠比安多藏區這個區域還要廣闊,但對「白哈爾」起源的分析也指向最開始的傳播中心就應該是現在的安多藏區,歷史上的霍爾吐谷渾所統治的區域,但其在西南和西北表現出的不同狀態也顯示出此類信仰的區域性特征非常明顯,有很大的差異性。

白哈爾,Rubin Museum of Art收藏唐卡,西藏風格,18世紀
「忒讓」在西北區域被認為是階層低下的底層神靈,但在傳播到西南轉換了一種解釋體系後,卻以「白哈爾」護法神的面貌出現,呈現出一種位居高位的特征。本教研究者認為「忒讓」是青藏高原原始神靈體系中「贊」的一種,而另外一些非藏學背景的研究者認為「貓鬼神」屬於民間精怪崇拜(即萬物崇拜)中的動物崇拜行為,兼有南方巫蠱的一些特征。「這些有害的精靈與我們剛才所談到的好精靈似乎是按照同一模型構想出來的。它們被表現為動物,或者半人半獸,」此類信仰包含有巫蠱和靈異的雙重特征,源於物怪的民間信仰之所以對各種不同的社會背景的人具有極大的吸重力,正因為它們為追求不分是非、個人和地方利益者提供機會,免受道德輿論的幹涉。
人們利用「忒讓」的邊緣力量,妥善地處理日常生活中的身心疾病、銀根吃緊等失序狀態。「忒讓」吊詭地同時受到敬重和憎惡,受到個人家庭的敬重,而受到更大範圍內因為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而產生的憎惡。索端智在對同處安多藏區的熱貢社群守護神進行研究之後認為:「守護神所具有的世俗之神的特點,它們缺乏基本的善惡觀念,實際上守護神信仰也根本不是建立在善惡觀念基礎上的。」與此相對的是,此類精靈性質的性質並不是特例,有其薩滿內容,東北和華北也存在此類性質的信仰,但也有其區域性特征,比如狐仙信仰就是華北區域的,而地仙信仰則是屬於東北區域的。「狐仙信仰的地區含括施堅雅的‘大西北’和‘大東北’兩大區域,大概涵蓋了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皖北和江蘇。」李慰祖透過對「四大門」相關的神話和儀式的描述及分析,確認了「四大門」信仰屬於「薩滿教」內容的體系,周作人曾把「四大門」理解為東北亞地區薩滿教的余脈。正如劉正愛在其研究中所發現的那樣:「四大門」和「地仙」兩個不同的地方性概念本身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地區的差異性。「動物信仰在不同的地域反映出了不同的社會文化特征,華北地區的‘四大門’和東北地區的‘地仙’表面上雖具有相似的信仰形態,但在東北地區,動物信仰經過融合多種地方因素已經發展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信仰體系。」「忒讓」的信仰則是涵蓋西北和西南區域的,但是需要謹慎對待的是:它在兩個區域中的解釋體系的差異性和因此帶來的地位的顯著差異性,由此也表現了它特殊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民間信仰是與當地的地方性知識緊密結合而形成的,其包含著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中的各種習慣、秩序,地方性極強。民間信仰的這些特征決定其具有內在的社會潛秩序和地方性特征。
他們的邊緣性具現了日常生活中文化沖突和妥協。忒讓信仰庇護了遊走在道德灰色地帶的欲望追求。「忒讓」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互惠關系是脆弱的。對它的任何不敬將瞬間招致很大的禍患。「忒讓」型別的精靈信仰崇拜中的私己,且常是不道德的寓涵,這些仍舊受到世俗道德的約束和佛教倫理的排斥。維系「忒讓」型別的信仰是一件高度個人化的事情。「忒讓」信仰在規範的社會秩序中是一種破壞力量,作為信奉者單向秩序的維護,而不是采用雙向平衡公平的合理約束,對社會的秩序具有一種潛在的破壞性,僅單方有利於信奉者自身的實用性目的,具有巫術的顯著特征。「鑒於巫術和宗教是有分別的,宗教創造一套價值,直接地達到目的。巫術是一套動作,具有實用的價值,是達到目的的工具。」
不只在中國,日本、南韓以及其他東北亞和西伯利亞的文化,也都能發現類似「忒讓」的精靈信仰,比如,Karen Smyers針對日本的稻荷信仰的人類學研究。我們也許從中得到一個制高點,觀察不同的人如何穿越種族和地理的界限,制造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樣性。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忒讓」精靈信仰不僅相對完整地自成體系,跨越整個西北和西南,展現出類「宗教」的特征,實際上還可能是一個更為龐雜的文化體系的一部份。「宗教既是與人生終極意義和價值有關的抽象的思想體系、宏大的宇宙觀和世界觀,也是嚴密組織的象征和儀式,同時也包括從多樣的大規模的集團(行為)到驅靈趕鬼及巫蠱咒術(地方習俗)等、以解決人生中各種問題為目的而采取的行為(所構成)的復雜的(文化)現象。」童恩正先生指出,中國北方東西向的草原民族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帶南北走向的藏彜民族走廊共同構成了所謂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而「其轉折點正在河湟一帶,表明河湟地方乃具有多民族及其文化走廊之匯聚樞紐的地位」。「忒讓」信仰在西北區域不同族群、不同生計方式間的存在,以及它從青藏高原東北緣向青藏高原南部的傳入也從民間信仰的角度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本文選自【七至十三世紀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關系史】,謝繼勝 / 王瑞雷 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