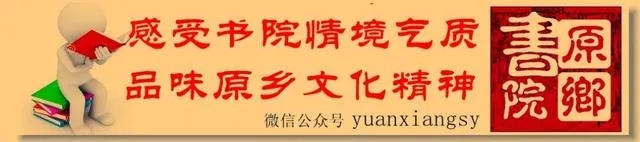
龐余亮
1967年生,現居江蘇靖江。著有長篇小說【薄荷】【醜孩】【有的人】【小不點的大象課】【神童左右左】(系列小說)【看我七十三變】【我們都愛丁大聖】,散文集【半個父親在疼】【小先生】【小蟲子】【頑童馴師記】【紙上的憂傷】,小說集【為小弟請安】【擒賊記】【鼎紅的小愛情】【你們遇上了好辰光】【出嫁時你哭不哭】,詩集【比目魚】【報母親大人書】【五種疲倦】,童話集【銀鐲子的秘密】【躲過九十九次暗殺的螞蟻小朵】等。曾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柔剛詩歌年獎、第五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第十三屆萬松浦文學獎、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第二屆揚子江詩學獎、第九屆冰心散文獎等。
龐余亮的家鄉是江蘇興化,出過兩個名人,施耐庵和鄭板橋。他多次去過兩位前輩的墓地,他們的墓地和他父母的墓地一樣,都是美麗興化的一抔土。「小」,是龐余亮的生命常態。他是家裏十個孩子中最小的,上學後是班裏最小的,被分配到鄉村小學教書,因為年齡小、個子小、體重小,被大家稱為「小先生」。他把15年的「小先生」經歷,再經過15年歲月的發酵,最終寫成了一部【小先生】,並憑此摘得魯迅文學獎。但是,他並沒有停止,繼續留在縣城,以「小」博「大」,推出【小蟲子】【小糊塗】。龐余亮表示:「‘小’讓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樣,讓我仰望世界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我俯視世界的時間。」
本期嘉賓 龐余亮
青年報記者 陳倉
1
鄉村的日子尤其緩慢, 在這緩慢而寂靜的生活裏,
有著其他生活所沒有的驚喜。
陳倉
:
龐老師好,你名字中間的「余」字是排行嗎? 你曾經有沒有想過起一個筆名? 你覺得名字對一個人有沒有什麽影響?
龐余亮: 我的姓名中,「龐」和「余」這兩個字是固定的。「龐」是姓,「余」是排行。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但我從小到小學五年級,並不叫現在的名字,而是叫「龐余東」。家裏人和村裏人都叫我「余東」。在我家鄉的叫法中,我這個「余東」就被小夥伴們置換成「魚凍」。我實在不喜歡這個名字。到了初一,到新老師那裏報名,老師問我叫什麽名字? 我看到老師手中並沒有花名冊,就決定改名,恰巧我最好的發小離開我們村莊,去縣城上初中了,他的最後一個字叫「亮」。就這樣,沒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成功地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龐余亮」。到現在,家裏人和村裏人還是叫我「余東」。有時候我想,如果我還是「龐余東」,那麽「龐余亮」在哪裏? 所以,「龐余亮」更像是我的筆名。
陳倉: 你是江蘇興化人,介紹一下你的故鄉吧。說到興化,這也是施耐庵的故鄉,你從小聽到的故事和我們有沒有不同? 你的文學愛好或者說是審美,是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培養起來的嗎?
龐余亮: 興化有施耐庵,有鄭板橋,我多次去過兩位前輩的墓地,他們的墓地原先和我父母的墓地一樣,都是美麗興化的一抔土。他們的故事就像鄰居家的故事。在納涼的時候,老人們常常繪聲繪色地講起他們的故事,說得就像親眼見到的一樣。我的敘事和抒情方式可能就和這樣的童年經歷有關。但我更加覺得,我的文學背景是無窮無盡的水。
2004年春天,我去北京魯迅文學院第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習。北京有邱華棟,新疆有劉亮程,河南有喬葉,浙江有鐘求是,江蘇是我。課程很多,有一課是當時的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講的,叫【氣象與國防】。課後,他又邀請我們去中央氣象台和國家衛星氣象中心參觀。在國家衛星氣象中心,解說員說到了1991年,國家氣象衛星發現中國有一個縣消失了,立即報告了國務院。那個解說員說,這個縣就是江蘇的興化。我當時就舉手,我就是江蘇興化的,地勢低窪的興化消失在衛星雲圖上的時候,我和癱瘓在床的父親就在洪水的中央。我還記得那個夏天,我反復讀的一本書,是湯瑪斯·伍爾夫的【天使,望故鄉】。這本書和那個夏天,重新塑造了我。
陳倉: 你目前在靖江工作,興化和靖江都屬於泰州。現在是一個大移民時代,很多人都在全國各地到處跑,在上海的叫滬漂,在北京的叫北漂,你雖然一直生活工作在泰州,但是有沒有那種漂的感覺,或者叫做鄉愁的情緒?
龐余亮: 靖江是完全由長江孕育起來的沙洲,人口基本上來自於移民,很有創造性。興化講江淮方言,靖江講吳方言。我在兩個方言之間穿梭,而我現在用的是帶有兩個地方口音的普通話。但我發現,兩個方言體系中的詞根都是相同的。我的移民軌跡是從裏下河到長江,好像從毛細血管來到動脈裏。我在這個動脈裏回望我的故鄉。也正是這樣的回望,讓我獲得了一種間離的力量,或者是敘述的力量,我的很多作品幾乎都是在靖江完成的,但是寫的都是興化,我的如胎衣一般的興化。但肯定不是鄉愁,說鄉愁太矯情了,因為兩地直線距離只有120公裏。
陳倉: 我看到相關資料,你從揚州師範學院(現為揚州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興化沙溝鎮的一個鄉村學校教書,在那裏一待就是15年。你能不能講講那是一段什麽樣的歲月? 這段經歷對此後的文學創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龐余亮: 1985年,師範畢業的我來到江蘇興化的水鄉深處,成為了一名鄉村教師。當時我18歲,身高1.62公尺,體重44公斤,長著一副娃娃臉,被學生和家長稱為「小先生」。在鄉村學校,每一種生活都是在重復。鄉村的日子尤其緩慢,但在這緩慢而寂靜的生活裏,也有著其他生活所沒有的驚喜。安靜讀書,安靜創作,嚴格地對自己進行文學訓練。我訓練自己寫詩,寫童話,寫小說。23歲時,我的一篇非常幼稚的小說收到了一位編輯也是作家的來信鼓勵,他寫了整整兩頁紙,他說我有文學才華,必須堅持寫下去。這位作家叫鮑光滿。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作家來信,對我鼓勵太大了。說實話,沒有那15年寂寞鄉村生活中的文學自我訓練,肯定沒有【小先生】,也肯定沒有作為作家的我。
陳倉: 你的文學創作算是從那時正式開始的嗎? 那你還記得第一次發表的作品嗎? 你最近一次發表的作品是什麽? 幾十年過去了,你對比一下,變與不變的是什麽?
龐余亮: 我的文學創作應該從1986年算起。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是在1987年春天,【揚州日報】「梅嶺」文學副刊發了我一組詩,叫【拔節的季節】。那天我正好20歲。到了1988年,我的詩歌就先後在【詩刊】【解放軍文藝】【青年文學】等刊大量發表了。那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有本【青年詩選】,我的詩被選入了第二輯,海子、駱一禾和汪國真也是那一輯的。最近一次發表作品應該是【飛天】第8期上的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叫做【明天醒來我在哪一只鞋子裏】,恰恰就寫了詩人的故事和命運。幾十年過去了,我發現我最愛的還是詩歌,在鄉村學校15年寂寞生活中,熊熊燃燒過的詩歌。

2
獲得魯獎以後,我和過去一樣
「潛伏」在小縣城,照常生活,繼續寫作。
陳 倉: 說到這裏,我們得談談【小先生】了。【小先生】取材於那段鄉村教師經歷,據說是從煤油燈下開始的。【小先生】為什麽遲到了幾十年? 你講一講其中的幕後故事和創作花絮吧。
龐余亮: 【小先生】的起點在煤油燈下,我記下了【一個生字】。那是學生們的第一個故事。那時的我,剛學會像老先生那樣,一邊在煤油燈下改作業,一邊吊起一只鋁飯盒,利用煤油燈罩上方的溫度煮雞蛋呢。我想起了白天犯下的錯,有個學生問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說說,這個字怎麽讀?」我真的不認識那個字。我的喉嚨裏仿佛就堵著那顆不好意思的雞蛋,緊張、惶恐、心虛。我有個優點,知錯就改,不想第二次犯下同樣的錯誤,於是開始記錄學生們的故事,慢慢素材就多了起來。最初的目的不明顯,但覺得記下來會有用。
15年之後,我離開了鄉村學校,去了靖江電視台做法制節目的編導,完全不同於鄉村教師的生活。但我心中一直沒放下那些記在備課筆記背後的故事,於是,一邊拍案件故事,一邊開始整理【小先生】。【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萬字,第一稿有28萬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覺得不滿意,繼續修改。我的修改時間變得漫長起來,前後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從28萬字變成了現在的12萬字。
陳倉: 【小先生】獲得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大家談論得比較多了。像小說一樣,得從現實故事結束的地方開始寫,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小先生】裏的人和事都有原型,這麽多年過去了,你有沒有跟蹤過【小先生】裏的學生、老校長、總務主任等人? 這些人的現狀如何?
龐余亮: 學生都像敏督利一樣被命運吹散到各地了。比如我做老師的第一個小班長,他看到了【小先生】,他說他記得我的故事是:一個人躲在宿舍裏焚燒詩稿。天吶,這個故事肯定是真實的,但我卻忘記了。他們大部份都到城市裏謀生了,一部份在縣城,一部份在揚州。前幾年,揚州的學生還集體請我吃了一次燒烤,那個喝多了的夜晚特別難忘,我們不像是師生,而像是多年未見的兄弟。
我的年輕同事也是有故事的,比如那個教會我踢足球的同事就很有毅力。我們常常相互鼓勵,他在悄悄復習考研,我在悄悄寫作。後來,他在第二次考研的時候考取了一所財經類學校,如今在省級機關工作,非常優秀。有幾次我們見面,談得最多的還是我們的鄉下足球,苦中作樂的鄉下足球。我們都沒有辜負鄉村學校的寂寞時光。
【小先生】中的老校長已快90歲了,上次國慶,長大的學生要搞一個活動,把我請過去了,也請了老校長。每個人都穿上了統一的T恤。他見到我劈頭就問:聽說你把我寫到文章裏了? 我嚇了一跳,不知道說什麽好。後來他也沒說什麽。看到他笑呵呵的樣子,估計活到100歲沒問題。
【小先生】中的總務主任是個非常可愛的老頭。因為子女多,所以他生活非常節儉。他中山裝的四個口袋裏永遠有四種煙,那是禮敬不同人的,他自己只抽最差的煙。後來因為心血管病去世了,每次記起他,就想到了他那既狡黠又和善的笑容。
陳倉: 第二個問題是,【小先生】獲獎已經整整一年,「小先生」這一年過得怎麽樣? 有什麽比較大的改變嗎? 從昔日的鄉村教師,到如今的著名作家,這中間可以說變化巨大,也說明付出的太多,你有什麽需要和朋友們分享的嗎?
龐余亮: 去北京領獎,像一個長長的夢。從北京歸來,我回到了我的縣城。夢就一下子醒過來了,因為在縣城生活中文學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著名」這個詞一點也不存在。我還是像過去那樣,白天步行30分鐘上班,晚上繼續步行30分鐘回家,然後讀書寫作。第二天繼續如此,兩個30分鐘,微信的步數正好超過了10000步。我已經56歲了,寫作已35年了。我必須清醒。
陳倉: 我們還是趕緊來談談你的新作吧。在今年3月份,你推出了散文集【小蟲子】。為什麽要以【小先生】【小蟲子】作為書名?以「小」命名的文學作品很多,最早是張愛玲的【小團圓】。你怎麽理解文學中的這個「小」字?
龐余亮: 「小」是我的生命常態。我是父母的第10個孩子,也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從6歲上村小開始,就註定與「小」密不可分。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個子最小的學生。全班排隊我註定排第一個,座位也是最前排的。師範畢業後到了鄉村學校,又是最「小」的老師,年齡小(18歲),個子小(1.62公尺),體重小(44公斤)。「小」讓別人和學生看我的眼光不一樣,「小」也讓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樣。「小」讓我仰望世界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我俯視世界的時間。
陳倉: 魯迅文學獎的頒獎辭說,「【小先生】接續現代以來賢善與性靈的文脈,是一座愛與美的紙上課堂和操場。」【小蟲子】和【小先生】之間有血緣關系嗎?你能否結合兩部作品,談談「賢善和性靈」算不算其中的DNA?
龐余亮: 【小蟲子】的寫作時間是2022年春天,當時被困在了家裏,我一下子有了整塊的時間,開始寫作我一直想寫的童年生活:【小蟲子】。【小先生】中有「賢善和性靈」,【小蟲子】裏有「賢善和性靈」的種子。很多這樣的種子,就在我的童年裏閃爍。這就是寫作對於我的獎勵,追溯和審視自己,在追溯和審視的過程中逐漸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命運。
陳倉: 【小蟲子】被譽為中國版的【昆蟲記】,你介紹一下你所寫的蟲子吧。據說其中還有一些上海的記憶,這是怎麽回事?【昆蟲記】的作者同時是一位昆蟲學家,你關於昆蟲方面的知識是怎麽獲得的? 你的【小蟲子】和【昆蟲記】有什麽不一樣呢? 遇到了寫作困難嗎?
龐余亮: 按照人生的閱歷,【小蟲子】遠遠在【小先生】之前。之所以一直沒有寫作【小蟲子】,是因為我實在無法放下【小先生】,18歲到33歲的鄉村教師的我,那才是我人生最黃金的歲月,也是我生命中最明亮的歲月。處理好最明亮的部份,我的目光這才回到我生命中最幽暗的部份:童年。我剛說了,我是父母的第10個孩子,我出生的時候,父母都快成為爺爺和奶奶了。在多子女的貧困家庭裏,我是被忽略的那個,我最好的玩伴,就是那些飛來飛去的小蟲子。白天和黑夜裏,全是那些奇怪的好玩的小蟲子:瓢蟲、蜜蜂、螞蟻、米象、蜻蜓、天牛、屎殼郎、螞蚱、螞蟥、尺蠖、袋蛾、麗綠刺蛾……到了冬天,大自然裏的小蟲子蟄伏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世代,和我做伴的還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
可以這麽說,小蟲子和我,那是我孤寂童年的全部。其中「禍起西瓜瓢蟲」和「蝴蝶草帽」這兩章故事裏全是童年和上海的故事,主要是因為蘇北人都有一個骨子裏的上海崇拜情結,這情結影響了大人,也影響了我們小孩。這本【小蟲子】,我集中寫了我能夠寫出來的40多種小蟲子,其實,和我相處的小蟲子遠遠不止這些,很多小蟲子還在我生命的更為幽暗處呢。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不準備寫科普或者研究類別,因為我不會。一個作家不能為難自己。我要寫出陪伴的饑餓和孤單童年的那些小蟲子,把小蟲子當成我的食物,當成我的敵人,當成我的朋友。
寫作【小蟲子】的困難是敘述視角,為了尋找到【小蟲子】裏的第三人稱敘述視角,我找了將近半年時間,創作過程一再被自己推翻。一開始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寫得很不舒服,我與文本裏的那個童年的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人了,有時候表達起來,會產生一種不知道是現在的自己在表達,還是過去那個童年的自己在表達。後來我改成第二人稱,還是不對勁。有一天我對自己說,何不用第三人稱呢? 果然,第三人稱讓我感受到了敘述和表達的自由,能進去,還能出來。這也是【小蟲子】中段落特別短,很多一句一段的原因所在,通道寬敞,進出自由。這樣的敘述視角得到了很多表揚。
陳倉: 趙麗宏評價【小先生】時,用了「幽默、清澈、純真」幾個詞。陸梅評價【小蟲子】時說,書裏的母愛與成長,像一對閃閃發光的翅膀,帶動了「小蟲子」的起飛和翺翔。你的作品似乎特別適合學生閱讀,請問你是用兒童文學的心態來寫作的嗎? 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有沒有一個結合點?
龐余亮: 謝謝! 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的結合點是「成長和愛」。比如【小先生】中,我想表達的是好老師是和學生一起成長的。這就是【小先生】最想傳遞給讀者的。15年,我真的和我的學生一起成長起來了。在【小蟲子】的開頭,我特別寫上了一行題記:「獻給/那些總被認為無用的孩子們/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會飛」。【小蟲子】的寫作也給了我奇跡,因為我重新發現了恩情和愛,還有成長。那是我多年忽略的童年寶藏。小蟲子會飛,那些被認為無用的孩子,其實也在蓬勃成長呢。我寫尺蠖和飛雞的故事,當母親和老害按住那只叫老蘆的母雞,把母雞能飛的翅膀剪掉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從寫尺蠖寫到了廣闊的童年,有對於父親母親的感恩,還有對於成長和生活的理解。在成長和愛中,【小先生】的師生合二為一。同樣,有了成長和愛,小蟲子和我也合二為一。

3
碎 片化 輕松化的閱讀是沒有營養的,長期下去我們的靈魂就會營養不良。
陳倉: 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兒童文學需要淺顯一些,所以要求相對低一些。但是我感覺,你的文字並不簡單。你能否舉例說明一下,你是怎麽保持足夠的文學性和思想性的? 輕松閱讀和思想性之間是什麽關系?
龐余亮: 我很不喜歡「淺顯」這個詞。兒童文學的要求比成人文學的要求更高。必須沈澱,必須回到原點,必須坦白。比如【小蟲子】裏的疼痛感,其實是所有孩子都會有的感覺。童年和童年的疼痛,還有在疼痛中的成長,就是作家很重要的創作源泉。很多書寫童年記憶的散文,沒有成長的痕跡,也就沒有對成長的呈現。寫成長特別難,必須把你的心剝開。你只寫表面的溫暖和甜蜜,而不寫陰影的部份,是不可以的,那肯定不真實。哪個人的成長過程沒有陰影? 誰的成長過程沒有疼痛?重要的是,原生家庭的陰影和疼痛是和愛混合在一起的,我就是想用【小蟲子】,既寫出童年的清澈,也寫出清澈下面的渾濁。
陳倉: 擠暖暖、踢鍵子、溜草垛、跳繩、「架雞」等遊戲節目,煤油燈、紙飛機、長辮子、泥操場等校園場景,還有輟學、重男輕女等社會問題,勾起了一代人的回憶。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東西已經消失了,年輕的讀者,尤其是現在的學生,根本不熟悉那個年代的校園生活,你的文學作品卻依然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你能否說說,你的作品中永不過時的東西是什麽? 文學作品的價值在於高出現實,你認為高出現實的那一部份是指什麽?
龐余亮: 有兩本書,改變了我的文學趣味,一本是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讓我學會了如何調整自己的生命重心。還有範用先生,他的【我愛穆源】讓我學會了愛,如何追溯生命中最清澈的源頭。有了這樣的底色,【小先生】的每篇文字都有了參考標準。還有,我的寫作潛意識裏有一個自我評定,「白紙黑字」的文章,無論長短,都需要作為一個藝術品,不能輕易放過自己。我文學生涯開始是詩歌寫作和童話寫作,所以【小先生】裏有詩歌,有童話,也許,這就是高於現實的那部份。
陳倉: 我最早讀到你的作品是詩歌,你曾經是一個很優秀的詩人,參加過【詩刊】社第十八屆青春詩會,後來為什麽要換頻道? 寫詩、寫童話、寫小說、寫散文,你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一種文體? 我看到你最新的簡歷裏,列出了你的小說和散文,卻沒有列出你的詩集,是要淡化詩人身份還是要和詩人的身份告別?
龐余亮: 詩歌溢位來的部份,就是散文和小說。在所有的文體中,我最喜愛的是詩歌。它是我的初戀,我偏執的愛。今年我還出了一本新詩集呢,叫【五種疲倦】,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做個廣告,這是我所出的詩集中,自己最偏愛的一本。
陳倉: 詩人的經歷對你的其他文體創作有沒有影響? 其實,很多著名作家都有寫詩的經歷,比如莫言、賈平凹、張煒、阿來、畢飛宇,而且他們現在似乎還在寫詩,你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龐余亮: 有過詩歌寫作史的作家,就像被閃電照亮過的田野。被閃電照亮過的田野和沒有被閃電照亮的田野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就是詩歌的恩情。從很多大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詩歌的恩情。
陳倉: 靖江的語言屬於吳語,現在是普通話時代,大家從小都學普通話,平時又都說著普通話,作家大多數都是用普通話寫作。你結合自己的實踐,談談這方面的問題吧。
龐余亮: 我在寫作的時候是用普通話,但在敘述一些特別名詞的時候,會用方言。比如【小先生】中有,【小蟲子】中也有。但困難的是,有些方言實在不好寫出來,只好寫成了普通話的表述,比如【小蟲子】中有個「袋蛾」,我們家鄉不叫「袋蛾」,叫「吊死鬼」。這是我的困境。為了更好地表達,還是采用了「袋蛾」。
陳倉: 這麽多年,你的創作量很大,優秀作品不斷,獲得了眾多文學獎項。如果讓你挑選一部(篇)作品,留給一百年後的讀者,你會挑選哪一部(篇)?
龐余亮: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一個厚臉皮。如果厚著臉皮回答的話,我覺得是下一部。請讓我繼續厚著臉皮介紹我的新書:【小糊塗】。【小糊塗】是【小先生】三部曲中的最後一「小」,還是寫我的童年、我和泥土和饑餓的故事。我寫得更從容,更接近了我的文學理想。
陳倉: 現在的年輕人都沈迷於網路,樂於碎片化的輕松的閱讀,而你的作品讓人讀了以後,心靈會得以寧靜。你覺得讀書對年輕人有何意義?
龐余亮: 碎片化輕松化的閱讀,是沒有營養的閱讀,長期下去,我們的靈魂就會營養不良。以我為例,我的童年很孤苦,因為我的家庭和出身。但我很感謝我遇到過的一本本書,是一本又一本書拯救了我。如果沒有一本本書,我不知道我會成為什麽。在讀書的過程中,我慢慢理解了我的童年,包括我脾氣不好的父親。因為好書給了我向上向前的能量。
陳倉: 除了寫作,你業余生活中還有其他的興趣愛好嗎?
龐余亮: 我的業余生活除了讀書,還有打桌球。相信嗎?很多正規軍都會敗在我的球拍下。為什麽呢? 我的桌球是自 學的,屬於標準的「歪把子機槍」。千萬不要用桌球比賽規則來衡量我、規範我,那樣的話我就絕對屬於違反規則的打法。好在我的球友和我打球的時候,總是「視而不見」,總是「熟視無睹」,這樣,我的「歪把子機槍」就發揮神奇作用了。



全文刊於【青年報.生活周刊】 2023年11月12日02-03版 「上海訪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