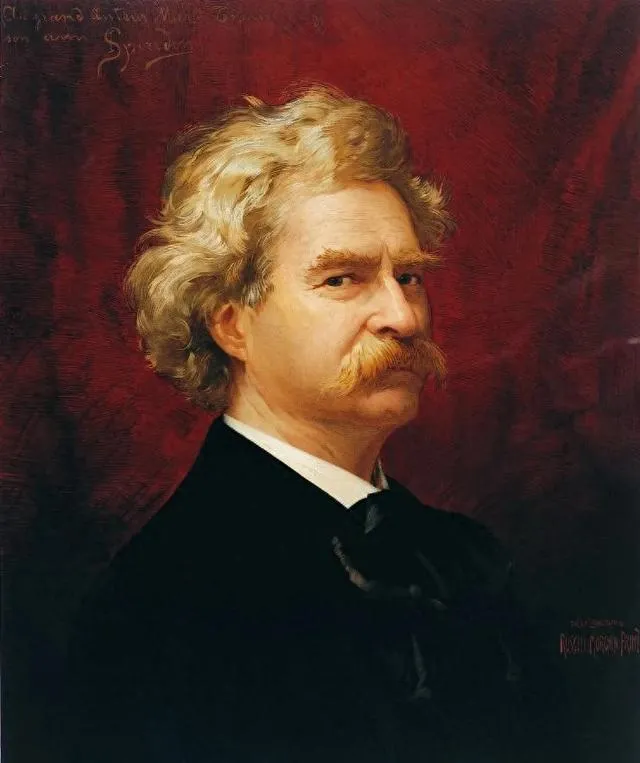
頭幾天裏,我們都感到心滿意足,只顧欣賞那蔚藍的盧塞恩湖[1],以及它四周層巒疊嶂、白雪皚皚的群山——尤其是那些山叫你看了心醉神馳,因為,當太陽燦爛地照射著雄偉的積雪峰頂,或者當月光輕柔地環繞著它時,呈現出的那一片景色確是稀有罕見、美麗迷人的——但是最後我們決意再要乘上輪船,去四下稍微遊覽一番,然後捷足先登裏吉山[2]。好極了,那天風和日暖,我們的弗呂倫[3]之遊快樂極了。所有的人都坐在甲板帆布篷下面的板凳上;所有的人都有說有笑,一面贊賞那美妙的景色;在那片湖上泛舟,真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樂事。群山展現出永無止境的奇觀。有時候它們從湖水中突地湧現,屹然高聳,那龐大的形體最為氣勢磅礴地遮蔽著我們那艘渺小的汽輪。這些山並不是積雪的峻嶺,然而它們向天空攀升,高接蒼靄,頂峰都被浮雲掩蔽著。它們不是荒蕪不毛的,形狀醜惡的,而是全部籠罩著青翠,看上去是那麽寧靜,那麽幽雅宜人。而且,有時候它們幾乎是崛起突落,你簡直沒法想象一個人怎麽能在那樣的斜坡上站穩了。然而,山上有路徑,瑞士人每天都上上下下地走著。
有時候,這樣一重險怪的崖壁,好像船塢中巨大的船庫那樣微傾著——但接著它又向天空繼續上升,像法國式的復折屋頂[4]那樣構成稍陡一些的傾斜角度——你還可以看到,令人頭暈目眩的復折屋頂上築有一些像燕子窠的小東西,而且你很快就可以看出,原來它們是一些農民的住屋——可不是,這些人都在縹緲淩空的地方住家。要是一個農民在睡夢中起來行走,或者他的孩子從前面院子裏翻了出去呢——那樣,要找到遇難者的殘骸,他們的朋友就得從高入雲霄的地方下降,走上多麽長一段愁悶人的路程啊。然而,那些遠在天際的人家看來卻是那麽吸引著人,它們遠離開這個紛紜騷擾的人世間,沈睡在那種寧靜和迷夢般的氣氛裏——毫無疑問,一個人只要學會了在那上面住家,他是再也不肯到一個更卑低的地方去生活了。
在這些巨大的綠色屏障當中,我們迅速地駛過了湖邊那些極富雅趣的曲折的港汊,沿途欣賞著前所未見的美麗景色。它好像一卷氣勢宏偉的圖畫,在我們前面展開,然後又在我們後面合攏;我們時不時感到一陣興奮和驚奇,因為我們會突然臨近一座像容弗勞[5]那樣崔嵬的白色巨巖,它在遠處傲然兀立,又像一個形狀與它類似的巨人,他在較低的艾爾卑斯山崩塌下來的亂石上露出了頭和肩部。
有一次,我正在貪婪地吸收這些奇妙的景色,竭力要盡可能趁它們沒消失之前看個痛快,這時候一個年輕人怡然自得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凝思遐想:
「我想,您是一個美國人吧——我也是的呀。」
他年紀大約是十八歲,也可能是十九歲;細瘦個子,中等身材;一張臉在坦率中透出愉快;眼睛靈活,但顯得有些任性;獅子鼻好像是靦腆地羞縮在下邊新長出的柔軟胡髭當中,正等待人家引導它出來;下巴頦兒松泛地搭拉著,似乎這樣才可以在骨頭框子裏靈便地活動。他戴的是一頂低筒狹邊草帽,帽筒上箍著一道寬闊的藍色緞帶,緞帶前面繡著一個白色船錨;穿的是華麗的短垂尾上裝,褲子,坎肩:一切都是那麽精致整齊,合乎款式;底下是紅條紋的長襪,後幫極低、用黑絲帶系著的漆皮鞋;脖子上圍著藍色緞帶,敞開著領子;襯衫胸前是細粒的鉆石飾紐;小羊皮手套上沒一絲皺紋;袖口向外突出,上面是一顆發了黑的銀袖紐,紐子上制有狗臉(英國的巴兒狗)圖形。他手裏握著一根細手杖,杖端是一個鑲著紅玻璃眼珠的英國巴兒狗頭;臂下夾著一本德文語法——【奧托氏語法】。他留著短發,頭發是直的,但是梳得很光;後來,他剛轉過頭去,我就看到他後面的頭發是很仔細地分開梳的。他從一只精致的盒子裏取出一支香煙,從隨身帶的摩洛哥的皮套裏取出一只海泡石煙嘴,把煙裝在煙嘴裏,然後伸過手來取我的雪茄。於是,趁他借火的時候我回說:
「是的——我是美國人。」
「我就知道您是的——我一看就知道了。您這次來,乘的是什麽船呀?」
「‘霍爾薩奇亞’號。」
「您瞧,我們乘的是孔納德公司的‘巴塔維亞’號。您這次航海,情形怎麽樣呀?」
「風浪很大。」
「我們也是。船長說他幾乎從來沒遇到比那更大的風浪。您是打哪兒來的?」
「新英格蘭[6]。」
「我也是。我是打新布魯菲爾德來的。有誰跟您一起來嗎?」
「有——一個朋友。」
「我一家人都跟著來了。一個人出外旅行,時間過得太慢了——您說對嗎?」
「稍微慢一點兒。」
「這兒以前來過嗎?」
「來過。」
「我可沒來過。來這兒還是第一次。可是其他的地方我們都去過了——巴黎和所有的地方。我明年要進哈佛。現在一直在學德語。要學會了德語才能入學。法語我可懂得不少——在巴黎,或者在任何其他說法語的地方,我都能跟人家很好地交談。您現在住的是什麽旅館?」
「施魏策爾霍夫。」
「這不可能嘛!真的嗎?我從來沒在會客室裏看到您。我老是去會客室,因為那兒有很多美國人。我跟許多人交了朋友。我只要看見一個美國人,就很快認識了他——於是我就跟他交談,就跟他交上了朋友。我老是喜歡跟人家交朋友——您也是這樣吧?」
「咳,是呀!」
「您瞧,它可以使這樣的旅行得到調劑,再好也沒有啦。只要我能跟一些人交朋友,可以跟一些人聊聊天,我就不會在這樣旅行的時候感到沈悶了。可是,如果是不能交幾個朋友,在這樣旅行的時候跟他們談談說說,我相信這樣的旅行可太沈悶啦。我愛聊天,您也是吧?」
「是。」
「這次旅行的時候,您可曾感到沈悶嗎?」
「不是所有的時候,只是有的時候。」
「這話對!——瞧,您必須四處兜兜,交一些朋友,要說說聊聊呀。我就是這樣。我永遠采取這個辦法——我只管到處溜達,溜達,溜達,老是談話,談話,談話——我從來不會感到沈悶。您去過裏吉山嗎?」
「沒有。」
「準備去嗎?」
「大概要去的。」
「您準備住哪家旅館?」
「我還不知道。有幾家旅館嗎?」
「有三家。您可以住施賴貝爾——您會發現那兒都是美國人。您說您是乘什麽船來的?」
「‘安特衛普市’號。」
「我想,那是一條德國船。您準備去日內瓦嗎?」
「去。」
「您準備住哪家旅館?」
「日內瓦金幣旅館。」
「您可別住那家旅館呀!那兒沒美國人!您最好還是住橋那面的一家大旅館——那些旅館裏擠滿了美國人。」
「但是我要練習我的阿拉伯語。」
「天哪,您會說阿拉伯語?」
「會——可以跟人家很好地交談。」
「咳,去他的吧,在日內瓦您就沒法跟人家交談——他們可不說阿拉伯語,他們說法語。您在這兒住的是哪家旅館?」
「妙景灘公寓旅館。」
「咳,您該住施魏策爾霍夫呀。難道您不知道施魏策爾霍夫是瑞士最考究的旅館嗎——查一查您的貝戴克[7]吧。」
「這個,我知道——可是我原來以為那兒沒有美國人。」
「沒有美國人!咳,我的天,那兒的美國人可熱鬧極啦!我幾乎總是待在那間大會客室裏。我在那兒認識了許多人。現在他們已經沒我剛去住的時候那麽多了,因為,現在那兒住的都是一些新來的了——其他的人一住過就走了。您是打哪兒來的?」
「阿肯色。」
「是嗎?我是打新英格蘭來的——新布魯菲爾德是我在國內住的那個市鎮。我今天高興極了,您呢?」
「美極了。」
「我就是這樣說嘛。我喜歡這樣到處溜達,自由自在的,又可以認識一些朋友,又可以跟他們閑聊。我只要一看見一個美國人,很快就認出了他;於是我就過去跟他攀談,和他成了相識。只要能結識一些新朋友,跟他們聊天,這樣旅行的時候我就從來不會感到沈悶。我真喜歡聊天,只要我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您呢。」
「我覺得它比任何其他消遣都更好。」
「我也是這樣想法嘛。瞧,有的人喜歡拿一本書坐下來讀,一直讀下去,要不就是呆呆地四面望,對著那片湖水或者這些山呀什麽的大聲兒嚷嚷,我可不那樣;不,先生,如果他們喜歡,就讓他們那樣吧,我並不反對;可是,對我來說,我就是喜歡談話。您去過裏吉山了嗎?」
「去過。」
「您住的是什麽旅館?」
「施賴貝爾。」
「就數那地方好!——我也在那兒住過。那兒都是美國人,對嗎?永遠是那樣——永遠是的。一般人都是這樣說。所有的人都是這樣說。您這次來乘的是什麽船?」
「‘巴黎市’號。」
「我想,那是一條法國船吧。這次航海,情形……恕我走開一會兒,來了幾個我沒見過的美國人。」
他二話沒說就走了。再說,他走的時候倒沒受到傷害——原來我已動了殺機,很想把我那根登山杖像根魚叉那樣在他背上紮進去,但是,我剛舉起武器,這個念頭就隨之消失;我覺得很不忍心殺他。瞧他是這樣一個快樂的、天真的、忠厚的傻瓜。
半小時後,我坐在一條板凳上,懷著極大的興趣,仔細鑒賞我們的船在它旁邊掠過的一座巋然傲立的巨巖(孤零零的巖石未經人工斧鑿,而是在大自然高超不凡的、出神入化的擘畫下形成的),一座雄偉的金字塔形巨巖,它有八十英尺高,大自然在億萬年前設計,準備以後給那些有資格享受它的人用作紀念碑。時間終於到來,如今這座莊嚴威武的紀念碑上面已用大字鑿出了席勒的名字。這一雕鑿,說也奇怪,一點兒也沒貶低這座巖石的價值,或者汙損它的本來面目。據說,兩年前曾經來了一個外地人,他用繩索和滑車把自己從巖頂上吊下,在那上面添滿了比席勒名字更大的藍顏色的字,那些字是:
請用蘇汝痛;
請購太陽牌爐漆;
黑爾姆博德氏布枯[8];
降血壓請服本乍靈。
他被捉住了,最後查明他是一個美國人。法官審判的時候對他說:
「你來自一個國家,那裏任何一個狂人,為了要把一枚骯臟的錢幣裝進口袋,都享有特權褻瀆侮慢大自然,從而褻瀆侮慢大自然的上帝。不過,本案的情節有所不同。由於你是一個外國人,又是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所以我從輕發落;如果你是一個本地人,那我可要嚴厲地處罰你。現在,聽我的吩咐:你必須立刻從席勒紀念碑上擦幹凈你那罪行留下的一切墨點;你要付清一萬法郎罰款;你要坐兩年牢,而且要服苦役;刑滿後,我們要抽你一頓鞭子。給你全身塗滿柏油,粘上羽毛,割了耳朵,讓你騎在一根木棍上,把你擡到本州的邊界,然後把你永遠驅逐出境。這次審理你的案件,免於判處你最嚴厲的懲罰——這並不是對你個人開恩,而是給那個偉大的共和國留一點兒面子,她不幸生出了像你這樣的敗類。」
輪船上的板凳是背對背一溜兒排列在甲板上的。我後面的頭發無意中觸到了兩位女士後面的頭發。不一會兒,一個人過來跟她們搭訕,我聽到以下的談話:
「我想,你們是美國人吧?我也是呀。」
「是的——我們是美國人。」
「我就知道你們是——我一看就能知道。你們這次來,乘的是什麽船呀?」
「‘切斯特市’號。」
「哦,是啦——那是英曼航運公司的船。瞧,我們乘的是孔納德公司的‘巴塔維亞’號。你們這次航海,情形怎麽樣?」
「一路風平浪靜。」
「這可是運氣。我們遇到的風浪可大極了。船長說他幾乎從來沒遇到比那更大的風浪。你們是打哪兒來的?」
「紐澤西州。」
「我也是呀。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說打新英格蘭來的。新布魯菲爾德是我的老家。這幾個是你們的孩子嗎?是你們二位的孩子嗎?」
「是我一個人的;都是我的孩子;我這位朋友沒結婚。」
「我想,是獨身吧?我也是。僅你們二位女士一同旅行嗎?」
「不——還有我丈夫一起。」
「我們一家人都跟著來了。一個人出來玩,時間過得太慢了,您說對嗎?」
「我想肯定是的。」
「瞧那兒,彼拉蒂斯山又出現了。瞧,它是以龐修斯·彼拉多[9]命名的,那家夥把一個蘋果從威廉·退爾[10]的腦袋上射了下來。人家都說,旅遊指南裏詳細地談到了這一掌故。我可沒去讀它——那是一個美國人告訴我的。我才不去讀什麽書哩,在這種時候還是到處溜達快活。你們看到威廉·退爾當年講道的小教堂了嗎?」
「我不知道他還在那兒講過道。」
「哦,可不是,他講過。是那個美國人告訴我的。他呀,從來不合上那本旅遊指南。有關這片湖的掌故,他比湖裏的魚知道的更多。再說,人家都管它叫‘特爾的小教堂’——這您總該知道。您以前來過這兒嗎?」
「來過。」
「我沒來過。來這兒還是第一次。可是,其他的地方我們都去過了——巴黎和所有的地方。我明年要進哈佛。現在一直在學習德語。要學會了德語才能入學,這本書是【奧托氏語法】。它是一本刮刮叫的好書,能叫你學會我已經有了,有他[11]。可是,在這樣到處溜達的時候,我才不去認真地學習它哩。只有心血來潮的時候,我才把我那些小寶貝兒很快地溫習一遍:我已經有了,你已經有了,他已經有了,我們已經有了,他們已經有了。[12]您瞧,那樣兒有點兒像在唱‘現在——我——要——躺下就寢’[13],此後,我可能接連著三天不去理它一下。它太叫人傷腦筋啦,我的意思是說那些德語;你必須少量地吸收它,否則呀,瞧你的腦子會一下子都混攪在一起,你只覺得它們在你腦殼裏亂得一團糟,好像許多奶油和面粉揉在了一起。可是,法語就不同了;學法語算得了什麽。我可不怕說法語,就像流浪漢不怕吃餡兒餅一樣;我能咭咭呱呱一口氣把我那些小玩意兒都說下去:我有,你有,他有[14],以及後面的那一套,就跟說a-b-c一樣容易。我在巴黎,或者在任何其他說法語的地方,都能跟人家很好地交談。你們住的是哪家旅館?」
「施魏策爾霍夫。」
「這不可能嘛!是真的嗎?我在那間大會客室裏從來沒看到你們。我老是去會客室,因為那兒有很多美國人。我和許多人交朋友。你們去過裏吉山了嗎?」
「沒去過。」
「準備去嗎?」
「我們打算去。」
「你們準備住哪家旅館?」
「這個我還不知道。」
「啊,那麽你們就去住施賴貝爾吧——那兒滿都是美國人。你們是乘什麽船來的?」
「‘切斯特市’號。」
「啊,對了,記得剛才我已經問過您了。瞧我老是問人家乘哪條船,所以有時候就會忘了,又去問他第二遍。你們準備去日內瓦嗎?」
「準備去的。」
「你們打算住什麽旅館?」
「我們想住公寓。」
「我簡直不能相信,你們會喜歡住公寓;很少美國人住公寓。你們到了這兒,住的是哪家旅館?」
「施魏策爾霍夫。」
「哦,對了,這個剛才我也問過你們了。瞧,我老是問人家住哪家旅館,所以我的腦子都被旅館給攪糊塗了。可是,這樣才可以找話談呀,我就是愛談話。談話能使人精神爽快——您也是吧——在這樣旅行的時候?」
「是的——有時候是的。」
「啊呀,我也是的呀。只要是有話談,我無論如何不會感到沈悶——您也是這樣吧?」
「是的——一般如此。但也有例外。」
「哦,當然啰。我就不高興跟每一個人都談話。如果他開始嘮叨個沒完,談什麽風景呀,歷史呀,繪畫呀,以及諸如此類的討厭的話題,我很快就會感到不耐煩。我會說:‘哎呀,現在我可得走了——希望以後再見。’——接著我就去散步了。你們是打哪兒來的?」
「紐澤西州。」
「哎呀,真恨死人啦,這個我剛才也問過你們了。你們看過盧塞恩的獅子嗎?」
「還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可是那個告訴我彼拉蒂斯山的人說,它是值得一看的,它有二十八英尺長。聽來這好像不太可能,但是,不管怎樣吧,反正他是那樣說的。他是昨兒去看的,說它已經奄奄一息,所以我恐怕它這會兒已經死了。可是,這沒關系,它肯定要被制成標本的。您說這幾個孩子是您的……還是她的?」
「是我的。」
「哦,您已經說過了。您準備上……哦,這個我已經問過了。哪一條船……哦,這個我也問過了。你們住的是什麽旅館……哦,這個我問過您了。讓我想一想……嗯……嗯……這個,我想,要說的就是這些了。再見[15]……我認識二位非常高興,女士們再見[16]。」
一八八〇年
* * *
[1] 盧塞恩湖在瑞士北部,海拔一千四百余英尺,以風景奇麗著稱。
[2] 裏吉山在盧塞恩湖邊。
[3] 弗呂倫:鎮名,在盧塞恩湖東南隅。
[4] 又稱「重斜屋頂」,屋頂二層疊接,有著兩層不同的傾斜角度。
[5] 艾爾卑斯山的高峰,高達一萬三千六百余英尺。
[6] 美國東北六州的統稱,包括緬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夏州,麻薩諸塞州,羅德島州和康乃狄克州。
[7] 指德國出版商卡爾·貝戴克(1801—1859)所發行的各種旅遊指南。
[8] 布枯是一種南非產的灌木葉,可以入藥。
[9] 龐修斯·彼拉多:古代羅馬的猶太總督,他讓猶太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
[10] 威廉·退爾:十三世紀末瑞士愛國者,曾領導人民反抗奧地利的統治,相傳暴君格斯勒命令他射親生兒子頂在頭上的蘋果。
[11] 原文為德文,句子不通,意在諷刺說話人無知又要表現。
[12] 原文為德文。
[13] 「現在我要躺下就寢,
求主保佑我的靈魂;
如果我竟然長眠不起,
求主將我的靈魂接去。」
這是基督教兒童臨睡前唱的一首祈禱歌,兒童為了「完成任務」,往往機械地、迅速地、漫不經心地唱一遍。
[14] 原文為德文。
[15] 原文為德文。
[16] 原文為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