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倫理規則構造的世界。社會的倫理隨時隨地在判斷和裁決人們的行為: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什麽是道德的,什麽是不義的,什麽是善的,什麽是惡的……凡此種種,都在倫理的範疇之內。一方面,我們在接受倫理,如學習、內化,另一方面,我們也拿著它們去評判周圍的人和事。
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人類活動。因為年代的變化,倫理被作了「舊倫理」與「新倫理」的區分,彼時的舊倫理可能變為此時的新倫理,反之亦然。由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掀起的關於愛情、關於酒神、關於性別的諸多爭議,又何嘗不是一場有關倫理的碰撞?

【瘋狂原始人】(The Croods,2013)畫面。
多年來致力於倫理研究的哲學者菲利普·基切爾就認為,倫理不是一個最終的系統——盡管我們每個人會認為自己所接受的倫理是最終的、不會再變的規則——而是一個始終處於過程中的人類計畫。即便是沈浸在網路資訊世界「無所不知」的現代人也還是會為彼此的倫理標準爭執不休。
這是由初民社會開啟的倫理計畫。當我們去看他們的倫理,或許又多了許多困惑。以食物分配為例,把有限的食物平均分給部落每個人還是按需求或按勞動貢獻分配?每一種做法都有其道理。今天的人甚至可以猜想,初民們嘗試了各種各樣的分配方法。為什麽現代人熟悉的似乎只有一種呢?比如沒有高低貴賤的平均分配。也許在如此之多的規則中,只有一種成功維系了聚落的規模。繁衍的成功使他們采用的倫理規則被繼承了下來。這是基切爾提及的一種猜想。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新書【前進演化與倫理生活】相關章節。
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英]菲利普·基切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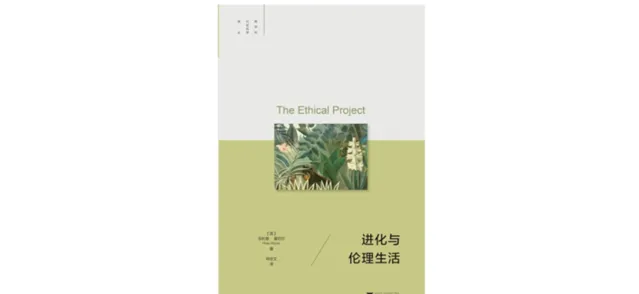
【前進演化與倫理生活】,[英]菲利普·基切爾著,鐘世文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4年6月。
從彼到此
在倫理計劃剛開始時,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群體中,所有的成年成員都能夠參加討論,而在討論中他們所說的能被其他所有人聽到。在營火周圍,他們從社會生活中尋找解決利他失靈的方法。他們會討論什麽樣的問題呢?
資源短缺也許是一個選項。也許有的時間段非常困難,他們經常為了貯藏的食物不足進行爭吵。
假設今天是不錯的一天,群體中每個成員都有足夠的食物。他們聚集在一起並且反思他們最近的爭吵,他們所有人都能脫離在困難的環境中自己的角度,至少暫時能,並且思考當食物的數量太小以至於無法給予每個人想要的數量時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想象針對不充足的食物的可能分配方式,每個人不僅僅考慮她/他自己的部份也考慮其他人的部份,並且試圖了解他人所感受到的結果。從他們的反思和交換中出現了一致同意的分配方案以及執行這一分配方法的規則。

【上帝也瘋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1980)劇照。
不管他們是否會如所假設的那樣進展順利,關於分享的對話是能夠想象的。同樣,討論者會同意目標是增加食物的供應,考慮到每個群體成員減少饑餓的願望是應該得到支持的,或者他們也許都同意放棄那些導致暴力的行為。社會嵌入的規範引導能夠開啟倫理計劃,但這些可能產生的規範看起來簡單而粗糙。這些拓荒者的計劃是如何發展成當代生活中極為豐富的倫理道德的?我們如何從當時的開端發展到如今的局面?
我們沒辦法透過提供倫理計劃的實際前進演化過程來回答第二個問題。線索太少。因為對於長達五萬年(或許更多)的倫理計劃,我們僅僅只有最後五千年的文字記錄。在書寫出現時,詳細的規則系統已經存在了。很明顯,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發生的許多事情,僅僅留下了社會變化的間接指標。知道起點(小型群體的討論)和後期階段(現在的倫理生活和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記錄),我們就可以辨別出發生了什麽改變。

【冰川時代:斯克特歷險記】(Ice Age: Scrat Tales,2022)畫面。
其中有一些明顯的改變。在五千年前,人類組成了比倫理計劃開始時的群體要大得多的社會。這些大型的群體中,早期階段的平均主義已經讓位給了復雜的階級制度。倫理生活已經和宗教纏結在一起了。同時倫理生活也開始解決早已超過前人概念認知的問題:城邦的公民追求的是不同於決定如何分配稀缺資源的世界的美好生活。新的角色和機構出現了,產生了關於財產和婚姻的規範。在更為細節的方面,利他主義的概念得到了擴充套件,超越了目前所討論的概念,發展了關於人類關系的新的倫理觀點。
毫無疑問這些改變的確發生了。承認解釋這些改變事實上如何發生的困難給實用自然主義留下了一個問題。反對者批評說倫理實踐起源的解釋只有透過改變物件才說得通——一些東西確實出現了,但它不是真的「倫理」。我們如何獲得「倫理視角」?命令如何內化?懲罰的系統如何前進演化?這些疑問透過質疑用實用自然主義的語言給出解釋的可能性而變得更強烈。沒有可行的從遠古到現在的路徑。
倫理是一場接一場的「文化競爭」
在倫理計劃最初的四萬年間,我們的種族由小型群體組成,每個群體都發展了一套嵌入社會的規範引導的模式。第一個建立起一套回應利他失靈的規則的群體是最醒目的,也許群體間的差別早已存在。或者,即使這些群體面臨著同樣的利他失靈——稀有資源分配或者控制暴力的問題——社會慎思後所接受的命令在不同群體間是不一樣的。
這些差異為新的行程做好了準備:文化競爭。在規則的內容和社會化以及執行的系統中都會出現差異。但為了簡便,我們只考慮所采取的規則的不同。
假設種族中的群體都有同等有效的社會化和懲罰系統。一個群體宣布:獲得的食物在所有人中平分;另一個宣布:食物只給努力搜尋的參與者分享;還有一個群體宣布:食物根據對個體付出努力的共識判斷來分配。每一個群體對所采取的所有規則都同等程度地服從。這些群體參與了「生活的實驗」。文化競爭來自一些實驗比其他的更成功這一事實。
較小和更大的成功在這指什麽?一種衡量方式把握了達爾文演化論根本的指標,那就是不同群體中成員的繁殖成功率。因此倫理規範成功與否透過生活在采取這一倫理規範的群體中的成員留下的後代的數量來衡量。這並不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幾代中接受這一規範的個體數量就會增多,因為更大的留下後代的成功機率可能會被拋棄這一規範的傾向所抵消。
設想有兩套規範,E和F。
生活在選擇了E的社會中的人平均能留下3個後代而生活在選擇了F的社會中的人則留下2個後代;如果兩個社會都無差別地把他們的規範傳遞給生物上的後代,並且假如存在著所有個體都同等操練的生物競爭,那麽社會E將會以社會F的犧牲為代價而得到成長。但如果社會F的成員無差別地將他們的規範傳遞給了生物上的後代,而社會 E 的成員有六分之一的後代遷移到社會F,那麽比例將會維持不變。因此,規範也許獲得一種型別的成功(生物繁衍)而失去另一類的成功(遵守命令的成功)。

肖維巖洞復制畫。
文化競爭考慮的是後一種型別的成功,並且透過比較采取這一規範的群體的大小得到準確的衡量。把透過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忠誠度來表現的文化成功與繁殖成功(達爾文演化論的衡量標準)區分開,似乎看起來多此一舉。因為你也許會假設文化形式的傳播與加強繁殖成功的能力毫無關系的可能性是極小的。留下的後代增加但又透過放棄這些規範而抵消了文化成功這一令人驚訝的後果僅僅只是幻想。這一類的傾向會受到自然選擇的阻礙:沒有轉變傾向的個體會選擇留在生物繁衍上更成功的文化中,他們會留下更多的後代。因此我們應該期待在文化能夠保證許多忠誠於它的人和文化實踐所提高的生物繁衍間有松散的關聯。
這裏用一句著名的口號:「基因牽著文化走。」
對文化傳承的機制以及它和達爾文演化論的交互作用的細致關註揭示了學習他人的優勢如何產生模仿,在自然選擇下維持穩定,並且有時出現不適應生存的傾向。為了辨別倫理實踐解釋中的歷史可能性,並不需要一般性的解釋:我們不需要任何基因-文化共同前進演化的復雜理論就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但是,註意到生物和文化成功之間沒有聯系這一點十分重要。要求服從的規則不需要是那些促進繁殖成功的規則。盡管如此,重要的一點是在一些場合下,特定的倫理規範產生的一些達爾文式後果,比如服從這些規範的後代更容易生存和繁衍,在其他族群接受這一規範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文化競爭並不會產生成功的規範在不同群體間傳播這種殖民征服式後果。一系列的規則可以零散地傳播,其中的某些被其他群體接受,但一些可能會被拒絕。一個群體所信奉的規則可以影響其他群體所接受的規範,即使後者沒有完整地接受所有規則:我們這些根據獵人的貢獻來分配食物的人發現鄰居給部落裏所有成員平等的獎勵,就會被激勵用一種包含兩種規範特點的方式來調整我們的實踐行為(「參與聯合行動的人都能獲得平等的食物!」)。
對於倫理計劃的前四萬年來說,人類的小型群體透過社會嵌入的倫理規則來引導他們的生活。面對現有的規則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嘗試新的辦法。有時,他們和其他群體互動,從中看到一些激發修正自己規則的東西。
最終,一些群體融合在一起,一方或者兩方此前規則的特點在之後的社會實踐中持續出現。一些群體滅絕或者解散了,他們的倫理實踐隨之一塊消亡了,雖然一些幸存者也許會把此前規範的一些方面帶到他們加入的群體。有時新的成員加入,也許作為伴侶而被接受,他們為篝火討論帶來了新的觀點,產生了兩個(母體的)群體此前沒有想到過的綜合規範。這一型別的過程結合起來就造成了一些種類的規則變得普遍而另一些慢慢消失。

【啟示】(Apocalypto,2006)劇照。
看不見的倫理執行者
文化競爭如何能從簡單的社會嵌入的規範引導這樣的早期冒險演變成最近幾千年復雜的倫理實踐?讓我們從倫理和宗教的纏結開始。
從理想來看,冷靜的討論會解放和拓展已有的心理利他主義傾向。但從現實來看,與他人完整的互動也許只能偶爾(如果有的話)實作。思考也許是由那些厭倦了頻繁的爭吵和渴望帶來和平的共識的人所承擔的。為了方便,他們尋找共享的規則,希望以此來規範那些沒有成功與他人合作的同伴,但他們也準備好了當他們認為可以避開這些規則時就打破規則。討論者們會討價還價,為了從施加給他人的限制中受益,他們會放棄一些他們想要(真正想要)履行的行為的限制。
這些爭論也許是好事,尤其是存在懲罰的時候,很多型別的潛在的利他失靈都會被避免,因為旁觀者很簡單就可以明白發生了什麽並且推行彼此同意的準則。雖然當群體的其他成員沒有辦法檢查你是否遵循了準則的時候,你會傾向於違反它。如果你的內心有反對的聲音,它也不會特別堅定或者很強烈。
在規範引導的早期歷史中,人類群體從公共規則中獲得了好處,這些規則公開套用到公開的環境中,但是群體中的許多——也許是所有——個體都願意在他們認為自己無法被發現的時候不服從這些規則。鑒於引入和調整這些規則的人的精心選擇,對這些規則的服從通常來說有利於提升群體成員平均水平的繁殖成功率。比如,考慮通常會保證每個人都有食物的分享規則。群體透過社會嵌入的規範引導,在達爾文式的生存掙紮和文化競爭中獲得進步,即使對規則的服從僅限於行動者能夠預料到他人可以觀察到他的行為時。
文化競爭的優勢同樣也會以一種或者兩種方式出現:透過他人對這一群體成員可以滿足普遍共享的願望的感知,以及透過給他們更健康的食物或者任何有利於額外的達爾文式的適應力的東西。獲得在更廣泛的條件下對規則的服從的能力可以在文化競爭上產生額外優勢,同時通常都會增加個體所期待的繁殖成功率。提高服從的技能促進了文化的(也許還包括了生物上的)成功。
這是什麽樣的技能?當他們在一起反思他們的倫理實踐時,慎思者會發現不服從經常是由不會被發現的信念造成的。他們記得是那些自信自己不會被發現——也因此可以避免懲罰——而違反規則的人犯了錯誤。在群體中,成年成員精煉這一計畫來社會化年輕成員。也許他們反復灌輸對違反規則後果的持久恐懼,灌輸原始形式的良心來使得人們在沒有明顯的觀察者在場時能夠遵守規則。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完成這些行為,群體的後代就會傾向於更頻繁地服從規則,隨之而來的是正面的達爾文式效應和文化效應。

【禁忌】(Tabu,1931)劇照。
但這一恐懼是如何被激發的?在人類的文化中——在成功生存下來的實驗中——較常見的做法是訴諸不可見的,對違反倫理規則作出回應的實體。西方的一神論使用這種方式:存在著無所不知的神,他觀察一切,作出判斷,懲罰沒有服從命令的人。
前輩繼續觀察後輩的行為並且如果發現命令被打破了就停止幫助。神靈往往和特定的地點與動物結合在一起,如果規則被違背的話,就會報復整個群體。在自然中存在著隱藏的力量,人們只有和它們結盟才能獲得成功,而違背那些規則就會威脅或者摧毀這一結盟。民族誌證實了不可見的力量(通常是人格化的,但並不總是這樣)的流行性:正如有人告訴他們,當他們做了不應該做的事,一個住在天上觀察著人類所有活動的「全能的父親」會對他們感到非常憤怒,比如他們吃了被禁止的食物。
一旦看不見的執行者這一觀念深入人心,對恐懼的懲罰就可以被嵌入到復雜的情感反應系統中。長者所頒布的命令可以被當作上帝或神靈的願望(或者影響人類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力量的傾向)。如果神是某個特定群體的,他們也許會被看作為特定的群體制定了規則,這些規則既表現了神靈的幫助也構成了群體的認同感。後來群體的倫理實踐會回溯到他們的祖先獲得神靈幫助並且得到了神靈的命令這樣的故事。對懲罰的原始恐懼轉化成了更為積極的情感——敬畏,尊敬——並且命令被看作是獲得神靈幫助的標誌而讓人樂於接受。群體成員把這些規則看作是他們身份的構成部份。
提出的推測過於簡單了。在一個充滿了明顯不可預測的現象和無法解釋的改變的世界中,我們的祖先求助於有特殊能力的看不見的實體。一些群體更進一步,把社會秩序與這些存在聯系起來:
非人的力量會回應破壞規則的人,祖先或者神靈會報復這些不服從規則的人,神靈透過為群體所認知的命令來表達他們的意願並且能夠監視人們的行為,即使行動者認為他是獨自一人。采取了這種方法的群體獲得了強有力的保證成員服從的機制,並且比那些援引與道德領域無關的看不見的力量的競爭對手做得更好。與宗教纏結的倫理學是極為普遍的,因為看不見的力量和倫理行為之間的特定聯系在文化競爭中有極為重要的優勢。
哲學家通常反對極為普遍的把倫理學嵌入宗教的做法。他們論證,從柏拉圖開始便否認宗教能夠為倫理學提供特定型別的基礎。
但是,他們沒有觸及因為具有增加服從性的能力,宗教也許對倫理實踐來說是有價值的,甚至是必要的這一觀點。神諭式的倫理學方法絕不是非理性的行為模式,它可能反映了文化競爭的深刻事實。
如果倫理與倫理有沖突
數萬年以來,基礎資源的平均主義分配對倫理計劃來說十分重要。弱小的小型群體需要所有成年個體的參與。他們當然會使用許多當代狩獵-采集部落所使用的,促進成員間平等的策略的原始版本。比如「!Kung」這一部落采取措施來保證狩獵能力的差異無法擴大。他們對吹噓自己殺死獵物的行為有嚴厲的懲罰,培養被用來阻止驕傲和傲慢的嘲笑行為,並且有把獵殺獵物的行為歸結給箭的擁有者的習慣,同分時享箭的行為是非常普遍的,這就能有效地減少狩獵上的差異。違反這些傳統被看作會招來厄運。在早期人類生活的環境中,沒能發展出類似策略的群體將會失去規範引導所帶來的優勢。
但是,在文字記錄中第一個可見的社會已經包含了不同的地位和等級。是什麽導致了這些差異?
早期城市(傑利科、加泰土丘)的考古發掘使得這一點變得清晰起來,直到八千年以前,人類能夠生活在比倫理計劃早期階段大得多的群體中。當一千人或者更多人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之內時,透過面對面的保證來維持和平的策略也就不再適用了。必須有彼此同意的規則系統來解決潛在的沖突以及陌生人間的關系。一些涵蓋了小型群體之外的個人間交換的重要命令在更早的時候一定獲得了實質性進步。最終,直到一萬五千年前,人類群體能夠階段性地聯合起來,因為一些遺跡中留下了可以證明存在更大聯盟的東西。
此外,存在著早期階段群體間和平合作的間接證據——甚至還可能證明不同群體間貿易的存在。最早期的原始人的技術都是免洗的,二十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制造出需要的工具,當他們離開時就會扔掉這些工具。對他們來說,工具不會對人們的遷徙產生重要的約束(人們不需要帶著工具跑),工具也不會被看作財產(如果一把斧子被他人拿走了,制作者能夠輕易制造新的斧頭)。
但隨著原始人逐漸分散開來,他們把工具資源留在了原地,到了二萬年前,這些群體要到距離他們發現制作工具原材料(對於用黑曜巖制作的工具,這一特點非常顯著)的地點極遠的地方(相距一百公裏或者更遠)搜尋食物。這些群體需要攜帶工具(雖然沒有在記錄裏保存下來,出於可理解的理由),也需要配合彼此以及其他群體的行為,從而使得長距離的交易網路或者獲得他們所需物質的旅程成為可能。距離會導致明顯的被剝削以及攻擊,群體的規範也就需要包括那些能夠處理這些危險的規則。
即使他們沒有與其他群體交易,他們的倫理規範需要包括至少在某些條件下禁止傷害群體外個體的規則。這類的規則預示了後期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比如傑利科和加泰土丘、烏爾、烏魯克及巴比倫。
在人們聚集到一起建造金字塔和金字形神塔之前很久,我們的祖先就開始用遠方的材料制造工具,把特殊的材料帶到山洞中畫動物,用特殊的人造物品埋葬死者。到一萬五千年前,人類群體開始制造雕像並放到墓穴中,如果不假設超驗存在的福祉也是人們實踐考慮的一方面的話,這一行為很難得到解釋。
幾千年前,人們花時間來分離出用於裝飾山洞巖壁的顏料,發展繪畫的技術,並且在法國和西班牙等地區制造了非凡的藝術。這些活動不太可能出現在任何仍然在為了滿足基本的食物和庇護需求而掙紮的社會,也不太可能出現在沒有初期勞動分工的社會。距離現在三萬年前,為群居生活創造規則的行為,即倫理計劃,必然獲得了較好的發展。
早期的法律規則為發生在史前後期的倫理規則的前進演化提供了最清晰的指示。古代近東地區的文字記錄包括了體現理想行為的故事、來世的神話以及部份法律規則。比如,「吉爾伽美什史詩」告訴了我們對蘇美爾和巴比倫等級社會中高等人士期待的圖景;類似地,埃及【亡靈書】中純潔的宣言向我們展示了什麽型別的行為算作違反倫理,也因此說明了倫理規範的結構;最明顯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典裏所發現的規則列表,從公元前兩千年的裏皮特·伊許塔法典到漢穆拉比法典(一個世紀之後)以及之後的規則告訴我們哪些行為是明確禁止的以及各種社會違約的相對重要性。

【史前一萬年】(10000 BC,2008)劇照。
法典的開篇通常強調立法者帶來了和平胡解決矛盾的方法,法律被看作超越充滿原始暴力和恃強淩弱的社會生活的方式。殘存下來的石碑和石柱不能提供給我們對當時所執行的法律的完整解釋。
它們修正了已存在的法律,提供了能夠解決在創造社會秩序時出現的問題的規則。這些「法典」體現了從文字出現時開始的社會規則發展的多級過程。它們碎片化的特點極為明顯。它們為每種特定型別的事件都制定了條款。這些都是越來越復雜的社會所出現的新問題。新石器時代的牧民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農民早已發明了控制暴力、保護他們勞動果實和管理性關系的規則。
當他們被整合進需要社會合作來提供足夠灌溉的世界中的更大的單元時,新的問題出現了:準則該如何標準化,一個人如何保證他的土地被恰當地使用,公共的溝渠和堤壩要如何維護?殘存的法典極其仔細地處理這些問題,以及由於大量的人口聚集在相對較小的區域而產生的社會摩擦導致的各種型別的暴力和性關系。它們產生於對暴力行為該如何制止,性關系該如何規範以及財產該如何保護的共同理解的背景下。後期巴比倫法典的擴散揭示了史前文化傳遞的普遍性(一旦倫理計劃前進演化到允許群體間和平互動時,擴散很快就會消失)。
對我們的目標來說,界限應該是模糊的。幾乎所有的社會,在所有的時間裏,都不僅僅透過教育倫理規範(至少是當代哲學所理解的倫理)來社會化新成員。在遠古社會,年輕人被告知什麽是宗教義務,什麽是法律,什麽是禮貌和社會習慣。哲學討論中倫理學的特殊概念來自歷史的行程。後來的判斷區分了倫理義務,它們都來自早期不分類別的規範實踐。
規則類別的區分通常來說很有意義,因為規則有時會互相沖突,並且有時(但並不總是如此)會透過更為抽象的方法來決定什麽樣的規則有優先權。若人們被命令參加特定的儀式,但是,在典禮進行時,參與者聽到其他群體成員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群體中保護其他人的規則是否優先於完成儀式的命令?不同的群體也許會有不同的決定。一些群體,也許是文化上最成功的群體,宣稱幫助和保護同伴的命令比要求完成儀式更重要。(粗略來說)許多社會,當代的和歷史上的,都把命令劃分為三類。最根本的一類是與超驗存在有關的命令;第二類被用來鞏固並且有時也可以改變從社會討論中出現的規則(比如法律的問題);這兩類命令對於相對而言不重要的命令來說具有優先性,而最後一類規則是用來引導人們行為和習慣的。
對這些類別的區分沒有解決所有優先性問題,因為兩個神聖的命令可能是相互沖突的(崇拜的規則可能和救人的規則相沖突)。這些類別,以及把一些規則看作服從於另外一些規則的方式,都是規範引導文化發展後的產物。並不存在某種不可避免的結果。
原文作者/[英]菲利普·基切爾
摘編/羅東
編輯/羅東
導語部份校對/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