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生活】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夏天的,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會有多面目全非。
普通人的生活中本來就充滿了未知和意外,而 當社會失序,正常生活難以為繼,我們將怎麽消化?怎麽對抗?
王占黑的全新小說集【正常接觸】中寫的就是這樣的時刻——
普通勞工和行動青年兩個世界的秘密交疊,打工人內心隱藏的願望,失業青年們因貓結緣的特殊際遇,一個女孩不斷地給對面的鄰居爺叔寫著永遠寄不出的信……
現代的街頭走著無數倒黴、失意、疲倦的青年人,在社會的發條上艱難懸掛,各懷心事。 宇明,一個上海小職員,面對著窒息的工作、堪憂的健康、母親的不理解,將如何繼續前行?今天,我們節選了【正常接觸】中「動物之城」一章,聽見 一個普通人在生活之海掙紮時的真實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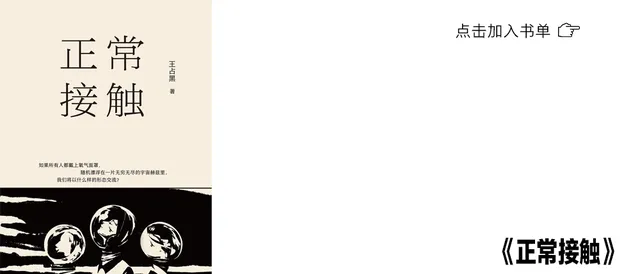 以下內容選自【正常接觸】
以下內容選自【正常接觸】
夜晚的光線走到某個位置上起,黃浦江就折疊了, 兩岸的寫字樓聚攏在同一處,像峭壁,跳下去就是流動的深淵。 我不開燈,和貓待在一起,靜靜看上個把鐘頭。
以前侯永貞不管走到哪,只要望見那個扁扁的開瓶器,哪怕只有一角,必定要拍下來發給我,意思是,我路過你了。她就是這樣,情願忽略這中間插著的無數棟彼此遮擋的高樓。我跟她解釋過很多次,我的辦公室在二十三層,相當於開瓶時虎口握住的位置。
這意味著無論從哪個角度拍,她的照片裏都不會有我。 為什麽一棟樓僅憑高度就能帶給人這樣強烈的虛榮和滿足 ,人們爬上頂峰一覽眾山小的時候,從來不會想知道遠處的山裏有什麽,自己腳下又踩住了什麽。
第二戶比第一戶小很多,但有一套極舒服的組合沙發。這個驚喜源於一場毫無征兆的大雨,我被迫留下來陪貓多玩了會,它睡著後,我只有幹等。再睜眼,天黑了,貓還在腳邊,外面的地早已幹透了,太久沒有過這樣穩妥的睡眠。此後我把上門頻率改成兩天一次,到了先拉窗簾,反鎖大門,躺進沙發睡一覺。

【疼痛難免 】
真的神了, 這沙發好像一旦觸碰到人體就會釋放出某種元素,叫人以快到難以置信的速度失去意識,但又不提供復雜的做夢功能 ,因此睡著的每一秒都是待機充電。充完,我會在一個鐘頭內把近三天的事全部做完,排日程,清賬單,更新表格,把操盤手發來的照片一一轉給客戶,再提醒兩方確認收發款,這多少讓我找回點從前上班的感覺。目前為止,我已經找到三個操盤手,合作起來很順暢,應該算得上各取所需,有人急著賺錢,有人要寵物活著,而我只想要看更多的籠子。
這個讓人隨時入睡又隨時振作起來的小房間,我願稱之為貓籠。業主是個剛畢業的男孩,從墻上地圖的標記來看,他就在兩站地鐵開外的高新科技園上班。家裏除了沙發,余下空間都讓給寵物。 這樣的獨居生活,我想象過無數遍。以前總是羨慕外地來的同事,遠離父母,在哪裏工作就在哪附近找房,跳了槽,大不了重新換過。
玩真心話大冒險時提起,卻遭到一桌人強勢圍攻,有女同事覺得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憤怒地說,你要是覺得好,自己搬出去試試。之後當話題轉向相親中碰到的媽寶男,她的眼神有意無意朝我掃過來。其實我跟侯永貞提過幾次,她沒松口,堅稱有錢租房不如攢下來買一套,那時她已相當操心我結婚的事情了。不過這些都是舊話,忘掉最好。
工作完成後,我關掉落地燈,貓、沙發和周圍的漆黑融為一體。 只剩下一雙發亮的眼睛牢牢盯住我,我想,這是因為我的眼睛也正在燃燒。
頭痛差不多是從工作第四年開始的,大多數情況撐到下班,回家倒頭睡一覺,第二天又是一條好漢。 但經過一年的高強度出差,我的作息徹底亂掉,夜裏睡不著,早上起不來,睜眼閉眼都是失重的狀態。 當時從家到地鐵先要坐四站公交,下來轉三部地鐵,分別經受虹口足球場和人民廣場的人海考驗,最後突破陸家嘴的防線熬到辦公室時,整個人如同死過一遍。好在沒多久家附近挖通了新線,不用花半個鐘頭堵死在公交上了。

【倫敦生活】
但過於密集的換乘經常讓我忘記要去哪,面對消失在各個風洞的人頭,我甚至搞不清自己是上班還是下班。新建的地下過道裏漫散著一股刺激的三夾板氣味,好像還帶著點血腥和酸臭。我睜不開眼,只覺墻太白了,廣告板太亮了。有一次在扶梯上兩眼一黑,突然彎了下去。類似的狀況之後又出現過兩次,醒來,看到自己被陌生人團團圍住。他們的頭聚攏在我上方,目光垂直落下,見我開口,又迅速散去。我看了看手機,每次都只失去十秒左右的意識,三次加起來也不過是乘直梯從地面降到月台的時間,並不耽誤什麽。
去檢查,一切正常,我的頭、胃,我的脊椎,都沒有顯示出過早報廢的跡象。腫瘤指標證明,我身上也尚未存在我爸的致命痕跡。醫生建議去看精神科,精神科建議服用抗焦慮藥物,他們都說,最重要的是調整好你自己。而我的想法剛好相反, 我當時想,如果自己身上找不出實際可見的問題,就只能調整自己之外的東西。
我決定從侯永貞引以為傲的地方離開,回到學生時代實習過的公司,這讓她挺不開心,和朋友聊天,還是三句不離那個高聳的開瓶器。要命的是,頭痛並沒有因為工作強度減弱而得到緩解,我甚至開始在辦公室出現幻聽和失明。我把問題怪罪到公司新換的廉價家具上,一路跳槽,事情開始失控。 痛苦的不僅是頭,還有自己對於每走一步都是錯上加錯的無可阻擋,像經過一個光滑的下坡,我腳裏只有一輛手剎失靈的獨輪車。 我跟侯永貞攤牌,扛不住了。她又哭又罵,打電話叫侯永泉來。從小就這樣, 她不相信看不見的東西,如果看不見,那就是自己心態沒擺正。
侯永貞最常舉的例子是自己,她說,你看看我,一個人拖大你,再苦再累也過來了,人都是這樣的。她最喜歡說最後這句,用來總結自己,也用來刺激我。每當我不想做感到為難的事情時,她就會這樣說。 但我那時就是不行,我努力了,真的過不去了。

【疼痛難免】
侯永泉勸了幾趟,最後跟他姐姐說,道理也是有的。他反過來勸侯永貞不要再管了,他說,等宇明身體好轉,不用你講,自己會重新上場的。侯永泉給出的保守估計是半年到一年。可惜他和我都搞錯了, 比賽雙方既不是我和職場,也不是我和時間。在這場較量中,我並不擁有一次叫停的權利。
最後一次面試,我回到家,脫掉西裝躺下來,看著侯永貞出門前留下的電視訊道,北極熊扒著一塊浮冰,坐在近乎融化的海平面。一個男低音平靜地說,這頭幼熊已在茫茫海上漂了一年。我想,和我差不多。男低音繼續說, 看著自己腳下的冰塊一天天變小,它除了等,沒有別的辦法。 此刻它心裏在想什麽?失散的家人,還是地球的未來?字幕跳出,這集即將在一串冷漠的疑問句中放完,我沒有力氣換台。
看著那頭幼熊如同雕塑一樣的背影, 我突然覺得它並不關心什麽家人或者未來,只是企圖透過反復回想來確認一點,自己從前到底是活在地面還是海上,盡管答案不再重要。 字幕捲動,鏡頭向上搖,搖向遠處的夕陽,血紅的,把畫面底部越來越小的北極熊照成一團冰上的火。它燒起來了。而現在,只有在這間漆黑的屋子裏看到那雙發亮的眼睛,我才能忘掉,自己已在冰上坐了五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