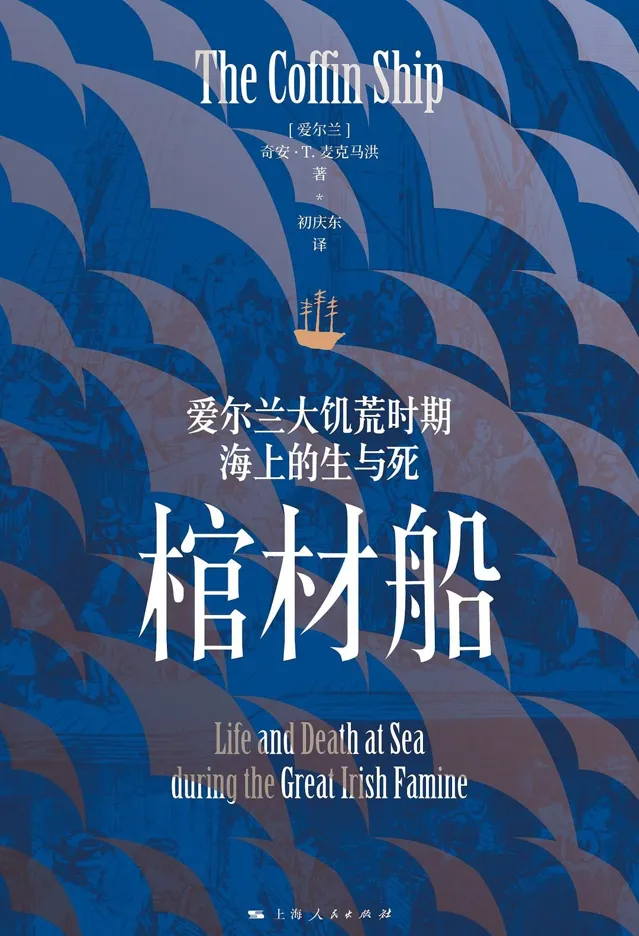
【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愛爾蘭] 奇安·T.麥克馬洪著,初慶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88.00元
自十七世紀中期以後,幾乎擁有愛爾蘭全部耕地的英國地主只關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使大多數愛爾蘭人只能依靠在小塊土地上種植馬鈴薯來維持生計。1845年夏天開始傳播的一種不為人知的病害使馬鈴薯作物大面積受災,引發了越來越慘烈並且持續到1852年的大饑荒,愛爾蘭島八百萬人口中有一百多萬人餓死,近兩百萬人被迫移民逃荒。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這不僅僅是天災,同時也是人禍,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英國政府不但對大饑荒的不作為、援救不力,而且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要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因此至今很多愛爾蘭人認為政府在知道餓殍遍地的時候而不作為、在並非完全沒有能力的情況下不救援,就是對愛爾蘭的種族滅絕,其行徑與納粹屠殺猶太人、鄂圖曼帝國滅絕亞美尼亞人一樣是犯下反人類罪。
愛爾蘭大饑荒時期的移民潮由此產生,災民們或單身或舉家漂洋過海,逃離到處是饑饉與死亡的故土。雖然並沒有發生過在村鎮道路、交通要道上到處堵截、禁止逃荒等更為滅絕人性的人身暴力控制行為,那些逃難移民的道路仍然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艱辛與危難。愛爾蘭歷史學家奇安·T.麥克馬洪(McMahon Cian T.) 【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 ( The Coffin Ship: Life and Death at Sea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2021)講述的就是這個因大饑荒而產生的大移民和海上航行的生死故事:從啟程前與海外親友的聯系到如何籌錢購買船票,從如何了解所有相關資訊到以何種方法抵達啟航港口,從如何才能上船和在航行中發生的一切到抵達目的地之後如何上岸找到立足之處。移民在航行過程中仍然要在生死線上掙紮,許多人在船上因疾病、暴力等原因死去,最後葬身大海,這些移民船因此也被稱作「棺材船」。
看來麥克馬洪力圖讓中國讀者和他一樣對於大饑荒時期的移民血淚史感同身受,因此在「中文版序」的開頭就講述了一個有關中國人的故事。1852年秋,「格特魯德」號(Gertrude)從愛爾蘭啟程前往中國廈門,在廈門征募了三百多名契約華工後駛往古巴的甘蔗種植園,以補充那裏的勞動力。華工與船員之間的關系由於食品供應和語言不通等問題從一開始就高度緊張,在這段長達四個月的航行中發生的各種沖突,最後導致了有十七名華工移民被船員開槍打死並有更多人受傷的悲劇。作者認為契約華工的遭遇與【棺材船】一書的核心人物愛爾蘭人之間有著非常重要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重塑十九世紀中葉世界歷史上大規模移民浪潮的重要組成部份;華人和愛爾蘭人在移民海外的航船上死亡率相近,高達百分之十;最重要的是,華人和愛爾蘭人與其他經歷漫長路程的移民都同樣感受到溝通不暢和暴力的影響,也都被齊心協力和大無畏精神所形塑。作者接著還談到對十九世紀的契約華工而言,「苦力」(coolies)一詞具有種族歧視的色彩,「如果可以傾聽他們的聲音,那麽我們對他們經歷的歷史解釋會有什麽變化呢?」(第3頁)有關中國人生命的悲劇故事和被貶低、被歧視的命運,當然不應被我們忘記。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中國普通民眾所經受的所有戰亂、大饑荒、迫害的苦難史,必須思考如何「傾聽他們的聲音」,如何重新解釋他們所經歷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棺材船】就是一面雷蒙·亞倫在【歷史意識的維度】(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1961)中所講的那面鑒古論今的「歷史倒後鏡」,十九世紀的愛爾蘭移民和那些遙遠的「棺材船」不再與我們無關。
關於「棺材船」(Coffin Ship)這個帶有恐怖色彩的術語,一般認為起源於大饑荒時期。麥克馬洪指出實際上這個術語的出現早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且在饑荒時期很少被提及;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反英鬥爭中才開始流行(第4頁)。問題是麥克馬洪在「中文版序」和「導論」中一再指出,雖然對移民海上生活的關註是重要的,但是以「棺材船」這一術語作為描述大饑荒時期的移民航船狀況的一個準確而且流行的表述,會使愛爾蘭移民被束縛在「棺材船」的形象中,忽視了他們的活力、創造性和能動性;「這種表面的刻板印象不經意地剝奪了移民的人性,將他們的聲音淹沒在歷史檔案之中」(中文版序,第2頁)。「長期以來,這種將饑荒時期的移民船只描述成‘棺材船’的線性敘述模式,使人們對這一航行的真正理解蒙上了陰影。然而,當使用移民的話語去劃破它的表面時,我們對移民的實際生活便有了一幅更加復雜卻愈發清晰的畫面。」(導論,3頁)這是一種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揭示了某些流行術語會給歷史研究蒙上刻板的、固化的陰影。在這方面我們也遇到過不少相似的例子,仍然有待澄清與研究。因此,麥克馬洪之所以將書名定為「棺材船」,就是要從這個流行術語入手,扭轉那種固化、刻板的關於愛爾蘭移民船的說法和留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以獲得對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的完整認識以及更廣泛意義上人類移民的完整認識。他說:「我在書中的目標是將這一航行過程從晦暗不明的歷史中拯救出來,然後重新安置航行的船只,將其與寓所和每周發行的報紙一同作為移民史富有活力的組成部份。」(第5頁)
具體來說,作者透過在世界三大洲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尋找與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相關的各種書信、日記、政府檔及報紙等所有史料,在閱讀、分析和研究這些資料的過程中始終聚焦於移民的親身經歷,而且把航行前後的全部過程,把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所有跨國聯系的行為、事件等都作為研究的物件。他說:「我最初的目標是辨識與理解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跨越大西洋的生存策略。」後來在研究中進一步確認的是:「一個人耗費在船上的數周甚至數月時間,僅僅是航行的一部份。19世紀的海上航行確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收集離開所需物品開始,到在當地社群定居結束。在這一過程中的每一步,移民都要依賴地方性和國際性的聯系網路。因此,本書的核心觀點是,遷移過程絕不僅僅是個體從這裏到那裏。實際上,透過鼓勵金錢、船票、建議與資訊的跨國交流,航行本身在愛爾蘭人大流散的世界性網路中催生出數不勝數的新線索。」(導論,第5頁)這又是與揭示在「棺材船」術語下被遮蔽的移民的人性、鮮活性相聯系在一起的重要主題:運用跨國史以及正在迅猛發展的海洋社會史(maritime soci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力圖展示航行本身就是人類遷徙謎題中至關重要的一塊拼圖」(中文版序,第3頁)。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麥克馬洪的這一研究議題屬於移民史、海洋史、航行史、跨國史和微觀史的領域,具體來說既是對移民群體與個人的微觀研究,同時也是對在跨國網路與特定時空中形成的共同體社會的綜合性研究。
作者在「導論」中有一段文字是對全書內容和關鍵要點的生動而深刻的表述,值得引述:「全書五章內容依次考察大饑荒時期海內外的愛爾蘭人在啟程、航行、抵達的過程中同心同德、相互支持的復雜面相。從在十字路口的揮淚告別到路遇利物浦的騙子和盜賊,前兩章考察了航行的早期階段。第一章論證了準移民如何透過復雜的社會關系網路,有時跨越數千英裏以獲得啟程所需資源。然而,在統艙中獲得立足之地只能算是第一步,他必須按時到達船只起航的港口。而要做到這一點,正如第二章表明的那樣,常常意味著需依靠同樣的跨國和地方交換網路,使航行成為首要之事。第三章探析乘客在統艙的海上生活,有學者曾將之與‘高密度的城市環境’作過對比。在一個周圍都是陌生人的生態系中,移民的共同體意識突破了朋友和家庭的傳統束縛,這些在他們家鄉占主導地位。海洋航行在真正意義上是以共有的經歷為基礎,而不是親屬關系,這為社會秩序奠定了心理基礎,也是在新世界建立新共同體的基礎。海上生活使愛爾蘭人從‘向外移民’(emigrants)變為‘向內移民’(immigrants)。第四章分析船上死亡的情況。經過對可獲得的死亡數據的條分縷析,轉向分析死亡和臨終者對一個給定船只上的微型共同體和生活在陸地上的人們的影響。研究表明,盡管船上的死亡率可以將漂浮不定的共同體撕裂,但也可以將他們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後,第五章涉及移民到達新世界面臨的挑戰。移民著手重建他們與愛爾蘭的聯系,這與他們在北美和澳洲組建新的聯系是同步的。總體而言,依據上述各章的簡要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航行不是一條漂泊的執行緒,反而是移民生命肌理的一個重要接縫。」(14頁)正是以上這些內容與論述,使「這種將移民航行作為19世紀全球網路連線鏈條的思路,為理解現代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視角。……超越海量的統計數位、官方報道和陳詞濫調,去傾聽移民自己的訴說,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混亂但更加真實的圖景,而且也有力地證明了成百上千次的航行如何幫助我們重織被撕裂的聯結紐帶。……本書正是以這些消失的聲音為精靈,帶領大家穿越一段隱藏已久的歷史的‘無軌深淵’」(15頁)。從「消失的聲音」想到了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保爾・湯普遜(Paul Thompson)的那部名著【過去的聲音:口述史】( The Voice of the Past ,1978),似乎感覺麥克馬洪是在透過書信、日記等資料對那些愛爾蘭移民作口述史訪談。透過這些書信,作者「努力去理解愛爾蘭移民是如何思考和言說大饑荒時期的航行過程」(270頁),力圖讓那些消失在「棺材船」的航行中的聲音重新回響起來。
讀完全書之後,我比較關註的是全書最後的「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這是作者對在研究中使用的資料與相關認識論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補充說明,對於了解作者的學術意圖及本書的學術貢獻很有參考價值。
首先是在跨國視野的移民研究中把海洋史、航行史研究納入進來。一方面要拒絕接受根深蒂固的「陸地中心主義」(terracentrism),這種觀念無視海上航行的生活空間的真實性與重要性;另一方面,雖然已有的海洋航行研究聚焦奴隸貿易和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對奴隸造成的心理影響,麥克馬洪的研究也受到這些著述的影響,但他還是提出了重要的新的研究路徑:大多數奴隸在他們身後沒有留下航行的書面材料,而大饑荒時期愛爾蘭人的書信、日記和報紙得以存世,這些史料有助於了解移民航行的每一個階段,可以揭示出移民的聲音與動機。「總體而言,這些手稿檔案提供了目擊證人的敘述,它們是以‘自下而上的歷史學’路徑研究移民經歷的核心資料。」(271頁)
其次,傳統的移民史傾向於研究在發生在兩個國家之間的移民,麥克馬洪的研究則是力圖「對前往東、南、西、北的移民經歷予以統合」,也就是要書寫「兼顧流散的或跨國的(transnational)與比較的或兩國間的(cross-national)移民史」(272頁)。這當然是一種頗有風險的學術意圖,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比如如果要概括性地論述前往北美與澳洲的自由移民與流放犯人的移民經歷,容易抹殺或忽視了他們之間的差異——在愛爾蘭人內部、在前往澳洲的與跨大西洋的移民之間、在自由民與犯人之間都充滿了復雜的差異性。作者則是力圖「在認識到這些差異的同時超越這些差異」,在整個移民過程的研究中,把由通訊、跨洋航行對移民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跨越網路作為基本研究視角,把「移民共同體」(emigrant community)的概念滲透在整個研究之中。
另外的挑戰來自研究這些移民書信、日記等第一手資料的時候產生的困難,「我很快就意識到現存檔案無法構成大饑荒時期離開愛爾蘭之人的一個完整且有代表性的核心樣本」(273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十九世紀中葉愛爾蘭移民在社會經濟、地域、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語言等方面的差異與相互影響的方式,使得要在這些資料中提煉出有代表性、綜合性的定性與定量分析都幾乎是不可能的。鑒於對於相關爭論和對所使用的資料的優缺點的認識,麥克馬洪認為「連貫的、定量的內容分析方法不適用於本書。盡管我了解一些書中援引的少量書信的背景資訊,但絕大多數書信缺少全方位數據。……我從這些資料中爬梳出有用的定性資訊,但要以一種系統的、定性研究的方法來比較對照的話,將是徒勞無功的。所以,我最後采用的方法是極為直截了當的。我打算利用移民書信和日記,復原大饑荒時期愛爾蘭人在移民過程中所想的和所談論的內容」(275頁)。這裏談到的「連貫的、定量的內容分析方法」和「系統的、定性研究的方法」都是在移民研究中經常使用的,通常人類學家會比較擅長對移民群體、動因、文化現象進行定性的闡釋性研究,而人口研究者和社會學家會更關註透過定量分析得出某種移民遷移模型。但是對於在具體史料中存在的難以歸納其性質或無法量化檢驗的問題,一味固執堅持這兩種方法的研究結論很難在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等方面取得認同。
麥克馬洪從戴維·菲茨派屈克、克爾比·米勒和戴維·格伯的爭論中發現存在的抽離語境、缺乏代表性等方法論問題,因此要尋求解決辦法。他說:「當我發現「共同體」(community)對這些作者和他們的讀者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時,我又回過頭去看我的筆記,尋找一種方式可以將移民的聲音和諧地融入圍繞這一概念的合理解釋的合唱中。當我寫作這些段落時,我有意大段抄錄、直接摘引這些檔案,希望增強移民自身早已消失的聲音。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希望在處理這些書信和日記時能夠更進一步:不是幹癟地敘述事實和數位,而是飽含深情地將這些實物視為遙遠的親友用以修復脆弱的社會關系的手段。」(276頁)「共同體」這個概念在移民史和當代移民的研究中無疑是很重要和有效的概念,即便我們只是曾經與海外的移民群體有過一些接觸,也會感覺到那麽自然而又明顯地存在著的那種「共同體」的氛圍。麥克馬洪所表述的「飽含深情地將這些實物視為遙遠的親友用以修復脆弱的社會關系的手段」這句話,本身也有某種情感的感染力,引人深思。
說到底,在今天重新認識和思考大饑荒時期的移民,不僅僅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同時更是對改變現實有積極意義。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的移民潮過去之後的一個半世紀中,又有七百萬愛爾蘭人離開愛爾蘭,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乘坐的是蒸汽船、後來是乘飛機,「但大饑荒時期的帆船仍然是移民經歷的一個有力象征。它的力量反映在像皮特·聖約翰(Pete St. John)的【阿薩瑞的原野】(1979 年)和倫敦愛爾蘭人的龐克樂隊波格斯樂隊(The Pogues)的【萬人航行】(1988 年)這樣的民謠和歌曲中」(262-263頁)。這種象征力量在於不斷喚醒人們對於大饑荒的饑餓、逃亡、移民艱辛和海上生死歷程的記憶,從而對當代饑荒中的受難者和難民「報以根深蒂固的同情之心」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衣索比亞北部遭遇旱災和饑餓,愛爾蘭行動(Actions From Ireland)和愛爾蘭明愛(Trocaire)等愛爾蘭非政府組織為災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二十年後,愛爾蘭作家約瑟夫·奧康納(Joseph O’Connor)的小說【海洋之星】( The Star of the Sea )講述的是大饑荒時期的一艘移民船的故事,作者認為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愛爾蘭人的經歷中得出的主要教訓就是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幫助世界上數百萬正在遭受饑荒,甚至會餓死的窮人。2019 年10 月,在一位愛爾蘭人駕駛的一輛冷鏈運輸車中發現三十九名死去的越南難民,愛爾蘭議員馬丁·肯尼(Martin Kenny)指出,船運貨櫃就是「21 世紀的棺材船」。【愛爾蘭時報】( Irish Times )專欄作家芬坦·奧圖爾(Fintan O’Toole)主張出台嚴苛的法律來保護移民勞工,並提醒他的讀者:「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棺材船。」(264頁)這句話很令人感到心悸與悲傷,不僅是因為「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棺材船」,更是因為我們已經太快地忘記了它們。
麥克馬洪說,「培養對不幸之人的共情並非易事」(同上)。在過去幾年期間,我們在資訊媒體中目睹過多少普通人不幸的、悲慘的故事;在今天的俄烏戰爭、以巴沖突中,更有多少無辜平民每天都在經受著死亡的威脅及各種災難的煎熬。作者說:「現在就像19 世紀中葉那樣,現代性的離心力仍在侵蝕人類同心同德的紐帶。經濟不安全、大規模移民和過時的無知使很多人向內轉,在種族和國家中尋找安全感。……我希望透過了解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的經歷,可以穿過這些聲音片段和統計數位。這樣做時,我們可能要學會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帶著行李前往港口、駛入黑暗中的人。」(同上)全書最後的這句話特別令我感動,眼前好像就出現了在茫茫夜色中拖著行李、扶老攜幼穿過整個城市走向車站、碼頭的那種情景。這幾天在美國哥大、哈佛、耶魯等大學校園發生了學生抗議活動,無論如何,其中關於人道主義同情的呼聲表達的就是「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帶著行李前往港口、駛入黑暗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