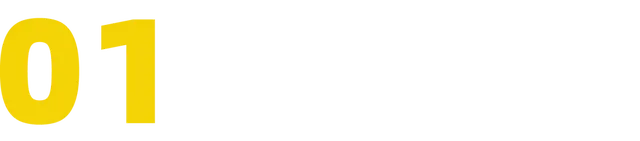
波瀾與平靜
八千米攀登、無氧、女性,把這三個詞任意組合,都很不一般。但今天要講述的,不是關於一個有天賦的女性如何在山上屢屢創造記錄的故事,至少對於何靜自己而言不是。
你可能看過【Free Solo】,知道徒手攀巖的Alex Honnold,他有一個很不尋常的大腦,對恐懼的反應和常人不一樣。徒手攀巖在900多米高的酋長巖上時,他大腦中的杏仁核是關閉的。這些年來也有很多人認為何靜是天賦型選手,要知道,在八千米的「死亡地帶」,連有「喜馬拉雅的超級人類」之稱的夏爾巴人,仍然需要補充氧氣。
但實際並不是這樣,幾個月前,她在華大基因做了一次身體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她不僅不是天選攀登者,而且資質相當平平:「登山基因」弱,先天耐力中等,先天爆發力弱,缺氧耐受能力正常水平……各項指標都沒有什麽突出。

▲何靜在華大基因所做的身體檢測結果。供圖/何靜
那麽是什麽驅動著她一次次選擇無氧攀登?她是一個怎樣的攀登者?
與何靜的對話中,當你試圖挖掘她更深層次的驅動力時,總是被打斷,並且她會把這些在我們看來很厲害的經歷,稀釋再稀釋,最終都歸為一句話——「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愛好者」。
而當你想探尋她在山上的更多故事時,她會更加小心甚至排斥——「你要讓我回憶的話,相當於把我的傷口再給扒開,你們又不管它的愈合,最後我就只能自我療愈。」
下山後的何靜也會常想起山上的故事,這時候記憶會像倒帶一樣,把她又拉回到那個場景中,寒風吹入肺中的疼痛,走到力竭時的自我懷疑,和那些生死攸關的時刻。那些隱藏在她內心深處的故事和細節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她身旁的山友口中略知一二。比如八千米上失聯的隊友,遲滯20多個小時的救援,和得知「人還活著」後一瞬間的釋懷相擁痛哭。

▲攝影/何靜
雲南省登山協會會長龍江,2017年見證了何靜的第一座無氧攀登——馬納斯魯峰 (海拔8163公尺) 的攀登,其後的兩年他們又一起攀登了馬卡魯峰 (海拔8463公尺) 和安納普爾納峰 (海拔8091公尺) ,談到何靜在下山後的沈默,他表示自己也是這樣,下了山不願意再聊山上的細節。
所謂驚心動魄的故事,無非是生與死的故事,裏面多少有些傷痛。「原來我們一起17個登八千米的朋友,包括在國外登山的,後來不在了的就9個了。」龍江說。
在何靜看來,能與之講出這些故事的,只有一起登山的那些人,「而且還一定得是你的隊友,你跟他講這些,他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麽。我們現在不在同一個環境,所以沒辦法產生共振。」

▲攝影/何靜
她也不想評價他人,無論是在正式訪談還是在閑聊中,她生怕自己的一句評價惹來非議,當話題指向她之外的其他人,她就會機敏地感知到什麽訊號,馬上嚴肅地對你說:「我們不是說好不評價別人嗎。」
她不混圈子,以前手機裏半年沒聯系的人就刪了,偶爾向她提起一位圈內的資深玩家,她會不好意思地低聲問你:「他是誰?你知道我不太認識圈內的人。」
但她也有在攀登領域悄悄欣賞的人,那是兩位阿式、無氧攀登十四座的女性,一位是Nives Meroi (梅洛伊) ,當年在十四座女性登頂的最後階段主動結束競爭,其後很多年才復出;一位是Gerlinde Kaltenbrunner (格琳德·卡爾滕布魯納) ,也是在十四座中完全沒有去爭第一的心態,只專註於登山,而且爬的幾乎都是非常規路線。在何靜自己看來,她與她們之間最大的差距在於——「我是一個愛好者,而且僅僅是一個跟隨者。」

格琳德·卡爾滕布魯納(Gerlinde Kaltenbrunner)被稱為當今最強女登山家 圖片來源gerlinde-kaltenbrunner.at
她很欣賞Gerlinde在攀登與生活之間的平衡。Gerlinde此前並不是一個職業攀登者,而是一個護士,她在自己的愛好中有了一番建樹,完成了這些之後,仍然回歸到自己的平靜的生活中。何靜也不是一個職業攀登者,在攀登之外,她有著一份穩定的事業,做著科研類的工作。
從某種程度來講,登山只是何靜的一個愛好,就像有人喜歡足球,有人喜歡下棋,都能讓人有成就感,只不過何靜的成就感是在山上。
「你總得選擇一個地方,要突破自己,要不然生活真的就像溫水煮青蛙,你就只能是上班、下班、結婚、生子,就會過這樣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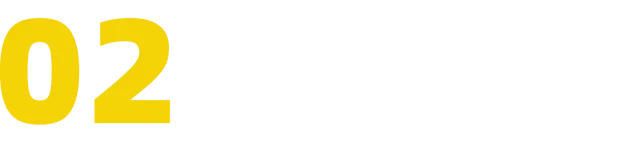
走向高山
走進何靜的家中,除了墻上掛著的幾張她親自拍下的雪山照片,和臥室陽台上散開堆放的一些裝備外,並看不出來太多攀登者的痕跡。
但痕跡又無所不在。她的自律性很強,即便是聊天進行到深夜,她次日清晨仍會準點起床跑個10公裏。她的背包裏最近常揣著一本打印版的國外登山書籍,家裏的沙發上,或出行酒店的床頭邊,她都會拿出翻一翻。
十多年她一直堅持長跑,尤其是開始八千米攀登後,她一周五天早上都會跑個10公裏,騎單車往返40公裏上下班,除了負重訓練外,還有定期的越野跑和一周三次爬樓梯。

▲2017年何靜在中國三峽超級越野賽。供圖/何靜
入坑八千米攀登以前,何靜也曾是一個喜歡買包,踩著細跟高跟鞋的精致愛美女生,現在她好久沒去商場了,不愛打扮自己,衣櫃裏有很少、風格很單一的衣服,就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周,她才剛被閨蜜拉著去買件新衣服。「現在越來越休閑了,不是說不在乎,女孩子都愛美,但是你得有取舍,花錢花在刀刃上。」
這個「刀刃」,就是登雪山。
何靜與山的相遇在2006年,有一天她在大學老師的家裏翻看老師在戶外登山時的照片,一看便著迷了。從短距離徒步到長距離徒步,從低海拔山峰到高海拔山峰,在因為無氧攀登而被更多人認識前,何靜的戶外生涯已走過了17年。
2011年,何靜的姥姥突然病逝,至親離世讓她一時無法接受,那一年春節,何靜不想在彌漫著悲傷氛圍的家裏過年,便和母親提出去外面轉一轉。母親很理解,於是何靜和朋友們相約去了四姑娘山二峰。
第一次登雪山,一切都特別不專業,何靜還記得那時自己就是穿著一件長款羽絨服,沖鋒衣也是臨時買的。但表現不錯,何靜算是很輕松地登頂了人生第一座雪山,當時有同行者看她狀態這麽好,還開玩笑對她說:「你很有登珠峰的潛質啊。」

▲攝影/何靜
那時何靜對珠峰的認知,都只是來源於學生時代在課本上的了解。在遇見人生更高大的山峰前,她站在五千多米的四姑娘山二峰,已經感受到了:在大自然面前人原來是那麽渺小,生死好像也都不是什麽重要的事兒了。
從四姑娘山起步,5000+、6000+,邁過慕士塔格這座7000+的門檻,清冽的山風變得冷峻,空氣越來越稀薄,感受越來越痛苦,直到有一天她站在八千米的門檻前問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嘗試了?
2016年,她的第一座八千米從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開始。當時標配是兩瓶氧氣,但何靜在整個攀登中只用了1瓶,她爬的很快,沖到頂峰時黎明的天空還被黑暗籠罩著,甚至看不見對面巍峨高大的珠峰。

▲2016年,卓奧友峰攀登。供圖/何靜
大部份國內商業攀登者,在攀登了一座八千米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珠峰,何靜的隊友們也是這樣。但當時的何靜覺得35萬的珠峰報名費,太貴了,不劃算,所以沒有一起去。
然而,當隊友們在5月末從珠峰回來時,何靜對自己感到了一種失落,她看到隊友們身上好像帶著光環一樣,覺得是英雄歸來了。那顆沈寂的心又開始躁動起來,「我就想我不登珠峰的話,能不能嘗試一下其他的8000公尺山峰?」

▲2017年無氧攀登瑪納斯魯峰時所攝。供圖/何靜

▲2017年,何靜無氧登頂馬納斯魯峰。供圖/何靜
機緣巧合之下,恰好十四座俱樂部的創始人張偉來到西安做馬納斯魯峰攀登推介會,從高度和難度上來看,馬納斯魯峰與卓奧友峰大致相當,因為此前在卓奧友峰攀登時只用了一瓶氧氣,何靜於是萌生了嘗試無氧攀登馬納斯魯峰的想法。
做出這樣的決定,一方面是因為非常現實的理由——省錢,在尼泊爾一瓶氧氣需要花費將近8000元人民幣,如果自己能不用氧氣,省下的錢正好可以支付精靈的小費。
而另一方面,對何靜來說,這也是一種自我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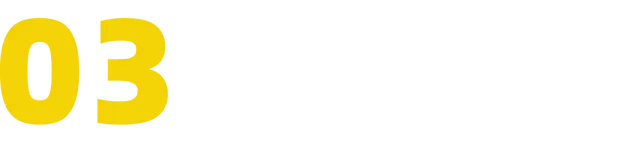
無氧
在數百人的登頂隊伍裏想要找到何靜並不難,因為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帶著氧氣面罩的登山者,除了何靜。
沒有氧氣面罩的隔離,八千米的冷空氣在呼吸之間直接進入肺部,龍江把這種感覺描述為一種痛覺,2013年他在登頂珠峰的時候,在山頂上因為要拍照就把氧氣面罩摘掉一會, 「8000公尺極寒的風灌到你的肺部裏面的時候,那種激烈的疼痛,會讓人產生一種痙攣!」 短暫的疼痛感讓他記憶猶新,所以談到像何靜這樣的無氧攀登者時,他說自己總是心生敬仰。

▲2022年,無氧攀登珠峰。供圖/何靜
沒有真實體驗過的人或許無法想象那種感覺。你可以試著帶上厚厚的口罩,身背幾十斤重的背包,爬到30樓下來,再反復多次,體會下沒有寒風的「無氧」感。據說中國首位無氧登頂珠峰的男子穆薩,就是這樣在日常訓練中模擬無氧條件下的雪山攀登。
1978 年,「登山皇帝」梅斯納爾 (Reinhold Messner) 和夏爾巴精靈Peter Habeler完成了首次無氧攀登珠峰,直到在他們登頂之前,許多科學和醫學專業人士都認為不帶瓶裝氧氣攀登珠峰是自殺行為。梅斯納爾後來也寫道,在他絕望地爬向頂峰的過程中,他感覺是「一個狹窄的、喘息的肺,漂浮在薄霧和山峰上」。

▲2022年,無氧攀登珠峰。供圖/何靜
采訪拍攝時,陽光打在何靜的臉上,讓她雙頰的高原紅更加明顯了,這是長時間在高海拔登山留下的銘印,除了高原紅,還有在交流過程中她常自我調侃的「斷片兒」的大腦,「人大腦有上百億個細胞,其實大多數的細胞一直都在那閑放著,偶爾燒死幾個,我覺得還好。」
這是下山後的玩笑話,在山上這可就不單單是損傷幾個細胞的事兒了。
在八千米之上使用氧氣,可以增強攀登者身體的力量和耐力,但更重要的是,氧氣可以增強大腦的認知能力。缺氧的大腦會做出錯誤的決定,而珠峰上的錯誤決定就意味著死亡。這就是夏爾巴人也使用氧氣瓶的原因:他們服務客戶的工作需要頭腦清醒。
▲2019年4月25日,何靜成功無氧登頂世界第十高峰——安納普爾納峰(8091公尺)。供圖/何靜
龍江說曾經在安娜普爾納峰 (海拔8091公尺) 上,他們的一位隊友在體力衰竭後產生幻覺,他在冰崖下方對自己的夏爾巴說:「你把我推下去吧,我就留在山上了。」也是在這一年的安娜普爾納峰上,何靜在無氧攀登將近17個小時後幾近崩潰,她拉著龍江的手哭著說: 「龍哥,我為什麽要來登山!」 下山後的何靜並不記得自己短暫崩潰的場景了。
龍江曾專門為何靜寫過一篇文章,文章裏有這樣一句話: 感受痛苦,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是他們從事運動魅力的一部份,也是宿命的一部份。
一旦決定了無氧攀登,就意味著攀登全程不能攜帶氧氣,如果在中途任何一個環節吸了氧,就被視為攀登無效。除了這些約定成俗的規則外,還有無氧攀登對於天氣近乎嚴苛的要求,何靜說自己攀登時,風速不能超過每秒20公尺,溫度不能低於零下40度,溫度太低會有凍傷的風險,風速太高會快速帶走身上的熱量,而無氧本身就會導致血液迴圈特別緩慢。
▲2023年7月21日淩晨沖頂迦舒布魯姆1峰,途中等待修路隊的過程,何靜不知不覺進入嗜睡狀態。供圖/何靜
「一個人決定攀登八千米雪山,實際上是不理智的,但是去了以後,就要很理性地對待每一次攀登。」何靜在山上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在珠峰南坡,有氧攀登的攀登者只有行至海拔7000公尺以下的1-2次拉練,而對於何靜,有時候一呆就是一個禮拜,有時候隊友會拿著對講機「罵」她:「在上面都快沒吃的了,還不下來!」
在2022年進行珠峰無氧攀登適應時,何靜上上下下了四次,最高抵達海拔7900公尺的四號營地宿營一晚,這幾乎是其他攀登者在適應階段不會觸及的高度。在采訪中何靜也提到, 她並非靠天賦而無氧攀登,科學且嚴格的高海拔適應拉練,才是她能夠成功無氧的密碼 。
▲透過冰裂縫。供圖/何靜
沒人告訴她應該怎麽做,她只是透過實踐自己去驗證。有時候這種嚴格也會冒失大意。
2018年攀登馬卡魯峰,何靜在海拔適應拉練時準備了5天4夜的幹糧上山,但遇到了暴風雪,她和精靈在上面扛了8天7夜沒能下撤。
「好幾次,明知馬上襲來的暴雪會要了我的命,可我實在沒力氣挪動一步了,都是出於求生的本能,不斷掙紮躲閃著。」何靜在采訪時曾說。體力透支,外加風雪肆虐,她甚至悲觀地想到自己可能就要永遠的留在山上了。這次經歷讓她清晰認識到了海拔適應的科學性。
選擇無氧攀登對何靜而言,就像走一條少有人走的路,註定是一場艱難而孤獨的征程。
一個人的征途
2022年5月14日,何靜無氧登頂珠峰,在她登頂的時段,頂峰一絲風也沒有,她沒有特別的興奮,摘下厚厚的手套,展旗,拍照,又趕快帶上手套。
一套動作後,何靜在頂峰停留了將近半個小時,始終在環看著四周——
在她身體的左邊,是尼泊爾,身體的右邊,就是祖國的境內。此時,她還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回國,從2021年4月抵達尼泊爾,一直到2022年5月14日登頂珠峰,她因為疫情而滯留尼泊爾超過1年了。
▲供圖/何靜
2021年3月,她留給單位一堆保證承諾書,一個人奔赴尼泊爾。這場攀登之旅大費周折,當時出國政策剛剛開放,她打了兩針疫苗,又費很大力氣做好父母的思想功課——在珠峰之前,她從來沒有跟父母坦白過自己的八千米攀登,這次瞞不住了……
「珠峰就是你最後一座了!」
「好。」
原本,這可能真是最後一座,但夢想止步在海拔8400公尺。2021年的珠峰天氣狀況並不好,印度洋上飄來的一陣氣流,帶來了不穩定的天氣條件,「我進入大本營太晚了,5月12日才完成珠峰適應。」5月12日後,一直到6月1號前,何靜再沒等來特別好的視窗期。
因為對天氣的苛刻要求,那一年沒有任何人成功無氧登頂珠峰。更糟糕的是,此時疫情肆虐,航班異常,直到八月份才有一些隊友從第三國輾轉回國。但誇張到10萬一張的機票,讓何靜望而生畏。她想著,登珠峰這件事沒有完成,或許回國後再出來就是天方夜譚了,不如就繼續在尼泊爾堅守。
在枯燥的等待與訓練間,七峰公司春秋季的道拉吉裏峰攀登計劃給何靜帶來了一絲光亮,但到了報名時她卻很糾結,擺在眼前的是實實在在的費用,登頂珠峰失敗了,已經花了將近50萬元,如果這一次再失敗的話,壓力可想而知。
猶豫之時,精靈的一句話讓她堅定了想法,「沒有人能夠告訴你到底應該怎麽做,這件事情的決定權在你手裏,如果你不嘗試的話,你永遠都不知道結果。」
老天眷顧,2021年10月1日,何靜無氧登頂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裏峰。登頂那一天正是國慶,何靜在海拔8167公尺的頂峰,動情地唱了一首【歌唱祖國】,此時她已經6個月沒有回家了。
▲2021年,何靜無氧登頂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裏峰。供圖/何靜
從道拉吉裏峰下來,迎來的依舊是國內沒有正常通航的訊息。何靜的心情從希望轉為失望,失望再到絕望。一位國外的隊友在得知何靜沒辦法回國後,向何靜發出邀請:「我們去徒步吧,看看地震之後對當地人們到底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
10天的徒步,讓這段滯留尼泊爾的經歷,多了一道不同的色彩,而10天後隊友回國,何靜心裏冒出一個更為瘋狂的想法,她買了一張地圖,只帶著這張地圖,獨自一個人再次上路,在不到40天裏,徒步尼泊爾960公裏。
從加德滿都搭乘公共交通到吉裏,然後從吉裏出發長途跋涉5天,這條旅途被稱為「先鋒之路」,因為在20世紀60年代機場建成之前,喜馬拉雅山脈的攀登先鋒們,就是這樣到達盧卡拉,再前往珠峰大本營的。如今,這些步道上幾乎再沒有遊客或攀登者,也不容易找到背夫,大多數攀登者都會選擇乘飛機從加德滿都直接抵達盧卡拉。
▲從加德滿都經過吉裏前往盧卡拉和EBC。
在這40天的徒步中,何靜也走上了這條道路,孤身一人行走的她,遙想七十年前艾德蒙·希拉蕊和夏爾巴丹增·諾爾蓋,就是這樣跋涉在這條通向珠峰腳下的路上,敬畏之情就會油然而生。在「先鋒之路」上的行走,讓何靜發自內心地懂得了:攀登珠峰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滯留在異國他鄉,除了行走,無處可去,漫漫無盡頭的九百六十公裏路途上,何靜心裏想的最多的,便是遠方的珠峰——2021年這場攀登沒有登頂,登山費用並不會退,明年還要繼續嗎?此時她其實已經動搖了。
▲供圖/何靜
直到11月29日那一天,這場徒步之旅帶著她慢慢走向了珠峰南坡大本營,冬季的珠峰大本營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國外攀登者,正在嘗試冬季攀登珠峰。何靜一個人走在正午熾烈的太陽光下,有那麽一刻她擡眼望去,珠峰寬厚巍峨的身軀,驀然挺立在她的面前,像一個金色的巨人,對她發出溫柔的邀請。
如今再回憶起那個畫面時,何靜的眼裏依然透露著閃閃光芒。那一刻何靜下定決心,2022年繼續無氧攀登珠峰。
「如果這件事沒做成的話,你回去就是個失敗者。」
突破
何靜面對采訪時是抗拒的,她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太多人知道。
她一直對我們說,自己的故事真的沒有什麽意思,不值得提。在低調的另一面,我們發現她其實非常顧忌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她不是沒有受到過這種言語的中傷,曾經一個很親密的朋友在談論她所做的事情時說——「她可能是為了名或為了利,才做這件事。」「這件事」指的就是無氧攀登,以及一次次在八千米上創造的記錄。何靜為此受傷了很久。
今年年初,「戶外探險」電話聯系何靜,問她是否願意接受中國戶外金犀牛獎年度突破獎項提名,何靜幾番拒絕。即便是在完成了 74天無氧連攀四座八千米高峰 後,她仍在仔細掂量著自己的成績能不能當得起「突破」二字。下山後,那些瘋狂懷抱著的野心,好像並沒有那麽強烈了。
▲攝影/何靜
2021年無氧珠峰失敗後,2022再次嘗試時,何靜的心理壓力極大,她想如果再不成功,那麽不僅不會再無氧了,八千米山可能也就就此不登了。
為了避免像2021年一樣錯過視窗期,何靜在從加德滿都徒步抵達大本營後,當即第二天就去了二號營地進行海拔適應。對於普通攀登隊員,珠峰攀登只需要進行1-2次高海拔適應力拉練,最高不會超過海拔7000公尺,但無氧攀登的何靜四次過危險的昆布冰川,把從C1到C4的營地都住了一遍。
「你已經適應到了3號營地,已經可以了,不一定要住到4號營地,這個風險太高了!」國外的隊友對她說。
「因為是無氧,如果我不在4號營地住那一晚上,我覺得心裏沒譜。」何靜這樣想。
▲供圖/何靜
但真的無氧住在海拔7900公尺的4號營地時,何靜身體的每個細胞都在抗拒,「難受到想死的心都有。」她說。狂風加暴雪的夜晚,她和精靈擠在一頂帳篷裏,帳篷裏面也都是雪,根本沒有辦法入睡,她無比羨慕地看著在一邊吸著氧氣的精靈,「沒有辦法,這是自己的選擇。你因為這件事堅守了這麽久,所以就只能扛!」
沖頂的路從下午6:00一直走到次日早上9:00,在海拔8500以上,她走的特別的慢,腳步沈重,一步一呼吸,身體幾近極限的邊緣,完全是靠意念支撐到頂峰。
2022年5月14日,何靜成功無氧登頂珠峰,這是首位中國女性無氧抵達世界之巔。耗時兩年的攀登終於成功,但她沒有在第一時間把這個好訊息告訴任何人。「就是感覺這件事做完了,沒有那麽激動,只是對我自己的一個交代而已。」
▲2022年5月14日,何靜成功無氧登頂珠峰。供圖/何靜
不告訴外界,是因為她不喜歡由喜劇轉悲劇的故事,此時她的心還在懸著,另一個更大的計劃在心中盤算——無氧完成珠峰與洛子峰的攀登。這兩座山峰毗鄰並透過南坳連線在一起,從大本營到三號營地,珠峰與洛子峰的共用一條登山路線,之後分開而去,到達不同的頂峰。剛從珠峰下來的何靜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她沒有告知外人,怕別人覺得她不自量力。
5月15日剛剛下撤到珠峰大本營,16日的早上,七峰探險公司的老板過來找何靜說,如果想抓住當下的視窗期,她當晚就必須要出發。此時何靜在大本營才休整了16個小時。
何靜第一時間覺得,這簡直是跟她開玩笑。她當然可以考慮再等後面的視窗期,但2021年珠峰失敗的陰影又飄到她大腦中,她決定當即出發。
2022年5月20日,何靜成功無氧登頂海拔8516公尺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創造了一個登山季同時無氧登頂珠穆朗瑪峰和洛子峰的世界紀錄。下山後的她才了解到,曾經也有國外的攀登者想嘗試珠峰與洛子峰的無氧雙登,但都以失敗告終。
▲2022年5月20日,何靜成功無氧登頂海拔8516公尺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供圖/何靜
珠峰與洛子峰的無氧連登後,何靜又在一番焦急的等待後,於6月26日拿到K2的攀登授權,她當晚就飛到巴基史坦,成為整支隊伍中最後一個報到的隊員。7月22日,何靜完成了世界第二高峰喬戈裏峰 (8611公尺) 的無氧登頂,並再一次於幾天之後的7月27日,無氧登頂布洛阿特峰 (8051公尺) 。總計,何靜在2022年耗時74天就一舉完成了四座8000+海拔的高峰的無氧登頂。
進入2023年截止目前,何靜再次用4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幹城章嘉 (8586公尺) 、南迦帕爾巴特 (8125公尺) 、迦舒布魯姆1 (8080公尺) 、迦舒布魯姆2 (8035公尺) 和卓奧友 (8201公尺) 五座八千米山峰的無氧攀登。
此時有個問題你也許好奇想問她:每年4-5座,這是你提前悉心規劃好的嗎?
她說: 「完全沒有任何的規劃,只是覺得出國一趟特別不容易,能多爬一座就多爬一座,這樣可以節省費用。」
▲2022年7月22日,何靜無氧登頂世界第二高峰喬戈裏峰(8611公尺)。供圖/何靜
除了個人的突破外,何靜沒有為自己的攀登成就賦予額外的意義,或者做出什麽更為宏大的表達,在她看來,在山中真正的突破應該是具有探險色彩的攀登。而自己能否去做這些,也要隨緣,時機到了自然就會去做。
到目前為止,何靜已經完成了13座八千米山峰的無氧攀登,距離十四座只剩一座希夏邦馬峰。目前在世界上,即將完成無氧攀登十四座的另兩位女性,就是她十分欣賞的兩位女性攀登者Gerlinde與Meroi,她們還差一座山峰——重登馬納斯魯峰的真頂。
十四座首登之爭,無論是有氧或無氧,十余年來從未從八千米攀登的名利場上真正退場,有人野心勃勃,有人覺得無趣主動結束競爭。何靜對這個話題似乎並不感興趣,她無意去爭誰最先做到,她坦誠地說,這兩位女性做到的遠比她難 (Gerlinde與Meroi不跟隨精靈,完全自主攀登,且在出現「真假頂」一說前,已經無氧登頂全部14座) 。「就算自己先於她們完成了,在我心中真正做到的也是她們,因為從攀登形式上,自己永遠做不到那樣。」
2013年登頂珠峰的龍江,對八千米山峰上名與利的追求司空見慣,但他在何靜身上看不到這一點,「她自己不願意去宣揚,甚至很多時候,都是我們這些熟識的山友在微信上來發一發她的東西。」
攀登17年來,作為一次次在八千米上打破記錄的女性,何靜仿佛是在刻意躲避聚光燈,曾經有媒體冒然前往何靜父母家中采訪,二老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熱情接待了記者,何靜為此大為生氣。她不想讓這些虛無的東西打擾到家人和自己平靜的生活。
攀登的年頭越來越長後,她再回頭去看那些質疑之聲,也能夠平靜的對待。時間不一定會讓他人放下偏見,但攀登教會了她學會放下——
「不要躺在過去的成績裏沾沾自喜。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它就已經結束了,我們得向前看。」
生死:學會堅持,懂得放棄
當我們試圖追問攀登者關於「生死」的問題時,實際在心裏已經有了答案。對於生和死,她可能早就想過了,想通了,才會去做。
何靜不忌諱談論生死,「我們生來對於死亡都有恐懼感,在嘗試8000公尺攀登的過程中,我們知道自己會跟死亡接近,但是也清醒的知道,它不會拿住我們,只要我們不突破那個界限。」
▲供圖/何靜
2019年,何靜跟隨由南韓登山者洪成澤率領的登山隊前往洛子峰南壁。洛子峰南壁被稱為是世界上最艱難、垂直的山壁之一,從南壁攀登海拔8516公尺的洛子峰十分具有挑戰性。
一分錢不用花、有頂級的攀登者帶路、國家地理雜誌全程跟蹤拍攝,這場攀登對於何靜誘惑極大。可是去了之後,她才意識到這有多恐怖,即便是現在已經登頂了13座8000公尺雪山,在她的評估系統裏,洛子峰南壁也是非常難的。
這也是何靜第一次單獨跟隨國外的隊友們一起登山,在一次沖頂失敗下撤中,因為操作失誤,何靜的下降器掉落山下,沒有下降器意味著下降的巨大難度和風險,何靜心中希望可以有隊友陪著自己下降以確保安全,但她沒想到的是,第二天早晨起來「一個個跑的比兔子都快,就剩我一個人站在二號營地……」
▲洛子峰南壁。攝影/何靜
在平撫了一時的驚慌後,何靜暗自想:與其等死,不如自己下撤。平時學習的技能派上了用場,她用半扣繩結做保護,在長達3個小時的下降中全神貫註,她心裏只剩下一個信念——「一定要活著回去!」
洛子峰南壁是一場極其艱難的攀登,前兩次接連失敗,準備第三次再次嘗試時,只剩洪成澤和何靜兩個人,國內的朋友發訊息試圖勸退何靜,告訴她已經沒有天氣視窗了,何靜再三確認天氣後,最終選擇了放棄。
然而有一個畫面這些年來一直印刻在何靜腦海中——那是在洛子峰大本營,第三次沖鋒,洪成澤一個人孤獨前往一號營地的身影。
「他還在堅持,那一刻我看到他一個人孤獨的身影在前往一號營地,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在為了他的夢想在堅持。孤獨,但是又讓人特別佩服,是夢想的力量還是什麽,在驅使著他再一次出發……」
▲供圖/何靜
她仰慕那些為理想而堅持的人,但登山於何靜而言終其只是一個愛好,她不會為了它拼出性命。在她認識的攀登者中,也有人因為無氧攀登而凍傷,或者永遠的離開了。但在每一次攀登中,何靜是不允許自己有任何一點點的凍傷的,在行進的途中或在頂峰,她總不會忘記搓搓手或者做些其他保暖措施。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一定得保證我能毫發無傷,活著回來。」
家人
有一天何靜突然發現,父母家裏的電視總在放著西藏電視台。
這是個從小到大家裏都很少看的電視台,何靜就問母親:「怎麽突然看這個?「 母親對她說,這樣就可以看到你那邊的天氣情況了。
她發現一向不理解她登山的母親,開始以這樣獨特的方式關心她,開始有意無意了解她在做的這件事,到底是什麽。
▲2023年7月21日拍攝於迦舒布魯姆1峰。供圖/何靜
2022年何靜在尼泊爾攀登珠峰時,父母只知道她前一年攀登失敗並因為疫情滯留那裏,卻並不知道她又開始了第二次嘗試。何靜沒有透露,而是向他們撒了一個謊,說是陪朋友去山裏拍高山杜鵑。
「我在每次適應力拉練後,會在距離珠峰大本營四五公裏的一個地方,用一點點訊號給他們發個資訊,說我最近挺好的。」
5月12日從二號營地出發時,她給父母錄了一段視訊,說:「親愛的爸爸媽媽,請原諒我用這種方式跟你們說一段我心裏的話,守候一年,今天我就要從二號營地出發向珠峰發起最後沖擊,放心我會平安回來……」
在每次攀登之前,何靜都會留下一封遺書,這封信改了又改,已經寫了20多封。她知道每一次的攀登都是有風險的,遇到風險後父母怎麽辦?「你總得做好交代,不能自己走了之後留下一筆糊塗賬。」在信中她會寫下銀行卡的存款、密碼、父母要怎樣安頓,自己的遺物應該怎麽處理掉……
▲何靜在世界之巔表達對父母的愛。供圖/何靜
以前何靜在家裏很少聊登山的話題,有一次在新聞上,父母看到一個有氧攀登凍傷的人,就馬上打電話問何靜:「人家有氧都凍傷了,你沒事吧?」 何靜漸漸就不再對父母隱瞞了,每次出發前都會明確地告訴他們——我要去登哪一座山、它在哪裏、山有多高,以及是什麽難度。
「我覺得只有讓他們知悉了之後,我每次又能夠毫發無傷的回來,他們才會更加的信任我。」
采訪中我們問到何靜,過去一年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麽?
並不是任何一座山峰,而是 2022年8月,何靜終於在滯留尼泊爾一年半後,回到祖國,回到家中。經歷了那麽多後,再見到父母後,並沒有想象中的痛哭流涕。
媽媽對她講了這樣一句話: 我覺得一個人一輩子要能做成一件事情,也挺值得驕傲的,我發現你是做到了,所以我還蠻欣慰的。
▲2023年7月16日拍攝於迦舒布魯姆2峰。供圖/何靜
暗流
無氧登頂了十三座八千米,登頂那一刻的感覺是什麽?下山後這些記憶意味著什麽呢?
「其實好像是一股暗流。你也並不知道波濤它什麽時候會出來,但它是存在的,有時候會突然之間就蹦出來。」何靜說。
只要那些留在記憶深處的快樂和滿足,甚至是有些潮濕的感受還在,生命裏綿延的思緒波濤,就不會停止。
下山之後別再追問一位攀登者,在山上發生了什麽,就像蘇格拉底說的:改變的秘密,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建造新的東西,而非與過去抗衡。
撰文 | 了了 編輯 | 徐丹 各拉丹東 供圖 | 何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