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建新本文由陳建新撰寫。陳建新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思考,為我們呈現了一篇精彩紛呈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她透過細膩的筆觸和生動的描繪,將主題展現得淋漓盡致。透過這篇文章,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陳建新的文學才華,更能從中汲取到深刻的思考和啟示。陳建新的文章,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和深思。

在告別宴上,周恩來贈送給美方轉譯書籍,以此表達中方的友好意願。或者可以說:在告別儀式上,周恩來向美方轉譯贈送了書籍,以彰顯中方對美方的友好情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總統踏上中國的土地,標誌著「世界轉折的一周」的開始。僅僅一周後,即2月28日,【上海公報】正式釋出,向世界宣告了中美兩國關系的和解與正常化行程。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無疑是20世紀政治舞台上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尼克森訪華期間,美方選派了理察·弗裏曼(後更名為傅立民,並曾擔任駐華公使)作為首席轉譯,而中國方面則指派了冀朝鑄為尼克森的轉譯,同時章含之負責為尼克森夫人轉譯。經過雙方協商,會談時主要使用中方的轉譯,而美方轉譯則坐在尼克森身後作為旁聽者。據章含之回憶,某日尼克森總統向周恩來總理暗示,希望與夫人交換轉譯,他認為盡管冀朝鑄工作表現出色,但因其身高與自己相近,不如女性轉譯更有助於塑造總統的「公眾形象」。因此,章含之與冀朝鑄經過認真商定,決定在北京的宴會轉譯仍由冀朝鑄擔任,而一旦離開北京,則改由章含之負責。所以,在杭州和上海等地的後續宴會中,大家看到的轉譯便換成了章含之。
章含之曾回憶道,在一次談判中,尼克森說了句話,譯成中文大概是:「我們美國和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利益是並列的。」當時中國的轉譯就直接轉述為:「兩國間的利益是平行的。」這句話的字面意義在正常情況下並沒問題。但尼克森身邊的轉譯弗裏曼突然插話:「總理閣下,能否允許我稍作點評?」周恩來總理有些疑惑,但還是答應了。弗裏曼說:「我認為貴方的轉譯並不十分準確。」周恩來總理精通英文,便詢問:「哪裏不準確?」弗裏曼解釋道:「將總統的話譯為‘兩國利益是平行的’,在中文中,‘平行’意味著永遠不相交,就像雙杠一樣,永遠不會碰在一起。總統的意思是,盡管兩國目標不同,方向各異,但最終會有共同點,因此‘平行’這個詞並不貼切。」周恩來總理饒有興趣地問:「那你認為應該怎麽轉譯?」弗裏曼回答:「如果我來轉譯,我會說總統的意思是兩國利益殊途同歸,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最終會匯聚到一起。」

在尼克森訪華期間,弗裏曼(傅立民)陪伴他參觀了明十三陵,並在此地留下了珍貴的合影。
關於當時的中方轉譯者的身份,章含之並未明確透露,僅提及「非我所為,另有他人擔綱此任」。她補充道:「我在場時也未想到更佳的措辭。」實際上,不論是誰,在場的中國轉譯都未能找到比「殊途同歸」更貼切的詞匯。此事對周恩來總理及在場的中國轉譯人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章含之對此感慨道:「‘平行’這一詞匯通俗易懂,初中生學習英文亦能輕易掌握。然而,要精確轉譯出‘殊途同歸’,則需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否則可能難以表達其真正含義。此事在當時對中國轉譯界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因為我們一直對自己的轉譯能力充滿自信,卻不料被一位美國轉譯所超越,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兩天後,我們抵達了上海,並在2月27日的晚宴上進行了告別。當時,【上海公報】已經順利簽署,大家都沈浸在喜悅之中,整個晚宴的氣氛異常熱烈。在這次晚宴中,周恩來總理註意到了弗裏曼出色的中文能力,並對他表示了贊揚。他好奇地詢問弗裏曼是在哪裏學的中文,弗裏曼回答說是在台灣。周總理聽後深感感慨。隨後,周總理指著身旁的章含之對弗裏曼說:「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他在82歲時完成了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現在讓她送你一套。」章含之回憶道,周總理還補充了一句富有深意的話:「我想她看不懂她父親的東西,你看得懂。」這讓章含之有些措手不及,感覺像是被周總理突然擊中了。據說,弗裏曼對周總理提到的【柳文指要】非常感興趣,晚宴結束時還特地提醒章含之,希望在明天登機返回美國之前能夠拿到這本書。

在總理的明確指示下,章含之在2月27日晚宴結束後,緊急向上海外辦主任馮國柱求助。起初,他們在整個上海都無法找到一本【柳文指要】。鑒於弗裏曼將在翌日上午隨尼克森返回美國,時間變得異常緊迫,所有人都感到焦慮不安。然而,幸運的是,他們最終從參與接待工作的朱永嘉那裏獲得了一本。據朱永嘉透露,「在上海,只有我手頭有一本【柳文指要】,這本書是張春橋特意轉交給我的。」朱永嘉當時在上海市委寫作組工作,而在2月27日和28日這兩天,他被臨時調來擔任上海方面的新聞發言人。那本【柳文指要】最終被弗裏曼帶回美國,並如今被珍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
對於周恩來送【柳文指要】給美方轉譯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解讀。以下是結合時代背景進行的客觀分析: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柳文指要】是明朝文學家柳宗元的選集,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學術價值。作為一位文化名人,周恩來很可能對柳宗元及其作品有著深厚的興趣和研究背景。因此,他選擇送一部【柳文指要】給美方轉譯,可能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向外界介紹和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展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文化交流是促進國家間相互了解和友誼的重要方式之一。透過互譯文學作品、書籍等,可以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增進彼此的理解和認同。因此,周恩來送【柳文指要】給美方轉譯,也可能是一種表達友好意願的方式,希望以文化為紐帶,拉近兩國人民之間的距離。最後,我們還需要註意到,贈送圖書本身也是一種禮儀和文化交流的形式。在中國文化中,送書被視為一種高尚的表達方式,寓意著知識傳遞和文化傳承。因此,周恩來送【柳文指要】給美方轉譯,也可能是希望透過這種具有文化內涵的方式來表達對中國的尊重和友好之情。綜上所述,周恩來送【柳文指要】給美方轉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推廣,又表達了對外國文化和人民的尊重和友好之情。同時,這也是一種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社會交往的良好方式。
贈送書籍背後所蘊含的深意在贈送書籍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多重用意。這一行為不僅代表著知識與智慧的傳遞,更體現了一種情感的交流和文化的傳承。透過贈送書籍,我們可以將自己的見解、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傳達給他人,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拓寬他們的視野。同時,這也是一種對知識尊重的表現,傳遞出對受贈者的期望和鼓勵。在更深層次上,贈送書籍還是一種社會交往的方式,透過書籍這一媒介,我們可以建立起與他人的聯系,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友誼。因此,贈送書籍背後所蘊含的深意是多方面的,既體現了對知識的尊重和傳播,也傳達了情感、文化和社交等多重意義。
出版【柳文指要】是毛澤東、周恩來為推動出版工作所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這一舉措不僅展示了他們對於出版工作的重視,也體現了他們對於中華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對於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透過出版這本書籍,他們希望能夠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同時,這也反映了他們對於柳宗元文學作品的贊賞和推崇,以及對於其思想價值的認同和傳播。因此,可以說,【柳文指要】的出版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工作。
章行嚴,本名章士釗,生於1881年,逝於1973年,他是湖南長沙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他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有著深厚的交往和聯系。1949年以後,他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務上擔任了重要角色。
【柳文指要】是一部深入研究唐代文學家柳宗元作品、生平胡思想的專著,由章士釗在75歲高齡時開始撰寫,歷時十年,最終完成了百萬字的巨著。盡管在當時面臨著康生的壓力,但這部古籍研究專著仍然得到了中華書局的出版,這本身就是一個難得的奇跡。事實上,只有依靠毛澤東的支持和周恩來的關心,這個奇跡才能夠最終實作。章士釗在這部著作中,不僅深入挖掘了柳宗元的文學成就和思想內涵,同時也展現了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歷史眼光。因此,【柳文指要】不僅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也是章士釗晚年學術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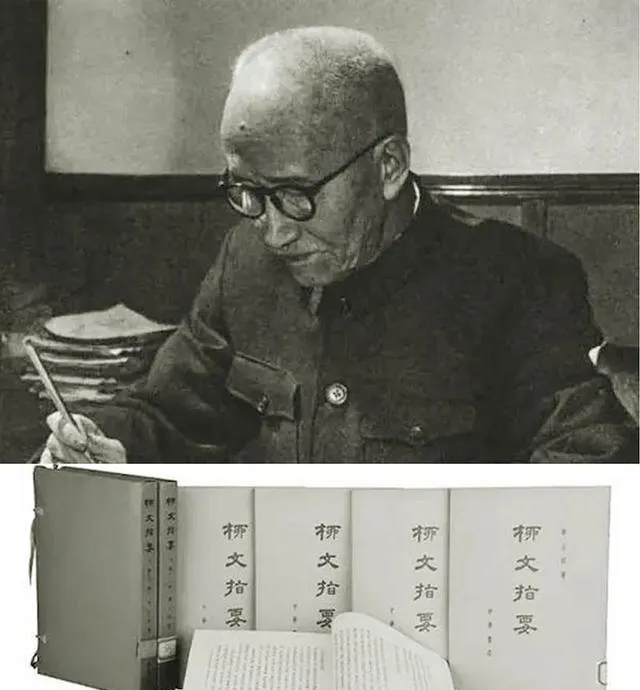
章士釗與【柳文指要】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為章士釗與這部著作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章士釗開始撰寫【柳文】之際,毛澤東得知此事後,主動向章士釗透露了自己對柳宗元作品的喜愛,並希望能在書稿完成後先行閱讀。1965年6月,章士釗將【柳文】的初稿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在閱讀【柳文】時,其細致入微的態度甚至體現在對秘書謄寫錯誤的指正上。他在回信中贊揚了章士釗的作品:「讀後感覺引人入勝,期待下部作品的完成和及時贈送。」待下部作品閱讀完畢後,毛澤東再次致信章士釗,表達了他對作品的喜愛之情:「……已經讀過一遍,仍想再讀。上部亦然。另有友人亦想一睹為快。關於作品的核心問題——唯物史觀,即階級鬥爭的探討,雖對此觀點不能強求於觀念已固的老一輩學者,因此無需修改。但日後歷史學家可能對此提出批評,希望你有所準備,不必懼怕他人的評價。」
經過康生的審閱,他發現這本書確實存在不足之處,尤其是對柳宗元這位歷史人物的階級分析不夠深入。因此,這本書的出版受到了阻礙。章含之在回憶中提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章士釗曾寫信給毛澤東,希望能夠得到他的指示,讓中華書局盡快排印【柳文指要】。經過這樣的努力,最終【柳文指要】得以順利出版。
在1971年的四月和六月,周恩來在與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的兩次會面中,都深入了解了【柳文】的出版進展。在首次會面時,他明確指出:「老年人撰寫關於古人的作品,可謂是晚年的一大傑作,只要印刷精良,便無可挑剔。」「如果這本書的出版效果還能令人滿意,那麽就能證明我們對舊文化並非一概否定。」而在第二次會面時,他又著重強調:「務必盡快完成印刷,章士釗目前身體抱恙,能在他生前看到這本書的出版,也將是他生涯中的一大貢獻。」
在10月7日,周恩來審閱了【柳文】並批註:「我同意,可以立即安排印刷出版。」經過周恩來的多次關心與推動,該書終於在10月底由中華書局成功出版。全書字數超過120萬,分為14冊,采用線裝三函的形式,共計印刷了3000部。據章含之回憶,新書問世時,章士釗激動得雙手顫抖,那年他已經步入90歲高齡。這份喜悅激發他仿照陸遊的詩意創作了一首七言長詩。章士釗甚至自費購買了百部該書,並請秘書購買了紅紙裁成小條,他親自題字後貼在每一部的扉頁上,贈送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的同仁和朋友。其中,章士釗贈給毛澤東的那本【柳文】,毛澤東經常翻閱,甚至在逝世時還留在臥室的書架上。而中華書局按照慣例送給他的那本【柳文】,他在1972年初轉贈給了自己的女兒李訥。
在那個時期,【柳文】的出版無疑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波瀾。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了推行政策、重新開機出版業務、再度實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所采取的一項關鍵行動。毛澤東親自參與了這一典型的示範計畫,意在激勵當時幾乎陷入困境的出版界,促使其煥發新的生機。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與出版口的領導團隊會面,對出版工作給予了重要指導。他特別指出,青少年缺乏讀物是一個問題,不能將所有舊小說都歸為「四舊」範疇。隨後的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期間,周恩來兩次與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會面,並強調出版部門應多印刷歷史書籍。他進一步表示,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將【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束之高閣是不合適的,這種做法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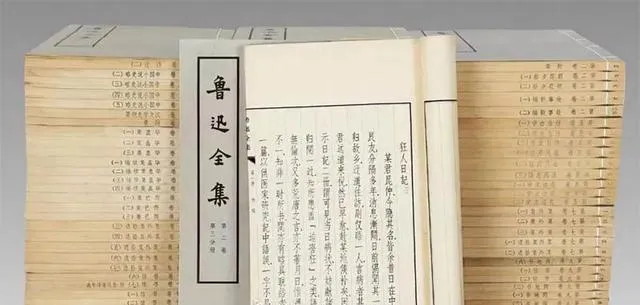
在尼克森訪華之前的1972年2月11日,周恩來與李先念召集了一次會議,參與人員包括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及國務院業務組的成員。會議中對一項特定政策進行了批評,該政策規定四部古典小說只能出售給中國國內讀者,而不允許售賣給外國人。這一政策在當時的「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制定,當時文化部已被撤銷,國務院文化組承擔了原文化部的職能。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指示將【柳文】作為禮物贈送給美方,其意圖顯而易見。此外,他還選擇了【魯迅全集】作為國禮送給了尼克森。這兩種文化經典的贈送,無疑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獨特魅力。透過這一舉動,周恩來不僅展示了中國文化的精髓,更傳遞了中國對外友好的積極資訊。
在尼克森訪華之後的1972年4月中旬,一個引人註目的事件發生了:【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四部古典名著以總計20萬部的數量被印刷並公開對外發行,這一舉措無疑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註和討論。
第二點,我們要積極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並激勵外交部轉譯人員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周恩來一直秉持著全面、辯證的態度。他主張在肯定中國古代文化豐富歷史記載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其中正史和野史、筆記等不同形式的存在。他認為漢文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提出了將自身所掌握的歷史遺產進行傳承的願景。然而,「文革」運動的興起導致中國傳統文化遭受了嚴重的沖擊和摧殘,這是周恩來所不願看到的。因此,在可能的條件下和範圍內,周恩來努力減少和糾正「文革」的錯誤,並盡可能保護受到沖擊的知識分子,章士釗也是其中之一。盡管如此,「文革」以來對傳統文化和教育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仍然存在且難以完全消除。
在中美雙方進行的轉譯交流中,中方轉譯在傳統文化知識方面的不足,對於周恩來總理和在場的轉譯人員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當看到這樣的狀況,「觸動」和「受刺激」這樣的詞匯可能都無法準確描述總理內心的復雜情感。作為一國之總理,面對這樣的局面,他心中的感受無疑是復雜的。
章含之在回憶中提到,當周恩來得知弗裏曼的中文是在中國台灣學習時,他的內心充滿了感慨。甚至在場的中方轉譯也感受到了他對台灣地區傳統文化的贊賞之情。然而,感慨之後,周恩來立刻向弗裏曼推薦了一本厚重的【柳文】。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在向美方轉譯傳達一個資訊: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和真正的傳承者都在大陸。因為【柳文】是章士釗用古文寫成的,這也展現了周恩來的睿智之處。

那麽,為什麽周恩來沒有親自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安排任務,而是選擇讓章含之尋找一本特定的書籍送給弗裏曼呢?其實,透過對他說給弗裏曼的那句話——「我想她看不懂她父親的東西,你看得懂。」——進行深入解讀,我們就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周恩來實際上是在激勵章含之等外交部轉譯人員更加努力地學習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外交事務無小事,「轉譯並不僅僅是傳聲工具」,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事務中分管了26年,他親自指導轉譯工作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
第三點,深深牽掛著祖國的統一大業。
眾所周知,章士釗這位傑出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在其一生中並未加入任何政黨。自1949年起,章士釗繼續以無黨派的身份參與社會活動,與毛澤東維持著開放而富有成效的溝通與交流,同時他們在互動中也保持著適當的界限。
章士釗因其在中國革命和民主建設中的政治地位,與各派政治勢力的良好關系,以及與毛澤東的私人友誼,使他成為兩岸三地溝通的關鍵人物。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使章士釗能夠遊走於北京和香港之間,與過去的故友保持正常交往。身為老派文人,他的出色古詩詞造詣使他經常與香港、台灣的友人進行詩文交流,這也為他在兩岸間的溝通工作帶來了便利。1949年後,章士釗在兩岸三地的溝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6年、1962年、1964年,他三次奉命赴香港,與台灣方面接觸,探討兩岸統一的問題。
【柳文】的出版無疑給章士釗帶來了深深的喜悅與寬慰。自1972年下半年起,他便多次向親近的人提及去香港為祖國統一事業貢獻余力的想法。談及這段往事,章含之回憶道:「我確實擔心父親的健康無法承受長途旅行的辛勞,然而毛主席似乎很支持父親的這一願望。最終,主席請總理考慮一個周全的計劃,即在保證父親健康的前提下,安排他去香港。事實上,這個決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意願來做的。當我將這一訊息告訴父親時,他非常高興,並表示毛主席理解了他的初衷。」
在1973年的5月,也就是尼克森訪華滿一周年之際,92歲高齡的章士釗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承載著毛澤東的深切期望與囑托,再度踏上香港的土地。然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這位深受人們敬重的愛國老人便在香港安詳離世,但他那份未竟的事業,卻永遠地留在了人們的心中,激勵著後來者繼續前行。
盡管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弗裏曼曾經閱讀過【柳文】,但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當年贈送此書給弗裏曼的舉動,確實在中美關系的開發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022年2月,正值尼克森訪華50周年之際,弗裏曼在華盛頓外交學院的一場線上演講中,強調美國對華政策不應陷入誤區,而應致力於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他明確指出,「美國才是中美沖突的始作俑者」。
本文系【黨史博采】獨家策劃,以原創筆觸呈現歷史風雲,旨在為讀者提供深入且獨特的黨史解讀。
任何未經授權的轉載都是被禁止的。
任何侵犯他人權益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權益捍衛者: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











